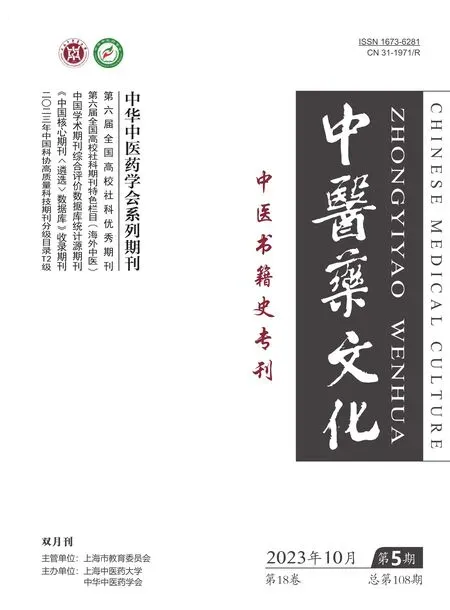清代士人的医书阅读活动探赜
刘希洋,庄 超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青岛 266100)
明清时期,医书不断增多,传播日益广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借阅医书、购买医书、抄录医书、施送医书、讨论医书及其相关问题的现象已司空见惯①参见刘希洋《清代医书的非商业性出版和传播探赜》(《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 年第2 期,第98-113 页)。。医书的广泛传播对医学的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都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②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梁其姿《明清中国的医学入门与普及化》(见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29-47 页)、冯玉荣《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明清之际的儒医与“医宗”》(《学术月刊》,2015 年第4 期,第141-153 页)、周焕卿《庄一夔〈福幼遂生编〉的刊刻、流播及其对医学的贡献》(见程章灿主编《古典文献研究》第十八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年,第81-100 页)。。近年来,随着书籍史、阅读史、医疗社会史的勃兴和相互借鉴,历史上的医书阅读行为也受到学界关注,出现了一些新颖的研究成果③参见张仲民《晚清出版的生理卫生书籍及其读者》(《史林》,2008 年第4 期,第20-36 页);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清末出版的生殖医学书籍及其读者》(《学术月刊》,2009 年第1 期,第128-142 页);张笑川《〈慎宜轩日记〉所见清末民初士人的心性修养与健康维护》(《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 年第11 期,第12-18 页);张瑞《晚清日记中的病患体 验与医患互动——以病患为中心的研究》(《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 年第11 期,第25-31 页)。,让我们得以从一种新的视角,更加立体、客观、深入地认识历史上不同人群的生活、心态及其背后关涉的世态,揭示更多医学、社会和文化相互交融的多元历史面貌。不过,阅读活动是“物质性文本载体(如书本)与抽象性的思想文化之间的桥梁”[1],清代士人阅读医书的活动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中发生的?医书阅读给人们的医疗实践带来了哪些影响?不同的阅读目的和方式究竟如何形塑读者的观念与行为选择?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并不深入和清晰。
本文试从清代士人的医疗实践出发,重点探究方论类医书④方论类医书,主要是指专门收载、论述各类病证及其对应医方的著作,在各类医籍中数量最多,其中以“××方”命名的医书最具代表性。此类医书从宋元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在明清时期日益进入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多因简明、通俗、实用而广受人们欢迎。参见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二、三、四卷(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1—1993 年,第2423-4924 页);薛清录主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259-373 页);阎瑞雪《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 年第4 期,第476-491 页);张慧芳《方书源流述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9 年第10 期,第56-59 页)。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阅读应用实态,以期从读者阅读和接受的视角理解医书、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对患者、医者、医疗市场以及医疗实践的影响。关于清代士人医疗实践的记载,日记、年谱、笔记、诗文集等史料无疑最为丰富,不少成果都是利用这些史料从患者的视角研究医学与日常生活、社会变迁的关系⑤国外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英]罗伊·波特(Roy Porter)与多萝西·波特(Dorothy Porter)合著的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The British Experience, London: Fourth Estate LtD, 1988.国内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蒋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医病关系为例的探讨》,见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帝国与先知》(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第181-212 页);邱仲麟《医生与病人——明代的医病关系与医疗风习》(见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8 年,第253-296 页);涂丰恩《择医与择病——明清医病间的权力、责任与信任》(见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一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149-169 页);张笑川《〈慎宜轩日记〉所见清末民初士人的心性修养与健康维护》(《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 年第11 期,第12-18 页);张瑞《晚清日记中的病患体验与医患互动——以病患为中心的研究》(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 年第11 期,第25-31 页)。。这些研究充分表明,“自下而上”地思考古代与生命、健康相关的议题,能够让我们更加立体、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医学的延续和变革问题以及特定历史情境中不同群体的心态,从而更好地呈现医学、社会和文化相互交融的多元历史面貌。本文综合利用方论类医书和上述几类史料,就清代士人在哪些情境下阅读医书、如何阅读利用医书及其对医疗实践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论述。
一、士人阅读医书的基本模式及其特征
阅读是较为私人化、个性化的一项实践活动,每个人所拥有的医书、能够接触到的医书、对医书的认知以及如何利用医书等都不尽一致,相关史料也很繁复,难以一概而论。从清代士人的日常生活看,他们对医学熟悉程度的不同,是影响他们看待医书的态度、阅读医书的模式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两类群体(即不知医士人和知医士人)阅读医书的实践构成了清代士人阅读医书活动的基本面相,而在具体的阅读情境与方式方面,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
(一)以工具性阅读为主:不知医士人的医书阅读活动
不知医士人通常没有医学基础,在遇到医疗问题时基本不能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更难以提出适用的应对方案。他们阅读方论类医书,大多以工具性阅读为主,即主要是为了获取治疗疾病的有效方法,往往因读者自己或其亲友患病而发生,随着患者痊愈而停止,救护患者是读者阅读医书最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疗效是读者阅读医书最主要的期待。这种阅读模式大致包括三类常见的情形:为应对紧急情况而临时检阅医书的临时性阅读,经常通过检阅医书应对疾病的习惯性阅读,因医药短缺、生活贫困等被迫依靠医书满足医疗需求的被动性阅读。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身体突发不适的情况很多,临时在医书中寻找相应的治疗方法已是清代士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清初,金陵孟氏中医儿科传人孟河继承父业,擅于治疗婴幼儿疾病,深受人们好评。官员方亨咸经常让孟氏为子孙辈诊治疾病,称赞孟氏编写的《(新刻)幼科百效》为“保赤良书”。康熙十七年(1678),方亨咸患了痧症,此病是婴幼儿常见病,他想到了孟河的幼科医书,“因读是书,纤微悉验,服之如神”[2]4133,按照书中的医方服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治十一年(1872),官员林肇元的朋友万石卿从桂林带回一本新近刊行的《小儿脐风惊风合编》,林氏看后,计划将其在贵州地区重新刊印。过了半年左右,林氏按照该书中的医方治好了一例新生儿的疾病:“癸酉夏,适余六侄生,越日,小儿若昏迷,予之乳,不嚼而哭,令室人按是编脐风类视之,见儿口中起白点,脐下起青筋,已直至心坎下,如法治之,立愈。”[3]因此,林氏更加信任此书,随即将其出版。更常见的一种情形是,很多人在医治无效时纷纷通过查阅医书来寻找应对之策。虽然求医是人们应对疾病、维护健康的基本途径,但医生诊治无效的情况时有发生。面对这种困境,人们通常会通过各种渠道求助于其他拥有医疗知识或技艺的人,从医书中寻求应对之策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的选择。比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河南太守施诚刊刻了《轩辕逸典》一书,主要收录小儿痘疹方面的治疗方法。扬州人刘耀奎的叔父从书肆中买到了该书的抄本,读完之后非常珍视它。不久,刘氏家里一个仆人的两个婴儿患了痘疹,“一时业是科而名藉甚者皆弗治”,此时,刘耀奎的叔父“为之按证求方,依方施治”[4],最终治愈了他们。
临时查检医书难免具有随机性、盲目性。事实上,通过查阅医书为自己或亲友救治疾病已是很多士人的一种习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当属官员李棠阶。道光至同治年间,李棠阶在家人患病后都会参阅至少一种医书来确定疾病、观察病情、寻找最佳治疗或养护方案。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棠阶的妻子即将生产,他“检《傅青主女科》及《达生编》”[5]101-102,产后第二天和第三天,他接连检阅医书中的产后医方,以便护理妻儿。道光二十六年(1846),李棠阶的侄孙呕吐腹痛,他们请来一位刘姓医生诊治,不到三天,侄孙的病便好了。过了五天,疾病复发,他们又请来刘医生治疗,没想到这次非但没有治好,还使病情发展成为慢脾风。于是,李氏家人又请来一位姓原的医生,但效果仍差强人意。到了20 日,他们又请来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准备按照《福幼编》中的医方让患者服药,还没等服药,侄孙的病大作,李氏家人急忙让医生按照《福幼编》中镇惊的医方进行治疗,但最终未能挽救他的性命。过了两天,李棠阶又查阅了《幼幼集成》中关于惊风的治疗方法,这才明白是误用寒凉之药导致的[5]335-344。
在医生短缺、药价昂贵或生活困窘的条件下,医书往往是一些人仅可依赖的医疗资源。比如,光绪十八年(1892),江苏无锡士子周镇从别人那里抄录了一本常州孟河医派名家马培之撰写的《外科传薪集》,将其珍藏起来。过了五年,周镇的母亲腰背部长了脓疮,周镇“因家境艰难,未延专科治”,只能参照《外科传薪集》中的外敷方法,慢慢治愈了母亲的疾病,“自外敷出毒收口止,均将此书检方用药,化重为轻,幸而获痊”[6]。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梁漱溟的母亲连续多年患病,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多方求医问药,又要解决两个儿子的学费问题,家里十分困顿,无力延医。据梁漱溟和其哥哥回忆,在母亲病重期间,父亲梁济很多时候都是“自检方书制药剂”[7],只能参照方书自主制作一些药剂为母亲治病。
从以上诸种具体的生活情境可知,将医书视为有形的工具,在遇到疾病时从中寻找应对方法,在清代士人的医书阅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阅读通常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几乎不会掺入读者的主观意见和意愿,其最直接的目的在于致用——帮助患者或其亲友摆脱病痛的困扰和折磨,从而决定了士人常常会以快捷化、片段式的方法和节奏阅读医书。尽管通过参阅医书救护患者既有许多成功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案例,但是当医书的工具性阅读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性选择之后,也就逐渐习俗化,人们并不会因为某本书中的某些疗法没有效果而直接完全否定该书,更不会否定这种方式对满足医疗需求的价值。
(二)工具性阅读与学习性阅读兼备:知医士人的医书阅读活动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在读书、做官、写作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涉猎医书,注意积累医药知识。与不知医者相比,他们具备一定的医学修养,常常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甚或拟订出具体的救疗方案。知医士人阅读医书,在工具性阅读之外,更为突出的是学习性阅读——围绕书中的理论、经验、信息、观点、方法等进行阅读理解、消化吸收、纠错、抄录、改造等,其直接目的并非应对一时一地的疾病,而是答疑解惑、增进认识、预防保健、整合和扩散知识等。
在医书的工具性阅读方面,知医士人一般不会盲目地检阅医书,而是注重参考名人名著。比如,晚清时期长期在地方上担任儒学教授的陆以湉因家人遭到医生误治死亡而钻研医术。一次,他的亲戚李氏患了噎症,且“医告技穷,奄奄待毙”。无奈之下,陆以湉检阅了清初歙县著名儒医程国彭撰写的《医学心悟》,其中载有专门治疗噎阻的“启膈散”,李氏服用了四剂便可进食,又经过改方调理,不久就痊愈了。官员恽毓鼎平时留意医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的妻子胎产发动,腹痛不止,但胎儿一直未出生。他认为这种情况“只可守《达生编》之说,静以待之”[8]。《达生编》自1715 年刊行后,成为清代最流行的胎产方书之一,主张生产要顺应自然规律,不可妄加干预①参见俞莲实《清代产科医书和女性的生育:以〈达生编〉为中心的考察》(见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209-237 页)。。恽毓鼎正是遵照此书的意见,静静等待。不久,他的妻子顺利产下一名男婴,恽氏家人深感欣慰。
在医书的学习性阅读方面,三类阅读活动在知医士人群体中最为普遍和颇具特色。其一,通过阅读医书来解答心中的疑惑,增进对疾病、身体等方面的认识,在知医士人中颇为流行。比如,嘉道时期,士大夫梁章钜常常涉猎医学,在与他人交往或阅读其他类型的书籍时也关注各类医药知识,每当有疑惑时,他都会从专门的医书中寻找确切答案。一次,有人问梁章钜屠苏酒的涵义,梁章钜以《广雅》和《集韻》对“屠苏”二字的解释予以回应,认为民间将屠苏酒方与孙思邈辟疫之药联系起来,能够起到“屠绝鬼气,苏醒人魂”作用的说法十分可笑。他还以南宋医家陈言所著《三因方》中关于此方的记载作为佐证:“尝忆得《三因方》上有此药酒,用大黄配以椒桂。盖孙思邈出庵中之药,与人作酒,因遂名为屠苏酒耳。”[9]之后,梁氏在笔记中详细记下此方的配料、制作流程和使用方法。
其二,积累医疗保健知识也是知医士人阅读方论类医书的重要目标之一。对此,清代众多知医士人留下的笔记作品都辑录有诸多医疗保健知识,特别是各类实用的医方知识。在这方面,梁章钜的事例也颇具典型性。梁氏注重“摄生”“养生”事宜,在其笔记中专辟“摄生”类目,从不少医书和其他书籍中搜集、抄录了诸多医疗经验和相关知识。梁氏因眼睛经常患病,所以平时特别注意辑录各类治疗眼睛疾病的医药知识。他曾记下宋代医书《苏沈良方》中治疗目疾的特效方法,并叙说了两个使用此方很有效果的事例[10]。当读到歙县医生程国彭所著《医学心悟》时,他特意抄下关于目疾虚证和实证的论述。还有一次,在朋友提供的洗眼方法与自己常用的方法不一致时,他专门查阅《良方集录》一书,“乃知皮硝(六钱,拣净)、桑白皮(二两,洗净,生者更佳)二味本系洗眼仙方”,并将详细制作步骤和使用方法摘录下来,以备日后使用[11]。
其三,通过阅读方论类医书,为编撰简易医书、传播医学知识提供素材,在清代知医士人中也是常见的阅读活动之一。乾隆年间,安徽休宁人方允淳在游历南方数省时看到很多偏远山村的民众“产育而自接生,遇疑难辄母子两伤,或斫丧靔元,抱恙不觉,致宗祧斩绝,或强种神痘,而殀丧其子”,于是他阅读了不少医书,但发现这些医书或专门性不足而难以检阅,或阙而不全。最终,他决定“搜罗古今秘旨,细心详选,善者录,疑者删,积汇成书”,编成《广嗣篇》一书,刊印行世,希望“使穷乡僻壤无颠连待毙之民”[12]。嘉庆年间,江西萍乡士子文晟在求学期间常常患病,他“每查取古人成方,试之辄效”。后来,在做官期间,他搜采多种医书,先后编写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方面的方书[2]3365。从中可见,知医士人的社会地位、学识、见解以及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积极传播医学知识,而其最基本的途径,便是从各种医书中辑录出相关内容,这一过程无疑伴随着士人对医学知识的理解、加工乃至再造。
上述三类医书阅读实践在清代知医士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构成了学习性阅读的基本内容。由前述众多事例可知,学习性阅读重在以医书中的知识为基本参照,开展多种具有逻辑性、思想性、整体性、连贯性特征的活动,在理解、吸收和转化医学知识的同时,得到理解或作用于现实的力量,可谓医学知识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其阅读节奏是相对缓慢和循序渐进的。而从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来看,士人群体在学习性阅读过程中对医书的查阅、截取、重整、抄写、编辑和对医学知识的理解、消化、评价、反馈、转化等,正是医学知识影响士人生活方式、知识结构、思想观念、行为选择的过程。
二、医书阅读对士人日常医疗实践的影响
从上述两类人群阅读医书的各类活动可知,许多医书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消费品,为人们提供关于疾病、身体、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帮助人们方便快捷地解决一些医疗问题。从医书编写、出版、流通、传播、阅读、利用的整个体系来看,随着人们日渐频繁地接触、了解和利用这些医书,疾病、身体、药物、药物性质和功效、方剂配伍、医方主治等知识便会扩散开来,进而潜移默化地转变为患者、读者知识储备中的一部分,这无疑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人们应对疾病和维护健康的水平。而从日常生活层面来看,医书阅读活动对清代士人的医疗观念、行为、思维具有多重影响。
(一)增加士人获取医疗资源、应对疾病的渠道,提升病患一方的话语权
求医是最普遍的解决医疗问题的方式,但清代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建树有限,医疗市场的管理十分松散,庸医劣药充斥其间,有医疗需求的病患及其亲友往往为择医问题费尽周折和心思,医患关系不佳①参见马金生《明清时期的医病纠纷探略》(《史林》,2012 年第1 期,第71-79 页);张田生《清代的医病矛盾与医家应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6 期,第144-153 页)等。。在这种医疗卫生条件下,求医未必是最佳选择,而医书是医药知识的载体,相对中立、客观,患病后查阅医书,可以让患者及其亲友省去诸多麻烦,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接触和互动,不必卷入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因此,阅读医书给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摆脱苦痛、维护健康、拯救生命的渠道。
更为重要的是,医书阅读活动对医疗场域权力的分配和相互制衡具有实质性影响,其突出表现是,病患常常通过阅读医书掌握医药知识,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医疗话语权。在文本面前,医者利用专业知识役使患者的机会随之减少,而病患的主动性相对增强,病患学习、掌握医学知识,在医疗场域与医者对话的可能性,以及选择、决定医疗方案的话语权也会随之上升,这在客观上无疑形成了一种制衡医者专业权威的力量。这种权力机制在清代士人家庭生活中可以发挥减少医者误诊误治、过度医疗的作用。比如,嘉庆元年(1796),江苏阳湖秀才陆继辂的母亲得了温病,医者用太阳经表剂,本应出汗,但是过了几日也并未发汗。陆继辂记述:“年来太孺人以不孝多病,留意方药,诘医者邪在少阳,何以服羌活,不服柴胡?医大悟,易方投之,即夕壮热尽退。”[13]陆继辂近来多病,他的母亲留意方药,知道一些药物的功效和方剂配伍方面的知识,因而在医者没有用柴胡而用了羌活的时候,能够直接指出问题所在,成功避免了一次医疗事故。
不少士人把阅读医书所得医药知识应用于日常医疗实践,不会轻易屈从医生的诊断,甚至以此质疑医生的临床诊疗方案。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当属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翁氏学识渊博,在为官期间常常阅览医书,医学修养颇厚,还能不时为亲友开方用药。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家里的仆人王升染了疫病,并且越来越重,翁同龢记述:“医者以木瓜等及清暑之剂投之,了无效验,恶症均见,余既深知此病非姜附不治,又昨日灯下检近人所刻《四圣心源》,中论霍乱转筋必用附子,遂处一方,以附子、干姜、生姜治之,适有人持治时疫方用姜附重剂者,遂决意照方更投一剂,虽略转,而神气甚败,且视其命何如耳。数日内时症益多,药方亦甚乱,余意总以阳症宜清解,阴症宜温中。”[14]215由此可知,在翁同龢看来,医生所开的清暑类医方是药不对症,为验证自己的想法,他专门查阅了清初儒医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并且自拟一方来医治王升,这个医方正好与其他人治疗时疫所用药物相似。不过,效果似乎不是太好,翁同龢感觉自己遵循的阴阳之理受到了挑战。第二天早上,王氏说病好了,到了下午,病情又反复起来,无奈之下,翁同龢请来两位医生为其诊治,都说所服药物是正确的,未能治愈可能是因为病情太重了。同治七年(1868),翁同龢的母亲患感冒,咳嗽厉害,且筋骨酸疼,翁氏将经常延请的顾肯堂医生请到家里为母亲诊治。然而,过了三天,“慈亲今日转比昨日不爽,未申间即卧,发热喘促,脉右寸关洪数,似外感未清”,在此情形下,翁同龢分析了母亲的症状、脉象,认为“顾君之药专治气分,未免过轻”,用药分量不够,于是,他“照《李氏刊方》第一方服之(连翘等味)”[14]586,按照一本方书中的医方为母亲治病。
当然,上述行为只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并非所有士人都会付诸实践,而且随着患者病情、主治医生、医疗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人们也会改变惯有的方式,并不会完全依据医书而置他人的主张于不顾。
(二)促使自主诊疗疾病之风在士人群体中盛行
医书的广泛传播,以及士人群体阅读医书活动的广泛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自主诊疗疾病成为清代士人面对疾病时的一种重要实践倾向— —不管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士子;不管是常见疾病,还是大病、急病。比如,明末清初,文士范祥的父亲在习医过程中偶然于家中发现了一本《痘疹发微》,经过详细阅读,他认为此书价值较高。不过,他并未将该书立即公之于世,而是先在家人身上试验书中的疗法:“先据其首卷稀痘一篇,验之于予及二弟,而予弟兄竟以是辄效。又十年,以是验之于予二子,而小子又以是得效。”[2]4306经过多次试验,范祥的父亲才“信乎是书之剖精析奥,无微不发,为大有功于人也”,并让范祥和其兄弟校正此书,最终在康熙二年(1663)将其出版。咸丰十一年(1861),官员邵灿准备从上海北上,暂时居住在朋友冯泽夫的住处,两人交谈期间,邵氏将自己三年前在淮安做官时刊刻的《难产第一神验良方》赠送给了冯氏,此方是邵氏在北京得到的。不久,冯氏在妻子临盆之际,让妻子按照这一药方服药,结果“平安无恙,得一子,且产后产妇甚为健旺”[2]4000。冯氏非常高兴,由衷称赞该方神验。由此可知,尽管医学的专业化发展往往使人逐渐形成“疾病、健康问题只能交给医学专业人士处理”的思维和习惯,但从前文所述的历史经验可知,正是医书的广泛传播和工具性阅读行为的广泛存在,塑造了清代士人医疗实践的另一面:依靠文本而非专门机构或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疾病、维护健康。两种历史面相其实没有明确的界限和不可逾越的壁垒,可能随时转换,也可能并行不悖,因为它们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宗旨展开——摆脱苦痛,维护健康,延续生命,恢复有序、稳定的日常生活节奏与秩序。
自主诊疗疾病风气的盛行,对病患一方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前所述,患者及其亲友依靠医书而非专业人员治疗疾病,实际上强化了自身在医疗场域的主动权、自主权、选择权,不必受医疗市场中许多规则或权力关系的束缚,遭遇庸医劣药的几率降低。如果必须求医,那么患者及其亲友通过阅读医书掌握的医药知识也会让他们提升自身话语权而非一味盲从医生,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减少医者利用专业权威役使病患的机会。另一方面,依靠阅读医书自主诊疗疾病,往往需要读者根据患者的病因、病情选择合适的诊疗方案,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会出现参阅医书犹疑不决、无效甚至误治的情况。比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官员许宝蘅的妻子生下男婴,三天后,小孩面红喘急,大哭无声,也不食奶,许氏“查《达生编》,名嘬口症,颇危险,急以犀角磨冲与服,又以西牛黄与服”[15],但并没有起作用,孩子最终夭折了。
(三)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士人“唯书本是论”的思维与行为倾向
当阅读医书成为诸多士人解答心中疑惑、增进自己认识的习惯性行为之后,书本中的观点、信息等会潜移默化地渗入士人的内心,且如果一旦在生活中遇到难以理解的医疗现象时,翻检医书便成为士人的重要选择。
乾隆五十八年(1793),京师发生瘟疫,人们用晚明医学家张景岳和吴又可的方法治疗染疫患者,但效果并不好。而安徽桐城籍医生用重剂石膏将官员冯应榴的小妾治好了,消息传开,很多人都开始用此疗法,效果很好。大家对此都很不解,大学士纪昀也十分惊讶:“虽刘守真之《原病式》,张子和之《儒门事亲》,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考喜用石膏,莫过于明缪仲淳(名希雍,天崇间人,与张景岳同时,而所传各别),本非中道,故王懋竑《白田集》有《石膏论》一篇,力辩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未可执为定例也。”[16]显然,纪昀对医学的认识基本源于正统医学体系中的各类名医名著,对这些名医很少使用、名著中也很少出现的有效医疗知识表现出诧异、困惑、不解甚至怀疑的态度,只好“姑妄听之”,最终还是以五运六气这种在精英文化圈较为流行的理论暂时平息了内心的紧张。除了一般性的解惑之外,士人阅读医书也会深入更为专业的领域,对某些医学观点、现象、理论等加以理解、引用、分析或领悟。比如,社会上流传着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为“医宗四大家”的说法,陆以湉读书遇到此问题时,专门抄下新安医生罗浩所著《医经余论》中的观点予以批驳,并称赞罗氏所论“足以正数百年相传之讹”[17]。
文本知识与口述知识常常互为来源、文本知识的相对固定和医生临床诊疗的灵活多变、医书的“无声”和医生的“有声”等诸多矛盾情形也时刻影响着人们的决策,使读者在选择相信医书还是选择相信人之间常常表现出犹疑、摇摆甚至自相矛盾的状态。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苏镇江文士赵彦偁患了风热病,耳轮红肿,其让一位姓景的医生诊治,景医生告诉他不用敷药,只要服用荆防败毒饮即可。赵彦偁有些不解,回到家后,他查阅了《外科正宗》一书,发现医生所言与书中所载基本一致,这才放下心来。不过,当读到“时毒门”中“时毒亦有轻重有吉凶,凶者亦可致命”一句时,他又忐忑起来。第二天,他仍然头晕、发寒热,以为自己所患为凶证,急忙延请另一位医生来诊治。没想到,这位医生和景医生的观点一致。医生的轻描淡写和赵彦偁内心的强烈担忧形成强烈反差,使他开始怀疑医生,甚至扩大开来,批评内科医生不会外治、外科医生不懂医理,批评很多医生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等等[18]。不过,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没过多久,他就痊愈了。
由此可见,方论类医书并非以济世惠民的单一面貌进入人们日常生活,而是像其他文本一样形成了一种作用于士人日常医疗实践的规训力量,为士人提供了一套规范化、标准化、中立化的知识鉴别工具。清代士人在参阅这些医书时,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唯书本是论”的思维与行为倾向,一方面对医书特别是名人名著中没有记载或不主张使用的疗法大多持怀疑、批评的态度,并以它们为评判标准发现并检视其他知识形式,如各类所谓“奇异”“罕见”“异端”的民间疗法、口耳相传的经验知识,另一方面则以它们为依据来质疑医生的诊断、疗法等。
三、士人阅读利用医书的基本困境及其原因
面对包括方论类医书在内的众多医学文本成为广大非专业人士的阅读对象,有的人高奏凯歌,认为这是社会的福音。比如,康熙年间,官员钱朝鼎在评价江苏常熟士人朱鸿雪所编《方便书》时说:“凡有疾者,不必求医,不必市药,信手拈来,立可奏效,且一览了然。贤愚共晓,家藏一册,则人可为医,调之方便,洵不诬矣。昔陆羽著《茶经》,王积著《酒经》,俱足不朽,然未若是编之有益于民生也。”[19]而有的人则满怀忧虑,认为医书增多,特别是通俗医书的流行非但难以帮助人们应对疾病,反而有可能带来更多风险。晚清儒医马冠群曾评论说:“独取《本草备要》《(本草)从新》《医方集解》《濒湖脉诀》《医宗必读》诸书以为授受秘笈,外此一切罢去,不复过问。此数书者,其显近简约,诚便于记诵,无有《灵枢》《素问》之艰苦,然其言不皆是也,且局于成法,不能通变,以尽善自信为是,不能虚衷以求益,私一尊而薄众说,既惮于兼收博采,沿讹袭讹之言亦混同收入,不复订正,最为误己误人之大错。”[20]这些不同的声音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影响着士人群体的选择。一次,叶昌炽长了疮疡,他检阅晚清名医王维德所著《外科全生集》,看到其中有名为平安饼的医方,可以除去毒根。于是,他照方帖敷,没想到帖上去之后疼痛更加剧烈,彻夜难眠。他在日记中愤而写到:“甚矣!尽信书不如无书也。”[21]从中可知,几乎所有医书都以济世救人为价值引领,但“尽信书不如无书”或许才是现实生活世界中很多读者真实的心声。他们既乐于见到医书为人所用、帮助民众维护生命与健康,又不敢完全信赖和依靠医书,总体上表现出爱恨交织、迟疑不决的心态。那么,究竟哪些因素阻碍着士人群体方便快捷有效地阅读和利用医书呢?
其一,医书种类繁多且质量参差不齐,读者选购医书较为盲目。从雕版印刷术日渐普及的宋代开始,大量方论类医书的出版和传播就受到诟病。在医学济世的美好理想引导下,由政府和士大夫群体主导的医书编撰、出版和推广运动,力图让普通百姓也能够了解、学习和运用医药知识。这种理念及其实践带来的负面效应之一,即不少医书越来越趋于简单化、通俗化。特别是晚明以降,在社会需求日益增强、市民消费文化兴盛的背景下,各类旨在满足非专业人群医疗保健需求的医书广泛流传于世,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消费品。在此潮流中,医书因袭陈方、详略不当、互有歧见的情况十分普遍。明末清初,士人吴国翰前后养育的10 余个子女中有六七个都死于痘疹。痛定思痛,他遍览古今医书,参互考订,发现很多可以应对痘疹的良方,他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然学者往往悉举成书,口诵心维,历岁月而淹熟者无虑数辈,及用药而先后倒施,温凉误用,虚实舛观,致有庸医杀人之咎。读书之效,茫如捕风,何也?岂书之误人哉?要以繁冗者不芟截当,参驳者未能简汰故尔。”[2]4318乾隆十五年(1750),在书院工作的文士方允淳完成了《广嗣篇》的编辑工作,他之所以编写此书,是因为他在游历过江浙楚闽等地方时,发现许多民众都有产育方面的困难,然而“坊间保产、保婴诸书,非散而无纪,即略而不详”[2]3915,很难切实指导人们解决实际问题。可以说,医书的数量虽多,但真正令广大士人满意的医书并不多。
此外,晚明以来,坊刻医书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医书的商品化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书坊、书商为赚取更多利润而常常对医书进行包装或名不副实的广告宣传,这无疑会对读者选购和利用方书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嘉庆三年(1798),福建四堡邹氏书坊刊刻了《医宗宝镜》一书,据作序者邹璞园说,该书是龙虎山张真人家藏秘本,张真人将此书传给了好朋友邓复旦,邓复旦为了济世利人而将此书公布于世。在书名页,有“医林第一书”的题字,还有“药性精详,医方明备,及论症论脉无不极其穷微探奥,抉摘无遗,诚足为杏林中之全璧,医学内之捷径也”的广告词。而据学者考证,该书基本上属于抄袭之作,将清代汪昂的《本草备要》和《汤头歌诀》、金代李东垣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和《脾胃论》、金代张元素的《医学启源》、宋代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论》、明代皇甫中的《明医指掌》等医书略作改动后组合而成[22]。由此可见,所谓“龙虎山张真人家藏秘本”完全是书商为了吸引人眼球而炮制出来的噱头,书中医方是否有效并没有经过验证。由于道教神仙信仰在民间非常盛行,而“龙虎山张真人”指的正是道教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他具有降妖伏魔的超凡能力,因此,以他的名号售卖医书,无疑能够以大众熟悉的文化符号增加该书的权威性和销量。据美国学者包筠雅的田野考察,四堡书坊曾刊印过大量简易方书,很多方书其实都像此书一样,经过简单加工就可以输送到外地市场上进行售卖[23]。
与上述情况对应的是,很多士人购买、抄录、阅读、利用方论类医书时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少人选购医书时很看重其口碑,而医书口碑的好坏很多时候又取决于其市场反响。例如,晚清时期,鲍相璈编撰的《验方新编》一书很受欢迎,许多士人都收藏、参阅此书。而它之所以能够从广西武宣这一偏僻之地风靡南北,其实与广州十三行富商潘仕成、晚清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丁日昌、洋务派代表人物梅启照、李鸿章的妹夫张绍棠等重刊和传播此书密切相关[24]。经过“名人效应”的加持,《验方新编》的权威性大大增加,更为世人看重。然而,在人们实际阅读利用该书的过程中,出现不少无效甚至被该书误导的现象。晚清绍兴世医何廉臣曾指出,《验方新编》中有很多医方都无效:“《验方新编》一书,世俗最为通行……然其中效者固有之,不效者亦不少,穷乡僻壤以助医药之不及则可,而谓可恃此以全生,则亦未敢遽信……其中无不庞杂,间有峻厉之方,意编书者似于医事未尝有精诣也。”[25]综合这些话语可知,一方面,《验方新编》十分流行,几乎家置一编;另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参阅此书开展医疗活动时又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如此纠结的现实情境难免给人带来迷惘和困惑,使人不敢完全信任医书。
其二,疾病、身体、医药等所具有的专门性、复杂性,是士人将阅读所得转化为医疗实践的一道门槛。不管医书通俗化程度如何,它们始终是专业性的文本和知识。虽然大多数医书会告诉读者关于疾病、症状、药物及其用法用量、疗法及其使用规范等方面的知识,但读者要将这些信息准确地与患者所患疾病及其身体状况对应起来,即使对于医学修养较好的知医士人来说也并不容易做到。同治七年(1868),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羊角风发作,其家人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生,翁同龢“读黄元御书,以为当用姜附,而不敢独断也”[14]599,虽然从黄元御的医书中找到了对应的医方,但并不敢直接使用。同治十年(1871),翁同龢的母亲患病,他先后请来很多医生为母亲诊治,不少医生所开药方都不尽一致。有一位名叫赵朗甫的医生认为其母亲胸中阳气不舒,脾气也逐渐困涩,因而开了温通之药,包括半夏、茯苓、生姜、黑梔、炙草、厚朴。而这个医方与《温病条辨》治疗热病的原则有背离之处。面对这种窘境,翁同龢感慨:“伊熟于黄氏之书,故持论如此,若以前治法而论,则如此等药皆每服所必用,而今日拘于《温病条辨》一书,则又畏之如虎。人子不知医,真无从措手耳。”[14]897-898也即,对于同一病证,不同医书中的治疗方法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黄元御和吴瑭都是名医,到底该如何用药,翁同龢非常疑惑,尽管读了很多医书,但他还是感到束手无策。
此外,文本知识的相对固定性和有限性,与疾病、患者、病情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之间存在矛盾。医书一旦编辑出版后一般无法轻易变动内容,而处境不同的患者及其亲友阅读利用这些医书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变通,但很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所谓具体情况,主要涉及气运、风土、个人禀赋等、患者病情多变等问题。比如,乾嘉之际,官至户部尚书的安徽歙县人曹文植曾指出:“夫《灵》《素》经书,千古不易,而天地气化,人生禀赋,随时为厚薄,且南北异宜,山川间隔,一郡一乡,气感各别,即一乡之中,又随世变转,而寒热、水旱之不齐错出乎其中。吾见今之疾不必同古之疾也,又况药物之产随地气变迁,或同一名而古今迥殊,或犹是一物而前人审验未真,久而益辨者,而谓第执成言,遂可自足也哉?”[26]显然,曹氏的医学演进观念具有浓郁的自然主义色彩,自然界的气运变化、地理差异、气候变迁深刻联系着人们的身体和疾病,因此,尽管医书已经汗牛充栋,但在不同的时空中治疗每个人的疾病时不可固守成言。所谓“方宜有不同,老壮之非一,山居与城市异治,膏粱与藜藿分途……运用在一心,临证如临敌,选药如选将,求其至当而后已”[27],更是士人群体倡导因时因地制宜和随机应变的写照。
综合来看,这种自然主义的医疗理念所秉持的核心治疗主张是:一切成方、成法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因人而变。显然,要在如此多样、复杂的情况中阅读利用医书,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会面临不小的挑战。
本文探讨了清代士人阅读医书的一般模式及其基本特征,阐述了医书阅读活动对清代士人医疗实践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考察了清代士人在阅读利用医书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及其基本原因。当然,阅读活动具有很强的私人性、个体性,本文只是对清代士人医书阅读史的初步研究,相关论述难免挂一漏万。
在日常生活中,清代士人阅读医书时基本以工具性阅读和学习性阅读为主,不知医士人群体倾向于前者,而知医士人群体则兼具二者。医书的工具性阅读,通常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几乎不会掺入士人的主观意见,其最直接的目的在于致用——帮助患者或其亲友摆脱病痛的困扰和折磨,从而基本决定了士人阅读医书的方式和节奏——快捷化、片段式。医书的学习性阅读,则重在以医书中的知识为基本参照,开展多种具有逻辑性、思想性、连贯性特征的活动,在理解、吸收和转化医学知识的同时,得到理解或作用于现实的力量,可谓医学知识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之一。
医书在人们的日常医疗实践中发挥作用,对医疗场域权力分布具有实质性影响。医书进入社会大众的生活之后,医学知识的中立性、客观性大大凸显。在文本面前,医者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役使患者的机会便随之减少,而病患的主动性相对增强,病患学习、掌握医学知识,在医疗场域的话语权也会随之上升,客观上形成一种制衡力量。当然,医书并非以济世惠民的单一面貌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它们同样构成一种规训力量,常常被当作“真理的载体”,清代士人往往以它们为标准评判其他类型的文本或知识,或质疑医生的诊疗。尽管阅读医书已成为清代众多士人的生活习惯之一,但总体看,爱恨交织、迟疑不决才是士人实际利用医书时的真实状态。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受到医书繁多且质量参差不齐、读者选购医书具有盲目性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又与医药知识的专门性、疾病的多变性、诊疗的变通性等医学内在原因密切相关。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士人阅读利用医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医书在“需求”层面的基本状况,不管是何种医书,拥有通俗的语言、简易实用的知识和广泛的流传度,并不等于它们必然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阅读和使用,所谓明清以来“医学普及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类医学文本和知识变得容易获取、便于阅读,并不完全适用于医疗实践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