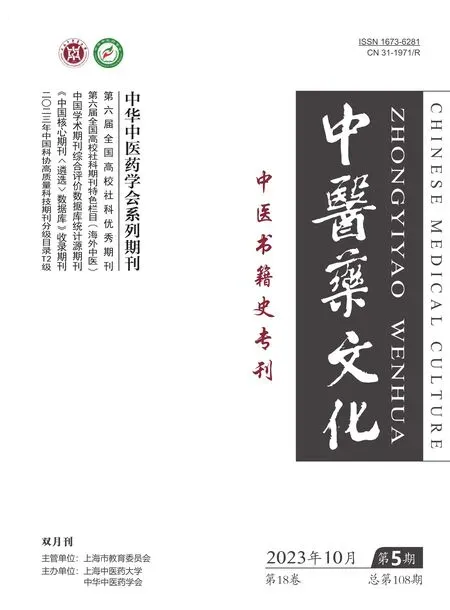瘟疫背景下王孟英重订《霍乱论》及相关研究
于业礼,徐 双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王士雄(1808—1863),字孟英,世以字行。又字梦隐,号潜斋、半痴山人等,浙江海昌(今浙江海宁)人。少年丧父,终身未入仕途,无宦海经历。王孟英出生于医学世家,其曾祖父王学权(秉衡)曾著《重庆堂随笔》,未竟而终,祖父王永嘉、父亲王大昌续为增补,至王孟英再行评注,终于完成并刊印。此外,王孟英一生著作及评述先贤医书甚多,主要有《温热经纬》《随息居重订霍乱论》《随息居饮食谱》《王氏医案》《潜斋医学丛书》等。尤为值得称道的是,王孟英擅于温病理论及临床诊治,被尊为“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
咸丰、同治年间,王孟英避难上海,时值霍乱猖獗,亲朋故友罹难众多,使得他对早年自撰的《霍乱论》一书重加订正,是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以下简称《重订霍乱论》),是一部有关霍乱诊断、治疗和预防的专书,也是我国医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霍乱专著,被近代学者曹炳章评为“实为治霍乱最完备之书”(《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
近代以来,从学术史角度对《重订霍乱论》价值进行研究的著作也较多。尤其是王孟英在《重订霍乱论》中提出预防霍乱诸措施,体现出医学中的预防思想,多为现代学者所关注。相关研究如黄英志[1]、施仁潮[2]、陆翔等[3]先生。也有学者从环境医学、防疫角度进行研究,如申红玲等[4]、沈丽菊等[5]。孟凡滕、宋素花[6]从疾病治疗角度出发,将王孟英与张仲景对霍乱病的治疗进行对比研究,也是很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王孟英与张仲景所论述的霍乱并非完全相同的疾病,在未深入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似有不妥。《重订霍乱论》是王孟英晚年的重要著作,其之所以著成,与王孟英晚年生活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既往诸先生的研究,多着眼于《重订霍乱论》学术史方面的研究。虽在年谱等著作中对王孟英晚年生活有所考察,但对王孟英晚年经历与《重订霍乱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重订霍乱论》的成书过程等都很少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在考察咸、同时期疫病的基础上,结合王孟英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治疗霍乱的经历,阐述《重订霍乱论》成书背景、具体过程和历史意义等。
一、颠沛流离:战争与瘟疫背景下王孟英的晚年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全国多地遭遇瘟疫,而江浙一带因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灾害尤为惨烈。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影响下,原本繁庶的江浙地区遭受了一次人口巨减的惨剧。这一时期江浙的“瘟疫”,是包含多种疾病名称的集合体,如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以及可能存在的伤寒、百日咳等,因具体的时空背景不同而意义不定[7]。疫病涉及的区域则与军事活动紧密相关,江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非常惨烈,而在后期卷入战乱的常州、镇江以及浙西部分沦为战场的山区,也出现过严重疫情。最后,上海——一个影响比较间接、因其租界的特殊地位导致大量人口涌入— —同样疫情惨重。其中,霍乱的反复尤为明显,其余绪甚至延至20 世纪前半叶。
据王孟英所撰《归砚录·弁言》(1857),其祖籍为盐官(今浙江海宁),至曾祖时迁居至略近内地的钱塘(今浙江杭州)[8]346。王氏家族所在的浙北地区因太平天国运动,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咸丰三年(1853)南京被太平军攻破并定都,苏浙皖赣等由此陷入浩劫。战乱的直接影响便是无数民众的颠沛流离。王孟英曾对离开杭州的经历作了一番解释。他说:
殆癸丑(1853)春,金陵失守,杭城迁徙者纷如,窃谓吾侪藉砚田以糊其口,家无长物,辛丑(1841)之警,有老母在,尚不作避地计,况今日乎?第省会食物皆贵,既非寒士之所宜居,而婚嫁从华,向平之愿,亦不易了,倘风鹤稍平,可不继志以归籍耶?[8]346
王孟英提到,由于金陵被太平军攻陷,以至于杭州出现了许多迁出的避难者。在此,他追溯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情形,当时家有老母,因此没有选择离开,因而这一次也不认为有必要躲避。不过,事后来看此两者差异明显。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后者旋即撤军;而定都江宁(改称“天京”,即今南京)的太平天国政权则与清政府分庭抗礼,长期盘踞。因此,王孟英在辛丑年(1841)的经验,并不能照搬至癸丑年(1853),他生命最后一阶段的颠沛流离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在太平军刚刚攻占江宁之时,清军江南大营被击破、战乱延伸至浙北苏南之前,远非时人可以预料。与此同时,民生之艰难可以想见。《归砚录》中,章华征在和诗中提到“先生视病不受贫者之酬”。在展现王孟英豁达爽朗的同时,也暗中揭示了当时贫病交加情况的普遍。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由于太平天国的西征、北伐,以及内部爆发的严重内讧(天京事变),直到咸丰十年(1860)五月,清军再建的江南大营被击破之前,王孟英所逗留的渟溪及其周边地域尚且残存一份平静,期间王氏调养生息,亦间有走亲访友。太平军攻略东南之后,战火波及常州、无锡、苏州以及浙西等地,即“庚申之难”。王孟英婉谢了亲友的邀请,选择了已经开埠的上海作为避难之所,尽管当时华洋杂居的上海在很多人眼中尚属“九夷”之地。当然,王孟英在赴沪之前还去了一次濮院,期间的经历可以参看《乘桴医影·序》。同时,王氏还曾努力地著述新书,《随息居饮食谱》及《鸡鸣录》二书亦完成于此时。同治元年(1862)四月,太平军攻破濮院,王孟英前往上海。同年五月抵沪后,王孟英居住在上海县城东门外的“德泰纸号”,因其老板周采山兄弟恰与王氏为故交。某陈姓家属病患被王氏治愈,感激之下为王氏提供了别处住所,他终于得到了一处安稳的落脚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8]186。这一时期的许多医学诊疗活动,此后沉淀为《乘桴医影》中的医案。
上海周边的青浦、松江等地,虽然一度遭到太平军李秀成部的攻击,但从整体上看,战事相对较小,且随着李部西撤逐渐西移而日趋稳定①据余新忠的考查,咸丰十年、十一年的嘉兴濮院,同治元年的嘉兴、秀水、上海、长洲、元和、吴县、吴江、嘉定、南京等地,上述地区暴发的疫病可以判断为霍乱。这些地区都呈现出天灾人祸叠加的可怕情形。。不过,正如王孟英所述的那样,无数人因为这一“孤岛”的存在而大量涌入,增加了各种疫病暴发的几率。晚年的王孟英避开了战火,却无法躲避可怕的瘟疫,直接导致了一代名医在上海的陨落。据近期整理出版的《管庭芬日记》及蒋寅昉相关书信,可以确认,王孟英辞世是在同治二年(1863)五月二十六日②参王翚、王光磊《王孟英卒年考》(《浙江中医杂志》,2015 年第12 期,第925 页),此文引有萧逎甲致蒋光焴信中的一段话:“天有旱意,酷热非常,疫疠大作,系吊脚痧一症,有热有凉,治之非易,且往往不及措手。王孟英兄竟于前日作古,陆定圃、汪谢城所诊俱不得效。”如其所述,王孟英感染了吊脚痧(即霍乱,详见后文),经陆定圃、汪谢城诊治未愈而亡。其中,汪谢城即汪曰祯,王孟英好友。陆定圃即陆以湉,存世有多种著作,其著作《冷庐医话》中曾提及王孟英,却未载其死事。王翚、王光磊先生文中未注明引用材料出处,但有“笔者又赴浙江图书馆查阅馆藏清人信稿”等语,可知该信是收藏于浙江图书馆。,享年56 岁,具体死因正是霍乱。另外,《温热经纬》书后有仁和唐文溶著的《跋》一篇,其中记有“今年与秀水庄君眉仙共事申江,乐数晨夕,见其案头有先生大著《温热经纬》,展读未竟,会先生来访庄君,遂得亲承道范”等语,这篇《跋》的著作时间是同治二年五月,其中又曰:“且知先生亦以避难僦居于沪,自此可常得追随,洵不仅一时之欣幸也。”[8]107故当时王孟英应尚在世。这篇《跋》中记载的王孟英访庄眉仙一事,是目前所知他生前最后的活动事迹。
二、内外合邪:王孟英对咸、同之际瘟疫的观察
作为医者,王孟英对瘟疫的敏感性远超常人。不管是在濮院还是上海,他都一直未停止疾病诊疗活动,对瘟疫的发生发展也很关注。由于既往的经验,使他一开始就认识到咸、同间的这次以吐泻转筋症状为主的瘟疫,主要为霍乱。接触到最初的病例时,也能运用黄芩定乱汤等将患者治愈,但他对霍乱的了解,也因不断地观察和思考,经历了由略到详的过程。也是因这些观察和思考,让他对霍乱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乃至对温病学说的发展,都有了更多的认识,最终得以完成《重订霍乱论》这部巨著。
王孟英在濮院期间,就对霍乱的发生有所耳闻。《重订霍乱论》卷三中,他回顾同治元年(1862)三月间吕慎庵向他讲述邻家童子的病例及余杭纸客的病例,描述症状为“陡然吐泻转筋”,而重症患者则会出现“舌卷囊缩,形神脱离”等。
王孟英最早接触到霍乱患者,是在抵沪以后。患者共两位,其一韩氏,旋即不治而亡。另一位纪运翔,年仅17,病情颇重,症状呈现为“手面皆黑,目陷窜睛,厥逆音嘶,脉伏无溺,舌苔紫腻,大渴汗淋,神情瞀乱,危象毕呈”[8]146。由于周采山的强烈推荐,乃至软硬兼施,王孟英用尽全身解数进行诊治。他考虑到时节未交芒种,患者所感应非暑湿之邪,仍是冬寒内伏所化的温病,顺应地采用了温病疗法,用黄芩定乱汤及针刺曲池、委中穴等辅助形式,最终治愈了患者。
黄芩定乱汤是王孟英自创医方,后经过加减,由周采山刊印。同治二年(1863),王绍武在屠甸,得到该方后,“劝人合药施送,几及千料云”[8]147,而闻名后世。清代后期的多种医书中都转载了这个医方,并有用之治疗霍乱等病的医案记载。该方由黄芩、焦栀子、香豆豉、原蚕沙、制半夏、橘红、蒲公英、鲜竹茹、川连、陈吴萸组成。在最初使用时,王孟英曾自述该方组成配伍:“方以黄芩为君,臣以栀、豉、连、茹、苡、半,佐以蚕矢、芦根、丝瓜络,少加吴萸为使。”[8]146近代医学名家冉雪峰评曰:“虽尽脱古人范围,而香豉、省头草、蚕砂功能醒脾解秽除毒,时行霍乱,亦可节取,较俗说颇高一格。”[9]但该方是王孟英最初诊治霍乱时使用的医方,与后来通过观察和思考后最终确立的治疗大法并不一致。
王孟英在诊治纪运翔过程中,关于时节的思考也值得关注。如当时温病学说盛行,王孟英作为“温病四大家”之一,其对疾病的认识,无不以温病学知识为根本。如对瘟疫的发病时节问题,他就提出质疑:“窃谓此病之盛行,多在夏秋暑湿之时,何以今春即尔?”[8]146时节与邪气的关系,可溯至《素问》“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及相关论述,经王叔和、郭雍、吴又可等人阐发为伏邪理论,清代温病学家更是大加发挥[10]。如刘吉人《伏邪新书》谓:“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伏邪。”[11]伏邪的种类有多种,霍乱以吐泻症状为主,属湿邪为患。伏湿之病,多发于夏秋季节,此次咸、同间瘟疫却是春季发病,与既往温病学理论不符。经过思考,王孟英认为:“暑湿既可伏至深秋而发为霍乱,则冬伤于寒者,至春不为温病,亦可变为霍乱也。虽为温病之变证,而温即热也,故与伏暑为病,不甚悬殊。”[8]146此说混淆伏温、伏暑与伏湿为一,颇为圆滑,有自圆其说之嫌。
而夏至后,随着见到的霍乱患者越来越多,王孟英发现此时的患者发病较芒种前更为严重。在观察的基础上,他认为这已不简单是伏邪温病,引其曾祖《重庆堂随笔》中有关疫病的论述,认为瘟疫流行既久,热气、病气与尸气胶着为毒疠之气,在内之伏邪与在外之疠气相合为患,故而发病更为严重。他虽仍坚持伏邪温病之说,但已不得不另寻理论支撑,最终联想到疠气之说。疠气之说倡于明代吴又可《温疫论》,如在《自序》中即曰:“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12]虽然吴又可将这种异气称之为“杂气”,但在清代诸家的引用中,已经把“杂气”和“疠气”等名词混为一谈了。不过王孟英此处引其曾祖之说,认为疠气乃是热气、病气、尸气等胶着而成,并非天地间另有一种异气,与吴又可之说又有不同。
由这些观察而来的经验,也成为王孟英探索瘟疫病机、厘定治疗大法的重要根据和出发点。如他据此提出对霍乱之所以表现出寒性症状,乃是客邪外束、伏邪不得发而闭于内所致,实为真热假寒。认清了霍乱真正的病机,王孟英也由此确定治疗大法为:“故必先以夺命丹开其闭伏,愈后变证不一,然随机而应,甚费经营,非比往年之霍乱,虽系危证,但得转机,即可霍然也。”[8]147很明显,此时王孟英治疗霍乱的方法已较运用黄芩定乱汤治疗纪运翔时完全不同。另外,咸同、年间的瘟疫并非王孟英经历的第一次霍乱,早在1837—1838 年间,他就已经诊疗过不少霍乱患者,并据诊疗经验,写作《霍乱论》一书。《霍乱论》卷下记载了王孟英自创的燃照汤、连朴饮、驾轻汤、致和汤、蚕矢汤、冬瓜汤等多首医方。此次诊疗霍乱之初,他也再次创制了黄芩定乱汤,但确定霍乱的治疗大法以后,他并未再创制新的医方。简单看来,这似乎是王孟英医疗水平的降低,其实恰恰相反,这正是王孟英临床诊疗水平提高的表现。中国传统医学讲求圆机活法,临床诊疗疾病,不在于处方用药的新颖或独特,而在于认准病机。王孟英认清霍乱病机以后,治疗“先以夺命丹开其闭伏”,然后“随机而应”[8]147,可谓圆机活法。
至此可知,王孟英在咸丰、同治年间的这场瘟疫中,积极投入救治工作,并通过观察和思考,积累不少医学经验,既丰富了温病学说,同时也完善了霍乱的诊疗理论。但与王孟英相比,同时代的其他医者并不完全如此。如相对于患者而言,医患关系之间知识信息的不对等,很容易造成某种强烈的暗示或误解,医患双方在事前对于结果不确定性的估计并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是在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有待诊治的患者选择空间非常有限,这给了某些医者非常灵活的操控空间。王孟英在对瘟疫观察的同时,也对其他医者的所作所为有所观察,发现庸医为多。他曾感慨道:“每见此地市医临证,虽极轻之病,必立重案,预为避罪邀功之地,授受相乘,伎俩如是,良可慨已!”[8]148普通人或许因为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也无法理解医者群体内部的一些话语及其规则,根本无法区分某人治与不治的具体原因。当然,除了庸医和避罪邀功的俚滑之辈,也有不少医者因理论经验不够、能力不强,或执着于以温热药救治霍乱的古代经验,以致大量病患死亡。因此,王孟英也意识到更有效的做法是清晰地给出诊治霍乱或其他传染病的具体措施,避免模糊操作空间过大给病患带去的额外伤害。那些发生在自身周边的惨剧,亲朋的丧生,对王孟英的打击与刺激尤为强烈,使得他最终下定决心,重新订正旧著《霍乱论》一书。
首先是好友金簠斋的亡故。有关金簠斋的资料目前非常罕见,只能根据王孟英提及的内容略知一二。金簠斋是浙江元和(今杭州市)人,年长王孟英两岁,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同样作为一名医者,金簠斋著有《转筋证治》一书,咸丰七年(1857)已在苏州刊印。金簠斋仰慕王孟英已久,曾得知王孟英著有《霍乱论》。此时瘟疫暴发,金寻求此书的愿望越发强烈,但遍搜坊间而不得。后通过王孟英的表弟周鹤庭,得知王孟英已达上海,于当年六月十九日前往拜访(金抵沪在此年初)。两位医者一见如故,交谈甚欢。不过,当金簠斋提出要拜入王孟英门下的请求时,王孟英以“余何敢当”为由拒绝。金簠斋旋即又提出请王孟英重订《霍乱论》一书,王孟英也没有答应。约在当年七月,王孟英再次接受崇明县宰姚欧亭邀请,再次前去崇明为他诊病,行之前,将此前完成的《归砚录》书稿交给金簠斋,托他校订。等王孟英自崇明返回,金簠斋已将书稿校订完毕。王孟英被他感动,准备将其他书稿也都托他校订,并有了重订《霍乱论》一书的想法[8]350。然而世事难料,八月二十八日夜间,金簠斋感染了瘟疫,发病迅猛,待王孟英天明赶到时,已“正气溃散,勉投参药,竟不能救”。王孟英十分伤心,“不觉涕下之如雨”,在给金簠斋的挽联中,他写下“风凄秋夜,那堪衰鬓丧知音”[8]149等语。
其次,其他王孟英的亲友中,先后罹难者为数众多。如他在《归砚录自序》中道:“回忆亚枝于申春闭城后,溘然而逝;荣甫于酉冬城陷后,未闻下落;赠言诸君,如海槎、菊斋、二郊,并归道山。敬民孑身窜难来申,于六月十七日哭母身亡,年甫三十一,尤可伤也;彭、章两闺秀,亦已化去。”[8]350此年闰八月初旬,他接到二女夫婿发来的信件,提及其妻,也就是王氏次女定宜,在八月二十三日因感染瘟疫,并于次日去世。信中详细说明了二女儿染病与治疗的情况,王孟英据病情分析,二女儿所患的当是伏暑,但诊治的崔姓医生却用了附子理中汤、附桂八味汤等辛热类方药治疗,故而认为其次女是因误治而死。据说,在王氏次女弥留之际,曾对其夫感慨:“吾父在此,病不至是也。”王氏次女的夫家戴氏,同样是医学世家,其祖戴干斋、父戴雪宾均有医名[8]365。医者崔某误用热性药物,戴氏一家竟然不察,让王孟英尤其气愤。在给次女的挽联中,他写出“濒危思父疗,虽曰死生有命,尔如铸错,试遍了燥热寒凉诸谬药”[8]149之类的语句,悲怆之意溢于言表。
王孟英在为他人就诊时,颇为注意辨别瘟疫发病的寒热属性。因温病热治而死的惨剧,一而再地发生。如果说,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惨剧或许存在医者避罪邀功的可能,但其次女因误治、且同为医者的亲家戴氏父子无察,就只能归结于时人对于霍乱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这些悲剧汇集在一起,让他认识到重订是书的重要性,并坚定了决心。所以他写道:“良朋爱女,同病同日而亡,斯重订之役,尤不可已矣!”[8]149种种痛心的经历,令王孟英坚定信念,潜心发挥其医学造诣,最终造就了《重订霍乱论》这一不朽的著作。
三、浴火而生:《重订霍乱论》的产生和价值
在探讨《重订霍乱论》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王孟英撰写《霍乱论》时的情形。据《霍乱论》卷下所言:“丁酉(1837)八、九月间,吾杭盛行霍乱转筋之证。”[13]卷下第3 叶王孟英撰写《霍乱论》,最直接原因是为辨明痧证中的吊脚痧,与霍乱的关系,他认为“吊脚痧即霍乱之剧而转筋者”。这一观点,在当代已被学界所接受①余新忠曾经指出,清代嘉庆、道光年以降,(现代医学中的)霍乱常常被称为“吊脚痧”。所据当即是王孟英之论。。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吊脚痧的性质,并因“古书未载”而痛感“治无善法”。王孟英辨明两者实为一事,从而为治疗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并创制燃照汤、蚕矢汤等方药。也因此,《霍乱论》被评为“铸古镕今,阐经斥异”,是“补偏救弊之书”(《霍乱论·张洵序》)。
《霍乱论》完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为海丰张鸿(柳吟)校订,由王孟英的同乡王仲安刻印完成。咸丰元年(1851),又由杨素园(照藜)与《王氏医案》10 卷合刻于吟香书屋,今二者并存。内容上,《霍乱论》共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分为“例言”“总义”“热证治例”“寒证治例”4 门,引《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经,以及刘完素、张凤逵、张路玉、郭右陶等后世医者讨论中与霍乱相关的证治条文,王孟英于其下进行阐释和解读,提出观点。下卷分为“引释古案九则”“附录俚案十则”“列方”3门,“列方”门附有“外治转筋方”。前两门中分别载有罗谦甫、汪石山、叶天士等人及王孟英自己的治疗验案;后一门中所载则包括五苓散、白虎汤、人参白虎汤等经方验方,也包括刮法、刺法、灸法等外治方法。总体来说,比较专门,但也较为简单,更类似于后世在瘟疫中流行的急救“小册子”。
时隔20 余年,王孟英决定重订《霍乱论》一书。经考,具体开始重订的时间是在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初旬,《自序》中提及的完成日期是“壬戌闰月丙午”,即闰八月二十六日。虽然重订工作总共历时不足1 个月,但内容上进行了大幅的增加和修订。
从内容上看,《重订霍乱论》对《霍乱论》有所承继,但更多的是修正与增补。先看修正的方面,如在《霍乱论·总义》引《伤寒论》“又云,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13]5一条,为论述霍乱之证治,归于“总义”门中,所处位置似不甚妥当。《重订霍乱论·病情篇》则将此条归入“寒证”下,则更为清楚。再如上文已论述较多的对瘟疫发病时节问题,著作《霍乱论》时,王孟英所见该病多发于夏秋季节,曾从运气的角度,提出“每发于夏秋之间者,正以湿土司气而从化热耳”[13]5。而在同治元年,王孟英却在三月即见到霍乱患者,于是在关于运气的讨论中,他修改原来的观点为:“故太阴所至,不必泥定司天在泉而论也。”[8]121
相对来看,增补的内容就较为分散了。如《重订霍乱论》卷二“治法篇”,虽部分医方和外治法内容承自《霍乱论》,但相比之下,《霍乱论》所载治法只是简单罗列于卷下医案之后,未单独成篇。而《重订霍乱论》中,所载包括伐毛、取嚏、刮法、焠法、刺法、搨洗、熨灸、侦探、策应、纪律、守险等节,是按治疗顺序进行排列的,自“伐毛”至“守险”,成为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增补的内容还包括《重订霍乱论》卷三“梦影”一节和卷四整篇。“梦影”中所载,均是王孟英的诊疗医案,但其中有大量医理的阐发,上文所引其对霍乱病因病机和发病时节的认识等,均是出自其中。既往研究者往往因其是医案而未加重视,其实不妥。《重订霍乱论》卷四《药方篇》,论述霍乱相关证治中主要使用的药物70 余种,是王孟英用药经验的总结。其后所载霍乱治疗方药,也比《霍乱论》所载更为充实,方论按语也有新的增加。此外,内容上的扩充,主要还包括卷一每节内都新增加了按语,前冠以“雄按”,或“按”“又按”字样。这些按语是对所引既往诸家论述的申论,或进一步发挥,是王孟英完善霍乱诊疗理论最集中的体现。如对于霍乱病位表里的问题,王孟英引徐大椿“此霍乱是伤寒变证”之说,又引张路玉“霍乱吐利,由饮食所伤”之说,按曰:“霍乱……但既有发热头痛,身疼恶寒之表证,则治法必当兼理其表,此仲圣主五苓散之义也。然表证之可兼者,不独寒也,如吸受温热风暑之邪者,皆能兼见表证。”[8]115首先对《伤寒论》中霍乱用五苓散作了辨析;其次也阐明霍乱所兼表邪,不独寒邪,也包括温热暑邪等,为后续论述霍乱热证作铺垫。
另外,《重订霍乱论》在征引他人论述上,也增加了不少内容。如除《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原病式》《治暑全书》《痧胀玉衡》等医书及刘守真、张凤逵、尤在泾、张路玉、郭右陶、王晋三等名医医论外,尚引有《医彻》《病源》《治法汇》《医通》《补亡论》《医说》《脉学联珠》《疫疹一得》《外台》等医书及徐洄溪、叶天士、薛一瓢、王清任、杨素园等名医医论。值得注意的是,其所引医书中,有一条出自金簠斋《转筋证治》,位于《病情篇·总义》之末。作:“此证重者,立时脉伏,乃邪闭而气道不宣,勿轻信庸工,为脉绝不救也。”[8]116这也是目前可查到金簠斋《转筋证治》唯一留存的内容。
综上可见,《重订霍乱论》是对《霍乱论》一书的重订,但增补内容甚至大于《霍乱论》原书内容,即便是原有篇幅下的条目也有许多改动。故《重订霍乱论》虽说是“重订”,但更可称得上是“新著”。或者《霍乱论》还只是一部救急的小册子,而《重订霍乱论》已是一部论述霍乱的专著。
最后,再对《重订霍乱论》的刊刻传播的情况略作梳理。如所周知,由于费用的高昂,明清时期医者的著作,多是赖为官或为商者资助才能刊印出版。即使是医名噪于一时的王孟英,也不能例外。他早期的著作,资助出版的就有杨照藜、汪曰祯、陈坤、蒋寅昉、张柳吟、周光远等人[14]。《重订霍乱论》的刊印,也是在王孟英多位朋友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如在著作工作开始之初,就有“吴县华君丽云”,将“家藏下岩青花石一片”赠与王孟英。华丽云今无考,其所赠青花石是彩石中的精品,又称“珐琅彩”,十分名贵。而《重订霍乱论》的刊刻,则是赖镇海陈亨(春泉)崇本堂的资助。《重订霍乱论》有陈亨同治二年(1863)五月所作的跋,可知其事。又《随息居饮食谱》张保冲题辞载:“且《饮食谱》一书,闻历伯符方伯已刻于鄂垣,今陈君又刊于沪,而《重订霍乱论》诸稿同志者,亦将梓以寿世。”[8]168可知陈亨是先刊刻了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一书,后又刊刻了《重订霍乱论》。至于参与《重订霍乱论》校订的“诸稿同志者”,据是书各卷首题名,则有吕庆能(淞舟)、林植梅(癯仙)两人,两人均为甬上(今宁波市)人。其后,《重订霍乱论》一书刊刻不绝,清末以前计有光绪六年(1880)四明吴氏刻本、光绪六年(1880)节略刻本、光绪十一年(1885)群玉斋刻本、光绪十一年(1885)福州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文光斋刻本等20 余种刻本、石印本。
王孟英的著作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方面是因为王孟英对治疗霍乱的思考得到了历史实践的检验,后人得其遗惠。从《瘟疫霍乱答问》中谓“王孟英《霍乱论》力辟辛热之非,可称暗室一灯”[15]等语便可得知。又光绪二十八年(1902)卫生子所撰的《翻刻〈重订霍乱论〉缘起》中,也说道:“遍搜坊间,霍乱书苦无善本,惟王梦隐此书,分别寒热,审因用法,相证处方,绝不偏执,尚为可法。”[16]评论虽高,而此书实当。另一方面也表明,晚清时期霍乱的戕害始终未绝,而系统论述霍乱的著作却不多,所以王孟英此书才会被不断刊刻重提。这一点现代医史学者已经较为熟悉,毋庸赘言。
客观地看,王孟英为后人留下的对霍乱的认识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的《重订霍乱论》并非全无瑕疵。如对于霍乱病因病机的考察,王孟英虽论述霍乱所表现出的寒性症状实为真热假寒,不过仍是借《伤寒论》兼病之说,委曲求全。后世医家,其中有完全抛弃伤寒旧说,认为霍乱纯为热证者,便攻击王孟英之说模棱两可。此外,战乱时期剧烈的人口流动、物资的匮乏、医者群体能力参差不齐等等因素,都不是一部《重订霍乱论》所能解决的现实问题。当然,咸、同年间的惨祸,本身就是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叠加出现的结果,作为一名医者,王孟英的贡献与局限都不可能、也不必要承受全部的历史重担。
另外,王孟英还有一些不易为人察觉、却又非常重要的贡献。如前所述,明末医家吴又可提出疠气学说,自成一家,是我国历史上对瘟疫认识的一大丰碑。不过,囿于现实,这样的描述尚显玄虚。时隔两个多世纪,王孟英的观察更加具体化了,如他说:“故疫之流行,必在人烟繁萃之区,盖人气最热。”[8]147这已经点明了瘟疫与城市人口密集之间的关系,也让他创造性地提出“守险”之说。如“霍乱时行,须守险以杜侵扰,霍乱得愈,尤宜守险以防再来”[8]132,守险即预防。《重订霍乱论》中,王孟英从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到个人日常养生防护,共例举14 条预防瘟疫的方法①有学者将王孟英所提出的“守险”,归为环境医学思想和方法,亦不无道理。但考虑到当时的瘟疫背景,似从公共卫生防御体制建设角度考虑更为合适。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前揭申红玲、沈伯雄《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环境医学思想研究》等文。。平心而论,这些观察与思考,总体上属于“方向性”的思考,较为笼统宏观,不涉及具体的建设层面。不过,我们也不必就此对前人过于苛责。一方面来看,近现代的公共卫生建设,是晚清国门大开以来欧风美雨浸润的产物,在我国传统帝制时代并不存在类似的政治职能设计,何况如同下水管网、民用自来水或是检疫制度等事务的诞生,在与晚清同时代的西欧北美也只不过刚刚进入公众生活;另一方面,进行近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调动相当可观的社会资源,包括在当时(相当于19 世纪中后期)先进的人才与技术,这都不是身为一介布衣的王孟英所能掌控的②王孟英本人也萌发出苍茫无力的痛感,他说“非吾侪仰屋而谈者,可以指挥而行也”,并且更多地冀希望于“其有卧龙之才者,出而拨乱反正,以至中和,则天地位,万物育,化日舒长,更何疫疠之有哉”。。因此,当王孟英在医学专业以外,以从业者的身份提出类似于“公共卫生近代化”的问题,本身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历史中,大规模的疫病与战乱总是给普通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然而杰出的医者也往往因痛入骨髓的精研深思,使得诸多里程碑式的医学著作跨世而出。东汉末年的张仲景、金元之际的李东垣、明清易代的吴又可莫不如是,咸同年间的王孟英也侧身其列。不过,王孟英笔下微露的公共卫生建设思想萌芽,在此前历朝历代从未存在实现的可能。而到了19 世纪后半叶,西学东渐已然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潮流,为空想转变为现实提供了全新的基础,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