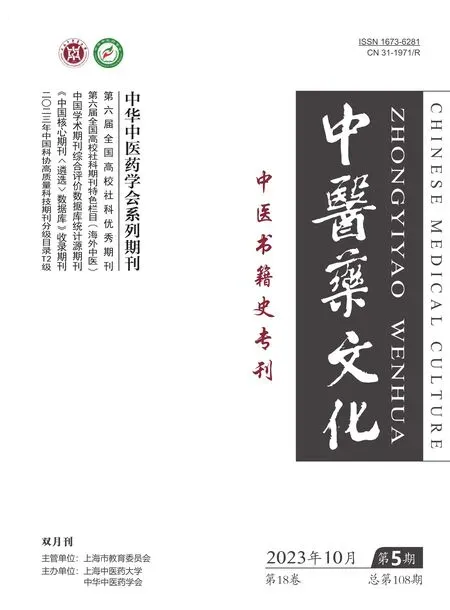中医书籍史研究刍议
杨东方,陈一凡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029)
中国传统医学源远流长,医籍浩如烟海,2007 年出版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著录成书于1949 年以前的医籍(不含法医、兽医类著作)就有13 455 种。对医籍的研究,学术界利用传统文献学方法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更多的是把目光聚焦于目录梳理、版本考证、异文辨析、价值评定等方面,忽视了医籍本身的生产、传布、流通等环节,以及医籍在读者世界中如何被阅读、接受,承载的知识与技术如何被选择、应用,同时对医籍与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互动关系亦重视不足。20 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书籍史研究则在上述方面可资中医学界借鉴。
目前,关于书籍史研究,学术界虽有不同认识,但一般认为其以书籍为中心,旨在全面考察书籍创作、制作、流通、接受收藏、流传等“生命周期”全过程,以及相关参与者、影响因素等内容[1]。相较于西方书籍史研究更注重印刷书籍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有学者指出,我国的“书籍”尚可追溯至印刷术产生以前更为久远的时代;同时,欧美与我国书籍诞生背景及其中参与者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并不能将其理论与方法简单地移植至我国的研究中来[2]。
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从我国书籍特点出发,在医学书籍史领域开展断代或个别医籍的研究,如针对《千金方》等唐宋方书的流变过程[3-4],金元时期北方医家李杲医籍及其学术思想的南传方式[5],明代涉医日用类书的成书、流传与阅读[6],清末报刊杂志中“卫生”书籍广告中蕴含的消费、阅读与政治文化[7],近代传染病书籍中反映的知识观念与社会变迁[8]等话题进行探索。也有学者提出,可从阅读史的视角深入挖掘中医稿抄本中所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等多元内涵[9],皆为我国中医书籍史的研究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可能的方法。有鉴于当前尚缺乏对中医书籍史的系统论述,而医籍“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又各具独特价值,均可作为视角单独考察,故现分而述之。
一、创作有因,知人而论
创作涉及面极广,就作者而言,由于所处时代、区域、身份、学识等各方面的差异,书籍的创作会呈现出不同风貌。譬如清代医家与汉学家的注释类医籍就有很大区别。医家重实用,不屑于文字的考证、训释。清代张志聪注释《素问》就提出:“注中惟求经义通明,不尚训诂详切。”[10]37其注《四气调神大论》“不施则名木多死”曰:“不施则名木多死,盖木为万物之始生也。”[11]在张氏看来,“名木”不影响经义的通明,故不加训释。汉学家胡澍则有不同思考,他认为“名木”常被误解,需要认真考辨。其在《素问校义》[12]中广泛援引经史百家中“名山”“名川”“名都”“名器”“名鱼”之用例,归纳出“名”有“大”意,释“名木”为“大木”,与张志聪的“不尚训诂详切”形成了鲜明对比。
鉴于创作情况复杂,故在研究中要综合考虑,评价才能切中肯綮,否则即为无的放矢。如批评胡澍的考证过于烦琐、不够简明、不切实用、于临床无益,或批评张志聪的训释空疏、不厚重,均属未联系作者身份的片面之言。汉学家本就强调无证不信、实事求是,求证讲究广征博引;而医家则以临床效果为最大追求,即使医籍中的字词训释有误,但如若不影响临床效果,也不为失。日本考证派大家丹波元坚有言:“训诂虽不精,而施之于疾病必有实效者,乃为得经旨矣。”[13]其父丹波元简虽然也认为“文字训释,非医家可深研”,但又提出:“、温温、剂颈、擗地之类,不究其义,于临证施治之际,不能无疑滞,故细检查考,多方引证。”[14]可见与临证有关的重要字词仍需认真考释,其言值得效法。
除作者身份外,创作目的等医籍创作中的其他方面也值得考究。四库馆臣曾批评明代黄承昊的《折肱漫录》“其论专主于补益,未免一偏”。对此,程永培有不同认识:“黄履素,前明万历丙辰进士,幼而赋质虚弱,年至七十余岁,自云药品十尝四五,则一生无日不在病中矣!有妄投峻剂,为医误者,有调理不善,而自误者,历验亲切,遂著《折肱漫录》一书,一则曰养神篇,一则曰养形篇,一则曰医药篇,其意是惕病者之鉴戒,原非为医家立说也。”[15]应当说,程永培的评价更为公允、到位。再如,方书类医籍数量惊人,几乎占了古医籍总数的六分之一[16],其中多有为生活于深山僻壤、求医困难的民众而编纂者。危急之际,民众“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即为这类书籍的价值。至于批评这些著作“不察起病之本”,未能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及陈陈相因、未加创新等,则属欲加之罪。
二、抄刻凭人,变化丛生
创作之后书籍将投入生产制作,一般呈现为抄本、印本等形式。写本时代,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刻本时代,抄写也是重要方式。但在抄写过程中,往往带来文本的变动,一方面是无意的误抄,另一方面则是有意的增删。特别是先秦两汉时代,“文本的公共性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个体性的作者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17],其文本的流动性更大。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就云:“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于是,作品在抄写过程中逐渐衍化出不同风貌,《神农本草经》就是如此。对此,陶弘景《本草序》有叙述:“旧说皆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于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但后多更修饰之尔。”这也导致作者、卷帙等著录的差异。如《隋书·经籍志》著录为:“《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又《神农本草经》八卷。《梁》有《神农本草》五卷,《神农本草属物》二卷,《神农明堂图》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神农本草,三卷。”《唐书·艺文志》著录为:“《神农本草》三卷。又《陶弘景集注神农本草》七卷。又《雷公集撰神农本草》四卷。”因其系历代累积而成,依据最终定型本判定“其作者、真伪或时代”十分困难,甚至“没有那么重要”[18],故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层积过程的考察上。对于著作权清晰的作品,也常在抄写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文本,譬如《伤寒论》就有唐本、淳化本等不同。至于那些不易收藏或流通的民间抄本更是如此,因抄写主要出于个人需求,与印本更侧重于满足社会需求大有不同[19]。亦即是说,抄本一直存在着文本的流动性问题,值得作为书籍史与阅读史的研究对象认真考察。
印本主要满足社会需求,文本基本定型化,一般不存在文本流动性问题,但刊刻过程及其相关参与者仍值得关注。其中,刻工就尚未引起中医医史文献学者足够的关注,实际上他们对医籍的质量、传播等皆有一定影响。如晚清民国期间的著名刻工陶子麟(又名子林),湖北黄冈人,设刻书肆于武昌,以姓名为店号,擅长摹刻古本,所摹刻的宋元善本几可乱真。卢前《书林别话》云:“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有黄冈陶子林……为一时所称。”[20]他为杨守敬刊刻的《脉经》、为刘世珩刊刻的《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为柯逢时刊刻的《活幼心书》《本草衍义》等医籍都是公认的善本。特别是他在战火之中保存了武昌医馆整理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小儿药证直诀》书稿及萧延平整理的《本草述》刻板,为三书的最终出版做出了突出贡献。前两书的情况,萧延平在《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序》里有详细说明:“是书乃柯巽庵中丞创办武昌医馆时出以相示……适晤梓人陶子麟,询及前事,陶告以是书正拟开雕,而武昌义起,幸当时与《钱氏小儿科》一并藏之笥箧,携往沪上,未经散佚,因以原书归余。”后一本书的情况,萧延章《刘蠡园先生本草述跋》有叙述,当初萧耀南请萧延平校梓此书,惜“杀青甫讫而两人相继下世,梨枣高悬,三都纸閟,刻板藏于梓人陶子麟家”[21]。而后,在萧延平之弟萧延章的推动下,书籍顺利出版。
当然,有些医籍未能出版也跟陶子林存在一定的关系。譬如柯逢时一直期望刊刻《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两种大部头医籍,当得知杭州丁氏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钞本在南京,柯逢时给缪荃孙信函中说“或即饬陶匠派人来宁写样”,但陶子林事务繁忙,根本无力刊刻那么多医书。对此,柯逢时抱怨道:“(陶子林)管事太杂,不能应手。甚矣,办事之难也。”[22]因此,《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最终也未能出版。再如《黄帝内经明堂》,杨守敬原计划为汪康年刊刻此书,汪康年“本意是打算编撰一套丛书,名曰《振绮堂丛书》”“但是,时移世改而意变,乃根据自己的新想法,把其中起初拟出的某些书籍抽换了,《悉昙字记》《黄帝内经明堂》《帝范》应该就是被抽换掉了的”[23]。书板藏在陶子林处,后罗振玉曾想将这三种收入《国学丛刊》。杨守敬致罗振玉信函云:“足下欲买之,即恳以洋银兑付(缘近日需款甚急),其板片由陶子林汇交为便。”[24]但直至民国四年(1915)杨守敬去世,罗振玉一直未收到书板,原因不详。
不仅仅是陶子林这样的名家,即使不知名的刻工对医籍也颇有影响。如宋代舒州刻工就因个人原因,随意更改了《太平圣惠方》中药物的分量等。《夷坚丙志》卷十二《舒州刻工》载:“绍兴十六年,淮南转运司《刊太平圣惠方》板,分其半于舒州。”又云:“蕲州周亮,建州叶浚、杨通,福州郑英,庐州李胜……此五人尤耆酒懒惰,急于板成,将字书点画多及药味分两随意更改以误人。”王明清《投辖录·舒州刊匠》亦云:“淮西路漕司下诸州分开《圣惠方》,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钱不以时得,不胜忿躁,凡用药物,故意令误,不如本分。”官刻书籍尚且如此,坊刻本的刊刻过程更不受监督,也愈加值得关注。
三、缃帙缥囊,入手有道
制作好的书籍就进入流通环节,主要有馈赠与贩卖两种方式。私人之间的馈赠,有出于个人交谊者,如丹波元简从其弟、佐伯侯高标手中获得了“见赠”的《丹方鉴源》《黄帝灵枢集注》《玄珠密语》等医书;也有出于报恩者,如丹波元德因治愈同僚村田长菴先生的背疽,而获得村田氏所藏的《素问集注》《灵枢集注》[25]。当然,为了得到馈赠,有时还得主动索求。比如,方孝孺就替亲友请郑叔度帮忙索求《格致余论》《丹溪医按》两书:“敝亲陈仲夷善医而好学,闻戴原礼先生摹印得《丹溪医按》及《格致余论》,意欲求之,烦兄转索一本。”[26]除了私人馈赠,还有慈善行为的赠送,尤以方书为多,很多序跋均有记载。例如,顾海洲序言:“《小蓬仙馆方抄妇科》一书……与夫疾痛之隐,有不肯为外人道者,而医家临症又仅凭切脉,故往往予影响疑似之间执方而试,岂有把握?乌能立奏奇功耶?诚不若是书之为愈也。余质之名家,确切不讹,勉集梓费,印送流传。”[27]3935小斋氏跋云:“予承乏鳌江,公余之暇,检拾书笥,得友人持赠长沙翁兰畦廉访重刊越中钱氏《胎产秘书》,为胎前、产后、临产三门。翻阅之余,觉其条分缕析,统括精微,诚为产科宝鉴,遂印刷五十部,分送邑之海滨,俾产症者得有准绳,可以按方拯救。”在社会看来,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故还劝人刷印:“望乐善君子转相劝勉,刷印施送天下……其功德更无量矣。”[27]3947
私人馈赠一般是单册,公益赠送面向社会,更有助于书籍的流通,但跟贩卖相比仍有劣势。裘吉生论述清代汪朴斋《评注产科心法》时就谈道:“其书素为慈善家印送,以致爱阅者反少购处。”[28]一部书籍如果不进入市场,则很难满足社会的需求。鲍廷博就指出,因为程永培本《苏沈良方》“不列坊肆”,故“无以餍四方之求”[29]。《疹科类编》序言中也提道:“自此书一出,人隋珠,家卞璧。然未付坊刻,传世甚少。”[30]《医经句读·自序》更言:“顾自兵焚之后,古本经籍,坊肆罕见,无怪乎今之医者无所折中。”[31]而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即使官刻有时也得调整。比如,宋代元祐三年(1088),鉴于“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故“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32]。
一般医生主要通过市场渠道获得医书。唐棉村《伤寒百证歌序》就云:“近世习医,仅有借径于俚师,问津于坊刻耳。”但市场也是双刃剑,作伪现象随处可见。丹波元简曾在《医賸·妄改书名》中言:“汪颖著《食物本草》而改为《东垣食物本草》,王永辅著《惠济方》而改为《简选袖珍方》,艾存英著《如宜方》而改为《回生捷录》,李东璧作《脉学》而改为张孔受《脉便》,程云鹏著《慈幼筏》而改为张介宾《慈幼新书》,陈司成著《霉疮秘录》而附之于窦梦麟《疮疡全书》。凡此类不一而足,皆使人眩惑。乃因书估欲易售耳。”[33]因此,考察医籍的流通方式及其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也颇具意义。
四、横看成岭,侧看成峰
一部医籍只有被阅读、被接受,其价值方得以彰显。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由于思想认识、价值取向等原因,往往对医籍进行一种个性化的接受,即所谓的读者再创造。即使师徒之间,观点也不尽相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的结束源于朱震亨的批评,即四库馆臣所言“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朱震亨的弟子戴原礼却喜《局方》之方,以至于有人发出“《和剂局方》丹溪《发挥》辨之详矣,戴原礼乃丹溪高弟,今观其所著《证治要诀方论》,皆祖《局方》,何也”[34]417的疑问。朱丹溪因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看到了“据证检方,即方用药”的不良风气,而戴原礼则看重《局方》中药方的价值。对此,精通医学的俞弁阐述道:“丹溪但辨其用药者误耳,非方之罪也。血虚证,不宜用香燥之剂;痿痹证,不可混作风治。亦何尝屏弃之乎?今人遂以《局方》例不可用,或者有宜北不宜南之说,殊不知《内经》治寒以热,治热以寒,微者逆之,甚者从之,权变得宜,消息以为治要。可限以南北之方,而无寒热之异哉!原礼盖得丹溪之心法者,其有取于《局方》,非苟然也。”[34]417
朱震亨、戴原礼师徒对《和剂局方》的不同态度代表了对医籍不同知识的选择。有时对整部医籍的接受也会截然相反。如《苏沈良方》,四库馆臣评价甚高:“史称括于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今所传括《梦溪笔谈》,末为‘药议’一卷,于形状、性味、真伪、同异辨别尤精。轼杂著时言医理,于是事亦颇究心。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四库馆臣为士大夫,对于苏轼、沈括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医家往往有不同认识,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就将《苏沈良方》比作唐宋集诗。对此,俞弁解释:“盖言不能诗者之集诗,犹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诗之不善,止不过费纸而已,不致误人。一方之不善,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噫!后之集方书者尚慎之哉!”[34]418
一个区域、一个时代往往盛行一种风气,这就导致很多书籍的接受呈现出因时、因地而异的特点。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主要盛行于宋金元时期的南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自宋、金以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行于南。”又云:“《局方》盛行于金元。”清代医家章虚谷也意识到医籍的接受与时代、地域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在《医门棒喝》中云:“如明张景岳,亦由平日阅历所见,立论主于扶阳。既称‘全书’,乃又肆议河间、丹溪为非,则不自知其偏也……景岳与河间、丹溪相去各百数年,其时气化,其地风土或各不同,不可相非也。又如张子和,所治多藜藿中人,故其议论以汗吐下为妙法。薛立斋为太医,所治多商粱中人,故其方案多和平温补,以缓治见功。可知各由其阅历不同而论说遂异。”[35]可见医籍或优或劣,在读者世界中常呈现出迥异的看法,尚需结合时空、境遇等因素客观评价其褒贬之得失。
五、牙签玉轴,流转万千
一部书从创作到接受,似乎已完成其使命,实而还有一个流传与否的问题。上古时期强调医学的秘授,《黄帝内经》有“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的记载,长桑君授给扁鹊禁方时也有“毋泄”的要求。这种秘授秘藏的观念一直沿袭到后世,在专科类医籍中更为常见。和尼赤《活幼心书·决证诗赋·序》言:“然板行于天下,人得而有之者,往往大方脉之书为多。彼为小儿者每以专科自名,或私得一方,即祖子孙相传,世享其利,他人万金不愿授也,其肯与天下后世公共之哉?”[36]事实正是如此。台北图书馆所藏旧钞本《幼科折衷》二卷,为明代秦昌遇所撰,其两则题记均可证明秘藏观念。第一则题记为:“《幼科杂症》二本,又痧、痘症汇齐总钉,切不可借亲友骗去即抄,连此原本必不肯还,切嘱切嘱!康熙五十五年桂月内苏州杨文蔚亲笔。”这只是叮嘱,而第二则题记则是诅咒:“谨防偷去,如做情借去,男盗女娼。”[37]
“小儿者每以专科自名”之言也表明,这是专科的普遍特点。儿科如此,余者亦然。如伤科典籍《劳氏家宝》中“劳天池公家宝原叙”也表明了秘传的要求:“余少游江湖,遇一异人,业精此症,讲之甚明,上骱有术,接骨有法。余侍奉如父,随行一世不惮辛劳,方得传授,试之无不效验如神,以为子孙保身济世之至宝。今将原伤骨骱论方,著之于书,后世子孙一字不可轻露,当宜谨慎珍藏,毋违我之嘱。”先是回顾获得秘技的艰难过程,进而提出“后世子孙一字不可轻露”的要求。为了达到“谨慎珍藏”“一字不可轻露”的目的,被传授者往往需要盟誓。《劳氏家宝》还有展平的一段话:“劳氏祖传秘书,得之不易,论列诸方,神效非凡,所当视为无价之宝,受传者坚嘱,当守秘密,不可一字轻露,曾以名誉为质焉。”[38]甚至是立毒誓。郑瀚《重楼玉钥续编·自叙》载,喉科名家黄明生之所以不愿意轻易传授其术,就因为曾立下毒誓,其言:“予非吝而不传,实有因耳。昔授受时,曾立不传之誓,违之则主乏嗣,既诫于前,何可背于后耶?”[39]“违之则主乏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可谓最恶毒的誓言,而轻传者“无嗣而殁”的记载又加大了誓言的威慑力。秘藏传统及其对医籍流传的影响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另外,很多藏书家历经艰辛搜集了大量的医书,为何搜集、从何搜集、如何利用等也值得考察。
同时,因秘传及天灾人祸等原因,医籍散佚严重,裘沛然《中国医籍大辞典》著录亡佚医籍4 700 余种[40],实际数字可能还远大于此。《隋书·经籍志》著录医籍256 部,4 500 余卷,现存的不足10 部,数十卷而已,由此可见一斑。亡佚者中又有很多历史上重要的医籍,如唐代规定“诸医、针生,各分经受业。医生习《甲乙》《脉经》《本草》,兼习《张仲景》《小品》《集验》等方;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41],其中《本草》《小品》《集验》《明堂》《流注》《偃侧》《赤乌神针》等官方医学教材都已散佚。因此,医籍秘藏的传统与其亡佚的具体过程都需要认真梳理。
部分散佚医籍的残篇遗文有幸散存于它书,学术界尚能进行辑复。譬如,历代医家利用《证类本草》等辑复《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等,四库馆臣利用《永乐大典》辑复《脚气治法总要》《旅舍备要方》等,日本学者利用《医方类聚》辑复《五藏论》《食医心鉴》等,诸多亡佚医籍的部分内容得以重见天日。然而,辑佚过程复杂,个人的功力及散见材料的多寡都会影响辑佚的成效,甚至有时因识见不广导致出现误辑,即辑录并未亡佚的书籍。比如,四库馆臣辑复《苏沈良方》,负责统筹安排的是纪晓岚,具体操作的是王嘉曾。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云:“此书世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收其全部。余领书局时,属王史亭排纂成帙。”[42]307该本后作为聚珍版丛书之一影响甚大,即鲍廷博所说的“会朝廷诏颁内殿聚珍版本于各直省,于是其书复大显于世”[43]。但实际该书并未亡佚,只不过传本较少。从原本存世而言,辑本《苏沈良方》的价值不大。但从该书的传播而言,却很有意义。如辑本的校勘者蔡葛山就曾受益于此书:“吾校四库书,坐讹字夺俸者数矣,惟一事深得校书力。吾一幼孙,偶吞铁钉,医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日渐弱。后校《苏沈良方》,见有小儿吞铁物方,云剥新炭皮研为末,调粥三碗,与小儿食,其铁自下。依方试之,果炭屑裹铁钉而出。”[42]307
在医籍流传研究中,还要关注异域的流传。就医籍在日本的流传而言,贡献卓越者甚多,著名的学问僧圆尔辨圆(1202—1280)即为杰出代表之一。1235 年(南宋端平二年,日本嘉祯元年),圆尔辨圆入宋求法,1241 年(南宋淳祐元年,日本仁治二年)回日,携回了内外典数千卷,藏于京都普门院的书库,自己编纂了《三教典籍目录》,惜已散佚。其法孙大道一以(1305—1370)据之编写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传世。该目按照千字文排列,医籍主要见于“玉”“出”“昆”“冈”字。具体涉及以下医籍[44]:
“玉”字:《王氏本草单方》①宋王俣硕父撰《编类本草单方》三十五卷,已佚。《直斋书录解题》:“《本草单方》三十五卷。工部侍郎宛丘王俣硕父撰。取《本草》诸药条下所载单方,以门类编之,凡四千二百有六方。”10 册、《十便方》②即南宋郭坦《十便良方》,四十卷,又作《备全古今十便方》《新编近时十便良方》等。8 册、《大观本草》《局方》③即《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存。1 册、《活人书》④即宋朱肱《南阳活人书》,二十卷,存。2 册、《易简方》1 册、《王叔和脉诀》1 册、《通真子脉诀》①即宋刘元宾《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三卷。1 册;
“出”字:《和剂方》5 册、《图注本草》②即宋刘信甫校正《新编证类图注本草》,四十二卷。9 册、《本草节要》③宋庄绰撰,三卷,已佚。1 册、《素问经》10 册、《明堂图经》④唐甄权等校订,已佚。2 册、《本草节文》⑤即宋陈日行《本草经注节文》,已佚。3 册、《易简》1 册;
“昆”字:《魏氏家藏方》⑥宋魏岘撰,十卷。6 册、《指迷方》⑦即《全生指迷方》,十卷,宋王贶撰;原书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厘为四卷。2 册、《十便方》8 册、《本事方》⑧即《普济本事方》,宋许叔微撰。4 册、《单方》10 册;
“冈”字:《五脏秘旨》1 册、《十便方》8 册、《枕中方》⑨《摄养枕中方》,一卷,唐孙思邈撰。8 册、《要穴抄》1 册、《药抄》1 册、《明堂图》⑩唐甄权等校订,已佚。1 卷、《指迷方》5 册、《消渴饮水方》1 册、《家藏秘方》(散册)、《杂杂方》《外境治方》2 册。
圆尔辨圆带回的这些医书原本大都散佚,仅有宋版《魏氏家藏方》存世,上有圆尔辨圆亲笔手录的和歌一首,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45-46]。但通过抄录、刊刻等方式,除了《王氏本草单方》等少数医书外,大部分医书都流传下来,如《易简方》《通真子脉诀》《魏氏家藏方》等医籍后都在中国国内失传,因日本有存,得以回归;《十便方》等医书国内只有残本传世,日本所传版本有补遗价值,这对于古代医籍的保存具有重要意义。
在汉籍东传的过程中,商人们也发挥了极大作用。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等著作对此研究颇多。医籍方面,因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8)之前相关资料匮乏,故对商人们的贡献了解不多。至江户时期,日本与中国通过长崎港进行贸易,并详细登录中国船舶所载图书,以此为基础产生了诸多目录,《分类舶载书目》就是其中之一⑪《分类舶载书目》:日本中村亮编,日本文化七年(1810)九月成书(据中村亮跋),二册,内阁文库藏,收入大庭脩编著《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吹田市: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日本昭和四十七年)。中村亮先根据长崎奉行所的记录编纂了《舶载书目通览》,后又抽出书名、作者,按类编成此书。。该目录记载了元禄十二年(1699)至宝历年间(1751—1764)中国书籍输入日本的情况,其中医籍竟有100 余部,且多不止一个版本。现在,部分医籍国内失传,又从日本回流。如《行笈验方》(又名《王肖乾先生行笈验方》),“该书不见于中国古代书目著录。日本《医籍考》著录此书,并录王梦吉之序。今惟日本内阁文库存该书两种,一为康熙八年序刊本,一为江户抄本”[47]。《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康熙八年(1669)序刊本影印出版。这种回流往往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开始常仅回流一两部,秘藏于私人之手,流传极稀,直至刊印出版,化身千万,才保证了该书在国内的广泛流传,意味着回流工作的彻底成功。在回流过程中,多有医家的推动、东瀛访书者的购求,更有商人、书坊的贩卖等,可参见拙作《晚清民国期间〈圣济总录〉的回流》一文[48]。
六、多因交织,乃成书史
在医籍创作、制作、流通、接受以及收藏流传等各个环节,都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政治层面,如宋代帝王重视医学,宋太宗更是颁布了“访求医书诏”,指出“许诣阙进纳,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偿之,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49]。虽然征求的是前代医书,但对时人创作医书也是极大的激励,以至于宋代医书极速增加,《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医书比《新唐书·艺文志》多四五倍。又如嘉靖帝尚医,很多人“假方书希进”,也促使了诸多医籍的诞生。被弹劾罢官的赵继宗,“仰国恩之未报”,想进献医书,因担心浩繁,“有渎圣览”,乃“略举诸证精要”,成书《儒医精要》,“具本封进”“蒙圣旨:书送太医院,礼部知道”[10]752。除了刺激医书的编纂,也能促使一些人下定习医、撰写医书的决心。在嘉靖皇帝刊刻医书的鼓舞下,科举失利的李时珍发现编纂医书也能流芳百世,解除“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焦虑感,进而习医编纂出《本草纲目》,他在进献的遗表中还不忘宫廷刻书对他的影响:“世宗肃皇帝既刻《医方选要》,又刻《卫生易简》,蔼仁政仁声于率土之远。”[50]有激励,就有阻碍。如道光二年,皇帝下令禁止针灸,导致针灸著作大幅度减少。创作如此,流传亦然。《开元广济方》《贞元集要广利方》因是皇帝敕编,故能利用各种方式传播。《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四“榜示《广济方》敕”云:“朕顷者所撰《广济方》……宜命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板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颁《广利方》敕”云:“朕以听政之暇,思及黎元……勒成五卷,名曰《贞元集要广利方》,宜付所司,即颁下州府闾阎之内,咸使闻知。”而《本草品汇精要》因主持编纂的太医院院判刘文泰误致明孝宗猝死而被列为禁书,至康熙年间校正增补,直到民国时期方才经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51]。《吕晚村先生评医贯》的著者吕留良则因雍正年间受曾静案牵连,而被定为“大逆”之罪,此书亦被列作禁书,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二十二日《贵州巡抚图思德奏续经查获奉禁各种书籍解京销毁折》(附清单一)中“附应禁书目清单……逆犯吕留良《医贯》五部”(宫中朱批奏折)[52-53],皆为医籍受政治因素影响而被留置、禁毁之例。
经济方面,如所处时代经济繁荣,民众具备购书能力,就会促进医籍的创作与制作,甚至连书坊主也主动编纂医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明中后期就是如此,此期间涌现出一批热衷于编刻医籍的书坊主。其一,洪楩,明嘉靖时钱塘人,字子美,室名清平山堂,有刻书坊“清平山堂”,辑刊《医药摄生类八种》,除《医学权舆》《寿亲养老新书》外,其他如《食治养老方》等医籍均为洪楩编纂。其二,余象斗,约生活于嘉靖末年至崇祯初年,字仰止,号三台山人,室名三台馆,福建建阳县人,出身于刻书世家。其书坊名“双峰堂”,刊刻了《袁氏痘疹丛书》5 卷、聂尚恒《奇效医述》2 卷等医学著作,亲自编选《必用医学须知》丛书,子目4 种:《叔和王先生脉诀袖中金》1 卷、《李东垣药性赋袖中金》2 卷、《校讹诸症辨疑袖中金》4 卷、《校正大字医方捷径袖中金》3 卷。其三,胡文焕,生卒年不详,字德甫、德父,号全庵,又号抱琴居士,浙江钱塘人,著名刻书家,在杭州设“文会堂”,在南京设“思莼馆”,编有《医家萃览》《寿养丛书》等医学丛书,另编刊的《格致丛书》子目中也包含了18 种医书,其中由胡氏自行编纂者有《素问心得》《灵枢心得》《医学要数》《类修要诀》《香奁润色》《应急良方》《养生食忌》等。其四,吴勉学,万历年间人,字肖愚,安徽歙县人,刻书坊名“师古斋”,曾校刻《河间六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等,编纂有《痘疹大全》《师古斋汇聚简便单方》等,另又校对汪机《新刻汪先生家藏医学原理》13 卷。其五,胡正言(1584—1674),字曰从,室名十竹斋,原籍新安,寄寓南京,嗜好藏书和刻书,创“饾版”和“拱花”,和兄长胡正心开设“十竹斋”书坊,编选有《十竹斋刊袖珍本医书》,另编纂《订补简易备验方》16 卷。其六,汪昂与汪淇。汪昂(1615—1694 年前后),字讱庵,安徽休宁人,有书坊“延喜堂”。汪淇,生卒年不详,字憺漪,又字右之,浙江钱塘人,有书坊“蜩寄”。两人合办书坊“还读斋”,出版了李梴《医学入门》、龚廷贤《万病回春》等医籍,又都曾编纂医籍。
思想文化对医籍的形成也具有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王学盛行,医家则多以己见著书;从明末清初开始,朴学兴起,医家又多重考古,这从伤寒类著作的撰著中便能看出。明代的《伤寒六书》《伤寒全生集》《伤寒补天石》《伤寒五法》等都有好抒己见的特点。《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伤寒补天石》就指出:“明代诸医家,于伤寒一科,藉口于今昔异宜,往往好抒己见,自陶华《六书》开其风气。维城自名其书曰《补天石》,在发明仲景未尽之意,原与墨守古训以作注解者宗旨不同。其人在当时亦有医名,不免徇俗,于仲景学说非有深研切究,故于仲景言外时有引申,而于仲景本义未必尽能实彻。”到了清代,医家开始注重仲景医书原貌的问题,认为王叔和、成无己改变了书籍原貌,评价甚低,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伤寒错简派著作。如果著作尊崇成无己,则往往不被社会认可,如《张卿子伤寒论》。张卿子的弟子张志聪名声显著,所撰诸书盛行于世,而《张卿子伤寒论》一书却流传不广。对此,《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分析:“清初伤寒诸书,踵方氏、喻氏之后,多以攻王叔和为能事,即张志聪《集注》本亦与成氏原编立异。是书以成氏说为主,以诸家之说为辅,并采兼收,尚无门户之见。然亦因未独立一帜,故后来治仲景者少称道及之。”[54]因此,影响医籍“生命周期”各环节的诸多因素都值得进一步挖掘。
总之,书籍史的研究理路可开阔医籍研究者的视野,为其研究视角的选择提供启示,而对医籍“生命周期”全过程开展长时段的观察,或以不同环节为切入点,将同类型、同时期、同地域乃至同一位医家的医籍进行有机整合与研究,可期逐步形成以医籍为中心、多学科交叉、多时空兼容的动态交互网络,实现医籍研究成果的深化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