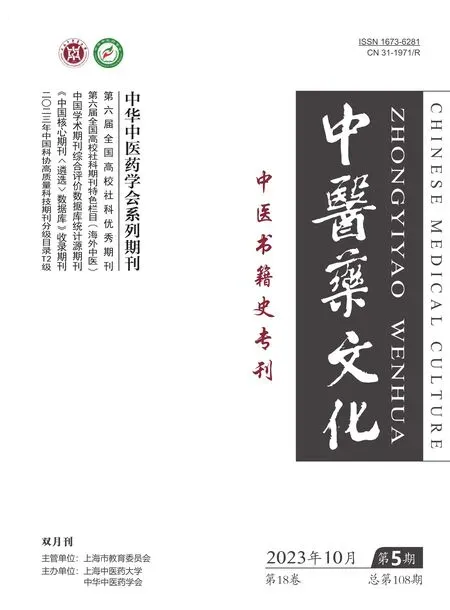以书籍史研究中的传播视角探析中医古籍生产的创作者
温佳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中医古籍浩如烟海,流传至今的仍有上万种,是中医药知识保存、记录、交流、传承和传播的根基和载体。随着医籍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其本身的生产、传布、流通等环节,以及中医书籍在读者世界中如何被阅读、接受,其知识如何被选择、应用等涉及书籍史、出版史、接受史的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从传播的角度探讨书籍史也逐渐渗透到中医古籍研究领域,并为医籍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引和方向。目前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即生产、流通和传播效果[1]。古籍的生产是传布、流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根据李致忠的《中国古代书籍史话》记载,创作是书籍生产流程中的首要环节,另外还包括生产材料和生产方法[2]。
书籍的生产材料基本经历了从甲骨、青铜器、石片、玉片、缣帛、简牍到纸张的过程,生产方法则是先后出现了刀刻、铸造、笔写、印制等。生产方法是随着生产材料的变化而变化的,逐渐形成了在纸张上进行书写或刻印的固定模式,中医古籍亦是按此脉络进行生产。创作作为首要环节,不仅反映着创作者的阶级意识,也反映着相应的时代气息,还体现了不同创作者的不同倾向和不同风格。创作者一般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2]。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根据创作任务的不同还涉及不同的主体,主要包括内容创作者和实物创作者,二者既可以独立存在,亦可以统一。因此本文将中医古籍生产过程中的创作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探析。
一、内容创作者
中医古籍的创作也符合上述规律,其内容创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业者,或者是由这些人员组成的团体。由于医学学习途径的多样性,即包括自学、家传、师承、科班等多种形式,从业者的阶级构成就相对复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除君主外,主要是士、农、工、商,均有可能成为医学的从业者并撰著医籍,因此可以从不同创作者的角度,窥见其阶级意识和时代特点。
(一)统治阶级创作者
统治阶级创作者即以君主及王室贵族为代表,除个人兴趣外,其对医学的态度可以影响整个医学史的发展,其所进行的医籍创作也多可反映统治阶层对于医学的需求,通过医籍的创作及传播达到巩固政权、完善医疗制度、促进医疗教育等目的,具有内容范围广、应用性强的特点,成果多为整理性质的本草著作或方书。如北宋时期大力推行科举,重文抑武,形成了文化繁荣、科技昌盛的时代,医学也得到大力发展。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徽宗等多位皇帝喜好医学,其中较为突出的为宋徽宗。宋徽宗赵佶改革医官制度、兴办官药局、完善国家慈善制度、重视医学教育、主持修订并亲自编撰医书,其所实行的政策与相关医著,均成为两宋时期医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影响了后世医学理论、教育等发展。他曾自撰《圣济经》,该书不仅是北宋时期医学理论性著作的集大成者,还作为宋代学校课试命题蓝本,诏颁全国。赵佶还组织多位医官编辑《政和圣济总录》,并命医官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将官药局所收集的制剂处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后经多次增补,颁布全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法典”,其中所载方剂一直沿用至今并为临床常用[3]。朱橚为明太祖第五子,明初战乱始平,百姓生活贫苦,经常有以树皮草根为食者,此时朱橚作为统治阶层的代表,在个人意愿及时代需求的背景下,组织人员对这些草本的食用经验和方法进行总结,撰成《救荒本草》,此书在当时不仅用于救荒,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民心、巩固了政权,而且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影响深远,仅明清时期就出现了10 余部以救荒为主题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植物学,并在世界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另外,他也组织编著了《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等多部医学作品。
医籍内容创作者中的创作团体,也多是在统治者的号召或允准下进行活动,这些医书无论是质量还是影响力,在中医学发展中优于大部分个人著作,因此也可进一步印证统治阶级作为内容创作的参与者,具有应用性强、传播性广、影响力大的相对优势。除上述提到的《圣济总录》《和剂局方》外,《唐本草》即是在苏敬上疏后,唐高宗指派长孙无忌、李勣、许敬宗等22 人与苏敬一起集体修订,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药典。北宋宋仁宗设立校正医书局,是校订和刻印医药书籍的机构,在医书的创作环节中既是内容创作者也是实物创作者,包括了由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孙奇、孙兆等人组成的团体,校注了《素问》《甲乙经》《本草图经》《脉经》《伤寒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论》《外台秘要》《金匮要略经》等多部医书。宋以前医籍多辗转手抄,讹误较多,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校正和刊行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更直接影响后世医书整理工作的质量。元代《饮膳正要》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食物营养和食物疗效的专著,也是以饮膳太医忽思慧为主进行集体创作的作品。明清时期直接以太医院署名撰著医书,如明代《太医院增补医方捷径》《太医院增补青囊药性赋直解》等。清代吴谦为太医院院判,在乾隆皇帝的要求下,领衔编纂《医宗金鉴》,除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还有纂修官14 人,副纂修官12 人,效官、誊录官等共70 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
(二)综合体创作者
古人多认为“医儒相通”,产生了诸多如“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因学以明医,籍医以明学”的思想,因此在读书者所在的“士”与普通医者所在的“工”的阶层中出现了某种特殊的联系,这种“士”“工”阶级结合的综合体成为了古代医籍创作的集中人群。“士”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的社会地位较受尊崇,多指官员和以读书考取功名之人。但若单以早期古代医生而言,其职业属性则属于“工”的行列,自周代起就将包括医生在内具有技艺的劳动者统称为“工”,将医术高明的医生尊称为“上工”或“良工”。《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曰:“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唐代《师说》亦言:“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5]在历史的推进中,医生本身的属性也在从“工”逐渐演化成“士”“工”的综合体。隋唐以前,医学教育不甚完善,从事医疗的途径多为自学、家传或师承,其基本方法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难免会混入靠偏方、巫术、个人经验来治疗疾病的人员,所以早期单纯的医疗从事者是很难进行医籍创作的。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系统接受医学教育的医生比重增大,且从北宋推行儒生学医的政策之后,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很多医生都是儒学之士。这也是医籍内容创作者与早期单纯的医生区别之处,医籍的内容创作不是仅有医疗经验就可以完成,还需要文字的撰写和组织能力,相较于普通医生,具有较长时间学习经验的知识分子则更具优势。因此,医籍内容创作者的主要构成便是“士”与“工”结合的综合体,其中包括了因各种原因、以各种途径涉足中医领域的人员,创作内容多样,包括从理论到临床的方方面面,其著作不仅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医学发展,还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综合体中包括担任非医学职务,但在医籍创作中有突出成就的官员。其官职多为朝廷委派,与撰著医书无较大关系,其医学经历及撰著原因均与个人立志学医相关。如撰著《伤寒杂病论》的张仲景,为长沙太守,通过序言便可知其创作背景。东汉时期,战乱频仍,灾疫连年,在医学上已有《黄帝内经》《难经》等理论的积累,其本人也“宿尚方术”。隋唐时期《黄帝内经太素》的撰者杨上善,曾先后任隋太医侍御、唐太子文学。宋金元时期朱肱为进士,曾任奉议郎,在其考取进士之后,无意为官,此时虽已定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但缺乏系统性研究,朱氏着眼《伤寒论》21 年,撰有《南阳活人书》流传后世,但在他著医书之后,当时朝廷大兴医学,朱氏还因此被征为医学博士,并于政和四年负责朝廷医药政令。王好古以进士官至所在赵州专门负责教育事宜的教授,兼提举管内医学,他博通经史,究心医药,尤好经方,曾同李杲学医于张元素,一生著述可考者达20 余种,其内容不仅体现了张、李之学术精华,也体现了金元时期医学争鸣的特点,代表著作有《医垒元戒》《阴证略例》《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明清时期医学发展更体现专科性并突出整理的特点,王纶于明弘治间事任礼部郎中,后又于正德间迁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政绩颇著,又因父病同时留心医药,曾著《本草集要》《明医杂著》《医论问答》等。
除此之外,历代官员中均有专门负责医事活动的人员,医事职官是我国古代职官的组成部分,曾设置如疾医、医师、太常、太医令、太医博士、药医师、医生、医士、郎中、大夫、院史等多种职务,他们也是医籍创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以明清时期为多。此类创作者兼具官员和医师两种身份,互有促进作用,因医术精而为官,为官后更精湛医技,撰著内容因与从事职业相关度较大,一般突出医家个人所长,并主要以临证类居多。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无论是撰述《脉经》,还是整理《伤寒杂病论》,均为医籍的创作和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宋代翰林医学赵自化曾撰《四时养颐录》为献,宋真宗改名为《调膳摄生图》。王惟一也在宋仁宗时期曾任尚药御,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至明清时期,医学的发展进入到一总结阶段,医著数量剧增,其中不乏医官所著。赵可琢等人对明代御医所著文献进行了考察,得知明代御医中有97 位医家所著医学文献237 部,存世有99 部,亡佚有138 部[6]。如薛己曾官至太医院院判,内外妇儿兼通,自撰及校订书目共27 部,包括《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等。龚廷贤亦为太医院太医,有医书24 部,包括《济世全书》《寿世保元》《万病回春》《小儿推拿秘旨》等。李时珍也供职太医院,有医书10 余部。徐春甫也曾在太医院任职,有《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幼幼汇集》等著作问世,其中以《古今医统》影响最大,清代御医的数量更多,但存在记录不清的缺点。清代《太医院志》中对太医院院使的记录都不甚全面,根据《中医人名大辞典》的记载,清代太医院官员共126 人[7-8];据《清宫医案研究》记录,参与皇室诊疗的便有391 人,目前对于清代从事医官的实际人数并无具体统计,对相关著作也难以查清,但有诸多代表人物可体现其医籍内容创造者的身份。如尤乘曾任太医院御前侍直,著有《寿世青编》《勿药须知》《脏腑性鉴》《喉科秘书》《食治秘方》,并对其老师李士材所撰的《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篆》进行增补。乾隆御医黄元御,医术精湛,医学理论著述甚多,仅记于《清史稿》的就有医书11 种,计98 卷,凡数十万言。另如任锡庚、徐大椿、汪必昌、陈莲舫等均为御医。
另外,还有诸多无心政途或弃举从医之读书人也属于综合体之列,完成了医籍的内容创作。如三国时期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9],仍撰《青囊书》(已佚)。东汉皇甫谧虽出生名门,但自幼不求上进,在40 岁左右患风痹证后才悉心学医,并撰集《针灸甲乙经》。在此时期,针灸学逐渐从草药医学中独立出来,而《针灸甲乙经》为针灸学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充分体现了皇甫谧的学术成就与特点,如他提出的“针刺先神后气”理论,强调个性化治疗等。东晋葛洪为江南士族,受到个人性格和当时盛行的道教中遁世思想的影响,有意归隐山林,多著书立说,有《肘后备急方》传于世,其著作中也多体现葛洪受到的道教影响,如《肘后备急方》中消毒所用方“太乙流金方……中庭烧,温病人亦烧熏之”“虎头杀鬼方……每月初一、十五半夜院内烧一丸”[10]。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金元四大家”,其中除张从正随父学医外,其他三人均自少时便崇文好读,但均因家中亲人患疾便留心或专事医药。刘完素自幼好医,后因痛失母命而以医为志,一生著述较多,如《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内经运气要旨论》《伤寒直格》等;李杲出生书香门第,母亲患病杂治而死,于是立志学医,其著述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等;朱丹溪怀惠民之心,并因母亲有疾,由儒转医,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等。而这种无意功名、弃举从医的情况在明清时期并不少见,其原因一般有无意功名、科举失利、遭逢变故、家学渊源、困于生计等[11]。据相关资料统计,仅明一代,现有医书传于世的医家中,有明确文献记载其为中途弃举从医者多达数10 人,其中包括李时珍、龚廷贤、汪机、吴崑、邹志夔、李守钦、李中梓、万全、缪希雍、李梴等明代著名的医学大家。这些人在医学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且均有著作,但他们起初都是从事举业,后来弃举从医,成为著名的医学家[12]。因科举屡试不中而弃儒业医的有汪昂、陈士铎、王子接、沈金鳌、余霖等。遭逢变故的如《医学传灯》陈歧在著述中言:“固为温饱之计,而删述纂修之功,固当亦有责焉。”[13]说明自己因幼年丧父又遭天灾,无法投入举业的无奈。世代业医的民间医家如张志聪、张倬、李用粹、钱潢、叶天士、陶承熹、汪文绮、顾世澄、魏之琇、王孟英等[11]。上述医家均有著作行于世,虽未从严格意义上进入仕途,但其中部分人员成为了以医术为技的太医,也体现了“士”“工”结合的特点,如《明史·方伎传》中就明确记载凌云弃举从医后,通过医学成就又得以在太医院就职,“凌云,字汉章,归安人。为诸生,弃去。北游泰山,古庙前遇病人,气垂绝,云嗟叹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针其左股,立苏,曰:‘此人毒气内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云针术,治疾无不效……孝宗闻云名,召至京,命太医官出铜人,蔽以衣而试之,所刺无不中,乃授御医。年七十七,卒于家。子孙传其术,海内称针法者,曰归安凌氏”[14],并著有《经学会宗》《子午流注图说》《流注辨惑》等针灸著作。
二、实物创作者
中医古籍可根据其实物的呈现分为非印刷类和印刷类。非印刷类主要是手写(绘)的书籍,又有简牍、缣帛、卷轴、金石拓本及写本、抄本、稿本等。印刷类的分类就相对复杂,根据刻写的时代、地区、刻者等有不同的类别[15]。
非印刷类的医籍实物创作者或为作者本人、创作团体,或为从事此项工作的工匠。如古人用简牍时,如有错讹,即以刀削之,故古时的读书人及政客常常随身带着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因刀笔并用,历代的文职官员也就被称作“刀笔吏”。稿抄本中既有亲自撰写者,也有雇人抄录者,雇人者多为藏书家,被雇佣之人多以抄书谋生,称为“书佣”。清道光间管庭芬,精目录学,喜抄书,所抄书籍百部有余,其中便有徐缄《急痧方诊》。另如上海图书馆所藏《医方抄》,书封题“明范子宣卧云山房抄本医方,壬辰残腊收于四明,黄裳”。可查见此本即系卧云山房本,为范大澈(即题记中所称范子)雇人所抄[16]。稿本中由作者亲自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订的为清稿本。如清代儒医陆懋修现存于世的医著中,稿抄本医籍多达数十种,包括《仲景方汇录》《病家须知》《灵素约囊》等,多为自己手录。
印刷类中医古籍有木刻本、活字印刷本、石印本、油印本、铅印本和影印本,其中以木刻本最为典型,其实物创作者在狭义上一般指刻工。在广义上,实物创作者除刻工外,应该还包括主持雕版、印刷的组织者或出资者,他们并非都像刻工一样亲自雕刻印刷医籍,但在实物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学界多根据出版机构的不同对木刻本进行分类,包括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而从版本学的角度进行分类,相关研究内容丰富详尽,就不再赘述,以下仅从广义的实物创作主体的角度总结中医古籍创作者的特点。
一为有明确记载刻工为医籍的实物创作者,这种记录为古籍文献研究的完善与考证提供了重要线索。刻工既指刻字工艺,也指专门从事雕版的人员,本文中提到刻工均为刻字工人。自雕版之业兴盛起,刻工多记其姓名于书口或序跋后,留下了除书籍内容之外更多的材料,而这些关于刻工的记录被统称为“刻工题名资料”,对于其研究则包括其姓名、里籍、刻字风格及习惯等方面。近年来,对于刻工的研究逐渐在古籍研究工作中受到重视,成为补充版本信息、鉴定版本、厘定内容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刻工作为诸多书籍的实物创作者,也是书籍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反映刻书业的发展、地域变迁、异地流动等内容,是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目前刻工资料的记载可参考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书后附刻工人名及刻书铺号的索引,充分体现了对刻工的重视[17]。翟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收录刻工信息万余条[18],另有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19]、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全录》[20]、郑幸《清代刻工与版刻字体》[21]等工具书可查询刻工信息。在中医古籍研究中参考刻工信息进行考证者亦有实例,如在《伤寒要旨药方》的版本考证中,对于其为宋本还是明本存在争议,但钱超尘先生在《〈伤寒要旨药方〉考注》中介绍,通过原书的版式,刻工黄宪、毛用的考证,黄丕烈的3 篇跋语,并与《洪氏集验方》对比研读,可断定“其为宋板,固无疑意”。黄宪和毛用皆为南宋乾道间当涂地区刻字工人,且二人共同参与《伤寒要旨药方》和《洪氏集验方》的刊刻工作[22],因此可将二书进行刻印风格及内容的对比。这就提示虽然刻工对自己工作书籍的内容并无明显影响,但从目前记载来看,若某些刻工参与中医古籍的刊刻工作较多,或刊刻书籍较多,将相关书籍进行对比研究亦有一定的价值。如南宋刻字工人李昱,参加刻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及《外台秘要方》,明代嘉靖间刻字工人黄鑪,刻印过《新刊仁斋直指附遗方论》《伤寒类书活人总括》《小儿方论》[18]223。
二为内容创作者与实物创作者的统一。如明代朱橚所撰《救荒本草》《普济方》均由本人组织于开封刻印。《救荒本草》原书两卷,永乐四年于开封刻印,书中明确记载了“永乐四年岁次丙戌秋八月”,但目前此版本已亡佚[23]。《普济方》现有明永乐周藩刻本,而以上均属于官刻本中明代特有的藩府刻本。南宋陈文中善治小儿痘疹,刻印自撰的《陈氏小儿病原方论》。明代方有执刻印自撰的《伤寒论条辨》《本草抄》《或问》《痉书》,在《伤寒论条辨》明万历二十一年初刻本中可见方有执撰“刻伤寒论条辨序”,其中言明“吾将刻之。刻之以待。庶乎斯道之世其绵有在”[24],且末尾有牌记“古歙灵山大方家梓”。金陵本《本草纲目》是其最早版本,也是迄今唯一由李氏家族自编的版本。另如明代皇甫中刻印自撰的《明医指掌图》、张三锡刻印自撰的《医学六要》。
三为本人有医著,另组织校刻他人著述者。如南宋刘信甫,本人业医,著有《活人事证药方》,校刻了寇宗奭所撰《新编证类图注本草》。元朝尚从善,自撰《本草元命苞》《伤寒纪玄妙用集》,序刻吴恕《伤寒活人指掌图》。明代王肯堂,生平好读书,尤精于医,其室名郁冈斋,不仅刊刻自己的医学论著如《六科证治准绳》,还刻印了诸多他人医著或其他类型著作,如孙思邈大字本《千金翼方》、鲁伯嗣《婴童百问》、龚信《古今医鉴》等。明代张时彻,刻印自撰的《摄生众妙方》及自辑的《急救良方》,还刻印多部他人的诗集文选,如张邦奇《张文定公文选》、陈束《陈后冈诗集》等。明代蒋仪刻印自撰的《药镜》,并刻印王肯堂《医镜》。清代徐大椿刻印自撰的《医贯砭》《兰台轨范》《医学源流论》《伤寒类方》等,于雍正十年还刻印尤怡的《金匮心典》。清代王琦自辑《医林指月》,其所创立的书室宝笏楼除刻印本人著述外,还刻印清代汤右曾《怀清堂集》。结合上述两个特点,刊刻医籍的太医院又成为了特殊的实物创作主体,既可以达到与内容创作的统一,又作为出版机构刊刻医家的著作。除前文提到创作的医籍外,刊刻医籍如南宋太医局本《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元太医院刊《御药院方》、明成化九年太医院刻本的《奇效良方》、明嘉靖四十一年太医院刊本《卫生易简方》、明万历二年太医院校刻本的《补要袖珍小儿方论》。
四为以喜好医书刊刻为特点的个人或书室(书房、书斋)。明代曹卓曾任抚州推官,擢刑部郎,所组织刻印书籍多为医学书目,如《医学纲目》《古本东垣十书》《医说》等。明彭端吾为万历年间进士,组织刻印医籍多为痘疹专书,包括《痘疹全书》《痘疹世医心法》《痘疹碎金赋》。明杨道会在万历间刻印李时珍多部著作,如《本草纲目》《濒湖脉学》《脉诀考证》《奇经八脉考》。
宋代环溪书院,至元代犹存,其主要刻印书籍均为医籍,如《仁斋直指方论》《小儿方论》《伤寒类书活人总括》《证类本草》等。目前记载元代古林书堂所刻之书也为医籍且以内经类居多,如《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新刊黄帝灵枢经》《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五运六气诸图附论》《黄帝内经素问遗篇》等。种德堂为元代熊氏书坊名,至明代其后裔熊宗立、熊瑷、熊冲宇等仍沿用其名。其中熊宗立好讲阴阳医卜之术,因此组织刻印自己及他人的多部医籍,如《类编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新刊袖珍方大全》《伤寒运气全书》《外科精要》《新刊补注释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伤寒论著》《原医药性赋》等40 余种。元代广勤书堂一直到明嘉靖间犹存,刻印医书甚多,如王叔和《新刊王氏脉经》、何若愚《子午流注针经》、陈师文《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图经本草》、王执中《针灸资生经》、胡广等编《新刊性理大全》等。明代藩王朱厚煜赵府居敬堂,作为藩刻本的代表,组织刻印的医书有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王冰《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王叔和《王氏脉经》《修真秘要》等。明代刘龙田乔山堂,刻书甚多,包括王纶《明医杂著》《本草集要》、吴恕《新刻图注伤寒活人指掌图》、许叔微《注解伤寒百证歌发微论》、钱文礼《雷正增注伤寒百问歌》等医著近20 部。明吴勉学的师古斋,也将医书刻印作为主要的出版方向之一,且多进行较大规模的丛书刻印,刻印了《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河间六书》《东垣十书》《医学六经》等。清代朱麟书的白鹿书房刻印多部医籍,内容以伤寒类为多,且其中有活字印刷本。如李中梓《伤寒括要》、戈维城《伤寒补天石》、尤怡《伤寒贯珠集》、钱谅臣《伤寒晰疑》、周扬俊《金匮玉函经二注》等。另外还有元刘锦文日新堂、元翠岩精舍、明平政堂、明存德堂、明安正堂、清贞节堂等均刻印了诸多医书。
中医古籍的生产流程可从创作、生产材料和生产方法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生产方法随着生产材料的变化而不断演进,逐渐形成了生产方法主要为书写或刻印,生产材料主要为纸的固定模式。创作作为生产的首要环节,包括内容创作者和实物创作者。从封建社会的阶级角度对于医籍内容的创作者进行分析,有以君主及王室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创作者,由于其多服务于个人兴趣及政治统治的需求,创作内容多为具有整理性质的本草或方书类著作,相对来说具有应用性强、传播性广、影响力大的特点。而医籍内容创作的主体则为体现“士”“工”阶级结合的综合体,其中包括担任非医学职务,但在医籍创作中有突出成就的官员、医官及无心政途或弃举从医之人,此部分创作者在时代背景及个人经历的影响下,创作内容方向广泛,涵盖理论研究及临床治疗。因此从内容创作者的角度便可窥见对后续传播与接受范围的直接影响。医籍实物创作者在非印刷类医籍中,或为作者本人、创作团体,或为从事此项工作的工匠。在印刷类医籍中,刻工及其工作都是必要步骤之一,但其在医籍中的记录和体现并不普遍,所以从广义上也应该包括组织雕版及印刷的主持者或出资者,他们均为医籍的出版与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中医古籍生产流程的研究,尤其是创作环节的分析,相较于传统的文本层面,更强调人物实体和物质实体,可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深度挖掘中医古籍所蕴含的社会生活文化信息,为后续的流通和接受等研究奠定基础,是医学史、文献史、版本史研究的延伸,也是以传播为视角的中医书籍史研究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