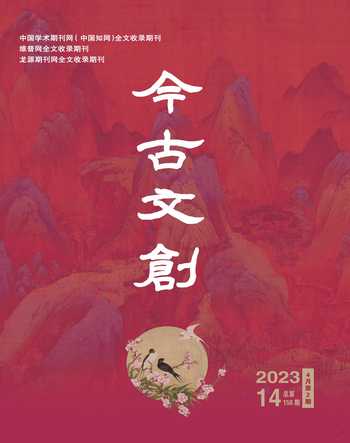论《小妇人》中的疫情书写
【摘要】 瘟疫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扰乱正常生活秩序和经济发展,是人类的巨大难题。疫情期间,以瘟疫、疾病为书写材料或书写主题的文学作品数量可观。猩红热是19世纪不时肆虐美国社会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小妇人》中以猩红热为情节书写,叙述在家庭空间下的真实生活和人性温情,丰富人物形象,促进时代思考。通过奥尔科特对猩红热的书写,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化发展道路的一些思考,启示疫情书写的现实关怀。
【关键词】 疫情书写;《小妇人》;人性温情;现实关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4-000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4.002
瘟疫是人类历史中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它来自大自然,一旦出现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不稳定性和不可知性。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从天而降的疫情给人们带来的恐慌和无助也留在了文学作品中。
就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从《诗经》《山海经》开始便对疫情有所涉及,曹丕与曹植的书信与文章中都有对建安年间的瘟疫的回忆与哀伤,《水浒传》更是以瘟疫开篇。西方文学对疫情书写也不少,如古希腊时期的《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罗密欧与朱丽叶》,20世纪的《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不难看出,瘟疫伴随着人类历史前进而一直存在。
19世纪猩红热在美国北部演变成一种流行病[1],美国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中也有所涉及。目前学界对《小妇人》的解读主要着重于对人物形象和小说主题的分析和阐释,以及对影视改编和翻译作品的思考,对猩红热情节没有过多关注。本文试从《小妇人》的疫情书写出发,细读疫情表达,体悟人性温情,推进时代思考。
一、家庭空间内的疫情表达
奥尔科特在小说的一开始用一种日常的生活的口吻描述了马奇一家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背景——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时期,这是个流血的不安的时代。西方的19世纪是一个以人、以理性、以科学为主的时代,再加上工业革命的不断进步,挑战上帝权威,重视人的能动力量成为命题。这也是个动荡的时代,美國女性自由主义思潮等自由民主的新兴思想冲击着19世纪传统的父权政治:以“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要求女性,希望她们恭顺、温柔、持家。彼时社会认可传统妇女形象,妇女若想使自己的社会地位上升就必须依靠自己的丈夫。作者规避了战争中的矛盾冲突和父权社会的依附色彩,把作品的叙事空间固定在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中,从不同的家庭状况反映社会发展状况。
马奇家的住宅和劳伦斯家的住宅隔着一道篱笆,便是两户人家的差距——简陋老旧的红砖房与精致宏大的宅院。赫梅尔家里更是一贫如洗,光墙裸砖。圣诞夜当天,马奇四姐妹收到圣诞礼物各自欣喜,而赫梅尔一家却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劳伦斯先生还可以送出冰激凌、蛋糕、水果、夹心软糖和鲜花这类“不足挂齿的东西”[2]。这是三个家庭物质层面的差距,也是战争带给不同家庭的影响,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社会阶层断层加剧。
尽管美国的医疗体系日趋完善,19世纪各种传染病在美国白人社会仍然会产生很大影响[1],猩红热作为一种多发于少年儿童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对青少年的影响依旧存在。《小妇人》作为奥尔科特的自传体小说,父亲勃朗生·奥尔科特思想观念超前,对家庭不管不顾,母亲和她承担着家庭重担,她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真实的写作素材。马奇四姐妹梅格、乔、艾美、贝思都是极为普通的女孩,梅格温柔美丽、爱美虚荣,乔大大咧咧、冲动叛逆,艾美自私自大、野心勃勃,贝思善良恬静、胆小怕事,她们性格各异,摩擦不断。贝思在其他姐妹都不愿意出门看望赫梅尔一家时硬撑着头疼悄声出门,她“一向平静的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3],这也为后来猩红热的感染埋下伏笔。乔在知道贝思感染猩红热后不离不弃地守护在床前,梅格帮助汉娜一起打理着整个家,艾美在马奇阿婆家里打磨性子自我反思,贝思最终在医生和乔的照料下痊愈,却被猩红热拖垮了身子,猩红热对生命个体造成了损失。
奥尔科特虽以马奇一家四姐妹为主要描写对象,在猩红热一节中还有调皮不羁的劳瑞、温暖善良的劳伦斯先生、刀子嘴豆腐心的马奇阿婆、清醒细心的汉娜等等,从马奇家、劳伦斯家、马奇阿婆家、赫梅尔家延伸出来的生活图景,一切关于疫情的描写全是日常的书写,一切都随着生活的脚步慢慢前进,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也没有什么起伏转折,为读者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瘟疫的发生都是摊在一个个家庭中的,尽管承担着苦难,生活总要前进。
二、疫情苦难中的人性温情
疫情是一个能够引起人们感伤和共鸣的话题,人们面对瘟疫,有对未知的恐慌,对平静生活的怀念,或是激烈地抗争,或是守望相助,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在告诫着人们,生命并非是一帆风顺或一眼望到尽头的如愿以偿,总是有些坎坷。如若父亲病重,母亲离家是对马奇四姐妹的第一重考验;众人渐渐偷懒,贝思突然感染猩红热是一个更陡的山崖。所以当她们第一次相对独立地面对瘟疫时,梅格、乔和艾美对贝思感染猩红热的不同反应和心理状态暴露了真实的一面。
梅格是传统的家中长女形象,她温柔娇美,担责持家,引导帮助妹妹们成长;虽有些虚荣,但会及时反省,总体来看还是个实打实的周到的长女形象。但她心里其实并不那么乐意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她不是很愿意去照顾病人,在她对赫梅尔一家和对贝思的话语与心理中便可明显探知。只因她是长女,有着对家庭的责任,所以迫使她成为妈妈的好帮手,妹妹的好姐姐等等一系列被他人肯定、认可的社会角色。
乔作为小说中男性特色突出的女性,同样也作为家中与梅格不同的年长的女儿,她的身上有更多的隐忍和责任。尽管是个像男孩一样的存在,风风火火,大大咧咧,乔是作者设定的一个反男权主义的现代思维的女性形象。但从某方面来说,她仍旧没有摆脱世俗的制约,主要还是父亲的期盼。虽然家庭中对父亲的着墨并不多,但是父亲的影响仍旧存在,“在家庭决策中,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将他的利益诉求表述为家庭利益,这是一种隐性的支配与被支配过程”[4],乔可以因为父亲的期盼去改变自己自由散漫的性格,去成为一个真正的小妇人,担起对家庭的责任,不眠不休地守护在贝思床前,去照顾她珍爱的人。
艾美寄人篱下,只能从劳瑞的只言片语中知晓家中的近况,在知道她离开之前有可能得到绿松石戒指,所以分外乖巧听话,事事体贴;她也喜欢织锦缎长裙拖地的沙沙聲,在穿衣镜前搔首弄姿,款款而行。贝思病重,母亲归家,艾美坐在母亲膝前,述说着在马奇阿婆家的种种和自己内心的感受,表明对虚荣和自私的体悟和否定。每个人对生命的体悟都有所不同,疫情只会放大苦难和人性,也会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情与美好。
疫情书写中的苦难与温情在家庭空间内存在,推动情节发展,主人公也在疫情中自我成长。《小妇人》中每个家庭的结构都不太完整。马奇家父亲角色的模糊,赫梅尔家没有一个担当的男性,马奇阿婆终身不嫁,劳伦斯家只有祖孙二人,每个家庭面对疫情所表现的是守望相助。梅格和乔相互依偎,盼望贝思痊愈。艾美被要求送去马奇阿婆家。马奇阿婆收留了艾美,埃丝特给艾美提供了房间,时时祷告,告诉艾美马奇阿婆的一些遗嘱和打算,引得艾美深思。
汉娜是家中的帮手,马奇四姐妹是她看着长大的,所以对于四姐妹的关系更加明晰和通透。她知道梅格和乔的无助,知道随意给马奇太太发电报会带来恐慌,知道艾美自我中心不顾他人的性子会影响到家庭状态,所以她选择不发电报、送走艾美,是个极理智的人。
劳瑞是马奇姐妹的邻居,也是她们的好朋友。当艾美不愿离家而向劳瑞求助时,他劝说艾美,承诺每天都去找她,给她带贝思的消息,带她出去驾车或散步,引她妥协。当贝思的病情恶化时,劳瑞偷偷给马奇太太发电报并送来父亲身体好转的消息,扶着凄楚难抑的乔坐下,抚慰着一颗几近破碎的心。也正是劳瑞的这一“冲动”之举,让马奇太太提早知道了贝思的情况,并在最合适的时候赶了回来。劳伦斯先生和劳瑞在贝思最凶险的时候守着马奇家,也是在无能为力的氛围中一根坚强的支柱。
贝思作为家里最安静的姑娘,性格温柔细腻又容易胡思乱想,喜欢呆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意走出来,可是在逐步的成长中她逐渐变成了为他人着想、行善积德的性子。她愿意为母亲去帮助那些穷困潦倒的家庭,为了照顾病重的婴儿可以一周每天都去赫梅尔家,从而不幸染上了猩红热,在无人愿去照料的时候,她可以忍着头痛无声无息地出门。艾美因贝思感染了猩红热被迫去马奇阿婆家寄住,在马奇阿婆家的这段经历让她为了之前的虚荣和自私感到羞愧,这是她成长经历的一个大转折点。乔是一个冲动的假小子,这也是她第一次耐着性子守候在贝思身边,尽职尽责地照顾着。梅格在初入浮华时,认为金钱对她来说十分重要,她就是因为金钱匮乏才与他人不同,才没有见过富人早已司空见惯的东西,等到经历了磨难之后才惊觉拥有亲情的珍贵和美好。
马奇太太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在临行之前对四个姐妹做了不同的叮嘱,并留下“满怀希望,勤恳做事”作为信条勉励姑娘们,在她们逐渐懈怠下来时,贝思的猩红热让她们被动接受了现实,从而发现她们对母亲的期望做得还很不够,一步一步地做出反思,梅格愿意收起抱怨的性子,乔愿意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只愿贝思能够恢复。在母亲从华盛顿返回之后,艾美在母亲膝前做出自己对虚荣和自私的反思,梅格和乔经历了磨难,倒头安静而平稳地睡下了。此类种种,都是女孩们的成长,正是猩红热情节推动了后续乔与马奇太太关于爱情的讨论,也埋下了贝思病重的伏笔。
奥尔科特用温情笔调将疫情苦难淡化,将对死亡的恐惧、对疫情的未知淡化,在平常的日子里展现家庭和美与人性温情,是普通人对生存的渴望,对疫情的另类抵抗。疫情或许会带走人的生命和健康,让人觉得痛苦不已,但它带不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留下治愈的希望。
三、疫情创伤下的时代思考
对于西方文学中的瘟疫书写,管新福做了一些研究,他提到西方近现代文学中的瘟疫书写“逐渐突破由古希腊文学、基督教神学所建构的神降瘟灾、天神赈灾的叙事模式,具有人本、理性的光辉,开始聚焦于瘟疫源头的科学思考、追溯;认可瘟疫隔离救治和政府管控的作用,进行启蒙和祛魅,强调理性思考和隔离治疗的核心作用,体现了人类理性和医疗技术的进步”[5],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对如何更好地进行疫后民众精神的安抚、救治经验的总结、积聚赈灾勇气等都具有现实意义”[6]。《小妇人》也不例外,奥尔科特受超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哲学探讨”[7]。猩红热的冲击,让梅格与艾美对精神富足的理解更深,认为家庭中的欢笑与安宁比金钱更为重要;乔对家庭成员的存在更为看重,认为家庭的温暖更让人珍惜和流连;贝思是家里最善良安静的存在,默默地向这个家庭和世界播撒自己的爱和无私。四姐妹的人设并不那么完美,但她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反思,不断蜕变,逐渐形成了美好品格,给予人们更多面对疫情的勇气。
《小妇人》不仅从女性独立成长的视角出发,讲述四姐妹如何从爱慕虚荣、躁动不安、自私自利、胆小害羞的小女孩逐步成长为负责周到、认真顾家、奉献自我的小妇人。在这一段成长历程里,既少不了马奇太太的关心与教育的原因,也少不了姑娘们在一段段与亲情、友情、爱情相关的情感中逐渐纾解和治愈自己的过程。劳瑞偷偷给马奇太太发了电报,马奇太太准备连夜赶回。乔听到消息搂着劳瑞不放,这是他带来的好消息,这是一阵明亮的风,是友情带来的幸福。劳瑞调皮地开解乔,逗她再向他扑过来,二人的情愫渐深,已不仅是友谊之情,更是男女之爱,可见劳瑞已经醒悟自己对乔的感情,是爱情带来的幸福。贝思退烧了,梅格和乔在角落紧紧拥抱,正巧,一支白玫瑰在夜里盛开,妈妈也从华盛顿归来,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在马奇家中绽放。贝思在昏睡中醒来,第一眼看到半开的白玫瑰和妈妈的面容,听母亲说故事,这是亲情带来的幸福。《小妇人》从家庭环境出发,书写温情故事,带给人精神层面的安抚与鼓舞。
更有学者从解构主义出发,认为小说背后蕴含着多重符码:“女性需要构建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人们需要重视精神的力量,人们需要探索自立自律生存独立的路径,主流社会需要对文化诉求做出回应”[8],对现有的社会状态用创作做出全新回应,促进时代思考。
四、结语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或是以瘟疫为书写背景,讲述瘟疫流行下人物的生存与死亡,又或是以不同的文学体裁进行疫情书写。还有一些文学作品,疫情在笔下人物的人生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人物成长和情节发展。本文以《小妇人》为启发,认为在对抗和战胜疫情时,也不该忘了疫情下的个体命运,更应该重视受疫情波及的人类群体的心灵重建与认同重构。人们在疫情中主体身份认同的丧失和社会层面心理的失衡怎样去抚慰和平衡,这或许是疫情文学创作者所要努力的方向,也是疫情文学创作所要追逐的重点。
参考文献:
[1]丁见民.传染病与19世纪中期以前北美白人人口的增长[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120-131.
[2]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M].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
[3]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妇人[M].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5.
[4]闫平.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管窥《小妇人》中美格遭受的隐性性别不平等[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 (08):108-109.
[5]管新福.避瘟、祛魅与隔离疗法——西方近现代文学中的瘟疫书写[J].名作欣赏,2020,(22):126-130.
[6]管新福.病毒、隐喻与临床救治: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J].名作欣赏,2020,(16):123-126.
[7]杨美玲.《小妇人》中的超验主义哲学[J].宿州学院学报,2017,32(06):75-77.
[8]刘淑君.《小妇人》中的解构主义及其背后的多重符码[J].今古文创,2020,(15):6-9.
作者简介:
周佳利,女,汉族,福建莆田人,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