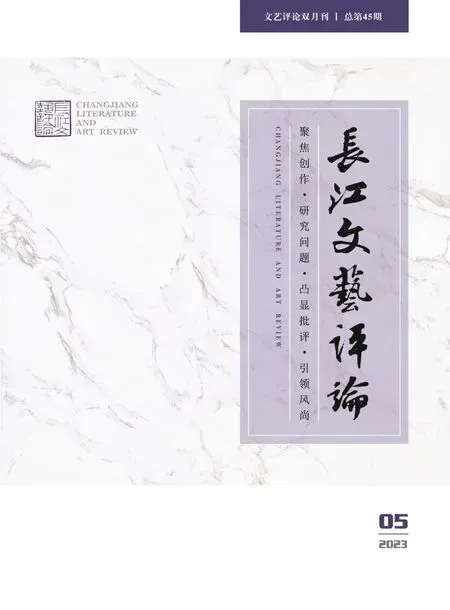刘纲纪先生的学术研究与书画创作
◆范明华
刘纲纪先生1933年出生于贵州省普定县马堡乡号营村,初名长寿,曾用笔名刘荧,1952至195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毕业后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直到2019年去世。他一生致力于美学和美术史论研究,是海内外公认的美学和美术史论大家。同时,在学术研究之余,他也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专业功底和个人风格的书画艺术家。[1]刘纲纪先生的学术研究始于大学时代,早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公开发表了批评前辈学者胡蛮《中国美术史》的文章,并完成了第一本专著《“六法”初步研究》的初稿。[2]而他的书画创作,则源自少年时代的艺术兴趣和专业训练。他曾在中学时代拜当时寓居安顺教授美术的著名画家胡楚渔为师学习书画[3],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美学和美术史论研究及书画创作均有着深刻的影响。刘纲纪先生生前谈及他为什么走上美学研究之路时曾多次说过,他之所以选择美学研究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学时代特别喜欢美术和文学,并且受到胡楚渔和当时鼓励并支持他学习文艺的语文老师、班主任王德文的影响;二是大学时代有幸遇见了朱光潜、宗白华、马采、邓以蛰等美学和美术史论领域的一代宗师,并且特别受到了亦师亦友、师生关系相处十分融洽的两位恩师——宗白华和邓以蛰先生的亲炙。在刘纲纪先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学术与艺术始终相辅相成,未尝须臾分离,这与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和中国传统美学中一直倡导道艺相通的思想传统密不可分的。[4]
一
刘纲纪先生最为人熟知的学术身份是“美学家”,然后是“美术史论家”。但他其实首先是一个哲学家。要了解刘纲纪先生的美学和美术史论观点,必须先了解他的哲学观点。而强调从哲学出发或准确地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去解决美学和美术史论的问题,这既是他的学术主张也是他的研究特色。从大学时代开始,刘纲纪先生就坚信,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美学和美术史论,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既有别于西方传统也有别于中国传统美学和美术史论的新的结论,从而建构出美学和美术史论的新的理论形态。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呢?这是一个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刘纲纪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这是一种与旧唯物主义、尤其是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实践唯物主义。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在《一本用庸俗社会学写成的中国美术史》中,明确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教条化和庸俗化,即把艺术同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直接挂钩或对应。1980年以后,为了在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中批判从自然物质出发解释美的发生的机械唯物主义美学观,同时也为了彻底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看法,他先后写作了《实践本体论》(1988)、《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1989)、《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问题的重新考察》(1996)等一系列哲学文章。[5]这些文章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试图从本体论层面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特质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实践而不是与人无关的“物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社会实践本体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归结为“物质”的看法是一种倒退,是一种排斥人的主体地位、忽视人的实践活动、贬低人的精神作用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6]刘纲纪先生指出,当时学术界流传的、从自然物质出发解释美的发生的观点,实质上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在美学上的体现。只有破除了这种观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二
这种推崇人的实践,反对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既是刘纲纪先生美学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美学代表人物”的学术形象。在美学方面,刘纲纪先生的研究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和中国美学史两个领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领域,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在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美学的基础上,系统发掘和论证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除了参与新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美学思想为基础的美学原理教材即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的编写之外,他还在《美学与哲学》(1984初版、2006新版)、《关于马克思论美》(1980)、《关于美的本质问题》(1983)、《关于“劳动创造了美”》(1982)、《美学十讲》(1981年)、《美学对话》(1983)、《美学纲要》(1988)、《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当代美学问题》(1998)等一系列文章、著作和讲稿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看法,包括重新阐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美”的命题,以及他本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美是人的自由的实现”或“美是基于社会实践的人的自由的感性显现”的新命题,同时还在同时期撰写的《艺术哲学》(1986年、2006年)中,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派美学关于艺术的看法,即从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去解释艺术的本质和发生的看法。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刘纲纪先生试图用“反映”来统摄并解释再现与表现、形式与内容、理性与情感、具象与抽象、艺术美与现实美之间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所说的“反映”既不是排斥实践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被动“反映”,也不等于排斥人的情感、想象、意志等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性的反映”或排斥人的主观创造的、简单的、照相式的“摹写”。相比于哲学美学的研究,刘纲纪先生在中国美学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除了为海内外学术界熟知的两卷本《中国美学史》(1984年、1987年)之外,还有像《刘勰》(1989年)、《周易美学》(1992年)等专著以及大量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论文。其中,《中国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美学史著作,也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即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美学史著作。刘纲纪先生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既有高屋建瓴的哲学思辨,又有深入细致的历史分析,甚至还有字义、句读的分析考证,其内容涵盖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禅宗美学和楚骚美学,涉及的文学艺术门类包括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音乐等在内。刘纲纪先生强调,写中国美学史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史,要从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殊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去看待中国古人的思想,把中国古人的思想放到特殊的社会历史的坐标上去看,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科学的评判。这种看法,实际上也是他所坚持的以实践为本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在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中的一种自然的延展与体现。
三
除了哲学美学和中国美学史研究,刘纲纪先生的另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美术史论。在美术史论研究方面,刘纲纪先生也是海内外公认的名家和大家。他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书法史论尤其是书法美学研究;二是中国绘画史论研究;三是美术原理和西方美术研究。书法史论方面,他出版了《书法美学简论》(1982年)和《书法美》(1995年)两部专著,同时在《中国美学史》以及一些单独的论文中也有对中国书法历史和理论的广泛讨论。他的《书法美学简论》是新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书法美学著作,其中的艺术反映论观点曾引起了关于书法艺术本质的广泛讨论,甚至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误解或误读。刘纲纪先生认为,许多批评者仍然是站在机械反映论的角度来理解他所说的反映论。他认为他作为一个实践唯物主义的坚持者,根本不可能赞同机械的反映论,他讲的“反映”并非机械的摹写,而是指艺术从根本上来讲是来源于人的社会生活。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无可辩驳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后来写《书法美》,他引入了中国古代《周易》美学中的生命观、交感论、古代书论中的比象说以及西方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符号学美学的观点来解释中国书法,比如用交感论及《周易》的符号模拟来解释书法中的心物关系以及书法造型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用符号学美学家苏珊·朗格的“生命形式”或“动力形式”来描述中国书法的结构特征等,虽然对《书法美学简论》中的观点进行了补充、拓展和修正,但他在《书法美学简论》中提出的书法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反映论观点并没有改变。相比于书法史论研究,刘纲纪先生对中国绘画史论的研究更早,成果更多。这包括中国绘画基本理论和元明清三代文人画家倪瓒、文征明、董其昌、龚贤、渐江、黄慎、“四王”的个案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如《“六法”初步研究》《文征明》《“四王”论》《董其昌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倪瓒的美学思想》《渐江与云林》等均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其中关于“六法”的句读和阐释、关于文人画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关于倪瓒“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的思想、关于董其昌和“四王”历史地位的重估等论述均被人反复引用和讨论,也同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经典。除了中国书画史论之外,刘纲纪先生对于一般美术理论以及西方美术也是非常重视的。他曾经写过一部《美术概论》教材,并且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建构一个美术学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解决美术与社会生活、美术与政治等美术学理论中的根本问题。[7]此外他还写过一些讨论西方美术和现代艺术的文章,包括在1979年“星星美展”之后不久发表的《略论“抽象”》和《漫谈西方现代绘画》等文章,[8]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些文章看,他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对西方现代美术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探索给予充分肯定的学者之一。刘纲纪先生做学术研究,非常强调三个原则或方法:一是倡导实事求是;二是主张辩证地对待一切现象和问题;三是强调要有历史的眼光和比较的视野。因此,他虽然喜欢中国美学和中国美术,但对西方美学和西方美术从来就不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9]而他这种做学问的原则和方法,其实也正是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四
刘纲纪先生的美学和美术史论研究,既得力于系统的哲学训练,也得益于对美术尤其是中国书画的兴趣与感悟。他对书画的兴趣从少年到暮年一直未变,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美学和美术史论研究与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鉴赏、分析和批评,是互为表里、相互补充的。他所创作的书画作品,从时间上看,大部分是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而这个年代也正是刘纲纪先生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中国美学、美术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时代。研究与创作,在此逐渐融为一体,理论体系的系统化、精密化与书画技法、境界的老到圆熟互相映衬。
在刘纲纪先生的书画创作中,书法作品的数量多于绘画作品的数量。其书法作品涉及篆、隶、楷、草四体,而以隶、草为多。他的书法创作,从时间上说,与他写作《书法美学简论》和《书法美》等著作有直接的关联。从《书法美学简论》和《书法美》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书法历史的考订与梳理,对历代书家和碑帖的点评与分析,以及他对书法用笔、结构和意境的美学分析。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理论分析的延伸,而他的理论分析,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创作经验的升华。因此,看他的作品,或是看他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刘纲纪先生的隶书作品用笔朴拙,结构舒张,气象浑厚,多得力于汉代隶书,其中可以看到《石门颂》《曹全碑》等名碑用笔的影响,但在重视笔墨意趣这一点上,又有自己的创造。相比之下,刘纲纪先生数量最多且最具艺术个性的书法作品是草书。从《书法美学简论》和《书法美》等著作来看,他对历代草书家的点评与分析也最为精到。据他自己说,唐代的张旭、怀素、明代的祝允明、徐渭等草书大家的作品都对他有影响,但心摹手追又不止于一家一派。从他的创作来看,事实上也是如此。就用笔和结构而论,他的草书作品中,甚至还可以见出隶书的笔意和楷书的结构。刘纲纪先生曾在一次讲课中对初唐书家欧阳询大加赞赏,并告诫喜欢书法的学生如要学习书法不妨多看欧体。欧体楷书重骨气,重神态,尤重结构,是当时南北书风相互融合的典范。我们从刘纲纪先生的草书作品中,也约略可以看出欧体楷书的这个特点。刘纲纪先生的草书,用笔亦枯亦润,亦实亦虚,势如飞动,连绵不断,有古人所谓“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的意趣,但又非常讲究结构和章法。因此,他的草书,险劲与稳重并存,意趣与骨力兼善。其艺术特点,不止于表现在用笔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结构和布局上。一般来说,中国书法中的草书,不难于用笔而难于结构和布局。没有好的结构和布局,则用笔失据,来去无由,以至剑拔弩张而流于狂怪。刘纲纪先生的草书作品,尤其是那些大幅作品,笔迹婉转而又不失矩度,字字放得开而又字字收得拢,这是与他重视结构且精于结构分不开的。
五
与书法作品相比,刘纲纪先生的绘画作品数量较少。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绘画费时多于书法。而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画画,这对于一个伏案写作的学者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就创作的时间经历来看,刘纲纪先生从事绘画创作的时间要早于书法。他早年的艺术教育偏重于绘画,他对艺术的研究也始于绘画。从胡楚渔先生习画时,他主要学习的是具有浙派风格的山水画,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喜欢上倪瓒、黄公望、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王原祁、渐江、龚贤等人的作品,并且基本上都有相关的研究专著或专文问世。刘纲纪先生的绘画作品大多为山水画。他的山水画,有精密严谨的一类,也有粗犷洒脱的一类。前者多建立在对古代作品的研究和赏会基础上,而后者则多为写生稿本的提炼和加工。总的来看,刘纲纪先生的绘画风格,主要源自中国文人山水画的传统。从他写作的有关古代画家的一系列专论和专著来看,他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元明清三代的文人画。但刘纲纪先生的绘画作品仍有自家的面目。传统文人画多受道家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追求萧条淡泊、虚静空灵有如荒天古木般的意境,因而常于意境的表达上无形中传达出“静”与“空”的旨趣。我们看刘纲纪先生的绘画,似乎也有“静”的特点,因为他的作品构图严谨,画面简洁,再加上大面积的留白和极少量的点景人物和屋宇,都容易传达出“静”的感觉。但他的作品也是“动”的。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用笔劲利、用墨深厚、色彩明丽的特点,再加上苍松、红叶、飞瀑等突出的景物构成,也都容易产生出“动”的感觉。用刘纲纪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其实更喜欢儒家刚健中正的精神境界,而且试图在画面中表现出这种境界。在《周易美学》一书中,刘纲纪先生曾对儒家经典《周易》的思想和美学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周易》对天地生生之德的礼赞,对阴阳变化之道的阐发,以及贯穿其整个思想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进取精神,在刘纲纪先生的著作中都有很精彩的美学表达。因此,刘纲纪先生的山水画,虽然借用了传统文人画的某些技法,但他的作品所表现的精神境界和审美境界则具有当下的意义。换句话说,他追求的不是一种超然淡漠的隐逸情调,而是一种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
六
刘纲纪先生的书法与绘画创作,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艺术类别,但其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共通的特点。刘纲纪先生自己说,他的书画不能简单地说是文人的书画,而应当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学者的书画。学者的职业是学术,而学术追求的是严谨。刘纲纪先生的作品,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严谨。这种严谨的作风在书画作品中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用笔,一是结构。用笔的严谨是笔无妄下,行笔有因,作品中见不出不足或多余的笔墨。结构的严谨是布局合理,有章可循,虚实、动静、开合、顺逆互相照应、互相生发。看刘纲纪先生的作品,给人一种非常干净整洁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与他在创作当中特别重视用笔和结构密不可分的。但是,刘纲纪先生的作品除了严谨的一面之外,还有活泼新奇、充满激情的一面。他在《中国美学史》和《书法美》等著作中,对中国美学和书画理论中的“气韵”“骨”“力”“意境”等概念有非常清楚的论述,并且也曾用苏珊·朗格的“动力形式”“情感形式”及《周易》的“刚健中正”与阴阳变化之道来说明中国书法的美,因此,刘纲纪先生在书画作品中试图表现的并不是一种四平八稳的严谨,而是一种充满动态美感和内在张力的平衡。从他的草书和泼墨山水中,可以更为清楚地感受到他所追求的,正是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着力研究过的、谢赫《画品》中所说的“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而在变化中追求统一,在统一中追求变化,并由此达到一种既富有秩序又包含生机、既充满激情又具有高雅格调的艺术境界,则是中国艺术的最高法则。刘纲纪先生的书法与绘画创作,就某一件单独的作品来说,可能会给观者留下许多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但这些作品也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在用笔、结构和意境中所表现出来、可称之为“清刚”“雅正”的美感,这种美感的形成,与刘纲纪先生长期的学养是分不开的,透过这种美感,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即感性地理解作为一个美学家的刘纲纪先生,他对美和艺术的见解。他的书画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他的学术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17—19世纪法国美学主潮》评介
——《巴蜀美学史稿》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