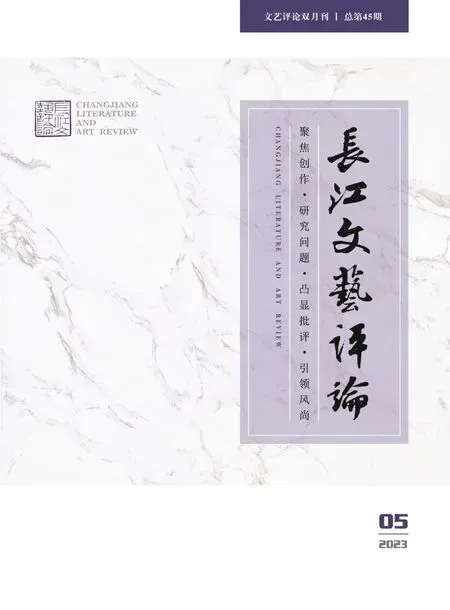献给雪山大地的壮丽史诗
——读杨志军长篇小说《雪山大地》
◆孙 涛
《雪山大地》[1]是杨志军继《藏獒》《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作品之后又一部反映青海高原的精品力作,这既可视为作者四十年文学道路的阶段性总结,也可说是作者长期扎根西部为人民奉献出的又一创作里程碑。小说曾同时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2023年又以高票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近年来在党的文艺政策引领下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这部作品,作者以近60万字的鸿篇巨制全景式展现了现代化建设大潮中青海高原藏族牧区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真情讴歌了一群长期扎根高原、默默奉献的草原建设者形象,以一种纵横捭阖、从容有度的笔触反映了青海高原这块古老大地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为新中国的发展历史留下了一部磅礴壮丽的草原史诗。
一、高原牧区的山乡巨变
《雪山大地》在地域上聚焦青海,时间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小说中频繁提到的沁多县、阿尼玛卿州等地在地理上对应了青海省东南部广大的高原牧区,这是作者生活了近40年的故乡沃地,凝聚了作者的无尽深情。小说中贯穿写到雪域高原上生产、教育、商业、医疗、环保等一系列内容,真实细腻地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后牧区人民在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隐藏在生活表象背后更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化以及精神世界变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以“父亲”走进沁多草原蹲点、住进牧人桑杰家开篇,故事随之徐徐拉开了帷幕。桑杰是个孤儿出身的“塔娃”。所谓“塔娃”,即是草原上的流浪汉、卑贱者,没有帐房居住,没有衣袍暖身,也没有食物来源,只能四处乞讨,干零活、打短工。但尽管生活贫穷,桑杰却有着西部牧人固有的厚道、真诚的品性,在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桑杰一家与父亲一家建立起血脉相通、骨肉相连的真挚情谊,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桑杰因贫苦身份被选中接任角巴担任了沁多公社的主任,从此肩负起了使命和责任,悲苦命运也逐渐转变。因缘际会中,桑杰与原公社主任角巴的女儿卓玛结为夫妻,他的三个子女都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随之他又接连担任畜产站站长、沁多学校校长、沁多贸易董事长,成为第一批在牧区进行商品贸易的生意人,第一批从草原来到城市安家定居的牧人……到桑杰老去的时候,他最初塔娃的身份早已成为历史,所积累的财富高达数千万,完成了一个从传统牧人向现代城市人的蜕变。显然,桑杰这一形象凝聚了作者对高原牧民的美好感情与美好期待,从他身上,我们能够鲜明感受到高原牧民面对生活坚韧不拔的劲头以及面对未来的蓬勃向上的巨大力量。
以桑杰不凡的生命轨迹作为典型个例,作者成功还原出高原牧民“当家作主”这一必然的历史进程。同时,作品还广泛辐射了青海藏区牧民在经济条件、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商品经济等领域发生的沧桑巨变,这不仅体现在具体的人的身上,还体现在具体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比如小说中频繁写到婚礼。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起步期,牧民生活并不富裕,因此即使是沁多草原最有经济实力的角巴德吉嫁女时也不过是准备了糌粑、酥油茶、风干肉等品种不多的食品,父亲当时仅能够拿出一支钢笔作为贺礼献上自己对新人的祝福。改革开放之后,牧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作为第二代的江洋和梅朵的婚礼就显得异常排场与热闹:有彩色的藏袍、花氆氇靴子、蜜蜡的项链、玉石的镯子、绿松石的戒指,酒席上还有鱿鱼和海参,婚礼场景的变迁反映出牧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对未来的信心和期待。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沁多学校从最初只有几十个学生发展到师生上万人、从简陋的教学条件发展成拥有七座五层教学楼的地区名校;沁多医院由原本的一个小小卫生所发展成门诊齐全、设施齐备的综合性医院;沁多小卖部由“没有什么食物,只有一种瓷噔噔的小月饼”发展成大型百货商店尼玛村康(太阳商店);沁多县由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县城发展成一座人口剧增、建筑连片、基础设施完备的现代化沁多城,凡此种种,作者都给予了认真细致的书写,从这些变化我们不难体会到一种朝气蓬勃的发展状态,这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牧区经济发展的辉煌成果。
当然,高原牧区的山乡巨变,既表现在牧民身份的转换与物质财富的提高上,也表现在牧民观念的变化与精神的变迁中,而后者无疑更加重要。长期以来,青海藏族由于受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和宗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比较封闭保守,习惯于周而复始的简单生产,满足于条件低微的“吃饱穿暖”,缺乏金钱观念和商品意识,也拒绝接受新生事物,这就在无形中限制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势必要从改变传统观念开始,把商品意识根植于牧人的脑海中,才能不断促使青海藏区社会进步、经济振兴,进而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这在《雪山大地》中有着很细致入微的呈现。例如,“文革”结束后回到小卖部的父亲想在草原开展牛羊贸易,一方面让牧人将牛羊换成钱购买生活用品,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降低存栏量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继而持续发展,然而这一想法却遭到了草原牧民的强烈反感与抵制,甚至连最亲的家人、最好的朋友、政府官员乃至阿尼琼贡的香萨主任都表示不理解不支持,父亲的工作面临重重困难。尽管诸事艰难,父亲在沁多草原游说的脚步却没有丝毫放松,依然走家串户苦口婆心地劝说,通过流动样板展示、赛马会贸易等各种方式向牧民们宣传,让他们看到钱的意义,进而转变思想观念,最后终于赢得了牧民的信任。杨志军说:“《雪山大地》中我想表现的不仅仅是山乡巨变所带来的景观变化,不仅仅是他们收入的增加,也不仅仅是我们在辽阔的草原牧区建起了一座可以定居的城市,而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心路变迁史”。[2]实际上,观念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改变高原牧区贫穷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想在高原牧区发展市场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就势必要首先改变牧民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摆脱传统的封闭和狭隘观念,继而走向真正的开放与现代,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山乡巨变。从这一点来说,《雪山大地》不仅写出了高原牧区的山乡巨变,还合逻辑地揭示了这一巨变背后更为深层次的观念和精神巨变,这些共同构筑了这部作品在这一主题上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
二、崇高的草原建设者形象
高原牧区的沧桑巨变,凝聚了几代草原建设者的汗水辛劳,广袤的草原处处可见他们奋斗的足迹。《雪山大地》成功塑造了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草原建设者,他们是整部小说中最为鲜明动人的艺术形象,同时也寄托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血脉深情。杨志军曾在一篇文章中追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支边者群体,他说:“这30年里(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笔者注),我们国家有过多次支援大西北的行动,比如大批干部的西派西调、内地工厂的整体西迁,底层移民的西进开荒,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支边运动——中国知青运动的发端就是支援大西北,它最早出现在1954年,当时就有许多青年去了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那时候的特点是:国家需要、政府号召、集体行动、个人服从。个人的浪漫情怀、理想色彩以及自我追求、生活选择,都应该是以建设边疆、改造自然为目的的生命奉献,是集体英雄主义前提下的自我实现。”[3]实际上,杨志军的父亲母亲曾经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支边者,父亲曾经参与创办《青海日报》,而母亲则是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或许从小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行举止与辛勤付出,作者很容易理解这一代人的辛酸与不易、理想与追求,父母的形象也被不自觉带入到文本之中,与小说中的父亲母亲形象重叠,继而完成了艺术性的同构。
首先,父亲母亲身上闪现着草原建设者理想主义的光辉,他们执着坚定,有着改天换地的勇气与信念,一股蓬勃的拓荒精神与乐观主义情绪充溢其中。小说中父亲和母亲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有开拓性的意义,比如父亲被抹掉副县长后选择当校长,原因是当时整个沁多县还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个真正的学生,因此他想办一所学校,让所有的孩子都来上学。创业自然是艰难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没有校舍、没有经费、没有教师、没有学生的情况下父亲竭尽全力四处奔走,选定“一间房”作为校舍、用牛皮绳拉起几道牛皮墙分隔成了教室和宿舍、苦苦哀求牧民让孩子上学、协调多方采办教学用具,最终这些努力让沁多小学得以建立,这不仅是沁多县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整个阿尼玛卿州的第一所学校。再如母亲,作为医生的母亲初到牧区卫生所面临的同样是诸多困境:没有专业医生、药品短缺、设备简陋。母亲便不辞辛劳向县里采购药品、联系省里医院让卫生所医生去实习、自己手把手教学生、争取县财政专项拨款,母亲的期望是:按照国家医院标准对待沁多县医院,增加药品的配给和医护人员的编制,而这一切也在母亲的不断争取和努力下逐渐变成了现实。同当时很多草原建设者一样,无论在理念还是行动上父亲和母亲都具备当地牧民少有的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总想干一些别人不想干的事情,想做一些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似乎是那一代支边人特有的理想激情与浪漫情怀,在父亲母亲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善良与爱构成了父亲母亲重要的人格特性,他们主动融入藏区,视藏族牧民为父母为兄妹为子女,传达出人人相亲、物物和睦、相爱相守的价值观念与人生信条。宣扬善良与爱向来是杨志军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在《雪山大地》中通过父亲母亲的形象表达得尤为深刻。父亲在草原上办学校、建沁多贸易、开展新草种引进种植以及实施十年搬迁计划,母亲救治“哑巴”才让、建设沁多医院乃至后来在生别离山完成扎根病区医治麻风病人的壮举,这些行动的出发点皆不是出于私心或私利,而是真正为了草原牧民的安居乐业与民生福祉,其内在的驱动力即是对整个牧区藏民们兄弟姐妹般的善意和爱。在父亲和母亲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汉藏两个民族的血脉交融、骨肉相连,还深切体会到了汉民族追求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与藏族牧民崇拜雪山大地的坚定信仰的交相融合,而这一切交融都基于这样一个条件:向善而生。杨志军说:“地广人稀的高寒缺氧,促使这里的人对温情充满渴望。他们热爱交际,喜欢抱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异乎寻常亲近,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生存的严酷,消解自然的荒凉和环境的落后带给人的种种窘迫。”[4]《雪山大地》中书写父亲一家、角巴一家、桑杰一家和睦亲善、守望相助的情节和场景很多,这实际上就是从几个家庭的微观层面对善与爱所进行的具体直观的呈现,同时,小说中还详细写到作为下一代的索南、才让、江洋、梅朵、琼吉、普赤等人的成长与结合,他们由彼此相遇相爱到组建家庭生育子女,年轻一代将父亲母亲善与爱的品性完全继承延续了下去,象征着草原建设者与藏区牧民世世代代血脉相连,最终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的坚不可摧的爱的共同体。
再次,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草原建设者富有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他们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人民与事业,也从中获得超越个体与小我的崇高精神力量。《雪山大地》前七章详细记录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前父亲母亲在高原牧区的艰难创业,其中虽不乏成功开拓功绩的喜悦,也并不缺少充满悲剧意味的失意心酸。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海牧区,经济落后,生产方式单一,物资严重匮乏,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再加上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交通闭塞,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这本身就对心怀理想的草原建设者构成了巨大挑战。而事实上,自然环境的恶劣并没有阻碍建设者奔赴草原的脚步,工作上的诸多挫折与磨难也没有消磨他们的意志与决心。这里让人惊叹的是父亲母亲面对困难挫折的豁达态度,比如父亲为救角巴自己扛下了运送瘟牛肉的全部责任,被免副县长后从容地等待组织再次分配;遭到老才让恶意举报丢了校长的职务并被解除公职,坦然回到机关小卖部当起了临时工;还有因“强巴案”全家罹难,父亲入狱数载,母亲不得不躲进生别离山,但归来后父亲并没有过多抱怨便开始踌躇满志地筹建沁多贸易,而母亲更是安心扎根在生别离山卫生所,为麻风病患者看病诊治,即使后来自己染上麻风病也无怨无悔,最终因此奉献出了生命。细细想来,父亲母亲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面对挫折与不公也会伤心无奈,但只因他们心中还装有更高远的理想与更多的草原牧民,便不会为暂时的失意而懊恼退却或者止步不前,这是真正的草原建设者的担当精神,也是他们能为牧民们爱戴、赞美以及永远怀念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三、雄浑壮丽的草原史诗
细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史诗”是一种自觉而普遍的追求。按照洪子诚的说法:“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5]如我们所熟悉的《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人世间》等小说皆把史诗性看作其崇高的美学理想乃至审美标准,都体现了鲜明的史诗品格,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也不例外。作为一部有积累、有准备的长篇佳作,《雪山大地》气势恢宏、画面壮观、人物众多、内容丰富,呈现出独具西部特色的雄浑壮丽的史诗风格。
首先,《雪山大地》架构宏大、组织严密,以父母建设草原为主线进行的广阔的时间空间延展,全景式地展现草原历史变迁和时代风貌。史诗类长篇小说一般规模宏大,线索纷繁、出场人物众多,如何将浩繁的人物事件进行严密组织,进而有序统合,这是任何长篇小说作家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很考验作者的创作功力。我们看到,《雪山大地》做到了既规模宏伟又秩序井然,史诗形式得到完美呈现。从时间上看,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父亲到沁多公社蹲点写起,继而写到60年代建立沁多小学与沁多中学、70年代建立沁多医院、改革开放初期成立沁多贸易、80年代开始实施牧区十年搬迁计划,一条不断发展的线索清晰可见;从空间上看,小说以沁多县为主要舞台,继而辐射扩展至阿尼玛卿州、西宁、兰州、丹久尼玛无人区等多个区域,由草原到城市,由城市再回到草原,广阔的青海高原画卷渐次展开。值得注意的是,《雪山大地》是一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当代现实感的作品,这当然不仅是因为其从历史一直延续到当下,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对照,让人明白当代青海牧区由一穷二白到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它的发展充满坎坷,它的脱胎换骨来之不易,其中有党的政策的正确指引,有草原建设者的勤奋耕耘,更有牧区人民观念的转变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持续追求。从这个角度看,《雪山大地》既有对历史的基本理解,又具有现实的参照维度,因而它毋宁说是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的“当代史诗”。
其次,《雪山大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细腻笔触还原草原牧民生活细节和生活状态,堪称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雪山大地》书写了青海高原的大时间、大空间、大变化,但这些“大”又是通过很多“小”来体现的———小人物、小事件、小细节,整体上呈现出细致又丰厚、微观透视与宏观鸟瞰相交融的特点。杨志军长期生活工作在青海,因此他对藏区牧民的日常生活可谓十分熟悉,于是作品中便有很多关于衣食住行、节日风俗、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的描写,有的甚至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例如第十二章写赛马会,作者先是详细描写了大会的筹备、会场的准备情况,然后几乎是像纪录片一样记录了赛马会的整个流程,从开幕式到歌舞表演,再到走马赛、障碍赛、分组赛、捡哈达赛、跑马赛,每一个环节都如临其境,每一场比赛都扣人心弦。再如第十五章写藏式婚礼,新娘素喜从下马、进门、上楼到入厅的过程都交代得十分清楚,每次都得唱一次颂歌、献一条哈达,尔后新娘要坐在新郎身旁和双方亲属围坐一起会餐、互送礼物,参加婚礼的亲友们也献哈达、送礼品、唱婚礼歌,以表示祝福。除此之外,我们看到《雪山大地》还广泛涉及到高原牧区的自然风貌、饮食起居、民居建筑、雪山大地崇拜、民族歌舞、藏药藏医等内容,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文化属性贯穿始终,而作者正是依靠对这些生活细节、生活状态的精准捕捉和呈现让作品产生了扣人心弦的力量,《雪山大地》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来自日常生活的史诗性和知识魅力。
再次,《雪山大地》做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交融,辽阔壮美的草原风物与健康美好的人性交相辉映,小说整体上呈现出清新刚健的风格。杨志军在很长的时间一直以青海高原作为小说的艺术舞台,这里有高原、雪山、湖泊、草原、千里无人区、动植物,有西部高原特有的风沙、冻雪、马群和戈壁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派雄奇宏阔的瑰丽风景,显示着高原牧区强大而彪悍的自然伟力。《雪山大地》通篇都是用一种赞美欣赏的态度描写牧区风光和民俗风情,雪山草原的雄伟宁静与父亲母亲高尚的人格相互映衬,与高原牧民们质朴敦厚的美好人性相得益彰,这些都让小说在现实主义之外增添了不少浪漫主义的气质与品格,显示出现实与浪漫的混融。小说中最令人感动的是父亲母亲去世时作者满怀抒情意味的描写,作者写道:“草原展示着夏天最彻底的秾丽,绿色就像刚刚洇染过,带着亮光和潮湿覆盖着所有土壤,地形的波浪变成了牧草大面积翻滚,从平川到山腰,衔接着红色和黄色的苔藓地带,苔藓之上是雪线,是覆雪的山峰、逶迤的冰岭。”“不要再送我回去,也不要让人来看我,就让我安安静静躺在雪山大地的怀抱里吧,你看,身边的野马滩草原这么绿,面前的野马雪山这么白,再没有比这里更干净更吉祥的地方来啦,扎西德勒。”这是多么宁静而美好的高原风景和高尚的人生境界,当父亲母亲为草原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理想与生命岁月,当旧日的坎坷以及艰辛都已成为往昔,一切的悲伤失意或成功喜悦都随之消散在雪山大地的深处,留下的则是草原建设者们坚韧执着的开拓精神与干净澄澈的心灵,他们与雪山大地的雄伟圣洁、西北草原的辽阔强悍永远融合在一起,鼓励着一代又一代建设者和牧区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扎根沃土,奋勇前进。从这个意义上,《雪山大地》的确无愧为一部雄浑壮丽的高原史诗,它饱含了杨志军对青海高原数十年山乡巨变的真诚感喟,凝聚了对几代草原建设者艰辛探索的深情礼赞,在宏阔的时空跨度上还原塑造了重大历史事实以及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为人民留下了富有时代精神气质又令人难忘的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