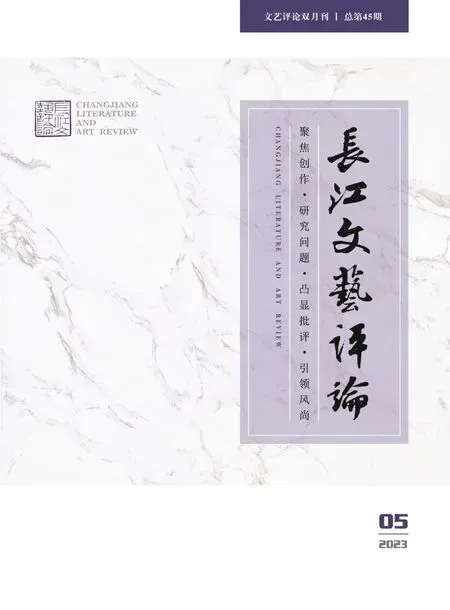诗证和自洽
——评李少君诗集《每一次的诞生都是痛苦》
◆朱必松
李少君进行诗歌创作已有四十余年,我认识诗人也有近三十来年。我感觉自己应该写一篇整体性的文章,从自然主义新的认识论高度全面立体地评价一下李少君。
珞珈山是一个出诗人的地方。珞珈山还是一座有思想的山,遍布圣迹。它是一座诗意的高地,是可以为山立传、为水写史的精神家园。珞珈山春天的白鹭、樱花和鸟鸣都充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交响乐魅力,珞珈山成为了诗人李少君诗学经验的“逻辑起点”,其精神结构飘向无限远方的涅槃圣地。
一、生命互证意义的共性与差异
我作为李少君诗歌文本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几乎在近六年内阅读完了李少君公开发表的所有文章。这正如海德格尔为什么单单选择诗人荷尔德林作为探寻诗的本质客体一样。因为诗人李少君一直在思考着诗的本质,从最高的意义上看是历史的,因为它预示了历史的时代;但作为历史的本质,它是唯一的本质性的本质。我也一直在探寻着我同诗人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但除了我们青春时代共同的“闯海人”身份之外,我们再也寻找不到过多的共性。也正是这种“闯海人”共同身份缔造了我们之间可以用时间来验证和互证的友谊。
我同李少君真正较为频繁的接触始于2019年元旦前后,那是我在北京第一次参加有关的文化活动。李少君是这样介绍我的:这是我当年一起在海南闯海时的小兄弟。我当时在京城是“两眼一抹黑”,听到他这样的介绍,我的心里是温暖的。他在心理上并没有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还是回到了“神奈川”海浪的青葱岁月,这就是李少君的睿智之处,用细节打动了我。
《每一次诞生都是痛苦》这本诗集所编选的诗,我几乎阅遍了该书的不同版本,但这次我依然还是从头到尾再认真地阅读了一遍。这需要有一种强烈的个人情感作为依托还要附加诗歌文本自身的吸引力和鲜活性、经典性的魅力。
李少君的文化标签是“自然主义”诗人,我们就应该从自然主义的源头作一些考证和论证。我个人认为,自近代以来东方世界自然主义诗学集大成者应该是印度的泰戈尔,毋庸置疑,泰戈尔是继承了王维、李白、杜甫、陶渊明等中国古典诗歌中自然主义传统的。但只有泰戈尔达到了那种“心与物共、物我合一”的境界。美学家朱光潜曾指出:“每首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feeIing)和意象(image)两个要素。情趣是可以比喻而不可以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1]相对于诗人李少君来说,就是那首传播力非常广泛的《抒怀》: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间而一两声鸟鸣)/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云的写真集、窗口的风景画、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木瓜树下还有间而一两声的鸟鸣,诗人通过这些意象,展示了自然、植物与人和心的情景交融。
我喊父亲的声音/在林子里久久回响/又在风中如波纹般荡漾开来/父亲的答应声/使夜色似乎明亮了一下。(《傍晩》)诗歌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新颖的自然意象,建构了一种明快的、温暖的、动情的美学画面。
爱诗的少女是美丽的,你要好好珍惜。你要做那徘徊树下,打着赤脚在沾满露水的草丛上的少年,等待着,向四月的小路上眺望,等着她哪一天飘然而至。当鸟儿啄落的一颗果子打在你的头上,当一片黄叶落在你的青发间,她总会来的,你要忍心地等着。(《爱诗的少女是美丽的》)
这首散文体诗完全是泰戈尔式的一份爱的宣言。泰戈尔曾经说,世界是从爱生的,是靠爱维系的,是向爱运动的,是进入爱里的。李少君诗歌中也充溢着“爱的哲学”。
情人的泪,泛滥起一场一场的大洪水,有人不知有救,仅仅抓住一根草就沉下去了;有人在一个波浪上呼号,却不知回头即是岸;也有人仰望苍天,在卷入漩涡的刹那,仍面带着微笑,做着爱情的美梦;更多的人,在水中漂浮,心底渴望着一座坚实的岛,双手不停地划动,游向某个彼岸。这就是爱的辩证法。(《情人的眼泪》)
诗人既把爱情的柔美和甜蜜流溢于人间,又把爱情可能遭遇到的种种可能性进行了辩证法式的阐释,这就把爱情的“心语”抽象化,情人的眼泪成为了一种意象,一种美感,强化了其象征性的意义。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古希腊哲学家斐德罗认为爱神是最古老的神灵。因为根据赫西俄德的《神谱》,天地开初是混沌,之后就提到了地母盖亚和爱神爱洛斯。有了爱神之后,才有了万物的结合和孕育,以及其他神和人的创生。随后,斐德罗讲述了爱神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好处。爱神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指引,那就是羞耻感和荣誉感。这两种感情在相爱的人之间表现得格外强烈,不管是爱者还是被爱者,当另一方在场的时候,就不会有耻辱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走了很久都没有风/一走到湖边就有了风?/杨柳依依,红男绿女/都坐在树下的长椅上/白堤在湖心波影里荡漾/我和她的争吵/也一下子被风吹散了。(《西湖边》)云、雨、风、水等自然景象经常被诗人用来表达情感,抒发感情。杨柳依依、红男绿女、树下的长椅、白堤以及湖心的波影等构成了一幅清幽的、静谧的图画,有着错落有致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风作为一种平常的“物象”似乎赋予了其灵魂,她既可是虚指也可是实指,这真正体现了诗人“心与物共、物我合一”驾驭意象和语言的能力,体现出的是一种有意境的鲜活的画面感,这就是一种有美学趣味的意象。
二、自然诗人自身的精神面相
李少君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更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只是其诗人的光芒遮蔽了他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的光芒。虽然他在武汉大学读的新闻系,但近四十年来,他是一个真正用功,勤奋读书的人。他的阅读涉足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到文史哲政经、中国古代文论、中西方美学和哲学。没有全面阅读和研究李少君的人,误认为他只是一个单一的诗人,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具有思想能力的诗人和学者。
我最早读到李少君的随笔和文论是在2011年,是《印度的知识分子》《〈天涯〉十年:折射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变迁》以及《在自然的庙堂里》等等。李少君还写了小说《蓝吧》《海口之恋》《1999年的A城》《我们的发烧年代》等等。其骨子里的思想高度和文采深深地征服了我。在其新著思想文化随笔集《诗歌维新:新时代之新》中,李少君有着前瞻性的思想见地,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部,较为清晰地梳理出中国诗歌的主体精神和历史使命。
“中国心学照亮人的内心世界,康德美学让启蒙理性的主体之光照亮现代的意义世界。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工具理性正在消解人的自我意识及自我存在的价值。如何重构价值体系,抵御异化,复归人、人心,是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诗意的境界以其独有的超越性美学价值,对当代社会的异化问题作出回应。诗歌观照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但这里的人不是指个体、个人,不应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而应该是大写的人,指向人民性这一核心要求”[2]。
诗人对创作主题性新时代诗歌经典有着独特的精神思考,这自然与其作为《诗刊》主编的社会身份是分不开的。李少君的一些关于中国诗歌传统和创新的文论,诸如《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人民性”“主体性”问题的辩证思考》《自然对于当代诗歌的意义》《中华诗词的当代性》《在世界之中》《21世纪与新时代诗歌》《百年新诗中的北岛与昌耀》《人诗互证与诗歌境界》《长江与中国诗歌精神》等都拥有一定的高度和精神质地。在《百年新诗中的北岛与昌耀》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就很新颖: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现代性问题解决不了,新诗的问题也就解决不好,但新诗本身也是现代性的探索者和先行者。[3]
学者张旭东曾指出:在“五四”之前,人们常常把中国经验等同于落后的经验,而将西方经验称之为进步的象征,由此就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陷入了“要中国就不现代,要现代就不中国”的两难境地。“五四”将“中西对立”转换为“古今对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困境,“五四”成为“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分界点,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从此可以“既中国又现代”。[4]
三、思想者的宿命以及其精神结构
海德格尔曾经说:“他之所以选中荷尔德林,并非因为他的诗作作为众多的诗作之一揭示了诗的普遍本质,而只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作受诗的天命的召唤身不由己地表达出诗的本质。对我们来说,荷尔德林是真资格意义上的诗人之诗人。这就是我们必须选中他的原因。”[5]
同样的道理,我之所以选中李少君作为揭示“诗之本质”的个案研究对象,也是唯一的对象,也是因为李少君是受“诗的天命召唤”的诗人。其中至少有三点原因可以支撑我的观点:
其一,自2014年起,李少君从海南《天涯》杂志主编的位置调入《诗刊》社后,他一直负责编务工作,从《诗刊》的副主编干到主编,他一直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的火热诗歌现场,他广泛地接触了国内外不同层次和不同文化背景或者说不同特质的诗人,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其他的诗人不可能拥有的。
其二,从1985年武汉大学期间成为珞珈山诗派的主要创建成员之一,到2014年从海南《天涯》离开北上,他的诗歌写作实践的积累就有整整三十年,到今天的2023年,李少君已经写诗写了整整四十年。201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少君自选集》,他自己收录的第一首诗是《致——》:世事如有意/江山如有情/谁也不如我这样一往情深/一切终将远去,包括美,包括爱/最后都会消失无踪,但我的手仍在不停地挥动……这首短章的背后其实蕴藏的是李少君一生的诗歌激情、宣言和理想。这也就是李少君诗歌之“天命”。
其三,李少君思维开阔,眼光格局颇具“世界性”,这点从李少君执掌《天涯》到执掌《诗刊》这个二十年的奋斗期,足以证明。《天涯》是一本思想类的杂志,《天涯》的主编不是任何人可以当的,阅读过《天涯》思想和随笔类文章的人就知道。《天涯》的十年是李少君思想能力的锻炼期,他是从《天涯》起步,逐步锻造了其思想的能力和格局。《诗刊》的十年,特别是其执掌《诗刊》的近五年,力主在《诗刊》年度奖中设置了一个“国际诗坛诗人奖”,要求获奖诗人必须来中国领奖,首个“国际诗坛诗人奖”颁给了加拿大女诗人洛尔娜·克罗齐,这是李少君执掌《诗刊》以来,对中国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最斐然的成绩和举措。仅仅讲述以上三点,李少君作为一个“天命的诗人”就足以成立。
诗人荷尔德林在1799年1月写给他母亲的信上说:“……诗极为自由地构拟出自己意象的世界,沉浸于想象之域乐而忘返。这种游戏因此躲开了种种抉择的严峻性,要作出抉择就总免不了以某种方式犯下罪孽。这样一来,写诗就真正达到无利害的超脱。同时,写诗也是毫无功效的,因为它仅仅是不断地诉说和倾谈。写诗与那种直接把握实在并力图改变实在的活动完全是两码子事。”[6]
荷尔德林在一封日期标明为1800年的残篇断稿中说:人寓居于茅屋中,衣着褴褛,聊以遮羞。因此人更加热切更加关注地守护着精神,宛如守护神圣之光的使女,这是人对他自身的领会,从而人变得任意专断,他超绝般地获得了支配与完成的更高的力量,这样,人类拥有了最危险的东西——语言,结果使人对那永恒的活的东西创造又毁掉,毁掉了又挽回,甚至对情人和母亲也是如此,使他得以证实自己的存在——那他所承继的东西,他从您那里,从您那神圣的占有物那里领会到广被万物的爱。
语言,这“人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活动”的领域却是“所有拥有物中最危险的东西”。人证实自己的存在,证实对此亲昵的归属就在于创造一个世界并使它生机勃勃,进而又毁掉一个世界,使它急遽衰微。人的存在的证实,从而其本质上的完美的证实都在于抉择的自由。此一自由即把握着必然,使自己置身于最高责任的链环之中。这种归属于所有存在着的存在者的关系证明成为历史而现实化了。为了使历史成为可能,语言就必得赋予给人。从而语言就是人的拥有物之一。[7]
诗在语言的国度以语言的“材料”创造了自己的产品。荷尔德林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诗是用词语并且是在词语中神思的活动。以这种方式去神思什么呢?恒然长存者。但恒然长存者能被神思到吗?它不就是一直现存的吗?不!即使恒然长存者,也得携牢,否则将会不胫而走。
荷尔德林也在另一处提出说:“你对神性讲述,可这正是你全然忘怀的事,第一批果实从来不是给凡人的,它们属于神祗。果实必须更普通更日常化,这样才会为凡人所有。”纯粹与普通同样都是说出的东西。因此,词语作为词语从来没有直接保证它是一个本质性的词语还是摹仿性的词语。相反,本质性的词语由于其简朴看起来就像是非本质性的词语。另一方面,那被装扮得像是本质性的词语,只不过是为心灵背诵或重复的某些东西。所以,语言必须总是在其自身确证的显现中展示自身。这样就危及了语言的最重要的特征——纯真的述说。
李少君的诗叙述了很多“纯真”的语言,他诗中的语言接受的程度是广泛的、大众性普及的。我在研究李少君的同时也研究了欧阳江河等,欧阳江河的佛系性语言受众相对较少,只限于专业性知识分子的偏爱和阅读。而李少君的《霞浦的海》《西山暮色》《鼓浪屿的琴声》《在松溪遇见青山》《敬亭山记》《在坪山郊外遇萤火虫》《初溪》《草原上的醉汉》《抒怀》《珞珈山的鸟鸣》《春夜的辩证法》《青海的草原上》《一片原野》《欧洲的冬天》等等都充溢着这种“纯真”性的语言。
章太炎在《齐物论释·序》说的:“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李少君有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笼统于一身的能力。李少君一直试图以他的文化抒情来替代其政治抒情,文化同政治的联姻从来是辉煌而悲壮的,这点是李少君引起诸多争议性的深度原因,那么他就必须“以毒攻毒”来消解这种障碍,也就是必须以不间断的文化抒情来解构他的政治抒情,这点将在后面专章论述。
四、“人民性”与政治抒情
从2022年到2023年立春前,李少君一共写了三首诗:《端午怀屈原》《送别——致李叔同》《来雁塔之问》。为什么诗人的诗会越写越少?米兰·昆德拉从很早的时候就放弃了写诗,歌德和托尔斯泰写了一辈子的诗。他们这三人在诗歌和哲学上都有很高的成就,特别是歌德和托尔斯泰。李少君试图逐渐用其理性的精神建筑来代替他的感性诗学大厦。
虽然文化抒情是所有政治抒情里最边缘化的选项,但文化抒情又是政治抒情中的“无用之用”,也是一项最不可或缺的选项。文化抒情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其政治抒情是表面化的还是真正触及到其政治诗学灵魂的一种景象。这就需要诗人用不间断的文化抒情,一种不断超越其自身文化属性的文化抒情来实证。
吉狄马加《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完成了其文化抒情显性的政治属性,而李少君开辟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径,即是从长江、黄河,从《诗经》《离骚》中梳理他的隐性的文化政治抒情,这种文化属性的政治抒情是深耕中华文化传统的,是一种不断自我提升的思辩和思想能力的证明。
诗歌是善良和美的化身,正如捷克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在诗中写的那样:“要知道摇篮的吱嘎声和朴素的催眠曲,还有蜜蜂和蜂房,要远远胜过刺刀和枪弹”。李少君的文化政治抒情有浪漫主义特征。中国当代诗人或说是诗歌批评家、理论家还从来没有从“文化属性”去分析过王维、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等诗人的关联,更没有人从长江、黄河这两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的文化意义上去全面分析同中国古典诗歌和诗人成长之间的关系,起码李少君实现了一次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和视角较为独特的阐释。
钱穆认为:好的诗歌,能够体现诗人的境界,因此,读了好的诗歌,你就可以和诗人达到同一境界,这就是读诗的意义所在。我研究李少君既是一个致敬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过程。
李少君在《“人民性”“主体性”问题的辩证思考》一文中说过:在诗歌心学的观点看来,达到相当的境界之后,所谓的主体性,不仅包括个人性,也包括人民性,甚至还有天下性。这同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思想是一脉相成的。所谓的诗歌的人民性也就是诗学的政治性,政治主张及其文化信仰以及意识形态中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等等。
中国的诗歌提倡“境界说”,通俗地讲就是“家国情怀”以及诗人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显”与“隐”的区分。诗人绝大多数是无法进入政治枢纽的,从中国的上古史到现当代的社会现实境况,但像杜甫那样“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的政治理想是值得倡导的。
《昭明文选》里称:“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向之者诚也。”严格意义上说,李少君是一个命运的幸运儿,但依然留有“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一匹疲惫战马样的遗憾。
李少君是否也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吾不得而知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夫之在《诗广传》中称:“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
用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观点阐释:意义的世界就是被历史文化以及传统赋予的,这些东西构成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自我认识,在历史文化以及人的关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坐标轴。
李少君在《人诗互证与诗歌境界》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人诗互证,既是古老的诗人之为人的意义,也是未来的诗人得以自立自证的标准和尺度。因为,诗人永远是人,诗如其人。诗,一直最具个人性和独特性,也证明人之个体性和独特性。
真正的诗,永远只有真正的个人才能写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诗也是人类的目的和未来。
诗人作为最敏感的群类,像李少君这样从其个人性走向其“人民性”是出类拔萃的,这是需要一种境界的,这种境界就是哲学家冯友兰所倡导的天地境界:“一个人可能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事的意义,自觉地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这就是我说的天地境界。”诗人兼学者的李少君正在自觉地向这种天地之境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