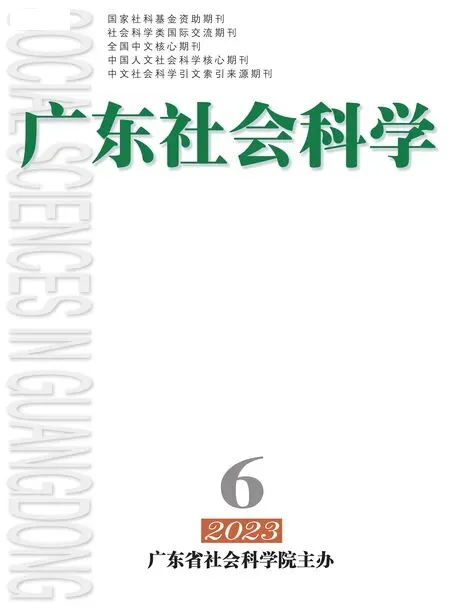异军突起:清代骈体题图文探论*
路海洋
文学与绘画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绘画史的一个突出特点,而由此蕴生出来的题画或说题图文学,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体量庞大、成就不俗的一个类型,南宋孙绍远《声画集》八卷,辑录唐宋两代109位诗人的818首题画诗,清代康熙年间陈邦彦所辑《御定历代题画诗类》更达到一百二十卷、8962首,由此二集已可略窥古代题画文学之发达。自宋代以来,就不乏对题画文学进行探研者,近几十年,不但题画诗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题画记、跋和题画词、曲也成为学者不同程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古代题画记、跋中,有一类作品总体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那就是自魏晋时期即发展起来、至清代乃蔚兴的骈体题图文。清人姚燮曾在《皇朝骈文类苑》序类中单辟“题图之作”子类,辑录清人此类作品22篇,这是目前可知将骈体题图文单独汇集、予以突显的唯一文献,但姚燮的“深意”应者寥寥,更没有人对此进行专题研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清代骈体题图文的义界与文体特征
清代骈体题图文,是指清人创作并题写于绘画作品上的骈体之文。这里还有两点需要略加说明:一是“题图”。中国古代的题图或题画文字,除了题写在绘画作品之内,更多的是题于画外,包括引首、拖尾及诗塘等处。清代骈体题图文大部分都题于画外,题文内容往往较长,是其不宜题于画内的主要原因。二是“骈体之文”。骈体文是相对于散体文而言,从文章形态上来说,它的特征包括五点,“一曰多用对句,二曰以四字与六字之句调作基本,三曰力图音调之谐和,四曰繁用典故,五曰务求文辞之华美。”①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页。当然,由于作家个人好尚、理论取向导致的行文风格之多样,清代骈体题图文不一定都体现以上五点特征,但无论如何,多用四字、六字对句和音调谐协,是该类作品的基本共性特征。
文章写作必然要涉及文体运用,清代骈体题图文所运用的文体,主要有序、记、赞、赋及题跋等。序、记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是清代骈体题图文的最大宗。吴讷说:“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②吴讷著、凌郁之疏证:《文章辨体序题疏证·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这里提到的“其言次第有序”,正是序体的一个基本特征。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云:“序,东西墙也。文而曰序,谓条次述作之意,若墙之有序也。”③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二八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与吴说互参。结合序体发展史来看,其不但行文具“次第有序”的特点,而且还长于议论、叙事,徐师曾《文体明辨》云:“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2106页。清代骈体图序从古代序体一脉承衍、发展而来,其文体特征确实表现为“善叙事理、次第有序”且以议论、叙事为长,不过也有一些作品以写景、抒情擅胜。典型的如胡敬《西溪秋雪图序》和《春江话别图序》,几乎全篇都是写景;董祐诚《方彦闻鹤梦归来图序》则叙议中饱含深情,有着浓郁的抒情特色。
关于记体,一般认为记载事实是其基本特征,所谓“记者,记事之文也。”⑤潘昂霄:《金石例》卷九《学文凡例》,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1478页。“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也。”⑥吴讷:《文章辨体序题疏证·记》,第162页。而韩愈《画记》及柳宗元的多篇游记,被认为是记之正体。不过,学者们很早就发现,记事并非是记体的唯一特征。吴讷就指出,韩愈《燕喜亭记》已“微载议论于中”,而柳宗元《永州新堂记》《永州铁炉步志》“则议论之辞多矣”,到了宋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张耒等则创作了“专尚议论”的一些记文,⑦吴讷:《文章辨体序题疏证·记》,第161—162页。于是长于议论便也成为后世记体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清代骈体题图记也以记事、议论为基本特点,不过也有一些作品特别是山水、游宴图记,其写景、抒情的比例往往远高于议论,也常高于叙事,如徐熊飞《李海帆大令龙湫纪游图记》《东湖访旧图记》、金应麟《家杏楼皋亭问桃图记》等。
结合具体作品,还可以对清代骈体图序、图记的文体特征作进一步总结。首先,叙事、议论是清代骈体图序、图记共有的行文特征,不过图序中议论的比例要高于叙事,图记中叙事的比例则要高于图序,其中虽有例外,但总体格局就是如此,这与古来序、记的文体特点也是相符的。其次,清代骈体图序、图记存在文体“越界”、文体交叉现象。一是一些图序写得更像图记,而一些图记写得更像图序,前举胡敬两篇图序及洪亮吉《青芝山下卜邻图记》、吴锡麒《张船山池南老屋图记》等就比较典型;二是一些图序、图记尤其图记,只是将绘画作为一个由头甚至脱离绘画展开记叙,如前引徐熊飞、金应麟的图记,完全可以命名为《李海帆大令龙湫游记》《东湖访旧记》《皋亭问桃记》,张鸣珂《半园图记》可径改为《半园记》,而胡敬《春江话别图序》改作《永嘉山水记》似更切题。类似的文体交叉、文体“越界”或说“破体为文”现象,在清代骈体图序、图记中并不鲜见,应当说,前述第一类可称为变体为文,不无创新,第二类则“越界”过多、影响到文体的独立性,不宜提倡。
题跋不是专指性文体称法,而是一种笼括的类指性命名,徐师曾《文体明辨》对它的内涵有比较切实的概论:
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书者,书其语。读者,因于读也。……曰题跋者,举类以该之也。①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第2107页。
要言之,题跋就是题于简编(也包括绘画)之后的题、跋、书后、读后等文字的统称,其功能主要是揭示题跋对象的内涵、意义或表达题跋者的思考。清代骈体绘画题跋的数量不少,以议论为主兼及记叙、抒情,是此类文章的总体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题跋与图序较为相似②姚燮《皇朝骈文类苑·序》有云:“言有序曰序,叙而抒其序也。纡徐不迫,次第有经,檃括而中乎旨也。……绎其绪余,遂衍为题辞、书后及跋与引之目,然其揆一也。”此论可作为文章此处的很好注脚。引文见姚燮:《皇朝骈文类苑》卷首,清光绪七年刻本。。
清代骈体题图赞、赋的数量,相对于序记、题跋而言并不多,但也是清代骈体题图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赞、赋产生的时间都比较早,在漫长的历史迁变中,其文体也发生了较多变化。但归结到清代骈体题图赞、赋而言,图赞一般都有赞美之义,故王先谦《骈文类纂序目》说“赞之于颂,名异实同”③王先谦:《骈文类纂》卷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21页下栏。;同时,图赞多继承了古来赞文“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④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颂赞第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6页。的特点,一般为四言押韵短文,通过有限的文字来议论、抒情,当然也有少量图赞如李慈铭《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结合)韵文;也有一定数量序、赞结合的图赞,有些是序、赞皆骈(如查揆《小檀栾室读书图赞并序》、方履篯《沈贞妇绘古图赞并序》),有些则序骈而赞非骈(如吴慈鹤《钱武肃王画像赞并序》、董基诚《鹤梦归来图赞并序》),后者应排除在骈体图赞范畴之外。清代骈体图赋的数量略多于图赞,其基本体式是前缀小序、后以赋辞(也有少量作品有赋无序,如杨芳灿《斗寒图赋》、胡敬《秋声图赋为金听泉作》等),小序叙作图之由,赋辞则“铺采摛文,体物写志”①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第八》,第80页。,其往往将叙事、写景、议论、抒情糅合在一起,可以说是综合了骈体图序、图记的文体功能与行文特点。
二、清代骈体题图文蔚兴的历史原因与总体面貌
清代骈体题图文的蔚兴,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艺术史现象,而是多种因素合力推动下的结果。概言之,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清代画学及题画文学发达的影响。清代画学是在继承明代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陈师曾所谓“(画学)自明之万历至于康熙、乾隆之间,成一贯之状态”②陈师曾:《中国绘画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6页。。不过,由于朝廷政治方略的深刻影响,清代画学的兴盛程度要远高于明代,潘天寿对此曾有扼要论述:
满人以游牧起长白山,富尚武力精神。自世祖入关以后,全以武力席卷中原,威服四邻。继则提倡文教,收拾民心,开科举鸿博,编纂图书,以虚名学术,牢笼汉族文士。虽出于政治之方略,而影响所及,足以驱天下于浩博之一途。承学之士,又投其结习之所好,沉蟫于文史之间,以终其生活。致清代之文艺学术,继有明旧势而昌大之;绘画亦然。故一时画人竞起,为空前所未有。综《熙朝名画录》《国朝画征录》《国朝画识》……等计之,不下六七千人,可谓盛矣!③潘天寿:《中国绘画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
伴随着清代画学的兴盛,清代的题画文学也高度发达。从历史上看,五代至清的画学被称为画学史的“文学化时期”④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将中国古代画学史分为实用时期(唐虞以前)、礼教时期(三代秦汉)、宗教化时期(三国至唐)和文学化时期(五代迄清),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的分期与郑午昌一致,只是部分时期的朝代范围有所不同,这主要指五代被潘氏划入了宗教化时期。分别参见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4页;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绪论》,第2—3页。,文人画繁兴、绘画讲求书卷气、画学与文学密切结合,是这时期绘画的突出特征,而这种特征在明清两代表现得尤为明显⑤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自序》,第5页。。与画学的“文学化”大势相对应,题画文学也在五代兴起,在宋代进一步发展,至元代乃形成第一次发展高潮,“明清两代题画继承元代传统而更上一层楼”,尤其清代,“题画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题画已成为中国画的主要特色之一”⑥张金鉴:《中国画的题画艺术》,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9页。。清代题画文学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表现为题画作品题材的繁富、作家作品的众多、题画款式的多样⑦张金鉴《中国画的题画艺术》总结出古代题画的单款、双款、标题、纵题、横题、隐题、间题、落花、方块、长篇、参差、大字、顺行、折扇、通屏、钤印等16种款式,这些款式在清代题画艺术中皆有体现。,又体现为题画文学样式的丰富(诗词曲赋、散文及骈体无所不包);而题画成为清代绘画的一个主要特色,对应着的就是绘画即题诗文乃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时代好尚,像清初“四王吴恽”“四僧”及清中叶“扬州八怪”这样的画人,就几乎是无画不题,而一般文人倩人或自作绘画,也喜欢邀人品题,有些作品甚至是一题再题。清代骈体题图文首先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发展、兴盛起来的。
第二,清代骈文复兴的直接推动。中国古代骈文发展,经历了六朝的鼎盛、唐宋的继兴,在元明两代走向低谷,但到了清代又迎来了一次复兴,刘麟生有云:“清代作者,渐有追踪徐庾远溯汉魏之趋势,而究其所作,亦未必能陵轹唐宋。要之起衰振弊,能以骈文之真面目示人,则清代作者之贡献,殊足以跨越元明矣。”①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清代骈文的复兴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文学体类的深度开拓就是重要标志之一,马积高对此曾有精要的概述:“清代一些骈文家既有意与古文家争席乃至争文统,凡六朝人已用骈体来写的体裁固然用骈体来写;唐宋古文家所开拓的文章领域,他们也试图用骈体来写。”②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骈体山水游记和题图文,就是清代骈文家在古文创作领域以外耕耘、创辟而成就较为突出的两大体类③清代骈体山水游记的创辟特性与文学史意义,参见路海洋:《论清代的骈体游记》,《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在这个意义上,清代骈体题图文的蔚兴,也可以说是清代骈文复兴大势带动下的一个重要成果。
作为清代题画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骈体题图文的创作群体规模、作品体量、题写形式多样性、总体成就都比不上题画诗,但也自成面貌、别树一帜。首先它的创作群体是比较庞大的,清代的大部分骈文家都写过数量或多或少的骈体题图文,吴锡麒、洪亮吉、查揆、郭麐、胡敬、董祐诚、金应麟、张鸣珂、黄金台、姚燮、李慈铭等,都是此体名手,一些画家如恽寿平、石涛、郑燮等题图也有一些骈体文;其次它的作品数量是比较可观的,如吴锡麒一人创作的骈体图序、图记、题跋就有55篇,黄金台的题图序、记也有近40篇,有清一代的骈体题图文有数百篇之多;再次这些题图之作的题材也非常丰富,举凡隐逸、游赏、雅集、读书、仕宦、思乡、怀旧、体物等题画诗词、散文所涉及的绝大部分题材,其皆有涉笔。清代骈体题图文的艺术造诣也不容小觑,除了姚燮《皇朝骈文类苑》、王先谦《骈文类纂》等所选诸佳作而外,清代还有相当数量的此类作品,它们或就图挥写,擅于写景、造境,或因图阐绎,长于议论、抒情,总体艺术水准、艺术成就是比较高的。这是横向的概述,还可以通过分期的方式进行纵向描述。
结合清代骈文发展的阶段特点,可将清代骈体题图文的演变分为三个考察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至康熙末。此时的骈文承明末而来,实用性的书启及诗文序是作家写作的主体,题图之文仍集中于散体。比较有代表性的骈体题图文作家,有尤侗、章藻功、黄之隽等。尤侗创作了一些骈体图(像)赞,往往骈中兼散,体现出清初骈体图(像)赞的基本特点。章藻功有骈体题图文20篇,是清初创作这类作品较多的作家,这20篇文章集中于题图序、跋(中有题图赋1篇),而且这些图序、题跋的文体界限比较模糊,大体皆可归为图序一类。黄之隽有题图骈文11篇,除了1篇图赋,其他也是图序和题跋文字。此期骈体题图文创作者及作品数量都有限,佳作也很少,可称为清代骈体题图文的萌生期。
第二阶段是雍正初至嘉庆末。清代骈文创作在此时蓬勃发展,臻于鼎盛,骈体题图文也随而勃兴。除了吴锡麒、洪亮吉、郭麐、胡敬、查揆而外,包括杨芳灿、曾燠、王芑孙、张问陶、刘嗣绾、方履篯、王衍梅、董基诚、董祐诚、徐熊飞、吴慈鹤在内的一批骈体题图文重要作家陆续登上文坛,就是刘星炜、袁枚、孔广森、袁翼、黄安涛等“志不在此”的作家,也创作了部分思想内容、艺术水准都可圈可点的佳作。在清代中叶诸多骈体题图文作家中,吴锡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此体大家,他的题图文不但数量最多、成就颇高,而且其近50篇题图序、记所呈现的写作结构、风貌,奠定了清代骈体题图序、记的基本格局。作为吴氏浙江同乡的胡敬,也是此期骈体题图文的大家,他创作了24篇题图作品,体式多变、风格多样、质量亦高,而且一些作品“破体为文”,表现出与吴锡麒奠定的题图文格局相异的风貌与取向,这些作品成为后来“破体”题图文的标杆。再如杨芳灿和徐熊飞,他们骈体题图文的数量不算太多,但成就较为突出,是未被骈文选家重视的此体重要作家。由于此期题图文创作最为蓬勃,可称为清代骈体题图文的鼎盛期。
第三阶段是道光初至清末。与清代后期骈文虽渐趋衰落而仍然保持一定发展势头相似,清代后期的骈体题图文也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绩。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金应麟、谭莹、李慈铭、姚燮、周寿昌、赵铭、徐锦、张鸣珂、谭献、缪荃孙等,此外冯煦、洪符孙、吴清皋、张预、何栻、缪德棻等,或多或少也都写作了一些骈体题图之作。诸人中,金应麟、李慈铭、姚燮、张鸣珂、缪荃孙的作品数量较多而创作成就较高。金应麟题图之作,佳者往往文笔老辣沉浑,那些讽议时事的作品,更体现出清代骈体题图文中极为少见的现实感、时代感。李慈铭、姚燮、张鸣珂三人皆善绘事,姚燮所画墨梅驰名一时,而张鸣珂还是有名的画史研究者,他的《寒松阁谈艺琐录》是画史重要著作。他们创作的骈体题图文虽然都没有论画谈艺,但各具面貌且不乏佳篇。缪荃孙博学多才,所作多篇题图文气韵沉厚,堪称名手。可将此期称作清代骈体题图文的继兴期。
三、清代骈体题图文的艺术功能与旨趣
题图文学是依图而生的艺术创作,它与图画本身天然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从汉代开始就越来越趋向紧密。当然,中国古代题图文学中的文图联系,又大体呈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文对图的依附性很强,文的内容自图而来、以图为归,很少伸发,可说是就图言说;另一种是文对图的依附性较弱,文的主体内容是对图画内容的较大幅度衍伸,有时甚至只是将图画作为一个话题引子或触媒,可以概括为因图衍述。清代的骈体题图文既有就图言说型,也有因图衍述型,但不论是哪种类型,文都是对图的“解释”。从根本上讲,题图文学中文作为图的“解释者”,是文、图两者本身的艺术特性、本质所决定的。图画是一种空间的艺术,它也有记录事实和承载意义的功能,但它记录的事实只能是典型却有限的历史瞬间,它承载的意旨、意趣、意境也是“沉默不语”的,因此古人称图画为“无声诗”;而文学是时间的艺术,它可以记录历史事实的前因后果和具体过程,可以用不同的语调表达意旨、意趣,用不同的笔致描述意境。于是,在图文结合的题画文学中,文就当仁不让地担任起图画“解释者”的角色。
在清代骈体题图文中,文对图的“解释”功能是非常丰富的,但它的主体部分大体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即纪实和述意。纪实功能在绝大部分题图骈文中都有体现,但就图言说型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它包括复述图画形制和内容、叙写作画缘由、呈现图画涵纳的人物背景与事件过程等方面内容。清代骈体题图文对图画的具体形制很少涉笔,即有涉笔,文字也极简省,对图画内容的正面描写也比较有限。前者如查揆《家梅坞家累图序》写图,只说“图纵不三尺,横略倍之”①查揆:《筼谷文钞》卷五,清道光十五年菽原堂刻本。,别无其他描述文字。后者相关作品稍多,如李慈铭《薛慰农太守烟云过眼图序》,就薛时雨《烟云过眼图》册内八幅图画的内容,依次展开细致、如实的描写②李慈铭著、刘再华校点:《越缦堂诗文集·越缦堂骈体文》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73—1174页。;又吴锡麒《汪对琴松溪渔唱图序》用“流水不远,行云欲归,微闻寒吹之声,有助鸣榔之响”①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十,清嘉庆《有正味斋全集》本。数语,虚笔笼括图画内容、勾勒图画神采,而《汪饮泉昉溪秋景小照序》则用“斜照欲下,枫矜瘦红;凉花已多,芦堕荒白”②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十。这样诗意的语言,对图画内容进行扼要的正面描述。李、吴之文,或细笔如实地、或粗笔写意地复述图画内容、勾勒图画神采,但都做到了“就图言说”,其对图画内容描写的几种类型,也是清代骈体题图文此类描写的基本范式。
叙写作画缘由是清代大部分题图骈文的基本构成因素,不必赘述,而呈现图画涵纳却难以充分言说的内容则有必要略述。作为静态的空间艺术,图画虽能呈现典型历史瞬间,但这些瞬间的前因后果、发展过程,它只能作“有意味”的省略,而清代许多图记和部分图序的重要功能,就是将图画“省略”的内容展现出来。如金应麟《家杏楼皋亭问桃图记》《曹岚樵黄门桐江春泛图记》即在略述图中人物出游起因的基础上,依次记写其游赏途中所观景致及内心感怀③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六,清道光三十年刻本。,方履篯、徐熊飞等人类似游记、事记的图记也是如此,那些游览过程中随时变换的自然景致和游人丰富的内心感怀、事件发展的曲折过程,都是图画难以言说的;又如袁枚《陈检讨填词图序》先述图画由来,继则对陈维崧的家世、才华、生平遭际、填词好尚与风采等娓娓叙写④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小仓山房外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14—2115页。,文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都是图画无法言说而籍文充分展现出来的,类似的作品在清代骈体题图文并不少见。
述意功能在因图衍述型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这一功能主要体现为概括绘图目的、阐绎画作意旨。这类作品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图画策划者在请他人代绘或自绘图画时,总有一定的目的、追求、意趣,可称之为“文人之心”,因为图画是沉默的“无声诗”,因此题图文就成为阐释、发挥这“文人之心”的重要载体。如蒋葆存绘《蒋村草堂图》四帧,通过这些图作,读者可以对蒋村草堂的形态、布局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但若非了解蒋氏绘图的背景,一般并不能准确把握作者绘图的实际目的,而通过胡敬的《蒋村草堂图序》,我们就可以清晰把握蒋氏绘图的初衷:“《蒋村草堂图》者,蒋君葆存睠先人之敝庐,念乔木之留荫,写此以表旧德,景前徽,意弥厚也。”⑤胡敬:《崇雅堂骈体文钞》卷一,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再如吴锡麒友人陆半帆作《人海虚舟图》,此图题材比较抽象,看上去寄意微渺,但经过吴氏序文的阐绎、归纳,我们知道陆氏作此图的深层意旨乃是“叹遭遇之不常,而人生如寄”,而他追求的境界则是“耳清而柔橹如闻,心定而虚澜不起”⑥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九。。
与书写题材的丰富多样直接相关,清代骈体题图文蕴含的旨趣也是多种多样的,颂隐逸、倡雅游、明孝思、重友情、感祖德、励苦读、讽时弊、论兴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颂隐逸是清代骈体题图文涉笔频率很高的主题,这与清代题画诗的情形是相似的⑦刘继才总结清代题画诗的思想内容特征,认为有三点,第二点就是“抒发抑郁之情与向往林泉之志”,而且刘继才指出这一主题在清代题画诗中“所占比例较大”,“并且从清初到清末,这类作品始终较多”。引文见刘继才:《中国题画诗发展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8—412页。。归处林泉、高蹈出世,是中国古代文人长久追求的人生理想,但其归隐之念背后蓄藏的往往不是闲情自适,而是无奈和苦涩。清代骈体题图文对士人仕途坎坷而思归林泉的叙写是较多且动人的,曾燠《楞伽山房图记》写王芑孙“十年九陌,一官五湖”,“门绝迹而似水,屋打头以如舟”,宦途如此无望、生活如此困窘,芑孙生出“著书以销岁月,啸傲而凌沧州”的归隐之愿便不难理解,而结合他才华超卓、早著文名的过往和“傲似杜陵,狂于阮籍”的个性,我们应能进一步体会到他无奈归隐背后难以消除的愤激不甘。①曾燠:《赏雨茅屋外集》,清道光间刻本。吴锡麒《家兰雪扁舟归养图序》所写吴兰雪“一官博士,五载长安,晨昏则索米而炊,风雨且借驴而出”②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续集》卷二,清嘉庆《有正味斋全集》本。的薄宦苦况,与王芑孙是比较相似的,虽然吴兰雪的宦途或有顺达的一日,但现实的长期困苦,让他由图绘折射出来的归隐之念显得分外感人。士人宦途不顺固然引人同情,一般的涉世困苦、进取乏途也能动人,吴锡麒《曹月锄操船图序》开篇对士子孤篷逍遥的境况有文情豪迈的描写,但当作者笔触转向曹月锄现实生活时,文章就被忧郁之思所笼罩了:“惟此苦叶浮沉,旅萍飘荡,欲收帆而不得,将转柁其何方?彼岸茫茫,回头不易;此身泛泛,著脚都难。”③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十。由此一扬一抑,文章末尾对友人即便进途无望也能萧散归隐的安慰,就充满苦涩意味了。
清代骈体题图文对倡雅游、明孝思主题的书写频率仅次于颂隐逸主题。亲近自然、纵情山水,既是文人搜剔诗材的需要,更是他们畅发襟怀、安置心灵的需要,诗情盘礴时他们常会有拥抱自然的渴望,应世烦扰时他们也常生回归林泉的祈愿。因此之故,清代骈体题图文所描写的山水林泉几乎总是美好的,记写的游赏过程和心境也常是美好的,这就直接或间接地凸显了此类文字提倡雅游的旨趣,吴锡麒《赵味辛上春登岱图序》《桃花春水渡江图序》、王芑孙《横云秋兴图记》、方履篯《鹤楼雅集图记》及徐熊飞《李海帆大令龙湫纪游图记》《林小溪大令铜山纪游图记》等等,都是如此。“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许多贫寒士子不幸遭遇而很难忘怀的人生之恸,因此怀述往昔、寄托孝思就成为清代骈体题图文经常书写的主题,而感念慈母之教在此类主题中占比最大,吴锡麒《洪稚存同年机声灯影图序》《味雪图序》、杨芳灿《萧百堂夜纺授经图序》、李慈铭《王弢甫工部秋灯课诗图记》等都比较典型。这类作品所写的士子大都“弱遭偏露”④杨芳灿:《萧百堂夜纺授经图序》,杨绪荣、靳建明点校:《杨芳灿集·文钞》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01页。,但寡母贤淑坚毅、不隳家风,在艰难困苦中课子读书,“坏壁萝悬,破窗纸裂,吚唔课读,宛转鸣机……麻衣对母,锦字教儿。驰夕如梭,焚膏易烬。邻梦醒而残音未歇,渔讴动而微火犹明。”⑤吴锡麒:《洪稚存同年机声灯影图序》,《有正味斋骈体文》卷九。类似的场景被作家们反复描绘,其在辛酸中蕴蓄温馨。然而“爱日不恒,惊飙倏集”⑥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越缦堂骈体文》卷三,第1211页。,没等到孤儿养母,大树便已摧折,其痛如何!题图文的写作,即将图画策划者的沉痛怀念、无尽孝思成功地阐绎了出来。
清代骈体题图文涵摄的思想主题或说旨趣还有很多方面,如杨芳灿和胡敬的同题之作《小檀栾室读书图记》以及谭献《石交图记》之述论友朋情深,董祐诚《方彦闻鹤梦归来图序》、姚燮《兰窗读画图引》之描写夫妇情好,吴锡麒《张船山池南老屋图记》、徐熊飞《惺园图记》之写乡关之恋,吴锡麒《南宋画扇摹本题辞》、金应麟《谢文节公琴图后序》之论历史兴亡,金应麟《高古民梦游昆仑图后序》之讽议时政,孔广森《书周长生先生画像赞后》之推扬勇直品格,等等。这里不详细举述。
四、清代骈体题图文的文学史意义
在清代勃兴的骈体题图文,题材、思想内蕴、艺术功能丰富而艺术水准较高,那么在文学史上,这数百首作品的出现有着怎样的文学史意义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
第一,拓宽了中国古代题画文学的疆域。从历史上看,古代题画文学的远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画赞、图诗,即便从东汉武氏祠石室画像题赞论起,它的发展历史也绵亘了1800多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是骈体题图文的一个较为兴盛的时期,但此时的该类作品主要都是像赞;唐宋以后题画文学日渐繁兴,但清代以前诗歌一直是题画文学的主流,元明以降崛起的题画词、曲仍可归入大的题画诗范畴,绘画题跋则高度集中于散体,像唐代欧阳詹《征君洪涯子图赋》、李观《八骏图序》、白居易《荔枝图序》这样以骈体为主的题图赋、序和元代张雨《倪瓒像赞》这样标准的骈体图赞,一直比较少见。但到了清代,由于清代骈体题图文的兴起,中国题画文学的格局便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很大改变:骈体题图文第一次比较集中地涌现,并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从此,骈体题图文便成为中国古代题画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板块的“面积”和重要性虽无法与题画诗(含题画词曲)相提并论,也要稍逊于题画散文,但如果没有这一板块,清代题画文学将失去很大的光彩,中国古代题画文学的天空也将显得黯淡。清代骈体题图文对于古代题画文学的意义,还具体体现在它既以复古的精神,将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而后趋衰落的骈体画赞复兴起来,又以充分的创辟精神,将宋代以来主要在散体领域日益盛行的题图序、记与图画题跋用骈体来大量创作,从而开创了骈体图画序、记、题跋兴盛的全新局面,同时,它还为历来发展不足的骈体图赋打开了有一定宽广度的新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清代骈体题图文的蔚兴定性为“异军突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丰富了清代骈文复兴的内涵。清代骈文的复兴包含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的意蕴。显性层面指的是相对于元明两代骈文的相对衰落来说,清代骈文取得了超越元明的总体成就,“其高者率驾唐宋而追齐梁,远为元明所不能逮”①谢无量:《骈文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第79页。,进言之,就是超越元明而一定程度恢复唐宋甚至魏晋南北朝骈文兴盛之局面。隐性层面则与唐宋以来就“纷争不断”至清代发展尤烈的骈散之争相关。从清初开始,陈维崧、黄始等就针对文坛长期以来存在的重散轻骈观念提出了不同意见,此后由于一些散文家旗帜鲜明地贬抑骈体文,骈文界乃针锋相对地提出要为骈体争地位的一系列主张,后来更进而发展为要求和散体争文统。李兆洛在袁枚、蒋士铨、曾燠等人基础上②袁枚、蒋士铨、曾燠等人的骈文尊体主张,可参阅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6—129页。,观点鲜明地倡扬骈散一源③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云:“文之体,至六代而尽变矣,沿其流而极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引文见李兆洛选辑,陈古蔺、吴楚生点校:《骈体文钞》卷首,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4页。,其已隐然有与古文争正统之意;阮元进而强调古文“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而骈体乃“有韵文之极致”④阮元:《揅经室集·揅经室续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65—1066页。,这就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与古文争文章正统的意见。与骈文理论相配合,清代的骈文创作就如前引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所说,“凡六朝人已用骈体来写的体裁固然用骈体来写;唐宋古文家所开拓的文章领域,他们也试图用骈体来写”,骈体题图文的蔚兴就是清代骈文与古文对垒、刻意创辟的重要成果,这或许也正是姚燮《皇朝骈文类苑》将清代骈体题图文单独收录的“深意”所在。换言之,骈体题图文在清代的异军突起,既是清代骈文复兴大势影响下的结果,也是清代骈文与古文抗衡内在需要的产物。进一步讲,清代的骈体题图文以整体创辟的姿态立身于清代骈文创作大格局中,既拓宽了清代骈文创作的版图,又拓展了骈体文应用的领域,从而切实充实了清代骈文复兴的内涵。
第三,凸显了清代文人的雅趣高尚。古代读书人好文尚艺有着悠久的传统,“文”是“孔门四科”之一,“游于艺”也是儒家对君子的一个基本要求①《论语·述而篇》有云:“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引文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7页。,宋代以后,文人兼擅诗文创作和书画等艺术门类的品鉴、实践,就成为越来越明显的文化现象②明胡应麟《诗薮》有云:“宋以前诗文书画,人各自名,即有兼长,不过一二。胜国则文士鲜不能诗,诗流靡不工书,且旁及绘事,亦前代所无也。”胡氏指出元代文人比较普遍地兼工诗与书画,这种情形在明清表现得更为明显。引文见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40页。。当然,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能诗工文是读书人的基本素养,而嗜书爱画甚至挥毫绘写,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则仍有兴趣好尚的性质。就清代骈体题图文所涉及的绘画作品而言,它们很少是图画策划者自己的手笔,而一部分是前贤或时贤之作,更多的则是图画策划者邀请画家友人完成的“命题作文”。结合这些图画作品的内容来看,其蕴含着几个值得注意的信息:一是清代骈体题图文涉及的图画策划者对绘画都有比较浓厚的兴趣,他们心期隐逸、爱好雅游、展明孝思要绘图,重友情、感祖德、励苦读要绘图,就是做了一个神幻绮丽的梦也要绘图(金应麟《方云泉鸳湖旧梦图记》);二是清代骈体题图文的创作者对画学也有相当的喜好甚至擅长,特别像李慈铭、姚燮、张鸣珂、黄金台等本身即是画家,吴锡麒、胡敬等则是有名的绘画鉴赏家,他们与所题之图的策划者有着共通的喜好;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图画构成了图画策划者和题图文创作者精神交流的有意味场域,图画策划者通过画图纪实表志,题图文创作者则通过文章阐明、发扬了画图中涵纳的主旨、意趣,他们彼此藉由图画进行丰富的精神沟通、共鸣、辨阐,可以说策划图画与题图成了清代数百位文人间的一种风雅的交往方式,他们在清代近三百年的时间内藉由图画这个场域,开展了意旨广泛多样的精神交往。如果说清代大量文人图绘与诗歌、散文题写的紧密结合,已经体现了文人群体重文好艺的风雅趣尚,那么此时异军突起的数百篇骈体题图文对于题画文学的介入,则更能凸显清代文人的群体性雅趣高尚。
第四,体现了清代骈文家的人文情怀。由于受到文艺风尚和绘画题材的限制,中国古代题画文学对风雅旨趣的表达一直占据主流,山水题画长于表达山川之美以及文人的林泉之思、隐逸之趣,人物画热衷于呈现各色人物的个性、神采,花鸟草虫画则形神兼顾,常借助美好的物象寄寓士大夫高尚的人格追求,当然其中也不乏关注一般人生存苦痛以及社会动荡、政治积弊等的现实主义作品,清代的骈体题图文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如果考虑到骈体文具有突出的唯美主义倾向,那么清代骈体题图文对读书人生存苦痛以及民生、时政等现实主义题材的关注就颇值重视。前引曾燠《楞伽山房图记》和吴锡麒《家兰雪扁舟归养图序》《曹月锄操船图序》《张仲亭酒匄图序》诸文,或直笔呈现士子仕进乏途、生活窘迫的现实困境,或曲笔揭示他们表面风雅、狂放背后的精神苦楚,都体现了题图文作者对中下层读书人生存艰难的深切人文关怀。这类作品在清代骈体题图文中并不少见。姚燮《盛川乡赈图记》和董基诚《三十六陂春水图跋》是清代关注民生的代表性骈体题图文作品。前者写盛川遭逢夏雨之灾,“老弱齐命,疮痍遍衢,殍者暴露,弃儿枕藉”,因有林制军“勤求民瘼”“晨度夕咨”,方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①姚燮著,路伟、曹鑫编集:《姚燮集·复庄骈俪文榷》卷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44—1245页。这篇长文的大旨虽在赞颂主政者的贤德,但作者在其中浸润的心系民瘼之情,显然是真诚、充沛而引人瞩目的。董文的主旨与姚文相似,乃在赞颂高邮知州兴修水利之贤,②董基诚、董祐诚:《栘华馆骈体文》卷二,清光绪十四年活字本。但同为父母官的作者,其题图为文的内在指向也在于黎民百姓的生活安定。金应麟《高古民梦游昆仑图后序》的视野比姚、董之文更为阔大,文章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对高古民这样有干济之才者不为世用表达了愤慨,另一方面则对“当轴者”面对强敌入侵“犹且高谈贾策,远述桑经,谓金石可以和戎,谓采缯足以息寇”的迂执提出了态度鲜明的批评③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五。。这样具有强烈时代感、现实感的作品,既凸显了清代骈体文作家的人文情怀,又和前述各类作品一起,提升了清代骈体题图文的现实品格。
结 语
有清一代,画学发达和骈体复兴,两者交集共振,促成了骈体图文的异军突起。从清初到清末,尤其是乾嘉以降,诸多骈文家包括一部分画家,先后参与到骈体题图文的创作中来,他们以充分创辟的精神,既较多写作前人已有一定积累的骈体图赞,又大量写作古人较少涉笔的骈体图序、图记及图画题跋,即便是骈体图赋这样向来发展不足的体类,他们也不少用力。清人写作的各体题图骈文作品,主体是承续古人成法、“戴着镣铐跳舞”,但也不乏交叉越界、破体为文的可贵尝试,因而体现出值得重视的文体创新精神。作为图画作品的“解释者”,清代的骈体题图文既有针对图画形制、内容、神采、创作缘由及涵纳的人物生平、事件过程等的纪实呈现功能,又有针对图画主题、意旨的概括及阐绎功能,而后者更能见出它相对于图画的创造性价值。经由骈体题图文所阐绎出来的清代图画作品的思想主题、旨趣是非常丰富的,而这丰富的思想内涵也提升了清代骈体题图文的品质、内蕴。基于多样文体类型、章法结构和丰富思想内蕴的清代骈体题图文,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写景、造境、叙事及议论,可谓无所不擅。可以说,经过两百多年的持续累积,清代骈体题图文的总量虽无法与题画诗歌同日而语,也难与题画散文等量齐观,但已经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较大规模;其虽然存在一些写作格套、思想单薄及艺术粗糙的劣作,但也颇多命篇灵活、思想新颖及艺术精湛的杰构;其既能复前人之古,又能站在前人肩膀上拓辟、创新,开立新局。因此,它既是清代骈文拓辟、创新的重要代表,是清代骈文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整体上在清代题画文学中形成了一道靓丽多姿的风景,也为古代题画文学增添了一抹颇为新鲜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