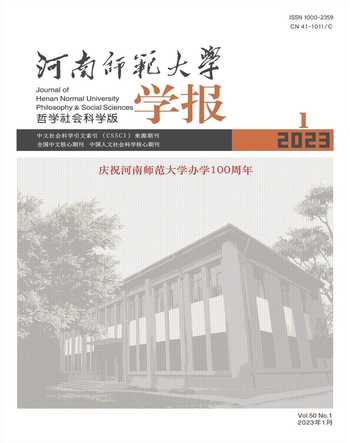情法纠结:陶刘案中的“重刑”与“减刑”之争
陈晔 任同芹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3.01.08
摘要:1932年初,发生于杭州的女学生陶思瑾杀死同性恋人刘梦莹的案件,因涉及同性戀爱、三角恋爱而备受关注。案件审理跌宕起伏,社会各界聚讼纷纭,媒体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专业律师和普通民众持续表达自身意见,在同情和仇视“杀人小姐”陶思瑾的争论中,通过轻刑与重刑的言语表达,将公众情感展示得淋漓尽致,公众情感与法律因此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既有东西方法律传统的纠葛,又有中国传统与现代法律思想的纠缠,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性的复杂面相。在此过程中兴起的公众同情,则推动了公众作为一种重要力量进入并影响社会,成为法律秩序甚至是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参与者,为我们理解大众情感如何渗入公共领域乃至于政治统治空间提供了典型的范本。
关键词:陶思瑾;媒介;大众情感;法律秩序
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1-0057-08收稿日期:2021-12-111932年2月11日发生在杭州西子湖畔的陶思瑾杀死刘梦莹案,因涉及同性恋爱以及与作家许钦文之间的三角关系,大众媒体竞相报道,社会各界聚讼纷纭,一时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围绕案件的审理,法学家、社会学家、各类报刊以及社会大众持续表达自身意见,与官方对此案的审理过程交相呼应,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刑”与“减刑”之争。近年来,随着性别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该案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对此案涉及的同性恋爱话语、生理科学以及新闻报道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却有意无意忽视了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量刑之争 主要成果有李世鹏《公众舆论中的情感与性别:陶思瑾案与民国女性同性爱话语》,《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冉琰杰《跨越阴阳:从陶思瑾杀人案看20世纪早期的同性爱》,《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1期;鄢子为《民国同性恋新闻之框架:以陶思瑾案的报道为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许维安:《“友谊”抑或“疾病”:近代中国女同性恋论述之转变(1920s-1940s)》,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重刑”与“减刑”的量刑之争作深入探讨,尝试从情感与法律的视角管窥近代中国法制现代性的复杂面相。
一、情感纠葛与陶刘惨杀案的发生
陶思瑾原属浙江绍兴籍,1928年9月,随其胞兄陶元庆由上海江湾立达学园转学至西湖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绘画系,与同系的湘籍女学生刘梦莹相识。因两人同一宿舍,“性情相投,互相倾慕”,不久即“遂同寝处”,甚至公开“自承同性恋爱不讳” 《陶思瑾与刘梦莹(上)》,时事新闻社,出版时间不详,第7页。。1929年秋,陶元庆忽然因病去世,其生前挚友、亦是小有名气的文学家许钦文“痛惜元庆之艺术”,在西湖边买地筑屋,搜罗其生前作品,设立“元庆纪念室”,因陶常偕刘前去许宅,三人遂相熟。在此期间,陶刘两人“同性恋爱”关系日益发展,并由刘提议订立盟约,发誓决不再与异性结婚 《陶思瑾杀人案判决书》,《大公报》,1932年6月1日,第2张第5版。。
然而,由于两人性格各异,情感交流并不顺畅,相处日久,时常产生种种摩擦。再加上两人均有各自的追求者,甚至自我制造了心理上的“情感”危机,以致两人相互猜忌不断加深,“此或疑别有所爱,彼或疑此已变初心,以致龃龉时起”。最为典型的就是两人与许钦文之关系。陶之胞兄在世时,许就向陶求婚而被拒。然而,其胞兄去世后,陶因家庭经济状况窘迫,又有赖于许之帮助,导致其内心极其矛盾。陶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绝对不会和他产生爱情的,我很仇恨他,我因为要受了他的帮助,我不能和他绝交,因为我家里是没有钱来给我可以读书,我的读书全是靠他的帮助,但是男子们总是这样的,一个女子一受他的帮助,他就要向女子求爱了,唉,这是必定的,男子们的心是很毒的,但是我是决不愿受了他的恩助,就把我的身献于他呵。” 《陶思瑾杀人案判决书》,《大公报》,1932年6月1日,第2张第5版。陶的这番记载应该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想法,尽管许在文学上较有才华和知名度,但陶对这样一位样貌平平且年长十余岁的文人并无多少爱慕之情 《陶思瑾与刘梦莹(上)》,时事新闻社,出版时间不详,第1页。。由于此时陶、刘两人处于热恋,陶常常将自己的痛苦向刘倾诉。虽然刘担心陶会因诱惑而抛弃自己,但更多的是对陶处境的同情。真正让两人关系出现裂痕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刘翻看了陶的日记,发现陶记载了一段异性追求者的文字,加重了其心中的担忧。同样,陶亦怀疑刘并非专注于自己,还爱着另外一个人,认为这与自己的情感付出明显不均衡,两人因此经常出现口舌之争,在双方争论较为严重之时,彼此甚至以“断交”相威胁 《湖滨喋血之刘梦莹惨杀案》,《中华周报》,第28期,1932年5月12日,第22页。。
在陶、刘关系出现微妙变化的同时,被陶拒绝的许钦文则逐渐将目光转向了刘。1930年5月,在刘担任主角的话剧《史推拉》演出之际,许冒雨前去捧场,事后在报刊上对其大加揄扬,“竭意趋承,以图得其欢心”,博得刘之好感 《陶思瑾杀人案判决书》,《大公报》,1932年6月1日,第1张第4版。。这虽然减轻了许对陶的追求,但却加重了陶、刘之间的矛盾,两人“疑忌日深,时相口角”,感情明显疏淡 《陶思瑾杀人案判决书(续)》,《大公报》,1932年6月2日,第1张第4版;《刘梦莹案起诉理由》,《大公报》,1932年3月30日,第2张第5版。。再加上该校绘画系助教刘文如与陶“感情甚好”,导致刘怀疑两人亦有同性恋爱关系,并视刘文如为情敌,要求陶与其“绝交”,“彼此坚持,致感情益趋破裂” 《陶刘案判决全文》,《时报》,1932年5月29日,第1张第3版。。
1931年寒假,刘因其胞姊刘庆荇由日本归国,同其暂住上海江湾,陶则返回绍兴老家。但刘始终怀疑陶移情别恋,专门写信要求陶与刘文如断绝关系,并嘱以书面答复,陶置之不理。数日后,刘再次写信催促陶尽快答复,甚至以杀死刘文如或陶思瑾并公布其同性恋爱之秘密进行威胁 《陶思瑾杀人案判决书(续)》,《大公报》,1932年6月2日,第1张第4版;《刘陶惨案二审判决书全文(续)》,《大公报》,1932年8月19日,第2张第5版。。1932年1月沪战爆发后,刘返杭避难于许宅。几天后,陶亦返杭为刘文如回川送行,路过许宅发现刘暂住于此,两人简短言语交流,随后陶即借口赴校打听消息,前往艺专送别刘文如,并在艺专留宿两晚,2月8日午后过许宅,计划于当天赶回绍兴,因刘极力挽留,陶亦暂留许宅,并邀请刘同往绍兴游玩。后因刘欲等其姊复信,陶遂决定11日独自返绍。但就在陶准备返绍的当天下午,许钦文外出送别友人,佣人亦被陶遣出购置雪花膏,许宅仅剩的陶、刘两人,因重提刘文如之事发生激烈争吵,陶一时愤起杀死刘梦莹,刀伤达49处,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因同性恋爱而引发的惨杀案。
二、人情与法理:“情杀减刑论”的提出
惨杀案发生之初,陶曾称刘为“自杀”,嗣后又说系杨信之所杀,但被问及杨信之为何人,却又不得而知,导致案情出現戏剧性变化 《陶思瑾与刘梦莹(上)》,时事新闻社,出版时间不详,第72页。。刘姊庆荇则称陶系“预谋杀人”。承办此案的检察官韦希芬经过多方侦查审讯,认为刘“绝非自杀”,乃是陶乘刘沐浴后且许宅无他人之时,持刀将其杀害,“为故意杀人无疑”,应对陶提起公诉 《刘梦莹案将开审》,《大公报》,1932年3月27日,第2张第5版;《西子湖边:刘梦莹真象》,《大公报》,1932年3月29日,第2张第5版。。
1932年4月2日,杭县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陶一改前此说法,承认刘为己所杀,但却强调其行为是出于自卫,并非故意杀人。其原因则在于刘要公开两人同性恋的秘密导致双方冲突,刘拿刀欲砍杀自己,自己奋力抗争将刘杀死。对于刘身上多处刀伤,陶则辩解是在情急之下乱劈所致,并非有意为之 《轰动杭市社会刘梦莹案法院初审详记》,《大公报》,1932年4月8日,第2张第5版。。
陶的辩护律师李宝森则提出陶的杀人行为是因精神衰弱病所致。两人虽因意见不合,时有争闹,但并无深仇大怨,不至于置对方于死地,“如非素有精神衰弱之病症,及当时受有绝大之刺激,而使神经错乱者,断不致发生如此不幸之事件”,请求法院选任医师进行鉴定,以“明瞭犯罪之真相,而量刑上亦可不致有畸轻畸重之弊” 《同性爱发生不自然举动》,《时报》,1932年4月8日,第3版。。原告方的意见遭到被告方的强烈质疑,刘庆荇声称“既有神经病,为什么能进艺术院” 《杭州刘梦莹案开审》,《时报》,1932年4月3日,第3版。。双方针对陶是否有精神疾病产生意见分歧,无疑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亦增加了审理的难度,杭县地方法院不得不以“证据不足,尚须调查”为由推延案件的审判进程。
4月8日,杭县地方法院以陶刘两人日记中记载的同性爱有碍风化,秘密开庭审理,听取原被告双方意见。围绕陶是否患有神经病抑或精神病问题,原被告双方及其律师展开了激烈辩驳。原告对于陶患有“神经衰弱病”的说法,质疑被告“何以第一次诉状并不提及”。被告律师对于刘庆荇在法庭陈述时使用“神经衰弱病”来混淆其与精神病的区别,则明确指出“两者不同”,陶“系精神衰弱病,应请医师检验”。原告则辩驳称“如因神经衰弱而杀人可以减刑,则人人杀人,皆可减矣” 《刘梦莹案杭法院二度秘密开审》,《时报》,1932年4月10日,第3版。。庭审之后,针对陶“精神衰弱病”进行鉴定问题,刘庆荇再次具呈诉状,提出陶犯罪时“并无心神耗弱之症,应请驳斥鉴定之请求” 《刘梦莹案两次开审后刘姊具状声请驳斥鉴定请求》,《时报》,1932年4月12日,第5版。。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于陶精神病问题的辩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各种报刊挖掘该案各类材料,长篇累牍予以报道,杭州某报纸还专门制作该案舆论测量表,各地戏院则纷纷排演戏剧,招徕观众。上海爵禄新剧场等戏院特地派专员前去调查,并据此编排戏剧,打着“同性恋爱妒情惨杀血案哀情悲剧”的旗号在报端登载开演广告 《爵禄新剧场》,《申报》,1932年4月13日,本埠增刊第4版。。杭州娱园游戏场亦公告排演新剧,遭到杭州艺专强烈抗议,并以“有碍风化”呈请杭州市府“即予查禁” 《刘陶案排演新剧》,《时报》,1932年4月27日,第5版。。
在此期间,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也发表文章指出,根据各方披露之资料判断,两人心理上“俱不无变态”,且“变态的感情生活已经达到很深的程度”。对于被告律师提出的陶患有精神衰弱,潘氏认为“似乎还是说得轻的”,其“精神病的症候实在很显著”,甚至产生了“很强烈的幻感,一种被迫害的幻感”。由此,他认为陶杀死刘“不但出乎嫉妒的心理,而且出乎因嫉妒而生的被迫害的幻感,并且出乎附带着幻觉的那种幻感”。由此可见,潘光旦认为陶思瑾已呈现出严重变态心理,甚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精神病迹象,在一定程度上与被告律师形成呼应。
除此之外,在上海法政学院任职、毕业于法国波尔多大学的法学硕士和医学博士阎世华亦公开发表文章提出,“杀人者死,古今同科,杀人而不判以死刑,除正当防卫外,精神疾病,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法律是明白规定的”,支持对陶的精神病症进行鉴定,并主张在法律量刑上予以运用 阎世华:《精神病与杀人罪》,《时事新报》,1932年4月21日,第2张第2版。。
可能正是因为此种舆论之影响,在4月23日的庭审中,法院对陶杀人细节的陈述“非常注意,并反复研训” 《刘梦莹案辩论终结》,《大公报》,1932年5月15日,第2张第5版。。四审开庭前夕,潘光旦再次发表文章支持被告辩护律师提出的精神病鉴定问题,认为这是中国法医学和犯罪学“前途很好的现象”,批评旧式律师至今还在“责任”和“抵罪”这些观念上做文章,“不识变态心理和行为为何物”。强调此案辩护律师的努力,对于这种旧局面的打破“一定会有几分贡献”,无论此后检验结果如何,“他们的努力是不虚掷的” 潘光旦:《再提陶刘妒杀案》,《华年》,第1卷,第5期,1932年5月14日,第82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精神病学专家极其缺乏,精神鉴定事实上操作起来又存在极大困难,法院虽然对此问题格外注意,但鉴定后的结果“是否能供法律上的采用,亦是问题”。因此,在5月14日的庭审中,法院以“目前尚有困难”,决定对陶的精神状况“不鉴定”,同时根据陶案发前后及其在看守所的心理状态宣布“在科刑上已有所斟酌” 《刘梦莹案判决》,《大公报》,1932年5月21日,第2张第5版。。
经过四次审理,杭县地方法院于5月20日正式宣布判决结果。法院认为陶故意杀人且行为残忍,但同时也指出其杀人原因在于两人习惯不同,性格各异,因此易起冲突,以致情感破裂,“初非由于恶性的行为,论情自堪惘恕”,依照刑法相关规定减轻刑罚三分之一,处以无期徒刑,褫夺公权无期 《陶思瑾杀人案判决书(续)》,《大公报》,1932年6月4日,第2张第5版。。由此可见,尽管杭县法院认定陶思瑾杀人行为残忍,且不具有正当防卫性质,但并未支持原告以及检察官提出的预谋杀人的判定,虽然陶的精神病鉴定问题亦因各种困难及适用问题未予支持,但从判决结果来看,情感因素在量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陶刘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同性恋爱关系,且两人之间并无深仇大恨,只因一时感情冲动导致杀人行为,因此,法院试图在法律与情感之间寻求平衡,陶也因此获得了减刑处罚。
但这样的判决结果并未得到各方信服。法院判决当天,陶当庭声明不服,声称自己是“抗斗杀人,与其他杀人不同”。刘庆荇则认为法院对陶的量刑较轻,提起上诉,“请处死刑” 《刘、陶上诉》,《大公报》,1932年6月3日,第2张第5版。。该案检察官韦希芬则坚持陶不仅是预谋杀人,而且手段残忍,“于情于理,绝无可悯恕之余地”,主张“不应减刑”“应从重办”,亦提起上诉 《刘梦莹案四审经过(续)》,《大公报》,1932年5月22日,第2张第5版;《陶思瑾案检察官韦希芬亦上诉》,《大公报》,1932年6月12日,第2张第5版。。另一位原告律师高凤洲则从法律角度强调“立法已觉从宽,处刑不能不严” 《刘梦莹案四审经过(续)》,《大公报》,1932年5月22日,第2张第5版。。因此,该案的初审判决不仅并未降低公众对案件的关注程度,反而激发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大的兴趣,时人的观感认为该案“绝不因国难问题而稍减社会上注意” 止水:《关于陶思瑾刘梦莹的观感》,《斗报》,第2卷,第8期,1932年6月11日,第9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对该案的关注“已由新奇的注意,进而为情杀意义的探讨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情杀减刑论”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是上海《时事新报》记者黄天鹏。
黄天鹏以“天庐”之名在《时事新报》晚刊“青光”栏目发表《论“情杀”》一文,指出“情杀”有别于“仇杀”,“杀人当然是残忍的变态行为,但‘仇杀和‘情杀显有分别。‘仇杀姑不具论,‘情杀情有可原。法律虽有本身的尊严,但‘法律不外乎人情,对于妒情的情杀的行为,应有相当的同情和谅解,凡为爱情而犯罪的减轻刑罚。”依据此种逻辑,论者主张对陶“应从轻减刑,因为这是为了爱情的‘情杀” 天庐:《论“情杀”》,《时事新报(晚版)》,1932年5月22日,第2版。。在看到陶刘案初审判决书后,黄天鹏再次发表文章提出,陶杀刘“完全为爱情的妒杀,我们一向主张情杀减刑论,法院原情悯陶的从轻发落,我们当然表示平允” 天庐:《同性恋爱》,《逍遥夜谈选》,广益书局,1933年,第64页。。由此,黄天鹏正式提出了“情杀减刑”的观点,表达自身对陶刘案量刑方面的意见,掀起了社会各界持续不断地对该案量刑的争论。
三、减刑与重刑:社会各界对案件的量刑之争
对于陶的量刑问题,在杭县法院审理过程中,原被告之间的激烈争论还局限在法庭之内。黄天鹏在公众媒介上提出“情杀减刑论”来呼应杭县法院初审判决结果,并在随后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倡此种观点,声称社会上“不少人具有同样见解,为补救这无情而只有利害关系的社会,‘情杀减刑论的舆情,今日愈有提倡的必要”,直接引发了关于陶刘案减刑与重刑问题的争论由庭内迅速向庭外扩展,两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使案件的审理充满波澜与起伏。
值得注意的是,陶刘案初审判决之时,恰逢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讨制定《大赦条例》,由于该案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各立法委员亦格外注意。1932年6月11日,该条例三读会上,对于“杀人出于预谋或有残忍行为”是否应在赦刑之列,辩论长达两个小时,陶刘案成为各立法委员引证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与刘梦莹同为湖南籍的立法委员、亦是立法院代院长邵元冲之妻张默君就主张对陶从重处罚:“杀人是残忍不德的行为,法律自应严重加刑处罚,我如为法官,必处陶思瑾以死刑。”最终该条例修正为“杀人出于预谋或有残忍行为”不在减刑之列 《要是张默君来审理,刘陶案陶思瑾决无生望》,《时报》,1932年6月16日,第3版。。
张默君的这种说法经媒体报道后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潘光旦指责张“又在‘残忍二字上大做其文章”,称其为“好一个厉害的执法者”!讽刺张根本不懂犯罪心理学 潘光旦:《无独有偶的同性奸杀案》,《华年》,第1卷,第11期,1932年6月25日,第25页。。《大赦条例》审读会后,主张对陶重刑的立法委员“又写私人信给杭州的执法者,贡献意见,要加重罪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浙江省高等法院对陶的判决结果 耐冲:《刘陶案之舆论》,《世界晨报》,1932年8月4日,第2版。。7月30日,浙省高院否决了杭县地方法院的初审判决,认定陶是预谋杀人,其杀人原因系双方感情“积结酝酿而成”,并非出于“高尚纯洁之爱情”,也不存在“一时情感之冲动”的因素。因此,在量刑时更加注重殺人行为中“预谋”因素的考量,陶最终被浙省高院判决死刑 《陶刘惨案又一段落》,《大公报》,1932年7月31日,第1张第4版。。
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公布后,陶的胞兄陶沛霖及被告辩护律师均表示不服,声称陶的杀人行为是出于抵抗,“初无杀人意识,更无预谋事实”,指责浙省高院对案件不公开审理是违法行为,并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经此波折,社会上对此案的兴趣更加浓厚,舆论“忽又活跃起来” 潘光旦:《只不讲理》,《华年》,第1卷,第18期,1932年8月13日,第342页。,“拍手称快者有之,抚膺惋惜者有之……各有各的见解,纷纷争辩,颇不一致” 《陶案讨论会》,《大晚报》,1932年8月1日,第2版。,可以说是“闹得满国风雨” 思君:《未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生活》,第7卷,第34期,1932年8月27日,第639页。。有的报纸以表格公开征集社会意见 絜非:《西湖春讯》,《申报》,1932年5月4日,本埠增刊第3张第12版。,上海的《大晚报》为此专门在报纸上开辟“陶案讨论会”专栏,发表社会各界对案件的看法;《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组织“陶案后援会”,亦持续不断推出专题文章。同时,上海青年界季步飞、王铁华、黄奂若、陈斯英、陆怡等十余人还发起组织“陶刘情杀案讨论会” 潘光旦:《只不讲理》,《华年》,第1卷,第18期,1932年8月13日,第343页。,对该案“加以详细之探讨”,在报端公开征求会员 《被判死刑之陶思瑾》,《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8月17日,第8版。。一些热心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士纷纷加入其中,积极展开调查,甚至还专门推举人员赴杭探问陶以了解案情 徒然:《望远镜与显微镜》,《生活》,第7卷,第34期,1932年8月27日,第633页。。据时人观察,此时上海各报的“附张上都主张为陶辩护,说情杀不应处死刑, 还有把陶比作莎乐美,好像莎乐美的杀人是情有可原的” 《时事短评:陶案讨论会》,《社会与教育》,第4卷,第12期,1932年8月13日,第2页。。社会各界的持续参与以及报刊的大肆渲染,推动舆论对此案量刑的关注和辩论走向高潮。
看到判决书全文后,一向主张情杀减刑的黄天鹏批评浙省高院的判决与初审判决“完全相反”,却与张默君的“意旨完全相同”,再次强调“法律有时也要原情,‘仇杀和‘情杀应有分别。仇杀是残忍的行为,自应依法严办;情杀罪有可原,则应从轻处罚”,呼吁有情之人对此判决“提出抗议” 天庐:《陶思瑾的死刑:三论刘梦莹情死案》,《时事新报》,1932年8月1日,第4张第3版。。从当时的大众舆论来看,应该说黄的“情杀减刑”主张代表了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因此,亦得到了不少社会大众的赞同和响应。西安的报纸上就有人不无深意地指出,浙省高院的判决“完全合着张委员的心愿”,在他看来,“情杀”与“仇杀”存在明显区别,陶杀刘的动机“确实由于爱与妒的表现”,“并不能以之与残忍不德的‘仇杀相提并论” 高攀:《三种不同的杀人》,《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8月15日,第6版。。署名“让枝”的艺术工作者则从法律与人情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各文明国家的法律均采取外严内宽主义,对于此案由同性三角恋爱产生的妒杀“更为常人绝无”,主张“法应赦免”,并进一步指出陶刘两人“这种爱之冲突,比之普通杀人犯,似当作一个例外”,判处死刑“为人情所不许” 让枝:《一个友人的意见》,《大晚报》,1932年8月3日,第2版。。远在广西南宁的李宝泉亦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假如陶刘两人“为纯粹爱情”,则陶即使有残酷杀人与预谋杀人之行为,“其罪不当重判也”,强调法律固有自身之尊严,但“决不能违背人情” 李宝泉:《爱情与民族:刘陶案所引起的感想》,《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8月18日,副刊第3版。。上海的罗玲在看到陶被判处死刑后,亦产生“一种惋惜的叹息和不服的共鸣”,强调陶之所以杀刘,“总免不了一个‘情字”。即便是预谋杀人,“于理虽属不当,但于情尚为可宥” 罗玲:《不服的共鸣》,《大晚报》,1932年8月5日,第2版。。法律学者林彬亦认同该案“是个情杀,当不能和其他的杀人罪一概而论” 林彬:《陶思瑾处死吗?》,《大晚报》,1932年8月4日,第2版。。值得注意的是,以律师为业的张清樾还提出陶是“偶意杀人”,出于“一时气脉之愤作,妬情之勃发”,认为一审量刑“不得谓非适当”,对二审判决结果提出强烈质疑 张清樾:《偶意杀人与预谋杀人》,《大晚报》,1932年8月2日,第2版。。蒋亚峤则认为无论陶杀刘是预谋还是偶意,是自动还是被动,“其为情茧所缚,愤而出此,事实确鉴”,即使她是出于预谋杀人,死刑的判决依然“还有商量斟酌的余地” 蒋亚娇:《赋性的孤僻》,《大晚报》,1932年8月5日,第2版。。同样,还有人对高等法院认定的“预谋杀人”表示怀疑,反问如果是有预谋的行为,“为什么会杀到四十九刀之多?为什么曾杀的这么残忍呢” 高鹤鸣:《听了陶案第二审宣判之后》,《大晚报》,1932年8月8日,第2版。。
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舆论都倾向主张对陶减轻刑罚,亦有不少人认为陶的杀人行为非常残忍,应从重处罚。浙省高院宣判当天,有守在法庭前的观众就认为陶“铁石心肠,竟惨杀热恋之同性,其死固由自取也” 《同性恋爱惨剧,陶思瑾判处死刑》,《中央日报》,1932年8月2日,第2张第2版。。谢宙中则强调陶的心肠与一般人有“不同的狠毒与凶暴,嫉妒性特别大”,甚至说这样的人“我们现在不除掉她,她将来更不知杀害多少人” 谢宙中:《陶思瑾该处死刑》,《大晚报》,1932年8月4日,第2版。!显然,谢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来看是比较极端的一种,尽管如此,仍得到某些人的赞同。有人还针对甚嚣尘上的“情杀减刑”论调指出:“杀人者死,律有明条。陶女士在举刀以前,早就应该知道,是杀人抵罪,固应得之咎,乃欲希冀减刑,这无非表示其心理的怯懦与卑劣。”该论者甚至还提出假如两人之间“有所谓情的话,正应相殉以赎咎” 《时事短评:陶案讨论会》,《社会与教育》,第4卷,第12期,1932年8月13日,第2页。。针对此种说法,黄天鹏再次发声,重申自己始终主张“情杀减刑论”,强调陶的杀人动机“是为爱情而起,就这一点纯情的动机而论,就是预谋杀人而且残忍,也应该减刑判决”,批评社会上一些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情,更不懂什么叫做‘情殺,‘情杀减刑自然不必说了”,呼吁主张重刑论者“卸去你们冷酷无情法律的眼镜,来读些纯情的文字,创造个爱情的新社会” 天庐:《陶刘情杀案的社会意义》,《时事新报》,1932年8月6日,第3张第4版。。
对于社会上的重刑与减刑之争论,持续关注此案舆论的潘光旦则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无论社会舆论与司法当局如何看待此案,都不能忽视陶“是有精神病倾向的”,强调如果不从此角度来研究案情,“而唯感伤主义是问,而唯‘杀人者抵罪的社会普通心理是问”,都是不科学的。在此基础上,潘光旦提出,在陶的家世与精神状态未经确实鉴定以前,“死刑的判决固属失诸操切武断,减刑论者根据也是异常薄弱”。同时,对于黄天鹏提出的“情杀”与“仇杀”有别的论调,潘氏也予以反驳:“情杀与仇杀的界限,事实上是很难分别的。以爱情始,而以杀害终,杀害的动机,间接虽发乎‘情,而直接未尝不出乎‘仇之一念。” 潘光旦:《只不讲理》,《华年》,第1卷,第18期,1932年8月13日,第343页。由此可见,潘氏一方面依然主张对陶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作为量刑的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也对黄天鹏等人的“情杀减刑论”予以反驳,强调“情杀”与“仇杀”既无严格的界限,也无明确的区别,无论是“情杀减刑”的“唯情派”,还是“杀人者抵罪”的“重刑派”,都缺乏对案件“事理”的推求。
同样,《生活》周刊记者邹韬奋也以回复读者来信的形式对“情杀减刑论”提出异议,反问“对爱人而忍下这样残酷无比的毒手,‘爱字作何解释,像我这样的‘俗物,实在不懂”。针对黄天鹏主张的“情杀减刑论”,邹氏提出“爱人只应该爱,不应该杀,因爱她而要杀她,这种爱何用我们提倡?下毒手惨杀仇人,固是‘冷酷无情,下毒手惨杀爱人,便不算‘冷酷无情而算得仁爱多情吗?我也觉得不懂”,指出黄的论调与创造爱情的新社会“有什么相干呢” 思君:《未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生活》,第7卷,第34期,1932年8月27日,第639页。。
面对潘光旦、邹韬奋等人的质疑和批评,黄天鹏再次发表文章予以反击。他依然坚持“情杀减刑论”的观点,批评许多人不懂“情杀”与“仇杀”如何分别,而曲解他的观点。针对邹韬奋的批评,黄氏强调其虽然主张情杀减刑,但是并不提倡杀人的爱,“生活记者以为主张情杀减刑就是提倡毒杀爱人,那是他的‘生活逻辑,我也‘实在不懂”,并希望大家能够认清“主张情杀减刑论果,并不鼓吹杀人造因,因果固有若干相连,但不能倒置”。他指出真正的舆论家固然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意见,对于事实不能一笔抹杀。因不满各方舆论的攻讦,黄天鹏宣布退出陶刘案的讨论 天庐:《结论陶刘情杀案并答生活记者》,《时事新报》,1932年9月2日,第3张第4版。。
此后,《时报》记者朱惺公也就陶刘案与黄天鹏、邹韬奋等人进行商榷。他虽然也承认黄、邹两人的观点“都不无理由”,但也指出黄主张的“情杀减刑论”以及邹的反对减刑说,均过于看重已经形成的“事实问题”,而忽略了人类真正的“先天本性”和“后天理性”,主张要更进一步去探求事实背后的一切远因与近因。在此,他提出陶的杀人动机既不是单纯的“情杀”,也不是偏执的“仇杀”,“当归之于‘妒杀”,因为有了“妒”的观念,在神经受到重大刺激之时,便可能产生杀人以泄愤的行为。尽管如此,朱惺公对于陶的量刑标准还是持谨慎态度,声称因为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他本人“不敢主张”陶的减刑 朱惺公:《陶案的犯罪心理剖析》,《惺公评论集》,机杼出版社,1933年,第59页。。
可能是受黄天鹏宣布退出陶刘案辩论的影响,虽然社会舆论对该案的关注并没有完全停止,但却明显趋于消沉,此后双方的辩论越来越少,各报开辟的陶刘案讨论会亦大多宣告结束。尽管如此,围绕陶刘案所展开的重刑与减刑之争,还是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正因如此,最高法院在接到各方上诉后,对该案“殊为重视”,甚至曾一度打算提解陶本人及传唤许钦文、刘庆荇等关系人到京审讯《陶思瑾案最高法院将提陶到京审讯》,《中央日报》,1932年9月29日,第2张第2版。。隨后,最高法院经过半年多的“缜密审查”,认为二审对于该案“事实方面尚未侦讯详晰”,将原判撤销,发回浙省高院更审《最高法院判决陶思瑾案发回更审》,《中央日报》,1933年5月21日,第2张第3版。。1933年8月11日,浙省高院作出更审判决,以陶虽无预谋杀人,但两人“素有情感”,“亦未始不可设法避免”,综合考察其杀人行为“亦属无可悯恕”,不过考虑到该案发生于“大赦以前”,遂减刑处以无期徒刑《陶思瑾杀人案更审判决全文》,《京报》,1933年8月28日-29日,第5版。。然而,由于该院检察官季赓扬不服,认定陶杀刘“确系出于预谋”,与事实“殊有出入”,再次上诉至最高法院《因陶思瑾未判死刑,检察官不服》,《益世报》,1933年9月9日,第3版。。1934年2月8日,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原审判决“认事引律,尚无不当,上诉意旨,纯系出于推测,难谓有理由”,决定维持原判《陶刘情杀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申报》,1934年3月17日,第3张第10版。。至此,跌宕迁延两年之久的陶刘案审讯终结。
四、结语
民国时期是现代中国法律秩序重建的重要时期,明显地呈现出变动社会的过渡性特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司法改革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执政的国民党则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司法体系。正如著名汉学家林郁沁所说,“在崛起的大众媒体,一个咄咄逼人试图集权化的国家,和羽翼未丰的、试图建立制度独立性的司法系统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涌现了一系列轰动性的案件” 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3页。。因同性恋爱、三角恋爱引发的惨杀案,陶刘案不仅满足了社会大众窥视私人情感的娱乐心理,而且因为案件审理的跌宕起伏成为持续吸引公众眼球的社会热点话题,“轰动性的犯罪审判和媒体炒作成为了舞台”,在制造消费的同时,亦贩卖着公众的情感,最终将该案件演变为一桩被媒体极度渲染的社会公共事件。
案件发生时期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化进程已经有了很大的推进,各种报刊媒介日趋繁盛,生存空间极大拓展,为公众提供了参与社会舆论的公共平台。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特征的都市文化迅速崛起,大众娱乐消费浪潮席卷而来,“软性新闻受到欢迎” 高郁雅:《阮玲玉“新女性”事件与上海新闻界:兼论小报在其中的作用》,连玲玲主编:《万象小报:近代中国城市的文化、社会与政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256页。,公众参与社会的意识觉醒,对各种社会问题积极发表意见,在与媒体的互动中逐渐形塑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参与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法庭的审判,社会各界包括媒体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专业律师和普通民众都参与到案件的讨论中来,依托各种媒体提供的公共平台,在同情和仇视“杀人小姐”陶思瑾的争论中,通过轻刑与重刑的言语表达,将公众情感展示得淋漓尽致。这种极富感染力的集体审判,既是制造现代都市情感的消费者,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讨论者。对此,时人就观察到,“该项事件,渐由事实问题而变为法律问题” 张清樾:《偶意杀人与预谋杀人》,《大晚报》,1932年8月2日,第2版。,代表政权统治合法性的法律与公众同情也因此展开了激烈的博弈。
法与情的问题,本来是传统中国社会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话题,但是在近代中国的场域中却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形式。这里面既有东西方法律传统的纠葛,又有中国传统与现代法律思想的纠缠,因而,伴随着陶刘案而兴起的法律与人情的讨论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法律现代性问题与传统文化中的刑罚观念之间所具有的矛盾甚至对立的一面。时人就曾指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法律思想……殊不知近代法律精神,对于‘抵偿观念已大修改,杀人者有时竟不抵命。除了绑票和行抢戕杀事主外,就是谋杀、故杀,也分情节而有轻重。” 白羽:《法律与人情》,《北洋画报》,第23卷,第1118期,1934年7月24日,第2页。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对于法律与情感的讨论已经非常普遍,从当时主流的言论来看,“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思想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时社会刑罚观念的新变化,也因此为诸如陶刘案这样的案件提供了公众同情兴起的特定时代氛围,公众作为一种重要力量进入并影响社会,成为法律秩序甚至是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参与者。由此而言,陶刘案中社会公众掀起的“轻刑”与“重刑”的量刑之争,则为我们理解大众情感如何渗入公共领域乃至于政治统治提供了非常典型的范本。
The Entanglement of Emotion and Law:The Dispute between “Severe Punishment” and “Commutation” in Tao Liu Case
Chen Ye1,Ren Tongqin2
(1.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2.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In early 1932, the case of Tao Sijin, a schoolgirl who killed her same-sex lover Liu Mengying in Hangzhou,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it involved same-sex love and triangle Love. The case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one, with the media, psychologists, sociologists, professional lawy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and expressing their sympathy and hatred for Tao Sijin, the Miss Murder. The public sentiment and the law thus played a fierce game, in which both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legal traditions were entangled,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modern legal thought were also entangled, to some extent, it reflects the complex aspects of modernity of the legal system in modern China. The public sympathy that emerged in this process promoted the public as an important force to enter and influence society,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order and even the social order, providing a typical model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popular emotions penetrated into the public sphere and even the space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Key words:Tao Sijin; medium;popular emotion;legal order[責任编校王记录]
作者简介:陈晔(1991—),女,河南永城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任同芹(1975—),女,河南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