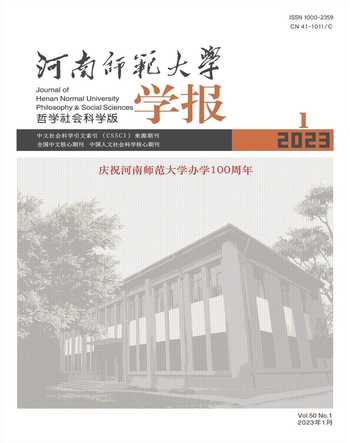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的融合:儒家伦理思想的德育价值转化
崔振成 李志前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3.01.21
摘要:儒家伦理思想秉持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一体融合的价值立场。道德主体性表现为内在超越与刚健有为;伦理他者性体现为主体间伦理互系共在、主体对社群的使命与责任担承;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的一体融合即内圣与外王在个体道德生命建构中的伦理融化与统摄守一,这一伦理设计有效规避了主体的“单子式”僭越、主体间的伦理冲突以及主体与社群间的价值裂解。在廓清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并保持必要的文化警惕前提下,儒家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一体融合的伦理思想为当代德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双重价值参鉴。在理论理性上,当代德育首先应致力于受教育者道德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培育其他者性伦理格局与使命自觉,最终实现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的一体融合;在实践理性上,当代德育要注重道德体验与伦理实践的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儒家伦理;德育价值转化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1-0151-06收稿日期:2022-01-2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逻辑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中华传统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人合一、顺道而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合而生、和而不同”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供给深沉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启示。从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价值营养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办教育”和“自主培养人才”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本气质在于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一体融合的价值立场与精神格局。其中,“道德主体性”的诞生与自强表现为“为己、克己、己立、慎独、自强不息”等“内圣”性道德生命塑建;“伦理他者性”的确立与刚健表现为“安人、立人、达人、爱人、刚健有为”等“外王”性伦理格局造就;“主体性”与“他者性”一体融合的儒家伦理思想是将“内圣”和“外王”的“双重伦理事业”统合交融,既注重主体性道德生命的挺拔,又注重他者性伦理生命的推延,从而诞生具有中国智慧、中国气派的原创性道德哲学。儒家伦理思想对当下我国的道德教育具有返本开新的启示价值:道德教育应该致力于“我”的道德主体性与“我们”的伦理他者性一体生成,将“我”的道德人格与“我们”的伦理实践全纳入人的完整道德生命建设之中。
一、道德主体性诞生:儒家伦理思想的起点
儒家对主体的力量始终抱有乐观的自信,强调“古之学者为己”和“为仁由己”的立己之学。儒家伦理念兹在兹于对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主体性生成,并坚持“颠沛造次必于是”的主体意志与主体实践。
(一)儒家伦理致力于道德主体性的生成
儒家对道德主体性的诞生与挺拔充满了高度的敬畏感和执着的建构性努力。儒家伦理认肯人是道德性存在者,道德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人既以道德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又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人须臾不可离开道德而在,“无论是多么强大的要求或高尚要求,如果离开了道德人格的要求,便没有任何价值;只有作为道德人格要求的一部分或者手段时才有价值”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何倩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14页。。道德主体性“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就可以庄严自持而修为己之德、以内化外而建君子之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儒家就是讲主体,客体是通过主体而收摄进来的,主体透射到客体而且摄客归主。”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三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63页。反之,孔子最担忧的是道德主体性缺失的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无论在安身立命的终极性价值追求上,还是在“修齐治平”的建功立业上,无不以个体道德主体性的生成为本质规定。
(二)道德主体性诞生的标志
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如此重视道德主体性的事实性生成,那么,其道德主体性诞生的标志是什么呢?在儒家看来,首先,道德主体性的诞生表现为内在超越。一方面要内心真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礼记·中庸),“诚于内”自然可以“形于外”。“儒家对道德的高度真诚与笃信是其主体自觉性的极致。”肖群忠:《真诚性、创发性是儒家道德主体性的根本》,《哲学分析》,2016年第4期。只有“自明诚”的功夫才能“尽心、知性而知天”,达至“此心光明”之境界,从而做到“克己复礼”的自我约束与自我超越。另一方面要否定性超越,即自我充分意识到生物欲望失控的危害,必须“克己复礼”和“反求诸己”,并在“自我否定”中不断自我反思、虚心若愚、求知若渴、内在超越。孔子所自述的“十五有志于学”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觉解过程,其实就是一路自我否定性超越达至道德自由的过程。否定性超越是儒家德性进阶的根本动力。其次,道德主体性的诞生表现在刚健有为。一方面要弘道立身,即发扬光大儒家所极力倡导的道义文明。儒家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德主体必须捍卫和弘扬儒家的仁道原则、礼义文明、哲思学意。诚如曾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要行道立业,即道德主体要由“内圣”而“外王”,在“立德、立功、立言”中确立道德主体性的意义、价值与成就。总之,儒家道德主体性诞生的标志表现为“克己超越”与“有所作为”的圆融一体。
(三)儒家建构道德主体性的教化方案
儒家不认为“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明确指出道德主体性永远具有“未完成”的特质。儒家建构人的道德主体性的教育方案,是以背景创设为基础,以内在修养为功夫,以外在范导为促发,以互系互就为进业,从多维度汇聚教育合力。首先,背景预设。孟子说人固有“四端”,而“四端”之引出需要“万物皆备于我”的情景。如此一来,“我”的道德主体性诞生之前必须“先在”预设“背景性安排”:家必讲孝慈、邦必修文德、国必制礼乐。教化情境创设是个体道德主体性觉醒的滥觞。其次,自主修为。儒家强调学以致道、见贤思齐、自主超拔的进德功夫。强调“志于道”和“博学而笃志”的伦理意志、“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伦理自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伦理信念、“吾日三省吾身”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伦理反思以及“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的修养实践等。再次,伦理范导。儒家特别重视伦理与道德间的双向互证:“克己复礼为仁”与“人而不仁如礼何”。儒家讲的自我进德总是离不开他者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无论是“入孝出悌”,还是“四海之内皆兄弟”,都诠释了在伦理的关系世界中建构道德主体性。安乐哲指出:“儒家的个人在内在关系、建构性关系中……儒家对人的理解是叙事性的,人不是永恒不变的灵魂,不是‘现成的人,而是‘生成中的人。”安乐哲:《儒家伦理学视域下的“人”论:由此开始甚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美国汉学家黄百锐也认为,“我们以生物有机体获得生命,通过和同类建立关系而成人”AmyOlberding.DaoCompaniontotheAnalects.Dordrecht:Springer,2014,p192.。总之,儒家建构道德主体性的教化方案是多维共建。
(四)儒家道德主体性的价值局限性
儒家固然意识到人禽之辨的本质在于道德主体性的“在”或“否”,但是儒家道德主体性本身却存在不可规避的价值偏狭:首先,道德理想主义的图腾超出道德实践的张力。表现为儒家圣贤与君子人格的高标道德要求与现实中道德事实性建构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容易导致两种极端人格,一种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圣贤人格”,另一种是知善行恶、道貌岸然的“伪善人格”,其次,道德主体性的道德清高抑制了的逻辑性和理性。儒家道德主体性坚持重“本体”轻“功夫”、重“形上之道”轻“形下之器”、重“德性之知”轻“见闻之知”等文化传统,造就了一批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清谈之士,其价值论上的偏重与认识论上的遮蔽很难开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体系。最后,儒家道德主体性强调“背负使命”,却避而不谈“权利赋予”。这容易驯化“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奴隶道德”和“易使之”的“顺民”,很难造就权利与义务共在的“公民”。显然,儒家道德主体性的哲学根基在道义和心性,而非自由与理性,“儒家的主体性思想主要不是从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上看待主客体关系,而是着重从价值关系上理解主客体关系”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性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质言之,西方单向度的工具理性依赖和儒家单向度的伦理道德依赖,都无法观照到人的完满德性与德行。
二、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融合:儒家伦理思想的格局
儒家道德主体性的诞生促成了“我”的“个体至善”,同时由内向外指向与他者互融共生的“我们”的“社会至善”:通过“仁”建立起“道德联结”;通过“义”和“礼”建立起“伦理联结”;通过“忠”和“恕”建立起“社会联结”。儒家伦理思想的如此境脉有效规避了西方“单子论”的主体自负、“原子式”的主体间冲突、“自我中心”的共同体价值裂解,充分彰显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精神气派和中国方案。
(一)儒家道德主体性向他者性统合的伦理前提
儒家伦理既主张道德主体“即俗而圣”“有限中求无限”的超越与张扬,又意识到道德主体的自身限度及其社会性(群)的存在特性,强调主体与他者统合互融不仅在成就他者,而且也通过他者的镜像成就自我。儒家主体性与他者性统合的伦理立场基于以下认识论与价值论前提:首先,主体间互融共在体现出人类力量凝聚的伦理必要。在儒家看来,主体性如果不能超越自我而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主体间融合关系,不仅社会秩序难以和谐,而且个体生存难以为继。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人以群在”是对道德主体有限性的突围解困,也是人类力量整合从而彰显人是万物尺度的存在高贵。其次,儒家“有情世界觀”的共情基础。《论语》开篇提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主体间共通性“乐感”伦理,进而扩延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有情世界观”,再而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贵和”性道德情感联结。孟子推导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伦理移情。“有情世界观”的儒家伦理为其主体性与他者性的和合融通提供了可持续性共情基础。最后,承认“他者”对于“我”的进德价值。钱穆先生讲:“中国人讲道德,乃在人与人之间,此即中国所谓之‘人伦。所以道德不是自守完成的,而且必是‘及人的。”钱穆:《中国思想史六讲》,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99页。儒家认为道德主体的诞生绝离不开与之共在的他者,向他者开放统合的“见贤思齐、择善而从”过程也是自我德性反观自照、深度觉悟与持续建构的过程。总之,儒家伦理从一开始就自觉坚持对道德主体性的超越,追求与他者一体融合的开放性伦理格局。
(二)主体间互融的伦理意志与胸怀
儒家伦理认为,主体与主体之间肩负伦理责任和义务:首先,在积极伦理意义上,主体之间具有“修己安人”的伦理意志。“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这表明儒家创始人突出道德主体对共同体中他者的伦理责任,道德主体成就绝不是儒家进德的终极目的,儒家将成就他者、成就共同体作为成德的核心参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推己及人”表达了儒家对他者承认、尊重与担当的伦理义务;其次,在消极伦理意义上,主体间秉持“忠恕之道”的伦理胸怀。“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表明,儒家消极伦理意义上的底线规定就是不将自我主观不欲之事强加之于他者的“忠恕之道”。“儒家忠恕之道以价值追求上的自他同一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作为基本出发点,实现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唐士其:《主体性、主体间性及道德实践中的言与行》,《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6期。总之,儒家主体间伦理互融既保持积极伦理的使命引导、又保持消极伦理的底线规约,从两个维度诠释了儒家主体与他者互系统合的伦理精神。
(三)主体与社群融合的伦理使命与抱负
儒家的伦理格局超越道德主体性而指向对家国天下的“他者性”使命担承:首先,“为生民立命”彰显儒家伦理的济世情怀。孔子提出君子进德之路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伦理扩延,并强调其艰巨性:“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尚书》也将个体修养德性的脉络自觉推延融合至家国天下的他者担承:“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北宋张载高度概括了儒家伦理的家国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由此可窥儒家伦理宏大的家国意识,“儒家学说中所体现的伦理主体性精神,其目标完全是为了要形成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群体”朱汉民:《儒家主体性伦理和安身立命》,《求索》,1993年第2期。。其次,“民胞物与”昭示儒家“万物一体”的天地境界。儒家承继西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天人伦理,要求人对天敬畏,对自然敬重,将天道的自然律令与人道的道德律令一体统合。“儒家天人合一论的最大特征是想把自然界的秩序还原为客观的人的道德原理,也就是使说明自然界秩序的存在论与人的价值论一致。”孙兴彻:《中国哲学天人关系论的考察与理解》,《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这充分彰显了道德主体“成己成物”与“万物一体”的天地境界。显然,儒家伦理格局将道德主体性推向家国使命与天地之境,体现出儒家主体性与他者性融合思维的开放性伦理立场。
(四)儒家主体性与他者性融合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
儒家主体性与他者性统合的伦理立场,有效规避了西方无节制的“自我实现”“原子式”主体间冲突、“自我中心”的社群裂解以及主体性僭越的“理性自负”等,但其毕竟与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生存方式和政治伦理紧密勾连,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道德主体的独立人格缺乏保障机制。不难看出,儒家往往將社会性和群体性绝对化,“或多或少以群体的认同,抑制了个性的发展”,“个性的涵养基本上归属于对他人的责任之中”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1页。。主体性独立人格得不到有效捍卫和保障,恐怕这是儒家主体性与他者性统合伦理遭遇到的本体性诘难。其次,容易陷入关系本位、情感优先、伦理原则普遍化受阻。儒家伦理将人伦关系投放到一个关乎主体生命空间与生命质量的高度,容易因关系而放弃原则、因情感而搁置理性,如此关系本位的伦理态度与处世方式很难将儒家伦理原则普遍化,出现“父子相隐”的伦理诘辩。但是共同体正义必须有普遍性原则作为维系之根,“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指的就是在由这种规范所形成的‘伦理总体性之下,主体间所共享的一种‘合理的共同生活结构”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伦理原则普遍化受阻很难担保事实性伦理公正与道德正义。最后,儒家统合性规制中存在明显的等级烙印。儒家人道伦理与政治伦理一体贯通,修身的功夫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前提,不可避免地杂糅进政治伦理元素。总之,儒家主体性与他者性一体统合的伦理立场既具有超越西方主体性哲学悖论的伦理优势,又存在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对此,应当保持必要的伦理清醒。儒家主体性与他者性一体贯通、和合兼容,在成就“我”之道德主体性的同时,眷顾到“我们”之伦理互系性,充分彰显出儒家伦理方案的中国特色与气派,为“植根于中国大地办教育”提供了可以阐发和镜鉴的德育价值资源。
三、融合转向:儒家伦理思想的当代德育价值启示
儒家伦理思想的教化链条是:道德主体性生成——他者性伦理迁移——主体对他者和社群的伦理使命担承,链条的收摄处在于一体融合至个体道德生命的建设之中。儒家伦理思想为我国当代德育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启示:当代德育应当转向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融合的教化范式,致力于“善”的“我”、“和谐”的“我们”一体造就。
(一)儒家伦理思想对当代德育的教育立场启示
儒家伦理思想的文化脉络与精神密码给予我们的重要价值启示是新时代德育要坚持道德主体性与他者性一体融合的教育伦理立场。道德主体性诞生的“个体化”与他者性觉悟的“社会化”是个体道德生命发展的基础性结构底色,其“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个体化的过程,反之,个体化过程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个体化与社会化两者是一致的”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2-303页。。坚持道德主体性与他者性一体融合的教育伦理立场,当代德育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道德人格、开放伦理格局、开阔道德视野、积极伦理责任的现代公民。
(二)儒家伦理思想对当代德育的理论理性启示
首先,当代德育应致力于道德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冯友兰先生说:“有觉解是人生的最特出显著底性质,亦且是人生的最重要底性质。”冯友兰:《觉解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儒家伦理思想从“知者不惑”的道德认知觉解到“仁者不忧”的道德人格范导,再到“勇者不惧”的道德行为实践,其实是圆融共进、一体共生的,通过觉解、范导、行为而实现道德主体性的造就与发展:第一,觉解和启蒙个体的道德理性。儒家伦理将“知者不惑”作为道德觉解的理性认知前提,只有对与特定社会生存结构相对应的道德价值、伦理规范、文明礼仪等在认识论上获得理解和通透,才能在主观意识、人格确立、价值捍卫、理想追寻等层面供给可持续性动力。因此,道德教育要启蒙和觉解儿童的道德认知,生成其道德理性,帮助其在是非、善恶判断上,能够做出理性分析和高阶选择。第二,范导和发展个体的道德人格。儒家认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人道德主体性生发的先在性基础结构,“四端”融合并接受范导,才能成就人饱满的道德人格。儒家道德主体性为原点的伦理思想启示新时代道德教育,应当在道德理性觉解、道德人格范导、道德行为促发中造就儿童的道德主体性,以个体至善的先决前提为社会至善的共同体理想提供可能性。
其次,当代德育要培育儿童他者性伦理格局与使命自觉。儒家伦理思想的独特气派在于其不断推延与融合的伦理格局,以及主体对他者背负“仁者爱人”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伦理使命。如此主体融合他者的伦理立场对当下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启发:
第一,引导和培育学生与他者伦理共在的道德意识。“儒家角色伦理将始于一个宣称:在任何有趣的道德或政治意义上,人都不能脱离与其交流的其他人而被理解。”张曙光:《主体性价值论的建构及其超越》,《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4期。儒家认为“我们”的“群在”是“我”的“安在”的前提,“‘我与‘他人的‘朋友或‘伙伴关系昭示我们人类的主体并非只是在与客体的相对关系中单方面地强化自己”安乐哲:《心场视域的主体:论儒家角色伦理的博大性》,《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我们”的和谐是自我道德品质提升的背景性资源。所以,新时代道德教育要培育学生的他者意识,承认他者、接纳他者、成就他者,通过与他者共在,养成开放性道德格局和关怀性道德品质。
第二,唤醒和强化学生成就共同体的伦理使命。儒家十分重视道德主体的伦理使命,强调道德主体对共同体(家国)、对人民(生民)、对自然(天地)所应承担的道德义务、伦理使命,私德与公德交汇在共同体的成就、捍卫、建设上才是主体德性的高阶状态。新时代道德教育要不断唤醒和强化学生的担当意识、集体精神和共同体情怀,要在儿童道德成长的每个阶段采取理念守一、任务分解、持续跟进的德育方案与方式,在其道德人格中植入责任意识、使命觉悟、家国情怀、天下精神等,在成就共同体的同时涵养高阶的主体美德。
第三,养成和锻炼学生勇于担当的伦理使命转化能力。儒家伦理一向保有“重行慎言”的实践传统,在道德主体性与他者性融合的德性养成过程中,必须在对他者、对共同体的使命转化中提升道德境界和倫理格局。因此,新时代道德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性、道德情感、道德意识、道德精神等,还要将伦理使命转化能力作为重要的价值指向,锻炼学生在对自身主体建设、对他者承担责任、对共同体履行义务过程中,表现出坚韧的道德意志、伦理关怀、捍卫正义、勇于担当的伦理使命转化能力。同时,新时代道德教育要规避儒家伦理立场的价值局限,确保道德人格摆脱对人、物的依附而获得相对独立和个性张扬。正如贝尔所言:“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在道德状况方面的差异,保证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获得道德独立地位。”DanielBell,TheComingofthePost-IndustrialSociety.AVentureinSocialForecasting,BasicBooks,1999,p74.
新时代德育要从儒家主体性与他者性一体融合中践行使命的德育智慧和价值养分,走融合性德育之路。
(三)儒家伦理思想对当代德育的实践理性启示
儒家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一体融合的伦理立场与教化脉络,注重在伦理实践中体验、感悟、生成和检阅道德,知行合一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根本遵循。因此,新时代道德教育秉持道德主体性与他者性一体融合的伦理立场,其德育实践策略应当具有高度的伦理实践意识和策略设计。
首先,伦理实践是道德主体性与他者性融合生成的生态场域。关注对人的道德认知与道德理性培育的道德教育,其要旨在于道德主体价值世界的敞亮与澄明。但是,道德主体性与他者性融合生成的美德必须在伦理实践中得到真正的体验、内化、磨砺和内生,与儒家“敏于事慎于言”的道德主张一致。只有在与普遍性伦理、与他者、与共同体等互系性伦理实践中,才能让道德主体超越认知、想象、玄虚,“在做中”升华主体性、觉悟他者性、融合生成主体性与他者性一体的可靠德性。
其次,在情境性伦理实践中陶冶道德判断、道德分析与道德决断能力。课堂教学无疑依然是学校德育的主要途径。但是,教学性德育必须通过情景性伦理实践创设,让学生在身临其境的伦理场景中、在虚拟设置的伦理冲突中、在精心预设的角色扮演中、在经典还原的案例分析中等其他情景性伦理实践中,训练其道德判断力、道德分析力和道德决断力,为个体的道德主体性与他者性的融合生成提供准真实性实践体验。
再次,在生活性伦理实践中磨砺人的道德意志、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能力。生活性伦理实践主要是指受教育者在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研学旅行等真实情景中所偶遇的每一次伦理交往、伦理故事、伦理抉择、伦理行动、伦理冲突等。学校道德教育要拓宽德育空间和德育形式,在开放性生活世界中开发具有德育意义的伦理实践场域和载体,让学生在自身道德体验、与他者交往、对共同体建设捍卫等事实性伦理活动中磨砺其主体性与他者性融合共生的道德意志、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能力。
最后,在动态的伦理实践中持续培育和发展人的德性。人的德性建构具有未完成性、反复性、长期性等特质,因此,新时代道德教育要超越静态德育思维,在动态的伦理实践中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道德体验平台、与他者相遇并伦理相待的机会、参与共同体建设并共享其成效的契机等,走出自我中心、认知导向、文本依赖、实践割裂的德育窠臼,培育并发展学生道德主体性与他者性一体融合的道德品性与品行。
“中国式现代化”“自主培养人才”与“植根于中国大地办教育”语境中的当代道德教育,不仅肩负着立德树人的育人使命,而且要以古今通理、古今通用的文化自信为学生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儒家道德主体性与伦理他者性一体融合的思想理路,可以为当代德育供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价值启示,深度开发与“双创性”转化是必要且紧迫的教育行动。
TheFusionofMoralSubjectivityandEthicalOtherness:theTransformationofMoralEducationValueofConfucianEthics
CuiZhencheng,LiZhiqian
(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
TheConfucianethicalthoughtupholdsthevaluepositionoftheintegrationofmoralsubjectivityandethicalotherness.Moralsubjectivityismanifestedasinnertranscendenceandvigorousandpromising.Theothernessofethicsisembodiedinthemutualrelationshipandco-existenceofethicsamongsubjects,andthemissionandresponsibilityofsubjectstothecommunity;Theintegrationofmoralsubjectivityandethicalothernessistheethicalfusionandunityofinnersageandouterkingintheconstructionofindividualmorallife.Thisethicaldesigneffectivelyavoidsthe“single”transgressionofthesubject,theethicalconflictbetweenthesubjectsandthevaluesplittingbetweenthesubjectandthecommunity.OnthepremiseofclarifyingthehistoricallimitationsofConfucianethicsandmaintainingnecessaryculturalvigilance,theethicalthoughtoftheintegrationofConfucianmoralsubjectivityandethicalothernessprovidesadoublevaluereferenceforcontemporarymoraleducationtheoryandpractice.Theoretically,contemporarymoraleducationshouldfirstfocusonthegenerationanddevelopmentofthemoralsubjectivityoftheeducated,andthencultivatetheethicalpatternandmissionconsciousnessofotherpeople.Finally,theintegrationofmoralsubjectivityandethicalothernesswillberealized;Inpracticalreason,contemporarymoraleducationshouldpayattentiontothemethodsofmoralexperienceandethicalpractice.
Keywords:moralsubjectivityandethicalotherness;Confucianethics;transformationofmoraleducationvalue[责任编校刘科,彭筱祎]
作者简介:崔振成(1977-),男,河南延津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育研究;李志前(1979-),男,河南台前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管理与德育研究。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JY013);河南省教育科學研究重大招标课题(2021JKZB05);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9SJGLX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