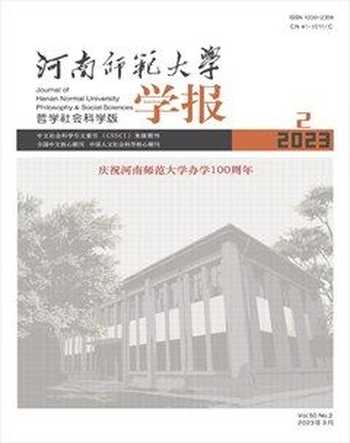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网络治理模式的演进逻辑
廖和平 邢硕
摘 要:网络治理模式由网络管控发展到网络共治,体现了由主客二分转向主体间性的逻辑演进过程。网络管控模式的理論根据在于对主客体进行二元预设,并将二者对立错置,技术与权力被异化为主体,个体受到技术异化和权力异化的宰制而沦为客体,并受到来自技术与权力的双重管控。要实现对网络管控模式从主体到模式的全面变革,需要从底层逻辑上重置主客体、重申社会性和重建认同来共同完成对技术异化、权力异化及人和社会异化的纠偏。网络共治模式得以构建依赖开放的权力系统,并将从根本上否定并扭转基于主客体分化导致的异化现象,进而摒除技术理性的统治缺陷,催生出基于主体间性而形成的权力共治主体。多元权力主体通过交往行动、平等参与和对话协商,最终达成基于合作的尊重理解与交往共识,以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实现对技术理性的扬弃,落实以主体间性为根基的合作共治。
关键词:主客二分;主体间性;网络管控;网络共治
作者简介:廖和平(1963—),女,湖南宁乡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政学理论与实践等相关研究;邢硕(1991—),男,河南长垣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126);湖南省党建理论研究基地一般项目(19DJYJY09)
中图分类号:D03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2-0023-07
收稿日期:2022-05-06
网络产生了日益凸显的网络社会问题。各国对待网络的态度也经由无政府主义式的网络自治转向网络控制。而为了满足网络参与者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要,则要对这种网络管控模式作出合理的调整,落实网络管控走向网络共治的治理理念。网络治理模式经由网络管控走向网络共治,其演进逻辑在于扭转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技术理性的全面统摄,并对建基于主客二元对立的技术、权力和人的异化进行全面纠偏,完成主客体关系与管理模式的双重变革,最终实现以主体间性为根基的合作共治。
一、技术嵌入:网络管控模式的理论预设
管理模式涉及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就管控而言,一般将政府作为管控主体,将政府外的组织、群体和个体作为管控对象。有学者认为,网络管控是以政府为主体、由行政机构制定并实施的干预互联网提供商的一般或特殊行为[ 邹卫中:《自由与控制:网络民主困境及其新路》,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0页。]。实际上,网络管控的情况更为复杂,作为一种伴随新的科技革命而出现并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中的信息技术,它兼具技术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也兼具主体与客体双重身份。网络管控是在主客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技术理性[ 技术理性也可称工具理性,是把世界及其构成要素看做达到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不产生价值和意义,其实质是实用主义。]指导下,将技术及占有技术的权力者作为主体,将其他网络参与者作为客体,主体对客体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及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和掌控。因此,对网络管控的分析,要以其技术性为起点展开。
(一)主客体错置:技术的异化
技术性是网络的根本属性和网络社会生成的底层逻辑。网络具有数字化特征,各种内容在网络上以编码形式出现,甚至网络的参与主体也需要网络对身份进行数字化演绎;网络具有信息化特征,网络传播的内容是信息,网络本身也是网络和现实社会之间信息勾连和传播的信息中介;网络具有连接性特征,能够通过分享信息将网络参与主体连接起来,从而使时空脱域活动成为可能。基于以上三种特征,网络表现出其工具性的特点,人们利用网络获取海量信息,依托网络实现跨时空的不在场交往,借助网络满足各类生活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可以说,只要技术允许,“线下”活动可以完美投射到“线上”。
可见,网络的普及对人类生活世界产生的影响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这个过程正如计算机伦理学先驱詹姆士·摩尔所说:“计算机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技术引入阶段。在这一阶段,开发和改进计算机技术……第二个阶段——工业化国家刚刚进入的阶段——是‘技术渗透阶段。在这一阶段,技术渗透到了人们日常活动和社会建制,改变了基本概念的意义,如金钱、教育、工作和公平选举。”[ 詹姆士·摩尔:《计算机伦理学中的理性、相对性与责任》,正萍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网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但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它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时,其在社会生活、信息传播、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的统治力量反而形成了对人的宰制。
法兰克福学派以反思的自觉对科学技术展开理论批判,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两重性——既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以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提高,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变体,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压抑人、操纵人,从而导致人由主体沦落为被奴役的客体,其批判的根源在于工具理性。理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具有哲学根基地位,理性的发展与主体性的生成和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同一的,它既表征目的本身,又是对目的的展现。然而,随着技术对生活世界愈加渗透,社会生活和社会行动逐渐被技术主导。
人们看似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和更丰富的生活内容,但实际上技术理性已悄然将人退化为技术的附庸,实现了技术和规则对人的统治。技术理性主张效率至上,基于实用主义立场追求功利,行动受功利驱使,借助技术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达到预期目的,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对人的全方位控制。网络社会是网络的技术性与社会性的结合,是建基于技术之上的社会空间。照此逻辑,网络社会是否首先要符合技术的统治需求?是否要遵循技术理性的管理逻辑来对待网络社会?马尔库塞曾提出“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43页。],人们出于利益追求,自愿加入技术系统当中,技术由解放的工具异化为奴役人和束缚人的工具,人自身成为无差别的同化物。人不再通过自身的意志来掌握和利用技术,相反,成为技术体系的组成要素,沦为技术的奴隶和物质资料生产、消费的奴隶,最终处在生活世界中的人沦为客体,置于技术控制之下,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主体地位。
(二)占有技术的权力:权力的异化
技术作为管控主体,是一种异化了的技术,對技术的占有生成的管控权力是一种异化了的权力。权力的异化在管控模式演变过程中体现为其自身的异化和技术引入后导致的管控效能的异化。传统的管控模式依据阶级身份的差别和对资本、军队力量的占有,以暴力的形式和强制的手段实现对人们的控制和统治,人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服从的是基于何种权力基础的“暴政”。然而现代技术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依托资本,技术完全可以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以此达成统治阶级权力的集中,形成一种以技术为底层逻辑、以资本为保障、以权威为主导的集权形式。异化的技术在成为网络管控发挥权力效力手段的同时,也嵌入了基于技术自身发展所带来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影响。
对待异化的技术和异化的权力显然不应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这似乎与“科技造福于人”的观点相冲突。实际上,说科技造福于人类,是指科技满足人类需要的层面,这恰恰也是占有技术的权力与技术相结合,从而导致权力被异化,进而缓慢入侵人的生活领域和意识领域。马尔库塞区分了人类的“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认为人们最基础的需要是满足衣食住行的生存需要,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需要的标准逐渐提高,“需要”的内涵也逐渐丰富。需求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的满足则依赖于社会制度的实现。
因此,管控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就在于统治阶级有意识地错置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利用了“虚假需要”。在统治阶级看来,占有生产力和生产资料而获得物质产品的需要是一种真实需要,而诸如思想、文化等对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创造性作用的需要则是一种虚假需要,这是对人这一需要的错置。当人们认为获得了“需要”的满足而沉醉其中时,实际上只是对给定的“虚假需要”的顺从。“真实需要”是人在自由状态下提出的需要,是体现了人的本性的自主性需要。当人们把顺从当作幸福,把所受到的支配当作舒适的生活方式加以认可时,就永恒地接受了管控的内在逻辑,成为统治权力之下被异化的个体。技术与权力的联袂,也最终达成了对社会的整体管控。
(三)形式认同:人和社会的异化
人在技术和占有技术的权力的双重管控下,被异化为服从于意识形态的简单个体,社会被异化为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单一形式。异化下的人和社会与技术和权力之间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认同”(同化)关系,这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管控根基,但实际上是对人和社会发展革新的桎梏。
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0页。]。马尔库塞指出:“技术设施在维系并改善各个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他们服从于设施的控制者。于是,合理的统治集团与该社会融为一体。”[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就此而言,“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在信息化的社会,网络技术钳制了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如人们虽然可以利用网络精准、快速得到想要获得的信息,但是反过来,通过技术算法,网络可以按照用户搜索习惯形成信息茧房,这种“自由选择”实际上是技术宰制下单一化信息的获取和对其他信息的剥夺,个体由此处于形式认同下的异化状态。
诚然,人在满足了“虚假需要”的前提下,与技术和权力产生了普遍的、隐秘的对抗关系。“虚假需要”基础上的意识统一导致经济、文化与政治生活被全面钳制。“就形式认同与异化的关系而言,同化机能越是强大,被同化的主体越是感到异化,因而,同化理论揭示了同化对于异化的根源性和实质性。”[ 杨乐强:《工具理性的起源及其同化机能: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同化理论探析》,《江汉论坛》,1998年第7期。]这充分表明,技术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为统治阶级的管控提供辩护。统治阶级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一方,合理性调控、制衡和统摄个体成员,个体成员合理性认同、确信和依托于前者,从而形成一种共时态的或结构性的包容认同关系[ 杨乐强:《工具理性的起源及其同化机能: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同化理论探析》,《江汉论坛》,1998年第7期。]。然而后者对前者的认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认同,前者通过“合理化”控制达到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否定和对其能动性的剥夺,个体的人则出卖和转让个体性以实现一种片面自足的生存,这是技术理性指导下统治阶级对个体成员造成的同化。
同化造成了同质化的个人和板结化的社会。人的灵魂被同化到技术规则之中,人们接受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个人错误地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当作其观念世界,以采纳统治阶级发布的“指令”来代替主动与他人发生关联,成为单面化的个人。个人意识消解的实质是个体被控制和操纵所内化,是以一种潜化、模仿的形式来取代认同,进而达到与整个社会的“一致化”。在生活世界中,形式认同内含了对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消解对立、消除否定的意义,以此来保证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稳定,实现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支配和对社会的全面管控,最终消解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可能。
二、技术悖论:网络管控模式建构逻辑的反思与批驳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科学技术批判的过程中,逐渐理顺了技术和权力控制人的演化路径:在主客二元对立被错置的前提下,技术以其理性效率原则将人们卷入了技术规则的洪流,依托资本,统治阶级与技术联袂,使技术成为权力的附庸,实现了从物性支配到对人的行为方式、意识领域的全面占据和掌控,参与主体沦为同质化的客体,社会沦为板结化的社会,最终人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要实现对网络管控模式的革新,关键在于恢复网络参与者的主体地位,限制管控权力效用的发生,重建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明确作为治理主体的网络参与者所具有的共治权力。
(一)重置主客体:对技术异化的规制
对技术异化的规制关键在于恢复人的主体性,主体性蕴含着事实与价值的双重意蕴,从事实与价值来看,人具有最大的内在构成性价值,其本身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主体性的工具性价值体现为他是维持社会活力的最深层根源,能够直观地催生人的行为,进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又能够极大地指导和提升个人行为的效率,有助于形成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与保护。主体性的双重意蕴还意味着,处在社会关系中个人的主体性状态与该社会对主体的权力赋予和保障状况密切相关。个体作为社会的参与者、行动的承担者和接受损益的利益相关者,不能被视为非人格化的机械式客体,而是具有独立人格尊严、自由意识,具有理性与自主性,既守规则也会犯错的人格化主体。总是像客体一样受他人支配和安排,听命于绝对统治的受制状态,都是个体主体性没有受到尊重的表现[ 余向华:《主体性与社会秩序的人本建构:转型变迁透视下的经济人假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关于人主体地位的确立一向是人本主义关注的问题。自古希腊罗马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启蒙运动对人性、人的道德性的考量,人们逐渐发展出了关于“人”的一个基本共识,即将人作为尺度,肯定人的价值,高扬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求。之所以强调网络参与者的主体地位,是由于只有当个体从被数字化、符号化了的原子式客体变为处于交往对话中的主体时,对他人的理解和尊重才能构成网络社会中形成共识的条件。网络参与者只有作为主体而发生交互关系时,才能构筑网络共治的坚实基础,从而促进网络社会的长足发展。但由于主客体的错置,使得技术和基于技术的权力成为管控主体,本应具有主体性的人却成了被认识和管控的客体对象。人们囿于自身的有限性,一方面受到技术理性的桎梏,另一方面又渴望获得价值意义。因此,要改变管控现实,变革管控模式,首先就要扭转被错置的主客体地位,用以主体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逻辑取代技术理性的管理逻辑,形成网络共治模式。
但是仅仅恢复人的主体性对于变革网络管控模式来说远远不够。一方面,不加限制的主体性最终将陷于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泥淖,另一方面,基于网络的双重属性,技术性扭曲了人的主体性,社会性反而为人們发挥主体性提供了条件。
(二)重申社会性:对权力异化的纠偏
网络承载着网络参与者开展各项活动、进行信息交流的社会空间,这使得异化的权力失去了发挥效力的场所,并为其他主体赋权提供了条件。因而,网络的社会空间属性及其所承载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是限制管控权力、纠正权力异化的重要路径。
从网络的社会空间属性来看,“互联网的全球性、多节点、高速度,使得它获得了无限的生机和敏感,这是政府所难以控制和把握的。政府管理互联网的原则应当是有限管理,保证互联网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是驾驭这种新媒介最好的办法”[ 丁未:《网络空间的民主与自由》,《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开放共享的网络空间因其横向扁平化的结构,扭转了管控模式所对应的中心——边缘形态的由上至下发挥权力效力的社会结构,从而破除了权力、地位、资本、种族等现实交往中的限制,“事实上更有益于民主协商,因为它颠覆了当面讨论中的礼仪束缚”[ 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46页。],更加彰显了网络参与主体交往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摆脱了对管控权力逻辑的信奉。基于网络的社会空间属性对权力进行限制,首先要坚定去中心化的呈现形态,满足网络参与主体间的沟通需求和地位维护,规避网络管控模式的一元权力主体现象,促进多元主体模式的良性发展;其次要维护扁平化的发展结构,稳定网络结构的横向发展态势,防止出现“金字塔”型结构衍生出的权力关系。
从网络的互构关系属性来看,网络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关系视角下考察不难发现,自我与他人可以通过社会交往以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形式实现共存。尤其在交互的网络社会当中,信息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接收者,这将传统的由主体到客体的社会活动转变为由主体到主体的社会活动。二是体现在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上。人是包含了自由意志在内的具有主体性而非单向度的实体,人不是一个封闭概念,社会性因素自然而然地融入自我当中,网络社会中的人始终与社会本身处在一个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的系统之中,社会始终承载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而非仅作为一个场域而外在于个人,人们的意识、行为形塑着网络社会的结构,反过来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关系的决定。
(三)重建认同:对人和社会异化的再造
认同意指社会成员确证相互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属性或价值方面的相似性。形式上的认同是个体间基于技术理性形成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以实质认同取代形式认同:一是要确立个体的自我认同,以此明确参与主体的主体地位和治理权力;二是要确立主体间的社会认同,以形成治理共识,获得实现共治的条件;三是要甄别社会认同的机制差异,以满足共治的内在要求。
首先,自我认同包括对自我属性的确认以及他人对自我的确认,前者表现为个体基于自我意识而认识“自我”,后者表现为个体通过与自我发生关系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交往而认识“自我”,这两个环节的认同是相互交织的:个体通过自我认同将自我同一性变成现实化的主体,又在社会场景中,与其他个体出于不同层面的共同需要和共同目的,产生在认知和价值评价上的一致意见[ 李萍:《论道德认同的实质及其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自我通过对自己行为的持续性反思不断确立自我的同一性,这也符合吉登斯所认为的自我同一性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的独立,个体的自我认同就可以成为对抗现代性同质化、均质化的有力武器[ 李萍:《论道德认同的实质及其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
其次,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构成了社会认同的一个隐含因素,是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共同目的的内在条件之一。社会认同表现为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价值和行动取向。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曾定义,社会认同是包括了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多方面的含义[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这表现出归属性倾向,表现出个体面向所在群体和公共生活世界,承认了相应的社会规范,接纳了相应的身份角色,以此确认自身在其中的位置,获得对群体和社会的归属。
最后,社会认同机制主要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网络对原有的社会建构进行了去中心化的处理,信息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向传递态势,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传递主体和形式的转换,这种双向的互动模式不断冲击着中心边缘式的传统结构。网络社会的种种多样性特征打破了现有的社会认同机制,使对价值的认同和对意义的接受替代了对固定群体的认同。“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背景下的认同,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学和个体心理学界定的个人认同或身份认同。个体的身份认同实质上是寻求个人怎样得到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同思考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处于何種层面、地位或角色,希求的是个体得到社会某种层面或某种群体的认可和接受。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发生了根本变化,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因为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不再是个体被社会认同,而是被网络联系起来的个体怎样评价、认可和接受社会。”[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江淮论坛》,2011年第5期。]网络主体之间结成了新的认同模式,借由网络平台,通过对话交往的形式,以自由意见和协商民主的方式,形成主体间的共识,趋向于形成新的社会认同,这既保障了主体权力的发挥,又体现了共治的内在要求。
三、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网络共治模式的有效实现
网络管控依赖于封闭的权力系统,催生了权力主客体的绝对分化,失衡的权力关系和失范的权力运行也在相互掣肘中背离了权力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与此相反,网络共治依赖于开放的权力系统,催生了基于主体间性的权力主体。网络共治下的多元参与者使用的权力是一种不可垄断的社会权力,多个权力主体通过平等参与和对话协商的交往行为监督和制衡主体权力,达成对网络社会价值的认同和对网络社会公共事务的共识并实现合作。
(一)网络共治主体间的权力制约
网络事务和环境造成的不确定性致使网络管控模式以及它所依托的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主客二分权力失灵,网络管控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越来越受到质疑。网络属性为其他主体赋权,形成了制约统治阶级权力的新生力量,对主客体的重置和对社会性的申明又激发了参与者的主体意识,由此形成主体和主体之间的权力参与形式。其他主体的加入需要在自我中心主义中寻求平衡。由此,主体间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网络治理思路,基于主体间性实现了对统治阶级的权力监督。主体间性不是对主客体的彻底否定,而是对主客体关系进行选择性的继承,保持对主体权力所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警惕和对过度运用权力的质疑,以确保权力运行方向和路径的合理性。
主体间的权力监督既是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发展的重要产物,也是网络共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行政权力的监督来自外在于它的社会权力,通过对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作用对象等方面的监督来约束行政权力自身,这是网络治理过程中对统治阶层权力进行限制的合理手段之一。治理权力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可以促成主体间的合理监督和有效交流,从而使各项公共事务在不同权力的角逐中通过商讨得以解决。网络社会中主体间的权力制衡,表现为参与者除了是构成治理权力的主体之外,还是构成交往权力的主体。这表明网络参与者既拥有权力,又处于制约之中。交往权力来自公众之间的话语交往,是在进行商议后形成的具有一定共同意志的力量,旨在权力博弈中谋求最广泛公众的公共利益。这暗含了网络治理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掌握话语权,而是不同主体间通过网络这一公共领域进行交往行动,表达各自的权力诉求,并在产生冲突时进行不同程度的让步,进而保证网络社会秩序趋于合理发展。由此,主体间的权力制约是实现网络共治模式的必然要求,也是释放网络社会活力、推动网络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最终实现网络共治对网络管控的超越。
(二)网络共治主体间的交往行为
网络共治是依靠不同主体通过多种交往行为达成共识,平等和协商交织于互动交往当中,最终形成主体间的认同,构织出社会共同体的交往秩序。
平等体现在主体准入身份的话语平等。网络空间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平台,参与者在网络社会中不受阶层和社会身份的限制,而“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诞生,为相对自发的、灵活的、自治的公共辩论提供了多样性的场所。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随着历史性的公共领域的崩溃,已经逐渐退入各自私人领域的公民,又一次以一种公共力量出现了”[ 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网络中交往的个体“既不是作为某种职业的从业者也不是作为某种物品的消费者出现的,因而他们往往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私人,而这些私人一旦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他们的共识就不再是普通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意愿,相反,这些共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意”[ 许英:《论信息时代与公共领域的重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这表明,任何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加入商讨过程中来,理想的公共领域“应提供开放的公共论坛,尊重弱势社群的发言空间,呈现多元化的报道以彰显公共领域的精义及多元社会的理念”[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网络为实现多元主体共治的自由进入、平等交流与协商对话提供了平台支持和技术支撑。
协商是在平等的前提下,主体间为形成统一意见而开展的自由认同形式。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愈发多样,个体对信息的选择也呈现随意性倾向,这很容易出现意见的分歧甚至冲突,但在协商语境下,意见分歧和冲突都基于平等立场的表达,都以达成共识为目标,分歧和冲突并不具备绝对性意义,通过协商对话总是能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协商过程不同于显性契约的约定,也不意味着多元价值体系下的虚无主义,而是在一种相对活跃的社会环境中,扩大和保证社会成员公共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在价值观上共商的基础。
交往行动对交往主体经由协商所确定的语境当中的互动行为进行协调,通过平等沟通和协商达成共识。将交往行动运用到网络治理当中,是参与主体通过公开参与,自主发表意见,在平等公开的语境下,就公共事务或政治事务达成共识。随着网络交流平台的建立,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平等地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个人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一切事务感兴趣,尤其是对那些原本认为归国家和政府管理的事务投入了极大热情”[ 陈卫星:《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27页。]。私人话题借由网络技术的传播和参与主体的交往行为而被打上公共的烙印。可见,交往行动正是由个体走向公共、由个体意见走向共识的必由之路,也是参与主体达成合作、共同参与网络治理的必要途径。
(三)网络共治主体间合作的达成
合作是人类存在于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合作与交往也始终相伴相生,因而,合作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种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的断裂就在于技术理性及其背后所依据的主客二分对人造成的异化。要克服技术理性的统治缺陷,就要重新寻求建立理性的根基和途徑。以主体间性为基点,通过交往和共识建立起交往理性,以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实现对技术理性的扬弃构成了主体间形成合作的有效途径,网络合作共治由此成为摆脱技术理性网络治理模式的代表。
合作的达成以肯定利益相关者的个人利益为前提,通过公开的辩论和协商妥协,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共同利益的共识,实现由个体到公共的转向。对共同利益的认同依赖于对交互主体性的尊重,由此形成的共识既代表共同意志,也代表个体意志,是参与主体经由协商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也对参与主体具有内在的约束力。网络作为一种开放的、便捷的非线性传播方式,每个公众都可以作为独立个体参与到网络社会中,网络的立场代表的就是公众立场。由此,参与主体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阐述相互之间对于公共事务和个体利益的期望以及相关的行为标准,并赋予共同利益以普遍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形成合作共识。
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达成合作的重要环节。理解是对主客体预设的抛弃,是对基于他者视角理解主体行为。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行为,人们产生交往理性,形成对他人的理解。理解的过程就是主体间意见逐渐达成一致的过程,主体间基于共同的信念,合力对一种意见内容表示同意。当个体以网络治理主体的身份而存在时,尽管可能出现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角逐,但其最终旨趣都趋向于达成公共利益和稳定的网络社会秩序,这样的结果指向必将推动参与主体经由理性选择达成合作。
总之,在网络治理过程中,“主体间性”始终贯穿于合作共治过程,个体、技术与权力之间不再表现出主客二元对立的立场,而是以相互承认与尊重为前提,以协商、理解的对等关系取代一方对另一方的威胁压迫关系,参与主体也不再只是技术理性下被异化的单向度的个体,而是在交往行为中以交往理性为判断依据的具有自我意志的主体。由此,主体间达成普遍有效的合作,共同参与到网络治理过程当中,最终实现以网络共治取代网络管控的模式变革。
From the Dichotomy of Subject and Object to Intersubjectivity: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Internet Governance Model
Liao Heping,Xing Shuo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model develops through Intern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o Internet co-governance, which embodies the logical evolution process from the dichotomy of subject and object to intersubjectivi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Intern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l lies in the dual presupposi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and the opposition of the two is misplac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Intern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 from subject to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alienation of technology, power and people and society by resetting subject and object from the bottom logic, reaffirming sociality and rebuilding ident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net co-governance model constructed depends on the open power system, which will fundamentally negate and reverse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caused by subject-object differentiation, abandon the ruling defect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give birth to the power co-governance subject formed on the basis of intersubjectivity. Through communication actions, equal participation and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finally reach a consensus of respect,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realize the sublation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with the r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the cooperative co-governance based on intersubjectivity.
Key words:dichotomy of subject and object;intersubjectivity;internet management and control;internet co-governance
[责任编校 陈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