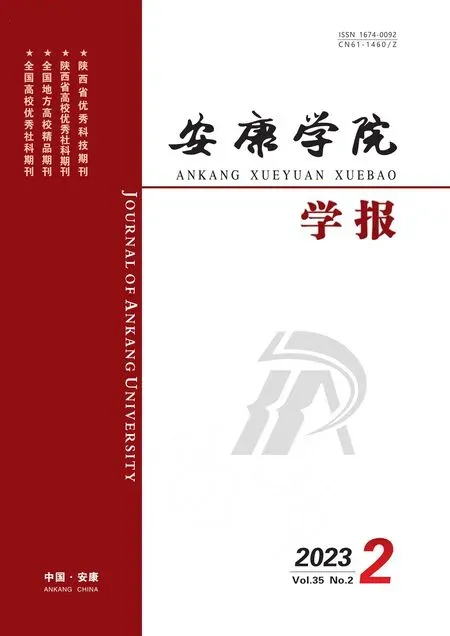陈瑚诗学论著考述
——以《顽潭诗话》《离忧集》《从游集》为考察中心
邵 乐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陈瑚(1613—1675),字言夏,号确庵,又号无闷道人、七十二潭渔父,江苏太仓人。自幼奇敏,年九岁“四书五经俱通”且“端重有成人度”[1]。负经世之才,凡河道、漕运、农田、水利、兵法、阵图等诸书,无不研贯。又善横槊、舞剑、技击等。陈瑚是明末清初学者、诗人,与同里陆世仪、江士韶、盛敬齐名,时人称“太仓四先生”,以他们为核心形成“桴亭学派”,在三吴之地及东南儒林中产生过一定影响,有“当今河汾”之誉。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入清绝意仕进,于太仓、常熟、昆山、嘉定等地乡村隐居讲学,授徒养亲。卒年六十有三,门人私谥“安道先生”,故居立为安道书院。其著述宏富,兼工诗文,著有《确庵文稿》,辑有《顽潭诗话》《离忧集》《从游集》。本文结合诗人生平,以《确庵文稿》为参考依据,拟从三部诗选来探究其诗学理念,以期对陈瑚其人其诗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陈瑚的三部诗选概况
(一)《顽潭诗话》概况
《顽潭诗话》是一部专门辑录明遗民社团——“莲社”的诗歌总集,具体来说,是清初太仓地区以遗民陈瑚为首的“莲社”唱和创作集。然《顽潭诗话》所收录作品及其作者较为庞杂,并不单纯等同于“莲社”的社诗总集。《顽潭诗话》名为“诗话”,实为诗歌总集,为何以“诗话”名之,此书的刻印者民国赵诒琛云“此书虽以‘诗话’名,实系清初高人逸士唱和诸作,隐寓故国之思”[2]569。陈瑚《顽潭诗话·自序》亦云:
所居有莲潭七十二,环茅舍皆莲花,吾与友弄舟嬉游处也。……此处林阴篱落之下,飞觥斗采之余,篝灯风雨,清谈永夕,不及时事之治乱、他人之是非,往往托之诗歌以见意。又不必尽出于其所自作,而凡所目见耳闻,皆可咏吟以消岁月。间于吾友散后,笔而志之,编年别部,汇成一帙。始自甲申,以迄今兹。其间有一人为一类者,《指南》《心史》之续也;有一事一类者,《月泉吟社》之续也;有一时为一类者,《谷音》之续也。[2]503
由上述不难看出莲社雅集内容的遗民特色,仔细研读《顽潭诗话》,可知此诗社也将遗民社团的文学创作主题基本囊括其中。《顽潭诗话》(见表1)分为上下两卷,以收录诗社成员的唱和诗歌为主。具体内容有卷上17组,卷下12组,陈瑚辑;另《补遗》4组,《附录》3组,其孙陈陆溥辑。每组作品实际上都相当于一个小集。

表1 《顽谭诗话》收录情况
该诗选特意选录了少数成员的部分诗文,如陆羲宾的《晚香亭集》、龚捖的《后印溪草堂集》与《晚翠庵集》、李国梅的《村居诗》与《北村自寿》,所录虽只占这些诗人全部创作的十之一二,但这些成员的诗文却藉《顽潭诗话》得以流传。
(二)《离忧集》《从游集》概况
陈瑚还编辑过《离忧集》《从游集》两种诗歌总集,二者内部同以作者立目,以人领诗。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二记载:“陈确庵自号七十二潭渔父,毛子晋令其二子受业。顺治戊戌诠次同志之诗,为之传记,曰《离忧集》。明年己亥复评次其门弟子之歌诗,为《从游集》。”[3]兹以选本《离忧集》《从游集》二者的序、跋来考察其异同。
1.编选目的
《离忧集·序》云:“戊子、己丑间,举讲学会,每月朔必考德课业,同志之士,靡然向风,相于往来,吟咏于七十二潭之上。于是有《离忧集》,吾祖诠次诸同人之诗歌而为之传记者也。”[4]55可知《离忧集》收录的诗歌为确庵同辈友朋之诗作。其名取义于“屈原放逐,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太史公以为离骚者,犹离忧也”[4]55,显示出浓厚的遗民意识。
《从游集·序》云:“《从游集》者,确庵子评次其门弟子之歌诗,用以宣导志意,考论德业者也。”[5]635可知,《从游集》收录的是确庵及门弟子之诗作。
2.入选作家及作品情况
《离忧集》中,“收遗民二十人,人各有传,选诗之数目不等。观其人,类皆当时重道敦伦、而又与确庵相知甚深之士”[6]51。“集中诸子之以诗名世者,惟黄翼圣、王挺、林佳玑、顾有孝等人而已。”[6]52表2 为《离忧集》选诗作者籍贯及其作品入选情况:

表2 《离忧集》入选作家及作品情况
由表2 可知,费参、黄翼圣、林佳玑、陆元泓、陆羲宾的诗作入选数量居前五,且以江苏太仓、常熟、兴化籍诗人居多。
《从游集》中,“所收三十一人,籍隶太仓者几半,得十五人,次为常熟,得九人。余则无锡二人;吴江、吴县、昆山、嘉定、如皋等各一人。盖皆当日人文荟萃之地也。”[6]70表3为《从游集》选诗作者籍贯及其作品入选情况:封之家。如顾湄之父梦麟、李王烨之祖流芳、侯荣之父泓,皆名重一时之士。亦有其父兄与确庵有密切关系者,如毛衮、表、天回之父毛晋;王抃、摅之父王时敏;瞿师周、有仲之父瞿共美。至江龙震、石洢之父,为确庵之同学友,而费来之父费参与确庵为中表兄弟,则谊更亲矣。书末所收陈逊、陈遫、陈陆舆,为确庵子,则更无论矣。嗟乎!沧海横流之际,遗民子弟,拒不出仕新朝,此不独赖有师如确庵者有以育成之,亦有藉其父执辈促以致之者明矣。”[6]71可知陈瑚《从游集》所选诗人基本皆为遗民子弟,且这些遗民子弟的父兄辈多数与陈瑚交好。

表3 《从游集》入选作家及作品情况
二、陈瑚的诗学理念
(一)倡导儒家诗教
明清易代之际,一些怀有救世愿望的诗人与有识之士,渴望通过宣扬儒家诗教来复兴传统文化。张伯行在《陈确庵先生文集序》中云:“娄江确庵陈子抱经纶济世之才而所如不偶,隐居考道,闭户著书,与同里陆桴亭诸子朝夕切磨,求濂洛关闽不传之秘。”[7]陈瑚《顽潭诗话·序》亦云:
昔者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春秋》作。然则《诗》不亡,《春秋》可无作乎。……汉晋以来,称诗之能道性情者,莫如元亮;能述政事者,莫如子美。是二公者,虽名为诗,而微文渺指之中,时陈悲痛之辞,刺讥之实,盖犹有《春秋》之遗意焉。然以视《三百篇》则风雅之变矣,此时为之也。自此以后,其体弥弱。宋承五季,大乱之余,明君贤相皆尊尚儒术,以礼仪渐渍其民。而周程张朱,真儒辈出,阴阳诱道,以助教化。[2]502
可知作为明遗民的陈瑚,在学术上传承的是程朱义理之学。其实,遗民的起源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伯夷、叔齐,而作为一个完整的、影响更大的社会阶层和文人集团出现,则是在宋金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纵观整个遗民群体,以宋遗民和明遗民影响尤为明显,而明遗民则最为显著。明遗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失掉故国,且清朝又实行剃发之令,这和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相违甚远,打击之大,难以言表。当民族歧视之辱、江山沦亡之痛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发而为诗,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就成为遗民诗歌的主旋律,陈瑚所辑《顽潭诗话》中大部分诗篇都体现了这一主旨。诗人怀念故国、感叹兴亡之情无所不在,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们的黍离之悲,且看华天御《穿山怀古》一诗:
一望蓬蒿接稻粱,昔年朋友共文章。夕阳陂上千秋泪,留与千秋吊夕阳。[2]545
西下的夕阳象征着渐渐远去的故国,昔年与朋友“激扬文字”,如今物是人非,诗人不禁潸然泪下。儒家最重要的人生信仰之一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兼济天下”的前提条件是此天下必须是汉民族所统治的天下。当清朝定鼎中原成为事实之后,儒者大多都会选择“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因为唯有这样,方可保留儒者的本原。如龚捖《遂初诗五章》,其一云:
宿抱逸民志,二廿加衿缨。翩然释儒服,始得心迹并。散发披道书,茹芝习无生。遥呼一尊酒,长谢当世名。[2]545
二十多年的漫长生活中,诗人依然坚守遗民之志。无论是他的“逃禅”,抑或是“习道”行为,都显现出他不与新朝合作的决绝心理。另外,爱国诗人屈原也往往成为遗民文人所提及且尊崇的精神偶像,如龚捖《遂初诗五章》,其三云:
卜居漆溪上,溪上多芳荪。惟此同心友,能顾蓬蒿门。慷慨挥蔬酌,静寂灯火言。愁来不可道,痛哭歌招魂。[2]509
诗人在国变之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归隐乡野,以蓬蒿为门,生活清贫,然居处却多香草香花,亦时有友人拜访,虽可聊解一时之忧,但是有愁却不可道,为何而愁,末句“歌招魂”点题,时代需要有像屈原这样的爱国之士。“端午竞渡”这一节庆活动本为缅怀爱国诗人屈原而设,通常情形下,一般民众都可在缅怀屈原的节日活动中获得教育和启迪。顺治初期数年的端午,对于江南遗民,特别是太仓地区的遗民来说,本应勾起他们的亡国之痛。然《顽潭诗话》卷上《端午竞渡》所描述的场面并非如此,陈瑚作序道:
甲申五月四日,得先帝后惨报,确信四海同仇,若丧考妣。诘朝乡绅有楼船广筵,纵观竞渡者,诸生郎玄翊愤而刺之。越明年五月,江上告急,羽檄星驰,而旧游如故,曾不为意,去北兵渡江之期,止四五日耳,人心若此,澌灭尽矣。伊士作诗记之,盖犹有悲痛之思焉。国俗既改,其风弥厉。戊子端午,自监司至舆台,皆出游河干,都人士女杂沓如云,几同溱洧桑濮矣。[2]51
甲申端午,距崇祯帝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仅一月有余,然江南太仓一带的乡绅并未因皇帝晏驾而难过,依旧沉浸在端午竞渡的欢快气氛当中;顺治二年(1645)乙酉端午,乡人又不顾长江形势危急,竞渡游乐之风依然如故,但在四五天后,清兵又旋即渡过长江;顺治五年(1648),去明亡仅约四年时间,端午竞渡之风又再次兴盛,时人仿佛早已忘却了亡国之痛。有感于此,郎玄翊作诗云:“痛心三月中旬事,龙驭宾天遏密初。若个漫抛亡国恨,画船闲看赛灵胥”[2]51。该诗讽刺了时人不知亡国之痛的麻木心态。
(二)强调“性情学问”
“诗言性情”说作为诗论主张,在齐梁时代已出现。梁朝刘勰在论诗、论文时曾多次提到“情性”“性情”等词。如《文心雕龙·明诗》中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又《文心雕龙·征圣》云:“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刘勰在论诗、论文中侧重于表现“情”这一方面,并强调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表达人的内在情感活动的,因而所表达的是人类真实的情感。钟嵘又在《诗品序》中从诗歌的视角明确提出了“性情”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此处的“性情”与刘勰所说的“性情”基本一致,仍是“情感”的意思。明末清初,复古倾向严重,故清初主流诗学家大都号召回归儒家诗学之传统,与清初主流诗派一脉相承,且陈瑚的诗歌创作也主张以性情为主,其观点散见于对诗友作品的品评中。如在《陈均宁诗序》中,针对虞山诗坛绮丽浮靡、错彩镂金之弊,陈瑚予以痛斥:
阊阖之间,虎丘之畔,春花秋月,香车画舫,酒肉如坻,箫鼓如沸。入其中,目眩而心移,色飞而神动也。越明日而再至焉,又明日而三至五至焉,则厌饫苦恼之意生矣。乃进之以幽人韵士,警之以鱼声磬响,洗之以妙香苦茗,然后恍然悟前者之失而后者之得也。诗之为道也亦然。世之作者大约虫鱼香草、风云月露,掇拾绚烂以为工,有能者出则必厌薄一切,扫而空之以为快。[7]320
故诗歌并不在于章句之工拙,辞藻之华美,诗歌创作的意义不在于其技巧与形式所展现出来的风格,而在于是否饱含诗人自己独特的真实情感与人生经验。陈瑚在《陆桴亭先生诗序》中云:
古今之论诗者亦多矣。其最有得者,莫如司空表圣,尝自择其诗而论之曰:“饮食之味必资盐梅,而其美则在咸酸之外。”今事其诗具在,诚如其云。顾其所论者诗焉而已,而未尝关于性情学问之微,天下国家之大也。表圣盖唐末之有道君子,要其所见,止于如此,不可以例其余乎?[7]317
显然陈瑚对于司空图以“味”论诗并不认同,因其论诗时只顾及韵味格调,而未及性情学问。诗,理应以言志为本,参酌学问,表达性情,进而关乎人伦风俗、天下国家之大事。陈瑚在《逸园文稿序》中云:“夫文章之道,发乎性情,止乎理义,其用底于经国治民,其功足以垂世立教,盖豹变成文,鸟吐为绶,物理固然,无足怪者。”[7]354所以“性情”是联结诗歌与社会人生的重要纽带,只有真正表现性情的诗歌才具有关涉现实的大作用。如在《太原二子诗序》中,陈瑚对观诗知志可实现经世致用有详细论述:
固哉今人之为诗也,徇其所好必己之为是,而他人之为非,交相诟厉而莫之胜也。古之论诗者不然。观其邪正以知其志,观其哀乐以知其情,观其曲直以知其行,观其广狭以知其量,观其壮老以知其气,而诗之道尽于此矣。不然,不论其世,不知其人,而徒浅浅焉求之文字之工拙、音律之乖和,是岂真知诗者耶?是故读《双文》《锦瑟》与扬州一梦之诗,则知其人必不矜细行;读《松月》《夜窗》之章,则知其人必不屑韩朝宗之援引;读《北征》《诸将》,则知其人必情不忘君,此观其邪正以知其志也。[7]321
(三)主张“以人存诗”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载:“人必论定于身后。盖其人已为古人,则品量与学殖俱定。否则,或行或藏,或醇或驳,未能遽定也。集中采取,虽前后不同,均属已往之人。”[8]可知其诗论主张为:但凡诗人还在世,其诗概不录入。沈德潜这一诗论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稍后于沈德潜的梅溪居士钱泳,对选诗家“只录已过者”的这一选诗做法持不以为然的看法,他认为选诗应当有规范,其《履园谭诗》载:
每见选诗家,总例以盖棺论定一语,横亘胸中,只录已过者,余独谓不然。古人之诗,有一首而传,有一句而传,毋论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传者而选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诗,以诗存人者。以诗存人,此选诗也;以人存诗,非选诗也。[9]138
已故诗人的诗歌必有诸多名家盖棺定论,优劣大多已有定夺。但钱泳认为,凡“诗可传”,皆可入选,但可传之诗,却不可一概而论,于是他提出了“以诗存人”和“以人存诗”两种选诗方法。所谓“以诗存人”,是指诗可传,今选诗以存其人。兹举一例,《履园谭诗》云:“唐瑀,字仙佩,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为明诸生,工歌诗,甲申、乙酉后,遂弃去,教授于沙溪、直塘之间,以终其身。与长洲汪钝翁友善,钝翁序其诗,以为使陆务观、范致能而在,与先生角逐于文酒之会,虽善论者未易优劣之也。其推重如此。今遗集不传,余偶得数首,录于左。”[9]139-140此即所谓“以诗存人”。钱泳认为“以诗存人”这种选诗方法的要义在于其诗“可传”,由诗以存其人。实际上,“以诗存人”仍属于选诗通则,“以人存诗”则不然,其要义在于其诗不一定“可传”,而联系到作者其人,那么其诗更加难能可贵,故由其人可存其诗。兹举一例,《履园谭诗》亦云:
铅山蒋心余先生,曾孙名志伊者,号小榭,能诗。道光壬午九月,余偶至邗江,相晤于王古灵席上,有《题小红雪楼诗卷后》一律云:“续书香海记前回,曾见山阳旧雨来。小草每依庭际长,寒花独向画图开。春风自扫元卿径,尊酒谁倾杜叟醅。赢得词人题妙笔,欲招黄鹤醉江梅。”[9]147
上述这首诗,并非一定可传,但联系到作者是与袁枚、赵翼合称“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先生的曾孙,能写出这般诗篇,故钱泳有“可谓善承家学”的评语,此即所谓“以人存诗”。陈瑚辑录的《离忧集》《从游集》恰好体现了“以人存诗”这一诗学理念。现代学者谢正光、佘汝丰在《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一书中,对陈瑚后学缪朝荃《离忧集·跋》作注云:
乃知确庵本意,固不在诗,而诗以人存耳。然所选既多友朋间唱酬之作,且不乏忆往怀旧之章,于考述清人入关后十载之间,士人往还之踪迹,及其仕显之抉择,当不无所补焉。且二十一人之中,颇有其姓氏不见载于明遗民诸录之中者,如陆钺、陆羲宾、瞿共美、瞿宣美、费参、吴自惺等,其生平行谊,赖是集得传。[6]52
所谓“以人存诗”,其实是以“人”作为评判的最重要尺度,诗歌的艺术价值则属其次,其人若有一、二诗作存世,便即刻存录,如《离忧集》中只选录李长祚《烈女行》诗一首。上述“以人存诗”的诗学理念,同时又暗含了编选者陈瑚阐幽明微的良苦用心,现以明遗民诗人黄翼圣为例。黄翼圣,字子羽,号摄六,别号莲蕊居士,于明崇祯年间由诸生应聘为四川新都知县,后升安吉知州。明亡后,弃官隐居于印溪,杜门不出,潜心于佛教。《离忧集》录其诗45首,其中有《次韵王奉常西田首夏杂兴》五首、《西田诗》六首及《村居杂兴》十首,表达了黄翼圣以隐居避世来反抗清朝统治的心灵诉求,并强烈地表明了诗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谢、佘二人又对缪朝荃《从游集·跋》作注云:
集中所收作者,惟顾湄及王抃、摅兄弟因获吴梅村青睐,得厕身《太仓十子》之列,诗名为世所知。……其余诸子,皆藉藉无闻。知是书与《离忧集》,其价值固不在诗歌。盖所收三十一人之中,其名氏见载于明遗民诸录者,仅上举梅村之三子而已。其余二十八人之行事,赖确庵为之传,则是集之史学价值可见。且所选诗歌,多友朋唱和之作,或挽悼忆往之篇。[6]71
兹列陈瑚《离忧集》中“西郊隐者”陆羲宾、《从游集》中冯长武小传如下:
陆羲宾,字素朴,号鸿逸,其先朱姓,宋文公苗裔,父慕山,因从母姓,始姓陆,自徽州迁太仓,遂为州人。鸿逸负经济才,精壬奇,知战略。遭甲申、乙酉之变,隐于西郊,所交皆名儒,四方至者,春秋无闲日,筑别墅于丙舍之旁,颜曰“春星草堂”。垒土积石,莳花养鱼,日与知己往来,吟咏不辍。其辞命意高远,复饶逸致,有《晚香亭集》若干卷。[4]72
冯长武,字窦伯,常熟人。父彦渊,博物好古,而死乙酉之难,窦伯痛之甚。出箧中藏书,自诸史百家、旁及二氏,钩编诵数,手不释卷。尝自叹曰:“父死不能读父之书,手则存焉尔。吾父遗书万卷,吾不忍不读,亦犹此志也。”夫为人沈静,不苟言笑。虽在稠人广坐,凝然独远。家贫,傍水竹为居,耕田自给,烟火裁通而已。友爱二弟,多分约取,有辟孟尝之风,为昆湖毛氏外甥,凡汲古近刻,校雠是正,多出其手。其诗窥见,原本蔚然深秀。盖其大父嗣宗先生,以古学名重海内,而三子皆能诗,虞人有“三冯之目”,窦伯克传其家学,宜其有闻如此。[5]648
陈瑚在《离忧集》《从游集》各人诗篇前撰以小传,应是本着“以诗存史”的编纂目的,同时也凸显出陈瑚“以人存诗”的存史意识。陈瑚所编选的《离忧集》《从游集》,为后世学者了解其友朋、弟子的生平事迹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同时对文学史、遗民史的深入研究,也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
三、结语
明清易代之际,一些怀有救世愿望的诗人和有识之士,渴望通过倡导儒家诗教来复兴传统文化,而陈瑚所辑《顽潭诗话》中的大部分诗歌,就表现了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这一主题。编选同时代人诗歌选本的风气,明清之际就已蔚然成风,而在陈瑚所成长生活的顺治时期,遗民主题始终是一大主旋律。陈瑚诗歌选本《离忧集》之名就取义于“屈原放逐,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太史公以为离骚者,犹离忧也”[4]55,显示出浓厚的遗民情怀。《离忧集》所录为陈瑚朋辈友人之诗作,稍后于《离忧集》一载的诗歌选本《从游集》,收录的是陈瑚弟子之诗作。《离忧集》与《从游集》所作诗人小传其名氏大多未载于明遗民录,这凸显出陈瑚“以人存诗”的诗学理念,且这些小传为后人研究他们的生平事迹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所以此二诗选在史学方面也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