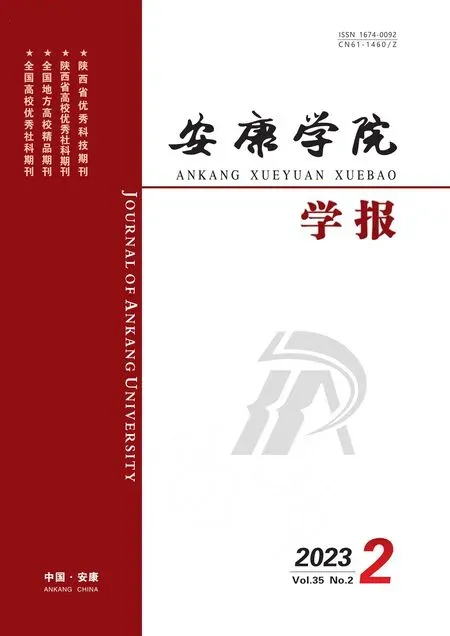唐代诗歌觱篥书写研究
赵慧芳
(1.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54;2.陕西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西域文化传入中原地区对固有音乐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在唐代文化多元的时代背景下,由社会再至诗歌的开放格局为诗人接受西域文化、书写西域觱篥提供了现实条件。作为乐器的觱篥在经过诗人诗歌化的勾勒后,其社会功能、情感导向、音乐表现力、乐人的社会地位、乐曲的延伸与承续等方面均有较之史书更为详尽书写,形成诗与史的互证。而学术界目前于觱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史籍与图像分析,对唐代觱篥诗歌的深入研究较少。本文将音乐、诗歌、历史进行交叉研究,以期在填充唐代觱篥色彩的同时,深化对唐代乐舞胡俗交融的认知。
一、唐代觱篥的历史积淀与繁盛境况
西域觱篥在唐代的盛行并非一蹴而就,乃随西域文化的数代传播积淀而成。胡震亨《唐音癸签·乐通》提及四夷乐进入中原这一历程,“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及宴飨,作之门外,美广德之所及也。自南北分裂,音乐雅俗不分,西北胡戎之音,揉乱中华正声。降至周、隋,管弦杂曲,多用西凉;鼓舞曲多用龟兹,燕享九部之乐,夷乐至居其七。唐兴,仍而不改。开元末,甚而升胡部于堂上,使之坐奏,非惟不能趁正,更扬其波。于是昧禁之音,益流传乐府,浸渍人心,不可复洗涤矣”[1]。周代四夷乐便被载入礼乐典制,接纳四夷被视为美德之所及;南北朝时期,西域胡乐开始对中原固有音乐格局产生冲击;再由周隋至唐,西域胡乐在华传播异常强势,形成了浸渍人心之态势。
觱篥在中原的流传之契机与前秦大将吕光率军攻破龟兹这一事件密切相关。公元382 年吕光于龟兹获其乐舞、乐人及乐器,《隋书》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2]409-410。此后吕光入凉州,变龟兹声为“秦汉伎”,吕光逝而龟兹乐分散,后魏太武平河西重获其乐,谓“西凉伎”,同书载西凉乐“至魏、周之际,谓之‘国伎’……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共工二十七人”[2]409。随着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积淀,西凉伎在魏、周之际已有“国伎”的地位,其中乐器与龟兹乐略有不同,但作为西域重要乐器的大、小觱篥依旧位列其中。
至北魏末年,觱篥已深入社会不同层面。《齐民要术》在描述6世纪前黄河中下游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劳作及饮食时提及:“熯呼干反菹法:净洗,缕切三寸长许,束为小把,大如筚篥。暂经沸汤,速出之,及热与盐、酢,上加胡芹子与之。”[3]将“熯”菜束成似“觱篥”粗的小把,用以料理。而将“觱篥”作为一衡量的参照物,可见随着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觱篥的形态已逐渐深植于时人的生活文化之中。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4]王国维先生亦认为:“盖魏齐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国,其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龟兹、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皆于此时入中国。”[5]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流动的社会政治形势,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带来深刻影响。
隋时,西域胡乐大聚于长安,文帝设七部乐,炀帝增设九部乐,而觱篥在西凉、天竺、安国、龟兹、疏勒等西域乐部中均有使用。《隋书》提及龟兹乐时载:“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干……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帝虽有此敕,而竟不能救焉。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2]409文帝具有强烈的华夏正声理念,而炀帝对于胡乐的接纳程度使其盛行于中原,为唐代觱篥演奏的空前盛况奠定了基础。
发展至唐代,安定、丰裕、多元的社会为人性的自然抒发提供了开阔的空间,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多元、开阔的胸襟与昂扬的风貌都是西域觱篥得以空前繁荣的缘由。唐武德九部乐中除清商与康国以外七部四夷乐皆用觱篥,贞观十部乐亦同是在燕乐、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高昌等乐部均有觱篥。元宗时,坐、立二部分列,《旧唐书》云:“今立部伎有《安乐》……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坐部伎有《毓乐》……自《长寿乐》已下皆用龟兹乐”[6]1059-1062,而作为龟兹乐重要乐器的觱篥仍旧占据重要位置。
相较筝、瑟、编钟等乐器,觱篥灵巧便携,音色的激昂嘹亮,颇为适合行走时以及马上吹奏。蔡邕《独断》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7],在唐代的卤簿乐中,《通典》记载大驾卤簿、皇太子卤簿、亲王卤簿、群官卤簿中均有觱篥。军乐中:“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8]2063敦煌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画面中仪仗乐队有前导8人,大鼓与大角各4,舞者8人,乐队10人,所持乐器即有琵琶、横笛、笙、拍板、鼓与觱篥等。
除出行仪式外,觱篥最为常用是在宴飨中。《文献通考》记:“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进酒,次并翰林使进,庭中吹觱篥,以众乐和之……第十九,角觝,宴毕。”[9]春秋圣节之宴前后共十九之制,每制乐舞略有不同,而第一“庭中吹觱篥,以众乐和之”,便可反映出觱篥在唐代的盛行。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中:“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10]4991亦说明宫廷内宴中所见《霓裳羽衣曲》有箜篌、筝、觱篥、笙等乐器。
文人士子或寄情于琴酒,自弹自乐;或娱同乐伎,赏心悦耳;或有朋相聚,相和高歌。至中晚唐时期,享乐之习愈甚,《旧唐书》中提道:“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6]485-486。而在聚会宴饮中文人士子吟诗、书法、绘画亦是必不可少,由此便产生了唐代觱篥诗歌的书写。
二、唐代觱篥诗的文化景观
作为乐器的“觱篥”走入诗歌文本,首先是基于上文所述觱篥乐器的社会功能及其独特性,引起社会的接受和悦纳,而后经文人士子在某一情境之中将其进入诗歌化的书写。由此,觱篥便不仅作为乐器被客观描述,乐器的艺术特征、乐人的演奏技艺、诗人的创作风格、读者的深层感受,觱篥在不同情景中被赋予更多的情感寄托与象征符号,或垂泪断肠,或激昂顿挫,这些语言的符号指向通过诗人与乐人的交流,被逐渐强化和传承,形成唐代觱篥诗中幽咽悲戚的情感导向与抑扬激越的音乐表现这一文化景观。
(一)诗人与乐人的交流形式及情感指向
觱篥又有“悲篥”之称,《通典》曰:“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8]3669。“悲”是对其音色的指向,这种音色所蕴涵的离散能量,在诸多诗作中迸发出心神悸动的遗韵。李颀《听安完善吹觱篥歌》中提道:“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旁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10]1354龟兹觱篥传入中原后,虽曲调变得更加新奇、精妙,但其表情达意依旧是闻者叹息,异客泪垂。温庭筠《觱篥歌》回忆与李德裕等人听薛阳陶吹觱篥时写道:“含商咀徵双幽咽,软縠疏罗共萧屑。不尽长圆叠翠愁,柳风吹破澄潭月。鸣梭淅沥金丝蕊,恨语殷勤陇头水。”[10]6752“幽咽”文本来源于北朝关陇的歌谣,“陇头流水,五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11],本是指陇头流水之声的幽咽,经过诗歌化的创作,衍生出将士思乡的情感意蕴,常被用于音乐诗中表达感伤情境,与其后的“愁”“恨”呼应,形成觱篥的“幽咽”之声。
还有一类觱篥诗作是诗人与乐人“未知的交流”,即听者与吹者互不相知,却在某一时空相交,经过听者的丰富想象,产生了觱篥的“隐听”诗。如杜甫《夜闻觱篥》:“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欻悲壮。”[10]2378白居易《病中多雨逢寒食》中“薄暮何人吹觱篥,新晴几处缚秋千”[10]5050。这一类“隐听”诗的情景是吹者或在宴席之中为人而奏,或是抒发己怀,独自吹奏,而听者在墙外偶然驻足,虽未直面却以心交。无论置身事外还是身处其中,产生的依旧是悲芳感伤的表意。
刘商《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第七拍说道:“男儿妇人带弓箭,塞马蕃羊卧霜霰。寸步东西岂自由,偷生乞死非情愿。龟兹筚篥愁中听,碎叶琵琶夜深怨。竟夕无云月上天,故乡应得重相见。”[10]1072《唐才子传》记载刘商“拟蔡琰《胡笳曲》,鲙炙当时”[12],用觱篥的悲戚之音和琵琶的哀怨之声,抒发文姬的望月思乡欲归故土之情。白居易《长恨歌》中有“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10]4826-4830,此处的“肠断声”既指唐玄宗为悼念杨贵妃所作《雨霖铃》曲,也是觱篥音色流露出的哀情,曲器相辅,更添悲戚之声。以上这种“代其言情”“拟其叙事”的形式,将觱篥置于诗中描摹,构成诗人与乐人“想象中的交流”,笔者将此类型定为“拟听”。事物经过想象的加工往往更具力量,就如“想象的共同体”更具凝聚力,而诗人“想象中的觱篥”之哀感较之“正听”与“隐听”更甚。
由此可见,诗人与乐人通过不同形式的交流,产生了不同层次的情感内涵,但其情感指向可归为“幽咽悲戚”。觱篥音色极致悲绝的艺术感染力,成为诗人心中的垂泪语和断肠刀,被赋予浓重的情感寄托,而这种感染力源自觱篥的音乐表现力。
(二)抑扬激越的音乐表现
诗歌通过文字、词汇的凝练成为语言的艺术,乐器通过其旋律技法、音色节奏成为听觉的艺术,两者通过物象的描述在一个空间内产生对话。这些物象的具体描述在觱篥诗中体现在拟声、拟形、拟象三个方面。
拟声是对觱篥音色、音声的物理性描摹,一般置于拟形、拟意之前或者穿插于其中。如“轹轹”“辚辚”“飕飕”“啾啾”等叠字,这是古代诗歌中常用手法,可以美化声律并烘托意境。通过觱篥演奏在某一瞬间所发出的音响书写文本,“轹轹”“辚辚”的清脆急落,飕飕的萧飒,啾啾的清越,多是写实描述,在觱篥“线性”音乐表达中加以“点性”,可见觱篥声音表现力之丰富。
拟形既有觱篥物理性的再现,又有对其想象空间的关注,是对觱篥音响效果的音乐性的模拟。如“管裂”“刀截”“婉转”“顿挫”“幽咽”“鸣凤”“龙吟”“虎啸”“雄吼”等文本,运用自然、人文、神话等或真实或虚幻的色彩,充分展示了觱篥乐器的丰富表现力。如李颀《听安完善吹觱篥歌》:“枯桑老柏寒飕飕,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10]1354诗中用自然、神话之声描摹音响,或寒风桑柏吹飕飕之声;或凤之九子,各鸣其清越之声;或龙吟虎啸奏磅礴之声;又或白道飞泉和秋日之声,对觱篥声音的多变作了生动描摹。
拟象是对觱篥的综合审美意境的表达。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10]4992中,薛阳陶一出场便使人见识其演奏技艺之深厚,“翕然声作疑管裂,诎然声尽疑刀截”,其底气饱满似能将管吹裂般,音尾亦是似刀截断般。如此技艺使觱篥表现力“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薛阳陶在婉软与顿挫、急声与圆转之间自如接连,其长音延展如笔直描,低音如石厚沉,高音则如云飘萧,觱篥张力之广阔使人为之惊叹。至第二日席中,薛阳陶再次吹奏觱篥,在丝竹纷乐之中,引领众音,冠盖称雄:“碎丝细竹徒纷纷,宫调一声雄出群。众音覙缕不落道,有如部伍随将军”。诗中觱篥之意象已有在宋代“因谱其音,为众器之首”[13]的头管之势。
再如李颀听安完善吹奏觱篥,在前段将觱篥声音描摹后,又说到觱篥的变调:“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10]1354。慷慨悲壮如《渔阳掺》,恍如云黄日暗,苍茫不已。再变调如《杨柳枝》,恍如春日上林苑中,繁花似锦,生气盎然,全诗将觱篥壮丽与凄美的表现力淋漓尽致得展现了出来。
从拟声、拟形、拟象三个方面所展现的表现力总体可概括为“抑扬激越”。觱篥的清越与磅礴、婉软与顿挫、低回与高亢等对立的情绪常同时出现,形成了觱篥抑扬激越的音乐表现力。
综上所述,觱篥在文人士大夫意识中,已不限于乐器之形以及西域胡器的能指符号,其功能亦不止于军乐、宴席的管吹乐器,蕴涵的所指象征已超越其乐器形态,在跳脱其实用意义的层次后,“幽咽悲戚”的情感导向与“抑扬激越”的音乐表现,深化为文人士大夫寄托情怀的文化符号,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含蓄蕴藉不同的饱满极致的审美趋向,而这种审美气质与格调源于对历史文化内在精神的承续,其显性表现是唐代开放性社会中张扬个性、舒张胸臆的自由与映射,也由此造就出唐代觱篥文化景观的核心机理。
三、唐代觱篥乐人叙事
音乐学者郭乃安指出:“音乐,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创造它的是人,享有它的也是人,音乐的意义、价值皆取决于人。”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14]这一呼吁。觱篥本身与外部社会的交互点便是乐人。通过唐诗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可以发现中原与西域不同阶层对觱篥的传承。
(一)薛阳陶叙事
宝历元年(825),由李德裕发起的“觱篥诗坛盛事”的中心人物便是薛阳陶。白居易诗作中“薛氏乐童年十二”,可推其约为813年生,十二岁时白乐天听其吹奏已发出“嗟尔阳陶方稚齿,下手发声已如此。若教头白吹不休,但恐声名压关李”之惊叹,可见其演奏技艺的高超。
《桂苑丛谈》再次提到薛阳陶相关叙事,“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镇淮海……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游观。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临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询之,果是其人矣……一日公召陶同游,问及往日芦管之事……声如天际自然而来……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职”[15]。记录了李蔚任淮南节度使时,偶遇薛阳陶,而此时的阳陶已为浙右小校,但其演奏技艺依旧“凤吹龙吟定不如”。
罗隐《薛阳陶觱篥歌》也有对此次阳陶所奏的书写:“西风九月草树秋,万喧沈寂登高楼。……功高近代竟谁知,艺小似君犹不弃。勿惜喑呜更一吹,与君共下难逢泪。”[10]7676据《唐方镇年表》记载,李蔚镇淮南时在咸通十一年至十四年,罗隐《投永宁李相公启》中有“伏思癸卯年中”[16]之语,咸通十二年为辛卯,“癸卯”或为“辛卯”之误书。由此可推论阳陶此次落幕吹奏的时间应为咸通十二年(871)九月,年龄应为58岁。
那么,薛阳陶具体身份为何?
唐代开放的社会环境赋予民间乐舞自由发展的空间,在玄宗后期“今欲陈于万姓,冀与群公同乐,岂独娱于一身”[17]的政策推动下,宴乐之风盛行,帝王士夫的身体力行使乐人的生存形式更加丰富,乐人流转于市井青楼、家宅宴席之中,亦有被豢养于宅邸家院。而无论是梨园子弟、民间乐人均为“乐户”,社会地位低下属贱民阶层。“大体上,可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二种:而官贱民又分为官奴婢、官户、杂户、工乐及太常音声人等。私贱民又分为私奴婢、部曲、客女、随身等。”[18]而家伎属于私奴婢。通过《唐会要》记载,可见蓄养家妓风气之盛,且为朝廷许可,如“天宝十载九月二日敕:‘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时,覃及中外’”[19],但蓄养的数量多少与主人的等级地位有关。
唐中叶后,随着市场经济与雇佣制度的发展,家伎可自由买卖和雇佣。而李德裕的家伎演奏技艺颇高,《乐府杂录·琵琶》中提到其家伎师从曹纲,颇有天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廉郊者,师于曹纲,尽纲之能。纲尝谓侪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灵弟子也’”[20]84。《乐府杂录·方响》也提到李德裕家伎吴缤善方响,“咸通中,有调音律官吴缤,为鼓吹署丞,善打方响,其妙超群,本朱崖李太尉家乐人也”[20]115。可见李德裕家伎颇有盛名。
《桂苑丛谈》记薛阳陶为“李相左右者”,罗隐《觱篥歌》记“李相伎人吹”,可见薛阳陶为李德裕的家伎。而家伎具有不稳定性,随着恩主政治处境的变化,或面临易主或被解散。白居易《感故张仆射诸妓》中便有相关描述:“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10]4845李德裕逝于850年,彼时阳陶约37岁。而在此间或此后,阳陶或被遣散又或被放免,最终应是脱籍成为官府负责运米事宜的浙右小校,并凭借李蔚赏识,为其二子授职。
(二)王麻奴与尉迟青“斗乐”叙事
《乐府杂录》记录了倨傲自负的河北幽州王麻奴,拒卢姓人邀请吹奏觱篥,遭怒斥其技艺不如尉迟将军,遂赴长安访尉迟青“斗乐”之事。“大历中,有幽州王麻奴者,解吹觱篥……时有从事……请麻奴吹一曲《子相送》,麻奴偃蹇,大以为不可,卢乃怒曰:‘汝艺亦未足称者,殊不知上国有尉迟将军冠绝今古!’麻奴大怒……不数月,到京,访尉迟所居,即常乐里也。乃于侧近就居,日夕加意吹之。尉迟每经其门过,如不闻。麻奴尚未分,因赂其阍者,方得通见。乃于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羝》,曲终,流汗浃背。尉迟……因自出银字管,於平般涉调中吹之。麻奴惊偾,垂泣拜之……遂将乐器碎之而归,终身不复言觱篥。”[20]105
此处的王麻奴“除戎师外,莫有敢轻易请者”,而卢姓人欲请其吹奏,按上文所示说明王麻奴并非家伎,而是流传于军中、宴饮中的觱篥乐伎。而尉迟青乃一将军,究尉迟氏之来源为于阗王室,相传唐以前属于Vijiya一族,尉迟为Saka语中的汉文译音,在长安居住的尉迟氏诸人,或为华化已久的魏尉迟部一族,或为隋唐之际尉迟质子入华者,抑或族系来历皆不明者[21]。最为著名的尉迟敬德出自后魏尉迟部,居西市南长寿坊,另有吴国公尉迟刚居嘉会坊、驸马都尉尉迟安居永平坊,三者居所自北向南毗连,或为同一部。而于阗质子则有著名画家、袭封郡公的尉迟乙僧和跋质那父子。文献记载代宗时期的尉迟青官至将军,且居于宫廷相近、豪爵聚集的常乐坊,善吹觱篥,其后文宗时期又有尉迟章善吹笙,尉迟氏艺术造诣颇高。而尉迟青是与魏尉迟部有渊源,还是系于阗质子后裔,今已不可考,且这则故事有夸大之嫌,弱化了唐人固于头脑的传统制度和等级秩序,使王麻奴能够在贵人聚集的常乐坊找到居处日夕吹奏,又使其能够贿赂将军府守门人得见尉迟青,富有传奇色彩。但其表达了西域尉迟贵族将西域觱篥在中原的传承,也表达了中原觱篥伎人对于觱篥演奏的极致追求。
通过以上与唐代乐人相关的历史叙事,一方面可看到觱篥在不同阶层、不同民族间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觱篥乐伎社会地位低下却又受人追捧,形成了社会身份的“双重性”。正是基于宫廷贵族、文人士大夫以及活跃于宫廷之外的乐人对觱篥的传播,使乐人的音乐活动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积淀。
四、唐代觱篥曲《雨霖铃》
唐代觱篥乐曲丰富,有掖庭女所作三次易名的《怨回鹘》,有王麻奴与尉迟青“斗乐”的《勒部羝》,有乐伎史敬约为唐懿宗随拍所作的《道调子》,亦有唐宣宗所作的《杨柳枝》《新倾杯》等曲,而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雨霖铃》。
(一)《雨霖铃》的历史考辨
唐代《雨霖铃》在诸多文献与诗词中多有矛盾之处,集中在创作的人物、时间、空间方面。《明皇杂录》记载:“帝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即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弟子善吹觱篥者,惟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22]公元756年因安史之乱,玄宗逃往蜀地,在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雨中听闻铃铛之音,音与山、静与动相呼应,为悼念杨贵妃所作,教授于觱篥乐人张野狐吹奏。与此相吻合的是《旧唐书》载:“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6]1051-1052,说明玄宗善制乐,且数量颇多。此为“玄宗入蜀于斜谷作乐说”。
与此不同的是亦有“玄宗入蜀于上亭作乐说”。《旧唐书》记载唐明皇入蜀的路线及时间:“六月……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朕须幸蜀,路险狭……辛丑,发扶风郡,是夕,次陈仓。壬寅,次散关……丙午,次河池郡……秋七月……甲子,次普安郡”[6]231-233,普安郡即今四川剑阁县、梓潼县等地。《碧鸡漫志》中也提到唐明皇自陈仓入散关、出河池的入蜀线路,未经斜谷(骆谷)路,且剑州的上亭中有刻诗记录明皇闻铃之地[23]31。罗隐有诗:“细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铃。贵为天子犹魂断,穷著荷衣好涕零。剑水多端何处去,巴猿无赖不堪听。少年辛苦今飘荡,空愧先生教聚萤。”[10]7665也提到明皇是在剑州(今四川剑阁县)的上亭中有感雨淋铃,而非斜谷。史诗互证,《雨霖铃》创作于剑州上亭的可能性更大。
与“入蜀说”相矛盾的是白居易的“居蜀说”,《长恨歌》中“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10]4826-4830,诗中与《旧唐书》所记载的时间与地点吻合,不同的是诗暗指玄宗登剑阁后,在居蜀期间夜闻雨闻铃而作。这一说法不无可能,公元756年8月,玄宗在蜀都府衙中得知太子已在灵武称帝,次年10月返京,居蜀期间作《雨霖铃》亦有可能。
此外,《乐府杂录》与上述记载差异较大,“雨淋铃者,因唐明皇驾迴至骆谷,闻雨淋銮铃,因令张野狐撰为曲名”[20]137,提出此曲是在公元757年玄宗回京时途经骆谷,闻雨霖銮铃有感,令张野狐所作,即“张野狐返京于骆谷作乐说”。根据《旧唐书》记载,玄宗返京的时间及路线为:“上皇发蜀郡。十一月丙申,次凤翔郡。肃宗遣精骑三千至扶风迎卫。十二月丙午,肃宗具法驾至咸阳望贤驿迎奉”[6]234-235。其返京路线先后经凤翔、扶风、咸阳,而骆谷位于今陕西周至县西南,虽古今各地域图略有差异,但骆谷于以上三地路线相距较远,返京经骆谷应有误。且从时间来看,十一月至凤翔郡,再向东至骆谷时已近深冬,闻雨之情景或较难。
张祜诗“雨霖铃夜却归秦,犹是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10]15884也提到张野狐叙述明皇垂泪教授的情景。陈寅恪先生解读张祜诗意为乐曲作于回京途中,明皇教授张野狐[24],有对诗意的误解之嫌。王灼《碧鸡漫志》认为:“祜意明皇入蜀时作此曲,至雨淋铃夜却又归秦,犹是张野狐新曲,非异说也”[23]32,即玄宗返京其情景却如入蜀之时,沉湎往日,是对明皇的哀叹,同时也有批判之意在其中,并非指返京所作《雨霖铃》。
以上诸说有异,但《雨霖铃》在记载中曾有再次吹奏之情景。《明皇杂录》:“车架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下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嘘唏,其曲今传于法部。”[22]46-47西京收复后明皇归华清宫,然物是人非,再听《雨霖铃》,悲苦不已。杜牧诗“零叶翻红万树霜,玉莲开蕊暖泉香。行云不下朝元阁,一曲淋铃泪数行”[10]6053,也提到了明皇在听《雨霖铃》这一情景。
由此可推论《雨霖铃》是在756-757 年间唐明皇所作、张野狐吹奏的觱篥曲,张野狐返京于骆谷作乐说应为误传,而无论是在入蜀途中还是在居蜀期间创作,可知的是乐曲所蕴涵的悲凉、哀怨基调被延续下来。至南宋时,有乐曲《双调雨淋铃慢》,陈寅恪认为该曲“颇极哀怨,真本曲遗声”[24]32。至今,亦有西安鼓乐中流传的《雨霖铃》。
(二)《雨霖铃》在西安鼓乐中的遗韵
西安鼓乐由笙、管、笛以及多种打击乐器组成,其起源难以考证,但诸多学者经考证后均认为西安鼓乐的演奏形式、曲式结构、乐器、曲牌等有唐代音乐的元素,其乐曲丰富而多元,有多首与唐代诗词以及唐代教坊曲名相同,如《倾杯乐》《婆罗门引》《遐芳怨》《虞美人》《雨霖铃》等。
据西安鼓乐学者焦杰所述,西安鼓乐《雨霖铃》(图1)是白道峪兴安禅寺教衍和尚教于教友余登瀛老先生的抄谱,1985年学院大力发展西安鼓乐,聘请其子余铸先生前来授课,余先生将父亲留下的多首古谱抄本带来教学,其中便有此曲。但遗憾的是老先生并未传授此曲的韵唱及更多信息,余先生也是第一次发现这首乐曲,其他西安鼓乐社中也未见此曲。经乐社成员译谱以及在笙、管、笛、琵琶、阮等多种乐器上的试奏,最后推论西安鼓乐《雨霖铃》有可能就是唐代觱篥遗韵。

图1 西安鼓乐《雨霖铃》(由焦杰先生提供)
杨荫浏先生与查阜西先生在考察北京智化寺音乐时将演奏音乐的僧人称为“艺僧”。寺院蓄养艺僧由来已久,《乐府杂录》中记载唐开元中有华严寺琵琶演奏技艺卓越的段善本[20]79,唐代归义军时期文献地亩残帐中有:“音声:王安君贰拾亩”,这里所记的“音声”人虽属杂户,但是可以被分配土地[25],可见社会制度给予艺僧一定的生存保障。这也成为宫廷乐人“退休”后维持正常生活的基础,卢尚书“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10]8930,严维“秦僧吹竹闭秋城,早在梨园称主情”[10]2914等诗均记录了这一情景。由此传承下来的寺院艺僧便成为宫廷音乐及至民间音乐的重要媒介。
由西安鼓乐《雨霖铃》乐谱可知其谱字音域为“合至高上”,《乐书》觱篥注:“今教坊所用上七空,后二空,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十字谱其声”[13]644,觱篥演奏音域为“合至五”。两者相似点为最低音均是“合”字,按以《乐书》谱字并未达到西安鼓乐古谱中的“高上”,若以此分析,西安鼓乐《雨霖铃》并非唐曲《雨霖铃》之遗韵。而从乐器法角度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觱篥最特殊的演奏技法——“一孔多音”。《香研居词麈》说到头管(即觱篥)的指位法中“五字有高、下、紧三声”[26],即在第九孔“五”字可奏出下五大吕清、高五太簇清、紧五夹钟清三字。《律吕正义》中也写道:“盖因大管有勾字孔,无凡字孔,取凡字与工字六字两孔,乃取高乙高上两字与最上一孔。”[27]也说明大管(即觱篥)指位法在第九孔可出高乙、高上二字,可解释为觱篥通过唇口的控制恰好可从“五”奏至“高上”。
从上述《乐书》觱篥的指位加之“一孔多音”的技法可奏出“合至高上”的音域,而西安鼓乐《雨霖铃》音域恰是“合至高上”,不可谓巧合。且西安鼓乐《雨霖铃》所传递的哀情与唐玄宗《雨霖铃》情思一致,可推由艺僧教衍明代洪武年间的抄本确是由觱篥所奏,是否为唐玄宗所作之《雨霖铃》则已不可考。但由此可见,寺院作为宫廷音乐传入民间的重要路径,艺僧作为历史音乐传承的重要中介,形成了中国古代音乐传播的特殊文化景观。
五、结语
觱篥作为西域乐舞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自北魏以来的数代积淀,在唐代多元文化共生繁荣与唐人开放包容的历史背景下成鼎盛之势,深植于宫廷朝野、市井生活并产生了大量觱篥诗歌。诗人与觱篥乐人或正听或隐听、又或潜听的交流形式,开创了唐代觱篥诗的繁盛之景,书写了觱篥幽咽悲戚的感染力与抑扬激越的表现力,二力结合产生了区别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西域极致性审美特征。除了诗人与乐人,还有一特殊人群在觱篥的历史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便是艺僧。其传承的《雨霖铃》虽已难以考证是否为唐玄宗之作,但从乐器法及音乐内涵分析,的确承袭了唐代觱篥的音位吹奏以及唐曲《雨霖铃》的哀泣情思。
总而言之,西域觱篥跨越了时空、民族与观念,在唐代多元文化建构过程中与中原文化形成深度交融,成为音乐与诗歌表情达意的手段。觱篥乐曲、审美与演奏亦成为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促进了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