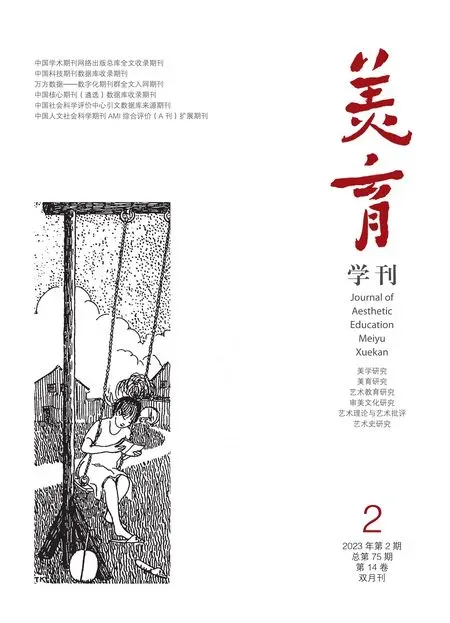洋画再造:20世纪早期广州西画教育的重建与推广
郭林林
(广州美术学院 科研创作处,广东 广州 510261)
一、西洋画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明代万历年间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万历七年(1579)耶稣会士罗明坚来到广州,两年后(1581)利玛窦在广州开始传教,同时也带来了圣母和救世主的画像等油画作品。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京觐见神宗皇帝并呈献圣像油画,在给神宗的上表中云:“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两架,万国图志一册,雅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异耳。”(1)韩琦等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卷二·贡献与方物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页。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美术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西洋画最早传入中国的官方文献记载。而澳门被葡萄牙租借后,西洋画亦随之传播至澳门,至今在新会博物馆仍保存有一幅清代之前的油画《木美人》(图1)。入清之后,传教士郎世宁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被召入宫充任宫廷画师,使用中国画具、颜料和纸张,以西洋画技法来绘制写实逼真的绘画作品,被称为海西画法。延至18世纪中叶,广州作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以西洋画法描绘中国风景的外销画兴起,画师努力学习模仿西洋画技法和风格,其中较著名者有林呱等广州画家,他们都曾于国外学习过西洋画技法。据《续南海县志》载:“关作霖,字苍松,江浦司竹径乡人。少家贫,思托业以谋生,又不欲执艺居人下,因附海舶遍游欧美各国,喜其油画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时在嘉庆中叶,此技初入中国,西人亦惊以为奇,得未曾有云。”(2)《续南海县志》,卷二十一,列传。也因为此,西洋画开始在广州地区传播,广州各级官员、行商热衷于邀请画师用西洋画技法为他们绘制肖像以留存。

图1 油画《木美人》,明末时期创作,广东新会博物馆收藏
二、旧式西画教育的落后与洋画运动的兴起
虽西洋画早在清代中期就已经传入广州,但直至20世纪20年代广州真正的西洋画教育依然是一片空白,西洋画教育主要是教授以放大尺来描绘临摹擦炭肖像画和临摹风景画。据艺术家吴婉描述广州当时的西洋画教育状况:“作为西洋画的形式而出现的,在市上就有所谓西法写相之流,什么美术写真馆等,就是除了旧有的‘大座装真’之外,兼写擦炭粉的肖像,那是以放大尺——即如现在自称写真的画家所用的放大尺,从照片上把人的尊容放在纸上,然后拿蘸着碳粉的毛笔,慢慢对准照相上的光暗擦成的……擦肖像之外,还擦一些风景,也是从风景的照片上搬过来的。”[1]当时广州的西洋画教育即是如此,然放眼全国也是一样,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画归来的胡根天对当时的西画教育状况了如指掌,他在民国晚期所作的《西洋绘画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中回顾了当时全国西画教育的发展情况:“说起国内的艺术教育,民国初年间,国人还不晓西洋绘画应该怎样学习,在上海、广州等大都市,醉心西方艺术的青年,他们所谓学习西洋绘画,最得意的玩意,便是找寻外国来的印刷画片开始临摹,或将摄影像片放大用炭粉照样擦写……上海方面,也和广州幼稚到同样可怜。现在上海美专的前身,就是民国二年由刘季芳(海粟)、乌始光(已故)、张聿光几位先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也一样教学生临摹稿本或写些照像用的背景。民国四年的春季,陈抱一短期留学日本白马会第一次归国(翌年再东渡,才入东京美术学校,民国十年毕业后第二次归国)。他在上海办了一间东方画会教学生写画,据说开始用木炭条写石膏模型了,这算是得风气之先。”(3)胡根天:《西洋绘画在中国的发展》,原载于1947年11月1日《中山日报·艺术周》,转引自广州市文史研究馆编《胡根天文集》,2002年,第103页。
虽则当时西画教育不是甚为普及,且依旧巢袭于往昔的旧规,远远落后于欧美西画的发展趋势。20世纪以来在新文化运动的号召下,发展现代主义西画教育的呼声渐趋强烈,并且随着一批艺术家的留学归来并参与到现代西洋画的教育与推广,鼎盛一时的洋画运动得以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在上海兴起,标志之一就是裸体画已渐次被社会接受,美术家陈抱一在《洋画运动过程略记》(续)中说:“民国十年前后的期间,上海的洋画研究风气,似乎已经通过了相当长久的摸索时期,而开始呈现开拓时期的症候来了。大概民国九、十年以前的洋画展览会中裸体人物画之陈列还不轻易实行,往往受到无常识无理解的干涉。但民国十年以后,对于裸体画之陈列,已渐次不致有人太过神经过敏了。”[2]与此同时,胡根天、冯钢百等一批留学日美学习西洋画的学生得以学成归国,他们在上海见到这一西洋画发展盛况,内心产生触动,将这一洋画风气带回广州,并开启广州的西画再造运动。
三、广州西画展览与现代主义启蒙
20世纪20年代之前偏处于华南地区的广东处于军阀混战的乱局之中,广东军政局面事变纷呈、人心不靖,无力发展教育。直至1920年孙中山领导的粤军驱逐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广州政局趋于稳定,随即成立了广州新的市政府,任命教育家许崇清担任广州教育局长(图2)。许崇清热衷于教育,并对美育抱有极大兴趣,早在1920年就撰文《美之普遍性与静观性》与蔡元培进行辩论,指出美育代宗教之说的二大误缪:“论者因此二大谬误,遂至混淆美之意识与宗教意识,又复混淆美之意识与道德意识,既主以艺术代道德之论,复以美育代宗教之说,论者视人性则太简,视道德又太轻矣。”[3]另外热衷美育的许崇清早在1915年日本留学期间就与胡根天等一批粤籍艺术家相识,胡根天对此曾追忆道:“1915年我在日本东京开始和许老认识,是朋友中接触比较多的一个……许老不是研究美术的,但对美术深感兴趣,并且深刻地认识到美术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4]

图2 胡根天(左一)与许崇清(左二)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合影,1922年
许崇清在担任广州教育局长之后即着手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筹建工作,他先委托广州画家陈丘山信邀此时已经回国的胡根天返粤,并在广州与胡根天面谈广州美术教育事业筹建事宜。胡根天对当时场景回忆道,“我回到广州之后,走访许老于大北直街西化二巷劳园,谈话当中,他提出两件事要我考虑怎样做:一、创办一间公立美术学校;二、首先成立一个群众性美术团体,两件事我都表示赞成”[4]。根据许胡两人商议规划,胡根天先要成立一个群众性美术团体,进行民众美术启蒙,然后再着手成立美术学校。于是胡根天就联系了陈丘山、梁銮、冯钢百、梅雨天等画家成立了“赤社美术研究会”(图3),之所以取名为赤社,据说是“因为赤色在色彩心理学上表示热烈、诚挚、积极和刚强,而我国古代五行阴阳学说认为南方属火,火色赤,故名”[5]。赤社成立之后接着就于1921年10月1日在广州永汉北路(今北京路)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和操场举办了广州首次西洋画展览会,又称赤社第一回美术展览会,展出了油画、水彩画、木炭素描、粉彩画和铅笔速写等共160多幅作品。当时论者认为“能够称为纯粹的西洋画展览会,在广州的,这算第一次了”[1]。这次展览因为是广东首次西洋画展览会,吸引了大批观众参观,获得了成功。胡根天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文章《赤社美术研究会的始末》中对当时的状况做了介绍:“永汉路是人来人往最繁闹的地方,我们用白布写上红字的一面横额‘赤社第一次西洋画展览会’挂在市立师范学校的街口。当时有些观众出于好奇心,有些则是抱着研究和学习态度而来的,所以每天参观的人相当多,作为西洋画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开始起了作用的。”[6]美术史研究学者陈滢对赤社第一次西洋画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胡根天、陈丘山、梁銮、冯钢百等人从日美等国留学归来所展示的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油画、水彩画作品给广州人呈现了西洋画正确的姿容,并认为“作为广东出现最早的西洋画展,它是作为纯粹的艺术品供观众欣赏的,具有自主的美学目的。它开启了广东社会欣赏西画的风气,作为广东西画启蒙的先声,影响是深远的”[7]826。

图3 赤社成员合影,1922年
与此同时,广东美术界另一件大事也在紧张筹备之中,这就是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会(图4)。这次展览会筹划者为当时国民党粤籍实力派大员、广东省省长陈炯明,陈氏在1920年驱赶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后倡导“保境安民、联省自治”,致力于将广东建设成为模范省,加之陈氏颇有文人气息,热衷于地方文化建设事业。陈氏素与岭南画家高剑父相熟,高氏留日学习过绘画,对展览一事颇为熟悉,之前二人于漳州合作举办过美术展览且取得了不俗效果,故决定在广州举办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具体个中缘由在当时报刊中已有评述:“本会(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发起之远因,陈省长平日对于美育,最为注重。尝谓一国之文明程度,视美术之消长以为衡。故从前在漳州时,亦曾开美术展览会一次,盖深知美术为工业之母,非振兴美术,不足以促工业之改良也。”(4)见《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会场日刊》第2号。此次展览会依照西方展览制度设有作品审查组,成员囊括了广东当时画坛各方,对送展的近千件作品进行严格甄选,据时任审查委员会西洋画审查委员的胡根天回忆:“我们首先就把千幅以上——其中包括孙中山肖像三百多幅,陈炯明像二百多幅的炭粉相以及炭粉风景画全部淘汰;其次不论油画、水彩、粉彩、铅笔等的临摹品以及广告月份牌画也给他落选了。结果入选作品只有一百五六十幅。另外加上审查员作品合共差不多二百幅。”[8]156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展览于1921年12月20日在广州文德路广东画业馆(今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展,并大获成功。据当时报纸报道仅开幕两天,就卖出五千多张门票,盛况空前:“此次美术展览会……顷查一二日共售券五千余张,足征粤人心理,崇尚美术,而会内美术之多且精亦可见矣。”(5)见《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会场日刊》“游览券销额日增”条。而此次展览会的许多作品以新颖的面目出现,特别是许多留学日本与欧美回国画家的西洋画的展出,打破了以往人们对西洋画的传统认知,也促进了西洋画在广州观众中的艺术影响。胡根天曾高度评价此次展览,认为“对于广东美术多方面的发展,作用是显著的。特别是对于西洋画方面的理解,在观众中逐步踏上了正确的方向,给予那些以擦炭相为号召引诱青年或以临摹抄袭为本领的不正之风一次无情的打击”[8]159。

图4 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览会全体职员合影,前排左三为高剑父、左四为陈炯明,中排左一为胡根天
四、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建立与现代西洋画规范教育
经过赤社第一回西洋画展览会和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之后,广东美术发展迎来了一个大好形势,群众对美术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全面地欣赏了真正的西洋画。社会对美术尤其是西洋画的观感得到了新的认识,促进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创建。用胡根天的话来说,就是“志愿学习美术的青年逐渐多起来,这就是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设立的时代背景”[9]76。就这样经过近一年的筹办,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于1922年4月24日在广州中央公园成立,成立之初因为校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胡根天等最终决定在广州中央公园东北角空地搭建临时校舍招生开课(图5)。

图5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全体员工合影,1922年12月,前排左八为胡根天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成立后由广州教育局长许崇清兼任校长,胡根天、冯钢百分别担任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据当时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生赵世铭的回忆:“胡根天为教务主任,兼任西画、艺术史、艺术理论老师;冯钢百为总务主任,兼任西画老师;赵雅庭任西画老师;陈丘山任水彩画老师;梁銮任图案构成法老师;沈光焘任国文老师;何拙任法文老师。”[10]57在系科专业上鉴于当时情况只设立了西洋画科,于1922年当年即开始招生。据资料记载,第一届学生共80人,其中女生12人,学生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分作两班教学,西洋画系的学制为四年,于1922年4月26日开学。[7]826之所以只设立西洋画科,据笔者分析应该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师资班底是以胡根天为主的赤社美术研究会成员,成员大部分为西洋画专业人员,在《尺社小史》中关于赤社(6)赤社1921年成立,至1929年改名尺社。具体改名原因可见《尺社小史》,大致因1927年夏间中国国民党实行分共后,“社会上无智者流,见了‘赤’字就有点恐怖”,为避免误会,改名尺社。早期的创建过程对此就有说明:“民国十年(1921)的秋间,同人中陈丘山、胡根天、容有玑、徐守义、梅与天等七八人相聚于广州,当时大约一则有点慨乎社会上对于西洋美术太不了解,二则自己一伙人也该有一种结合,不论自渡和渡人都有赖乎群策群力,于是赤社便组织起来了,并非自吹,这是中国南方破天荒的一个研究西洋美术的团体。”[11]由此可知以赤社成员为教员班底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早期的专业构成主要限于西洋画方面。其二是广州当时的画坛状况,画坛主要为两派所把握,一派是以高剑父及其门徒为主提倡在国画中引入西方写实画法具有日本画风味的折衷派,一派是以赵浩公、黄般若等人为主的主张延续传统画法的中国画画家,两派早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成立之前就互相论争,以至于形成一种相互攻讦的局面。对此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实际创办者胡根天亦熟知于胸,他曾在对广东第一次美展的回忆文中特别提到这一情况:“这一次省展的评选,中国画方面,由于以高剑父、高奇峰为首由日本引进的比较倾向于形似的画法(当时叫做‘折衷派’),和我国传统——主要是宋、元以来已经形成的各家画法之间,在过去几年间首先由高剑父挑起争论,人为地造成较大矛盾和对立,互不相让,甚至互相攻击。因此,在这一次美展评选一开始又出现了争论。”[8]154而且依据胡根天的观点,他对折衷画派的做法亦非常不认同,甚至屡次撰文进行讥评,并在《新国画与折衷》一文中表明他的态度,“我对于新国画的建立,否决了折衷这一个办法”,并且认为,“假使有人徒然以‘折衷’为标榜,认为这是百年的大计,而忘记了自身应当还有更远大,更健全的前途,这在政治上必然陷国家于附庸而失去其独立性,使艺术和文化也必然造成卑陋的风格而难有坚强伟大的发展。那是应当警惕的!”(7)胡根天:《新国画与折衷》,原载于《中山日报》1948年2月26日,见《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研究文选》(上),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340页。虽然胡根天不认同折衷派,但是折衷派主将高剑父却与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有着非凡的关系,是当时广东文化界的精英人物,并于1920年11月被任命为工艺局长兼工业学校校长,然而又因“甲工学潮”而被迫离职,旋由陈炯明委托组织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如果市立美术学校成立中国画科,时任省长陈炯明极有可能让自己的好友高剑父前来主持。有鉴于此,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在成立之初仅设立了西洋画科,而中国画科的设立则是在四年后的1926年,此时的陈炯明已因为发动“六一六兵变”反叛孙中山革命事业而被视为国民党的叛徒,并于兵败之后避居香港。与此同时,高剑父指派学生方人定发表论文,拉开了与国画研究会的笔战序幕,在这时候成立中国画科,并将折衷派反对方广东国画研究会成员聘为教授,使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成为国画研究会的阵营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五、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洋画教学成果
根据现存的校史资料来看,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西洋画系的学制为四年,采用新式的课程式教育方式来培养人才,一改过去单一依靠师承关系传授绘画的状况。学生入学之后,第一年和第二年以画木炭素描为主,对象是石膏模型和景物,然后是人物,素描有了一定基础后,就学习水彩、粉彩,第三年才开始画油画。1925年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程,以供三年级学生作画训练,这一举动在20世纪20年代是非同寻常的。[7]826除了木炭素描、水彩画和油画的技法课程之外,根据当时形势还开设有美术史、美学、艺术概论、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等理论课,以及国文、外国文和体育等普通科目,外国文以法文为主修科,日文和英文为选修科,共计有17门课程。在课程编制上,广州市立美术学校采用按照课时授课的方式:“市美各种科目依照规章分别编配,以实习时间为主体,各班实习时间多编在上午,理论课多编在下午。每日八时至十时五十分、下午十二时三十分至四时二十分为授课时间,平均每班每周授课时长至多四十小时至少三十七小时。各画系各班之理论功课,由教师自编讲义,或用课本教授。”(8)刘石心:《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一览》,广州: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1937年,第2-3页。据对西洋画科课程表中各科目课时的安排统计来看,课程设置强调实习课(即绘画实践),注重基础技法的训练。以课程来看,设置与胡根天在日本留学的东京美术学校类似。刘海粟曾于1919年9月赴日本考察美术,并将此次赴日见闻撰写成《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书,书中对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各科课程设置进行了专门记载,其中关于西洋画科的课程记载如下:“西洋画科第一学年专门习木炭画,写石膏像,并授以油绘静物和郊外写生……第二学年,用模特儿作木炭人体写生……第三四学年,教授油绘写生,人体以外还练习静物和野外写生。”[12]由此可见,胡根天在设置西洋画系教学课程安排时,是参照了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课程安排,而东京美术学校的课程安排据刘海粟观察又是和法国巴黎学院一样(9)刘海粟在《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中写道,“(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所有的制度和办法差不多和法国巴黎学院一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84页。,可见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西洋画科课程安排是和当时世界美术教育相接轨的西画教学方式。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师的选聘以留学归国的西画教师为主,虽则教师中早期以留学日本的居多,但同时兼顾聘任有留学欧美背景的西洋画教师。胡根天十分了解当时中国人在海外留学学习西洋画的情况,他在《西洋绘画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中就对这一情况进行了说明:“民国成立之后,到外国留学的风气,近则日本,远则欧美,一时真有风起云涌之概,学习西洋绘画的也不乏其人。最初十余年间,由日本归国的西洋画家……华南有陈丘山、许敦谷、谭华牧、何三峰、陈士洁、关良、丁衍庸诸先生……由美洲归国的华南有梁銮、冯钢百、刘博文、赵雅庭、黄潮宽、朱炳光、梅仑昆、余本、李秉诸先生。由欧洲归国的,华南有李超士、林风眠、陈宏、关金鳌诸先生。他们学成陆续归来之后,一面各以其自己的作品公开展览,作为新绘画的介绍;一面又多数从事于艺术教育,以栽培国内有志于西洋绘画的青年。”(10)胡根天:《西洋绘画在中国的发展》,见广州市文史研究馆编《胡根天文集》,2002年,第103页。所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在教师中既有留日的谭华牧、何三峰、陈士洁、关良等,也有留学欧美的冯钢百、赵雅庭等人。这些教师深受现代西洋画的影响,如冯钢百画风具有扎实的学院派古典风格,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广东画坛,曾被视为油画艺术的“正宗”。胡根天与何三峰画风绚烂,近于印象派;谭华牧则更进一步,画风凌厉接近野兽派;关良画风则倾向于稚拙单纯,充满现代意味。对这些现代主义的西洋画画风,校长胡根天也是了如指掌,他曾追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初期西洋画画风的发展轨迹:“大概由民国初年至十五六年,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差不多完全支配了西洋绘画整个画坛,十五六年以后,则后期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或先或后,增加了不少活动。这大概跟西洋方面的艺术潮流相一致的,不过还未达到充分发展的境地而已。”(11)胡根天:《西洋绘画在中国的发展》,见广州市文史研究馆编《胡根天文集》,2002年,第104页。这说明活跃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师的绘画风格是和当时世界西洋画发展潮流相呼应的。这些教师以所学新洋画带领学生进行写生、构图等洋画教学活动,更新了西洋画在民众心目中的认识,使广州地区的西洋画面貌焕然一新。这正如胡根天所说的:“这样,西洋美术的启蒙运动使社会上渐次普遍地开展了一个新局面,过去只懂得临摹抄袭的错误认识被扭转过来了。”[9]78
这些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并存的风格各异的画风也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州市立美术学校首届西洋画科毕业生赵世铭这样回忆当时各位教师的绘画教育内容:“何三峰的作风倾向当时风靡世界的法国印象派,谭华牧更跨进一步,接近后期印象派与野兽派之间简练清丽的风格,陈士洁较为保守,技巧亦逊一筹,不若何、谭两人之纯熟多变化,但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受过严格训练。令我们观感一新,和冯钢百老师的稳厚华滋、千锤百炼、大家典范的写实作风大异其趣。换一句话说,冯老师的大作,仿佛高不可攀,只许仰止,难以继踪。反之,后者清新可喜,平易近人。比较之下,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艺术风格的衍变,与艺术流派的多彩多姿。这个展览会在同学间播下革命性的种子,茁发了倾向自由奔放的嫩芽,吴琬(子复)对之尤为倾倒,影响一生,至死不渝。”[10]571922年考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吴琬也回忆说:“以印象派的作风,在画面上运用着绚烂的闪耀的色彩的何三峰现实的风景;以后期印象派作风,表现物体的内在的真实的谭华牧先生的人物,却给市立美术学校的学生以很深的影响……他们对于自己的老师冯钢百先生也怀疑起来。”[1]这就使广州洋画界的艺术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代主义成为洋画的主流艺术倾向。美术史学者陈迹曾对此做了至为恰当的评论:“20世纪中后期,留学日本的何三峰、谭华牧、丁衍庸、关良、许敦谷等,以及留学法国的陈宏、留学墨西哥的赵雅庭等,亦都先后受聘为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洋画教授;该校还聘请了陈之佛以及‘决澜社’的庞薰琹、倪贻德等来校任教;本校第一届毕业生吴琬、李桦等也相继成为该校青年教师。至此及稍后一段时期,在广州的洋画界,现代主义绘画——尤其是带有东方情调的类野兽主义风格的‘新派绘画’,几欲压倒原来的‘官学派或保守主义’,而成主流。”[13]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生受益于兼容并包、多元开放的学习风气,绘画水平得以不断提升,而且对西洋画的追求也趋向于现代性。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生很快在当时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中取得佳绩,据赵世铭回忆:“一九二九年四月在上海举行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中,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师生获选展出者多人,作品在特刊揭载者共六人,都是西洋画,计丁衍庸《女士读书图》、冯钢百《肖像》(图6)、梅雨天《隆冬》(图7)、许敦谷《肖像》、陈宏《欧妇》、何三峰《画室之中》。第二次全国美展,则于八年后(1937)四月一日起在首都(南京)新建之美术陈列馆揭幕……市美师生,西画入选者九人,图案四人,雕刻二人。”[10]97-103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还培养了如赵兽、梁锡鸿、李桦、吴琬等一批在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美术人才。1927年,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洋画系首届毕业生李俊英(李桦)、吴琬(吴子复)、赵世铭组成青年艺术社,宗旨是要“为艺术而努力,用方刚的血气去开拓新艺术领域,反对守旧因循的态度”,力图推动现代艺术发展。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立的先锋美术团体“中华独立美术协会”,骨干成员如赵兽、梁锡鸿、李仲生等,也曾经就读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受该校青年教师艺术思想和新派绘画的影响,走上了比师辈更新潮的艺术风格追求道路。

图6 冯钢百《肖像》(12)见《上海漫画》1929年第52期。

图7 梅雨天《隆冬》(13)见《美展》1929年第6期。
六、结语
这样,通过现代主义西画的展览和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创办,广州的西洋画教育和艺术创作面貌得以改观,真正的西画教育得以普及和提倡,现代主义西画创作大行其道,洋画实现了再造,对华南乃至中国的西画教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28年的《青年艺术》就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市美的出世,是应时代的要求的。她不特是南方美术界的中枢,同时也是画坛的灯塔。她的降生,便是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分野时期。她一方面训练出一班艺术界的新殿军,同时更给人们以认识艺术的标的。所以她在广东的艺术运动,以至在南方的艺术运动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无可怀疑了。”[14]同时,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还带动了广州画坛的现代转变,可谓是广州现代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不仅在广州确立了纯粹艺术的西画标准,还以培养的学生为根基催生了华南乃至全国现代美术社团的建立,其中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毕业学生李桦、吴琬、赵世铭于1927年创办的青年艺术社以及李桦、赖少其等于1934年创办的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最具影响力。
如果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放置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美术教育的版图及洋画运动的发展格局上来看,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则更是与上海一样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一极。如当代美术史家评价所言:“胡根天主持下的市美格局,实际上是当年在东亚地区已初具规模的现代美术活动网络的一个成功实践,自20年代初开始,广州、东京、上海三个东亚都市开始将引进西方现代美术体制的实践活动逐步推向高潮,三个城市间出现频为活跃的联动现象。20世纪初在东京等地学成归来的留学生纷纷谋职于上海和广州的美术院校,他们开始制度化、规模化地介绍西方美术观念和艺术生产方式。由此,沪穗两地率先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基地。”[15]当我们回顾百年前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和洋画运动时,广州的美术先驱者的西画展览和再造洋画的教育活动至今仍值得我们去再度探索,寻求先辈们那种筚路蓝缕推广现代美术精神、立中研西探索时代美育路线,而这样的时常回望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百年历程也能带给我们对当下美术教育的思索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