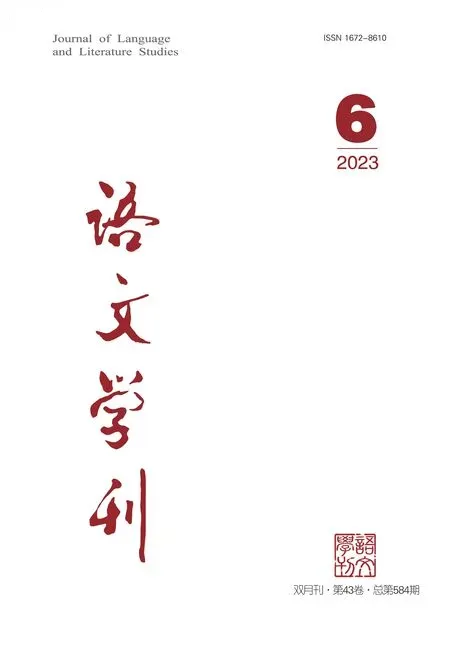《文心雕龙》的光明美学
——以“炜晔”为例看刘勰的美学思想
胡菀麟 张缤月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魏晋时期,文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学界向来将魏晋视作“文学自觉”的关键时期。而随着文体意识、文风意识的逐渐发展,争论异见也开始出现。例如陆机曾在《文赋》中言“说炜晔而谲诳”,意指“说”文体的言辞光彩华美,文风诡诈不实[1]99-120。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花费大量笔墨强调“说”文体的根本在于忠诚信实。他在引用陆机原句后,以“何哉”疑问作结,表达其对陆机理论的反驳态度。
近二十年来,关注陆机、刘勰这一分歧的学者不乏其人,但均以“说”文体作为分析的切入点。目前学界大致形成以下两种观点:其一,陆机对“说”认识深刻,刘勰误解了陆机。如李壮鹰先生认为:“刘勰把‘说’体换成谏议行为,把‘谲诳’讲成诡诈欺诳,当然就是完全错误的了。”[2]他将陆、刘二人分歧的原因归结于刘勰排斥小说,而陆机观念更开放、相对更重视作品小说性上。其二,陆机说法欠妥,刘勰对“说”的认识更胜一筹。如宋永祥提出:“刘勰对陆机‘炜晔而谲诳’的论断用来论‘说’接受了一半;不仅如此,还将之稍加改造用以论‘檄文’,从这些都可以看到他对陆机文论的继承和发展。”[3]诚然,在文学领域,对先出者和后进者不应作简单的优劣区分,但比较二者亦有助于发掘其间的继承、演变关系,探讨背后的成因,进而获得文学理论线性脉络的发展视野。
从陆机《文赋》可以看出,每组骈文短句里的前一词组主要用于形容文体表面的形式特色,而后一词组则形容文体内含的风格特点。如“铭博约而温润”,即“铭”体的形式“博约”,整体呈现“温润”感;“箴”体形式为“顿挫”,整体表现为“清壮”感。故而“说”体的形式是辞采“炜晔”,呈现“谲诳”感。从《文心雕龙》的表述来看,将“炜晔”“谲诳”形容词匹配“说”体,是刘勰对陆机论“说”最无法接受的一点,也就是二者的关键分歧点。在刘勰看来,“说”体在先秦时期可称“忠贞”之文,但进入战国之后开始逐渐走向“谲”“诳”等偏离正道的歧路,在立意层面带上了邪放意味,而“炜晔”却是光明且是“忠贞”之文才堪使用的。忠贞之臣,面对君主自当忠信,故不当“谲诳”;部分“顺风以托势”的臣子其心不正,故不称其文辞“炜晔”。故而刘勰认为对“说”体不能一概而论,唯有忠贞的“说”才可称为“炜晔”。对于观念变化的原因,与其说是陆机、刘勰二人思想的差异,毋宁说根源在于时代变迁、文化积淀背景下词汇发生了流变。
一、词汇:原始与流变
正如宗白华先生认为魏晋诗歌中“俯仰”一词蕴含了时人富有玄学的人生美学态度[4]124、钱锺书先生认为刘勰把“圆”看作艺术成熟的表现[5]277-290一般,从“炜晔”一词在不同文体的形容使用可以看出:一些词语经过长期的文化沉淀,在文学理论中被反复运用后,已逐渐脱离了其简单的字面原意,转而带上了时代色彩及创作者的个人倾向。因此,对于“炜晔”这类形容光明的形容词,就不应将眼光仅仅局限在《文心雕龙》的某一句话、某一篇章或是某一文体上,而是需对全书进行统计分析,再结合时代背景、社会文化加以观照,方可对刘勰潜意识里的文学审美思想达到整体、全面的把握。
首先应厘清“炜晔”一词的含义。关于“炜”,先秦时《诗经》有云:“彤管有炜,说怿女美。”[6]63在《说文解字》中,“炜”的解释是:“盛赤也。从火韦声。《诗》曰:‘彤管有炜。’于鬼切”,随后的一条注写道:“王莽传:青炜登平,赤炜颂平,白炜象平,玄炜和平。……如淳曰:青炜,青气之光辉也。”[7]485《文选》注曰:“方言曰:‘炜,盛也’”[8]352。从造字结构来看,“炜”以火为偏旁,取火光、光明之意,后逐渐由赤色泛化指代光的某种颜色。“晔”,亦是“光也”。郭璞曰:“‘炜晔’,盛貌也。”[8]可以看出,先秦文献已开始运用“炜”“晔”来形容火、光及颜色,但此时多以单字使用,尚未出现如“炜晔”一般的复合词。魏晋之后,各类文献中开始大量出现如“炜晔”“炳耀”等复合形容词。这些词的组合更给人以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之感,众多文人开始将这类词用于评判文风、文辞。如曹植评价吴质的书信是“晔若春荣,浏若清风”[9]429,提出赋应当“汜乎洋洋,光乎浩浩”,又如陈琳在《答东阿王笺》里赞叹曹植文章“清辞妙句,焱绝焕炳”[8]855等。这一现象除了体现汉字自身延续的发展脉络之外,还可看出时人对文字词采的自觉追求。对于陆机开宋齐一代文风,有意追求新的文字技巧这一点,学界已然公认。钟嵘曾评价陆机诗歌的风格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10]36这样的文学批评现象在魏晋时期密集出现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与当时蜡烛制作技术提高和佛教经文大量输入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一)光明的诞生:制蜡技术获得突破
南北朝时期,蜡烛的生产技术取得突破,照明条件得以极大改善。从出土的实物结合文字资料来看,秦汉灯具多以动物脂肪作为原料。此种油脂含饱和脂肪酸,常温下是固态便于制作形状[11]。《楚辞》里有云“兰膏明烛,华镫错些”[12]230,《潜夫论》里也有说到“知脂蜡之可明镫也”[13]104。但在当时,动物油脂可获取的数量十分有限。到了东汉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烛台,说明当时蜡的形状开始初具现代蜡烛雏形。此时的蜡烛制作已可以减少对动物油脂的依赖,转而从植物中进行提炼。目前能见到的关于蜡烛最早的文字记载是西晋作家范坚写下的《蜡灯赋》,文中对光明的描绘如“赫如烛龙吐辉,烂若翳阳复旭”[14]878,可见晋代蜡烛的制作工艺已较为成熟。对于黑暗的突破,是人类走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然条件限制的重要一步。以蜡为灯,比起燃烧动物油脂来说,火焰更为明亮、干净,且气味更小。由此观之,正是因为材料、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活物质的丰富,进而带来了诗歌意象的创新。烛、灯、蜡等光明意象频见于文人们笔下的诗篇,对光明的向往及歌颂也丰盈了文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南北朝时期才会出现大量咏蜡、咏灯的文学作品。如庾信《灯赋》、萧纲《列灯赋》、江淹《灯赋》等,《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石崇对蜡烛进行的炫耀性消费。不仅如此,在诸多宫体诗中,“蜡烛”意象还为诗歌增添了光照、时间、视觉、影子和燃烧等多重意蕴。田晓菲曾指出,佛教教义中的“蜡烛”具备更深层次的内涵:象征着君王普照百姓、觉悟般若智慧、冥想、虚幻和杀身成仁等含义[15]。对于时人来说,制蜡技术的突破,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更长时效的光明,哪怕这样的光明是有条件的、小范围的。但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却带来文学意象、创作手法和精神心态的多方面推进。
(二)光明的传播:佛教教义赋予特殊内涵
在南北朝的社会背景中,时人对光明的热爱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不容忽视,即佛教的东传。虽然学界内不乏学者注意到《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但关于佛教教义对刘勰审美观念的影响方面的探讨还稍显不足。对此,普慧曾指出:“《文心雕龙》的诸多审美范畴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这些术语,或直接从佛教哲学中引入……或根据佛教原意又加以创造组合,形成既有佛教哲学基础又有文学审美功能的双重范畴。”[16]虽《文心雕龙》对佛教词语的直接使用较少,但作为著述人的刘勰长期浸淫在佛教语义的语境里,其文学审美观念很难说没有受到影响。如果从刘勰的审美思想与佛教关系来看,《文心雕龙》别具一格的语言创新便多了一条解释的路径。
在刘勰生活的时期,《法华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一大批大乘佛教经文陆续传入中国,由于当时王室贵族普遍信奉推崇,佛教经文得以快速普及开来。其时佛经翻译大为盛行,生活在寺庙里的刘勰穷其一生都在参与佛经的汉译工作。在诸多经文里,常常能见到“金色”“光明”“照”“炜烨”“焕烂”等词,这些词均是用于描绘绚烂明亮的西天世界。在佛教教义中,“光”因能普照万物,譬喻为应身、般若德等义,“明”则因能普遍受益,譬喻为化身、解脱德等义。又如《华严经》所言,智慧即“光”,力无畏即“明”,“‘光明’比喻法身所起的不可思议力用,具有无量威德,能够催伏一切烦恼怨敌,并由此得到诸天拥护”[17]。由以上种种可知,佛家对“光明”的景象寓以了高深且积极的内涵,经文中诸佛、菩萨多从金色光芒中现身,如“尔时信相菩萨即于其夜梦见金鼓,其状殊大,其明普照,喻如日光”“于诸佛上虚空之中亦成香盖,金光普照,亦复如是”“如来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光明炽盛,无量无边”,等等。“放大光明”即普照一切无边世界,因而经文对于描绘色彩明亮绚丽的形容词有所偏爱。在众多佛经中,《金光明经》对于“光明”的描述最为普遍,且因其对国家社会治理及人民安乐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显示出“内圣外王”思想而迅速被统治者尊崇。经文中所言之金鼓有“其状殊大,其明普照,喻如日光”的效果,是以能喻法身法性,般若妙智。在《忏悔品》里,只要遵循忏悔法,即可“是金光明,清净微妙,速能破除,一切业障”。可见在教义中,只要诚心悔过,佛法之光便可以消除诸恶,来世便可得证无上道。据此,光明在佛教中甚至可以与纯净、圣洁相联系。刘勰逢此盛时,又有着与沙门、王室相交甚深的特殊经历,凭借其对佛典经文的熟悉程度,很难说其崇尚光明、光辉的审美思想与佛教毫不相关。
从社会背景角度来看,蜡烛制作技术的提高及佛教传入使得时人热烈地渴望并追寻光明。社会生活的需要丰富了语言的使用,形容光亮的词汇逐渐增加。文人们自发歌颂光明,又在理论阐述时将该类形容词运用于对文辞的描述。如此才有了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里众多炫目的光亮形容词,这些词与长期积累形成的写作技巧相结合,使文章进一步呈现出了灿烂的美感。
二、运用:改造与体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著作中,《文心雕龙》尤为光彩夺目。
就全书而言,描述光采明耀常使用的词有:炳耀、炜晔、炜炜、炜烨、光耀等,其中尤以重复使用的“炜晔”值得注意,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该词在魏晋文论中出现的频次较高;二是该词常用来描述文章特指的性质。即凡是用到这个词的地方,一定是在其文中心立意伟正的前提下。因“炜晔”所具备的光亮透彻之感,所以会衍生出“明显”“明白”的含义,如《六臣注文选》注“说炜晔而谲诳”时就说道“炜晔,明晓也”[8],唐代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谲诳。”[8]在文学理论的阐述中,“炜晔”多用来形容文辞如光一般绚烂华丽的盛貌。综合各方的解释来看,至迟在南北朝时期,“炜晔”一词已有两种含义,即明晓与言辞华美。
目前学界对陆机《文赋》中的“炜晔”取“明晓”之意的观点已基本达成了共识。陆机以“炜晔”来作为对“说”文体中言辞效果的评价,诚不为过。因为毕竟“说”是讲求实用性的文体,它只有说服听者才能实现自身的目的、价值,因此需要借助一定的修辞技巧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更清楚地表达说者的意图,这对“说”文体而言无可厚非。但若简而化之,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炜晔”均为“明晓”之义则不然。就《文心雕龙》中所出现的“炜晔”而言,次数实远多于《文赋》。下面将《文心雕龙》涉及“炜晔”一词的篇目进行具体抄录:
《论说》:“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狂’①,何哉?”
《檄移》:“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之也。”
《体性》:“若总其归塗,则数穷八体:……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
《夸饰》:“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辞入炜晔,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
《隐秀》:“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①;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
《时序》:“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暐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在使用过程中,“暐”与“炜”、“晔”与“烨”用语存在含混使用的特点,但具体含义大致相同。《文心雕龙》里“炜晔”一类词共出现于六章篇目中,分别是上部的《论说》《檄移》和下部的《体性》《夸饰》《隐秀》《时序》。
在《论说》篇中,刘勰先辨明“论”体,后探讨“说”体。在这一篇里,文体的“正体”观为一篇之骨。对“论”体进行表述时,其举例说明如庄周、《吕氏春秋》、《白虎通》等先秦著作“述圣通经”,堪称“论家之正体也”;而后直言“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是可以辨明是非的。对于反面范例的“曲论”,则认为虽然巧妙,却是一种“妄”,非“能通天下之志”的君子所为。可见刘勰对于文体立意出发点的是非曲直十分介意。对于“说”体,近代王闿运在《湘绮楼说诗》中,率先关注到陆机和刘勰二者之间的分歧。他在重点比较陆机和刘勰的观点后,认为刘勰错判了陆机的文体观念:“‘说’当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谲诳之使反于正,非尚诈也。”[1]118随后,许文雨较为客观地指出:“‘炜晔’之说,即刘勰‘言资悦怿’之谓,兼远符于时利义贞之义。而‘谲诳’之说,刘勰独持忠信以肝胆献主之义,反驳陆说,不知陆氏乃述战国纵横家游说之旨也。”[18]39范文澜先生在注《文心雕龙》时认可许文雨的观点,认为陆机的“炜晔”即是刘勰所说的“言资悦怿”,陆、刘二者最大的分歧在于刘勰认为“说”应“以忠信为本”,而陆机对“说”的政教观念痕迹较不明显[19]357。祖保泉先生则认为二人所说对象不同,因为:“就战国策士说辞言,陆氏之言有据;就‘说’这一文体说,陆氏之说有片面性,故刘勰不以为然。”[20]詹锳先生总结道:“陆机和刘勰论‘说’体的时候,都是就游说来立论的,只是游说的态度不同。陆机强调‘谲诳’的一面,刘勰强调‘忠信’‘肝胆’的一面,因此对于游说文字的风格要求也不完全一致。”[21]百年来,众位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可以明确的是,要探析刘勰心中的“炜晔”,首先离不开对“说”文体的讨论。在《文心雕龙·论说》里,刘勰首先对“说”体进行解字分析:“说者,悦也”,而后说明“说”体依靠口舌使人喜悦的本质,进而论述了“正体”的反面——“伪”,认为如果使人“过悦”则是“谗说”。如伊尹、姜太公、烛之武和子贡的例子,即是“说之善者”。而后“战国争雄”时期,特点是“辨士云踊”;到了“汉定秦楚”时期,特点是“辨士弭节”。“说”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使用者辨士之中也出现了部分“顺风以托势”的群体。刘勰顺着时间脉络对“说”体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和对比,褒贬之意虽未点明,但藏在言语间的是对战国后期辨士的道德审判。他突出了古人之正,暗责今人缺少风骨、见风使舵,这样的观点与其“师圣”观一脉相承。在层层铺垫后,刘勰方娓娓指出古今辨士的区别,即使用“说”体时应具备“唯忠与信”的行文立意。作为面向主君使用的文体,“自非谲敌”,因此应当正直忠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才是“说之本也”。可见在这《论说》篇中,刘勰的“正体”观一直贯穿其中。此即清代纪昀评价刘勰论“说”显得“树义甚伟”的由来[22]77。如果做不到正直忠诚、诚信敦实,那么这样的“说”就是无本之说,是上文“正体”的反面——伪说、谗说。要形容这样的伪说、谗说的言辞能焕发出“炜晔”光芒,是刘勰断断不能接受的。故而在论述“此说之本也”后,刘勰才会以“而陆氏直称‘说炜晔而谲诳’,何哉”进行反问收束,显示不能将“说”体笼统概之的个人主张,带上了文体细分之下的新时代特点。刘勰所言的“炜晔”与陆机所言明白晓畅之“炜晔”不同,他为这个词被赋予了一个“忠信”的前提条件。
在《檄移》篇中,虽未引用陆机原句,却同样使用了“炜晔”一词,这就值得格外注意。在《檄移》的开篇刘勰先对“檄”下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作为一种面向全天下讨伐敌人的宣言,不像“说”体一样有立意上的正或邪之分,只有写得好或差之别。接着他列举史上檄文的经典范例并从中总结出优秀檄文所具备的特点,即檄文务必要“刚健”,要“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优秀檄文的整体文风应当是如光一般清楚明白的。在檄文写作的修辞方面,刘勰并不拘于保守的道德观,而是主张以达成目的为导向,只要写作目的是正义的,可以灵活运用夸饰之类的诡异手法。此时“实参兵诈”,用文如用兵,面对敌人时怎样夸张渲染也不为过,为了“驰旨”可以“谲诡”。此即周振甫先生所言:“刘勰认为谲诳是有条件的,即可以谲敌。”[23]209檄文作为己方出师之誓,必然要昭告王师的正义性。因而对于檄文里的文辞,应如光一般明亮、摄人心目,且透彻简洁,才能达到下文所言“不可使辞缓”“不可使义隐”的标准。为了让自己的文辞显得更有气势和说服力,文辞就应该“炜晔”。可见与陆机相比,刘勰将描述“说”文体的词移用于“檄”,这样的标准是首先建立在说文、檄文面向的对象不同、写作的动机立意不同之上的。“炜晔”“谲诡”二词,“说”体不可用而“檄”体可用,显示出在刘勰的行文意识中,只要是写作的本心光明,那么华丽明白的文辞也附带正向积极的一面,可称“炜晔”。从《文心雕龙》里刘勰对“说”和“檄”的结论来看,其透露出潜在的一层含义即刘勰认为写作目的决定了文辞美感的性质。只有合乎“忠义”观念写作出发点写出的文章,才可用“炜晔”形容。此即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所言:“彦和谓‘言资悦怿’,正即‘炜晔’之义。惟当以忠信为本,不可流于谲诳。”[5]357
在《体性》篇中,刘勰将文辞风格分为八体四组,其中“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意指繁富风格的形成是由于广博的比喻成就了文采,从而分枝别派也拥有了光芒。在此可以看到刘勰对于繁缛文风并不排斥。博喻常常是骚赋、佛经采用的手法,是才气的体现。而将文体结构比作富有生机的树木枝干在《文心雕龙》中非独此例。
《夸饰》篇直言“炜晔”的主体是“辞”,就是指辞藻、文辞,如此则应取“华丽”之意。又与下半句的“萎绝”相对,那么即是指辞藻华丽的盛貌。此时刘勰亦将炜晔与花草联想于一处,或绽放艳丽色彩如春藻,或凋零枯死于寒谷,描绘出一幅幅鲜明对比的植物图画。
《隐秀》篇中,“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该句出现于篇末,概非后补。从这句来看,要在说明文中的警句与整篇文章的配合关系。那些运用得自然的例子,如同为树木添上盛放缤纷的花卉,如为丝帛添上鲜艳斑斓的色彩。此处,英华、曜、照、鲜及炜烨等词频繁出现,给人光彩夺目之感。且此处仍然将“炜烨”光芒与花草树木等富有生命力的植物相联系,将文章视作具有蓬勃生命的所在。
同样需要瞩目的是《时序》篇。刘勰对楚骚的感情较为复杂,这一点从《辨骚》的位置和篇中文辞可以看出。在谈及骚体时,刘勰评价道:“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用“艳说”形容其语言特色,同时肯定赋对“雅颂”的继承发展,认可其出新意是来自于纵横派的诡异俗术。从这样矛盾的情感色彩来看,刘勰对骚体褒大于贬。刘勰对赋的这一句评价,体现出他对赋体注重辞采表现手法的肯定,“是文学自觉之后追求抒情与辞采之美的一种表现”“刘勰对情之深挚与辞之奇伟是不反对的”[24]328。骚体赋的华丽、铺张,是语言的极致描写之美。刘勰用光彩明亮之“炜晔”形容其“奇”,是对骚体赋文体情感的肯定。而这一肯定的前提,是楚辞“取熔经意”,其出发点仍是以经为主,立意仍是高深的,只是“自铸伟词”,这样的词才可以说是“炜晔”“奇文郁起”。因此在《辨骚》中,刘勰评价《招魂》和《大招》时,用到“耀艳而深华”来进行描述。骚体的立意和中心思想可称崇高,骨气也较正直,便可以说其树立了文变的正面范例。关于类似立意、文骨的观点,刘勰在《风骨》篇中已表述得淋漓殆尽。
从以上具体篇章中“炜晔”的使用情况来看,刘勰的正、邪观念区分非常清晰,对于文体写作的立意十分注重。这样的“正体”观影响到其在描述不同文体时,对形容词的选择。此外,在说明文辞的使用时,刘勰常常借树、花等具体形象加上明媚敞亮的词,营造出一个具有光明美和生命动态美的情境,读来似有立体的鲜活生命跃然纸上。这是刘勰为《文心雕龙》精心打造的独特的语言美。
三、意蕴:生命与光明
人类对于光的追逐和思考由来已久。在西方,有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理想国》里以太阳作为善良的喻体。在中国,则有夸父追日为代表的神话故事和众多文字记述。如:《周易》中的《乾卦》正义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25]118《贲卦》疏云:“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内含文明”[25]207-208。可知古今中外各类文明对于光明都有着自觉的美的体验。而我国自先秦时期就已将“文”与“明”相联系,出现以火、以光喻文、喻人的文学现象。正如刘纲纪教授所言:“从中国美学的典籍来看,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日月之光与人类生活与美的关系,并把美和光明联系起来……《周易》一书一再使用‘文明’一词,‘文’既指卦象,又有美的意思,因此将‘文’与‘明’相连也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即美是与明亮的光相连的。”[26]282这一传统自远古发端,经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演变,至明代阳明心学提倡的“我心光明,亦复何言”思想亦可见回音。
刘勰敏锐的写作艺术感为《文心雕龙》增添了“生命美”。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作品中,光明意象的塑造都有助于构建空间结构的整体美,体现生命勃发的律动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生命蓬勃为底蕴,将儒、佛、道的思想带入了朴素的自然美学观念中。但其思想近乎驳杂、语言又因骈文束缚显得互训模糊,对辨析其美学思想增加了难度。
明清之后,《文心雕龙》渐成显学,各路批评家开始着眼于《文心雕龙》与佛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词汇和体例方面:朱东润先生认为“勰究心佛典,故长于持论”,他举例说明了刘勰援用的部分佛经字词[27]46;饶宗颐先生、兴膳宏先生从音韵角度进行切入;范文澜先生通过严密的论证进一步指出《文心雕龙》的体例是受到《阿毗昙心序》的启发。在思想层面:刘永济先生认为“彦和此书,思绪周密,条理井然,无畸重畸轻之失。其思想方法得力于佛典为多”[28]2。而当下学界更普遍倾向于圆通对待以上问题,不必拘泥于具体的一部佛藏经典或个别字词之中,如王元化先生和陶礼天教授就提到容易犯下的“语言类比法”弊病;袁济喜教授曾指出:“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主要在于精神蕴涵方面。它从大文化与人生意义层面,对于传统的儒道学说作了深化。进而渗透到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29]因而在讨论《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时,不应将个别字词与佛教用语进行简单联系,而是“应该考虑到佛学思想在这些‘语词’原有意义上的新的积淀性,由此来联系《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以及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来考察《文心雕龙》与佛学之关系,庶几可信”[30]。譬如“‘圆照’一词,本是一个佛教术语,通过与魏晋玄学的互渗和社会生活的交融,经过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逐渐从宗教领域向诗学概念转化”[31]。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将“圆照”“炜”“晔”这一类的词作为对子女的命名,体现出佛教的快速民间接受过程,反映了佛教术语日常生活化的特点。而后,这些术语经过日常生活的口语运用,开始逐渐普及开来。从而在南北朝时期能够“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开始它向诗学概念转化的过程”。诸如“炜晔”这样的词汇同理。经由单字形容词变复合形容词、日常生活向诗学概念发展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中才酝酿出了特别的光明美学意蕴。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选序》里就说道:“若夫天文以烂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贵……七穷炜烨之说,表极远大之才,皆喻不备体,词不掩义,因宜适变,曲尽文情。”[32]432在作家的笔下,文字似乎也有了生命,为文章增添了几分蓬勃的力量。在《文心雕龙》里,刘勰的生命观念屡见不鲜:“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等。其实古文论中的象喻传统并不鲜见,如选取自然界花草树木喻文,或以人体的器官运行喻文等。钱锺书先生就提出过“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的观点。但以“炜晔”来形容文辞这般,以光喻文则是魏晋后才开始频繁出现的。《文心雕龙》里,“炜晔”与“华”既同且异,都是指代文辞之美,但刘勰反对“华”,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美,从而强调要有风骨、兴寄。要如《周易》所言,唯“刚健”才能焕发出“辉光日新”。与“艳”相比,刘勰不反对“艳”,但“反对忽视内容而片面追求华艳”[33]。因而相较于“华”“艳”,唯有指代光明的“炜晔”更能说清刘勰的用词标准。
刘勰敏锐的写作艺术感为《文心雕龙》增添了“视觉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颜色词的运用不仅是眼部获得视觉上的效果,还有脑部获得的生理反应。优美明亮的色彩,有助于人体分泌有益于健康的生理活动物质,使人保持充满朝气的蓬勃的状态。阅读过程既然是一种眼部和脑部运动的结合过程,那么读者在阅读《文心雕龙》时,通过思考可以有效打通视觉和想象的边界。而光明、灿烂等词汇常常与活泼、希望的深层蕴意相关联,当读者阅读到文中描述明亮色彩的词语时,其脑海中会自动构建出一个光亮的氛围,从而获得愉悦的感觉。《文心雕龙》阅读的美感正是于此细微处向外焕发。黑格尔曾说:“颜色感是艺术家所特有的一种品质,是他们特有的掌握色调和就色调构思的一种能力,所以也是再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基本因素。”[34]281从熟练打通五感的写作技巧来看,刘勰不啻为一位优秀的文学创作者。
四、结 语
词汇使用差异的背后,是陆、刘二人未及言明的文学思想差异,而这一深层次的美学思想可以从光明的形容词汇“炜晔”看出。因此,在对《文心雕龙》修辞技巧的讨论中,除了对偶、声律、比兴、夸饰之外,还应有感情色彩方面。在运用字词时,刘勰心中的自然文学观使他认可手法的运用,而另一方面,宗经征圣的儒家文学观又使他认为这类手法的运用应当有节且应遵循经典范例。正如张少康先生所言,在刘勰的基本美学观点中,“自然是第一位的,法度是第二位的。然而刘勰又认为要达到自然之美的高度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要以各种法度、规矩作为桥梁”[35]297-298。从《文心雕龙》涉及“炜晔”一词的具体篇章看,刘勰的道统观为文辞加了一层前提,即只有在“道”的框架立意之下,文辞才能焕发出生机,才能称作运用得当。由此刘勰才会对“炜晔”的使用限定了具体条件,进而呈现出与陆机在“说”文体上的差别。这诚然是思想内容作用于艺术形式选取的一个细微体现。
魏晋之后,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开始大量出现如刘勰这样以光喻文的批评现象,这是一种带有视觉和生命审美的文学批评,从中可以透视出人类对光明的向往是根源于远古时期的审美观念,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触及了文学的审美本质,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注释】
①清乾隆五十六年金谿王氏刻增订汉魏丛书本作“炜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