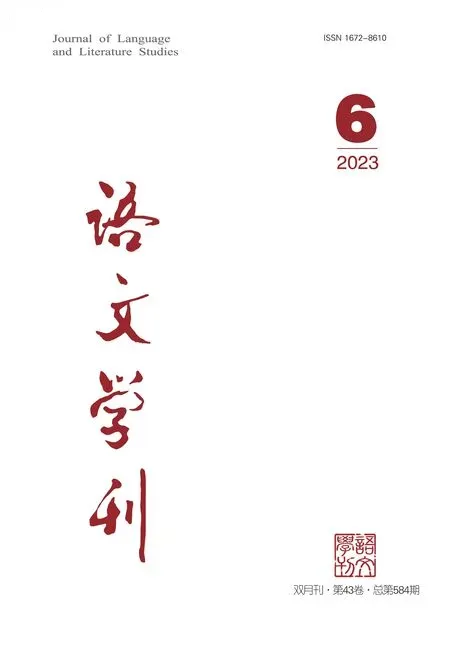英语世界《文选》译介与研究
戴文静 袁吉利
(江苏大学,江苏 镇江 212013)
《文选》由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该书本身的价值以及封建时代科举制度使得《文选》一直是一门显学[1]。自1918年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首次翻译《文选》中的作品以来,《文选》引起了英语世界学者的关注,译介对象也从《文选》中的作品逐渐转移到《文选序》。国内学界目前对英语世界《文选》译介与研究的关注不多,虽有一些学者作出了一定的探索,但多数研究只对《文选》中的辞赋进行了译介梳理,译本分析多局限于单个译者的单篇作品,且分析不够透彻。鉴于此,本文对英语世界《文选》译介与研究进行了深入探究,历时考察译介情况,分类梳理研究成果,以期对国内《文选》英译研究有所裨益。
一、英语世界《文选》的译介概况
《文选》体量庞大,共700余篇作品,单篇作品的译本数量众多且无法确认译自《文选》,因此本文仅选取英语世界具有代表性的10位译者的11个节译本进行考察,其中包含所有《文选序》译本,如下表所示。

表1 《文选》英译概况
如表所示,《文选》的英译者主要为中国、美国、英国和美籍华裔学者,其中美国汉学家占比最大。阿瑟·韦利是唯一的英国译者,而中国香港学者黄兆杰(Siu-kit Wong)是唯一的中国译者。美国译者中有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华兹生(Burton Watson)、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马瑞志(Richard B.Mather)这批专业汉学家,也有高校学生如戈登(Erwin E.Gordon)和魏彼德(Peter B.Way)。此外还有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James J.Y.Liu)和蔡宗齐(Zong-qi Cai)。
在选取的11个译本中,除康达维完整翻译了《文选序》和所有赋外,6位译者翻译了《文选序》,阿瑟·韦利翻译了部分诗赋,华兹生翻译了部分赋,马瑞志翻译了部分诗。《文选》本身庞大的体量、复杂的文体分类、校勘训诂等问题都为英译《文选》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也是目前英语世界暂无《文选》全译本的主要原因。
总体而观,《文选》的译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20世纪初:萌芽期
20世纪英语世界最先关注《文选》的是阿瑟·韦利。当时英国的汉学研究其实处于疲软的局面,落后于美国、日本的汉学研究,韦利在大英博物馆当助手时偶然了解到《文选》。虽然韦利没有从《文选》本身来研究这本选集,但他早期翻译的作品多半是选自《文选》[2]1179。《汉诗一百七十首》[3]于1918年出版,该书包括宋玉《风赋》和《登徒子好色赋》前半部分的英译。韦利在书中翻译了一些诗,例如《古诗十九首》、李陵《与苏武诗》和左思《咏史》等。1923年,他的另一部翻译合集《白居易〈游悟真寺〉及其他诗篇》[4]出版,书中包括了《文选》收录的三篇赋。不过,韦利却对《文选》的文学价值和选录标准持否定态度。他在该书的附录中提到,《文选》中收录了太多平庸作家的作品,并赞同苏轼对《文选》的负面评价[4]147。韦利的译本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译本,当时赋即为诗的观点在西方汉学界盛行,因此他是将赋看作诗来翻译的,这种翻译风格还对当时的英国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康达维认为韦利的译本虽然可读性较高,但并不符合训诂学的要求,而且也缺乏详细的注解[2]1179。作为英语世界首个《文选》节译本,韦利的译本无疑对《文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20世纪50年代:过渡期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西方虽然出现过《文选》所录部分作品的法译、德译和英译,但是法语和德语汉学界关注的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文选》,而英语汉学界则开始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中国文学理论本身[5]。然而,当时有关中国文论的英译本或研究比较匮乏,现存中文资料也不具系统性。于是,英语世界《文选》译介对象逐渐从《文选》中的作品转向了《文选序》。
1950年,英语世界第一个《文选序》节译本应运而生。加利福尼亚大学戈登在其硕士论文《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些早期观念》[6]中对早期的部分中国文论进行了介绍和阐释,其中第四章《萧统与其〈文选〉》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萧统生平;第二部分是《文选》的编撰背景和时代意义;第三部分是《文选序》的节译和阐释。戈登译出了《文选序》的大致内容,并简略论述了《文选》的文体分类方式。虽然戈登的译本是英语世界《文选序》的首个译本,但是受限于硕士论文的形式和研究内容的深度,并未产生很大影响。
随后,英语世界出现了《文选序》的首个全译本。1957年哈佛大学的海陶玮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文选〉与文体理论》一文[7]。该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发展;第二部分是《文选序》的英译;第三部分详细阐释了《文选序》中的文体分类问题。海陶玮的译本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注解,并借助清晰的图示对《文选序》中的文体问题作了细致地讨论。该论文得到了美国汉学界的认可,被收入1965年毕雪甫(John L.Bishop)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StudiesinChineseLiterature)之中。1994年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ColumbiaAnthology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又收录该论文,列于“批评与理论”部分。康达维曾极力称赞海陶玮的译本,他指出该译本“提供了以训诂学为基础的详细注解”,并“为中国文学的翻译树立了一个典范”[2]1181。
(三)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探索期
美国汉学家华兹生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专业研究者,他在研究《史记》的过程中了解到《文选》中的辞赋并进行了翻译。1971年,华兹生在《汉魏六朝赋英译选》[8]一书中翻译了《文选》收录的宋玉《风赋》等十二篇赋,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华兹生与韦利一样,他们的翻译都是旨在把中国文学文化介绍给西方普通读者,但华兹生将辞赋作为单独的文体来翻译[9]。除华兹生的辞赋翻译外,该时期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大多为《文选序》的翻译,还有目前翻译完成度最高的康达维译本。
自20世纪70年代起,英语世界中国文论翻译和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比较文学的发展[5]6。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就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翻译并研究《文选》。1975年刘若愚出版了《中国文学理论》[10],其中《文选序》节译被安排在第二章《形上理论》。刘若愚认为萧统在《文选序》中运用了形上的概念来证明文学的重要性[10]。该译本不仅包括《文选序》开头部分的节译,还有对萧统的文学理念的简要阐释。该书虽然在学界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但是其中有关《文选序》的论述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香港学者黄兆杰也发现英语世界现存有关中国文论的资料匮乏且零散。因此,他从1976年开始编译《早期中国文学批评》[11]一书,并于1983年出版。《文选序》的翻译在第十三节,黄兆杰在文内和文后都提供了丰富的注解,并附一篇介绍。在介绍中他提到,自己重译的《文选序》旨在向英文读者介绍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杰出的文本。他认为自己的译本与海陶玮的不同之处在于自己更重视萧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作用而不是其对文体的认识[12]。
直到70年代末,英语世界仍未出现《文选》的全译本,之前的节译本也缺乏相关注释。美国汉学家康达维一直致力于中国辞赋文学研究,他发现英语世界《文选》翻译与研究的资料匮乏,遂投身于《文选》译介[13]。他从1981年开始完成了《文选》前十九卷《文选序》和所有辞赋的翻译,并计划以八册翻译完《文选》。前三册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别是出版于1982年的《昭明文选(第一册:城邑之赋)》、出版于1987年的《昭明文选(第二册:祭祀、畋猎、纪行、宫殿和江海之赋)》和出版于1996年的《昭明文选(第三册:自然风物、鸟兽、情感、悲哀、文学、音乐和激情之赋)》[13]。该译本包含了丰富的注解,篇幅甚至远远超过译文本身,这与康达维专业六朝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和高深的学术造诣有关。康达维的译本相继出版后,受到欧美汉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书评涌现。这三册书在JSTOR数据库中存在16个书评,这些书评都充分肯定了康达维译本对英语世界《文选》研究的巨大贡献,但也指出了译本在注解、参考文献以及书籍装订等方面仍有值得商榷和改定的地方。总体而言,康达维译本不仅是辞赋文学研究最权威的参考资料,而且为英语世界《文选》的译介与研究带来了突破性的发展。
(四)20 世纪90年代至今: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至今康达维译本一直是辞赋文学研究最全面、最权威的参考资料,英语世界《文选》辞赋翻译也逐渐走向成熟。除辞赋翻译外,该时期还产生了三个较有代表性的译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魏彼德和美籍华裔学者蔡宗齐的《文选序》译本以及美国汉学家马瑞志的诗歌译本。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康达维可能无法如愿翻译完《文选》,英语世界何时能出现《文选》全译本不可预知,但《文选》译介并未停滞,而是处于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
1990年,魏彼德完成了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14]。其中《文选序》的翻译在其博论的第四章《〈文心雕龙〉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题为《萧统及〈文选〉》。该译本从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以萧统为中心的文人学术圈出发,阐释并评述了萧统的文学思想。然而,作为博论中顺带提及的小节,受限于篇幅以及深度,该译本并未有太多突破。
马瑞志的翻译合集《三位永明诗人》[15]于2003年出版,其中包括了《文选》中沈约、谢眺和王融的全部诗歌。该译本以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善注《文选》为底本,并将康达维译本和《六臣注文选》作为参考,还包括了丰富的译注,涉及历史、文学、地理和植物学等方面的知识。香港大学的魏宁(Nicholas Williams)认为该译本翻译精确得当,文风亲切易懂,短时间内无法被替代[16]31。
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在我国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手术切除是治愈肺癌的主要方法,但大多患者在肺癌确诊时早已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时机[11]。特别是当前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目标是缓解临床症状,提高生存率及延长生存时间[12]。
2005年,蔡宗齐翻译的《文选序》收录在梅维恒等人编的《夏威夷中国古代文化读本》[17]中《纯文学地位的提高》一节。这一节不仅包含萧统、其弟萧纲和萧绎的生平介绍和文学思想,还有萧纲和萧绎作品节译。该译本从萧统的家族关系以及其兄弟的文学思想出发来探究《文选序》中蕴含的文学思想,为英语世界《文选》翻译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除此之外,这本书旨在作为大学教材供相关专业学生使用,蔡宗齐翻译的《文选序》被列在“文学”一栏,其中还包括《诗大序》《随园诗话》以及《典论·论文》等经典文论的英译。蔡宗齐译本作为中国文论代表作品进入英语世界的大学教材选本,也可见《文选》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正逐步提升。
二、英语世界“选学”研究
目前,国内“选学”研究已日趋成熟,实现了从传统“选学”到新“选学”的过渡,成就斐然。而英语世界“选学”研究仍在发展阶段,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不如国内,其因有二:其一,研究《文选》需深入了解其编著背景,即梁朝的政治和文化;其二,《文选》选录作品跨时代和文体,从先秦到梁朝,从辞赋到碑铭,范围超越西方学科的边界[17]30。总体而观,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翻译与阐释、文体分类、与《文心雕龙》关系、编撰和选录标准等问题,有的学者针对单个问题研究,也有学者论及多个问题的交叉研究,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作品的翻译与阐释
华兹生在《汉魏六朝赋英译选》一书中除了翻译了《文选》中的十二篇赋,还在引言部分详细介绍了赋的发展并提出自己对赋体的理解[8]111-222。美国汉学家柏士隐(Alan J.Berkowitz)在《西晋招隐诗考》[18]一文中翻译了《文选》中收录的三首招隐诗,即左思《招隐(其一)》和《招隐(其二)》以及陆机《招隐诗》。柏士隐认为西晋的招隐诗所描述的并不是真实的隐士生活,而是宫廷生活。柏士隐还发表《〈文选〉的最后一篇:王僧达〈祭颜光禄文〉》[19]一文。他不仅在文中提供了《祭颜光禄文》的完整英译,而且通过介绍这篇祭文,详细讨论了祭文这种文体,以及祭文在中国中古时代的意义。美国汉学家高德耀(Robert J.Cutter)在《告别:中国中古早期的诔体转型》[20]中翻译了曹丕的《与吴质书》和曹植的《王仲宣诔》,并分析了诔体的发展和转型。雷久密(Chiu-Mi Lai)在《原创拟古的技巧:陆机的拟汉古诗》[21]中讨论了萧统在选编《文选》时对陆机所作拟古诗的偏好。这类论文都是在翻译某一篇或某一类作品的过程中对原作进行解读和阐释,进而将研究扩展到某一类文体。
(二)文体分类研究
1950年,戈登在其硕论《中国文学批评的早期观念》[6]49中提出《文选》的编选为刘勰的文学观提供了具体例证。戈登还在文中简单阐述了《文选序》中提到的“赋”“诗”“骚”等文体,他认为萧统的文体分类虽然只是初步的尝试,但也开创了新的文体分类方式[6]57。1957年,海陶玮发表了论文《〈文选〉与文体理论》,他在文中梳理了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发展,涉及曹丕《典论·论文》和挚虞《文章流别集》两部经典文论著作,分析了《文选序》中文体的分类方式,还对个别分类提疑问,并为各类文体名称提供了详细注解。此外,他还探讨了《文选序》中文体分类与《文选》实际文体分类不一致的问题,最后得出“《文选序》并没有列出所有文体类别”的结论[7]530。1983年,黄兆杰在《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中强调了《文选》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和“选学”研究的必要性。他提出萧统在《文选序》中表达了对“赋”“诗”和“楚辞”等文体分类的困惑。虽然萧统的文体分类从欧洲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有一定缺陷,但《文选序》中蕴含的文学批评思想“可以与欧洲最好的诗学和美学相媲美”[11]158。201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在《分类、经典和体裁》一文中梳理了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发展情况,他提出在公元二世纪晚期至公元六世纪之间最全面的文体分类是萧统在《文选序》中列举的38种文体[22]。与第一类研究不同,该类论文是将研究聚焦于《文选序》,而非《文选》收录的作品,通过分析《文选序》中萧统对文体的论述评析其文体分类思想,且多数论文持有正面评价。
(三)《文选》与《文心雕龙》关系研究
1986年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suder,Jr.)在《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手册》中对《文选》进行了全面介绍。倪豪士认为《文选》中的文体分类虽与《文心雕龙》有共同之处,但是《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方法更为精确[23]。1990年,魏彼德在其博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中探寻了萧统和刘勰在文学思想上的相似之处,提出萧统《文选》在文学史上率先对文学形式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萧统和刘勰都是最先对文学进行“新”批评的主要倡导者[16]192。他还在文中提出了《文选序》中文体与西方文体之间的相通之处,他将《文选》中的文体“赋”和“诗”对标“古希腊喜剧”(Greek Comedy)和“古典颂歌”(Classic Odes)。1997年,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和汉乐逸(Lloyd Haft)在《中国文学导读》[24]一书中介绍了《文选》中的多篇赋作,并且特地讨论了《文心雕龙》与《文选》之间的关系。她们认为《文选》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文心雕龙》中所表达的文学观。2001年,布朗大学教授多尔·利维(Dore J.Levy)在《中国文学导读》[25]一书中对《文选》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文选》在保存前代重要文学理论作品的作用上起到了重大意义。此外,他还表示,萧统在《文选序》中表达的文学思想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有共同之处。以上研究均认为《文选》与《文心雕龙》在文学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四)编撰和选录标准研究
1975年,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对萧统的文学理念和《文选》选文标准作了简要阐释,他提出萧统不收经、史、子的选文标准,反映了萧统推崇纯文学的理念[10]26。美籍华裔学者余宝琳(Pauline Yu)于1990年发表《诗在其位:中国早期文学的选集和经典》一文。余宝琳在文中指出《文选》的选录标准符合当时读者的整体文学观念,《文选》的编撰者不止萧统一人。她还提出萧统不收经、史、子的选文标准符合当时的文学观念,萧统则明确提出了纯文学和儒家经典之间的区别[26]。2001年,康达维在《挑出野草与选择嘉卉:中国中古早期的选集》[27]一文中探讨了《文选》和《玉台新咏》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中古早期选集在选录内容上的不同,强调了选集本身的意义以及对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
200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籍华裔学者田晓菲(Xiaofei Tian)的专著《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田晓菲将萧统及《文选》置于时代大背景之下,在书中细致讨论了《文选》与梁朝其他文学选集的关系并进行对比,还提及了《文选》编者和选录标准的问题。她在书中提出,《文选》反映的是对以往文学的观念和评价,虽然它在之后的唐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当时并不是梁朝文学选集中最重要的一部[28]。美国汉学家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的专著《帝国之间:中国的南北朝时代》于2009年出版。这本书涉及了《文选》编撰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并将《文选》与《玉台新咏》的选文范围和编撰目的作了对比。陆威仪提出,虽然《文选》不录经、史、子等文章,但是《文选序》重申了经典作品在社会和政治作用方面具有严格要求,这体现出该书表达了文学性质问题上的中立立场[29]。2018年,魏宁在《重谈梁朝文论分歧》一文中翻译了萧统所作《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通过分析该诗和《文选序》中反映出的萧统文学观,魏宁认为萧统强调了自然秩序、社会和谐和文学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中立的文学观念是编撰《文选》的关键[30]。
(五)相关议题的交叉研究
1982年出版的康达维译本,即《昭明文选(第一册:城邑之赋)》,是英语世界“选学”研究最全面的资料。该译本的引言共分为《中国早期文体理论和文体文集的开端》等五个部分,基本涵盖了“选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深入研究以上问题,康达维认为《文选》中的文体分类受到了曹丕《典论·论文》、挚虞《文章流别集》和陆机《文赋》等早期文集的影响。在《萧统生平及〈文选〉的选编》一节,康达维表示《文选》大概是由萧统及数十位文人共同编撰的。他还表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文心雕龙》对《文选》的编撰有影响,但这两本书中对“文”的阐释是相似的。康达维还提出《文选》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文学选集,而是“纯文学选集”,体现了萧统对纯文学的推崇。在《“选学”与版本》一节,康达维梳理了《文选》的现存版本以及“选学”在中国和日本的研究情况。最后,他指出虽然西方世界《文选》研究内容和深入都不及中国和日本,但也有海陶玮这样优秀的研究,而他自己的译本则是基于前几个世纪的“选学”研究才得以完成[31]。
康达维教授的学生王平(Ping Wang)目前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她的专著《中古中国朝廷之文化与文学:〈文选〉编者萧统及其交游》于2012年出版。王平在第二章《绅士之风:萧统的文学倾向》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萧统的文学倾向:(1)编者问题:王平赞同国内曹道衡等选学专家的观点,即《文选》的主要编撰者是萧统,刘孝绰在编撰过程中只起到了次要作用;(2)《文选序》中的文学观与文体分类:王平认为萧统在《文选序》中列举出的文体是详尽的,并提出萧统在《文选序》中强调文学的历时变化;(3)《文选》与其他文学理论作品的关系:王平讨论了《文选》与萧衍《金楼子》、钟嵘《诗品》以及刘勰《文心雕龙》的关系,提出这些作家对建立纯文学标准的共同向往;(4)《文选》与《玉台新咏》的关系:王平指出萧统编撰《文选》和萧纲编撰《玉台新咏》出于完全不同的文学态度,《文选》旨在制定标准而《玉台新咏》仅用于娱乐;(5)家族环境:通过分析萧统与弟弟之间的情感和交流,王平认为萧统的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太子身份的影响[32]。
三、结 语
纵观《文选》的译介史,笔者发现英语世界《文选》译介的四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1)20世纪初的萌芽期,英国汉学研究形势并不乐观,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韦利开始翻译《文选》中的作品。虽然韦利并不认可《文选》的选录标准,但他的译本无疑为英语世界《文选》译介和研究奠定了基础。(2)20世纪50年代的过渡期,汉学研究重心从英国向以现代新型汉学“中国学”为主导的美国转移。该阶段《文选》译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出于文学批评界自身理论构建的需要,他们将关注的焦点从上一阶段的诗赋翻译转向《文选序》的翻译和研究。其中,海陶玮译本为后来的《文选》译介提供了示范性的翻译。(3)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探索期,美国以中国学为主导的汉学研究不断发展,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华裔学者在《文选》译介方面起到引领作用,随后出现了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译本,该译本的出现标志着《文选》整体译介的开始。(4)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期,英语世界《文选》辞赋翻译已逐渐走向成熟,《文选序》和诗歌译本也不断丰富,蔡宗齐译本作为中国文论代表作品进入英语世界的大学教材选本,也可见《文选》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正逐步提升,但全译本仍未出现。由此可见,英语世界《文选》译介不仅与英语世界汉学发展形势有关,还与译者自身的翻译目的息息相关。
从上述英语世界“选学”研究的历程来看,“选学”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两大特点:(1)研究形式:研究从一开始基于《文选》译介,即《文选序》和《文选》收录作品的翻译和阐释,逐渐转向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与文学选集中的专业论文,最后再到聚焦《文选》本身的研究专著;(2)研究内容:英语世界“选学”研究与国内以训诂学为基础的传统“选学”不同,更接近许逸民先生提出的“新文选学”中的“文选评论学”“文选编纂学”和“文选文艺学”。汉学家大多精通中文,其研究论文及专著的参考文献中含有大量中国古典文献以及中文“选学”研究论文和专著,这是中西方“选学”研究趋同的原因。但上述研究尚存不足:其一,研究视角仍有局限,缺少关于《文选》版本、注释和校勘的研究;其二,《文选》总体研究还不够多,目前只有康达维和王平两位学者致力于萧统及《文选》的专门研究。
百年来英语世界《文选》译介和研究相辅相成,加快了《文选》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语世界“选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但总体而观,目前英语世界《文选》的节译本种类繁多,但全译本尚付阙如。此外,目前译介和研究主力军多为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国内学者参与全球对话的发声较少。因此,应加强中外译者的通力合作,在国学与汉学的生成对话和双向阐释中,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语言与文化优势,由此推动《文选》全译本的生产进程,创造国内外“选学”研究成果的新突破,进而有效提升世界范围内中国文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