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纹理的再现(三) 展现瞬间运动的笔墨纹理
杨崇和
49 注32 中所引高居翰著作,第124、125 页。
“视觉纹理再现”的前两篇文章主要关注10 至17世纪的画家们如何解决自然纹理的再现问题。1杨崇和,《视觉纹理的再现:十至十七世纪中国山水画中的例证》,载《新美术》2019年第3期,第55—73页,后文简称《纹理再现》;杨崇和,《视觉纹理的再现(二):自然、古典与气韵生动》,载《新美术》2021年第5 期,第181—196 页,后文简称《纹理再现(二)》。虽说数百年间文人画中常常流露出颇具个性的笔墨,但严肃的画家从未放弃追求自然纹理的再现。在《视觉纹理的再现(二):自然、古典与气韵生动》中,我们还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分析了山水画,试图建立纹理再现的客观标准。同时也应看到,元代之后,文人画家对再现的兴趣渐渐从自然景物的纹理转向笔墨自身生成的纹理。到了晚明,董其昌(1555—1636)终于提出颠覆性的山水画审美标准:“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立志将山水画变成笔墨之艺术而独立于自然景物的再现。2石守谦先生在研究董其昌《婉娈草堂图》已经指出这一点,参见石守谦,《董其昌〈婉娈草堂图〉及其革新画风》,载《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548—568 页;石守谦,《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石头出版社,2017年。本文是此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试图从董其昌的视角出发观看和讨论山水画中笔墨纹理自身的再现。
一 运动再现:瞬间与片刻
在讨论笔墨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运动再现”[Representation of motion]的基本观念。1964年6月贡布里希[E.H.Gombrich,1909-2001]在瓦尔堡研究院举办的“时间与永恒”系列讲座上做了题为“艺术中的片刻与运动”的演讲,他在开场白中说:“在艺术领域,空间及其再现问题以近乎夸大的程度占据了艺术史家的注意力;而时间与运动的再现却被莫名其妙地忽略。”指出这一课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3Gombrich,E.H.“Moment and movement in art.” The Image and the Eye:Further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Phaidon Press Limited,1982,pp.40-62。中译本可参见贡布里希,《图像与眼睛:图画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范景中等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9—60 页。此后的数十年中,这个被忽略的课题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丰富细致的研究成果接踵而至。一方面,再现画面运动感的主要元素被梳理清楚,它们是:动态平衡、倾斜、运动时产生的(有时是想象的)轨迹、运动的方向、离开起始点或平衡点的距离等等。4例如参见:J.M.B.de Souza and M.C.Dyson.“An Illustrated Review of how Motion is Represented in static Instructional Graphics.” 1st Global Conference-Visual Literacies:Exploring Critical Issues,Mansfield College,Oxford,July 3-5,2007。也就是说,具有这些元素的绘画能让观者感受到画中景物的运动感;另一方面,运动再现与时间密切相关,瞬间[Instant]和片刻[Moment]这两个原本并无严谨定义的时间单元在表述运动再现时也被明确区分,5Cutting,J.E.“Representing Motion in a Static Image:Constraints and Parallels in Art Science and Popular Culture.” Perception,vol.31,no.10,2002,pp.1165-1193。事实上,片刻和瞬间在照相技术发明之前并没有被艺术史家严格区分,这可以从贡布里希引用的18世纪文献中看出。在历史文献中用瞬间表达片刻时有发生,为使上下文顺畅,贡氏也会沿用瞬间来代指片刻,但贡氏本人在论及二者时,是将它们区别对待的。它们的含义分别简述如下:
瞬间高速照相机拍摄到的运动图像相当于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凝固了运动的一个剎那,它捕捉到的瞬间图像是肉眼难以分辨甚至无法看到的。这句话在今天很容易理解,但在1878年之前则不然。那时,大众对瞬间的认知主要是基于日常的经验,它几乎是“真实和可信的代名词”。6Prodger,Phillip.Time Stands Still:Muybridge and the Instantaneous Photography Move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3.1878年,迈布利奇[E.Muybridge,1830-1904]经过数年努力终于成功拍摄出一组赛马奔跑的清晰照片,7迈布里希为斯坦福[Leland Stanford,1824-1893]拍摄奔马照片的工作始于1872年,但直到1878年才拍出一组令人信服的清晰照片。奔马的姿态被瞬间摄影[Instantaneous Photography]所“凝固”(图1)。它和人们日常“看到”和“认为”的奔马姿态是如此不同,照片记录的马腿在奔跑时的真实动作与人们自以为是的姿势差异甚大。那种四蹄前后伸展、同时离地的动作虽然被千百年来的中外艺术家反复描绘(图2、图3),但其实并不存在。恰恰与之相反,当奔马的四蹄同时离地时,它们是收于腹下的。因此当照片发表后不仅在普通民众间,也在科学和艺术界引发震撼和争议。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进步,照相机捕捉的瞬间越来越短,以至于被一些学者称作“时间的胶囊”[Encapsulation of Time]。8参见 Eisner,W.Comics and Sequential Art.Poorhouse Press,1985。例如,在子弹击中玻璃瓶的剎那,高速摄影捕捉的瞬间能凝固玻璃碎片飞散在空中的形状,好比将时间装入胶囊,不再流动。今天,人们对照相机拍下的五花八门的瞬间图像早已见怪不怪,眼见未必真实而真实也未必可见的观念已融入我们的认知文化中。

图1 迈布利奇于1878年首次成功拍摄的赛马奔跑瞬间的清晰照片

图2 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的奔马姿态,陕西历史博物馆

图3 法国画家西奥多·杰利柯绘于19世纪初的奔马姿态,巴黎卢浮宫
片刻 在摄影技术能够“凝固”瞬间图像之前,画家绘制具有运动感的图像时所对应的时间是片刻。如果说瞬间意味着一个“时间点”,片刻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时间段”,其较前者更为宽泛,能完整囊括画家要叙述的故事。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维纳斯的诞生》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时间片刻中的运动再现(图4):先看画左方悬在空中的两位风神,他们向右倾斜的上身与身后飘舞的衣裾让观众感受到他们正飞向画面中央的维纳斯,其中一位鼓起腮帮,另一位微微张嘴,一起吹出白色烟雾,那是想象中风的轨迹;此时,维纳斯和春神的秀发、长裙以及手中的绣花斗篷迎风扬起(在静止的情况下它们本该垂向地心——静态的平衡点,但风力的作用使它们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还有风神扇动的翅膀、空中飘舞的花朵等等,上文提到的产生运动感的几种元素几乎全部被画家恰到好处地融入画中的情景中,完美地构建了他要叙述的故事。不过我们要问:这样一个既有完整的叙事又充满运动感的画面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的存在?贡布里希的回答是:几无可能!贡氏用电影拍摄的过程来解析类似《维纳斯的诞生》这样的画面:9贡布里希所引用和分析的画作是保罗·德·马太斯[Paolo de Matteis,1662-1728]的《赫拉克勒斯的选择》,参见注3所引贡布里希文章。设想一架摄影机正拍下《维纳斯的诞生》中的动态场面,这个过程也许经历了几秒钟并耗用了上百张胶片,每张胶片可以看作是一个瞬间。现在我们要从其中寻找一张与《维纳斯的诞生》画面完全一样的胶片,却发现:当风神的姿势和画作上相同时,维纳斯的右腿可能正跨向岸边,或者春神的右手尚未举过头顶;也许确有一张胶片,其中所有人物的肢体动作都和画上相同,春神却可能因风的吹拂刚好闭上了眼睛,或者飘在空中的花朵已落入水中……总之,和画面完全相同的那张胶片(或者说那个瞬间)几乎没有可能存在,若想得到它只能通过“摆拍”,相当于在上百张胶片中找出局部效果满意的几张(几个瞬间),然后将它们“合成”从而得到满意的画面,即这几个瞬间的集合刚好组成了一个艺术家想要的片刻。19世纪中叶之前,西方绘画中的运动再现大约如此,其所对应的时间是片刻并非瞬间。如此才能将不同时间点、不同层面的多重叙事融于同一画面以满足故事情节在人们心理上的真实感。相反,瞬间所“凝固”的物理真实由于缺乏时间上的延续性,常常无法满足画家或观众所期待的叙事。

图4 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另一方面,即使画家想要再现照相机所捕捉的瞬间图像,其可行性也微乎其微。1981年,马克·坦西[Mark Tansey,1949-]创作了一幅“画中画”,图中一位女画家正在绘制车祸发生一剎那的场景(图5),这当然只是画家的想象,现实中是无法做到的,它暗示了运动的瞬间再现和画家能力之间的矛盾。马克·坦西是位颇具哲学思辨的艺术家,他为这幅作品起了耐人寻味的名字:《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用以批评和讽刺那些不再关心具象再现的行动画派的画家们。如果说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1904-1997](行动画派的灵魂人物)所作的人像画还保留一些具象元素,那么画派的另一位巨擘,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Pollock,1912-1956]的“滴画”[Drip Painting]则完全摆脱了具象的约束。传统意义的图像在杰克逊·波洛克的画布上不复存在(图6),画布上滴溅的色彩真实记录了他挥洒颜料的每一个瞬间,“运动造成的视觉记忆,滞留在空间里”,10杰克逊·波洛克题在自己照片背后的句子,照片摄于他的画室,时间大约在1948—1949年间。“画布上出现的不再是图像,而是事件”。11罗森博格[H.Rosenberg,1906-1978]首先使用了行动绘画一词,并对行动绘画做了定义和分析。参见Rosenberg,H.“The American Action Painters.” Art News,vol.51,no.8,1952。而画布上再现的瞬间运动不仅记录下创作过程,同时它就是作品本身。

图5 马克·坦西,《行动绘画》,1981年,美国私人藏

图6 杰克逊·波洛克的“滴画”作品,纽约当代美术馆
事实上,运动的瞬间再现也同样存在于古典绘画,只是它们往往保留在原创画稿中,在最终完成的画作上已被刻意掩盖。16世纪时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已经意识到“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们的美丽的草图[una bella bozza]要比精细的完工之作更优美、更有力”。12转引自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63 页。话虽如此,瓦萨里的这种超前的审美并未在当时形成主流,多数艺术家和鉴赏家还是更喜爱“精细的完工之作”。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创作《自由引导人民》时留有一张油画稿(图7),画布上横涂竖抹的笔触,俨然是一幅行动画派的佳作。但在“精细的完工之作”中,这些反映画家最初创意的激情笔触都不见踪影,正是所谓一种艺术掩盖了另一种艺术。直到19世纪后半叶印象画派的出现,创作时的笔触才被画家刻意保留在完工之作上,13在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上刻意保留的笔触也偶尔可见,例如在伦勃朗的某些作品中,但那还只是实验性质的探索,既没有引起当时画家群体的广泛回响,也没有得到多少观众的赏识。它们忠实记录了行笔着色时的瞬间运动痕迹。

图7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油画稿,上海私人藏
基于运动再现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古典绘画最终呈现给观者的是运动场景,是片刻的再现,例如《维纳斯的诞生》;印象画派刻意保留在所描绘景物上的笔触,是瞬间的再现。而行动画派(及其他一些现代画派)更进一步,在波洛克的滴画里,景物完全消失,作品只再现了画家挥洒油彩的行为本身,即瞬间运动的痕迹。
二 笔墨纹理的再现
大约于14世纪初,赵孟頫(1254—1322)明确提出绘画的笔墨应与书法相通并将其付诸实践,他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14赵孟頫此诗题在其《秀石疏林图》(故宫博物院)卷后。 事实上,绘画以书法用笔并非赵孟頫首倡,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就有“善书者往往善画”的议论,但在赵孟頫的倡导和实践之前,书法用笔在主流绘画中未受到广泛的重视,也未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主张被当时的文人画家群体迅速接纳,逐渐演变成其后数百年间中国绘画的主流。从纹理再现的视角观看自赵孟頫至吴门诸家的山水画,我们发现,自然再现与古典笔墨时常出现在同一作品中,15《纹理再现(二)》中讨论的两幅文徵明的作品即属于这种情况。那时的名家巨手兼有传统笔墨的训练和洞见自然的能力,是董其昌所说“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的年代。16[明]董其昌,《画禅室笔记》,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67—448 页。进入晚明后,吴彬(生卒不详)这样的天才仍然能从自然纹理中发现灵感,17关于这个时期画家再现自然纹理的讨论,参见注1 所引二文。但总体而言,在经历数百年的发掘之后,依赖自然纹理汲取养分的笔墨创新几近枯竭。此时,董其昌另辟蹊径,彻底回归古典,在其中寻找创新的基石,以构建笔墨的新形式。他将皴法从匹配自然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走向展现笔墨自身纹理的新境界,形成了“山水画与自然的对立”。18石守谦,《以笔墨合天地:对18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新理解》,载《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308—331 页。那时的多数画家在董其昌的影响下更专注笔墨形成的画面效果,山水的自然属性反而沦为陪衬。事实上,明清之际人们在谈及绘画的气韵生动时,关心最多也正是笔墨本身。19这一点王世襄在《中国画论研究》中做过较详细的讨论,本文不再赘述。参见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3—286 页。张庚(1685—1760)有一段关于气韵发自笔墨的论述:
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下矣。何谓发于墨者?既就轮廓,以墨点染渲晕而成者是也。何谓发于笔者?干笔皴擦,力透而光自浮者是也。何谓发于意者?走笔运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疏密多寡,浓淡干湿,各得其当是也。何谓发于无意者?当其凝神注想,流盼运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谓之为足则实未足,谓之未足则又无可增加,独得于笔情墨趣之外,盖天机之勃露也。然惟静者能先知之……20[清]张庚,《浦山论画》,载秦祖永辑,《画学心印》卷七,清光绪四年(1878)刻朱墨套印本,叶四十三至四十四。
张庚自问自答地议论了笔墨和气韵之间的各种相关性后,最终回归到“天机之勃露”这一关键点上,“天机” 即大自然,它存在于“笔情墨趣之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脱离对自然的再现,绘画笔墨如何“天机勃露”?21关于气韵生动与再现自然的关系,请参见《纹理再现(二)》第二节“气韵生动:一种假设及其客观评测”。一句简单的“惟静者能先知之”似乎过于玄虚,我们准备从墨笔的运动及其纹理再现的观点来回应这个问题。
读者可能会问,笔墨纹理并非自然景物,何以云“再现”而非“表现”?事实上,不论真山水中的自然纹理亦或纸绢上的笔墨纹理,都是客观之存在,对视网膜来说生成的都是视觉纹理;而中国画家临仿、借鉴经典已有千余年的传统,既然被临仿之物是客观存在,将之称作“再现”或许更加合适。如若借用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三个世界”的概念来理解,那么自然纹理是“世界一”中的客观存在,画家将其再现于纸绢之上所形成的笔墨纹理则是“世界三”中的存在,是波普尔所称的“客观的知识”。因此,以古典画作为范本的临仿或创作可以视为对“世界三”中客观存在的再现。我们知道,再现自然(空间感或纹理)的绘画,其任务是将三维世界中的景物转换到二维平面上。而不论是“写实”画法追求的“形似”还是“写意”画法展现的“神似”,22此处“写意”是指画家所写景物的客观之意,而非画家胸中的主观之意。参见《纹理再现(二)》“附录”中关于“写意”的讨论。成功的作品都会让笔墨构成的图像产生逼真的错觉,这是一项颇具创造性的工作。不过,再现笔墨纹理(世界三)和再现自然(世界一)的情况有所不同,需要稍做区分。
(一)对古典笔墨的精确复制
笔墨纹理最直接的再现莫过于一丝不苟地临摹古代大师的作品,人们或许认为此种临摹缺失了再现自然时需要的创造性,然而这样的评论是否恰当须在具体历史环境下考察。在20世纪中后期的美术史主流语境里,清初“四王”(在王时敏的引领下)忠实于古典原作的严谨临仿往往被视作了无创意。罗樾[Max Loehr,1903-1988]甚至认为,像“四王”那样的画家是“画家学者”[Painter Scholar],他们的作品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学术,并建议将之排除在绘画史的发展之外。23Loehr,Max.“Phases and Content in Chinese Painting.”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Taipei,1972,pp.285-297.这类观点忽略了17世纪中国画坛的状况:当时的“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至吴门云间,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赝本溷淆,以讹传讹,竟成流弊”。24[清]王原祁,《雨窗漫笔》不分卷,清光绪刻《翠琅轩馆丛书》本,叶一。最近的研究指出,“四王”正是在当时古典绘画语汇的真貌几近湮没,人们不再清楚经典为何物时重新构建了古典图式和笔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重新发现并厘清了已经变得模糊的古典语言,从而推动了一场文艺复兴式的绘画复古运动,这在中国千年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5章晖、范景中,《〈古典的复兴〉序》,载《古典的复兴:溪客旧庐藏明清文人绘画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第iv 页。这种对经典的重构或许缺乏罗樾语境下的创新,但却在画史上具有文艺复兴式的功绩。26事实上,在“四王”创作的后期,特别是王时敏和王原祁祖孙,他们都在保存古典图式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笔墨纹理(详见下文关于王原祁画作的讨论以及注39 引文中有关王时敏绘画的分析)。今天虽然去古已远,但经典画作的真迹、高清印刷品或电子图像均可通过各种渠道看到,古典的范式清晰无误。如果有人可以忠实地复制古代大师的杰作,我们会赞赏其精湛的技艺,但它是否仍具有画史上的重要性则要后人来评说了。将画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置于历史环境中考察,不仅避免了观看“四王”时的盲点,还让我们意识到,明中期的吴门画家们何以没有亦步亦趋地规模元人,而是融合前代的风格,孕育出吴门新风。盖因其时去“元四家”未远,真迹流传尚伙,人们不难分清他们各自的风格特征,重构和复兴的价值还没有显现。
(二)对笔墨理趣的再现
以上是笔墨纹理再现的第一种情况:精确复制古典笔墨。现在来看与之不同的另一种再现:“复制”古典笔墨中的“理趣”。这样的再现更关注古典笔墨纹理形成的理念和趣味,27事实上,这种“理趣”(理念和趣味)本身也是“世界三”中“客观的知识”。而并不追求准确复制笔墨旧貌。那么,何为文人画中笔墨之理趣?
上文中我们谈及印象派画作上刻意留下的笔触,这让人联想到文人绘画中的笔墨。而讨论文人画的笔墨,不能不谈及书法。书法是相对抽象的艺术,除了字的间架结构,墨笔痕迹生成的运动感也是书法审美的要素。从运动再现的视角观看书法,可以理解如下:书法被写到纸绢上时,笔画记录了笔锋运动的瞬间,即它再现了墨笔的瞬间运动,而这个记录就是作品本身,这一点与摄影产生的瞬间图像性质类似。例如,图8-1 的楷书“年”字(白谦慎教授书写),其最后一笔“悬针竖”再现了行笔的三个动作,头部较粗的部分反映了起笔时的下按;竖直下行的墨迹记录了毛笔移动的途径;而底部出尖的收尾则预示了笔锋最终离开纸面。书写结束时,笔迹完整地再现了墨笔的瞬间运动,作品也随即完成。这种运动感在行、草书中更为明显。图8-2 的行书“百年”二字取自文徵明(1470—1559)《五冈图》上的题诗。二字连写,连接处从渐细到渐粗,宛若两字之间的婀娜腰身,墨迹的粗细变化令人感到提按笔尖的动作就在眼前;“百”字笔画边缘偶有墨色渗出,表明该处笔速较慢,最后悬针竖的收尾带有飞白,显示提笔时笔速增快。相比楷书,行书再现墨笔的运动时还让观众领略到行笔的节奏和速度感,尤其是带有飞白的笔画。苏轼(1037—1101)曾赞美文同(1018—1079)所作的飞白书,说它“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28[宋]苏轼,《文与可飞白赞》,载《苏轼文集》卷二十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二册,第614 页。文同的飞白作品今不可见,苏轼的描述可藉董其昌所书来体会,图8-3 中“及之”二字取自思翁跋《五冈图》,二字全用飞白,婉转流畅,说它“若游丝之萦柳絮”“若流水之舞荇带”可谓恰当。用大自然中“万物之态”比拟书法,在唐宋诗文中在在可见:29米芾对类似的比喻颇有微词,他说“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 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米芾《海岳名言》)或许这样的修辞无益学书法者,但从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它将自然物的动态和抽象的书法笔迹联系起来,通过自然之美引发人们对书法笔迹的欣赏。

图8-1 白谦慎教授楷书“年” (左)

图8-2 文徵明行书“百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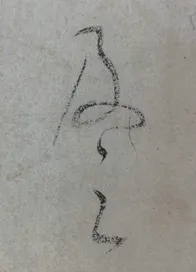
图8-3 董其昌飞白书“及之”(右)
“飘风骤雨惊飒飒。”“时时只见龙蛇走。”
([唐]李白《草书歌行》)
“飞沙走石满穷塞,万里飕飕西北风。”
([唐]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
“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
([唐]孟郊《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
“墨作龙蛇纸上飞。”
([宋]苏辙《次韵刘贡父题文潞公草书》)
“龙蛇夭矫锁黄尘。”
([宋]黄庭坚《题苏才翁草书壁后》)
“势从天落银河倾。”
([宋]陆游《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
在《纹理再现(二)》中我们指出,自然物在生长、形成或演化的过程中往往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作为自然物本体的一部分,是触发人们美感的因素之一。不言而喻,自然物运动的形态也是触发人类美感的因素,诗人的比喻在运动的笔墨与生动的自然之间建立了关联,藉以激发观众(读者)的联想,打通抽象的书法与“气韵生动”这个最高审美准则之间的通道。30气韵生动与自然物的关系,请参见《纹理再现(二)》中的相关讨论。
“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在了解到书法笔墨的运动感、特别是瞬间运动感关联着自然之美后,我们或许对赵孟頫何以倡导绘画须书法用笔有所领会,他要构建的文人绘画理趣是将书法笔墨,尤其是它的动感引入绘画,唤醒“潜藏在那些静穆的树石形象中永恒而盎然的活力”。31书法用笔的动感除了楷、行和草书,篆书也具有动感,“篆书圆润微妙的弯曲与均衡似乎蕴蓄着自然界原动力徐缓幽深的搏动”(方闻,《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李维琨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14 页)。关于书法与绘画关系的更广泛的分析和讨论可参见方闻的相关著作。事实上,从景物到笔触/笔墨,千百年来中外画家们一直探索着如何在静止的画面上展现运动感,赵孟頫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鹊华秋色》中将董源的披麻皴演绎为“典雅的楷书用笔”,而《水村图》全用水墨,皴笔中夹带着行草书中的飞白,加强了画面的运动感。不过,这些具有书写意味的山水作品仍然带有实验的性质;32《水村图》所采用的纯水墨绘画手法,也被认为是“风格极端主义”的体现(参见范景中、高昕丹编选,《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07 页)。而我更愿意接受另一种说法,“他(赵孟頫)那些以书法用笔探索的多种山水画语汇,尚未自成一家。应该承认……他本人也未能创造出一种出色的山水风格。赵孟頫去世30 多年之后,才出现了真正个人书法风格的山水画”(同注31,第115、116 页)。也就是说,在赵孟頫那里,山水画的书法用笔还在探索和实验中,尽管《水村图》的笔墨比起《鹊华秋色》已经成熟了不少。到了学生黄公望(1269—1354)创作《富春山居图》时,同样是披麻皴,却已有较多的变化,墨的浓淡、笔的疾缓都比松雪斋要复杂,一方面它们更逼真地再现了山坡上的纹理,33可参见《纹理再现》中图-8 和图-9 及其相关文字。同时也比经典笔墨更富含运动感,“在山水画中创造出充满活力的新形貌”;34方闻,《夏山图:永恒的山水》,谈广晟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第168 页。松雪翁的外孙王蒙(1308—1385)将本来直笔中略呈弧形的披麻皴改造成短促且弯曲的“牛毛皴”,皴笔面貌虽与松雪和大痴明显不同,动感却进一步增强了。到了明代中期,吴门诸家融合各种皴法,推陈出新,发展出运动感更为丰富的笔墨纹理。
总之,尽管不同时代的不同画家其笔墨纹理之形态各异,他们虽然并未精准复制古典笔墨,但都不约而同地再现了笔墨的运动,在新颖的笔墨纹理中呈现出古典笔墨的理趣,我们将此类绘画归为笔墨纹理的第二种再现,也许可以将其比作自然再现中注重“神似”的“写意”画(在此再次强调,“写意”是指写自然景物的客观之意);与之相对,纹理图样的逼真模仿可类比自然再现中注重“形似”的“写实”画。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如能在经典之上再现笔墨的运动感,则距离张庚所云笔墨之“天机勃露”相去不远矣。
我们在下节中讨论两幅绘于17世纪前后的画作,一方面看看画家是如何在脱离自然再现的情况下让笔墨纹理仍然生动,同时也藉此展示古典笔墨的理趣是如何被再现的。
三 理趣再现:从“皴笔重叠”到“熨干再画”
《婉娈草堂图》(图9)是董其昌43 岁时为好友陈继儒(1558—1639)所作,画中实验了具有创新手法的“直皴”,让画面的运动感洋溢楮墨。石守谦先生分析指出,“由于那些甚有清晰运动方向的直皴作用,不仅使土坡的各面显得含有饱满的动态,也使得整个坡面在各单元的连续之中产生斜向的充沛动势”,“崖壁却因(具有‘运动方向’的)直皴的作用,而产生似乎随时要释放而出的巨大动能”。此处的“运动方向”和“斜向”正是前文言及的生成画面动感的元素。不仅在山石上实验了直皴,思翁还将它们用于树干上,“由于那种似其山石皴擦的直笔的作用,更富有苍厚的动态力量,使得几棵看似安静的直挺树干,本身即产生其后方作扭曲姿态之小树所不能比拟的内敛动态”。35树与山体使用同样的皴法,我们在文徵明的《五冈图》中也看到了,参见注1 引文中的相关讨论。总之,董其昌“自信掌握了理想之‘势’的直皴,也带给《婉娈草堂图》中诸多取自古人之形象更丰富的活跃生气”。石先生的研究阐明了三个重点:一、董其昌采用了源自古典绘画中的直皴;二、对直皴的改进营造出画面的整体动感;三、画中山水之图式与婉娈草堂的实景之间无直接关联。三点归结所得的结论是,《婉娈草堂图》的生动画面并非源于对自然景物的再现,而是基于对古典画法——“直皴”的改革和创新。36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教授曾撰文对石守谦先生的“直皴”分析提出异议。他认为《婉娈草堂图》山体上的皴法受到西洋版画的影响,特别是画面右上方云边的山体上那些交叉的皴笔,班宗华推断那是董其昌模仿西洋绘画中的交叉排线光影法[Crosshatching]之结果。不过从中国山水画古典图式的视角观看,那些“横线”更像是米家云山上的横点,特别是在整幅画中,它们仅出现在云朵附近。董其昌拉长了那些横点,因此看起来似乎成了横向的短线。类似的画法还见于台北故宫所藏《奇峰白云图》,董其昌在这幅仿米家山的立轴上也在纵向的皴笔上施以拉长的横点,其画面效果和《婉娈草堂图》颇为相像。事实上交叉排线光影法中的线条主要是为了在版画(或素描)中表现阴影深浅的程度,不论是木版画的刀刻还是铜版画的蚀刻,其线条都粗细一致,间隔均匀,没有变化,亦无层次感,而线条之间近乎机械的交叉更凸显了人为的刻画(图10-1)。自然山体不会产生那样的纹理。难以想像,一味追求笔墨精妙的董其昌会借鉴如此机械刻板的方式来呈现笔墨自身的纹理。参见白谦慎编,《行到水穷处:班宗华画史论集》,刘晞仪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332—350 页。

图9 [明]董其昌,《婉娈草堂图》,台北私人藏

图10-1 意大利画家Giovanni Francesco Grimaldi 创作于17世纪上半叶的版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山坡局部

图10-2 董其昌《婉娈草堂图》山体局部纹理
事实上,在采用直皴使整幅画面释放出“巨大动能”的同时,思翁还在处理直皴的笔墨上做了创新,制作出如石先生所说的“皴笔重叠的现象”,这种新手法让笔墨纹理本身更富于运动感。现在我们来观察画中山体局部的细节,图10-2 中山石上的纹理呈现出半透明的特质,上一层墨迹压过下层墨迹之后,下层墨迹仍然依稀可见,这就是用“皴笔重叠”绘出的效果。虽然这类画法在前人的画作中也偶尔出现,但思翁在此是有意为之,并实施于整幅画作中,效果显著。自然界中,不论是树皮的皴裂、山坡上的植被,或是山石的风化,其纹理的形成过程是新纹理取代或覆盖旧纹理,致使旧纹理不复可见。例如山石的风化,随着大自然的持续侵蚀,较早的风化纹理层会被后来形成者所取代或掩盖,新旧纹理层之间不会有透明的重叠。在《纹理再现(二)》中,我们谈及山石的风化纹理中蕴含着大自然的动感,由于自然纹理(或传统的皴法)不具备透明性,观众感受到的是“单层的动感”。而“皴笔重叠”构成了一定的透明度,这使得纸面上的笔痕墨迹产生了“立体的动感”,因而记录了更加完整的创作过程、再现了更加丰富的瞬间运动,让脱离真山水的笔墨纹理呈现出超出自然的生动效果。
“皴笔重叠”的技法在董其昌晚年的绘画中愈显成熟和彻底。《江山秋霁》卷是他70 岁左右仿黄公望的作品,我们试将其与大痴作品中的笔墨做一比较(图11)。先看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中的皴笔,皴法基本是单层的,偶有重叠也并非刻意(全卷均如此),它们逼真地模拟了山坡上的自然纹理。37见注1 引文中的相关分析和讨论。再看《江山秋霁》的皴法,长条的披麻皴不时夹带着飞白,和图8-3 中书写时的用笔施墨几乎相同,是典型的书法用笔。卷中坡岸、树木乃大痴图式,纹理的透明度和层次感比《婉娈草堂图》更为明显,“皴笔重叠”的技法此时已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较之大痴,思翁的重叠皴法凸显了笔迹透明的层次,增强了画面的运动感,却于再现真山方面去大痴远矣,然其生动之处真可谓“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思翁对笔墨独立性的意识和实践已然高出古人,在《江山秋霁》的题跋中他情不自禁地高呼:“恨古人不见我也!”

图11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局部(上)和董其昌《江山秋霁》(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局部(下)的笔墨比较
值得指出的是,董其昌虽然认为画家在掌握了古典技法之后“进而当以天地为师”,不过他自己并没有“以天地为师”去追求形似,他非但没用笔墨模拟、匹配自然,反而让自然沦为陪衬笔墨的形模。他“以天地为师”是学习天地的创造力,用“皴法重叠”演绎古典笔墨,画出超越真山水的透明纹理,令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充满动感的笔墨本身,从而感受到半抽象的山水释放出的彰彰在目之跃动感。陈继儒曾这样评论董其昌临仿的米家山:“米家画在似山非山之间,玄宰画在似米非米之间。”38董其昌自题《九峰春霁图》手卷,跋文载《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第215 页。“似山非山”可视作对自然纹理的再现,“似米非米”则是对笔墨纹理的再现。如此看来,思翁不仅不以天地为师追求形似,即便临古亦不求形似,而是复现古人的理趣,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笔墨纹理的再现。
书法笔墨用于绘画几乎被董其昌实践到极致,他的学生王时敏(1592——1680)和王鉴(1609—1677)超越老师的地方更多是在古典图式的重构上,39参见章晖,《重构经典:王时敏对董其昌的超越》,载《新美术》2022年第5 期。而将笔墨纹理再现推向新高度的是王时敏的长孙王原祁(1642—1715)。虽然依旧留心大自然的“阴阳显晦,朝光暮霭,峦容树色”,40同注24,叶四。并在自然纹理的再现上继续取得成就,41王原祁用云的分形结构和纹理绘制山峰,虽然采用了纹理置换的手法,但置换所用的纹理仍然源于自然(云),仍可看作是对自然纹理的再现。参见杨崇和,《王原祁绘画中的几何学问题》,载《新美术》2015年第3 期。不过王原祁彪炳画史的贡献则是笔墨上的创新。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记录了王原祁为友人“克大”作画的情景:
折简招克大过从曰:“子其看余点染。”乃展纸审顾良久,以淡墨略分轮廓,既而稍辨林壑之概,次立峰石层折、树木株干,每举一笔,必审顾反覆,而日已夕矣。次日复招过第,取前卷少加皴擦,即用淡赭入藤黄少许,渲染山石,以一小熨斗贮微火熨之干,再以墨笔干擦石骨,疏点木叶,而山林屋宇、桥渡溪沙了然矣。然后以墨绿水疏疏缓缓渲出阴阳向背,复如前熨之干,再勾再勒,再染再点,自淡及浓,自疏而密,半阅月而成。发端混仑,逐渐破碎,收拾破碎,复还混仑。流灏气,粉虚空,无一笔苟下,故消磨多日耳。古人“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洵非夸语也。42[清]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85 页。
我们知道,书法讲究笔画单纯简洁,线条一笔而就,披麻皴就颇能体现这种书写特性。即使董其昌“皴法重叠”中有笔画的重复,它们仍然是一笔而就的披麻皴重叠,并未逾越单纯简洁的书法用笔原则。反观王原祁作画,却是“以墨绿水疏疏缓缓渲出阴阳向背,复如前熨之干,再勾再勒,再染再点”,其中反复“熨之干”是关键步骤。这种“熨再画”的方法可以按“画—熨—再画—再熨”的次序记录下笔墨落在纸面的每一次过程,43这种画法应接近“积墨法”,但未见积墨法有用熨斗熨干的记载。为强调熨干的步骤,特将王原祁的这种画法称之为“熨干再画”。避免了前一层墨色未干时,新的渲染皴擦与之相互渗透、混合。因此,笔墨的层次更加清晰可见、丰富鲜活,令画中的山石焕发出“妙如云气腾溢”的动感。44参见[清]秦祖咏,《绘事津梁》,载于玉安编辑,《中国历代美术典籍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第16 册,1997年。然而,这种费时耗力的“熨干再画”方法显然与书法用笔的简洁原则背道而驰,但实际上,他比董其昌又进了一步,不仅摆脱了再现自然的羁绊,还突破了自元代以降的书法用笔成规,创造出文人画审美的新境界。下面我们来看看“熨干再画”会产生怎样的视觉效果。
图12 是王原祁六十三岁时为友人陆毅(1654—1726)45陆毅生年据其子陆履谦等撰《陆毅行状节略》:“王父之殁,府君才九岁。”又据黄与坚(1620—1701)撰陆毅父母合葬墓志铭,知毅父荣卒于康熙元年(1662)9月,时毅九岁,则毅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陆毅卒年据民国《太仓州志》(卷二十,人物四,叶十七)载:“卒年七十三。”时在雍正四年(1726)。所绘设色立轴《春崦翠霭》,陆毅与王原祁同乡且同朝为官,故此幅乃精心之作,非同一般应酬。尺幅超过七平尺,在王原祁的作品中堪称大幅。构图藉鉴了黄公望《天池石壁图》,但画面复杂的色墨融合则超过古人。在有色彩的山石上用墨,宋画中已可见到,不过墨笔的使用通常收敛且单纯。赵孟頫在《鹊华秋色》青色的山体上布满墨笔披麻皴,乃开风气之先。此后吴门诸家、董其昌均有类似实践,王时敏后来居上,其色墨交融的画法胜过前贤,王原祁继武乃祖将之推进到更高层次。图13 是王原祁《春崦翠霭》山体上的皴擦细部,其笔墨的变化比之董其昌那种虽然重叠但单纯的书法用笔要复杂很多(图10):笔迹不但有轻重缓急,墨色亦呈现出干湿浓淡的变化,披麻皴只有寥寥几笔,成为点缀。墨笔混合在山石的色彩中达到了色墨融合,而又层次分明,那些斑驳杂沓、墨色交融的纹理正是麓台所追求的“墨中有色,色中有墨”的境界。应当指出,虽然王原祁在形式上突破了书法用笔,但其追求仍然是笔墨瞬间运动的再现,因此在理趣上,“熨干再画”和书法用笔的主张一脉相承。鉴赏家王季迁(1906—2003)曾用音乐比喻王原祁的绘画,说他“比元代画家更进了一步”,“元代弹的是二重奏、三重奏,王原祁则像个小的室内交响乐,声音丰富得多”。46徐小虎、王季迁,《画语录:王季迁教你看懂中国书画》,台北典藏艺术家庭,2013年,第216—219 页。17世纪由董其昌发起的那场笔墨独立于山水的革命,被王原祁推向高峰并在他的笔下画上了句号。

图12 [清]王原祁,《春崦翠霭》,纵133 厘米,横61.5 厘米,上海私人藏(左)

图13 王原祁《春崦翠霭》局部(右)
从本节的两幅作品中我们看到,董其昌的“皴法重叠”和王原祁的“熨干再画”既未用于再现自然纹理,也没有单纯地重复古典笔墨纹理的旧貌,而是在再现笔墨运动感方面“复制”了古人的理趣。它们都是上文讨论的第二种笔墨纹理再现的佳例。
四 余论
纹理再现的前两篇文章主要讨论了画家对自然纹理的再现,并尝试建立一个评测再现自然纹理的客观标准。本文借用“运动再现”的观念探讨了山水画的笔墨纹理再现。作为“世界三”中“客观的知识”,笔墨纹理的再现也应有其评判的“客观”标准。设置这样的评判标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本文未打算展开讨论,仅借余论谈一点初步想法。
由于没有自然景物作为再现的参照,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由经典作品构成的参照系以资比对,类似书法中的临书范本。有了参照系,笔墨纹理再现的优劣评判才有意义、才能达成共识,而不至言人人殊。对经典作品的选择需要根据绘画自身的性质划出边界,有些经典虽名声显赫,却未必适合纳入这个参照系。例如米芾的《珊瑚笔架图》,严格地说,这是一张示意图,诚非绘画,能逼真临摹此图的人与其说是画家不如说是书家。就笔墨纹理的第一种再现而言,评判其优劣的标准似乎直截了当,那就是摹本比之参照系中的经典原作要“形神俱似”。至于第二种再现,即笔墨纹理之理趣再现,情况会比较复杂,我们在上文中已举例说明,这是董其昌提倡的那种“脱去拘束”“神会意得”的临古。47见[清]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十二中《明董香光临古卷》落款。对第二种再现的评判标准究竟如何建立,还有待研究,不过陈继儒的“似米非米”论似乎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当然,不论这标准如何建立,它最终要能衡量作品是否“气韵生动”,这条中国绘画审美的最高准则。
从视觉纹理再现的观点探讨10 至17世纪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至此大致告一段落。48纹理再现的三篇文章中主要讨论了10 至17世纪的山水画,没有涉及18世纪之后的画家和作品,在此简述如下:虽然其时山水画的主流延续了“四王”建立的正统画派,但有成就的画家仍然在笔墨纹理的再现上显现出个性化的特点。同时乾隆朝的词臣画家们“以笔墨合天地”,用精致的笔墨再现实景山水,(参见注18)让“世界三”中的纹理重回自然,正可谓“空山独立始大悟,世间无物非草书”(翁方纲诗句)。19世纪,以张崟(1761—1829)、钱杜(1764—1844)为主的一批江南画家厌倦了董其昌的“笔墨少含蓄”和王原祁的“有笔墨而无丘壑”(钱杜语),重新回归吴门追随文沈,发展出丘壑分明,笔墨精雅的颇具装饰趣味的画风,他们的努力也可视为是对明代吴门画派的复兴;同时,追随正统的画家如王学浩(1754—1832)、戴熙(1801—1860)等在笔墨纹理的再现上推陈出新,各有建树。抽象绘画在20世纪兴起,赵无极(1921—2013)将中国山水画笔墨纹理的局部图像放大,改造后用油彩绘在画布上,产生了前所未见的、基于运动瞬间的抽象视觉效果(图14)。进入21世纪,纹理再现的创新并未停止,画家张洪[Arnold Chang]与摄影师秋麦[Michael Cherney]合作,创造出笔墨纹理与自然纹理融为一体的“混合山水”(图15);泰祥洲根据《纹理再现》一文中的讨论,巧妙地将灵璧石纹理植入董其昌《青弁山图》中,揭示古人以赏石“造山”之秘密(图16)。在书法方面,王冬龄的“乱书”让书法的笔墨彻底从汉字的结体中解放出来,全面展现笔锋瞬间运动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而书写过程最终呈现出的笔墨纹理构成了一幅具有强烈运动感的抽象画面(图17),令人想起波洛克的“滴画”。它或许可以化解“超越再现”从画面之外分析绘画时所遇到的一些困境:一、无法看见宋元绘画之间的内在关联,宋元间的画风转变被视为一种突变;二、无法察觉元代以降的绘画风格在笔墨上的演变,从而导致了元代以后画史终结的结论;三、难以评判绘画质量的优劣,当“动听的言辞与蹩脚的绘画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令人痛苦的差距”时,49矛盾、尴尬的局面就会发生。需要注意的是,一种观点只能提供观看绘画的一个特定视角,好比画家关注的是画中的构图和笔墨,鉴定家和收藏家则更在乎画的真伪,材料学者感兴趣的是纸绢的结构、色墨的成分,而拍卖公司和画廊却在考虑给它定价等等。因此,我们也再次强调:“纹理再现”的观点并非要取代或否定“超越再现”,而是为观众提供另一个视角,让中国山水画的观看更为完整和有趣。

图14 赵无极,《28.02.67》,香港佳士得亚洲20世纪和当代艺术(夜场),2018年5月26日

图15 张洪、秋麦合作《仿萧云从》(陈霄女史收藏)局部,图中深色方框内是秋麦所摄真山山体的照片,方框外是张洪用墨笔绘制的山体。自然纹理和笔墨纹理在此作品中融合如一

图16 泰祥洲,《纹理变形之三:董其昌青弁山图》(画家本人提供)
49 注32 中所引高居翰著作,第124、12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