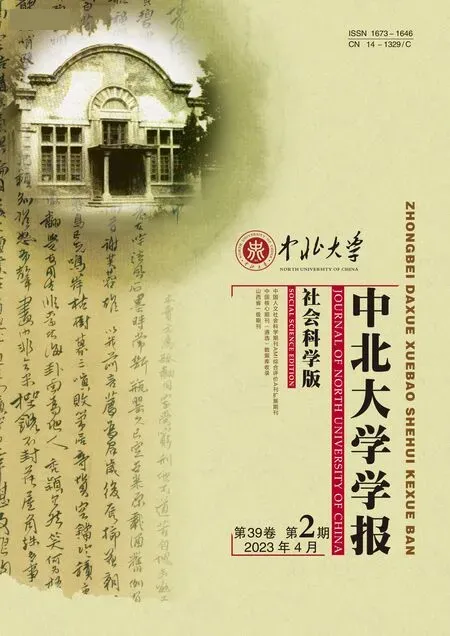声音的异托邦: KTV中的自恋主义与时空压缩
王 姮
(天津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系, 天津 300011)
20世纪以来, 以视觉为中心的表达形式逐渐改变了传统以语言为核心的传播方式。 从吸引人的眼球, 到在视觉塑造中隐含政治诉求, 再到视觉成为一种文化的霸权, 学界的批判与质疑也日益高涨, 指出“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1]173。 在对视觉文化的审视中, 人们不断指出图像时代所带来的精神桎梏, 同时, 为了使这种批判更具有建设性, 学界积极发掘一种听觉文化转向, 由此来寻找认识世界的新的范式。 麦克卢汉提出了“听觉空间”(Acoustic Space)的概念, 认为由于耳朵和眼睛生理性的不同, 耳朵不能像眼皮眨动那样可以聚焦、 透视和分割信息, 所以“听觉空间是有机、 流动、 发散的……是全息整体、 没有中心和边际的空间构造”[2]240-241。 因而, 听觉空间比视觉空间更能全方位地影响个体, 塑造文化。 由此出发, 我们将声音或听觉问题具体化, 以青少年熟知的社会文化场所KTV为例, 来思考这一特殊听觉文化空间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1 作为声音聚合场所的KTV空间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各种休闲娱乐方式相继出现, KTV等娱乐场所从日本传入中国。 KTV首先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空间而存在的, 它提供了付费空间, 借助预录在录影带或电脑等储存媒介上的、 可以消除主唱人声的音乐伴奏, 通过屏幕同步播放有节拍和提示的歌词, 参与者可以自由手持麦克风进行演唱。 目前, 学界有关KTV等娱乐休闲场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探索消费空间布局与活动规律, 如立足于宏观区位分析理念, 分析居民消费行为与城市休闲、 娱乐场所的空间关系[3]; 二是考察已有娱乐场所布局, 从城市地理学角度入手, 考察城市消费与KTV的分布态势[4]; 三是GIS技术在空间数据表达与分析上的运用, 即通过GIS空间数据分析的方法, 阐明KTV的空间布局规律, 并揭示与人口、 道路网络和商业等空间要素的相关性。[5]可以看出, 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空间, 对KTV的研究注意到了依托空间统计、 点模式分析及网络分析等技术性操作, 以地理学方法进行实地考察, 探讨空间的规划和消费行为。 然而, KTV场所并不单纯是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 它更是一种声音的集合地, 给消费者带来特殊的感官体验。
1.1 KTV的空间构成
就其空间构成来看, KTV的组成主要包括硬件部分(点歌电脑、 触摸屏、 点歌服务器、 功放、 音响、 电视、 投影机、 灯光系统)、 软件部分(收银系统、 订房系统、 KTV管理系统、 电脑点歌系统等)和配套部分(沙发、 茶几、 地毯、 杯具类、 娱乐道具)。 通常工作人员会根据人数不同推荐不同大小的包间给顾客, 但其中构成大致不变。
正如福柯所说, 空间是任何群体生活形式的基础, 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6]13-14KTV以声音为主体, 将关注点放置于带有表演性的声线上。 不同于舞台的常规性表演着重于诠释作品内涵或传递角色情感, KTV里的声音并非借助于传统性的声音模仿, 与原唱的相似度也并非评判的标准, 甚至唱功如何在KTV中也被排除于考量的范畴之外。 它借助于独树一帜的听觉美感重新诠释作品, 每个人都可以兼具听众和演唱者两种身份, 神游在由声音和光线构成的梦幻世界, 这成为空间中声音情绪得以传达和迸发美感之所在。 KTV可谓是各种声音交织、 争斗、 自由发散的地方, 这一光线与声音交织碰撞的特殊场所, 具有半社会性的属性, 既能满足人们社交的欲望, 又能形成一个个区分, 形成较好的隐私功效。 其隔绝外界的姿态呈现出密闭与隐私性, 成为区隔于其他社会活动的独立空间。 通常情况下, KTV空间的构成有赖于以下因素:
第一, 蜂巢式的包房设计。 蜂巢式结构满足了与外界不相关的隔绝愿望, 铸造了非现实的梦幻感。 根据人数的不同, KTV的工作人员一般会推荐合适的包间给消费者, 消费者进入之后若无特殊要求, 服务人员便不会擅自入内。 包房中的硬件设备, 如沙发、 茶几、 地毯、 杯具、 娱乐道具等设备, 营造出了家的温馨感, 室内的温情脉脉与室外工作场所的冷酷无情、 休闲时的自得其乐与疲于奔命时的身不由己在这里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美丽的休闲梦境便得以展开。
第二, 优良的音响设备。 优良的音乐效果将演唱和聆听融为一炉, 既制造出现场感, 又提供了逃避现实的入口。 小型KTV使用合并式功率放大器、 音箱、 麦克风等设备制造和音, 提亮音色; 基本规模的KTV使用前级效果器和音箱、 麦克风合并使用, 制造出回旋音效果;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许多KTV通过合并式功率放大器、 音箱、 麦克风、 BSV液晶拼接屏等设备, 将声光画面融为一体。 设备的使用美化了歌者原本的声音, 同时, 无论歌唱者的声音是否动听, 都有别与现实生活和工作场所中掺杂了对话性质甚至是权力争夺的话语形态。 置身其中的消费者暂时逃离了工作、 日常生活中的繁杂与无力, 从话语的世界中走出来, 沉浸于声音的世界中。
第三, 灯光的配合使用。 除主控照明设备之外, 还有频闪灯、 声控变换灯、 霓虹灯等, 可供消费者自主选择光色, 调整整个房间的环境气氛, 为整个空间渲染上暧昧的色彩。 光影交替赋予空间不同的情感色彩, 不同的灯光图案构成视觉韵律, 配合声音的传播使得整个室内空间充满活力。 与许多音乐欣赏场所不同, KTV没有明显的表演区和休息区分界, 因此, 它的灯光设计更加综合, 既有轻松浪漫的光线配合所点歌曲视频的播放, 又有适合整体观赏休息的温馨浪漫柔光。
1.2 KTV中的声音聚合
这些特殊的空间构成使得KTV成为声音的聚合空间。 然而, KTV的特殊之处还有赖于音乐的商品化。 早在音乐诞生和发展初期, 艺术形式偏重于集“创作”“表演”“接受”三位于一体, 人们通过音乐简单直率地表现着对大自然的感受和自身情感, 与劳动、 宗教结合在一起。 每个人既是表演者, 又是接受者。 那时的音乐不存在交换价值, 也就不成其为商品。 随着17世纪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剩余产品不断积累, 阶层分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区隔与分工日益明确, 音乐也理所当然地被卷入到商品化进程中。 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标出了它的特殊性, 许多声音开始成为付费的传播活动, 进入到商品的范畴。 当原本是自主表达形式的音乐被商品浪潮所吞噬, KTV作为有偿使用音乐的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成为观照商品社会的独特表征。
声音与空间的结合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特殊空间与在此空间中的人的境况。 首先, 声音是一种物理现象, 指的是空气中振动的传播, 同时, 它又是听者的感觉, “前者是因, 后者是果”[7]1。 因此, 声音的深层概念指的并不只是单纯通过介质传播的、 能够被生物的听觉器官所感知的波动现象, 它与人感知层面的思考和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息息相关。 其次, 声音不仅有着自身的阐释学内涵, 而且还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问题, 拥有了政治内涵, 即与社会重大资源的分配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机制等息息相关[8], 如切德所说:“从主观感觉的观点分析声音要比对声音做客观的评价来得复杂。”[7]2最后, 声音的社会内涵同样值得思考。 如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贾克·阿达利指出, 音乐的命名和认可从来都不是天然如此, 而是与时代的经济、 政治连接在一起, “音乐根植所属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科技中, 同时也制造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科技”[9]23, 需要将声音现象当做文本来进行社会分析和解读。 总之, 听觉的感官历史并非从当下意识形态而来, 而是要延伸到整个社会文化机制中, 延伸到批判理论甚至文化社会学前提之外的知识资源里面, 需要思考人类文化的普遍机制, 并关系到符号学和文化人类学、 结构人类学的纵深地带。
正如列斐伏尔所强调的那样, 论及主体与空间的关系, 人类空间不仅仅是物理场所本身, 更有着独特的社会属性。 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指出, 空间关系的生产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形式, 也就是说空间的生产既包含人所创造的实体空间, 也包括置身其中的语言、 符号、 声音对空间的表征和修辞。[10]124就KTV场所而言, 独立空间、 音响、 灯光等的配合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致幻的效果, 这种“个体高度暗示性的表现形式”[11], 在消费者进入的瞬间便悄然改变着主体的精神状态。 就身处其中的人来说, 这一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顺应了当代都市人半麻痹的主体精神状态, 起到了某些麻醉的作用。 置身其中的人不用直视物质世界残酷的丛林法则, 手拿话筒的行为满足了消费者掌握自己声音主动权的想象, 也就是说, KTV这一实际存在的另类空间, 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办公楼、 门市、 教室等其他功能型空间, 是现实存在的可以满足人们梦想的地方。
2 作为声音异托邦的KTV空间
KTV场所散落在各个角落, 从鳞次栉比的市中心到远郊的城乡结合带。 虽规模不同, 但这一娱乐场所凭借投资小、 资本可控等优势, 以不同的形式顽强存活在自己所占据的空间里。 经济繁华地带有“商务式KTV”, 集娱乐、 休闲和洽谈商务于一体, 提供食品、 饮品、 中餐的同时也提供人员服务, 在收取食物费用的同时也收取包房费, 配套设施先进豪华, 往来的大多是消费能力强的群体。 普通的带有量贩式KTV, 又称为“自助式KTV”。 “量贩”一词源于日本, 即大量批发的超市。 由此引出的量贩式经营, 即平价、 健康的消费方式。 量贩式KTV娱乐场所主要以白领一族、 家庭聚会、 公司年会为消费群体, 价格比较优惠, 一般以提供卡拉OK歌唱为主, 不能播放HIGH型DISCO音乐, 以计时钟消费, 不设最低消费, 酒水食品以量贩自助式购买。 此外, 在经济相继薄弱的城市边缘地区, 也会有打着KTV招牌的门面房提供简单的音响服务设备, 供人自点自唱。
在这一行为中, 唱功好与不好不构成考核的表征, 情感的表达则更被重视。 伯格森谈到的“记忆的初始功能就是唤起全部与当前的知觉相似的过去的知觉, 是提醒我们想到这些知觉前后的知觉, 并由此向我们暗示出那个最有用的决定”[12]262。 在KTV中, 通过这样的听觉反馈, 可以补充和完善知觉的经验, 甚至做出行为上的规训。
由此, KTV便成为一种带有精神逃逸色彩的异托邦, 所有的人和情感都在这个空间中显示出别样的意义。 这一概念最早由福柯在对乌托邦作进一步延伸中提出。 如果说乌托邦是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美好设置悬念, 那么, 异托邦则指存在于此岸的某处。 1966年, 福柯在的《词与物》中首次提出异托邦(Heterotopias)的概念, 并提出“乌托邦是处于语言的经绎方向, 且是处在语言的基本维度中”[13]5。 同年, 他在建筑研究会上做了题为“另类空间”的演讲, 正式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 在他看来, 乌托邦是虚拟的空间, 异托邦则是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 但却是有争议的、 被颠倒的,“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 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 所以与乌托邦对比, 我称它们为异托邦”[14]。 也就是说, 异托邦是一个虚假的逃避现实的瞬间, 在那个瞬间, 我们以为是实现了的美丽乌托邦, 实则被围困于充满着精致怨怼的当下。 现实是当下的现实, 所以只能在某一瞬间暂时逃离, 以想象和自我麻痹的方式达成逃离的愿望。 人们沉浸在象征自身生活的想象性空间里, 所有的现实问题在此被暂时搁置, 所有难以用规整的语言来传达的话语, 都演变成包含各种意义的声音发散出去。
KTV这一由包厢、 灯光、 音响设备交织而构成的奇妙空间给予消费者暂时的满足与幻想, 在这里, 人人都可以释放自己的声音。 声音在现代社会中凸显出了独特的意义和内涵, 各种力量竞相角逐争夺声音的合法化。 这便形成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它的建立源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实现合法化而做出的各种努力, 通过设置这种公共领域, 设定一定的主题来吸引关注, 由此, 权力的争夺则是通过将其他主题、 问题和争论排挤到一边来实现, 避免形成舆论和压力。[15]93KTV作为一种声音的聚合空间, 这种既开放又封闭的结构, 一方面满足人们自娱自乐的社交趣味, 另一方面则通过充斥于其中的声音来影响人们的心理和生理状况, 由此便带有了异托邦的脱逸色彩, 满足人们暂时逃离现实的愿望, 提供了想象性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3 自恋主义的个人生活表达
对个人来说, 异托邦梦境的入口从一开始就勾连着自恋主义的文化情境。 如吉登斯所说, 人的特质、 需求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因此, 人的性格发展和心理需求从来都不只是心理学的问题, 而更应从结构与制度层面关注人的生存境遇。 现代性进程的不断加速引起人的主体性缺失, 伴随而来的是种种人的异化现象。 伴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出现了一种与推崇勤勉的禁欲主义伦理截然不同的消费伦理, 它推崇享乐主义价值观, 提倡必须立刻满足任何需求。 消费伦理和个体化进程的加速共同催生了一种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 即自恋主义。 而作为一种社会态度, 自恋“指向一种虚假的永恒冲动, 驻足在一个时间或者事物的片刻, 并以这个片刻‘抵制’变化(未来)”[16]。 KTV中声音形成的异托邦, 展现了现代人从固化逻辑、 压抑空间中逃离出来, 在自己可控的声音空间中享受个体愉悦的尝试。
将意义凝固于当下, 相信当下的从容和温馨才是全部生活该有的姿态, KTV成为自我意识的孵化地, 在这里个人的情感和诉求得以表达, 诞生出一种带有自恋主义倾向的身份认同。 关于“身份认同”(Identity)这一后现代语境中的术语, 是精神分析、 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 它兼具“身份”和“认同”两种含义:“身份”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用某些明确的、 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 来确认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 “认同”指的是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 确证自己在社会文化中意义与价值。[17]183由此, 在整体性的社会生活中, 个体试图找寻到自身从属于哪种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 接受到来自群体的情感和价值规训。 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使得置身其中的人们一方面在日常琐碎的工作环境中颠沛流离, 另一方面又在可以投入KTV空间时争分夺秒地开启自我放飞之旅。 在此, 自恋主义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缝合了梦境与现实。
第一, 通过点唱明星或流行歌曲, 实现了“他人导向型”的自我身份的认同。 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按照人口变化趋势, 将社会划分为人口高增长潜力阶段、 过渡增长阶段和初期人口减少阶段3个时期, 并将这3个时期分别对应3种不同的社会性格, 即传统导向型、 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 里斯曼指出, 在当下他人导向型人格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人们“所追求的不是个人超越特殊同侪群体或特定文化的名望, 而是追求同侪的尊敬, 或曰比尊敬更为重要的——同侪的爱戴”[18]138。 在KTV中, 演唱者用自己的声音模仿者当红歌手的声音, 将自我带入到歌曲当中, 在短暂的表现时间中寻找着自我身份。
第二, 除却鲜明的意识层面的价值崇拜, KTV的演唱中还含有深刻的无意识成分。 声音能表现出来的愿望与潜意识欲望相联系, 那些在清醒状态下不允许被表达出的潜意识动机借助众声喧哗的嘈杂, 以另一种方式曲折地传达出来。 而无论显性层面还是隐性层面, 声音所揭示的大都拘囿于个人情感体验, 以“真情演唱”来创造一个个极具感染力的瞬间, 通过这种瞬间来实现自我的存在感。 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人们关心的仅仅是如何发出恰当的声音, 把物质社会的纷繁复杂弃之脑后,“一方面是泛滥的表达, 另一方面则是无所表达, 即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一种意义, 用来掩盖说的行为的毫无意义”[19]。 声音的传输不再以表达自身政治诉求和个人愿望为目的, 而是变成了因为担心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或是自己的声音被忽视而喋喋不休。
第三, 自恋情节也可以通过噪音式的声音传达出来。 阿达利在《噪音: 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 “音乐一是有组织的噪音”[9]2, 也就是说, 所谓“音乐”是权力中心在各种“声音”选择的结果, 而非纯然的存在, 所谓“噪音”则是未被权力选中、 整理、 纳入秩序的存在, 因而显得不合理。 在日常生活中, 噪音仿佛是一种干扰接收者接受信息的信号[9]34, 无论它本身是否具有意义, 其存在仿佛更像是多余物意义, 并带有对人的侵犯性。 在声音的传输中, 发声方通过中介将信息传递给接收方, 因为耳朵这一器官是无法关闭的, 讯息的表达并不仅仅是内容本身, 也包含了抽象的形式和弦外之音。 声音的无法拒绝性还使其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内涵及意识形态诉求, 因此, 可以作为强大的治理工具,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KTV空间中常常包含噪音式的声音, 即身在其中的人们无论是否手拿话筒, 都可以肆意地发出无意义的吼叫。 无调式的噪音将KTV空间之外井然有序的声音及其所代表的社会规则击成碎片, 并通过扩音设备发出狰狞的吼叫, 发泄着规则之外的自身情绪。 噪音的使用使得人们得以从固化、 压抑中逃离出来, 在噪音空间中充分表达和享受个体政治。
4 时空压缩的社会生活隐喻
希翁在《声音》中指出:“从声学观点来看, 约定俗成被界定为语音、 音乐与噪音的三个领域间, 在基本层面相互隔离的层面上, 显然不存在非常纯粹的连续分离。”[20]223也就是说, 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 并不仅仅是由其自然特性决定的, 同样, 噪音被称之为噪音, 也与文化环境与个体生活背景息息相关。 在现代社会中, 音乐代表了有节奏的韵律美, 噪音则是一种无序或不予承认的秩序。 在KTV中, 既定的声音认同被悄然打破, 人们不在乎充斥其中的音乐是否完整有调性, 声音再也不是一种自然波动现象, 承载这一自然现象的空间也“已经被打败了, 等待它的是终极的遗忘和毁灭”[10]31。 与此同时, “任何空间都体现、包含并掩盖了社会关系”[10]31, KTV也构成了一个社会空间, 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关系。 在这其中, 人与人的交往、 情绪表达与对话也随着声音与空间的变化悄然改变, 仿佛成为当下社会的缩影。 由此, KTV空间便成为当下社会的缩影, 在虚构的异托邦梦境中, 可以窥见人们真实的社会处境及社会关系。
具体看来, 在KTV包房的付费时间不得不结束之后, 戛然而止的声音便构成了声音异托邦的最后一个音符。 无论情愿与否, 人们将不得不走出这一看似自由的空间, 收纳起自我言说的欲望, 重新小心翼翼地面对现实生活困境。 同时, KTV空间一边装扮成可以自由抒发心情、 寄托自恋情结的样子, 一边又难以自我圆说。 当消费者走进干净空旷的KTV, 打开所有的音响与灯光设备, KTV空间努力掏空这一场所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将自身塑造为可供人随意打扮和装饰的自由之地。 然而, 这一空壳本身就蕴含着无法被改变的强大因素。 一方面, 消费者无论怎样调试设备, 都必须要在既定程序下进行操作, 所谓的DIY也难以真正打破技术因素的制约, 无法脱离现实条件制约; 另一方面, KTV空间中有许多交往性的声音, 即进入KTV中并不单单是为了自我情感宣泄, 更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方式, KTV空间不过是另外一种社交场所, 与饭局、 酒局无异。 当可以容纳自我情感抒发和自恋情结的仅有的表达空间都渐渐消散之时, 声音的异托邦便再也无力维持其自身意义的完整性, 成为永远无法被填满的“小客体”[21]133, 即处于被欲望所透视的眼光中的任何普通物体。 它消弭掉了所有具体的功能, 成为一个空白地带, 主体可以在上面投射任何支撑其欲望的幻想, 同时也成为现实界留下的剩余物。 由此, KTV空间成为一个投射幻想的空间, 并不指涉任何某一个场所、 行为或关系, 而是成为永远无法满足和达到的欲望彼岸。
也就是说, 无论KTV空间本身制造出如何浪漫暧昧的异托邦梦境, 这一环境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碎裂, 成为当下社会的欲望投射。 通过时间控制空间, KTV成为当下社会时空压缩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在《后现代的状况》中, 哈维集中阐述了“时空压缩”的内涵,“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 以至于我们被迫、 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22]300。 资本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 现实生活变得更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 时间范围缩短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对付我们的空间和时间世界‘压缩’的一种势不可挡的感受”[22]300。 资本通过加快资本流动速度的方式来缩减不同城市之间的阻碍, 以便把全球资源纳入资本运作的体系里。 在KTV这一隐喻性空间中, 消费者对空间的掌控受制于时间的限定, 时间一过, 所有的梦境和暂时的解放都将化为乌有, 不管人们乐意与否, 都只能走出包间, 重新回归到社会生活中去, 落入交织着繁杂与琐碎的生活之网中。 另外, KTV包房里可以唱起不同风格、 不同曲调的歌曲, 京剧与Rap同响, 古风与歌剧并存, 也折射出在“时空压缩”的当下社会进程中, 不同艺术风格可以在短时间内几乎同时出现, 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造成了一个在文化特征上的拼贴社会。 文化的转移与拼贴造成了文化繁荣的表象, 像是一块锦绣斑斓的丝缎, 包裹的却是枯骨嶙峋的肉身, 因为拼贴与混杂无法产生新的意义, 更不用说冲击固有的符号统治体系, 只能在语言的撞击与模仿之下谋求娱乐的快感。
通过营造容纳新型社会活动空间结构, KTV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以无尽的想象力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生活的情感体验模式, 使得个体欲望有了言说的可能。 同时, KTV空间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社会的隐喻性存在, 一边提供着意图解锁新的意义空间、 实现个体言说诉求的美好愿景, 一边又无可避免地成为当下时空压缩进程中, 文化复制与拼贴的时代缩影。
5 结 语
作为声音的聚合场所, KTV可谓是各种声音交织、 争斗、 自由发散的地方, 作为颇具生命力的娱乐场所, 这一光线与声音交织碰撞的特殊场所, 具有半社会性的属性, 既能满足人们社交的欲望, 又能形成一个个区分, 形成较好的隐私功效。 同时, KTV空间既开放又封闭的结构, 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社交趣味, 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带有异托邦色彩的逃逸, 提供了想象性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 由此, 声音的异托邦展现了现代人试图逃离现实困境的尝试, 带有强烈的自恋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