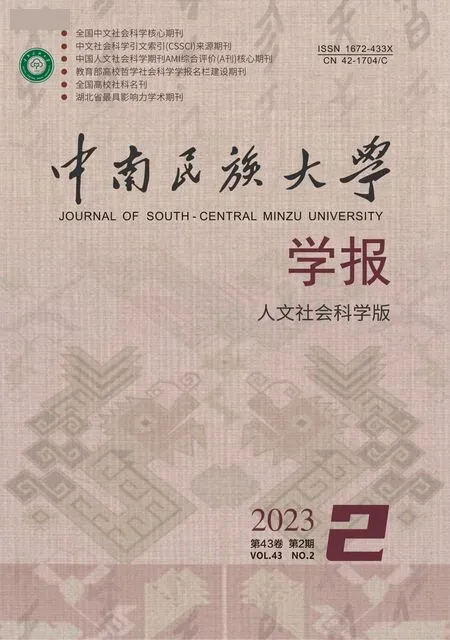兽之美者:滇象北往与贡象南来(二)
——基于历史民族学的人象伦理关系考察
郝时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三、驯象之贡:“喜看瑞物应升平,驯象南来万里程”
象牙之贡历史久远,大象活体之贡亦源远流长且规模庞大。且不论“商人服象”的时代,是指商人具备猎捕野象和役使驯象的能力,还是“贡象南来”的早期史证,至少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1],是为南地贡象南来的正史记录。由此开启了“象车,汉卤簿最在前”的皇朝仪仗“五辂”之制,以大象示威仪、壮声势的宫廷卤簿仪卫为历朝各代传承。晋武帝太康中平吴后,“南越献驯象,诏作大车驾之,以载黄门鼓吹数十人,使越人骑之。元正大会,驾象入庭”[2]。所谓“使越人骑之”,即指伴随驯象南来的藩属外邦的驭象者。由此可知,南蛮之地贡象,不仅由驯象驾驭者一路驭使入朝,而且驯象者将陪伴驯象留驻宫廷以尽饲养、训练和保障仪卫演示之责,故“贡象南来”包括了驯象者南来。
汉代传入的佛教,亦称“象教”,系指释迦牟尼弟子刻木为佛“瞻敬之,以形象教人也”[3]。此说虽与大象无关,但佛祖诞生的“乘象入胎”传说却赋予了大象与佛教的渊源关系。经文中“文殊骑狮子,普贤骑象王”之类的故事和见诸宗教造像范畴的大象图案,随着“汉时西域僧以象驮经至洛阳化为石”[4]的传说,强化着大象在皇权威仪中象征祥瑞的天命意义,以至人象互动关系中善有善报、盲人摸象、刻舟称象等故事,也在佛教典籍中国化的进程中成为流布社会、化导信众的民间知识。
大象之于人类,不属于驯化动物之列,但产象之地通过对大象个体的驯服以供役使,又十分普遍。殷商墓葬中的人、象陪葬遗骸,通常解读其人为驭象者。而驭象之技并非常人所有,故凡贡象必由驭象者调驯、驾驭而来,是为“专业人士”。佛教经典中记载了佛门“象调御”之道,如“昔者刹利顶生王有捕象师”,为其捕获野象后,王令“善调象师,汝今可速调此野象”。调象师的制象方法之一,是“使人捉钩,骑其头上”,钩其额而上下左右驯导之,使野象“除野欲念,止野疲劳,令乐村邑,习爱人间”。经“善调御、得上调御、得最上调御”之象,“可中王乘,受食王廪,称说王象”[5]。不过,佛家的驯象之道,只是对人间驯象之法的教义化渲染而已,其意在以佛法教化众生。类似故事如“憍萨罗主胜军大王,敕捕象人捕大野象,令调象者依调象法善调御之”。其后大王乘象游猎,因遇雌象群而座象“欲心炽盛,即便奔逐。象师尽术制不能回,王与象师俱被伤损”,大王追究象师之责,象师称“我能调身,不能调心”,世间“有谓佛世尊,能调众生身心诸病”,王遂“乘所调象往诣佛所,……佛即为王说甚深法”[6],云云。以示大王由此皈依佛门。
佛经中“象调御”的“捕象师”“调象师”之称,尚有众生平等之意。而人世间此等“专业人士”,虽有“挽索据脊”、驾驭庞然大物之技能,却被称之为“象奴”,如“滇人善驯象,呼象奴”[7]。宫廷驯象“使越人骑之”的越人亦然,实则因“象奴”皆为“蛮夷”之属。捕获野象以驯之,贵不在牙,故不可伤其体肤。捕象之法,通常于大象出没处沿路放置甘蔗、果蔬等物,且以驯熟之雌象为诱,引至无路可逃的封堵之处或陷阱之中,先以饥饿、后诱以食,野象“终亦狎而求饲,益狎人,乃鞭之以棰,少驯则乘而制之”。而“制之”利器即为“象钩”,通常柄长一米左右,头部接驳或嵌套金属刃钩(镢),驯者持钩骑于大象耳后颈部,击钩其痛点、反复喝令驯导[8]。史称“凡制象必以钩,交人之驯象也,正跨其颈,手执铁钩以钩其头,欲象左、钩头右,欲右钩左,欲却钩额,欲前不钩,欲象跪伏,以钩正案其脑,复重案之,痛而号鸣。……盖象之为兽也,形虽大而不胜痛,故人得以数寸之钩驯之,久久亦解人意。见乘象者来,低头跪膝,人登其颈则奋而起行”[9]。经此调御遂为驯象,“驯者,教能拜起周章,从人意也”[1]。至今人们所见马戏团、动物园、旅游点的大象“从人意也”的种种技艺表演,人们多以大象为兽中智商高者释之,孰不知其经历多少鞭挞、钩痛之驯导。
产象之地或产象之古国,“番人皆畜以服重,酋长则饬而乘之”[10]。故驯象、役象、驭象之技皆为这些地方或民族所独有。史称云南之地,“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马然,骑以出入,装载粮物,而性尤驯。又有作架于背上,两人对坐宴饮者”[11]。唐明皇时“每赐酺御楼,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动中音律”[12]的表演,实则由南蛮之地引进,即滇地“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前,设舞象。曲乐动,倡优引入一象,以金羁络首,锦襜垂身,随膝腾踏,动头摇尾,皆合节奏”[13]。这些地区更有冲锋陷阵之战象。
古罗马时代,北非迦太基的汉尼拔率几十头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与罗马军团交战的故事,是西方历史中象军之战的著名案例。但较之亚洲天竺诸土邦中“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14]之状,可谓小巫见大巫。《诸蕃志》记西印度注辇国“与西天诸国斗战,官有战象六万,皆高七八尺。战时象背立屋,载勇士,远则用箭,迎则用槊”[15]34;甚至有记载称真腊吴哥王朝强盛时,有“战象几二十万”[15]7之说。中国“古者军旅有象”[16],可上溯黄帝驾象车战蚩尤的壮举,或“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之说,亦延续到滇、桂等地所谓蛮夷驭象为阵以战的象兵传统[17]。
自汉以降,驯象之贡已成惯例,将驯象纳入宫廷卤簿仪仗、造象舆和象辇以乘坐或为先导探路(尤其是试桥梁稳固),为历朝各代所因袭。及至唐代,随着岭南地区的开发,宫廷驯象的豢养成制、数量大增,除仪卫之用亦为娱乐表演,以彰显“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18]的天下一统、四夷归心的盛世景象,而唐人颂象诗赋文学、造像绘画艺术之多也为前此所无,对此学界研究颇多[19]。其时,与驯象有关的大事,一是唐德宗时一度清明图治,“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银器勿以金饰。丁亥,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五坊鹰犬皆放之,出宫女百余人”[20],被史家赞誉为堪比禹放龙蛇,周公驱虎豹、犀象以养人的“无愧于先王”[21]之举。二是唐玄宗时安史之乱,安禄山入洛阳设宴款待诸戎胡酋长,令宫廷乐工奏乐、驱驯象拜舞以示祥瑞天降其身,然乐工雷海青拒不演奏,且“象皆怒目不动,终不肯拜。禄山怒,尽杀之”[13]的故事。驯象“宁死终不舞”的春秋大义,也为后人留下大象“遂与雷海青,垂名照千古”[22]的评说。
宋代宫廷尚象之风,除前述象牙事外,宫廷驯象对皇朝典礼仪仗、京城市井生活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是时,大象种群虽分布江南诸地,但在中原地区亦偶有流徙[23]。自宋太祖始,朝廷即专设养象所“掌调御驯象”[24],史称:“乾德五年八月,有象自岭南来,至都城外获之。其后吴越、广南、交州继献驯象四十五头,于南薰门外玉津园东北置养象所,作驯象旗。”[25]玉津园系皇家园林,饲养各类珍奇动物、栽植花果草木、耕种稼禾,是皇帝射猎观鱼、欣赏花草、观看农耕劳作的休闲之地,亦是举办宴饮、款待蕃邦贡使、他朝使臣之处,其中包括“旧例,北使到阙,玉津园射弓毕,观看驯象”[26],以彰显上朝大国威仪,北宋时契丹使臣初识驯象即在此处。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九月,“占城献驯象,能拜服,诏养于宁陵县”[25]。是时,养象所的驯象在宁陵县放养。即“每四月送象于应天府宁陵县西汴北陂放牧,九月复归。岁令玉津园布种象食茭草十五顷”[26]。即入夏至秋,驯象牧放于田野,及至入冬至春则在养象所饲料喂养。
北宋时期,不仅朝廷豢养驯象的体制趋于完善,而且驯象在卤簿仪卫阵仗中的利用及其规制也达到空前规模,甚至宫廷乐章专有《驯象》一首,以讴歌“嘉彼驯象,来归帝乡”的“神化无方”[24]。宋太祖、太宗时南郊引驾,先后以驯象十、六为阵仗,后不断完善其仪轨和规模,大驾卤簿仪仗从宋初万余人扩大到宋神宗时两万余人的规模[27],且颁行《南郊教象仪制》[25]以遵循,可谓空前绝后。《宋史》载:“宋卤簿,以象居先,设木莲花坐,金蕉盘,紫罗绣幨络脑,当胸、后鞦并设铜铃杏叶,红牦牛尾拂,跋尘。每象,南越军一人跨其上,四人引,并花脚幞头、绯绣窄衣、银带。”[24]。除大象背驮宝座、身着饰物外,跨背驭象的“南越军一人”,即是随贡象入朝的南越“象奴”。所谓南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28],宋时尤指安南王国。
宋朝多次颁定典礼仪制,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颁行的《政和五礼新仪》,系自《大唐开元礼》后中原王朝皇家礼仪颇具大成的仪典。其中卤簿先导之中道队列,“养象所押象官一员骑象,簇引三十人”[26],六象“分左右为三重,各持铁钩一人跨其上,执转光小绯旗”,在三重六象的队列前后、中间和左右,除执旗者外,还有执七宝钩二人、银钩二人、鍮石钩(黄铜矿石钩)二人、朱漆钩二人、铁钩一人行走[29],以彰显驭象利器之威。驯象仪仗不仅在皇朝卤簿序列中以象征祥瑞而位列先导,而且以其装饰华丽的庞大雄姿象征了君临天下的威仪。是故,每逢祭祀大典,卤簿仪仗之排练亦尤重于驯象队列的演习。
史称“遇大礼年,预于两月前教车象自宣德门至南熏门外往来一遭,车五乘以代五辂轻重,每车上置旗二口、鼓一面,驾以四马,挟车卫士皆紫衫帽子,车前数人击鞭。象七头前列,朱旗数十面,铜锣鼙鼓十数面,先击锣二下,鼓急应三下,执旗人紫衫帽子,每一象,则一人裹交脚幞头、紫衫,人跨其颈,手执短柄铜镢尖其刃,象有不驯,击之。象至宣德楼前,团转行步数遭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喏”[30]。大象拜起周章、通人意的行为,实则皆由驯象者以象钩驭使[9]。对中原王朝来说,举行大典、展现声势浩大的卤簿仪仗,包括了向四夷蕃邦显示礼仪之邦国家力量的效应。故典礼之际,亦安排朝贡使者、邻邦国使观礼。宋太祖朝始于玉津园款待北使宴射并观驯象的传统,也为契丹王朝效法中原卤簿之制向宋朝索要驯象埋下了伏笔。
宋仁宗在位四十余年,是北宋繁盛发展时期。期间宋辽关系总体上和平相处,礼尚往来不断,期间亦有以驯象为礼的故事。如前所述,辽之契丹似对象牙及其制品并不热衷,唯因俗而治的南面官用象牙笏。不过,辽朝却有接受域外贡象的记录。辽开泰九年(1020年)十月,“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次年三月复来请,辽帝“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2]。大食国唐季通中国,其地在波斯以西之阿拉伯地区,自公元八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开启了阿拉伯帝国的强盛时代。及至大食国贡象和亲于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疆域已裂解为众多国家,即宋人所记“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白答国,大食诸国之京师也”[9]。宋辽之际,巴格达亦相继为布韦希王朝、塞尔柱帝国所领据。其赴辽贡象和亲之大食国为哪一王朝无考,而贡象在辽地的命运亦无迹可寻。其后,则有契丹向宋朝索要驯象一事。
大食国贡象三十五年后,宋朝应允契丹索驯象一事。期间,宋廷曾遭逢驯象数量锐减的危机,“真宗天禧五年正月,玉津园养象所言:‘旧管象四十六,今止三头,望下交州,取以足数’。诏知广州段晔规度,如有,即以进来,勿须宣索”[32]卷97。宋仁宗至和二年、辽兴宗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正月,宋遣使赴辽朝贺并“馈驯象”,二月辽兴宗“召宋使钓鱼、赋诗”[31]卷20于混同江。有意思的是,驯象北上契丹留驻于哪里?若是上京临潢府(内蒙古巴林右旗林东镇),或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天义镇),两地分别处于北纬43°57′-44°00′和北纬41°17′-41°53′之间,且其时正值北方初春乍暖,气温仍在零下,宋“送契丹国驯象二”[32]卷177,是否遭逢了唐代长安宫廷驯犀越冬之际“饮冰卧霰苦蜷跼,角骨冻伤鳞甲蹜”[33]的悲剧,亦未可知。但作为驯象个体从初春渐暖的河洛之地北上风寒草原,当属中国历史时期南来贡象北上的一个奇迹。
不过,辽代文献、墓葬壁画中并未显现以驯象为仪卫的蛛丝马迹。辽代佛教大兴,佛塔林立,辽兴宗重熙十六年(1047年)所建庆州白塔[34]的砖雕图案中,胡人驯象图颇为生动[35],但这只是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传承的普遍规制。自汉始,砖雕艺术图案中的驯象题材就很丰富,且多有驭象者以象钩左右大象之状,“形成了独特的‘胡人—象’图像模式”[36]。在辽代,除佛塔图像外,其卤簿仪仗之“五辂”之制,虽“象辂行道,用之黄质象饰,馀如金辂,驾黄骝”[31]卷16,车舆仪仗唯驼马[37],旗仗亦无驯象旗。从这个意义上说,辽虽有驯象输入但未成为宫廷政治文化的要素和标志,或因豢养不佳而亡。
其时,辽兴宗以契丹“惟贵族近臣得与,一岁盛礼在此”的混同江“水上置宴钓鱼”[32]卷177,款待押送驯象而来的宋使,其礼仪非同寻常,系契丹统治者“春捺钵”[38]传统中的“卓帐冰上,凿冰取鱼”[31]卷16的“头鱼酒筵”[39]。其地在长春州(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东北三十五里的鸭子河泺[40],即今查干湖水域西南之畔[41]。当代,查干湖冬季凿冰捕鱼的盛况,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追根溯源其一方水土的渔猎文化传统,可知历史上契丹、女真等民族在中华文化多样性传承中承前启后的作用。就广义的文化而言,民间社会是传统文化形态、要素生成和传承的土壤,而某些传统为统治阶级制度化、仪式化,则会形成导引社会尊崇和规约民众认同的国家力量象征。
辽兴宗款待宋使王拱辰一行,是宋辽和平相处关系转折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时,辽兴宗对宋仁宗大有“无由一会”的遗憾,屡屡表达“朕与宋主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像”[31]卷16的愿望,甚至遣辽使耶律防“窃画圣容,曾未得其真”[42]。后遣使先“送其像及隆绪画像凡二轴,求易真宗皇帝及上御容”[43],索要驯象之请亦在其时。是故,此次虽宋朝皇帝御容未至但达“馈驯象”之愿,故辽兴宗厚待宋使。宴饮间详问宋帝家世,且每钓得鱼即亲弹琵琶劝酒,赞誉宋使王拱辰为“南朝少年状元,入翰林十五年矣”[43]。言谈中不仅解释了辽与西夏和亲等事,而且流露了对契丹皇位继承的忧虑,提醒宋使“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未得高枕也”[32]卷177,意在密切和维系辽宋和好关系。
辽兴宗求、易宋仁宗绘像和索要驯象之举,可谓前所未有。故宋廷朝议时“仁宗顾左右,皆嘿然不敢对”[44]。其后,宋仁宗虽馈驯象且应允御容之请,但至辽兴宗去世亦未获睹其容。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再度遣使以完其父志,并按宋之要求先送上自己的绘像以示辽宋侄伯之序,但宋廷朝臣仍意见不一,或称:“彼尝求驯象,可拒而不拒;尝求乐章,可与而不与,两失之矣。今横使之来,或谓其求圣像,圣像果可与哉?”[24]或议者疑契丹居心叵测,求索御容“虑有厌胜之术”[43]的施咒阴谋。但也有朝臣以“明信义,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势”论辩之,称:“契丹与中国通盟久矣,而向来宗真特于信好,自表殷勤,别有家书继以画像,圣朝纳其来意许以报之,而乃迁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辍,是则彼以推诚结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伤义,甚非中国待夷狄之术,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为辞。”[45]欧阳修“失信伤义”之论终占上峰,可见以“是非曲直”认知历史才是解读“大一统”意义的正途。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冬十月,宋“且许以御容约,因贺正旦,使置衣箧中交致焉”[43]。按大宋朝臣的论说,辽的驯象之求可拒,唯因驯象乃蛮夷外藩的职贡之物,虽有“馈”或“遗”的字眼讲究,但仍不免大宋之于契丹“以下献上”的朝贡之嫌;而契丹“向时尝借乐谱”[46]卷6则为礼乐文章之事,属天朝“有必须此以给其用者”[47]之优越,应与之。是论,实遵循春秋大义夷夏观的礼制。其实,辽兴宗要驯象并没有居高临下的索贡心态,驯象仪卫在中原王朝宫廷政治中早已是“礼乐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人嗜学中国”[48],尤其是辽兴宗崇尚儒学,推崇唐、宋礼仪,其驯象之需亦可理解为完备辽朝宫廷仪卫、以示正统的愿望[49]。这是中国历史上“四夷”之属的王朝模仿或移植、吸收或继承中原政治文化,认同大一统的常态。只是中原礼制之繁复讲究与四夷习俗之简约直白,相互难免有磨合、抵牾之处。
汉匈时期,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之说,在“五方之民”交相逐鹿中原、建立王朝的历史中,形成国号称大的正统政治传统,即“昔汤武革命,发大号以顺人。唐汉开基,因始封而建国,宜国号大宋”[50]。是故,契丹阿保机称帝立“国号大契丹”[39],后改大辽再复大契丹均属中原王朝之传统。皇朝“大”者之号,有政权“分庭”以示正统地位的倨傲含义,但并无政治“抗礼”以图另起炉灶的用心,实遵循“发大号以顺人”的汤武革命传统。大汉、大唐、大宋、大辽,及至大金、大元、大明和大清,无论何族而建,概莫如此。只是四夷之属立朝建国,多有其各自文化传统渗透其中的特点,故与中原王朝交聘关系中亦有“不为小礼以自烦”[1]的“天之骄子”随性[51],辽兴宗时期亦是如此。
辽兴宗遣使赴宋颇为频繁,甚至“不时而来”,出使名目翻新且有“今契丹使来无名” 的随意性,且其所请事端“非彼书语及,只是黠使口陈”[46]卷6。尤其是易御容、索驯象之请,更令大宋朝臣面面相觑,实无前例可循,唯感有违“华夏礼法犹在”[46]卷6的体统和尊严。辽兴宗生前虽未获宋帝绘像,但毕竟已得驯象,故其款待宋使尤重,史称“自来奉使北朝,礼遇之厚无如王拱辰”,以致数度担任遣辽史的王拱辰,亦有“南朝峭汉惟吾”[52]的自恃。其出使过程中有损大宋王朝体统的不端言行——赴辽途中“只着窄衣赴北朝饯宋选御筵,以随行京酒换去彼酒,痛饮无算,深夜喧酗,坐位失序,客主不分”,尤其是赴混同江御筵“当彼主亲弹胡琴送酒之礼,乃是损体生事辱君之甚”的行为,因事关“今后彼使来朝欲扳以为例,如何拒之”[46]卷7的大宋皇帝尊严,故受到“铁面御史”赵抃的反复弹劾,使北宋出使契丹使臣“违礼得罪”[53]的朝堂政治风波再起高潮。因涉及朝廷权臣党争,宋仁宗也只好颁诏告诫“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使臣僚,每燕会毋得过饮,其语言应接务存大体”[32]卷97了事。
契丹“头鱼酒筵”不拘中原王朝君臣礼仪之举,虽未引起宋辽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契丹主在“头鱼酒筵”上对藩属部落的倨傲态度,却引发了生女真部起兵灭辽的危机。辽天庆二年(1112年)二月,天祚帝耶律延禧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此举引起的契丹朝臣的不满和疑虑,而阿骨打亦“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31]卷6。拉开了灭辽与攻宋的序幕。金太宗天会年间,史称其“既灭辽举宋,即议礼制度,治历明时,缵以武功,述以文事,经国规摹,至是始定”[54]。所谓“始定”,实际上就是移植了北宋宫廷的一套礼仪。靖康之变,金军除根括洗劫汴京金银珠宝、齿革羽毛等资财外,将北宋王朝“礼乐文章”之属的所有载体竭尽索取,若卤簿仪仗之旗鼓车舆,文籍图书及其印版,上自天台浑仪、下及博戏之具,竭尽席卷北去。因此,金朝卤簿仪卫中的五辂之制和驯象旗,皆因袭宋制。其时,金军“须索无所忌惮,至求妓乐、珍禽、驯象之类,靡不从之”[55]。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年)六月,围攻汴京的金右副元帅完颜“宗望献所获三象”[54]卷3,即源于此。至于宗望所获驯象三,献至何处史籍无载,但养于燕京最为可能。
据《金史》记载,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熙宗幸燕,始备法驾,凡用士卒万四千五十六人”,规模亦堪称庞大。其仪仗队列中有“押马六人,象二十三人”的记载,表明有驯象仪仗。后,海陵王完颜亮弑熙宗继位,天德五年(1153年)迁都于燕京,行法驾黄麾仗一万八百二十三人,队列分八节,第一节,中道,为“象二十三人。节级二人,铜锣、七宝、石俞石、银钩各一,铁钩二,小旗十五,并服花脚幞头、青锦络缝绯衤癸衫,金镀银双鹿束带”[54]卷41。比较而言,与宋徽宗政和元年所定五礼新仪中的象队人数相同,即节级二人、击锣一人、执七宝钩和银钩各一人、鍮石钩二人、铁钩一人,执转光小绯旗十五人,共二十三人,“并服花脚幞头,绯絁防衫,金镀银双带”,区别主要在于并无“象五,中道前一,余分左右为二重,各持铁钩一人跨其上”[56]的记述。但是,金朝卤簿仪仗中曾用象,且基本按照宋朝卤簿之制陈布,则是事实。金朝卤簿仪仗之驯象,均在燕京现身,或许就是宗望从汴京掳掠的驯象三头,一直养息于燕京。只是天眷三年、天德五年距宗望献驯象,已经有14年或27年之久。当然,若其豢养得法,并非不可能。金朝仪象仅见于金熙宗和海陵王两朝,此后金朝卤簿仅存驯象旗二而无象。不过,至少今天北京人工养象的历史可推溯到金朝。
南宋偏安,朝廷卤簿仪仗因袭北宋规制,唯其规模有所缩减,其中驯象数量尤少。南宋驯象管理专设“象院,在嘉会门外。御马院养喂安南王贡至象三”[57]。每逢郊祀等礼典,“命象院教象,前导朱旗,以二金三鼓为节,各有幞头紫衣,蛮奴乘之,手执短镢,旋转跪起,悉如人意”[58]。不过,卤簿仪仗先导驯象仅为两头[57]。驯象仪仗,确有以祥瑞巨兽昭示君临天下的威势,但贡象南来之艰辛、饲养训导之耗费,亦是朝廷一大负担。皇朝域内域外之朝贡,一旦入关入境皆由各路府州县接待迎送,驯象之贡又关涉开路架桥、供给饲养、精心呵护,“象纲所过州县类有宴犒夫脚、象屋之费”[9],劳民伤财。且南宋高宗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备战之需迫切,致遣官赴大理买马。绍兴八年(1138年),大理国王遣使“以马五百及驯象”入献,宋廷“还马直,却驯象”[59],对驯象之贡兴趣索然。
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安南乞请入贡,贡物除金银珠宝外包括“驯象五头”,宋廷许之。但安南“后乞入贡,朝廷辄却之”[9]。事指“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安南献驯象。高宗曰:‘蛮夷贡方物乃其职,但朕不欲以异兽劳远人,其令帅臣告谕,自今不必以驯象入贡’”[24]。宋高宗却安南驯象之贡的重要原因,一是宋仁宗宝元初进封安南国主李德正为南平王,其子李日尊继位后“发大号”以“自称大越国”,有僭越中央王朝之嫌,故未得到天朝上国的承认。及至宋高宗时,安南国主李天祚虽系李日尊之孙,但率先向南宋朝贡,迎合了南宋草创之初重建天朝上国尊严的政治需要,即“建炎南渡,李天祚乞入贡,朝廷嘉其诚,优诏答之”[9],固绍兴二十六年允安南之贡。二是绍兴二十六年安南朝贡阵仗非凡,“所献方物甚盛,表章皆金字”,尤其是盛以金瓶的百颗珍珠,大者如茄子,中者似核桃,小者亦如枣核,实为罕见,这对遭逢靖康之变,至“二百年府库蓄积,一旦扫地尽矣”[60]的大宋王朝来说,面对蛮夷之属的安南“使者颇以所进盛多自矜”之状,大感有损天朝颜面,虑其“称大”之心未泯,故三十一年却贡驯象实有对“其国僣伪自李日尊始”[9]的政治考量。
当然,藩属邦国贡象之举并未因宋太宗“朕不欲以异兽劳远人”的利他态度而终止。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因宫中“见管驯养牙象二头,皆口齿高大,恐有不测,误大礼应奉,乞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速行计置,收置齿嫩、驯熟、雄良牙象一十头,限大礼前到”[26]。次年遂“朝旨符广西下安南买驯象”,安南国主李天祚顺势以贡象回应。此次贡物虽“似非绍兴入贡之盛”,但驯象之贡颇为隆重,“以五象进奉大礼……又以十象贺登宝位”,其意在得到南宋王朝的政治承认,诚如其贡使途中吟诗所称“此去优成赐国名”,终得到“封为安南国王”的地位和印信[9]。此次贡象十五头,亦随贡象公十五名[27]。当时,安南贡象之举在朝臣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则高宗皇帝前有却安南贡象的诏令,二来贡象之途的种种弊端也引起朝臣和地方大吏的不满,引发了以南来贡象“物或违性”,即违背自然生态的机理与“诚心爱民”的理学思想争论[49]。其时,湖北安抚使刘珙针对“安南贡象,所过发夫除道,毁屋庐,数十州骚然”之弊,“奏曰:象之用于郊祀,不见于经,驱而远之,则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国之疲民,困于远夷之野兽,岂仁圣之所为哉!”[24]刘珙以“周公驱象”之典,论列了皇朝象仪之制“不见于经”的违礼,直指劳民伤财之弊端。
是故,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诏却安南所贡象,以其无用而烦民”[24],却之。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就兵部申乞收买驯象一事(1)出处不明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3年)安南贡象15头且应符合宋廷所需“齿嫩、驯熟、雄良牙象”,而淳熙十六年(1189年),即16年后兵部再乞奏收买驯象,似表明宫廷驯象数量已不敷卤簿仪典之用,应属驯象豢养累年死亡减员所致。再次表示“见设象所,经从骚扰不可言,不如且已。将来郊祀,不用亦可”[26]。然而,虽偶有帝王以唐德宗“纵驯象、出宫女”为清明之鉴,朝臣亦反复谏言、屡陈其弊:“夫象大而无用,且又伤人,受贡远致,其害甚广,治道建屋、储粮卫送、校人求索、无所不至,其轻人而贵畜甚矣”[21];但对皇朝统治者来说,大象的祥瑞象征和仪卫威势,又是挥之不去的天佑心理。因此,对取向伐金雪耻的宋宁宗赵扩而言,驯象仪卫仍具有壮大宋王朝声势的意义。宋宁宗“庆元六年十月、嘉泰二年九月、开禧元年八月真里富国贡瑞象”[25],显然与此相关。开禧元年(1205年),即“开禧北伐”之始。
贡象南来,清人郭嵩焘诗云:“喜看瑞物应升平,驯象南来万里程。”[61]其路途遥远,梯山航海。域外贡象之路线,学人已有详考[62]。或经由陆路,“顷年贡象治路,略容象行,谓之象路”[63],历时耗费,期间不免“象实能浮,象奴所至水津,索舟以载,得钱然后驱以济”[9]的明白勒索;或经由海路,亦费时艰难。如开禧元年真里富国“所进象,令沿海制置司计置津发赴行在”,其历时长达数月,期间不仅照例“支给米面酒,馆待番官”,而且也难以避免“所进象在海遭风大浪摆,损四脚,兼伏热不食水草身死”[26]的后果。即便如此,朝廷也少不了“厚往薄来以驭四裔”[64]的赏赉赐封。至于养象、典礼之费则开销无算。
如同北宋,南宋朝廷若筹备大典祭祀,亦“预于两月前教习车象。其车每日往来,历试于太庙前,至丽正门,回车辂院一次”[57]。是时,内修司“修饰郊坛及绞缚青城斋殿等屋凡数百间,悉覆以苇席、护以青布,并差官兵修筑泥路,自太庙至泰禋门、又自嘉会门至丽正门计九里三百二十步,皆以潮沙填筑其平如席,以便五辂之往来。……又以车五乘压之以铁,多至万斤与辂轻重适等,以观疾徐倾侧之势,至前一月进呈,谓之闪试”[65]。所谓“闪试”,即预演。其演练用时之长、耗费之巨令人侧目。从宋元之际的一首诗文,大可体会贡象南来之耗费以及驯象仪卫的奢靡,“半年传舍劳供亿,德色中朝动搢绅。粉饰太平焉用此,只消黄犊一犁春”[66]。
宋朝贡象及驯象仪卫之利用,是唐代以后的一个高峰,并对辽、金模仿、移植中原王朝礼制产生了影响。但辽、金两朝,一则没有贡象南来的政治地理条件,二来所获几头驯象付诸仪典或为一时想象、或为昙花一现。南宋因袭北宋之制,亦图重振皇朝威仪,但毕竟靖康重创、偏安一隅且始终受到北方的压力,其贡象南来和驯象利用均呈式微之势。元朝大一统,平滇征缅等一系列南征活动,不乏与这些地区土邦象兵对阵和目睹大象之民间利用的经历,是为中央王朝大一统历史上深入产象地区之最,以至贡象南来再度形成高潮,并在卤簿驯象仪仗的仪典利用之外,开创了独特的皇帝乘舆驭象巡幸两京之制,及至对明清两代宫廷造大辂驾象以乘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