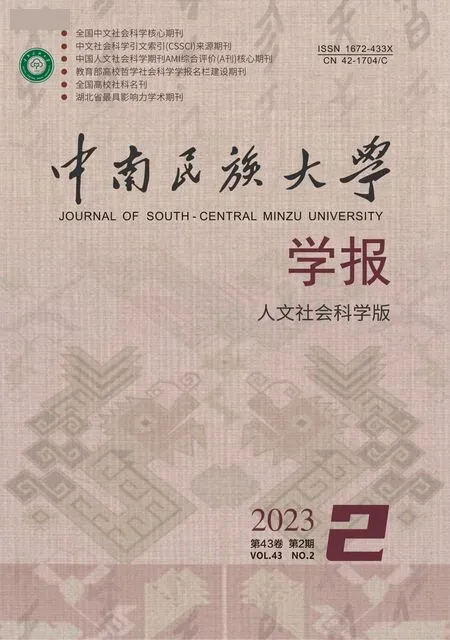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与海外传播
谢丹凌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8)
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当代民族文学不仅呈现地方性的文学经验,也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这些作品“敞亮了被遮蔽的文学地理,让‘世界’的图景更加完整”[1]。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发展,数十部当代民族文学英译本相继面世,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呈现出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引起了海外译者与出版媒介的广泛关注,也激发了汉学家们极大的研究热情。
笔者以1949年以来的民族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从译本—译介—接受三方面入手,立足1950-2020年间民族文学的英译成果,探析当代民族文学书写在海外传播接受的整体生态样貌。在研究方法上,以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数据库资源为基础,辅以海内外出版社的图书出版目录,着重梳理、举列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成果,探析译者、出版媒介在民族文学海外传播中的角色及价值。同时,运用谷歌图书、Worldcat、Jstor等数据库搜集整理学者专著与论文,分析总结英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民族文学的异域传播与接受提供参照与启示。
一、丰富与多元: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出版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当代文学的整体传播态势,民族文学的英译进程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组织性与连续性。从阿来的小说到吉狄马加的诗歌,从藏族到彝族、满族、回族、蒙古族等,民族文学英译本数量从少到多,题材从单一到丰富,向海外呈现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景观,其中尤以小说与诗歌的成果最为丰硕。
(一)小说英译成果
小说体裁在当代民族文学对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在当代民族文学的外译中,藏族小说尤受关注。藏族作家群体大多关注民间与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在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关注和对历史的体悟中探讨传统文化与现实冲突的深刻话题。作为第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作品的英译成果在少数民族作家中最为丰硕。截至2020年,他共出版了四部英译本,分别是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短篇小说合集《西藏的灵魂》,被誉为“第一藏族英雄史诗”[2]的《格萨尔王》和村庄史诗小说《空山》(第一部)。他的《阿古顿巴》《血脉》《三只虫草》《脱粒机》等刊载于英语期刊上,《鱼》和《草原的风》被收入英语作品集。这些小说创作让阿来无可争议地成为藏族地区政治、历史、文化叙事的主要代言人,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评论、推介阿来的作品。另一位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则在20世纪80年代就创造了一系列以西藏文化为主题的作品。1992年“熊猫丛书”推出了他的小说英译本《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2011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扎西达娃小说选:英汉对照》,其中收录了《归途小夜曲》《西藏,隐秘岁月》等作品。除了单译本外,《中国文学》和美国Manoa杂志都曾刊载扎西达娃的短篇英译小说。2001年美国独立学术出版商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出版的Sky Burials, Prayer Wheels, and Wind Horses收录了扎西达娃的《丧钟为谁而鸣》《风马之耀》和《归途小夜曲》,这些作品大多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20世纪历史中藏族传统命运与现代文明的碰撞。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蒙古族作家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随后,郭雪波、玛拉沁夫等作家创作的具有蒙古草原特色的作品英译本相继出版。回族作家张承志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英译本《黑骏马》,而早在1981年,他的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就被收录于作品集Prize-Winning Stories from China(1978-1979)。此后,《北方的河》和《九座宫殿》等作品陆续刊录于英语期刊或由西方学者编选的英语作品集。近年来,一批满族作家纷纷亮相世界文学舞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于近年来陆续推出的《血之罪》和《性之罪》等犯罪悬疑小说英译本,成为中国当代通俗文学海外传播的亮点。劳马2015年推出了自己的英译作品集《个别人》,叶广芩的《山地故事》也于2017年由英国独立出版商Valley Press出版。这些小说超越了民族地域性,向世界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文学话语样态。
(二)诗歌英译成果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诗人陆续在异域舞台亮相,其中西南地区的彝族诗人获得的关注最多。吉狄马加近十年来陆续出版了8部诗集译本(包括汉英对照本,其中1部为重版):《彝族》(2007)、《火焰与词语》(2013)、《黑色狂想曲》(2014)、《群山的影子》(2014)、《身份》(2016)、《我,雪豹》(2016)、《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以及《火焰与词语》(2018)(1)2013年版《火焰与词语》译者为梅丹理,2018年版译者为徐贞敏。。吉狄马加的诗集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性思考,向世界读者展现了彝族厚重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在他的诗作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少数民族独有的信念体系的风景,而这一风景的窗户对于当下的世界是开放的。”[3]201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收录了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全球20个国家诗人、学者对吉狄马加的研究文章,足见其在世界诗坛的影响力。
坚持用彝语诺苏话和汉语两种语言创作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汉名罗庆春)2005年开始在Manoa特刊上发表作品,他的英译诗集《虎迹:阿库乌雾的诺苏、汉诗选》于2006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版,这是彝族历史上首部彝英对照诗集,呈现了跨民族跨文化的精神旅程,受到西方诗坛和人类学学者的关注。此后,阿库乌雾陆续受到英美诗界的邀请,前往海外多所著名大学朗诵自己的诗作。Language for A New Century: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Beyond和The Poem Behind the Poem: Translating Asian Poetry等作品选都收录了阿库乌雾的诗歌。他的部分作品在英语文学圈受到热烈关注,在世界多元文化场域里广泛流通。
当代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从零星到系统,从单一到多元,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文学视域下展现了中国民族书写的活力与生机。随着海外知名度的不断提升,中国民族作家搭建了一座通往全球文学空间的文化桥梁,为今后更多民族文学进入西方学者与大众读者的视野开辟了先路。
二、“发现”与推介:当代民族文学英译本的译者与出版媒介
拥有象征资本是民族文学进入海外文化场域的前提。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定义中,象征资本指“被接受、且被承认为合法化的资本形式”[4], 具体表现为文学作品在异域文化语境中的声誉、名望和认知度等隐形资产。权威汉学家、官方机构与出版媒介在当代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中扮演了发现与推介的角色,共同促进了民族文学在异域文化场域中象征资本的生成与累积。
(一)译者与译介模式
权威汉学家群体是当代中国民族文学的海外“发现”者,他们赋予了作品文本及原作者象征资本。在阿来的四部英译本中,《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由被誉为“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5]的葛浩文与其夫人林丽君翻译。在对《尘埃落定》的译介中,葛浩文的译文既保留异域传奇的神秘因素,又消解了读者进入陌生文化语境的阅读焦虑。“熊猫丛书”的专家译者戴乃迭、沙博理、宽大卫和弗莱明等也都曾参与少数民族作品的英译。美国译者徐穆实长期关注中国民族题材的作品,自2013年英译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后,近年来将目光投向民族文学,陆续翻译了次仁罗布的《放生羊》、郭雪波小说《蒙古里亚》的节选,希望通过译本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此外,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加拿大学者石岱崙、美国学者赫伯特·拜特都曾翻译过藏族作家的小说。
在民族诗歌英译方面,两位美国学者成果比较卓著。美国“黑山学派”诗人梅丹理积极参与当代民族诗歌的翻译研究,英译了吉狄马加等诗人的作品。他忠实于原诗的语言表达,采用罗马注音方法标记彝语的语音系统,尽可能还原诗歌里的民族文化意蕴,以呈现“中国人的多元存在模式”[6]。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民俗学者马克·本德尔英译了阿库乌雾的诗歌,希冀将古老的彝族文化之魂推向世界。这些汉学家在民族文学与海外读者之间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中国民族文学蕴含着更鲜明、复杂的文化与地域信息,因此中外学者协作翻译是常见的译介模式。新世纪以来,由政府发起的中国文学“走出去”项目中涉及的民族文学作品,基本都采用了中外合译或中方译外方审的合作形式。葛浩文和林丽君翻译了阿来的两部长篇小说。这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西藏的灵魂》则由美国南俄勒冈大学退休教授葛凯伦和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泽平合译,译本“从语言、语篇和文体风格上再现了一个诗意盎然的‘藏地’……带领读者进入一个空灵神秘的文学空间”[7]。徐穆实与中国译者刘俊合译了获得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创作“骏马奖”的作品——《时间悄悄的嘴脸》,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试图将维吾尔族文化较完整地融汇于译文中。此外,少数民族诗人也积极参与到自己诗歌的英译与海外推介中,阿库乌雾与马克·本德尔合作,将自己的诗歌译成英语。总之,“一中一外”的译介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有效保证了译文的传播质量。
(二)出版媒介
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出版大多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传播行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海外传播的重要窗口,中国文学出版社发行的“熊猫丛书”率先译介了几部民族文学作品,包括郭雪波的《沙狼》、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张承志的《黑骏马》等,这些作品大多由国内译者翻译,部分译本甚至没有署名。以对外宣传为宗旨的“熊猫丛书”在翻译文本时因需与对外宣传的愿景保持一致,有些译本中的遣词造句时常受到学者的批评,传播效果不太理想。
新世纪以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发起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资助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作家协会启动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都相继推出了多部民族文学英译本,尤以小说为主。仅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为例,受资助的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英译本有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紫青稞》、严英秀的《纸飞机》、亮炯·朗萨的《布隆德誓言》、格绒追美的《隐藏的脸》、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达真的《康巴:一部藏人的心灵史诗》;土家族作家叶梅的《歌棒》;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僧舞》;满族作家钟晶晶的小说集《第三个人》。这些作品大多由国内中译出版社于2015-2016年出版,但依据美国阅读网站Goodreads和亚马逊购书评论数据,这些译本在海外大众读者中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
与国内出版社相比,英语世界出版媒介的推广更有利于民族文学海外象征资本的生成与累积,但这些海外出版主体大多是学术型出版商,面向的受众群体相对单一。海外出版社往往将少数民族作品编选入集,供高校课堂教学和学者研究,其面向的流通渠道为图书馆和专业学术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民族文学在海外商业市场的销路。新世纪初,海外学术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两部西藏文学选集,分别是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Song of the Snow Lion: New Writings from Tibet和美国出版商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推出的Sky Burials, Prayer Wheels, and Wind Horses。后者不仅收录了扎西达娃、央珍、阿来等几位藏族作家作品,还涵盖了格非、马原等汉族作家书写的与西藏有关的叙事文学。由美国著名汉学家陶忘机等编译的Indigenous Writers of Taiwan: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Essays and Poems于2005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选集收录了9部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获得2006年“北加州图书奖”,并成为海外高校课堂的文学选读教材。
总体而言,当代民族文学的海外推介以国内出版机构为主、西方学术出版商为辅。尽管这种传播行为更具系统性和组织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了民族文学在海外的接受。
三、阐释与偏见:当代民族文学的海外接受
在中国政府、权威汉学家和出版界的多重助力下,民族文学英译数量连年增加,但这些译本在海外大众读者群中却少有人问津。截至2020年,只有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全球的馆藏数据达到600家以上。老舍《茶馆》(1980年版)的馆藏量是260家,1956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龙须沟》是180家(2)主要资料来源:“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数据库下的WORLDCAT书目数据库。。除此之外,80%以上的译本只有零星几家图书馆上架,在欧美书店难觅踪影,大部分作品在读者阅读网站上也鲜有评论。民族文学在西方大众读者群中无法收获“共鸣感”或“同理心”,除了传播媒介、渠道等方面的因素,其原因或还在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理解鸿沟。然而,相较于西方大众读者的“冷眼”,一些海外学者对中国民族文学研究却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如葛浩文、梅丹理、马克·本德尔、罗鹏、蔡元丰等,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既是译者(推介者)又是研究者(专业受众)。换言之,当代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相当程度上依靠这些身兼译者、研究者、教师等多重身份的汉学家们,通过他们不遗余力地译介与研究,民族文学开始在西方知识界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本部分主要基于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来探讨当代民族文学的海外接受情况。
(一)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1.地域特色与国族想象。作为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理和文化空间,民族文学中呈现的地域特色与边陲文化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在西方人眼中,‘西方—东方—东方的少数民族’这样的双重投射无疑具备其对中国的独特期待”[8],中国的民族地区成为迢远的、被想象的“他者”。与英译传播的整体状况相似:“海外学者对我国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藏族文学。”[9]阿来所引领的藏地叙事的传奇色彩、国族想象与异域传统历来为学者关注。西方重要文学类杂志如Booklist、Kirkus Reviews、The Bookseller、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和Publishers Weekly都曾介绍过阿来的作品和创作背景,强调了阿来小说的文化意义与异域色彩。World Literature Today和School Library Journal都发表过关于阿来作品的专业书评,探讨其文本中所蕴含的生态文化与现代性视野下的民族历史。加拿大藏学研究者谭·戈伦夫称赞《尘埃落定》为“一个文化的传说,一个久远无法往复的时代的传说”[10]。华人学者蔡元丰认为阿来的叙述策略强化了空间维度,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创立了一种“共时史学”[11]。他在专著Remapping the Past: Fictions of History in Deng's China中也辟专章讨论了扎西达娃、阿来等作家笔下的藏区描写,并从文本分析引向民族身份和国家政治等一系列问题。巴拉诺维奇对《尘埃落定》的潜在声音进行挖掘与探索,还原小说叙述视角的丰富内涵,认为作品描绘了一幅包含历史风俗、族群伦理、价值信仰和性观念在内的西藏社会文化全景[12]。新西兰华人学者王一燕探讨了阿来如何将藏地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书写方式,从而将藏族村落置于国家文化政治的叙述图景中。她也着重分析了《尘埃落定》,认为作品折射出藏区变迁中的家庭与个人命运,“令世界深刻地认知、理解和尊重藏地的独特性”[13]。在文学表现形式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茨仁夏加在Sky Burials, Prayer Wheels, and Wind Horses的“前言”部分提到“藏族作家偏向现实主义,汉族作家青睐魔幻现实主义”, 肯定了藏族作家笔下还原了真实可触的、与土地命脉相连的民族记忆,从而构建民族认同[14]。在“Where is Tibet in World Literature”一文中,斯蒂芬·文图里诺从语言文化层面讨论“藏文—汉语”的转换过程,探析阿来文本中的多重文化含义。还有学者比较了以张承志为代表的回族作家与藏族作家的异同,认为前者作为穆斯林传统的继承者创造了“虚构的、非历史的、陌生化的”[15]民族叙事,后者则一直与他们的土地血脉相连,着力展现多重文化交融的西藏,从而在世界舞台上发出独特的民族之音。
此外,一些海外学者将藏族文学置于民族史、人类学、宗教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如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克里格的Tibet, Self and the Tibetan Diaspora: Voices of Difference一书在社会学的框架下呈现了藏族文学对个体生命的探索。不少西方学者编选少数民族文选的目的在于呈现异域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如Sky Burials, Prayer Wheels, and Wind Horses“主要通过故事展现西藏与西藏人民历史状况与现实命运”,具有“纯粹的地缘政治视角”[16]。杜克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Modern Tibeta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中将西藏文学与民族历史、社会变革相联系,将文本的讨论置于社会史研究的视域中。
2. 民族认同与“自我”身份。受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民族认同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海外学者以民族性与“民族诗学”为视角,探讨民族诗歌的现代性特征和文本审美内涵。“民族诗学”运动兴起于北美,丹尼斯·泰德洛克、德尔·海墨思和加里·斯奈德等民俗家、诗人纷纷号召将第三世界的口头诗歌传统引入西方大众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凉山彝族诗人在国际诗坛不断引发关注。梅丹理将这一族群与“为英语注入了巨大活力的爱尔兰作家群”相比拟,认为前者书写了对自然和土地的强烈情感,呈现了强烈的生态意识,表达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向度与深度。同时,彝族诗人往往将边缘身份和情感结构视为一种叙述与抒情的策略,“将少数族裔的身份意识贯穿在自我的创作中,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取材”[17]。 由此,民族认同与“自我”身份成为联结中西文化、打破国族文学之间彼此隔绝的关键语词。
在彝族诗人群体中,吉狄马加“作为一个来自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伟大灵魂,用诗歌承担起民族和民族精神与外部现实世界交流的使命”[3]。梅丹理称许吉狄马加为“世界诗人”,认为他以自己深刻的民族书写与世界伟大的诗人、传统进行对话,创造了诗歌里的独特隐喻与情感联结。在英译本译者序与“Son of the Nuosu Muse: The Poet Jidi Majia”等文章中,梅丹理以对《易经》符号系统的理解阐释吉狄马加的诗歌意象,探析诗歌内部蕴藏的自然言语节奏和诗性声音。马克·本德尔在《印度东北与中国西南的民族志诗歌》中对比了不同民族的诗歌,从跨国的视角探寻文化互动与民族特性。此外,西南民族诗歌里涉及的寓言、传说、故事、民歌和民间表演,长者、猎人、牧民和青年男女的形象,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等话题也多为海外学者所关注。
海外学者在中国民族本土书写、民族叙事与身份建构等方面研究成果丰硕,这些学术阐释仿佛一面面“棱镜”,有助于进一步呈现中国民族文学复杂、丰富的面向,以克服海外研究中的视差偏见。
(二)海外学者的视域偏见
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曾用“自治”一词表示文学空间的独立性,“民族文学空间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的地位取决于其相对的自治程度,而这种地位又决定了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空间所获得的资本”[18]。“自治度”较高的文学世界可以确立自身的准则,形成独立的资本交流方式,避免因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被刻板化甚至扭曲化解读。相比之外,尚处于世界文学等级“边缘”的中国文学在海外一直难逃意识形态偏见。
1.文学审美价值被政治阐释所遮蔽。海外学者和大众读者对中国民族文学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正来源于其预设的政治解读立场。中国文学一直无法规避“东方主义”的凝视,东方主义“从一个毫无批评意识的本质主义立场出发来处理多元、动态而复杂的人类现实”[19],使“异质性”的民族文学文本的丰富性与审美性被高高在上的、带有政治隐喻的解读遮蔽,而具有热切的本土社会批判和现实关怀的作品也在海外接受的视域中往往被拆解为一种夸张的反叛姿态。民族文学作品中确有对来自其他民族的“文化误读”的反击和自我心声的抒写,如藏族作家央珍在谈及创作时曾谈道:“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的‘净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单一的‘落后’和‘野蛮’之地。”[20]但是,海外学者由此夸大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如认为《尘埃落定》借怀旧之名反映了“对种族本质主义的抵抗情绪”[12],“二少爷(傻子)对自我的认知困境预示着藏族在与汉族的纠葛中迷失自我”[11]235。 此类阐释无视并消解了原文本中汉藏民族之间的情谊和新政权给藏区未来带来的希望,极大地歪曲了历史和现实。
2.套用时髦的西方理论术语随意曲解文本内涵。在海外视域的偏见中,民族文学里的“反抗”色彩往往被歪曲为充满符号性的“后殖民”书写策略,或被认为具有某种地缘政治学意味,从而迅速跌入他者化与奇观化的阐释怪圈。有些海外学者套用生态文学批评,将《空山》中“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中落在了后面的民族的处境”曲解为西藏传统民俗和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21]。还有些海外学者过度使用时兴的“族裔”理论工具研究中国民族文学。在西方学术界,“族裔”概念常常与“种族”概念并置,论及白人中心主义与少数族裔身份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而西方关于“民族”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逐步形成了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民族”是基于共同文化信仰之上、具有心理凝聚力的共同体,各民族既保持民族自身认同,又保持对国家认同。由此,有些海外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不甚了解,对中国的实际国情视而不见,其在理论层面的生搬硬套、凌空蹈虚与中国本土话语方式、传统资源、具体环境的脱节与错位,难免形成西方主流话语霸权下的阐释偏见和穿凿附会。
尽管“多民族、多语种同构同辉的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个性的文学生态和最为重要的美学特征,正逐步被世界文坛认可和尊重”[22],但民族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成效与我国政府和出版社的积极推介还存在一定的落差。长期以来,由于文化差异、社会及历史等因素形成的理解与交流障碍,一些西方受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消极认知长期存在。部分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夸大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以西方意识形态异化中国的少数民族形象,导致一些西方读者对中国民族历史、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产生误解,给中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对策与建议:当代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启示
根据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空间理论”,世界文学空间由中心和边缘(或半边缘)构成。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操控的世界文学版图中,一直徘徊于边缘地带。新世纪以来,民族文学英译数量逐年增加,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中外译者与出版媒介的助力下,越来越多民族文学走出国门,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与此同时,在“跨文化”“跨语际”与“文本旅行”的视野下,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民族文学的阐释带来了视角转换,为海外受众发掘了独特而丰富的异域文学遗产。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整体现状来看,民族文学在译介版图上仍位处边缘。海外译介与接受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几位作家,许多经典的文学译本在海外大众读者群中还未摆脱知名度低的窘境。真正健全的、有持续消费潜力的读者市场,应该是学者与大众共同发挥作用的市场,因此民族文学如何打破交流障碍、突破当下的交流困境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议题。在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框架下,我们有必要重新探索民族文学与世界范围内其他民族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方式,反思当代民族文学对外传播的路径与方法,从而预判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未来发展的可能。
一是选题策划。多民族作家将文化多样性与民俗经验融入文学创作中,呈现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学话语样态,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学在主题、内容、风格与手法方面不断创新,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组织译介民族文学作品时应系统规划选题,有计划地将传播优秀民族文化、书写现实经验、彰显中华民族认同的当代优秀作品推介到海外,正向构建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民族文学形象,为当代民族文学“走出去”承担应尽的文化使命。
二是翻译机制。文学翻译本身就是跨文化旅行,而民族文学往往含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语码,在翻译中难免产生误读、变化和“噪音”。海外译者的译文更为“地道”,符合异域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些译者在英美文化场域中的象征资本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推进民族文本在海外的传播。但是,由于不同文化间的隔阂与偏见,有些海外译者在译介过程中随意删改、曲解文本意涵的现象时有发生。民族文学的英译不仅要跨越语言障碍,更要跨越文化的藩篱,对自身文化环境的熟稔恰恰是本民族译者不容忽略的优势。因此,鼓励民族作家参与到自己作品的译介中,提倡中外译者合译或中方译、外方审的合作译介模式。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是提升民族文学的翻译质量与传播效果的重要策略。
三是学术话语。面对海外学者在对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时流露出的偏见,如何在国际学术空间发出中国声音、建立中国民族文学批评范式显得十分必要。“文化多元主义既强调不同文化话语的平等,也允诺主流与边缘的协商共荣。”[23]换言之,在将民族文学的海外研究作为反观当代文学的审美经验、建构文学研究国际化视野的同时,中国学术研究应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当代民族文学的审美表达与整体成就,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在彰显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中,为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中国阐释”。
总之,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历程中,既应还原当代民族文学的审美内涵,又要不断完善海外传播的机制,方能向世界传递完整、生动、真实的中国形象。诚然,文学的海外传播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扩容”,更是精神层面的交流与融合。一方面,提升民族文学在海外的知名度并非一蹴而就,培养志趣相投的域外读者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既要有世界性也要有民族性,长期坚守自身的独特风格和价值立场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随着跨文化的族群互动日益频繁,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相互碰撞、交相辉映,期待今后有更多葆有自身文化特色、坚守自我主体性的中国民族文学走向海外,在世界文学空间邂逅异域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