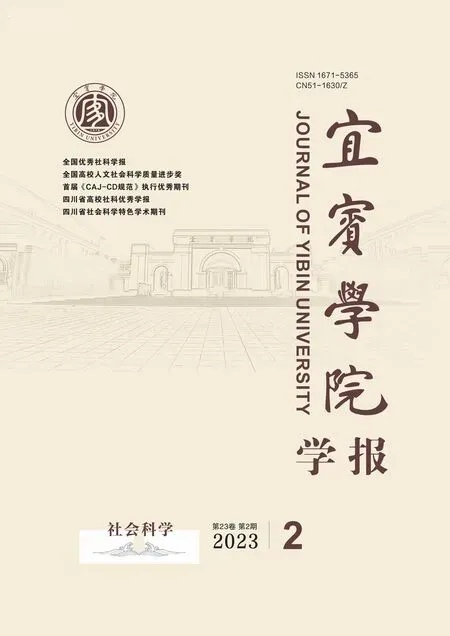论亚里士多德道德目的中的理性因素
邬洁静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研究中,关于德性行动的正确目的如何获得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①:非理智主义者认为目的的正确是由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来保障的,伦理德性(ἠθικὴ ἀρετὴ)不仅为行动提供目的,而且保证目的的正确,而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与此相反,理智主义者则认为灵魂的有理性的部分为行动提供目的,并且保证目的的正确。
在非理智主义者看来,理智主义者的这一主张所面对的最大理论困难就是如何处理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到伦理德性给予德性行动以目的的文本。因为亚里士多德在NEVI. 13. 1144a7-9;NEVI. 13. 1145a3-6;NEVII. 8. 1151a15-19;EEII.11.1227b23-26 明确指出伦理德性确定一个正确的目的。从而,这些文本就似乎给理智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理智主义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回应。莫斯(Jessica Moss)在她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休谟主义者吗》一文中对这些回应作了总结,认为理智主义者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传统解释,它承认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但是否认目的是由伦理德性提供的。第二种则承认伦理德性在目的的给予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坚持认为伦理德性之所以能够确定目的,仅仅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智的状态[1]207。本文认为,莫斯的这一概括基本上是准确的,而从理智主义者的上述应对策略中也能够看出,正是对灵魂的有理性部分如何给予德性行动以目的并且确保目的的正确的具体理解上,理智主义者存在不同的理解。他们的第一种策略通过否认伦理德性可以给予目的,主张目的是由理智(νοῦς)或是实践智慧(φρόνησις)等理智德性直接给予的。他们的第二种策略则指出伦理德性是理性的状态,从而将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德性给予目的的主张进一步理解为,正是因为理性的关系才使得伦理德性能够确定目的并保证目的的正确②。
本文立足于理智主义者的上述两条辩护路径,论证理性在道德目的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首先认为,尽管德性行动的最初目的是由伦理德性所给予的,但是伦理德性既不是灵魂的一种能力,也不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感受,它是一种品质,而且是一种通过习惯化而形成的好的品质,从而,简单地说伦理德性为行动提供目的就会是缺少分析的,而在对伦理德性的分析中我们总能够指出其在确定目的方面的理性因素。其次,尽管亚里士多德多次指出伦理德性确定目的,但要注意的是伦理德性并不能完全自足地提供这一目的,仅仅提供的是一最初目的。本文将对上述主张展开说明,前两部分针对第一点,第三部分则针对第二点。第一,本文将说明伦理德性仅仅是非理性部分的德性,它自身并非是非理性的。第二,本文将澄清伦理德性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听从理性的德性,而这也体现在其形成过程中。第三,本文将阐明道德目的的确立与实现需要实践智慧的参与,因为伦理德性所给予的仅仅是最初的目的,它需要实践智慧的确认才能真正被当作目的,并且需要实践智慧展开具体的思虑(βουλεύσις)过程,最终使得目的实现。显然,在这整个过程中,理性贯穿始终。
一、目的的正确不由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保证
对非理智主义者而言,非理性的伦理德性不仅能够确定德性行动的目的,同时也能够保证目的的正确。例如福滕博(William W.Fortenbaugh)所提出的,一个德性的行动既需要伦理德性,也离不开实践智慧。但伦理德性作为一种品质能够使有德性的人追求正确的目的,实践智慧具有的仅仅是作为手段实现目的的作用[2]192。而另一位非理智主义者莫斯对福滕博的这一主张提出了质疑,她认为这实际上是错误地将亚里士多德与休谟或是其它情感主义者相等同。
莫斯与理智主义者一样注意到这一主张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至少有以下四点冲突:第一,与休谟主张欲望是理性的主人不同,亚里士多德所明确指出的是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要听从理性(NEI. 13,III. 12,以及VII. 6);第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希求(βούλησις)作为一种用于确定目的的欲求自身即是理性的(NEIII.4),这与情感主义者所认为的目的的正确来自于非理性部分截然不同;第三,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与工具性理性——聪明——明确地区分开来,因而,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理智德性并非仅仅是手段性的;第四,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没有实践智慧,就没有伦理德性,有了实践智慧,就有了所有伦理德性(NEVI.13),这表明实践智慧对伦理德性的重要性。正如莫斯所指出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在目的的确立方面起着一个完全非休谟式的作用,一方面,实践智慧将德性所给予的目的视为目的并理解这一目的是什么;另一方面,实践智慧在思考如何实现目的时并非仅仅是工具性的[3]222-223。
但是,莫斯却同样坚持认为目的的正确是因为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即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而且伦理德性给予目的并使得目的正确。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可以给这一主张以文本支持,而之所以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莫斯则从如下两点做出辩护:第一,亚里士多德多次在文本中根据灵魂的二分将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分别对应于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与灵魂中的理性部分。第二,伦理德性是行动与情感的习惯化的产物。
尽管莫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段落(NEVI. 13. 1144a7-9;NEVI. 13. 1145a3-6;NEVII. 8.1151a15-19;EEII. 11. 1227b23-26)可以表明伦理德性给予目的并且保证目的的正确,但是,她基于伦理德性是非理性部分的德性,从而得出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进而主张目的的正确是因为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这样的推论则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
A1.如果非理性的部分也可以称为理性的话,那么理性的部分也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理性严格地在其中,另一部分能够像对父亲般的遵从理性。
德性也要按照灵魂的不同来加以区别。我们认为,其中的一部分是理智上的德性,另一大部分是伦理上的德性[4]3745。(NEI.13.1103a1-a6)
A2.既然理智德性涉及理性,那么,它们就属于拥有理性而主宰灵魂的那个灵魂中的理性部分;相反,伦理德性则属于那个在本性上听从具有理性的部分的非理性部分[4]4145。 (EEII. 1.1220a8-11)③
这两个文本都是关于两种德性的区分,根据A1、A2 可知,亚里士多德按照灵魂的划分区分了两种德性,即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并且指出前者属于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后者属于灵魂中的理性部分。莫斯同其它非理智主义者一样根据这一点主张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本文认为非理智主义者关于上述文本的这一理解是不正确的。上述文本仅仅表明的是,亚里士多德根据灵魂中理性部分与非理性部分的区分对德性做出了二分,即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其中伦理德性是非理性部分的德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进一步指出伦理德性本身是非理性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根据伦理德性是非理性部分的德性,就推出这个部分的德性必然是非理性的。
在这里指出“非理性部分的德性”与“非理性”这两个表述在理解上的不同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非理智主义者直接忽略了这一点。理智德性作为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德性,它与理性的关联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在理智德性方面,确认这一点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对于理智德性来说,它作为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德性,由于直接与思维相关,从而它作为灵魂的一种德性状态就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是对于伦理德性来说,尽管它属于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但是需要理性的规范。事实上,A1 和A2 都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A2 更是直接指出了理性的主导作用,即伦理德性作为非理性部分的德性是听从理性的。因此,我们绝不能由于伦理德性是非理性部分的德性便认为伦理德性与理性没有关系,从而简单地说它就是非理性的。任何试图从伦理德性是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的德性这一论断推出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这一主张的做法,都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和阐明的。
上述分析指出尽管伦理德性是关于灵魂中非理性部分,即欲求部分的德性,但它并不是非理性的。因此尽管亚里士多德确实指出了伦理德性保证目的的正确,但是目的的正确也不能因此被认为是由非理性的部分得以保障的。事实上,只要对伦理德性进行分析就可以知道其在确保目的的正确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因为理性,这正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二、灵魂中的理性部分确保目的的正确
非理智主义者还根据上述第二点,即通过伦理德性是由习惯形成的这一点来继续辩护“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这一观点。但是这一辩护同样是失败的,因为它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习惯化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但是,习惯化并不是这样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是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适应理性规范的过程”[5]195。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1-3 章(NEII. 1. 1103b21-3;NEII. 2. 1103b29-31;NEII. 2. 1104a27-9;NEII. 3. 1104b19-21)展现了行动和品质之间的关系,伦理德性就是通过重复做符合德性的行动而形成的,因而习惯化就是重复做符合德性的行动的过程。而在随后的第4 章,亚里士多德指出“我们通过做符合德性的行动从而变得具有德性”这一习惯化过程有一个问题,即除非我们已经具有德性了,否则我们如何能够做德性的行动,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还没有具有德性的时候怎么能够做符合德性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对此指出:
合乎德性的行动并不因它们具有某种性质就认为是以德性的方式,如公正的或节制的方式做的。(除了具有某种性质)行动者还必须是出于某种状态的。首先,他必须有知识。其次,他必须是经过决定而那样做,并且是因那行动自身之故而决定那样行动。第三,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稳定、不可变的品质而那样行动的。而拥有技艺,那么除了知这一点外,另外两条都不需要。而如果说到有德性,知则没有什么要紧,这另外的两条却极其重要,这种状态是重复做公正的和节制的行动的结果[4]3753。(NEII.4.1105a30-b5)
亚里士多德这里将德性行动区分为以两种方式被实施,一种是仅仅做了德性行动,一种是以德性的方式,也就是像具有德性的人那样做了德性行动,后者不仅要求行动是合乎德性的,而且要求行动者在做德性行动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具有知识,二是要出于行动自身而决定(προαίρεσις),三是要求出于稳定的德性品质。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解决方式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学习者如何能够通过做与具有德性的人不一样的方式做德性行动从而最终形成伦理德性?正如布劳迪(Sarah Broadie)所质疑的“亚里士多德越是强调不同,越发使得他人怀疑仅仅做这些符合德性的行动能够形成伦理德性”[5]194。因此为了解释上述三个条件的出现,习惯化的机械论解释必须被抛弃。
其中对于道德目的来说,学习者如何在这种德性行动的重复中学会为了行动自身,即为了高贵(καλόν)而行动。这里要将学习者区分为两种进行说明,一是普通学习者,一是具有自然德性的学习者。本文为了展现理性在道德目的设定中的作用以具有自然德性的学习者进行说明,因为自然德性与严格的伦理德性其区别在于后者具有实践智慧,而前者没有,因而能够更清晰地展现理性的作用。具有自然德性的人,因为他们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或者几种德性品质,例如有些人具有勇敢的自然德性,有些人具有节制的自然德性,而有些人同时具有这两种或者其它的品质状态,因而他们总是倾向于去做德性的事,可以说他们总是具有正确的道德目的,但是这一目的是模糊的。因为具有自然德性的行动者缺少实践智慧,事实上他们都不具备某一具体德性的知识,因而无法通过实践理性得出具体境况下什么有助于德性的实现,如此道德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甚至这一道德目的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可以说具有自然德性的学习者的道德目的的形成与实现完全是理性作用的结果。这里关于具有自然德性的人所具有的道德目的其形成与实现完全是理性作用的结果,而这正是习惯化的部分过程。
上文指出伦理德性为德性行动提供了正确的目的,但是,只要对伦理德性本身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伦理德性并不表现在根据一个人完全自然的感受为道德行动提供目的,而是表现在让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通过习惯化的方式,即依据理性进行调整之后为德性行动提供目的。同时,伦理德性自身能够保证目的的正确也不是单纯地由它自身内部的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来保障的,却恰恰是要通过灵魂的有理性的部分。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对德性的划分中所指出的,伦理德性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听从理性部分的德性(NEI 13. 1103a1-a5,EEII. 1. 1220a8-11)。前面所引的几段文本就能证明这一点④。
仔细考察A1还可知,伦理德性是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但却是听从理性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指出,若将非理性的部分也称为是理性,那么理性就有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严格意义上拥有理性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原先的非理性的部分,这一部分能够像听从父亲那样听从理性,即在听从理性的意义上拥有理性的部分。A2更直接指出“伦理的德性则属于那个虽无理性,但本性上能追随具有理性的部分的非理性部分。”这里我们需要简略介绍一下亚里士多德对于灵魂的理性与非理性部分的区分,以明确不同德性尤其是伦理德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将作为非理性部分的伦理德性界定为听从理性的德性的前述主张提供依据。亚里士多德指出,灵魂的动物性部分尽管是无理性的,却在听从理性的意义上分有理性。这样灵魂的理性部分被分为两个部分,分有理性的欲求部分和严格具有理性的部分。亚里士多德正是根据灵魂的划分区分出两种德性,即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伦理德性作为与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相对的德性表现为非理性部分完全合于理性,此时,灵魂中的动物性部分不像自制或是不能自制者那样与理性存在任何冲突,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即欲望所追求的与理性所规定的是一致的。因此,根据上述两段文本可以得出,伦理德性是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听从理性的德性,这一点体现在习惯化过程中。这样,我们就能够非常合理地推断出,德性行动中目的的正确是因为灵魂中的理性部分。
如果说这里仅仅只是推论,不足以表明伦理德性给予正确的目的是因为理性的话,那么对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德性的定义的考察则可以更为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德性是一种与决定相关的品质,它作为相对于我们的中道,受到理性的规定,是像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会决定做的那样[4]3757-3758。(NEII. 6.1107a1-3)
据此,我们可以从“决定”的理性特点以及“中道”与实践智慧的理性特点出发,来论证伦理德性中的理智要素。
首先,德性“是一种具有决定能力的品质”。因为作为思虑的结果的决定必定是理性的,因此作为决定状态的德性也是理性的。莫斯企图否定这一点,她认为尽管亚里士多德确实将决定和伦理德性联系起来,即指出伦理德性“是一种具有决定能力的品质”,但是,这一表述并没有表明决定与伦理德性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莫斯认为不能根据决定是理性的这一论断推出伦理德性是理性的。因为莫斯主张当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德性“是一种具有决定能力的品质”时,他仅仅想要表达的是伦理德性为思虑和决定提供了目的[1]210。那么根据这一解读,决定与伦理德性的关系就仅仅是德性给予“决定”目的的这样一个关系,即将决定从伦理德性自身的构成之中排除出去,从而也就排除了伦理德性自身的理性内容,以此表明德性依旧是非理性的。但是这一解释不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的定义。因为就“德性是一种关于决定的品质状态”而言,亚里士多德恰恰是通过决定来说明德性。此外,在NEII. 4. 1105a28-35 以及NEII. 5. 1106a2,亚里士多德也同样指出伦理德性必然包含有决定。而莫斯的解释却将二者的关系简单化了,即在这二者的关系中,只有德性给予“决定”目的的这样一个关系,若是二者的关系仅限于此,那么说德性是一种“决定”状态就显得非常奇怪,而且也使得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主张,即“决定与德性有最紧密的关系,并且比行为更能判断一个人的品质”(NEIII.2.1111b5-6)变得无法理解。因此,莫斯的这一解释完全不符合亚里士多德文本所产生的基本理解。我们依旧可以根据德性与决定的关系来表明伦理德性所具有的理智要素。
其次,亚里士多德指出,伦理德性是“相对于我们的中道”,而中道“受到理性的规定,像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会决定做的那样”。这里,伦理德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更是被明确了。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伦理德性的定义可知,伦理德性与中道相关;同时中道由理性所规定,这也就是说只有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才能命中中道。因而,没有实践智慧,一个人无法命中中道,也就没有伦理德性。我们当然不否认一个没有实践智慧的人能够做到在某一个行动中偶然地命中中道。但是对于德性来说,这里的命中不能是偶然的,必须是稳定的。以勇敢为例,一个人必须是在任何需要表现勇敢的时候都能够表现勇敢才可以说他具有勇敢这一德性。但是,若是没有实践智慧,一个人只能在这些情况下想要表现勇敢,却无法做到勇敢,因为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命中中道需要实践智慧。也就是说对中道的命中是需要实践智慧的,一个没有实践智慧的人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命中中道,因此也就没有勇敢、节制、慷慨等任何一个伦理德性,更谈不上拥有整体的伦理德性。正如亚里士多德自己所明确指出的,离开了实践智慧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善(NEVI.13.1144b31-32)。因此,伦理德性不能离开实践智慧而存在,因为只有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才能命中中道。如此即便道德目的是由伦理德性所给予的,但是对伦理德性的进一步分析却表明理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三、实践智慧对目的的确认与思虑
前文首先基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二分的讨论,批判并否定了非理智主义者所主张的“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观点,并指出伦理德性的形成过程即习惯化是一个听从理性的过程,从而得出目的及其正确性的来源并不在于非理性部分。随后,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定义的描述表明伦理德性不能离开实践智慧,而实践智慧本身并不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德性,恰恰是理性部分的重要环节。这样的话,即使同样面对非理智主义者所依据的那些亚里士多德文本,我们依然可以在承认伦理德性提供目的并保证目的正确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推论出行动目的的正确还是要依据理性,而且这一目的的确认与实现都需要实践智慧。
在道德目的如何获得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的下述文本对非理智主义者所持有的目的是由伦理德性所给予的这一主张构成威胁。
如果思虑得好是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人的特点,好的思虑就是对于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的正确的思虑,这就是实践智慧的真判断[4]3873-3874。(NEVI.9.1142a31-33)
这一文本指出,好的思虑是正确导向这一目的的思虑,实践智慧是对此的真判断。理智主义者与非理智主义者对这一文中的“这”有着不同的理解。前者认为这里的“这”指的是“目的”,而非理智主义者认为“这”指的是对达到目的的东西的判断。根据对希腊语原文的考察,从语法的就近原则出发,这一文本是支持理智主义的解读的。如此这一文本无疑成为目的是由实践智慧所给予的这一主张的有力证据。但是,这一文本是否能作出上述理智主义的理解仍然有争议。莫斯甚至认为可以在接受上述理智主义者的解读状况下仍然对这一文本做出非理智立场的解读,她指出这里的“判断”(ὑπόλψίς,apprehend)有一个理解上的分歧,既可以是对目的本身的认识,也可以是对目的的假设,莫斯认为这里要采取后一种理解,如此实践智慧就仍然是对目的内容的思虑,也就是对目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目的的方式的思考,并非对目的本身进行确认[3]231。
如上所述,理智主义者与非理智主义者对这一文本的解释充满分歧。而且,即便我们依照理智主义的方式对这一文本进行解读,即表明实践智慧与目的之间的给予与被给予的关系,我们也同样不能忽略那些表明目的是由伦理德性所给予的文本,因为亚里士多德确实在多处文本中清楚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即便目的是由伦理德性给予的,这一目的同样还需要实践智慧得以确定,因为思虑与目的的关系是明确的,而一旦进行思虑就表明目的已经被理性所肯定,否则对这一目的的具体思虑是无法展开的。伦理德性所给予的仅仅是一最初目的,正如前文关于自然德性的讨论中所指出的,具有德性的人希求高贵,会在具体情境中以高贵为目的,但是将这一对象真正作为目的,即作为实践活动的目的需要实践智慧的确认,如此实践智慧才开始针对这一目的进行具体的思虑。这一点也是非理智主义者莫斯所明确承认的。也就是说通过实践智慧,目的被理性地认定为目的。正因此,本文将伦理德性所给予的目的称为最初目的,将经实践智慧确认的目的称为目的。而实践智慧一旦确认目的,就需要思考目的是什么。正如索拉布其所指出的,实践智慧“使得一个行动者根据他对一般的善生活的概念,从而认识到慷慨对他的要求,或者更一般地说,在特定状况下,德性和高贵对他有什么要求,并指导他采取相应的行动”[6]113。
随后,一个人才开始运用实践智慧进行具体的思虑、决定并且相应地行动。当说思虑或者决定的仅仅是通向目的的事物时,并不能认为思虑的仅仅是手段。正如厄文(T. H. Irwin)通过对τὰ πρὸς τὸ τέλος(“趋向于目的的东西”)这个短语的细致说明所指出的,思虑的对象不是仅仅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其本身就有助于构成目的,也就是说,思虑的对象是目的的组成部分甚至全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虑与目的相关[7]570-571。而且,思虑的对象在其它情况下也可以成为目的,这并非主张思虑的对象是目的,仅仅否定的是非理性主义者所主张的思虑的对象是手段这一论断。因为尽管思虑都是基于某一目的进行的,但是思虑的对象,亦即结果同样可以作为目的再被思虑,以此类推。可以说,除却最初目的之外,其它所有的目的都是由思虑而来的。正如安纳斯(Julia Annas)所指出的幸福一开始完全是一个形式的概念,而非实质的[8]366。也就是说它仅仅是名字,而没有任何实质涵义,因此需要理性思考进行填充。但是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说思虑的对象是目的,因为在被思虑之时,它们仅仅是作为趋向目的的那个东西,而非目的本身,当这个东西被作为目的时,思虑的对象则是趋向这个东西的事物。总之,思虑在其思虑对象作为目的的构成与目的的具体化意义上与目的相关。
综上所述,最初目的需要经实践智慧确认成为实践活动的目的;随后通过实践智慧对这一目的进行具体地思虑并作出决定。道德目的的最终实现需要在实践智慧规定下的具体思虑的参与,通过思虑才将一个具体的道德目的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予以贯彻,正是通过具体的思虑,目的被现实化了,并且最终通过决定而与行动相关联。
结语
本文首先通过对非理性部分的德性与非理性在概念上的区分,指出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仅仅是伦理德性是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的德性,而非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接着通过对习惯化过程的分析,否定了非理智主义者试图通过表明习惯化是一个完全非理性的过程来为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这一观点进行辩护的可能性。如此非理智主义者试图通过引用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二分的文本来表明伦理德性是非理性的这一主张的论证被证明是失败的。尽管亚里士多德确实指出了伦理德性保证目的的正确,但是目的的正确也不能因此被认为是由非理性的部分得以保障的,因为伦理德性的形成需要理性。随后,本文致力于在接受非理智主义者所主张的伦理德性给予最初目的这一论断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伦理德性在给予目的方面的理性因素,即伦理德性是非理性部分听从理性的德性,并且伦理德性与决定这一理性活动密不可分,而且,道德目的在确立及其实现过程中又受到实践智慧的规定。因此,本文认为道德目的正确是因为灵魂中的理性部分。
但是,本文仅仅指出习惯化过程需要理性,但是并没有将理性在习惯化过程中的作用,即非理性部分到底是如何听从理性部分并最终形成伦理德性的过程充分地说明清楚;其次,本文也未对自然德性与严格的伦理德性的不同以及它们与实践智慧的关系做出清楚地阐明;再次,本文也并未对实践智慧在确定与实现道德目的方面的作用展开细致地说明;最后,本文还将道德目的限制在具有伦理德性的人所给出的正确的目的这一前提下,从而没有在一个更一般的理性行动者的道德目的的意义上展开讨论,这些都是需进一步思考的。
注释:
① 关于这种非理智主义的理解途径的起源与发展,索拉比在《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的作用》一文中(RICHARD SORABJI,Aristotle on the Role of Intellect in Virtue.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源于New Series,1973-1974 年第 74期,第107-129 页),将其追溯到沃尔特(J. WALTER)和福滕博。而莫斯在《德性使得目的正确》一文(JESSICA MOSS.Virtue Makes the Goal Right:Virtue and Phronesis in Aristotle’s Ethics,源于Phronesis, 2011 年第 56 期,第 204-261 页)中则更指出策勒(E.Zeller)同这一理解的关系。
② 采取前一种策略的有洛伦茨、马吉亚和索拉比。洛伦茨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伦理德性”(HENDRIC LORENZ,Virtue of Character i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源于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2009 年第37 期,第177-212 页)一文中以及马吉亚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功能、直觉与目的”(ROOPEN MAJITHIA,Function,Intuition and Ends in Aristotle’s Ethics,源于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2006 年第 2 期,第 187-200 页)一文中都认为希求是理性的,而目的来自于希求,因而目的是理性的,其正确性当然也是因为灵魂中的理性部分;索拉比在《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的作用》一文中认为伦理德性给予目的,但是目的的正确是由实践智慧保证的,因而目的的正确在于理性的部分。采取后一种策略的有库珀,他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和人类善》(J. M. COOPER,Reason and Human Good in Aristotle,出版于 Indianapolis 的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年,第 58-71 页)一书中指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正确的最高目的是由理智直觉所把握的,这就是一个人所知道的,这一直觉通过辩证法得到,是理性的。它既不是通过思虑而来的,也不是通过其它科学的第一原则推论而来。
③ 本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引文翻译自巴恩斯(J.BARNES)所编《亚里士多德全集》,并标注Bekker(贝克尔)页码。《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参照了廖深白译注本(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欧德莫伦理学》参照了徐开来译本(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徐开来译,苗立田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 可 参 看 伯 恩 耶 特“ 亚 里 士 多 德 论 如 何 变 得 善 ”(M. F. BURNYEAT,Aristotle on Learning to Be Good,源 于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由 A.O.RORTY 所编,出版于 Berkeley 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年)与谢尔曼的《伦理德性的结构》(NANCY SHERMAN.The Fabric of Character:Aristotle’s Theory of Virtue,出版于 Oxford 的 Clarendon Press,1989年),二者都认为理性在习惯化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作用,并且对此做了具体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