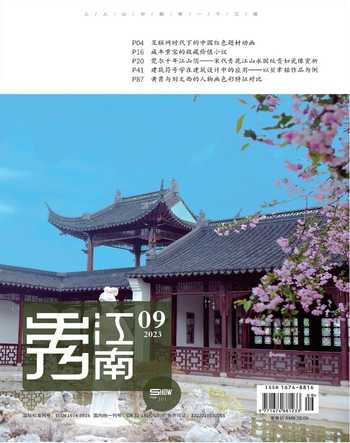《群学肄言》译序和译余赘语中的严复翻译思想


严复在翻译近代西学思想时所总结的“信达雅”是其翻译西方作品的理论基础,但严复在译作《群学肄言》时,体现其翻译观的“译《群学肄言》序”和“译余赘语”对西学思想解读的个人选择与语义附会在翻译思想上有违“信达雅”的初衷。我们不能武断地否认其背离“信达雅”的初衷,因为翻译实践的偏差是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特殊性和自身因素造成的,对所曲解部分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严复所欲所求以及严复在翻译过程中为何选择此种方式。
郭沫若先生认为“信达雅”属于译事三难,彻底理解和运用“信达雅”的翻译理论是不可能的,只能不断地向其贴近。三者的核心在于“信”,尊重所译文章的本意是实现文章通顺明白与雅俗共赏的基础,而做到“信”是翻译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文章无信而不立,这需要翻译者具备过硬的双语翻译能力以及掌握大量所译领域的理论知识。
《群学肄言》的翻译观
严复西学思想的构建
了解一个译者对其相关译作领域思想理论的掌握情况,有助于理解译者的翻译行为以及所呈现的翻译结果。严复接受达尔文和斯宾塞相关思想的时间在甲午战后,此时的严复并不能辨别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而往往将其混为一谈,但是在思想倾向上,严复更加倾向于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由于对两种思想的区分模糊,严复认为自然是进化的,社会亦然,“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欧洲自有民生以来,无此作也”。然而,在社会进化的具体方式上,严复对斯宾塞在其相关著作中所秉持的“任天而治”思想持不认可态度,反而倾向于赫胥黎的立场。严复在《天演论》的序言中提道:“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此为严复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思想的杂糅形成了严复所秉持的社会进化论。
杂糅的西学思想构建影响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所译文本的客观认知,致使严复在翻译之初就形成了一定的信息筛选。翻译实践与“信达雅”的偏差不仅是因为没有践行翻译理论,其深层逻辑是翻译之初严复在西学思想上的认知“偏见”导致的。
译序与赘语部分的译作思想构建
基于杂糅的西学思想构建,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将其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进行会通,以求通达。但是由于词义本身的意涵不同,在翻译实践中出现了附会的现象。在“译《群学肄言》序”中,严复认为“群学”的方法论与《尚书》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是一致的。将传统史学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意涵等同于群学的意涵,实属不妥。《尚书正义》对其的阐释为“正义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靡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为民兴利除害,使不匮乏,故所以阜财。‘阜财谓财丰大也。‘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尚书正义》的阐释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要求统治者品行端正、以身作则,不浪费、不奢侈,物尽其用,厚待生灵万物。这属于高度理论概括,没有方法论指导,反观严复对其译著中两个重要名词“群学”和“肄言”的定义:“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以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从中可以看出,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是理论与方法的集合体,即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和群体,从而更好地统治国家。此外,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所需要的研究工具已经出现了学科分类,在此背景下,通过科学的社会学理论分析社会现象,将各类学科作为研究工具分析不同领域的社会问题。此时的中国并无如此科学的学科分类,史学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学科领域十分庞杂,且受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我国对社会群体等基层的研究甚少,更多致力于研究上层政治,得到“治世”之经验以启迪后世之君。因此,这种贴合在表象和本质上都是存在偏颇的。
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严复讲到“独有其一,为政家所同,而其病于群学为尤深者,徒知主治者之为变因,而不受治者之为国命,治乱兴衰之故,求之于宪章法令者多,而察之于民品风俗者少,其违在宥之戒,代大匠斫,而为者败之”。这段译群并没有在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中有所体现,此处增译的目的是证明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与传统政治理论思想在内核上具有一致性,即通过斯宾塞的社会理论体系可以更好地分析和探究中国社会的走向。
“社会”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词汇之一,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中将其定义为“社会可以说不过是由若干个人所组成的一个集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其成员整体的特性,以与其成员个人的特性相区别,社會是有机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整合,由小变大,由简单到复杂……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管理机构的分工越来越细”。斯宾塞在此处给予“社会”的定义是基于社会研究本身,并未过多论述社会与国家和政权的关系。
严复将“社会”译为“群”是稳妥的,在解释词义时却将其与荀子的思想相结合。在“译余赘语”中,严复以荀子的“民生有群”为切入点立论,说明社会属于有“法”之群,进而将这种有“法”之群的结合体称为“国家”。接着,严复尝试论述西方对“社会”的定义与中国古代对“社会”的定义是一致的,即“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卪,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从中不难看出,与斯宾塞的定义相比,严复更希望从传统意义上的统治者视角解读社会,其本质是将此作为统治者的治理工具。同时,在借会荀子的相关思想上,严复认为荀子的“群”与西方思想所认为的“社会”概念不一致,且严复将荀子所言之“群”直接等同于西方所述的国家概念。不论从《社会学研究》原著还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上看,都是有失真实性的。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而言,严复更在意的是怎样用社会学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
严复的欲与求
严复对斯宾塞本人及其社会学理论十分推崇,他想要的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寻到与其理论相似之处并加以解读和推广。这种附会的本意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与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不相契合,而是严复多方考量的决定。严复想借此论证所谓的“西体”本质上仍是“中体”,西方的理论思想本质上仍是中国古人的发现而已,从而为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正名。同时,他希望借斯宾塞之“口”将自己的“强国保种”思想传递给中国的知识分子。诚然,严复的这种附会存在“偏袒”之意,其本质目的是传播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开化民智,强国保种。这恰恰是严复所求,吴汝纶在为《天演论》所作的序言中说道:“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与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器效名……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渝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严复所求,足见一斑。
如此译作之因
混淆的西学理论
对于一个翻译家而言,专业性不仅表现在双语的互译水平上,还表现在对所译领域理论思想的把握能力上。虽然严复十分推崇斯宾塞,其在“译《群学肄言》序”中大力称赞斯宾塞的原著《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学思想“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但是其混淆了赫胥黎、达尔文以及斯宾塞的自然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思想。严复对斯宾塞的“任天而治”思想并不认可,而是赞同赫胥黎的立场,并与荀子的“人定胜天”理论结合提出了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十六字箴言。这种混淆间接影响了严复的翻译实践,对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便缺失了辩证的考究。
功利和“私心”的考量
纵观严复的所有译作,功利性可谓贯穿其中,无论是其在哲学世界观上对中西哲学观念的异质区别“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还是其对传统中国“本末”观念的批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均体现了浓厚的功利性色彩,这种功利性色彩在当时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译者对所译文章的基本判斷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何严复会以一种两面三刀的方式翻译《群学肄言》。正如黄克武先生评价严复“受传统影响,又想批判传统追求现代,可是传统的烙印却挥之不去”,严复的一生一直处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矛盾漩涡之中,在漩涡中生存的严复从矛盾中寻找调和,即借译著之口传播西学思想,通过附会的方式为变法正名,希望以此拯救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在这种“调和”的指导下,其余所有思想与实践都以其为中心进行运作。严复的翻译思想及其实践并不是两个对立面,而是包容在严复“调和”思想下的两个有机部分。
作者简介:张涛旆,男,汉族,河南汝州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以翻译《沉默的大多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