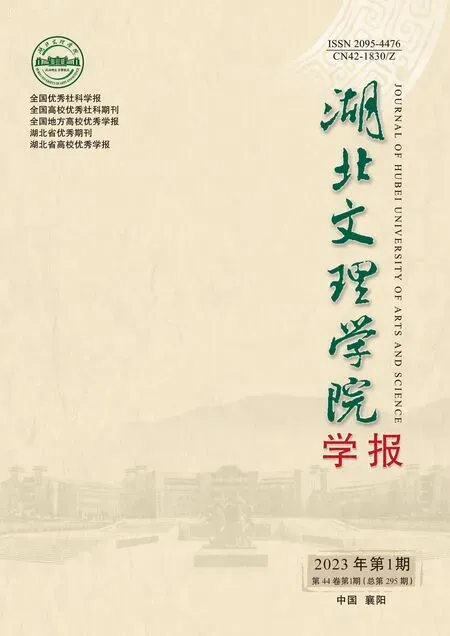朱光潜20世纪30年代的诗学活动及诗学观
邓慧茹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朱光潜作为20世纪30年代批评家中的代表人物,将其绝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研究诗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诗歌的实践活动:组织举办读诗会、在杂志中积极发表诗歌批评和理论文章、撰写“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诗论》[1]。他的文学活动不仅充分表现了他对于新诗发展的热切关注,而且鲜明地展现了其新鲜而独特的诗学观念,更是为新诗寻找出路的积极有益尝试。
一、诗学实践
成熟的诗歌理论体系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时间不间断的尝试和努力,朱光潜于1931年左右写成《诗论》初稿标志着其构建诗歌理论的初步尝试,其后,他又不断对《诗论》进行修改和完善,裨补阙漏,充实自己的诗学体系。除此之外,他积极开展读诗会,探索诗歌在形式上的特点,探究新诗在诵读上的可能性,主动参与诗学刊物的创办和编辑,在《大公报·文艺·诗特刊》和《文学杂志》中发表大量文章对诗歌的种种问题进行探讨。
(一)读诗会
1933年,朱光潜被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聘请为西语系教授,其居住地在北平后门内的慈慧殿三号,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适应,他在这里主持举办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文学沙龙——读诗会,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文学交流空间。参与读诗会的成员大多是北平各大高校的师生,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中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2]247朱自清在日记中记载:“赴朱光潜宅参加诵诗会、听顾颉刚作‘吴歌’讲演。在座有周作人、沈从文、林徽因、卞之琳、李素英、徐芳等。”[3]这些学者们虽有学缘、地缘和私谊上的联系,但将其汇集起来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其相近的文学观和审美趣味,因物质条件的富足加上身处自由平等气氛的高校环境之中,他们保持着一种超然自持的文学态度,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崇尚文学的自由性和审美性,他们与传统士大夫相似的身份使得其对于古典主义情有独钟,重视文学的趣味性,遵守“适度和谐”的审美原则,加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也接受过系统化、理论化的西方文化教育,常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将两者加以对照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
与当时京派文人聚集的另一个文学沙龙——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相比,朱光潜的“读诗会”主题显得更为明确。诗歌在众多京派文人眼里是文学之冠,朱光潜曾说“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4]349梁宗岱说“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是我们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5]他们对于诗歌的发展给予很大的关注,当时只重视内容而忽视形式的自由诗已经显现出自身的弊病,出于文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积极地为诗歌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将视线聚焦到诗的形式上,更为具体的来说,读诗会的主题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2]247经过长时间的诵读实验,沈从文得出结论,“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2]248朱光潜同样认为新诗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形式,人们错误地将新诗所提倡的“自由”认为是绝对的自由,脱离格律束缚的完全解放,诗人在创作时可以放任情感的宣泄,不加以节制,殊不知西方诗所谓的“自由”只不过一种相对的自由,在原有的规律上加以改变。对于西方自由诗的误解,再加上“新诗人在运用语言的形式技巧方面,向我们的丰富悠远的传统里学习的太少。”[6]导致新诗缺乏该有的韵律美,不再那么引人入胜。
通过朱光潜开办读诗会的背景、主题和内容来看,他对于“自由诗”完全忽视诗歌的语言节奏、音乐格律十分不满,想要借助读诗会的形式探索新诗格律化的新出路,表达出对于诗歌形式的重视。
(二)《大公报·文艺·诗特刊》和《文学杂志》
“《诗特刊》是受到读诗会影响,并在多位诗人严肃且热切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所衍生出来的刊物。”[7]它由慈慧殿三号的另外一位主人——梁宗岱所主编,集合了梁宗岱、朱光潜、叶公超、罗念生、林徽因、卞之琳等一大批重要的诗人、诗歌批评家和理论家。作为读诗会的主持者和刊物的重要参与者,朱光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从生理学观点谈诗的“气势”与“神韵”》和《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前者强调节奏对于诗歌的重要意义,“我们读诗时,在受诗的情趣浸润之先,往往已直接地受音调节奏的影响。音调节奏便是传染情趣的媒介”[4]369,音调节奏相较情趣意象先一步给读诗人带来愉悦感。后者则提纲挈领地讲述了他对于诗歌好坏问题的见解以及如何欣赏诗的问题,首先,他认为“诗的好坏应该同时从两方面见出。第一,它的意境是否新鲜美妙?第二,它的语言是否恰好传达它的意境?”[8]459充满个人趣味、新鲜独特的意境是诗的精华,而“语言在文法上应该能通顺,应该能恰好传达心里所要说的意思。”[8]460是将诗讲得“清楚明白”的必要条件。其次,由于每个人的天资秉性、性情修养、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对于诗的喜好不同,但无论是“明白清楚”还是“迷离隐约”的诗歌都各有存在的理由,要想真正地成为具有纯正趣味的鉴赏者,要“睁开眼睛多观察人性,很彻底地认识作者和读者在性情,资禀,修养,趣味各方面都有许多个别的差异”[8]467。朱光潜对于诗歌问题的探讨不仅涉及到诗歌的创作还有诗歌的传达以及欣赏问题,总的来说,“1930年代中期的此时,出现这样一次大胆而彻底的再次革新——其结果如何姑且不论,至少在观念的推进上——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9]
如果说在《大公报·文艺·诗特刊》的发展过程中,朱光潜只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发表了自己对于诗歌部分问题的看法,那么在其主编的《文学杂志》中,他完全就是以主体的身份传达了自己对于诗歌的见解,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朱光潜对于杂志栏目的设置以及内容的选择;二是朱光潜自己在其杂志中发表的诗歌评论和诗歌理论。《文学杂志》既编选大量诗歌作品,如卞之琳充满丰富空灵意象和饱含象征意味的《白螺壳》、废名既有有趣的单纯又有美妙的想象的《宇宙的衣裳》等,也重视诗歌理论的刊登,如叶公超针对新诗和传统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论新诗》、充分展现陆志韦主张“诗的节奏应根据语调的节奏而加以整理”[10]的《论节奏》等。朱光潜更是将自己所写的诗歌评论《望舒诗稿》放在正文发表,点出“他的诗在华贵之中仍保持一种可爱的质朴自然滋味”[11]的同时,说到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与其理论并不相符。他在介绍周煦良的《北平情歌评》时,直接表明了自己对于理想的诗的看法,他说“理想的诗应该能调和语言节奏和音乐节奏的冲突,意义的停顿应与声音的停顿一致。”[12]朱光潜在其自己主编的《文学杂志》中所采用的编辑策略,所涉及的编选内容无不体现出他对于诗歌的喜爱和关于诗歌问题的深刻见解。
朱先生常借助报刊杂志等载体来宣扬自己的文学观念,文章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内涵丰富,虽说零散,但却是其诗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其诗学观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诗论》
“《诗论》对诗学中的各种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都已尽量包罗无遗,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最为系统的一部诗学著作。”[13]《诗论》的出彩之处可以从两方面见出:一是其方法,为了探寻新诗的发展出路,朱光潜一方面将中国诗与西方诗作比较,研究中西方诗歌在创作和理论上的相同点和差异点,一方面对于旧诗的发展进行梳理总结,看看旧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从中西的横向比较中,他看出了中西诗在情趣上的不同,在节奏音律上的相异,从古今的纵向比较中他认清中国诗从原始的“自由诗”走向“律”的复杂性和必然性。二是其内容,朱光潜对于诗歌的研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次他讲解《诗论》时,他“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后来“改来改去,自知仍是粗浅,所以把它搁下,预备将来有闲暇再把它从头到尾重新写过。”[14]4《诗论》涉及的内容相当之广,包括诗歌的起源、内容、形式、节奏声律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朱先生也并非是点到为止,而是深入其肌理,探究其渊源,在梳理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朱光潜在美学上颇有建树,但是他第一喜爱的却是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15]200《诗论》不仅仅总结了他对于诗歌等文学问题的见解与看法,而且还渗透了其美学思想。《诗论》和朱光潜的另一本传世之作《文艺心理学》有着深厚的学理渊源,《文艺心理学》泛论文艺,《诗论》“应用本书的基本原理去讨论诗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15]200在《诗论》的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中,朱光潜利用了克罗齐的“表现说”,点出克罗齐的“表现即直觉”虽能够解释实质和形式的不可分割,但是还是存在着些许的漏洞:没有提到传达媒介的重要性、没有将“表现”和“传达”进行衔接、没有分清创造性的“传达”和无创造性的“记载”。可以说朱光潜对于诗歌的研究是以其美学思想和理论为基础的,与身兼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文人相比,朱光潜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于诗歌的理论建设更加具有学理性和系统性。
目前,学界对于《诗论》的研究还算丰富,从发表的成果来看,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于《诗论》版本的研究,如商金林的《朱光潜<诗论>的五个版本及其写作的背景和历程》;二是将《诗论》放在中西比较诗学中观察,如文学武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诗学理论建构——兼论朱光潜<诗论>的独创性》;三是对《诗论》中的某一部分内容进行研究,如陈德献的《朱光潜<诗论>的“音律”理论研究》;四是对《诗论》的价值进行研究,如李黎的《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读朱光潜先生的<诗论>》。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朱光潜美学思想、文学观念的文章将《诗论》作为其章节的组成部分。但是将《诗论》与其整个诗学活动放在一起进行详细研究,以窥探其诗学观的文章还比较少,有待学者进行填补。
朱光潜组织举办的“读诗会”聚焦于诗歌音律、节奏的探讨,在“诗特刊”发表的文章重视从生理学的视角对于诗歌进行研究,对诗的好坏作出了阐释以及欣赏中出现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朱光潜利用自己主编的身份于《文学杂志》中围绕着诗歌创作以及理论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自己用力最多的《诗论》中系统性地论述了诗歌的起源、形式、内容、节奏、音律等,并构建了情趣、意象、意境三大核心理论观点,其整个诗学体系在一步一步的诗学实践中得以建立起来。
二、诗学观
朱光潜“既有哲学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造诣,又深谙中外诗歌理论,精于诗歌鉴赏,因此他的思维空间相当广阔。”[16]再加上,他多种诗歌活动的展开,对于其诗学理论不断进行回顾和完善使得他的诗歌理论具有高度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一)实质与形式不可分割
朱光潜将诗的实质和形式的探讨抽象为思想情感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他对于“思想情感在前,语言形式在后”的说法极为不满,并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思想情感与语言的平行关系,“心里想,口里说;心里感动,口里说;都是平行一致。”[14]93虽然说它们是一个完整连贯心理反应中的三个方面,但是它们之间也并非没有差异,思想情感与语言的关系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范围大小不能完全重合,有些情感是不能用语言传达出来的,好的抒情诗往往可以“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以部分暗示全体,以片段情境唤起整个情境的意象和情趣。”[14]94有一种值得读者无限回味的韵味和不断品析的乐趣。
单从思想或者单从形式方面对于文艺作品进行考察,较为片面,有失公允。朱光潜自己在《文学与语言(上):内容、形式与表现》中,坦白到自己也曾犯过这样的错误“以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力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境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很注意它的语言文字如何。”[17]226但他随后就有所转变,在对情感思想和语言文字关系的探讨过程中,他首先条分缕析地阐述了克罗齐的“表现说”,接着,又指出其“表现说”最大的问题之处是对于“传达”的忽视,克罗齐没有说明艺术与传达媒介之间有何关系。每种艺术都有各自特殊的传达媒介,图画借助形色给观者视觉上的快感;音乐借助声音给人听觉上的快感;诗歌借助语言文字既给人听觉上的愉悦又给人视觉上的享受。朱光潜曾回顾过莱辛的“诗画异质说”,认为这一学说对于艺术理论的贡献甚大,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识到了传达媒介与艺术的重要关联,绘画、诗歌、音乐绝不能相同,它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性,“每种艺术应该顾到它的特殊的便利和特殊的限制,朝自己的正路向前发展,不必旁弛博骛。”[14]146诗人绝不可忽视其借助的传达媒介——语言文字,既要重视其意义性,推敲出最适宜的文字表现自己的情趣,也要重视其音乐性,使之读起顺口、听之顺耳,仅从形式就能产生出浓厚的美感。“语文的精确妥帖,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17]226自古以来,诗人们一直讲求文字的推敲,诗中的每个文字都与其所展现的意境、表现的节奏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诗是最难做的,一首能够流传千古的诗一定是内容和形式完美契合的艺术品。朱光潜在《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中讲到,近来新诗发展不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在于“作者在技巧上缺乏训练,又不能使每一首诗现出很显著的音节上的个性,结果是散漫芜杂,毫无形式可言。”[14]270没有形式的诗本质上不能称之为诗,它在文字意义之外没有任何能够值得读者回味的理由,这与其他的文学体裁又有何种差别?
诗的实质和形式不可分割,这是朱光潜根据新诗发展情况而发出的声明。要想促进新诗的发展也一定要朝着这两个方面努力。在实质方面,向人生取法,一切艺术的根基都在人生,要懂得欣赏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要感知世间的千变万化,将人生的路子走多走宽,敢于尝试,懂得钻研。在形式方面,学会取法,朱光潜点明当代诗人有三条路可走:西方诗的路、中国旧诗的路以及流行民间的路,但无论走哪条路一定要有聪慧的眼光和灵活的手腕。
(二)情趣、意象和意境
朱光潜强调要产生诗的境界须具备两个条件——意象和情趣。意象即当人凝神注视一件事物时,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的形象,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14]51,许多人会将情趣混同与情感,但是在朱光潜眼里两者绝不能等同,其中之原因,他在《诗的主观与客观》中有所说明“诗的情趣并不是生糙自然的情趣,它必定经过一番冷静的观照和融化洗炼的工夫。”[4]365情趣是一种从沉静中回味而来的情绪,它不像是热烈的熔岩一下迸发而出,它经过理智的洗炼和过滤。一般看来,意象是客观的,事物本身的形象是固定不变的;情趣是主观的,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产生的情趣都有可能是不同的,这就使得诗的境界一定是客观和主观的融合,朱光潜结合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情景关系的探讨将诗的境界定义为“情景相生而且相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14]54意境既然是情趣和意象的完美契合,那么意境要将经过冷静回味的情趣融入至清晰完整的意象中。
朱光潜明确地提出过自己对诗的情趣、意象和意境的要求。首先,朱光潜坚持诗的情趣是“沉静中的回味”而并非自然生糙的情感,写情的诗往往要追求“隐”,杰作如李白的“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愁怨之情虽全诗一字未提,但细细咀嚼便觉得无比之妙。朱光潜对于陶渊明诗歌如此喜爱的原因也在于他对于情绪的掌控,陶渊明对于人生悲喜剧两方面都能领悟,能出能入,“惟其有感慨,那种欣喜是由冲突调和而彻悟人生世相的的欣喜,不只是浅薄的嬉笑;惟其有欣喜,那种感慨有适当的调剂,不只是奋激佯狂,或是神经质的感伤。”[14]263可以说朱光潜所追求的情趣是自然情绪的升华,它绝非像火山喷发汹涌,却像流水潺潺温和。其次,诗人要能够欣赏不同的情趣。朱光潜多次表达过对于具有偏狭趣味的人的不满,认为他们不仅不能欣赏到其他派别的趣味,而且恐怕对于自己所欢喜的文学也不能完全透彻的了解,他认为“文艺上的纯正的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4]352,既能感触于苍劲悲凉的战争诗也能欣赏自然清新的田园诗。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无须言表,它可以说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作者通过创作意象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读者在阅读意象时既能把握作者的目的和意图,又能根据自己当时当地的处境进行二次创造。朱光潜对于诗歌中的意象选择有着明确的要求,第一,意象应该是具体的、清晰的,朱光潜说:“文艺作品都要呈现具体的意象出来,直接撼动感官。”[15]390“抽象的概念在艺术家的脑里都要先翻译成具体的意象,然后才表现于作品。”[18]意象乃是情趣的外化,情趣本就难以传达,若是意象再如此抽象又如何令读者阅读和感悟?第二,意象必须完整。“因为纷至沓来的意象零乱破碎,不成章法,不具生命。”[14]54因此艺术家们一定要进行过综合和创造,把自己的情趣当作线将杂乱无章的意象连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意境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探究,宗白华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物,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19]这是将生命主体和客观意象互相渗透的说法,无论是从朱光潜还是宗白华对于意境的定义来看,他们都认为意境的形成与人这一主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每个人皆是独立的个体,故即使看到一样的景,也会产生不同的情,这就要求诗人所创造的意境一定是新鲜的。
中国文学亲附人生,感于人生才有情可发,有诗可作。易感之人,情趣必丰,个人生活之种种,时代人生之大事,皆可成诗,人生情趣化是朱光潜一直坚守的人生准则,也是其衡量文学优劣的重要标准。但欲成为真正的诗人,必要掌握个人之技巧,种种意象的选择,独特的意境创造须得诗人的耐心琢磨。
(三)诗的音乐性
朱光潜在讲述诗歌的起源时,认为“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14]13而它们有个共同的命脉——节奏。朱光潜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节奏对于诗歌的重要性,首先“节奏是一种自然需要”[14]124,人以及整个自然界都生活在节奏之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人的生活节奏,月圆月缺,春夏秋冬是自然界的循环节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节奏是不可变的。但是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的节奏是可改变的,因为诗的节奏是由语言的节奏和音乐节奏两个部分所组成的,但“语言的节奏是自然的,没有规律的,直率的,常倾向变化;音乐的节奏是形式化的,有规律的,回旋的,常倾向整齐。”[14]132这使得诗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有规律的音乐节奏来提升诗歌节奏给人带来的快感,增强舒适性。其次,“节奏是传达情绪的最直接而且最有力的媒介。”[14]129无论古今,诗总被认为是抒情的工具,诗歌中文字的意义固然可以传递诗人的情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所蕴含的悲痛之情人人皆有感,但由于诗歌中的情绪抒发多得力于具体的意义,使得很多人忽视了音乐节奏对于诗歌的影响。朱光潜对于诗歌节奏的重视不仅仅表现在理论建设领域,其读诗会的开办也是为了寻求新诗的理想的节奏而努力。朱光潜认为“新诗的节奏是偏语言的。音乐的节奏在新诗中有无地位,它应该不应该有地位,还须待大家虚心探讨。”[14]136但朱光潜好像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音乐的节奏在新诗中是必要的。1933年,朱先生在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后发表了一篇《替诗的音律辩护》,明确反对胡适所说的“作诗如说话”的口号,他将诗定义为“专指具有音律的纯文学,专指在形式和实质双方都是诗的文学作品。”[14]223并讲出了诗有音律而散文无音律的基本原理。朱光潜在《诗论》中专门分析了中国诗的节奏和声韵,在对声、顿、韵等进行了详细分析之后,最终点明中国诗如何走上“律”的道路。
声音有长短、高低、轻重之分。“因为语言的性质不同,各国诗的节奏对于长短、高低、轻重三要素各有所侧重。”[14]155中国诗的声就是平上去入,因为中国地广人多的缘故,每个地区甚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发音习惯,加上声音有时受到意义或邻音的影响,使得“四声对于中国诗的节奏影响甚微。”[14]165它们对于诗歌节奏性虽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了。声音除去长短、高低、轻重三种之分,还有调质不同,选择合适的调质能够促进诗中字音本身的和谐以及音与义的协调。顿是诗歌节奏的真正调控者,朱光潜提醒学者们要注意说话的顿与读诗的顿的不同,诗歌是经过形式化的艺术,因此有时要注意其音乐性,所以在注重字意义上的连贯性同时,要尽可能地兼顾其声音上的完整。旧诗的顿虽然能对诗歌的音乐性产生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对于诗歌情调的表达却是一种束缚“节奏不很能跟着情调走,这的确是旧诗的基本缺点”[14]181,补救这一缺陷也是白话诗的目的之一。音韵是情感自然流露的节奏。韵的使用与各国语言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光潜将中国诗与法文诗类比,认为中国诗的节奏不能缺少韵的原因在于它的“轻重不分明,音节易散漫,必须借韵的回声来点明、呼应和贯串”[14]188,将韵作为一根线把涣散的声音联络起来,增强诗歌的整体感、和谐感。但朱光潜也指出,在中国旧诗中,律诗的押韵规则过于单调以及模仿古韵的弊病也必须得到矫正。
朱光潜对于诗的节奏和音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点明它们在诗歌中的不可或缺性,同时也对于律诗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其根本目的是想让时前的诗人能够重视诗歌的形式而并非只关注其内容和意义,寻求新诗的发展途径。
朱光潜在对实质与形式、情趣、意象、意境以及诗歌的节奏和音律等问题进行论述时,运用了中西比较和史论结合的方法,他的分析鞭辟入里,见解十分独到,可见其思维之缜密,逻辑之严谨,这使得他的诗歌批评能够在整个京派文学批评中脱颖而出。
在20世纪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家中,绝大部分其本身都是诗歌的创作者,朱光潜这样仅以美学家和理论家的身份进行诗歌批评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诗人批评家固然有其优势,他们能够在感性和理性之间达成一致,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中相互切换,互相求证,但是当他们进行诗歌批评时不免有一种“为己”目的,而朱光潜这种纯粹的诗歌批评家虽然说缺少诗歌创作实践的积累,但是他们阅读和欣赏过大量的诗歌作品,有较为深厚的学识作为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创作上的缺失,他进行诗歌批评更多是出于一种“为他”的目的。为探索诗歌在诵读上的可能性,朱光潜积极举办读诗会;为探讨新诗存在的问题、寻找新诗的出路,他与人争论,利用杂志报刊为自己理想的诗歌辩护;为完善中国的诗学建设,他不断回顾自己旧思想,实时更新,其诗学著作《诗论》更是一改再改。朱光潜利用中西兼具的眼光,博古通今的学识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他对于实质与形式的探讨让当时的学者认识到形式的缺失给予诗歌带来的巨大缺陷;他以克罗齐“直觉”说为起点,融合立普斯“移情”说,谷鲁斯“内模仿”说与中国传统诗论中的“顿悟”说等等建立起来的“意境”说,更是对于中国传统理念的新发展,为中国文论增添了不少的科学性和学理性。他对于诗歌节奏、音律的重视更是为诗与散文划出了鲜明的边界,为诗歌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朱光潜一系列的诗学活动充分表现出他对于诗歌的热爱,对于新诗发展前途的关注,他以诗歌理论为指导,并不断在实践中修改完善自己的诗学体系,实践出真知,朱光潜诗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坚持事实和学理并重,诗歌的存在必有它的理由,为其提供科学的辩护是朱光潜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