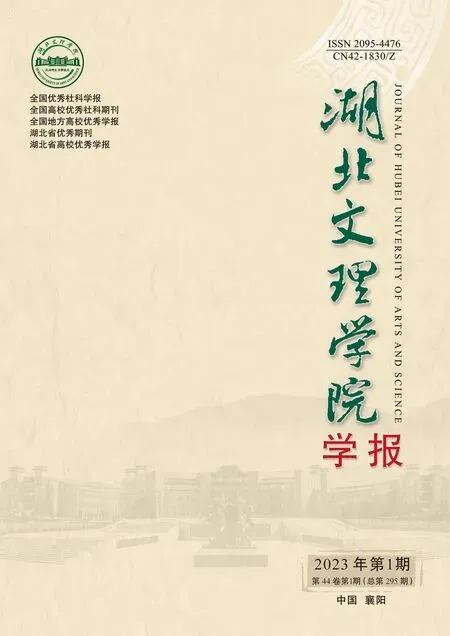刘桢诗歌审美实践脞论
高子芹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建安诸杰中,钟记室将刘桢与曹植、王粲三位列乎上品,且曰“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可知刘桢为其所重。《隋书·经籍志》载“魏太子文学刘桢集四卷”,逮至新、旧唐书却只载二卷。明清两朝,杨德周之《汇刻建安七子集》、杨逢辰之《建安七子集》、张溥之《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皆载录《刘公幹集》。彼时选刘桢诗三篇及以上者有:李攀龙之《古今诗删》、冯惟讷之《诗纪》、唐汝谔之《古诗解》、陆时雍之《古诗镜》、王夫之之《古诗评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之《古诗源》。因刘桢别集在传世过程之中有所散佚,经丁福保、逯钦立、俞绍初诸位学者之辑考,现存刘桢诗凡二十六首,中有十四首残篇。其诗言壮劲逸、文气夐奇,以贞骨凌霜的独特风格卓荦绝俗、彪炳可玩。
一、托意于物——审美接受与美感经验的二度建构
审美实践是文艺活动的行为方式,涵括审美接受与审美创造二者。鲍姆嘉通言曰美学之认识即是“感性认识的完善”[1],其人文作中恒将审美历程与感性认识并论。诚然,审美感受乃是审美客体观照体验中至关重要的元素,亦是审美主体在审美接受中的精神衍生物。咏物诗产生的情感基础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这一“神与物游”的构思阶段使得于客观层面的“象”——即客观经验所定义的固有符号附着上了创作主体的主观感受,从而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意符号。作为审美主体的文人士子,于观照外物之际产生相应的审美感受,并将其以文字的形态重构后再度呈现,咏物诗作便由此而生。
此处欲就审美接受理论探讨刘桢咏物诸作。《赠从弟》组诗三首咏三物,呈现出对萍藻、松柏、凤凰的审美经验。此诗其一所咏,为生于泛泛流水之涯的萍藻。“海闾生屈龙,屈龙生容华,容华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3],萍藻即浮萍。公幹在审美观照,即欣赏之时,从萍藻独生幽涧、孤随清波的客观本质中感受到了高逸绝俗的风神,接受了审美观照客体秉正傲俗的精神内核。其二所咏为松柏,松柏以其劲直且常青成为古之圣贤用以比德的物象。《礼记·礼器》有言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4]将竹箭与松柏“贯四时”且不“改柯易叶”的品质与人之坚守本性、刚直不阿相比附,逮乎魏晋之际,时人亦以“谡谡如劲松下风”“森森如千丈松”称扬李元礼、和峤之风范。公幹接受了这一比德传统,用松柏罹冰霜风雪之难而终年端正来勉励自己与从弟不为外阻动摇人格与心志。其三所咏的与一二之咏植物相异,全诗托意于凤凰。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5]公幹此诗主要颂扬的是凤凰奋翅骞翮而奔远翥、不与黄雀之属同群的孤高,借此称扬从弟不落尘俗、待时而飞,并兼以之自励。张玉榖赏析此诗云:“首章以萍藻比,慰清修之必见用也……次章以松柏比,勉劲节之当特立也……末章以凤凰比,戒盛德之宜养晦也。”[6]此处所咏的三物,是经过情感、联想等诸多心理功能加工改造之后的审美意象。刘桢赠与从弟的这三首咏物诗,是其作为审美主体借助审美器官对萍藻、松柏、凤凰进行审美知觉,以视觉感悟到萍藻所处之高洁、松柏枝干之笔直,进而在此审美感受之上衍生审美痛感的文学实践。
关于刘桢组诗所咏的“萍藻”“松柏”“凤凰”,中国古典文论中常将此类带有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视之为“意象”。其实,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象”论与西方符号学理论相通。康德曾将意象定义为“理性观念”,即通过“想象力”衍化而生的感性想象,苏珊·朗格则以“情感符号”来明确审美意象的本质。那么,由客观“符号”转化为“情感符号”,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元素无疑是“想象力”。置于古典美学之中,诗文中“象”成为“含意之象”的必要条件是“神思”。《文心雕龙·神思》篇有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7]审美主体通过“神思”感受外在事物,并且将其转化为包含主观经验在内的含意之象。“神与物游”的构思阶段使原本无义的客观符号附着上了诗人个体的主观感受,因而成为了具有情感属性的象征符号,此时文人笔下的“松柏”之属,已然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象。刘桢对于观览万物后所获取的审美经验进行二度建构,成为咏物诗生成的根柢,此种咏外物而述怀的传统对江淹与鲍照的文学创作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苍苍中山桂,团团霜露色。霜露一何紧,桂枝生自直。橘柚在南国,因君为羽翼。谬蒙圣主私,托身文墨职。丹彩既已过,敢不自雕饰。华月照芳池,列坐金殿侧。微臣固受赐,鸿恩良未测。[8]1571-1572
(江淹《刘文学桢感怀》)
曀曀寒野雾,苍苍阴山柏。树迥雾萦集,山寒野风急。岁物尽沦伤,孤贞为谁立?赖树自能贞,不计跡幽涩。
(鲍照《学刘公幹体诗》其二)
荷生渌泉中,碧叶齐如规。迴风荡流雾,珠水逐条垂。彪炳此金塘,藻耀君王池。不愁世赏绝,但畏盛明移。[8]1299
(鲍照《学刘公幹体诗》其四)
江淹之作取象“桂”“橘柚”,鲍照取象“柏树”与“荷花”,二子接受了原物象具有的象征意义,藉此表达对美好品格的歆慕与激赏。诗人们咏物之时,并非完全以“直寻”的方式对客观外物进行“再现”,而是掺入了主观层面的“神入”和“赋形”,笔下的善鸟香草已然附着上了审美主体对于懿德的向往与追求。
刘公幹固然是在对这些动植物的本质属性的观照基础之上,接受了它们或清逸或刚正的情感内质,但此种情感内质不仅是主体在审美观照之时直接所得,也可能是前人所赋予物的审美属性,诸如松柏之刚劲,历代皆有咏颂者。刘桢的“磷磷水中石”一句典出《诗·唐风·扬之水》[9],其“蘋藻生其涯”“采之荐宗庙”诸句则源自“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10],于此既可见公幹之经学素养,又可推知物与神游、托意于物的审美接受过程乃是文人墨客一以贯之的述怀传统。
此处尚需着重言及的是,审美经验的获得固然与审美客体的特质相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刘公幹作为审美主体,其本身具体的情感体验对于审美接受的最终结果颇有影响。因为审美主体的接受过程,并非是刺激—反应的被动程式,中间的主体认知层面作为审美主体,其本身的情感经历对于现下的审美观照不乏影响,它可以之于审美客体的规定性予以异化。比如主体感物所得,往往与其已有的情感体验相联。“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笑可哀者,载使然也。”[11]若以悲眼审乐,则凡天下之音乐皆著悲之色彩,即便面对喜乐之“刺激”,审美主体之反应亦因固有认知的干预而趋向悲戚。具体来说,刘公幹所描写的事物,已然是经过其本身的情感体验筛选之后重置的审美客体,当他描写二者,即由原来的审美欣赏主体摇身而成审美创造主体时,具体的审美情感便与审美接受所得有所区别,他曾作失题诗曰:
青青女萝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养恩,分惠不可赀。风雨虽急疾,根株不倾移。[12]194
《诗·小雅·頍弁》载曰:“茑与女萝,施于松柏。”[13]本诗所咏为女萝,却超脱了女萝本身依松枝而生的表层植物属性,也与其它诗人笔下的女萝相异,而是刘桢在秉持女萝依附内质的基础上,以托物之法赋予了它与己身关涉的具体情感内涵,自喻女萝,喻曹氏政权为松,刘桢之“得讬芳兰宛,列植高山足”亦是此意,以之表示依附攀援、万阻不渝之意。故而审美主体的观照体验,大多不会原封不动地进入其审美创造之中。审美创造过程,往往是美感经验的二度建构过程。即物达情、象外追神的审美实践,所达之情、所追之神,显然不全然是物、象所直接加诸审美主体的,这其中尚不乏主观情感元素的参与。
二、寄怀予人——审美创造与赠交以言的深沉内蕴
审美创造是审美实践的另一方面。固然,咏物亦是文艺审美创造的尝试,但更偏重之于审美客体即自然外物的接受基础之上的创造,而赠答诗作则由于情感内涵的主体化、个性化,在审美接受层停留的时长远逊于创造层。审美接受与审美创造之间,不可忽略的一个过渡点即是审美理想。审美理想是包含上文所述的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经验在内的审美意识形式,它推动着审美动机的生成,进而促就审美创造实践的发生与发展。之于刘桢作诗实践而言,此处的审美创作动机大多是个体性而非社会性的,尤其是其赠答诗,大多是情动于衷而发之于外。刘公幹留存诗作极少,完整者仅十二首。赠答诗愈加寥寥,但大都深挚动人、意绵情切。除《赠从弟》外,写予曹丕与徐幹之诗堪称上乘,然却与向赠从弟之诗风格大异。彼时的文人大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诗风变革的转折点。公幹建安九年随曹操征邺,十一年东征管承,十三年从征刘表,曾任曹操之军师祭酒、丞相掾属,曹丕之五官将文学,曹植之临淄侯文学,其人生与诗风之易因缘于公元211年的“平视甄氏”一事,《典略》载曰:“建安十六年,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世子酒酣坐叹,乃使夫人甑氏出拜,座中客多伏,而桢独平视。他日公(操)闻,乃收桢,减死,输作部。”[14]刘公幹为何平视甄氏,学界聚讼未休,但这一莽撞之举的下场即是被贬磨石,即便后来因其以石头“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秉性自然”自比,为曹操再度起用,然而入仕前期之壮志已然消磨大半。他曾于此后赠诗于挚友徐幹:
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兼烛八纮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12]190-191
刘桢另有残篇《又赠徐幹》:“猥蒙惠咳唾,贶以雅颂声。高义厉青云,灼灼有表经。”[12]191以之表达对于徐幹的颂扬之意。徐幹“轻官忽禄,不耽世荣”的高逸品性使得刘桢与之甚是投契。之于这首赠诗的写作时间,《义门读书记》以为:“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此诗有‘仰视白日’之语,疑此时作也,”[15]当是输作北寺之署吏时作。诗中表达了与友人一垣之隔却恍若相去千里的怅惘。不得相会的悲凉心绪促使诗人起坐难安,他茕然独行,凝望西园,思念愈发深笃,不禁怆然涕下。诚然,在对徐幹的深切情谊中,公幹同时寄寓了自身被羁桎的怨尤和对于彼时官员交通之禁尤严的不满。这与赠从弟之时奋发向上的昂扬诗风已然迥异,取而代之的是不得于时的凄凉意绪。
较乎《赠徐幹诗》,《赠五官中郎将》则愈发动人心弦,全诗总四首。首先忆及建安八年八月与建安十三年七月随从曹操“整驾至南乡”以征刘表与在谯地与子桓诸宾“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的饮宴之事;继而论述自己病居漳河之滨“弥旷十余旬”,子桓亲至探视,与其“清谈同日夕,情盻述忧勤”的相惜;其三则是重于秋夜抒怀。诗人夜不成眠,中宵泼墨,叙内衷百折于案头濡翰。念及子桓行将出征,不免担忧他为戎事操劳;其四则顺势而下,遥想子桓于“凉风吹砂砾,霜气何皑皑”的沙场之上,依旧“赋诗连篇章”“文雅纵横飞”[12]189的翩翩风度。四首以时间为线,自回忆旧事起,以遥望未来终,阖篇贯穿着公干对曹丕的情真意笃,间述己身病笃劳怯的凄戚景况,读之使人潸然。它业已超越了公幹向时着力劝勉友朋与抒发志意的赠别传统,整体格调趋向消沉,字里行间已难见到曩昔豪气。究其原因,赠于徐幹与曹丕之诗皆成于“平视甄氏”(建安十六年)之后,而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使得刘桢与徐幹、应玚、陈琳均罹难疾灾,故自建安十六年至其离世,公幹时常处于一种形固衰损、神亦倦倦的身心俱伤状态,以此审美情感为诗,字辞之间便不免颓殇悲凉之戚。
以赠别一类论及刘公幹之审美创造,乃因其中情如潭水、味似醇醪的感性经验表达以其主观性和特殊性更具创造意味。审美主体的情感体验对其创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公幹诗风的变易与其情感体验相涉颇深,其中最直接的便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经邦治国的名臣,然终其一生都仅是曹氏父子身边用以娱遣的文学侍从,“魏氏与诸子,不过如富贵人家养几个作诗相公陪伴自己子弟读书……其实非怜其才而大用之也。”[16]139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与残酷的仕进现实并不匹配,故而即便不被贬为署吏,其诗风亦难脱感伤情致:
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厌。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释此出西域,登高且游观。[12]193
纵观此诗,流露出的尽是诗人之于职事羁锢、案牍劳形以至无暇进食、夜以继日的文吏生活的厌倦。终日与簿领书相随的生活与其对自己仕宦身份的期待相悖,故而内心倍觉纡曲。对现存场域的不满与对自身定位的迷茫,成为此刻主导公干创造的审美情感,它将这一感性经验呈现于诗作之中,造就了其诗沉郁凄恻的别样风致。
三、气壮情骇——刘桢文学审美实践的风格
既已论及刘公幹咏物、赠答诸作,亦当以此为本探究其审美实践活动的风格,尤其是其审美创造中体现出来的诗歌特征。陆时雍《诗镜总论》否定刘桢之诗云:“骨干自饶,风华殊乏,苏子瞻谓曹、刘挺劲,须知诗之所贵,不专挺劲,”陈祚明则不然,以为“公幹诗笔气隽逸,善于琢句,古而有韵,比汉多姿,多姿故近。比晋有气,有气故高。如翠峰插空,高云曳壁,秀而不近。本无浩荡之势,颇饶顾盼之姿。《诗品》以为气过其文,此言未允。”[17]纵观古典文学批评史,诸家多以“气”评述刘桢诗风,《文心雕龙·体性》曰:“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18]又皎然《诗式》曰:“刘桢辞气偏,正得其中,”[19]胡应麟《诗薮》云:“公幹才偏,气过辞。”[20]29“气”是古代最重要的文论范畴之一,这里所谓之“气”显然不是聚焦于其物理属性而是偏向于人的精神气质的阐述,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诸家大多摒弃了“气”的自然属性而用以比附人的品性,从中探索不离本体存在的审美意趣。刘劭《人物志》以为元一之气为万物之源,决定五行与阴阳。人的道德品质取决于独特气质,独特气质取决于五行所属的异同,故而人之性决定于元一之气。其书《九征》篇论曰:“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21]11人之仁否、勇否、智否归根结底都是由“气”决定。虽然刘劭关于“心气”的理论尚不成熟,但已然关注到了“气”与品性之相涉。
学者大多好以“气”之劲逸评价刘公幹之诗文,但未脱抽象之弊。由于“公幹诗,质直如其人”,故刘桢之“气”体现在其人与其辞两个方面。就其名与表字而言,“桢”为刚木,即筑墙所立之两。桢木之于建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被委以重任的大材。以此为名,以“公幹”为字,体现了其父对其致仕济民的殷切期许。至于桢父,学界莫衷一是。《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曰:“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终于野王令。”[22]448现今或以为梁为桢之祖父,于此以父为是。父亲的博闻笃学与用世之举给公幹做了一个极好的示范,使得他年幼之时虽贫甚却不乏匡国之志,八九岁之时已然“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23]。其人的劲逸之气主要体现在为人的刚直上,即如其为邢颙辩解一事:邢颙为曹植之家丞,因守礼不屈而为崇尚不拘的曹植所疏离,刘桢为此仗义执言:“家丞形顒,北土之彦,少秉高节,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顒反疏简,私懼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22]448可见其耿直正义,时人亦以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八字为刘桢作评。
公幹为人尚劲气,作诗亦然。奉儒守官的家训促使其当遇见心悦的“圣明君”时,便高举双翮而飞奔往投,但所任官职并未供予他施展治世才能的广阔天宇,反而使他限制在无谓的阿谀与吏事之中,内中百折可想而知,于是诗中便衍生出了激宕刚劲之气。公幹之劲气是待时展翅的豪壮之气与志意不遂的不平之气,这从《赠从弟》中松柏之质直、凤凰之高逸以及《杂诗》中为冗事所扰的纡怨均可得见。即便是在以狭游奉酬为宗旨的《公宴诗》中,也不见阿谀谄媚之意,而是仍旧以“劲气”贯之。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评曰:“通篇只言游从之盛、景物之美,曾无一颂德语,又贤于仲宣‘克配周公’远矣,此应付诗中之有品者。”[16]139将其与王粲致力赞祷的公宴诗作相较,高度肯定了刘公幹之诗品。于“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的美景之中,君王盛宴群臣,公幹却只着墨于所见之景的描绘,缓缓道尽园林景色的幽雅与美好,毫无奉和之辞,且末尾还有“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的警戒之言,余意悠长而隽永,超越了一般公宴诗唯以谄上为意的写作意图,体现了刘桢之诗尚气的个性特征。刘桢诗歌创作之“尚气”,主要体现于形式之“言壮会采”与内容之“情高意重”。前者从其《赠从弟》与《赠五官中郎将》可见一斑。再如刘桢的《斗鸡诗》:
丹鸡被华采,双距如锋芒。愿一扬炎威,会战此中唐。利爪探玉除,嗔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12]194
丹鸡为扬其威奋力而战,利爪扑阶,双目怒瞋,张翅猛拍,勾喙复击,刘桢所写的恍若非鸡,而是一位竭力厮杀的英勇壮士。曹植与应玚均有以“斗鸡”为题的诗作,然而却仅将其作为贵族阶层娱乐消遣的游戏进行描写,刘公幹却不然,它在拼杀的雄鸡身上寄寓了自己的壮心与豪情,使诗呈现出激昂向上的格调与热情,彰示了一种卓荦高绝的阳刚之美,再度体现了其为诗为文“仗气爱奇”的审美创造倾向,生命价值与个性苏醒的张力由此蓬勃而出。造就刘桢之“气”的情感内核不唯壮志不泯的豪情壮志,其审美心理因素中尚有悲壮深挚的愁思意绪,“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秋日多悲怀,悲慨以长叹……涕泣洒衣裳,能不怀所欢”“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12]195,故友黯然临歧后久疏阔别之眷恋,所遇无故物转瞬即逝的忧生之嗟,体现出深沉而悲切的生命意识。刘桢以感伤心绪为情感内驱力进行诗歌创作,生根于汉魏之际的社会现实,以建安风骨的慷慨之气为底色,具有宏大而深切的悲剧精神与时代内蕴。以上所列诗作,均可从其文辞之中想见刘桢为人、为文所秉持的刚劲与气骨。“风格即人”,公幹文品与人品,于此得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多好着墨于“气”“骨”二者,刘公幹之诗有气故高,但却忽视了“骨”之臆造。钟嵘在称扬其作的同时,亦批判了其“气过其文,雕润恨少”[24]110之失。“骨”与作品的行文语言与行文技巧相涉,“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公幹诗重乎精神气质,之于文辞藻饰与结构编排的轻视造就了其诗歌有风无骨的艺术风貌,故而逊色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25]97的曹子建。然不可否认的是,刘桢以其刚正坚毅的品性与劲逸悲壮的诗风垂名,无愧于“曹刘”之刘与“建安七子”之一的美名。
及至明清之际,王夫之曾于其《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姜斋诗话》中提及“现量”一说,强调“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则禅家所谓现量也。”[25]821即无需刻意推敲,强调“现量”式的直觉性审美观照。刘桢诗见松柏、萍藻、凤凰、女萝、丹鸡,并未如王夫之所论忽视揣度与构思,并未桎梏与再现之于审美客体的直接感知,但主观意绪的附着,含意之象的营造,却恰恰成就了其“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24]110的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