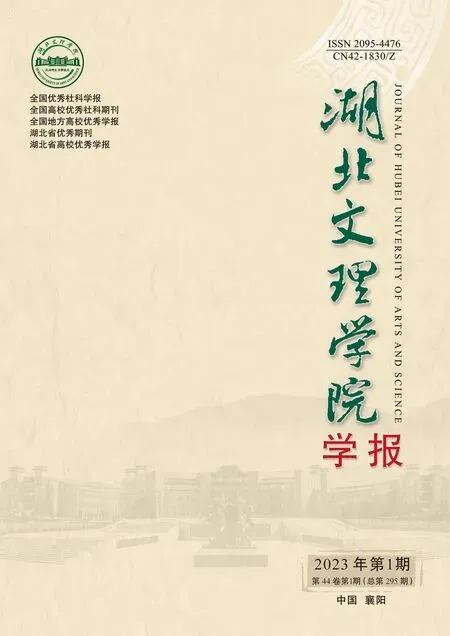曹禺创作焦虑的多重表达模式
——基于信件材料的考察
郭羽思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剧戏曲学系,北京 101322)
关于曹禺的创作困境,学界已有比较明确的描述和解释。曹禺曾说:“创作对我来说很怪,满脑袋都是马列主义概念,怎么脑袋就是转动不起来呢?我不愿意写旧的东西,写新的又写不出来”[1]他也非常看重黄永玉的批评:“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2]如此严重的创作困境根源何在?田本相指出曹禺创作生涯中的三次危机,分别源于题材库存枯竭、创作思想危机和精神衰竭残废。[3]张志平则认为,曹禺未写出“第六部名剧”是一种系统性危机,无论储备材料、积累经验、体验生活、模仿范本还是钻研技巧,都不能接触此危机。[4]王卫平认为,曹禺主观的劣势,包括感知、体验、积累的不足,创作着力点的不善于转换,迁移能力不强,创作主体的心理障碍以及性格、人格的缺陷都是不能忽略的。[5]这些研究业已涵盖了曹禺创作困境的全时间阶段与主客观成因。然而,在这些描述与解释中,曹禺本人的声音却显得微弱,来自曹禺主体方面的表达,往往局限于一些访谈文章。本文基于《曹禺全集》《没有说完的话》《曹禺巴金书简》和近年出版的《曹禺年谱长编》《你和我》等新旧文献中的大量信件材料,力求层次清晰地阐述,曹禺晚年面对不同关系的亲友,表达创作焦虑的多重模式。具体而言,可以分为面对友人巴金的“挣扎解剖”模式,面对女儿万昭、万方、继女李莉和李如茹的“鞭策寄望”模式,面对妻子李玉茹的“琐屑纪实”模式;作为三者的对比,还要简要讨论曹禺在创作生活中不感焦虑的一个阶段,即1941年前后,与方瑞通信中的“流通转化”模式。
一、“流通转化”:曹禺方瑞通信中的创作灵光
《曹禺年谱长编》和万方所著《你和我》中,首度披露了数量可观的曹禺方瑞通信,共计48节。除了曹禺落款“二月八日”的一封完整去信外,均为未注明日期的片段式密信。这些信件包含明显可与《北京人》和《家》对读的内容。
1940年夏,方瑞到达江安,并与曹禺相识。同年秋,曹禺开始创作《北京人》。曹禺承认“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6],曾文清与曹禺、曾思懿与郑秀的对应关系也容易推知。在写作《北京人》的当时,曹禺很自然地将对合法妻子郑秀的厌烦、憎恨、惧怕等多种感情投射到曾思懿身上。[7]
在此前提下,从曹禺方瑞通信中,可以隐约窥见信件文本与剧作文本相互流通转化的机制。例如:
你的根基是厚的,我一直相信你的力量只是潜伏着。我也相信你不肯使她长久蕴藉在心里,春天到了的时候,你的生命的力量会像山洪冲决了堤一般奔流出来。你是一棵大树的根芽,你生命内藏蓄着松柏的素质。说你是一枝幽兰,那是你的现在。我望见你的将来。[8]126
这非常近似于曾文清与愫方人物小传中的表述:
早年婚后的生活是寂寞的、麻痹的,偶尔在寂寞的空谷中遇见了一枝幽兰,心里不期然而有憬悟。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恍若一片明净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幽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9]
这封信写于1941年2月8日以后,此时《北京人》的写作早已开始,所以无法确定这两段文字是从剧本流入了信件,还是从信件流入了剧本。然而可以知道的是,当曹禺为曾文清与愫方的人物小传定稿时,他已经以“望见”方瑞“生命的力量”的“心地坦白人”自居了。只是这时他们的恋情处于隐秘阶段。曾文清对应着曹禺性格中聪颖醇厚、温和软弱的一面,愫方对应方瑞性格中哀静孤独、温厚固执的一面,二者都不幸处于曾思懿的压力之下。实际上,到《北京人》完稿上演的1941年10月,郑秀的确已经知道了这段婚外恋情。[10]261-262然而,曹禺方瑞通信向《北京人》文本的转化,毕竟还不甚清晰。到了1942年的《家》,由于恋情的逐渐明朗,这种转化不仅具有了更为显著的文本标志,而且产生出更多的人物变体。
1940年11月,曹禺起意改编《家》,并于1942年夏秋间完成。学界一般把《家》中觉新和梅的关系,投射到曹禺和方瑞身上。更有学者指出,瑞珏就是曹禺于婚姻内外的情感痛苦中所幻想的理想郑秀形象。[11]然而,曹禺和方瑞在《家》中另有一层原型关系,那就是曹禺与觉慧、方瑞与鸣凤的对应。已有学者指出,曹禺曾将方瑞来信的内容作为台词写进剧本。[12]但是曹禺一人可以对应觉新和觉慧两个人物,这一点在曹禺与方瑞通信中才有直接的证据:
总之,只过去一段苦日子,各种可能的打击经过以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好好安排一下,把这段短短的生命充实丰满,使这一对魂灵都不必在天涯海角各自漂泊。……想想上帝造了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活,真正地活着,而我们是真正地活过,幸福地活过。我们就没有糟蹋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都是世上无可比拟的骄子。[8]125
可见曹禺并非将此视为一段简单的恋爱,而是把它当做自己和方瑞重新“活着”的契机来看待的。《家》中具有这种品格的,显然是觉慧而不是觉新,他也反复宣告自己在爱情中“活着”:
觉慧(全身充溢着不可阻塞的生命的力量)我活着,我活着,我在活着!(大叫)鸣凤![13]202
这样的生命宣言,在觉新与梅之间受阻,却自然而然地流淌进觉慧与鸣凤的爱情体验中。同时,当曹禺和方瑞隐秘的恋爱逐步明朗,即将向周围人公开时,曹禺极力鼓励方瑞:
伯的信要写的,可怜的译生,我知道你心里的苦痛是说不出的,你不肯有一丝伤了伯的心。但是世上有一种不可避免的事,任何人也要在它面前低头,难道伯真舍得你“清操自晶”,在不可及的梦想中过一生?……我盼望伯来,我好当面和他谈谈,我要把我为你和我的计划完全讲明白。他知道我把你看得多高,多重,我把我的生命寄托在你身上,我没有犹疑,我不是那样轻浮的浅尝辄止的。[8]130-131
无独有偶,觉慧也认为必须要把他和鸣凤的恋爱“告诉人”,不能让鸣凤活在幻梦中:
觉慧(焦灼地)不,鸣凤,这样待下去,太闷了,我不愿意瞒着,我要叫出来,我要喊,我要告诉人。[13]203
由此观之,《家》相较于《北京人》,以曹禺、方瑞、郑秀的三角关系为原型的人物形象,从三个增殖为五个:觉新仍然来自曹禺性格中温和软弱的一面;梅亦来自方瑞性格中哀静温厚的一面;瑞珏来自曹禺内心假想的通情达理的“郑秀”;而真诚勇敢斗志昂扬的觉慧,和受到鼓励坦诚表白的鸣凤,却源于曹禺和方瑞从隐秘转为明朗的恋爱中,诞生出的崭新人格品质。此时曹禺的态度明显“反觉新”而趋于觉慧,在与巴金的通信中,他甚至点明:“我不肯像‘家’中的‘觉新’那样委屈了自己的生机”[8]97,因而将自己无法在觉新与梅的戏剧情境中实现的愿望,充分灌注到觉慧和鸣凤之间。
总之,从最新发表的信件来看,曹禺与方瑞的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人格品质与生活态度,这一切闪烁着灵光的感性素材,都被当时感觉敏锐、笔致细腻、创造力旺盛的剧作家曹禺,尽可能地转化和投射进了《家》的人物群像当中。他在信件中以灵魂共鸣的爱人身份,真诚恳切地表达爱情的受阻与激荡,这种充满戏剧性的书信体写作,顺畅高效地流入同一时期的戏剧文本当中,因而完全有利于其戏剧创作。
二、“挣扎解剖”:曹禺巴金通信中的创作延宕
自从1933年因发表《雷雨》而结下友谊以后,曹禺与巴金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络,例如20世纪40年代曹禺告知巴金自己与方瑞的恋情,60年代巴金曾在日记中记载“家宝来信”等[10]630。本文考察了收录于《曹禺全集》和刊登于《收获》杂志的百余封信件,发现曹禺晚年以作家和挚友身份面对巴金时,其创作焦虑表现得最为强烈,呈现出不断挣扎、自我解剖,最终归于无限延宕的表达模式。因而这部分材料构成了曹禺晚年创作困境的最直接证词。从中不仅能窥见曹禺创作焦虑的具体样态,还能总结出曹禺的生活经验不再成为其创作源泉的规律与成因。
曹禺巴金通信中的创作焦虑,首先表现为双方都高频率地提及创作问题。巴金坦诚地指出曹禺的问题,“你有很高很高的才,但有一个毛病,怕这怕那,不敢放胆地写,顾虑太多”。[14]曹禺对此的困窘和挣扎跃然纸上:
在京,还是那样。开会,写短文,见外友,实不胜数,总要事渐大,做一件是一件,实不想推托。但写剧本事未尝忘;你的话,我总要记住。忽发奇想,真想写本小说,作为最后“冲刺”。可见如何昏愦!
我也要学学你,写点东西。也许把《桥》续写,也许是写点与现实有关的东西,但肚里空空,我将寻找!寻找真能使我喷出熊熊火焰的东西!
我每天清晨起来,若有点精神,总在想点或者写点东西,不想昏过,想在我最后的几年中写出点东西,哪怕是极不像样子的,也要写出来。只是拿不准,什么时候可以成形。这远不如从前你和靳以在几十年前,约我写稿子,我写戏一月一幕,像写连续小说似的,按期寄出去,绝不误期了。[14]
曹禺向巴金坦承自己想要“写点什么”却写不出来,几乎是每封信必备的程式化动作,他似乎进入了一种思维怪圈,这种症候因为不间断的书写行为而日益强化,无法摆脱。何况,同为高龄作家的巴金仍在喷出“熊熊火焰”,他表示,“我一天就靠动脑筋才活下去。我不曾做到完全搁笔,就得讲真话,还要写文章,而且还要得罪人”。[14]这不能不让曹禺更感愧疚:
祝贺你,《巴金全集》你编好了,出版了。这是你的毕生的心血。你的爱,你的正义感,你的智慧在《全集》里放出热情,给人们以温暖和鼓励。……我平生最感到的,是你给朋友的热与力,你给我以无限。我是多么渺小,不是自卑,是我这一生的懒惰,整日地悠哉悠哉恍惚了八十年。[14]
公平地说,巴金晚年从事的散文写作,相比曹禺高度成熟的“五大名剧”,难度显然要低得多。但是在曹禺巴金通信的语境中,能否争取利用晚年时间继续写作,这不仅关乎本职工作,更加关乎与身体疾病作斗争,重拾和高扬自身的生命力,如曹禺所言,“我劝你写文章,也是为了保养身体,也是为了治病”[14]。然而,无论戏剧、散文还是小说,自1978年写出《王昭君》以后,曹禺的成形作品延宕许久,终究一无所得,而他的创作焦虑问题,从1992年通信之后,也终于鲜少再提。
曹禺巴金通信中的曹禺创作焦虑,当然不仅表现在数量和频率方面。其实,曹禺非常清楚自己创作困境的根源:材料缺乏,好发空论,琐事缠身,懒惰拖延。其中“琐事缠身”属于客观环境因素,“懒惰拖延”属于主观性格因素,一时之间都难以改变。“材料缺乏”与“好发空论”则关乎文学写作本身,前者既指宏观的写作题材,也指微观的感性素材,影响作品内容质料的丰满程度;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关系到抽象思维和哲学思想,影响作品的形式结构和主题深度。从信件材料来看,晚年曹禺在日常生活中,并未完全失去感觉的敏锐和灵感的闪光:
我忽然又像成了一个还不会说话,甚至不会走路的婴儿,缚在摇篮里,被一个大手举起,一来一往地忽上忽下地摆动着、起伏着,我不能哭,还不知道怎么才是哭,只会呻吟,小猫儿似地哼哼。我恐惧,仿佛又不是什么恐惧,感到莫名其妙的空虚,因为连恐惧、喜悦、痛苦都没有了。这是什么人呢?是我么?抑或不是我么?[15]477
更不必说深情隽永、富于诗性的“彩色的梦”片段,其实是非常好的戏剧独白:
睡了一夜,并不安稳,时醒时梦,仿佛我又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树林里一个人游来走去。当然有树木,有花,有阳光从树梢里透下来,甚至听见各种好听的鸟鸣,还闻见一片青草的香。我高兴,居然要唱,躺在好大好大一片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几乎要笑起来。……没什么话可说的,就唱一支歌吧。我正要高声唱出一支世上最美的歌,忽然我怎样用力,甚至于嘶喊,也没有声音,只感到痛,不知什么地方痛,就醒了。……芾甘,你曾梦过有颜色的梦么?我昨夜的梦都是彩色的,比最好的电影好得多,因为我身在其中。[15]479-480
单独审视这些片断,其质量并不亚于曹禺方瑞通信,然而由于晚年生活体验的逐渐固结,它们不再以丛集的方式连续出现,而是稀少地漂浮在数量庞大的通信之中,许多时候与上下文内容和风格完全割裂,因而不可能涌入虚构写作之中。与此同时,曹禺愈老愈弱的抽象思维,也不足以支撑他花费巨量的时间和精力,将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凝聚在精巧复杂的戏剧结构当中:
他想写“斗战胜佛”孙悟空,写如来,外加一个大学者,而大学者的脑子和心都空空如也。
还想写一个戏,一个人物叫“胆大”,另一个叫“胆小”,胆大、胆小和神要进行一场对话,想法到此戛然而止。
还有一个《黑店》,有了一张人物表,有他们的性格和各自的身世,还写出一段文字……
一页纸的顶端写着“张好好”三个字,这张好好是个歌女……可除了这一段歌词再没有别的。[8]261-262
这是万方对曹禺晚年创作情形的描述,再次印证了曹禺有力产生、无力综合他的创作素材。如要转而借助理性的思索,又痛感“到现在,我却不懂什么叫做人?大约多学一点哲学就好了”[15]479;他对当代社会现实的认知,自己也知道是“拉拉杂杂发些空议论,也是病中呻吟语”。于是,在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憎中,偶然的灵光只能算作“破天荒的奇迹”。[14]
因此,信件材料构成了对曹禺创作困境研究的过程性的佐证,曹禺晚年的创作困境,并不仅仅表现为没有写出“名剧”这个结果。他在反复向巴金解剖创作焦虑、创作任务的同时,其实也一直在尝试继续写作,这些不成规模的写作活动,恰恰证明了他创作的“质性”并未被彻底摧毁,只是再也无法凝聚为鸿篇巨制。除了虚构性创作屡屡失败之外,曹禺与女儿通信中的创作体悟,也成为他有意无意地表达、转移和缓解创作焦虑的重要方式。
三、“鞭策寄望”:曹禺与女儿通信中的创作体悟
曹禺写给女儿万黛、万昭、万方、万欢,继女李莉、李如茹的信件,部分收录于李玉茹选编的《没有说完的话》,部分收录于《曹禺年谱长编》。这些信件虽然基数不大,但是由于除万黛和万欢外,其余几个女儿都从事过文学创作工作,所以曹禺与她们的通信,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创作体会。例如,1980年万昭曾打算将《日出》改编为电影剧本,曹禺给出指导:
戏能跳出旅馆,分割大段对话,变动结构都应该。我不大主张一定忠实于原作。[10]771
此次修改很见功夫。你们用了心,已经有些电影化,但仍感你们舍不得改动剧本。忠于原作,要在精神,不在词句用了多少。
此剧本应以陈白露为主角。……她的死,不是为钱逼的。……因此,我十分赞同你们把方达生与她最后的对话放在最后,放在她死前一刻。那是十分有力的改动的。[16]317-318
可见,曹禺非常渴望自己的旧作能在年轻一辈手中有所变动,重新激发其作品潜在的生命力。此外,对李莉的影视编导工作,以及李如茹的写作尝试,他也极力支持。阅读李莉的《激流》剧本以后,他写下长信:
有两点,请注意:一、觉慧的“我控诉”稿件可作为基调,也可作为主题歌,这是“激流”中贯串的情感,它在悲痛场面可用,在有积极兴奋场面可用。觉慧是控诉旧社会反人性、反理智的压迫人、毁来人的代言者。
其二,我以为觉新这个人物不可写得过于重复。……不可一味写他那种忧郁、妥协,以至于害了人又害了自己的那种怯弱、糊涂,写到使人不可忍耐的地步。觉新这个人物写得十分真实,但剧本要有变化,要有突变。[16]341-344
对李如茹的“戏剧片断”、剧本和理论写作,则更加轻松明快地表示鼓励。
当自己的戏剧创作已“无力回天”之时,曹禺将大半生积累的创作经验,悉数倾注到女儿们身上。在诸女之间,万方的文学创作事业最得曹禺牵挂,因其不仅在创作风格上与父亲接近,更加遗传了其父的性格特征。细读曹禺与万方的通信可知,他对万方的鞭策之情显然不同于其他时候心平气和的“经验传授”,而是更深层次地触及人性弱点与现实风险,这些弱点与风险不仅仅指向万方,更以血缘纽带为基点反照回自身:
千万不要犯错误,多向领导与群众听取意见,这是年老的父亲的话,我也知道这是保守的,不成大事,但我真愁你如何写下去。你真能写出不犯错误的剧本么?我担心极了。[10]672
当万方以创作为志业之后,曹禺更是时刻耳提面命:
不怕改!不怕两三遍地改,十几遍地改。……耐性与韧性,百折不回的精神对你万分需要!我相信你的才华,但你一定要不怕折磨!“大器晚成!”万不丧气。偶有挫折,便感到一无是处,自己一生都完了!这是软弱的人,没有出息的人的软弱表现。[10]672
无论是对“犯错误”的恐惧,对“耐性、韧性”“苦干”与“勇气”的呼吁,还是对“软弱”“浮、不重”的批评,都应看作曹禺在向自己的内心发出呼告,因为他所担忧的万方可能在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正与他自己的性格弱点和人生经历若合符节。正是因为曹禺深知自己的文学创作已经遇到绝大的困难,所以才将希望寄托在年富力强、才气充沛的万方身上。对于“作家曹禺”而言,这是万分无奈之举;然而对于“父亲曹禺”而言,这又带来了极大的宽慰。曹禺与女儿的通信中,“作家”身份和创作焦虑,不再构成同辈作家的对比,而是构成后辈作家的源头与镜像,它通过有意无意之间卸载到女儿们身上而有所缓解。
四、“琐屑纪实”:曹禺李玉茹通信中的创作嬗变
曹禺晚年公开写作的匮乏背后,还存在着数量可观的私人写作,正是在这些书信、日记、手稿乃至“纸条”提供的私密语境中,他仍在维持其写作活动。此时,饱受焦虑的“作家曹禺”近乎消失,沉浸于日常琐屑的曹禺本人,反而更加自如地完成了虚构性创作向纪实性创作的嬗变。曹禺巴金通信已是一种相对私人的写作,然而这些信件还是容易进入个人文集、文学期刊等公共传播媒介。相比之下,曹禺与妻子李玉茹的通信,数量相当庞大,在目前可见的曹禺通信中占比最多;更重要的是,这些信件的情感语境最为私密,从未得到与《曹禺全集》和《收获》杂志同等程度的关注。
曹禺与李玉茹的通信很少提及创作问题,这里的“不表达”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百余封信件中仅有两处,其中一处还是因为收到了巴金来信。其余多数时候的信件,都充满了生活琐屑的铺陈。“懒于”公开写作的曹禺,在向妻子汇报饮食起居细节时,却不厌其详,丝毫不懒:
二十七下午我与小白到小方子家,她准备羊肉片涮锅子,肉足有二十斤。小蓬蓬吃两斤,小白也吃了两斤,我肉不可多吃,吃了粉丝、拌粉皮、真正北京烧饼。我尝了一点豆腐,奇怪,一点也不觉得好吃了。还有拌鸡丝,相当丰富,满满一桌子菜。她们服侍我,我真成了老太爷,只连说可惜妈妈不在北京。[16]92
另有一些生活趣事:
因为天天望信,恨不得一天收到你二十四小时的信。得到信后,我看了一段,就放在信封里,小白问:“怎么了?”“我不能都看,要留着一会儿再看。看完了,不就没有了么?”小白都笑了。我加意沉着,上午看了一页,午睡后,接着再看,今天再慢慢一遍一遍地看。[16]137
有万伟,就是那个基督教的狂人、我的侄孙。他从前告小白把佛教的书都拿开,别给我看,还找一个教婆,来劝我向上帝祈祷,而且拿出祈祷文,要我照着念,我没有理她。这次我告诉万伟,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决不相信基督教。他说你是我叔祖父,你病了,我来看你,此后,还要来看你。[16]247
与曹禺的戏剧创作相比,很难说这些内容具有多高的审美价值。然而其取材之务实、抒情之真诚、用笔之闲趣,至少超越了不少公开发表、立意草率、文笔粗粝的虚应故事。这说明曹禺在与家人亲切对话的语境中,实际上是“安于”不再进行虚构性写作的现状的。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写作活动悄然发生了由虚构到纪实的嬗变——不妨认为这些充满日常经验和生活情调的通信接近于散文。
此外,曹禺李玉茹通信中,还包含极少数溢出常规、激情迸发的诗性表达:
“他总在温柔的想着你/怀念你,如春水灌进兰花、荷花、菊花/的根,渗入土壤,滋养,催开,怒放/一朵朵艳丽的花,灿烂的花/香的花,有知觉的花,微微颤动的花/夜露浸湿的花/还有那沁入人灵魂的桂花/小得像一丛丛嫩黄的珍珠/那每棵嫩黄香甜的珍珠,也在唤着你!——/醒醒吧!不要藏在好梦里,虚幻的梦/骗与谎,阿谀与媚笑/织成的梦![16]76-77
这是一首长诗中截取的一小段,于辗转反侧的思念之情中掺入意识流成分,仿佛从纪实性写作滑向虚构性写作的细微踪迹。不过,同李玉茹的婚姻生活毕竟缺少戏剧性因素,如此热烈的情感流泻也就止步于此。与此类似的,还有曹禺写给早已逝世的生母的长诗:
母亲,我的母亲!/我七十四岁了/你才十九岁!我的小母亲/生下我,像未开的花,难产,死了/我没见过你,只看到一张相片/你坐着,一个小姑娘,发亮的眼睛,一双小脚/然而照片也丢失了,我只在朦胧记忆中看见你的幻影
妈,你短短的生命,少受许多苦/可我情愿你受一些苦,明白这个世界/虽然你还是那样苦念着我/对我微笑,我还是你心里那个呱呱坠地的小心心/你就这样想念我吧,我的妈妈/七十四岁的老头,叫“妈”,想叫醒他小小的母亲。[8]286-289
对母亲妻子直抒胸臆的呼唤,是最纯出自然而缺少戏剧性的事件,但其中埋藏着丰富的情感颤动和审美意蕴,如今依然令人动容。的确,此时的曹禺再也写不出一部杰出的剧本,然而这些数量不可小觑、质量亦超过“应景文章”的写作产物,至少作为文学史、生活史的重要材料,应该进入资料编纂和学术研究的视野。因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涯,并不仅仅呈现为整饬精良的文学作品,更应呈现为平凡流动的生活历程。与李玉茹的通信提示着,曹禺晚年写作的重心转移和形态嬗变,或许也是面对难以撼动的“创作焦虑”时,无意之中旁逸斜出的特殊表达模式。
信件材料是曹禺晚年陷入创作焦虑、困窘乃至病态的指示针。如果说以往研究,已经从主客观两方面,完成了关于“曹禺创作困境根源”的逻辑推断,那么本文就是将这一困境充分具象化和语境化,揭示出它在作家的主体性方面,总是随着身份关系和生活情境的转移而变化的的现象综合。曹禺在信件材料中,展示出了极为丰富的侧面,除了作为“作家”的自我,还有作为“丈夫”“父亲”“友人”的自我。“作家自我”在面对创作困境时,经常表现出一种道德性的紧张;而“亲友自我”却相对放松,即使在没有创作出成形作品的时期,也仍然闪动着感觉性和经验性的可能,无论是早年信件流通转化为剧作文本,还是晚年信件朝向纪实性写作的嬗变,都是研究曹禺创作问题时不容忽略的具体表征。因此,以往研究指出的诸多原因,往往是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机制,作用于“创作焦虑”这一动态现象的不同层面。通过收集整理信件中的直接证据,曹禺的创作困境与创作焦虑,具备了更加清晰生动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