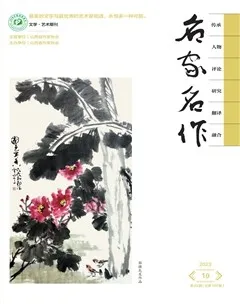艺术就是生活
木 之
我是一个做音乐的,人称艺术家,却自觉不“专业”。按照传统,“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我也算是音乐世家了。当儿子呱呱降临的时候,父亲说,让他学个什么乐器吧,我却不以为然。
儿子5 岁前,在我这个以崇尚快乐教育思想之名行懒散之实父亲的监护下,每天在树林、山上、湖边等各种野地玩得不亦乐乎。眼看着别人家孩子每天又是钢琴又是舞蹈的,今天考级明天比赛的,荣誉证书一张接一张,掌声一波连一波,家里人有点着急了。咱家孩子也不差呀,不行,要卷起来。美好的童年就这样在对比中戛然而止了。
儿子也开始像别人家孩子一样,做起了琴童。我背着跟他一样高的大提琴上班打卡,带着他赶时间、见老师、等候、背琴回家,而后每天就在脑袋里“认真练琴与快乐童年”“练琴就是好玩”与“要学就好好学”等各种思想博弈之下监督他练琴。练琴是很枯燥的,我尝试用生活的逻辑去引导。比如,每一个乐句就像是生活中说一句话,总是开头比较强,而后逐渐弱下来,说完之后会有呼吸;又如,音乐的节拍就像走路,可以快也可以慢,但大部分时候总是稳定的节奏,两只脚有轻有重;再如,手要放松,怎么办呢,自然下垂的状态下手型就是放松的。还挺有效果,他偶然的一句话提醒我,“就是平时玩的状态”,我大赞,“艺术就是生活”。
两年后,孩子提出不想学琴了。在家人不太坚决的反对声中,我决定让他回归“我的快乐童年”,不再学琴。其实,是我累了,他也累,这么小的孩子每次安安稳稳地坐上40 分钟,换位思考,我自己也做不到。
三年级,儿子进入校广播站担任小小播音员,让我指导播音,我不会,翻书又都是理论。我想,播音就是把话说清楚,咱依葫芦画瓢,观察一下新闻联播,现学现卖。我指导他,只要稍慢点说清楚每一个字,让自己的声音像音乐一样有高低起伏就行。他说,“这跟平时讲话没什么区别呀”,别说,效果还真不错!
四年级,儿子开始在学校晚会做小小主持人。面对那么多人,紧张也还好,就是主持词说得大失水准。回家后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像平时一样,只要放慢呼吸,做好你自己,“旁若无人”就行。后来,他就成了学校晚会主持的“老赖”,一直到小学毕业。
艺术看起来很远,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的继续与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