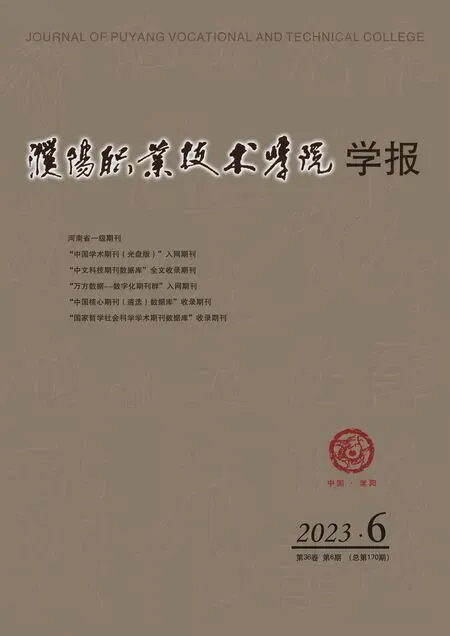陈伯海唐诗学质性论的理论意义
何 潇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陈伯海先生所创设的“唐诗学” 系统是将唐诗完整、 系统地论述归纳的理论。 以史料编纂工作为基, 对唐诗的整体形态有着系统的梳理, 所提出的诸如“什么是唐诗” 等问题, 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唐诗学” 不仅从历史文化等角度来阐释唐诗, 也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审思之, 促进了唐诗学研究。 然而, 学界目前对于陈伯海先生所提出的“唐诗质性论” 这一问题, 却鲜有关注。 笔者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入手, 对“质性论” 于唐诗学体系中的理论意义、 地位等问题, 以及文学史意义, 如唐宋诗之争等问题作出探讨。
一、 质性的理论意义
质性研究实则就是讨论本体,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正本》 云: “开宗明义第一章, 用来讨论唐诗的特质, 或者也可以叫作唐诗的本体。”[1]5
(一) 质性的本体性
对本体的讨论通常包含着两种含义: “起源”与 “本原”。 起源这一意义在中国哲学中通常以“根” 等概念来表达, 起源主要讨论的是事物存在的源流; 本原是事物存在的凭借, 也就是“使之成为它本身” 的本质。 前者重在探讨存在的“根源”,后者意在解释事物之 “根据”。 为了探讨这两方面意义, 海德格尔指出: “本源 (Ursprung) 一词在这里指的是, 一个事物从何而来, 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2]1亦即是说, “从何而来” 的根源及“何其所是” 的根据两方面问题共同构成了本体论的讨论。
在艺术领域的本体讨论中, 柏拉图的理式观念认为: 世界上只有三种床, 一种是自然的床, 一种是木匠造的床, 再一种是画家画的床。 自然之床是由神创造的, 是真正的、 永恒不变的床, 即床的理式 (Idea), 是完美的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客观可见的床, 但柏拉图认为客观是对理式的模仿, 艺术则是对模仿的模仿。 但这样的理解却有颠倒文学艺术作品的本体之嫌。 如前述, 追寻本体的含义可以分化为“根源” 与“根据” 两方面, 而艺术的本体并不是“自然的床” 就可以涵括的, 而应当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 或说“理念”。
举例来说, 画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创造出自然所不能存在的符合作画者理念的“完美” 的光影效果, 艺术的高明正在于精神意志的展现而非对自然的模仿。 故黄宾虹指出: “画中山川, 经画家创造, 为天所不能胜者。”[3]2类似的观点在 《文心雕龙》 中也有体现: “仰观吐曜, 俯查含章, 高卑定位, 故两仪既生矣。 惟人参之, 性灵所钟, 是谓三才; 为五行之秀, 实天地之心。 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 自然之道也。”[4]1“道” 需要通过人心感悟传之成文, 道能由人而得, 文立则道能显。 人的精神可以触及到本体, 而本体也可以显现于艺术作品中。
换言之, 探寻艺术作品的本质, 实际上指向的是 “概念”。 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正是作者的观念对于“理式” 的理解, 而这一理解又并非仅精神或被反映的自然事物某单方面就可包罗的, 正如黑格尔所言: “艺术家的才能和天才虽然确实包含有自然的因素, 这种才能和天才却要靠思考, 靠对创造的方式进行思索, 靠实际创作中的练习和熟练技巧来培养”[5]35。 自然的因素涉及了被反映的世界, “以意逆志” 式文学研究得以考察艺术家“思考与创造的方式”, 而这一切也都立足于对作品的理解与读者的接受的综合考量上。
要之, 对文学的本体的追问, 涉及的是包含世界、 作者、 作品以及读者各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内容。 对于本源问题中“从何而来” 问题的探讨, 会成为其“如何存在” 的本质讨论。 而艺术作品必然以用 “标准” 的概念来解释 “本原” 或更为清晰,主观评判与客观现实共同构成了标准。
从“模仿说” 的争论来看, 事物存在着理式与客观的相对性。 而回到唐诗学的讨论, 从理式的角度来看, 便有了观念的唐诗学的标准 (理式), 以及客观存在的文学作品。 如果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看, 唐诗质性的问题可以转换为观念的与现实存在的合题。 正如黑格尔指出: “理念不是别的, 就是概念, 概念所代表的实在, 以及这两者的统一。”[5]12正是在此意义上, 唐诗学在社会渊源方面等 “物”的方面进行了探讨, 又结合反映其内容的作品的讨论建构了唐诗的概念及其所代表的物质实在的统一。
(二) 质性对唐诗学研究的理论突破
据此则可将对唐诗的讨论, 从时代的概念中引入对诗歌本身特质、 属性的讨论上: “唐诗不仅是一个朝代的概念, 它还标识着一种诗的品格, 一种审美的传统, 一种有别于其他时代诗歌的特定的质态, 换句话说, 唐诗应该有它内在的、 不可移易的质的规定性。”[1]5这种表述要回答的问题是: 唐诗是什么; 什么样标准评判下的诗歌可以划分为唐诗?同时亦牵涉唐诗是从何而来的根源性问题。
引申到文学质性的问题上看, 对于质性的判定, 通常便会以“标准” 作为依据。 从这一角度上看, 在唐诗学的问题上对于“界定什么是唐诗” 的质性问题的回答就意味着: 对于符合什么样标准的诗我们认定其为唐诗。 由此也产生了对本体内容理解的不同。 也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对唐诗质性的理解千差万别, 同时也体现为唐诗学研究思路的转变。
朱立元《解答文学本体论的新思路》 一文中提出, 应当把“文学是什么” 的“本质论” 提问方式转换为“文学怎样存在” 的本体论(存在论) 的提问方式[6]10, 即寻找和论述文学的存在方式。
这种思路的转变提供了许多对文学的重新讨论的途径。 比如文学是以怎样的存在方式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 唐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 从接受学角度、 历史文化角度是如何被建构的; 或者说将文学本身视作一个与社会历史、 哲学宗教等紧密相关, 变化始终的大系统。 换言之, 可以从回答文学是什么, 到探寻文学的规律是什么。 而规律意味着不断变化的动态性过程。 于是陈伯海提出:
将唐诗本身看作一个不断运动与变化的过程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它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步摆脱前代诗风的拘限, 萌芽和生成自身的一些基本质素……终至整个内核的蜕化和原有质素的衰亡, 于是唐诗让渡于别样的诗歌。[1]6
将唐诗视作运动中的系统, 意味着对质性的研究要参照系统中各个部分的内容, 并且不能孤立地进行时段研究, 正是在此意义上, 陈伯海指出:“一部唐诗学的历史, 从根本上讲, 也就是人们对于唐诗的质的探索史, 是人的认识不断转换与深化的过程。”[1]216从而以质性探讨为核心, 以别流来探求其历史渊源。 换言之, 以魏晋六朝诗的特质为前提, 廓清唐诗的特质兼论唐诗性质的转变, 从而可以认识唐诗质性的产生之肇端, 构成了唐诗学整体系统的逻辑线索。
总体来讲, 唐诗的质性包括吸收前代汉魏所形成的“风骨” 与“兴寄” 等审美质素, 以及形式技巧, 产生了唐诗独特的 “声律词章”。 进而由兴象的两个方面发展, 一是以 “向实” 为方向的 “诗境”, 二是以“向虚” 为方向的“韵味”, 最终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一个唐诗质素, 可略以 “气象” 概之。 唐诗学质性总体上如此但又不断变化。
二、 质性论在唐诗学研究体系中的意义
如前述, 质性的本体意义是其他许多唐诗学研究的根本。 而唐诗质性的生成与 “前” 密切相关,是从历史传统中而来, 故有清源之必要。 继而唐诗的质性发展、 变异, 宋诗的质性又逐渐产生, 故又有别流的问题。
(一) 清源
清源是回答唐诗学本体的一个重要问题, 即唐诗的质性从何而来。 但唐诗的质性形成, 并非简单三言两语可言明, 而是在 “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 之六) 的情况下所完成。 借陈伯海之语讲, 大体上可概之为 “宪章汉魏, 取材六朝”“以文为诗, 博极其趣工” “诗词合流, 骈律互渗”[1]79。以宫体创作角度为例, 可略窥六朝诗质性的转变与唐诗质性的生成。
闻一多认为宫体诗是从题材上以 “艳情” 为主, 走向了一种堕落: “人人眼角里是淫荡, 人人心中怀着鬼胎。” 如 “相看气息望君怜, 谁能含羞不肯前!” (简文帝 《乌楼曲》) 之类诗作, 又说:“堕落是没有止境的。 ……变态的又一类型是以物代人为求满足的对象。 于是绣领、 袙腹、 履、 枕、席、 卧具全有了生命, 而成为被沾污者。”[7]19如《子夜四时歌·秋歌》 第四, “开窗秋月光, 灭烛解罗裳。 含笑帷幌里, 举体兰蕙香。” 以物写人, 但尽是艳情, 闻一多认为, 宫体诗赋予了物以 “人”的属性, 但这种属性却令人鄙睨, 因其只有淫荡而无情感。
宫体诗一方面以物代人, 另一方面又将人视作物。 闻一多认为宫体诗的质性表现在内容题材上的“艳俗”, 并造成了即便描写痛苦也是观赏玩味的态度, 指出其与现实绝缘的深层的“浮靡” 性。 闻一多认为直到卢照邻、 张若虚等人, 宫体作品才从宫体的内部进行了自赎。 换言之, 六朝宫体诗的质性的转变, 是从情感内容、 宇宙精神的角度完成的,并开启唐诗质性的生成。
但唐诗的质性显然不仅体现于题材内容上[1]83。故有学者指出, 闻一多也 “放弃从形式上去评价,只从内容上做批评”[8]79。 宫体诗反映出艺术技巧上的巧妙对唐诗质性的生成有着重大作用, 即使是对六朝诗风大为批判的陈子昂, 对六朝诗也有借鉴与模仿。 如其 《上元夜效小庾体》 其中 “芳宵殊未极” 一句也出自谢朓《游敬亭山》: “缘源殊未极,归径窅如迷” 句。 而且此类现象在唐人诗歌作品中颇为普遍, 即便是大诗人如李白、 杜甫、 孟浩然等也都从汉魏六朝诗中汲取营养[9]25-49。 陈伯海也指出: “复兴汉魏, 是要坚持它的方向; 借鉴六朝,则更多着眼于它的形式和技巧。”[1]83如沈约的 《丽人赋》: “响罗衣而不进, 隐明灯而未前。” 内容虽透露出明显的轻薄与浓艳, 但不写而写, 构思可称其妙。 再如写景状物的作品, 必是极有闲暇之人,方可使其观察细致入微而发见诗意。 如简文帝《折杨柳》: “叶密飞鸟碍, 风轻花落迟”, 庾信的“荷风惊浴鸟, 桥影聚行鱼”。 此种于细微至小处发见诗意, 且以仰视见鸟、 俯身观鱼的精妙炼句, 加之在同一个闲适的审美氛围中达成的对仗, 凸显了六朝宫体诗精致工巧之特性, 直可与唐诗佳作并提。
从六朝诗歌质性的角度上看, 这些宫体作品技巧的妙处在于从表述简单质朴的民歌中吸收了部分内容作为自身质素的特点, 并在永明体的格律对仗的写作探索中更进一步, 成为近体诗的前期实践。这得益于宫体诗的本身质性的特点。 首先从篇幅上看宫体诗通常较短, 易于表现刹那的诗境, 故也必须于碎片式的描写中观察凝练出最具诗意的内容。以庾信等人为代表, 总体上宫体作者的绝句艺术技巧较为成熟。 其次, 宫体诗的描山画水不似谢灵运标新立异, 但状物功夫又可称妙。 这与描写的题材也有关系, 既为宫体, 作诗的材料无非是女子, 亭台池榭、 花鸟鱼虫之类, 不得不在描绘情状上大下功夫, 状其声色。
(二) 别流
《唐诗学引论》 中引入了新的唐诗分期认识体系。 在其“别流篇” 中对传统唐诗的“四期说” 提出批评, 并把唐诗划为三期: 唐初至安史之乱前为成长期, 安史之乱爆发至穆宗长庆间为转变期, 敬宗宝历以下至唐末为 “衰蜕期”。 而唐末的 “蜕”字更代表其变异及生新之意, 进一步指出唐诗质性向宋诗的让渡。 分期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唐诗演进中的内在逻辑性, 这种逻辑性其实就是唐诗的质的形成、 转化与衰变的轨迹。
对唐诗分期的研究中, 陈伯海指出四期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处理李、 杜与元、 和的归属问题。进而指出前人的问题在于把“正变” 与“盛衰” 混为一谈, “正” 即是“盛”, “变” 即是“衰”[1]103,进而提供了新的思路, 即正确地认识唐诗质性产生“变” 的时段。 陈伯海认为唐中期以杜甫为代表已经产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言志述怀” 的宗旨改换成了 “感事写意”, 所谓 “蜕” 字可谓由此而生。 所谓感事写意者:
感事包含着 “述怀” 与 “感事”。 前者注重主观情怀, 后者重在客观事象的感发,……论事是重在理智的活动, 因而我们把它叫作 “写意”。 不称之为 “说理” 盖因 “写意” 的含义比 “说理” 广泛。[1]117
大体上, 感事写意从杜甫到元和诗人处生发。感事在张、 王、 元、 白处充分发扬, 写意则在韩、孟、 卢仝、 李贺乃至贾岛那里得到体现。 从这一转变可以看出, 唐诗的质性发生了变化, “唐前期是以‘风骨’ 为第一要素的”[1]127, 但诸如“气象” 等质性概括似乎已不能解释这一时期的唐诗。 如杜樊川之“长空淡淡孤鸟没, 万古消沉向此中” (杜牧《登乐游原》) 自不可与太白诗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李白 《望天门山》) 的阔大气势一概而论。 对此变化学界在唐诗之精神概念所反映的实在问题上已多有论及, 在思想理念上, 这一时期唐诗概念上的特质, 陈伯海概之以“兴寄” 取代了 “风骨”, 而兴象、 声律、 辞章等亦相应发生了变化[1]127。 质性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审美质素上,由“兴寄” 可知唐诗此时已经以感时伤事而有所兴寄之 “感” 的质性, 逐渐代替了 “风骨” 质性的“言述” 之旨。 可见质性又是别流研究的立论之要。
但此时的唐诗仍是以“主情” 为基调的, 故其质性只是开始转变, 待到“‘写意’ 凌驾于‘感事’之上, 压倒并取代了‘感事’ 的功能, ‘主情’ 诗学遂失去其最后的地盘, 而不得不让渡于 ‘主意’的路线。”[10]44此便是宋诗的质性了。 唐诗的这一转变, 亦体现在唐末诗歌中。
以唐末咏物诗可略述唐诗质性的“衰蜕” 与唐诗学“别流” 的意义。 即使是如“含蓄” 等唐诗中随处可见的特质, 在唐末经历了质性的变化后也改换了面貌, 有了新的含义。 以唐末咏物诗为例,“主意” 体现在延续杜诗形式技巧上的追求以及讽喻风气上, 理性思考逐渐大过追求诗意之美。 不同于六朝宫体诗, 即使同是咏物, 也要感事兼论事是这一时期一大特点。 如罗隐 《金钱花》: “占得佳名绕树芳, 依依相伴向秋光。 若教此物堪收贮, 应被豪门尽劇将。” 将咏物诗转化为 “贬人” 之作,因 “感物” 而借题写意, 但需指出, 虽为写意之作, 其贬斥为金钱折腰的时俗之弊的愤懑情感仍为此诗之要。 换言之, “主情” 仍是基调, 故唐诗的质性不失, 但这种诗作直接且大胆, 而且议论之风于诗中更加明显, 绝非盛唐诗之貌, 以 “气象”“风骨” 等质素更难评之。 而写意的成分同样浓厚,直开宋诗特质。
此外, 罗隐的不少名篇佳句纵是含蓄有韵味的诗作, 也非前期质素。 唐末别造一种含蓄, 以描述或议论的笔触在诗外点破诗旨, 发人省思。 哲理意味的诗风愈发浓厚, 像罗隐的 《蜂》: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 此句诗可评之含蓄,但亦非盛唐诗以情感表达之含蓄出发的质性, 含蓄的不是情感的表达方式, 而是讽刺之意, 却是一种偏向理智思考的“写意” 之作了。
由此可见, 唐末的唐诗正在逐渐丧失自己的质性。 唐末香奁体等回归六朝浮靡诗风的作品也开始出现, 这些无不透露出唐诗质性的改变。 表面上看变得似乎重蹈了六朝的老路, 但却是经历了整个唐代诗风的浸染, 又非简单的回归。 故陈伯海概括唐诗的质性发展变化时说: “由发扬主观, 到亢视客观, 以至返归自我, 这正是唐代时代精神演进的周期, 也是唐诗否定之否定的历程。”[1]134唐诗由前期的言志述怀让渡于中期的感事写意以示对现实的不满, 最后客观现实的书写也被唐人所放弃, 转入了自我的世界之中。
三、 质性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可见, 质性在唐诗学的论述逻辑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清源与别流的问题都由其所衍生且以其为根据。 此外, 讨论质性的必要性更在于, 质性可以使一个事物独立出来分辨区别于其他。 故质性讨论在文学史的角度上看, 可以分定唐、 宋诗之别。
(一) 分别唐、 宋诗
吴宓对于唐宋诗的质性界定为: “唐诗富于理想, 重全部之领域, 浑融包举。 宋诗偏重理智, 凭分析之功能, 细微切致。”[11]260唐宋诗的质性之别被其指为理想与理智之分, 表现在唐诗的博大雄浑和宋诗的细致分析上。 而关于如何评判唐宋诗, 钱锺书在 《谈艺录》 开篇第一节 “诗分唐宋” 明确提出: “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 他有一段著名的话称: “唐诗宋诗, 亦非仅朝代之别, 乃体态性分之殊。 ……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 为称谓之便。 非唐诗必出唐人, 宋诗必出宋人也。”[12]3所论大改前人分别唐、 宋诗的依据, 体性之不同虽与朝代有关, 但更多指向了审美要素以及诗歌的表现形态。
唐诗、 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 那么唐人中能有宋诗, 宋人亦能言唐诗, 时代的界限被打破。因为唐代诗歌中也不乏偏于议论的 “尚理” “主意” 之作, 譬如“思力深刻” 之杜甫[13]16, 而宋代诗歌不乏注重情韵的自然感发之作, 如张耒强调作诗的“直寄其意” “满心而发, 肆口而成, 不待思虑而工, 不待雕琢而丽”[14]362-363。 换言之, 以 “主情” 为主, 韵味见长的唐诗也可以出自宋人之手,以“写意” 为主, 尤擅工巧的宋诗也可出自唐人笔下, 将唐宋诗之分视为唐宋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 不如说实则是文学质性的两种体现。
故钱锺书指出: “与其把政治制度、 社会形式来解释文学和思想, 不如把文学和思想来解释实际生活。”[15]99-100此种思路将文艺作品的本体讨论纳入另一种轨道。 实际上, 仍需注意的是文学精神本身与所反映的客观现实的统一性。 以钱锺书为代表的质性划分唐、 宋诗的观念, 这种判断根源对诗本身的把握, 在分判唐、 宋诗质性要素之不同时, 在主、 客观统一性视角下, 诗人在表达方面的差异亦需考虑。
例如同为写“池水” 的唐诗与宋诗, 就透露出截然不同的质性。 此类作品盛唐时如太白“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 人的精神理想不受客观事物的约束, 而直述胸中之感。到晚唐如曹松 《春草》 “不独满池塘, 梦中佳句香。 春风有馀力, 引上古城墙” 一诗, 则是以物、事来引导情感, 且透露出现实与精神的分离。 此亦可见唐诗质性的转变, 但仍是以 “主情” 为基调,此类诗作不胜枚举。 然宋诗中不仅写池水者众多,且透露着明显的写意说理倾向, 如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子身为理学家, 此诗也渗透其理学思想, 其喻池水以“鉴” 字便体现出诗之蕴含深广的写意说理的宋诗质性。 取“鉴” 为喻与“心犹镜, 仁犹镜之明。 镜本来明, 被尘垢一蔽, 遂不明。 若尘垢一去, 则镜明矣”[16]1109的心性上的工夫修养有关。 而有学者将其理解为 “明镜止水” 之 “静” 的含义,实则不然, 这还与其“辟佛” 思想有关, 若将朱子的心性修养的目的解释为 “止”, 则无法将之与禅学区分。
实则其“镜” 之喻还有镜能观照之意: 有关于“鉴” 字,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曰: “有光能照物谓之镜” “镜亦可名鉴”, 而 “鉴所以察形。 盖镜主于照形”[17]703, 可见引“鉴” 字本身所包含之观照意才是主要意思, 而察形照影则有主体的能动性, 固非禅学之 “寂”。 此则又与其 “居敬” 工夫关联甚密, 朱子曾云: “圣人相传, 只是一个字。尧曰 ‘钦明’” “说尧之德, 都未下别字, ‘敬’是第一个字。”[16]366-367所谓镜之“明”, 则无非是保持自身灵明而常持醒觉之意, 故“敬” 字工夫是其“圣门之纲领, 存养之要法”[16]371。 如上, 只此开头一句之义理, 学界便多有争议与诠释, 此所谓宋诗“写意说理” 之质性, 同为写意之作, 但与唐诗于“主情” 基调下的理趣迥然相异。
(二) 质性理解不同的诠释多元化
唐宋诗的划分依赖于对质性的判断, 也就是标准的选定。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 标准认定的不同, 将会在同一个认知角度下, 造成同一个研究对象的不同结论, 如唐人选唐诗的标准。
第一, 对于唐诗质性认识的不同会导致选诗的各家标准不同, 从而影响选本收录内容。 即哪些符合自家标准的诗人诗作能够录入选本, 而多家选本甚至不收杜甫诗作。 这也表现在编选的范围大相径庭, 造成了有的选本以盛唐诗为最尚, 而有的以大历诗人为主要的遴选对象。 第二, 唐诗选本的主导思想不同。 唐人选唐诗有的以 “诗教劝讽” 为宗,而有的以文学性为首要标准, 如顾陶的 《唐诗类选》 树“察风俗之邪正” “审王化之兴废”[18]7959为选评准则, 又有如韦谷的《才调集》 却以艺术追求为最尚, 追求韵味高致, 主张 “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19]691。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在何? 仍在于唐诗的质性判断不同。 换言之, 为唐人所认可的唐诗并非简单地将本朝诗都收入其中, 而是有一个对于唐诗的标准, 只有符合这个标准的才会收录。 这从根源上看来自于对唐诗质性的认识不同。 如前所述以钱锺书的划分标准来看, 极有可能杜甫不符合唐人对唐诗的认识, 而是偏向于“宋诗” 的质性, 只不过当时并无“宋诗” 之说法, 故对于唐本朝的诗人遴选中不选其诗。 陈伯海亦认为杜甫兼具唐诗大成又开宋调, 而历代唐诗选本中不收杜诗的现象, 也是考虑到杜诗质性的特殊性: “明高棅按 ‘四唐’、 ‘九品’ 的框架论列唐诗, 不把杜诗列入各体 ‘正宗’的位置, 特设‘大家’ 一栏以容纳之, 或许便含带着这层考虑在内, 姑妄识之。”[10]44
如上述, 唐诗的质性是主“情” 而非尚“理”。关于这一点, 可以结合历代人对唐诗质性的归纳评判, 无论气象、 格调、 韵味等, 总是与一种审美情感的表述相关。 这些研究结论的得出是依赖对于唐诗质性的正确认识。 同时, 唐诗的质性也体现在唐代学术上, 有学者指出: “唐一代远不是一个理论总结的时代, 也不是一个思考学术的时代。”[20]48唐诗的创作成就历代难以企及, 但唐人诗学理论却极为少见, 即使有也多从作诗角度为主, 而非诗歌批评。 这一现象的原因如张潮《秋星阁诗话》 小引所言: “李唐之世, 无所谓诗话也。 而言诗者, 必推李唐。 ……夫唐人无诗话, 所谓善 《易》 者不言《易》 也。”[21]441换言之, 唐诗的 “主情” 质性甚至还影响了唐代本朝诗学理论的发展形态。
四、 结语
陈伯海的唐诗学以质性为核心的逻辑, 串联起对唐诗研究的各个重要部分。 从六朝诗的质性入手, 分析其形成及质素转变, 更有利于理解唐诗质性的生成。 而对唐诗质性的细致划分, 则可见唐诗的发展分期状况以及质素的蜕变, 并可略窥宋诗质性, 形成了体系完整的唐诗学系统。
换言之, 区分质性故使唐诗具有作为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成其为一个理论体系。 在此意义上, 故称质性研究为唐诗的本体(存在) 研究, 从而能将唐诗从整个诗歌文学史中独立出来, 同时能对“唐宋诗之别” 的问题作出有力和合理的回答, 使诗歌作品中具有了唐诗特殊属性, 符合这种特质 (标准) 的作品得以纳入“唐诗学” 的研究范围, 而非简单地以朝代演变为划分诗歌的依据。 唐诗学中以质性研究为主导的思路, 具有转变认识论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