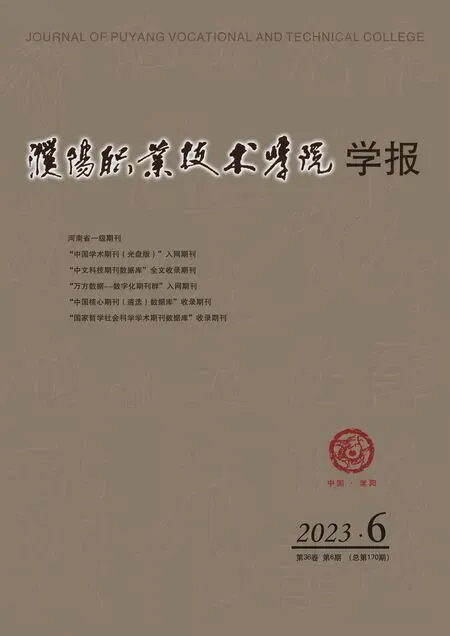《世说新语》 及刘孝标注中的“疾” 文化
陈 颖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世说新语》 是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名士言行举止、 仪态风流的一部笔记小说, 南朝梁学者刘孝标的注解博古涵今, 引经据典且所引典文大多已散佚, 文献价值极高。 《梁书·文学下》 记载刘孝标少而好学: “峻好学, 家贫, 寄人庑下, 自课读书, 常燎麻炬, 从夕达旦, 时或昏睡, 爇其发,既觉复读, 终夜不寐, 其精力如此。”[1]701由于刘孝标的博学, 他的注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极为后人推重。 《世说新语》 其书, 文字并不艰深, 但刘孝标注的重点是补充故事所涉及的人物及史实, 而他所引征的四百余种书籍绝大多数已经不存于世。目前, 对于《世说新语》 及刘注的研究多集中于人物形象, 魏晋风流与药、 酒之间的关系, 或是从语文教学的角度进行解读, 对于其中蕴含的“疾” 文化关注较少。 本文侧重于深入挖掘当时士人患病的仪态, 探究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一、 体疾与审美风尚
体疾, 顾名思义指的是人身体所患疾病。 魏晋六朝士人在何晏的带领下多喜食寒食散, 已然成为一种名士风尚, 大量摄入寒食散虽有美姿仪的功用, 却使得士人身体每况愈下, 其效果不亚于慢性毒药, 加之这一时期名士多爱饮酒, 饮酒服药亦使名士顽疾缠身。 《魏书》 有“人痾” 一节专门记载奇闻异病, 言及 “太宗永兴三年, 民乌兰喉下生骨, 状如羊角, 长一尺余”[2]2915, 怪状异病实在骇人听闻。 《晋书》 则记载裴楷等名士患有渴利疾、 目疾等多种疾病。 《世说新语》 不仅是魏晋时期的清谈故事集, 更作为魏晋时期的一部美学集成, 在展示士人体疾方面多与社会审美价值取向息息相关。
(一) 羸疾与“病态美” 的审美取向
魏晋名士对男性美有着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殊追求, 由于长期饮酒和吃药, 男性具有一种病态美, 再加上名士气质, 显露出来的是介于阴柔与阳刚、 风流与病态之间的非凡气度。 《世说新语》 多次记载卫玠之事, 均言及玠体弱多病, 称之为“羸疾”:
卫玠始渡江, 见王大将军。 因夜坐, 大将军命谢幼舆。 玠见谢, 甚说之, 都不复顾王, 遂达旦微言, 王永夕不得豫。 玠体素羸, 恒为母所禁。 尔夕忽极, 于此病笃, 遂不起。[3]210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 人久闻其名, 观者如堵墙。 玠先有羸疾, 体不堪劳, 遂成病而死。 时人谓看杀卫玠。[3]614
卫玠少而多病, 体型消瘦, 《玠别传》 中言“家门州党号为璧人”[3]614。 除却容貌妍丽, 卫玠所患羸疾是其体态轻盈、 弱柳扶风的根本原因。 论及羸疾, 《诸病源候论》 言: “夫血气者, 所以荣养其身也。 虚劳之人, 精髓萎竭, 血气虚弱, 不能充盛肌肤, 此故羸瘦也。”[4]92卫玠瘦弱, 不胜罗绮,体不堪劳, 劳而成病。 因羸疾而消瘦, 似有弱柳扶风之感, 加之卫玠容貌妍丽, 才华横溢, 时人奔走相看, 至于看杀卫玠, 展示了士人趋弱美的审美价值取向。 魏晋时期对于男性定位有了颠覆性变化,由趋向阳刚之美变成了趋向弱美, 这不仅仅是审美取向的转变, 更折射出魏晋士人对传统思想的反叛精神和标新立异精神。
除卫玠外, 士人羸弱不堪劳的现象普遍发生,成为魏晋社会常态, 且《世说新语》 中有多篇涉及士人体弱, 《文学》 篇中载: “林道人诣谢公, 东阳时始总角, 新病起, 体未堪劳。 与林公讲论, 遂至相苦。”[3]227谢朗少时多病, 身体孱弱却与僧人支道林谈论玄理, 以至于相互辩驳、 毫不相让, 一度被引为佳话。 《栖逸》 篇中又载: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 清贞有远操, 而少羸病, 不肯婚宦。”[3]653《文字志》 曰: “廞好学, 善草隶, 与兄式齐名。躄疾不能行坐, 常仰卧弹琴, 读诵不辍。”[3]653李廞从小清高雅正, 志向高远, 体弱多病致使他不思婚姻嫁娶与官宦仕途, 然专擅古琴。 无论是谢朗还是李廞, 疾病没让他们日渐消沉, 反而磨炼出了坚韧的心性, 对生命的体悟更加真切。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 以至民不聊生, 魏晋士人的 “致君尧舜” 之志已然消磨殆尽, 随之而来的是对战乱和死亡的恐惧, 其生命态度也逐渐由外而内, 目光转向对自身的关照。 此时的疾病正是士人关涉的一个层面, 他们在感悟疾病的过程中了悟生死之意, 将疾病看成生命的本真状态, 遂淡然处之, 豁达观之,超脱任之, 进而能够在享受病痛的过程中追寻自己所坚持的理想。 同时, 谈玄论理与弹琴诵读也成为谢朗、 李廞等人对抗疾病的一种手段, 是其自我疗救的一种方式。
上述事例均体现了魏晋时期的独特审美现象,即男性超过女性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 社会上对于男性容貌仪表的关注评品蔚然成风。 《世说新语》专设《容止》 篇以记录美如冠玉者的姿容, 较之其他时期偏重阳刚型的审美对象, 六朝之人多爱重肤如凝脂、 唇赛点朱、 面似月下白玉、 腰如风中杨柳、 口嘘兰麝、 体溢芳香的美男子。 比如东晋王导以皮肤白皙闻世, 手拿白玉柄麈尾, 手和玉浑然一体, 实堪称为 “玉人”。 慵软无力、 弱不胜衣并非女子独有, 也是社会对于男性的审美要求, 《世说新语》 中对于男子体弱患羸疾的叙写即是从侧面展现了这种审美风尚。
(二) 鼻疾与“洛生咏” 的吟诵风尚
除却社会 “病态美” 的审美要求与取向外,《世说新语》 还记载了大量的吟诵活动, 同样也与疾病密不可分。 其中便有桓温设鸿门宴欲伏杀谢安和王坦之之事。 时值坦之甚遽, 而问谢安“当作何计”, 谢安面不改色, 神色自若, 对坦之说 “晋阼存亡, 在此一行”。 因此, 谢安与王坦之相与俱前。《雅量》 篇中载: “王之恐状, 转见于色。 谢之宽容, 愈表于貌, 望阶趋席, 方作洛生咏, 讽‘浩浩洪流’。 桓惮其旷远, 乃趣解兵。 王、 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3]369
谢安面对桓温之埋伏尚且能安之若泰, 吟诵“洛生咏”, 得到桓温赏识, 免去灾祸。 刘孝标注解《洛生咏》 曲调说: “安能作洛下书生咏, 而少有鼻疾, 语音浊。 后名流多学其咏, 弗能及, 手掩鼻而吟焉。”[3]369“洛生咏” 即都城洛阳一带的书生在吟诗时, 常常采用的一种语调, 其发音方法和腔调特征带有明显的洛阳方音气息, 后人称为 “洛生咏”。 谢安患有鼻疾, 气不通, 故音闷浊, 所作《洛生咏》 风靡一时。 东晋之人效仿, 苦不得浊音,未能成, 竟以手掩鼻而吟诵, 这是士人引领吟诵风尚的一大体现。
“洛生咏” 兴起于西晋时期洛阳地区, 随着西晋政权瓦解, “洛生咏” 的风尚也逐渐湮灭, 直到东晋谢安因鼻疾而吟诵的“洛生咏” 风行南北。 虽然“洛生咏” 曲调在名士之间流行, 但听其音不免呕哑嘲哳难为听, 难称之为天籁。 《世说新语·轻诋》 记载: “人问顾长康: ‘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 ‘何至作老婢声。’”[3]845顾恺之认为 “洛生咏” 的音色浑浊, 像老年婢女的音色一样, 难以入耳。 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 中曾言及顾恺之厌恶“洛生咏” 的原因, 除却音色外, 还有地域差异和政治立场的限制使得顾恺之有 “老婢声” 的感慨。 余嘉锡言:
洛下书生咏者, 效洛下读书者之音, 以咏诗也…… 《晋书·王敦传》 曰: “含军败,敦闻怒曰: ‘我兄, 老婢也!’ 长康素为桓温所亲昵。 温死, 谢安执政, 而长康作诗哭温,有 ‘鱼鸟无依’ 之叹。 然则 ‘老婢’ 之讥,殆为谢安发也。 亦可谓不识好恶者矣。”[3]845
顾恺之是南方人, 因方音差异故不喜洛阳语调, 另顾恺之投靠桓温, 桓温与谢安政见相左, 故对于“洛生咏” 十分鄙视。 抛开顾恺之个人原因不谈, 单说“洛生咏” 曲调本身就难以学习模仿, 以致东晋士人皆掩鼻而作。
“洛生咏” 在东晋大盛, 原因归结为患有鼻疾的谢安大力倡导。 谢安作为当时引领风尚的名士,其一举一动皆被天下士人效仿, 谢安官拜宰相, 推崇“洛生咏” 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因素。 司马氏在建康代西晋而专权, 建立东晋, 此时士人皆对洛阳故都带有思念之情, 《世说新语·夙慧》 即记载晋明帝“举目见日, 不见长安”[3]590之事, 可见为政者仍然关怀洛阳之事。 谢安借鼻疾而吟诵“洛生咏”,无疑是向当权者表明其政治立场的一种手段。 除政治因素外, 当时士人流行“洛生咏” 也是对于既往名士的效仿, 洛阳在此前是文人名士的聚集地,“竹林七贤” 就曾在此聚会并流传出许多佳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 名士们追求标新立异、 与众不同, 纵然谢安再次倡导 “洛生咏” 有政治和文化等原因, 但其由鼻疾而引领的此种风尚却成为东晋名士争相效仿的一种吟诵风尚。
魏晋士人所患体疾, 并不仅仅影响个人生活与文学创作, 还能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无论是以卫玠等人为代表的羸疾, 抑或是谢安所患鼻疾, 均成为社会的风向标, 使士人的审美取向由 “阳刚美” 转向 “病态美”; 吟诵取向则由流畅清发的“吴越之音” 转向掩鼻而歌的“洛生咏”。
二、 省疾与名士风度
省疾, 指一方患病, 另一方前往探视的行为活动。 汉魏六朝之人多患疾, 从而带动“省疾” 风气盛行一时。 《世说新语》 中的“省疾” 从侧面展现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其中涉及的篇目多是以“省疾” 作为历史背景或者切入点, 进而展示进行“省疾” 活动的主人公双方各自的性格特点和为人处世的法则, 从而展示了魏晋士人风度。 “省疾” 这一活动在史书中多有记载, 《晋书》 载晋文帝之事曰: “及景帝 (司马师) 疾笃, 帝 (司马昭) 自京都省疾, 拜卫将军。”[5]33晋景帝司马师病重, 其弟司马昭回朝省疾, 虽然其中君臣礼数、 亲族情谊居多, 但是也可以从中窥见魏晋时期的省疾风气。 除君臣外, 《晋书》 又载师生省疾: “(姚)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 岐病, 泓亲诣省疾, 拜于床下。 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5]3007由姚泓省疾始,高贵如王侯公卿者见师傅皆需行礼, 带动士族风气, 轰动一时, 也展现了姚泓尊师重道的情义。 类似的 “省疾” 活动在 《世说新语》 中比比皆是,《容止》 篇则记载了风度翩翩的裴楷之事: “裴令公有俊容姿, 一旦有疾, 至困, 惠帝使王夷甫往看, 裴方向壁卧, 闻王使至, 强回视之。 王出, 语人曰: ‘双目闪闪若岩下电, 精神挺动, 体中故小恶。’”[3]612《名士传》 曰: “楷病困, 诏遣黄门郎王夷甫省之, 楷回眸属夷甫云: ‘竟未相识。’ 夷甫还, 亦叹其神俊。”[3]612
《世说新语》 中的记载言简意赅, 简短的故事情节为我们展示了栩栩如生的裴楷形象, 较之史书“及疾笃, 诏遣黄门郎王衍省疾, 楷回眸瞩之曰:‘竟未相识。’ 衍深叹其神俊”[5]1049-1050短短数句而言,《世说新语》 则鲜明地表现了笔记体小说的特点,着重刻画人物形象。 裴楷病重, 帝遣王衍省疾, 反而衬出裴楷的俊朗多才, 这一省疾活动衬出主人公的病容, 于《容止》 篇叙述恰到好处, 与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恰好吻合。 刘伶病酒, 裴楷病容皆令人为之一叹。 除此之外, 亦可从“省疾” 这一活动中窥探士人的义利观念, 塑造了众多重情重义的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德行》 中载: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 值胡贼攻郡, 友人语巨伯曰: “吾今死矣, 子可去!” 巨伯曰:“远来相视, 子令吾去, 败义以求生, 岂荀巨伯所行邪。” 贼既至, 谓巨伯曰: “大军至,一郡尽空, 汝何男子, 而敢独止。” 巨伯曰:“友人有疾, 不忍委之, 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 “我辈无义之人, 而入有义之国!” 遂班军而还, 一郡并获全。[3]11
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 东汉荀巨伯以高义退敌被传为佳话, 在友人极力劝解荀巨伯独自逃生时,被巨伯果断拒绝, 不义而偷生不如无生, 巨伯之高义遂使胡人感化, 使之自惭而退, 一郡得以保全。这篇简短的文字以荀巨伯省疾为背景, 进而通过遇胡贼这个巧合事件反映了巨伯之“义” 与道德感化的巨大力量。 另有《方正》 篇记载孔坦之病笃而胸怀天下, 其疾言厉色的质问也显示了正直而不擅委婉的性格特征: “孔君平疾笃, 庾司空为会稽, 省之, 相问讯甚至, 为之流涕。 庾既下床, 孔慨然曰: ‘大丈夫将终, 不问安国宁家之术, 乃作儿女子相问!’ 庾闻, 回谢之, 请其话言。”[3]322作为孔子的后代, 孔坦亦心系家国天下, 时值己病, 庾冰前往省疾, 因孔坦病重不觉潸然泪下却遭到孔坦慨叹。 这则故事以孔君平病重, 庾冰省疾为背景展现了二人的心性。 刘孝标在此注解 “坦方直而有雅望”, 孔坦正直果敢而感念天下家国, 庾冰重礼多情而虚心求教的形象皆跃然纸上。
《赏誉》 篇则记叙了桓大司马病, 谢公前往省疾的事。 时值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 为挽救自身威望遂于太和六年 (371) 废晋帝司马奕为西海公,拥立司马昱为新帝, 即简文帝。 第二年, 简文帝崩, 其子司马曜即位, 谢安、 王坦之等人拥护新帝隐隐与桓温分庭而立, 桓温病, 驻扎于姑孰, 谢安念及桓温提拔之恩前来 “省疾”, 桓温遥望而见慨叹曰: “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3]478由桓温语足可见其高爽俊迈, 即使后期对谢安、 王坦之设下鸿门宴, 桓温也因谢安步履从容而不至于赶尽杀绝。 在政治相左的背景下, 谢安仍能以恩义为先, 前去“省疾”, 由这一活动也足可见谢安正直坦诚、 胆识过人。
“省疾” 在汉魏士人群体中屡见不鲜, 《世说新语》 多有记载, 单由“省疾” 这一活动来看, 便能窥见不同的士人风貌和名士风度, 风流倜傥者有之, 舍生取义者有之, 方直雅望者有之, 不忘前事之恩者亦有之, 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名士风流画。
三、 称疾与政治抉择
魏晋时期, 士人真病有之, “称疾” 亦有之。“称疾” 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 “称疾不就” “称疾不朝” “称疾辞官”, 这三种均是古代士人远离庙堂的一种手段。 在历经了汉末的党锢之祸和曹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的政治漩涡后, 士人致君尧舜、立登要路的愿望大大降低。 罗宗强曾言: “汉之末世, 士人之心理趋向从与大一统政权亲近转变为与大一统政权疏离。”[6]393他们为保全自身, 关注的是自身的得失, 士人此时对疏离和淡漠政治的心态异常向往与热衷。 同时, 宦官和外戚的专擅弄权则将士人不断从朝廷话语中心推开去, 推向自我, 这些无疑都对士人的个性崛起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时的士人用石崇的话来说即是 “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牗哉”[5]1007。 因此, 《世说新语》 及刘注中叙写的魏晋名士“称疾” 行为,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士人的政治抉择与考量。 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 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 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一) “称疾不就”
“称疾” 是一种自我病态化的行为, “患者”通过疾病这一手段将自己的行动方式委婉化, 企图达到某种个人目的。 魏晋时期的“称疾” 并非真的有疾, 只是借口托词而已, 实际毫不掩饰自己的健康体魄, 其与两汉全盛时期的“诈病” 在表现方式上大为不同。 汉代全盛时期的“诈病” 先是声称自己患疾, 而后会采取特殊的表演方式让帝王或与“诈病” 休戚相关的人信服自己患病一事。 明代张景岳对于 “诈病” 一事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他曾言: “夫病非人之所好, 而何以有诈病? 盖或以争讼, 或以斗殴, 或以妻妾相妒, 或以名利相关, 则人情诈伪出乎其间。”[7]1304无论是汉代的“诈病” 或是魏晋时期的“称疾” 皆反映了官僚群体内部已经不能凭借正常手段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即如张景岳所言的 “人情诈伪”。 秦汉时期的士人常运用 “诈病” 的手段来实现争权夺利、 邦交斡旋、 保全性命、 价值选择等多种目的。 魏晋以降,“人情诈伪” 丝毫不弱于秦汉时期, 此时士人多效仿前人运用“称疾” 这一委婉化的手段来远离政治纷扰, 在政权倾轧之下企图保全自身。 《世说新语·言语》 载: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 正月半试鼓, 衡扬枹为《渔阳》 掺挝, 渊渊有金石声, 四坐为之改容。 孔融曰: ‘祢衡罪同胥靡, 不能发明王之梦。’ 魏武惭而赦之。”[3]64《文士传》 曰: “融数与武帝笺, 称其才, 帝倾心欲见。 衡称疾不肯往,而数有言论。”[3]64
祢衡恃才傲物, 帝甚忿, 欲辱之, 令衡为鼓吏作 《渔阳》 掺挝, 却不想祢衡于帝前易衣以作鼓,使得武帝笑曰: “本欲辱衡, 衡反辱孤。”[3]64于是便有了“击鼓骂曹” 的典故。 时值孔融作《荐祢衡表》 于曹操, 祢衡自称狂病, 称疾不前。 祢衡不欲往见武帝使用的便是“称疾” 这一手段。 《世说新语·品藻》 记载: “王子猷、 子敬兄弟共赏 《高士传》 人及赞。 子敬赏井丹高洁, 子猷云: ‘未若长卿慢世。’”[3]542《高士传》 赞曰: “长卿慢世, 越礼自放。 犊鼻居市, 不耻其状。 托疾避官, 蔑此卿相。 乃赋大人, 超然莫尚。”[3]543
《汉书》 记载: “(司马)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 与卓氏婚, 饶于财。 故其仕宦, 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 常称疾闲居, 不慕官爵。”[8]2589司马相如不慕权贵, 无心朝野政治。 为避官, 井丹选择直接隐居, 司马相如选择“称疾” 不往, 二人不屑攀附权贵, 只为保全自己的高洁品性。 刘孝标引司马相如例注解王子猷、 王子敬兄弟二人的言谈, 可见魏晋士人是赞赏这种做法并认为是名士所具备的一种品格, 长卿越礼自放的行为远比井丹高洁且不失风韵, 展现了魏晋士人个性自由, 也侧面反映出了一种深刻的叛逆精神。 《世说新语》 的主流导向即是赞美欣赏高蹈隐逸、 狂放不羁、 肆心而为者, 对于世家大族在政坛上的勾心斗角不予揭示, 描绘的大都是士族文人对于政治的不屑与疏离。 对于带有投机性质的入仕者则予以皮里阳秋的讽刺, 例如《言语》 篇记载:
司马景王东征, 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 因问喜曰: “昔先公辟君不就, 今孤召君, 何以来?” 喜对曰: “先公以礼见待, 故得以礼进退; 明公以法见绳, 喜畏法而至耳。 ”[3]77
《晋诸公赞》 曰: “喜字季和, 上党铜鞮人也。少有高行, 研精艺学。 宣帝为相国, 辟喜, 喜固辞疾。 景帝辅政, 为从事中郎, 累迁光禄大夫、 特进, 赠太保。”[3]77
李喜先是避君不就, 运用的方式即是“称疾”,当时司马氏与曹氏政权角逐而胜负未知, 于是李喜在此时的选择是为明哲保身而 “称疾不就”, 但当司马氏政权的威望已经树立, 且新晋政权的权威不容挑战, 再次征召李喜如果再次称疾不出即会招致杀身之祸, 因此李喜顺应形势进入朝堂, 官拜太保。 由“称疾不就” 到“入主庙堂” 则显示了李喜的政治选择, 《世说新语》 将其收录于《言语》 篇与其说是表彰辞令, 倒不如说是对李喜前倨后恭状态的嘲讽。
(二) “称疾不朝”
《世说新语》 一方面不能接受士人的躁竞入世之举, 一方面又在言辞之中对其加以开脱, 展现士人的某些难言之隐和内在衷曲, 对其热衷政治的心态, 深陷政治漩涡中的行为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世说新语·规箴》 记载:
谢鲲为豫章太守, 从大将军下至石头。敦谓鲲曰: “得复为盛德之事矣。” 鲲曰: “何为其然? 但使自今已后, 日亡日去耳。” 敦又称疾不朝……[3]561
《晋阳秋》 曰: “鲲为豫章太守, 王敦将肆逆,以鲲有时望, 逼与俱行。 既克京邑, 将旋武昌, 鲲曰: ‘不就朝觐, 鲲惧天下私议也。’ 敦曰: ‘君能保无变乎?’ 对曰: ‘鲲近日入觐, 主上侧席,迟得见公, 宫省穆然, 必无不虞之虑。 公若入朝,鲲请侍从。’ 敦曰: ‘正复杀君等数百, 何损于时?’ 遂不朝而去。”[3]561
王敦“称疾不朝” 固然有着放诞简傲的名士风范, 但是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 时值王敦功高权重且掌控了长江中上游的军队, 统辖州郡, 自收贡税, 成为东晋王朝一大威胁, 晋元帝惧其功高震主, 对其大加压制。 永昌元年(322), 王敦起兵于武昌, 后据于石头城, 帝搏无果, 加封敦为丞相,派长史谢鲲劝说敦朝见天子, 王敦称疾不朝, 径回武昌, 遥控朝政。 作者在这里运用王敦的言论来证明其难言之隐, “正复杀君等数百, 何损于时”。王敦审时度势, 看到了班师回朝必会命丧京中, 也为其 “称疾不朝” 带来合理性。 由此看来, “称疾”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 在君臣博弈、 政权争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 “称疾辞官”
早在汉代, 因为羞愧称疾而辞的官员不在少数, 《史记·张丞相列传》 记载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 丞相张苍以为并非如此, 之后黄龙见于成纪,文帝召拜公孙臣为博士, 更历改元, 张苍 “自绌,谢病称老”[9]409, 《世说新语》 中则记载了王羲之耻慨而“称疾辞官” 的行为, 《仇隙》 篇云:王右军素轻蓝田, 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 蓝田于会稽丁艰, 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 屡言出吊, 连日不果。 后诣门自通, 主人既哭, 不前而去, 以陵辱之。 于是彼此嫌隙大构……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 以先有隙, 令自为其宜。 右军遂称疾去郡, 以愤慨致终。[3]928
《中兴书》 曰: “羲之耻慨, 遂称疾去郡, 墓前自誓不复仕。 朝廷以其誓苦, 不复征也。”[3]929
王羲之与王述不睦已久, 王述晚年声誉渐隆,王羲之不平, 遂于述母丧事之上屡屡侮辱王述, 二者嫌隙更甚。 后王羲之欲分会稽为越州, 王述亦背地指令属下苛责会稽郡的诸多违法行为。 永和十一年 (335 年), 王羲之于父母墓前立誓永不出仕,三月即称病去官。 二王之间的恩怨是非固然是《仇隙》 篇所言之重点, 但是王羲之这一“称疾” 行为也仍然值得注意, 展现了魏晋名士退出朝堂, 远离纷争所采取的手段即是“称疾”, 且屡试不爽。
由此可见, 汉魏六朝士人“称疾” 行为与自身政治考量息息相关, 或 “称疾不就”、 或 “称疾不朝”、 或“称疾辞官”, 均展现了《世说新语》 的价值取向, 即标榜士人激流勇退, 远离朝堂纷争, 隐去了正史所载之政治倾轧, 全面展示了魏晋士人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