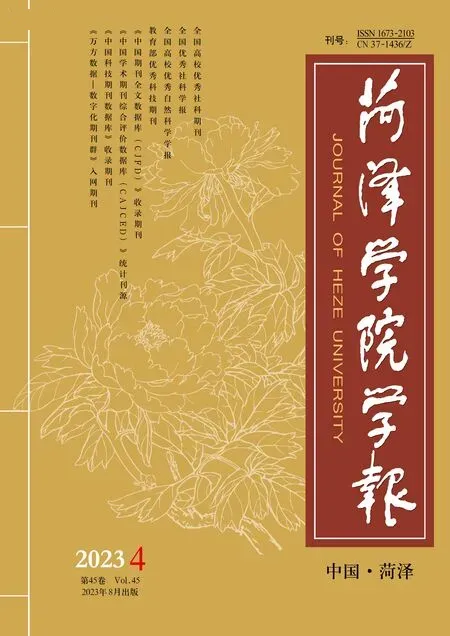从《金瓶梅词话》透视古本《水浒传》武松形象
——兼及杭州容本《水浒传》万历时代之创新
宋伯勤,杨东锋
(1.盐城盐都区政法委,江苏 盐城 224001;2.盐城实验中学,江苏 盐城 224001)
《金瓶梅词话》中武松打虎和杀嫂两个情节所描绘的武松人物形象,与杭州容与堂本《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是截然不同的。笔者以为《金瓶梅词话》中的武松打虎与杀嫂情节所涉及的武松形象,应该是源自正德嘉靖时期的古本水浒传故事,甚至也可能是更早的故事版本。本文意图通过考察《金瓶梅词话》与之前古本的关系来探测古本《水浒传》故事中武松的原始形象,并由此推定杭州容与堂本《水浒传》(以下简称容本《水浒传》)的武松形象可能与万历时代的文化诉求和读者期待有关。
一、两个不同的武松形象
《金瓶梅词话》自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就记载有传抄,关于创作的起始时间可能还要追溯到更早的嘉靖末期。到万历二十四年时,该作品在江南已经广泛传抄,但到万历四十五年,《金瓶梅词话》方才初次刻版,可见在刊刻之前,《金瓶梅词话》本故事已经流传了几十年。
可以确定的是,《金瓶梅词话》移植了万历初年杭州流行的水浒传说中的武松杀嫂故事,而第1回至6回,第9、10回,第87回,《金瓶梅词话》中的情节与容本《水浒传》第23至31回的情节也基本相同。
现有的研究多倾向于《金瓶梅词话》本中的作品人物系自《水浒传》第23、24回演化,认为只因《金瓶梅词话》主角是写市井细民,并无意展现武松英雄本色,并且在情节安排上,《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相比删减了武松的英雄事迹,所以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金瓶梅词话》刻意“矮化”了武松,颠覆了容本《水浒传》表达的英雄主义形象,把读者熟知的容本《水浒传》中的武松,改写成了薄情寡义矮小猥琐的亡命徒。研究者之所以产生这种观点,原因在于多把万历时期杭州流行文化里所刻画出来的英雄武松形象作为标准,即以万历新编容本《水浒传》第23回中的新武松形象作为标尺去对照《金瓶梅词话》本中的旧武松而得出的结果。容本《水浒传》中彩绘的英雄武松,一身豪气,盖世英雄,而《金瓶梅词话》本(以下简称《金》本)中的武松,平庸世俗,残忍凶恶,二者形象完全不同。
那么,《金》本中的武松形象,有没有其它来源的可能呢?比如是源自早期正嘉古本的原创人物?截止目前来看,学界尚无人探讨,更无《金》本中武松形象或源自早期正嘉古本的原创人物的说法。造成这种状况有着不难理解的现实原因,一是资料的缺失,古本及之前的材料我们现在几乎都难以寻觅到。二是人们或难以想到,也许古本人物遗迹还存在于另外的作品中被保存下来的可能。
二、《金瓶梅词话》本中武松形象的来源
“互文性”虽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文本理论,但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一直都存在,这是一种借鉴式的抄袭方法,也是文学文本创新中,借鉴抄袭当时经典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金瓶梅词话》本中古朴的旧武松形象,笔者以为应该是采用了拿来式的“互文性”方法,借用了先前比容本还要早的水浒故事中的武松形象,从而保留了一个与后来万历新编容本《水浒传》中完全不同的旧人物形象。
考察《金》本中打虎与杀嫂两个段落中展示的旧武松形象,与容本中创新的万历时代化了的英雄武松形象是全然不同的。《金》本呈现出的武松形象是坍塌的,这一形象的选择应该与《金瓶梅词话》故事背景的需要有关。
《金瓶梅词话》的故事背景假托于北宋末年政和年间,而万历时期杭州最新流行的水浒故事中的武松、王婆、西门、潘金莲,已经是属于时尚化了的新鲜形象。显然万历时代已成英雄的武松新貌不符合宋代底层人物的粗陋残暴的形象,因此为更符合北宋政和时代的民风民俗,《金》本可能在创作时刻意地让武松形象呈现先前文本的矮化乏味,即把先前老故事旧版本中粗陋残暴的武松形象直接抄袭保留下来,从而有别于容本从时尚作品互文来的崭新形象。这样做并不影响《金》本中主要人物故事,因为武松仅仅是串联场景的一个角色而已。反过来说,如果古本故事与容本万历时代化了的武松是两个一致的形象,《金》本的作者则无须一开篇就放弃如容本武松人物造型的“高大上”,再逆向地涂抹毁改,把几近完美的如容本中的英雄武松,改写成打虎的平庸,杀嫂的奸诈且凶残。《金瓶梅词话》需要一个返朴归真的古代武松形象,因而《金》本在创作时转向更早前的文本中去选择摘抄。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推测。
笔者以为,《金瓶梅词话》成书时,当时的杭州坊间应该流传着不同水浒传类型的故事文本。一个是正嘉时期的古本,是按照正德嘉靖时期的文化理念而创作形成的(其初始创作还更可前溯到成化、弘治时代文化)。另一个是正嘉古本在南方流传后,经过商业都市的杭州书会再度创新增改,二次新编成书的万历时代化了“容初本”(容本借以批评的母本)。“容初本”在早期的正嘉古本基础上糅合了更多的嘉靖后期到万历时期杭州的时尚精神文化元素。古文本与新编“容初本”的时间跨度,超过了50年的光景。
在古本《水浒传》成书后并且在杭州“容初本”二次成书之前,杭州书会的作者可能为迎合市民趣味,曾将古本等流行的水浒作品中叙述武松人物的故事劈出单列成篇增补添加,创新演化出了另外一部新鲜的长篇人物故事话本,此话本专讲武松打虎、王婆茶坊设计、西门庆潘金莲勾搭、武松杀嫂等。后来经过嘉靖中期至万历初年的说唱艺术演化,终于在古本结构的基础上演绎出了另外一部具有万历时代理念杭州文化特色的新鲜“武松杀嫂”作品。这部作品虽然后来又被再吸收乃至湮灭,但其对稍后成书的《金瓶梅词话》和“容初本”的贡献巨大。“容初本”与《金瓶梅词话》本(以下简称《金》本)两部作品,可能都是对这部万历初年极具杭州特色的新编“武松杀嫂”作品做了“互文性”抄袭。而“容初本”与《金》本的成书过程在时间上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如果有先后的话,可能《金》本的成书时间或许还略为超前于“容初本”。
三、从《金瓶梅词话》本中还原古本武松形象
元代至明初杂剧中的水浒人物形象都不甚高大,尤其武松。宋代龚开《宋江三十六赞》:“行者武松: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 罗烨《醉翁谈录》及宋元《大宋宣和遗事》,武松更是仅存名号而已。
《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的先前古本水浒故事文本的痕迹,保留了先前的古文本的样貌,武松形象极有可能就是出自更早前古文本的描绘。由是,我们拟从《金》本中的武松人物,试图来还原古文本中的武松形象。
《金》本中武松出场,应该是古本水浒传的武松出场,一开始便没有建立起英雄的形象。其首回是“景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打虎情节的互文是:武松就在路傍酒店内,吃了几碗酒,壮着胆,浪浪沧沧,大扠步走上岗来。与万历容本拔高了的刻画相比,《金》本中武松的形象和精神是“矮化”着的,是一个人性弱点显著的平庸人物。
《金》本武松,狮子楼误杀李外传,“迭配孟州牢城”,义夺快活林、大闹飞云浦,直到第87回碰到赵佶立太子大赦天下,才又回到清河当都头。流放多年后,此时英雄气概早已折磨殆尽。《金》本写其以色相,施展诡计,为“迎儿”招婿,用上门求娶的计策,哄骗王婆、潘金莲。其虐杀潘氏、王婆,非常残忍狠毒,“跳过墙来”杀王潮儿未遂,劫掠首饰,竟不顾迎儿生死,越后墙,“上梁山为盗去了”。杀人逃逸,人物面目基本是市井猥琐人物形象,连带梁山也成了盗匪的窝巢。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金》本在这大一节“互文”来的文字后面,作者还刻意写下一句感叹:“武松这汉子端的好狠也!”
《金》本中,武大有个女儿叫“迎儿”,其屡遭后母潘金莲打骂,第10回武松被押解孟州,央托左邻姚二郎看管迎儿:“倘遇朝廷恩典,赦放还家,恩有重报,不敢有忘”。古本中武松故事结构,写有“迎儿”作衬托。还有一个与金莲一起长大的“玉莲”,但在《金》本中,有人物,却无故事,也应该是从更早期古本作品中,只将人物互文式抄袭过来,但情节又被删减了。王婆说雌儿来历:“小名叫做金莲,娘家姓潘。原是南关外潘裁的女儿。”这也应是原来古文本对人物出身的交待。
所以据以上推断,正嘉时期的水浒故事或更早期的古本,塑造了先前演绎作品中的草莽人物形象,但都还只是水浒故事在文学演进史上的过渡,人物形象还远没有达到如后来杭州容本用万历时代理念重新塑造的高大英雄。从《金》本移植的古本,描写的武松是早期的本色面目:残杀了妇人、婆子,“倒扣迎儿在屋里。迎儿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儿,我顾不得你了!’”,仓促中遗弃侄女迎儿。这些古本文化的原作文字,更非是如后来万历时期的容本中那样理想化升华了的英雄豪杰面貌。
此外,古本武松止于上梁山却没有到杭州。《金》本写武松结局:“提了朴刀,越后墙,赶五更挨出城门,投十字坡张青夫妇那里躲住,做了头佗,上梁山为盗去了”。古本应该只有正嘉之前的故事,众英雄止于上梁山,没有受招安的结局,也没有归宿杭州的信息。这应是古文本对武松的终结,并不是《金》本作者互文时做了省略。古本撰创时,还没有发展到万历时代,还没有万历新编容本中汇集的万历时代更加丰富的杭州时尚文化,还没有万历初年才新编出现的攻打杭州方向诸多新鲜故事的创意和想象。明末清初金圣叹说:其所见古本戛然而止,信其言之不妄。
《金瓶梅词话》中的武松是古本遗迹,是正嘉之前文化的标本。如果认为《金》本武松是自容本形象逆向改写,那么所看到的是一个将大英雄向平庸“丑化”的涂改过程。但若更换成一个全新视角,循迹文学作品创作的路径,看到正嘉之前的是古文化草创,塑造出的还是尚处于平庸中的旧式的武松人物,《金》本正是抄袭采用了古本原作的武松旧貌。再看到万历初年是新时代的新文化爆发,新时代催生了文学创新潮流,升华成就了容本中全新的武松盖世英雄的形象。这个对武松人物再度创新的时段,是从正德(1506—1521年)嘉靖(1522—1566年)时代,再到万历(1572—1620年)时代的文化演化过程,是由正嘉之前旧时代旧文化向万历新时代杭州新文化的创新升华发展的过程。
容本《水浒传》的创新,是全面的整体的创新。书中的林冲、卢俊义、燕青,也都是万历时代杭州新时尚文化中创新的理想化了的文学人物,他们都是与《金》本的旧武松鲁莽形象格格不入的文学新面貌,这些新鲜人物的面貌上更有着万历新时代新文化观念的嘉许期待,已是万历新文化所崇尚的军官、富豪、城市游民阶级的英豪。而《金》本透视到的古本中“矮化”着的武松,则显然是一种旧文化时期的旧人物的立照,这是早前的时代文化对底层市民粗野鲁莽人物的文学形象的写照。这类旧武松之类的人物身上,还保留有更原始(作品初成的成化、弘治时代)的流匪气息,形象如同市井平凡,举止粗鄙庸陋,仍不甚完美,也无需要完美,但却是更加的古朴写真。
四、容本增添了万历时期杭州文化元素
晚明万历时期,经济繁荣国势中兴,杭州城市扩大,时代理念影响着文化创新,文学演进也飞跃发展。此时江南印刷技术日渐成熟,更刺激着大众文化的传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万历新编容本《水浒传》才升华了水浒的人物形象。此时容本对武松再创新,最明显的是增添了武松打虎英雄色彩。万历新编的文本,武松成为了水浒故事的头号英雄,“武十回”扩写英雄武松,在一百单八将中独占了最大篇幅,本真善良,行事果敢,坦荡磊落,疾恶如仇,力量与正义集于一身,形象被演化得几乎完美无缺。新编容本砍去枝蔓,紧凑过程,一改《金》本互文中武松杀嫂时间拖延,请邻居姚二郎等“做个证见”,让士兵把守门口,防止众人逃散,请胡正卿录下潘氏口供,留下王婆活证。武松说:“小人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带着人头、口供,押着王婆到官府自首伸冤。新写成的容本的武松,不贪财不恋色,快意恩仇、大义凛然。万历时代的创新,让新武松摆脱了旧文本中“帽儿光光”的“窄袖儿”诈婚描写的平庸狡诈,形象腾地“高大”起来。而且,容本还比《金》本丰富了整三回篇幅的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新增添的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醉打孔亮等情节,彰显了英雄形象色彩。又写武松朴实的性情,被施恩父子利用;写玉兰给武松带来妻室的念想,既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又是生活在烟火气息中的凡人。让武松对前程怀抱希望,渴望建功立业,但一挫再挫,逼上梁山,英雄形象在一系列情节安排中持续推高,成为水浒英雄中“上上人物”。
如果说酒、色、财、气是之前古本塑造的武松形象,那么万历时期杭州文化结晶的新编容本则以忠义品德重新定位,人物塑造得以拔高提升,向着英雄豪杰层面净化升腾。不仅武松被演化,水浒英雄整体都在演进提升,向着叱咤风云般的传奇英雄升华,如鲁智深化身侠义,杨志怒砍牛二,李逵砍倒杏黄旗,燕青风流倜傥,花荣儒雅有加,等等,众多英雄人物的面貌,经过万历初年的再度创新,经过“容初本”成书的凝练,已经全部焕然一新。
在《水浒传》的结局上,《金》本互文出来的旧式武松,止于“上梁山为盗去了”,未着杭州方向一个字。容本自第72回后,搜集了嘉靖中后期到万历初期的杭州书会艺人们新编的各种指向杭州地域的故事,汇写出了攻苏州、杭州,打清溪县帮源洞、战方腊等种种新鲜故事。容本新编增添的后续,描摹了杭州地理,详尽了杭州文化,张顺西陵桥“远望城郭四座禁门,临着湖岸”,宋江祭奠“朝着涌金门”“仰天望东而哭”,鲁智深听钱塘江信潮、“烧化于六和塔后”,武松“在六和寺出家,尽将身边金银赏赐,纳此六和寺中,后至八十善终”,林冲“风瘫在六和寺后,半载而亡”,在这些万历杭州书会新编增添的杭州新文化故事中,过于将武松等众多人物向杭州地域归纳,英豪呼啸山林的野性、人物出自山东的北方特色,已经荡然无存。
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的互文中,透视到以前古《水浒传》文本的武松面目,可以辨识出,《金瓶梅》是在容初本之前的杭州流行水浒故事基础上演化成书,而不应该是从其后来成书的容本《水浒传》中演进。《金》本中的相关回目,也绝不是从还在其稍后才创新成书的容本《水浒传》中借鉴而来。容本《水浒传》是以万历时代文化理念重塑创新人物的一部全新的作品,与正嘉之前的古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