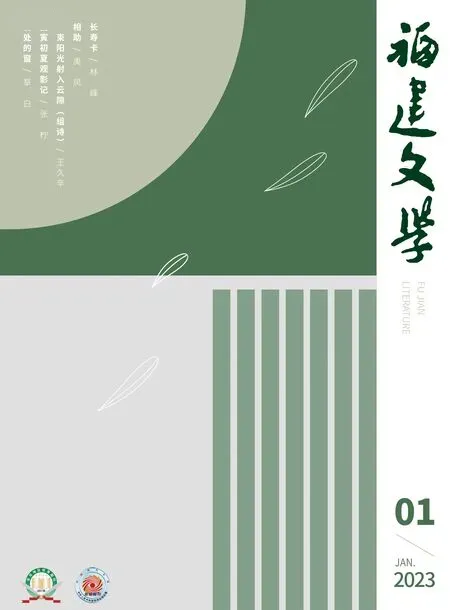下社街
张金湘
下社街被几座小山头包围着。三条小溪构成两个Y形汇集成河,向东山峡遁去。准确地说,下社街不是街,而是沿河的单边走廊,属于通常所说的犄角旮旯地带。这里是整个乡的中心地位,设有行政管理处,一条“车子化”蜿蜒至乡政府。于是有了商机,人们占据道旁有点位置的地方,搭起简易店铺,临溪岸一边的店铺,吊脚楼似的。“车子化”像一条瓜藤,店面顺藤结瓜,一脉一个。不知小街形成于何年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供销社垄断商贸活动,主导五金、粮油、化肥、农药、食盐、火油、食杂、文具等的供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生意才逐渐被店儿瓜分,直至挤垮。街上的店面以手工艺、食杂等为主。谋生的挣吃人停止走村入户的脚步,在这儿站店。街上没有公厕,身上有了急事,只能憋着。小时候有一次看见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正在和身边的人开着玩笑,突然从队伍里跳出来,避到转弯抹角处。班车简直就是移动仓库,在光临或离去时总是举步维艰。车载的是人也是货,是货也是人,和年暝牙节时才热闹起来的街道一样,成了一条大腹便便的贪吃蛇。
街头拐弯临溪边孤立着一坎新搭盖的店铺,两米多高低,板墙瓦顶,像个盒笼。打开木板门,铺内一目了然。分两边。一边吃住,一边是工作台。叮叮当当的锤炼声时而接连不断,一顿穷敲猛锤,时而一声一声,断断续续,从这里外传。这是中年汉子打铁智一天劳作的全部动静。
打铁智的铁制品,是全手工打造。柴刀、菜刀、铲子、镰刀、锄头、犁头、耧齿、耙齿、车角,饭店用的火炉,商号用的铁门,打野猪用的火铳等,他都能打得。这些工具器物,从铁坯熔炼到做出成品,要经历几十道工序,捶数百次。打铁智手脚麻利,趁热打铁,动作精准。炼坯,锻打,淬火,一举成件。几十年的累积造就娴熟的技艺,一切都在他的手下显得驾轻就熟,有条不紊。铁件这东西,讲究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打得不好,金如铁,打得精巧,铁如金。打铁智的手下出品,重剑无形,大巧不工,不中看,但中用,因而在坊间颇受追捧。然而,山里人口不多,居住分散,加上铁件毕竟是“牛筋马力”,经久耐用,不似剃头、剪指甲等那般,隔三岔五就得来一遍,所以,打铁智的风箱很轻,火炉很热,生意却很清淡。但是他不愿意放过丁点儿商机,除了农忙时回家外,其他时间都是日夜守着打铁店。于是有大把“不务正业”的时间。
打铁智打发闲时的活儿是下象棋。棋纸是一张包装箱的厚纸板画的,用的是木工墨,线条粗鲁,加上天天在上面磨磨蹭蹭,棋子、棋纸脏兮兮的在所难免。把厚纸板放床上,张开,摆棋,即开战。对折提起,即连同棋子一并收拢,顺手塞在床角,即是鸣金收兵,倒是便捷。打铁智打铁时打铁,没打铁时下棋。有人找来下棋,跟人下,没人寻来,跟自己下。于是经常听到他说:按理说,是要这样走的。另一个他说:按理说,是要这样对付的。两个自己经常争论不休,舌战不止。
打铁智铁打得好,棋也下得好。不知是铁艺助扬了棋艺名,还是棋艺光大了铁艺名,渐渐地,打铁智的棋艺和他的打铁技术一起,如高山击鼓——名声在外。渐渐地,找打铁智打铁的人多,来找他下棋的人也多。
对手心中所想的棋路,好像全被打铁智洞悉,而打铁智看起来的闲手全都藏着后续的手段,每个棋子底下好像都藏着一个刺客,稍不留神就给割断喉咙。打铁的生意经,打铁智念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下起棋来,他却是一副“欺行霸市”“目中无人”的大佬谱。他常常在对手看不出已是败局时就开始重码棋子,说,再来。有人不服输,非要下完,总是在被他那样暗示死刑时存些侥幸。他不奉陪,而是三下两下把各个可能的棋路演一遍,然后说,你看你看你仔细看,我打铁。说完立起身,来到炉旁,查验徒弟的工艺。徒弟所打的铁件有不足之处,他抽风、锻打、淬火,修正一下,再授意徒弟去执行。等对方七窍通了,要下就接着再下,不下就不下。或者他边忙着手里的活,边跟对手拉话。那边方听见对手说道:哪里输了?你这么一吃我,我这么一应,你又这么吃,我又这么应,还缓着一着呢。这边打铁智眼也不抬道:我要这么一吃呢?对手道:啊哈,还有一着反扑在里头呢,我倒没防备。
高矮胖瘦、官差流民及下棋有两下子的人都想找打铁智下几盘,都想以赢他为荣。退一层意思是,都想在他身上考查自己的棋艺水平达到哪个段次。场外不相熟的棋手,狭路相逢一起对打的时候,在开战前或战斗结束后,会以打铁智为参照物互相印证水平:你跟打铁智下过没有?赢了还是输了?回答下过或没下过,赢了或输了。然后拱起劲杀伐决断起来,或是对杀后互相再以有没跟打铁智过过招而确定一下对方棋艺上的实力。打铁智跟来人一般最多只下三盘,头两盘赢,最后一盘不是和棋就是输了。有的人一盘棋下好,立马站起来投子认输,不再下了。有的人下完三盘说,如果那一盘那一步走对了,输的是你,我们再来。他摆摆手说,不能再下了,我得打铁。遇到水平过得去的棋手,或是很熟的人,打铁智的手上又正好没活,他也不介意跟人家多下几盘。或是漫漫长夜,那就自当别论。
打铁智打铁是打铁,下棋是下棋。有人担心找打铁智下棋而耽误他打铁,影响生意,有时刻意找他买些铁件或找他修补工具,打铁智不置可否。时有乡党委书记是个好棋者,水平过得去,经常找打铁智下棋,经常切磋到三更半夜,鸡叫三遍。便有亲朋好友找打铁智找书记说计生或是其他事情的人情,打铁智从不肯应承。他肯定地说,书记是哪个,我不认识。
我们称杂货铺为“店儿”。店儿就像一个百宝箱,农村生活必需的物品一应俱全。那时候的商品大都以本来的质朴模样示人,散盐、散酒、散白糖……正是得益于这种原始的简散,才使得盐啊酒啊糖啊的分子在空气里自由奔窜、融合,鱼龙混杂,形成店儿里独具一格的味道。我常想,岁月如果有味道的话,一定是这个味道吧,浓郁、凛冽、腥膻、腐败中带着甜蜜。
下社街靠山一侧,有一坎店儿。虽然要走进店儿里,还得爬上五六个土石阶,店内通常是一片昏暗,但是我们对那店内的一切,早已洞察。其实就是一间厢的土木结构的民房,把底层临街一面的墙壁掏一个大窗口,上木栅片,改成店面。一进门,是通道,地面铺着六角红砖。内侧是两个折尺型靠墙而立的高大货架,货柜前有一张长宽定制的厚玻璃钢架柜台。货架的腰上有两个带着钥匙的抽屉,那就是“金库”。一个抽屉的金库通常半开着,里面的硬币、分钱、角钱、一二五元的钱,分门别类,历历在目,方便收取找零。另一个金库,铁将军把着,每天收到的五、十元大钞都要及时入库,上锁,夜里再盘点差错。
店儿内到处塞满货物,老鼠尾巴都不能转弯。那时的我们站着,头刚好露在玻璃柜台的台面上,要看清里面的东西,还得踮起脚尖。货柜旁边的角落里有三两个酒缸,墙上挂着盛酒用的酒提和圆锥形酒漏。对面摞着食盐、精糖,都是些有点濡湿的白色蛇鳞袋。开封后的盐、糖口袋里面,一把葫芦瓢子斜插在里面,盐、糖的进出全在它的股掌之中。高大的木架货柜上,迷蒙着灰扑扑的扬尘和垂吊的蛛丝,塞着满满的货物,火柴、香烟、味精、酱油、醋、香烛、鞭炮、草纸、种子一类。中间是方格层,摆的是些小吃食,特别惹眼。水果糖、芝麻棒、大辣片、山楂皮、“甜咸酸”、汽水等。玻璃柜台中的物品更多了,作业本、圆珠笔、玩具、小刀……琳琅满目的物品,隔着这一个柜台、一层玻璃,对着我们招手,挑逗着我们不断滋生出来又经过思想斗争后自我毁灭的欲望。
后来,店主在店门外的走廊上方挑出了一块巨大的帆布,沿街上和走廊间的斜坡搭上架,就完成了店儿的扩大。在这个地位上,只留一条一人经过的缝隙,架上摆放一篮篮一框框的货物。卖着三六九等级的青干、青炊、风干的黄花鱼、咸带鱼等鱼货,上中下等级蛏干、冬菜干、蚝干、龙眼干等的干货,还有海带、紫菜、黄花菜等干菜,以及各种水果。于是,当我们光临这家店儿的时候,可怜的物欲又被无限地增加和无情地浇灭了。
店里养着一只猫、一条狗。猫白白胖胖,看上去慵懒自在。只在某个角落坐班,为刷存在感,不时要“喵”一声,再“喵”一声。那条土狗拴在柱子上,对人构不成威胁,但它有要尽的职责与本分,一见人来便抻绳狂吠,见得轻佻张狂的人,气焰甚大。我们心生忌惮,生怕那孱弱的绳索突然崩断,从而命落犬牙。光临时,小着心。日复一日,狗还是那狗,来这里的人却有芸芸众生。狗便倦怠下来,习以为常。纵使哗然一片,它也只是扭过头淡漠地盯着,偶尔仰天长啸一声,有时甚至头也不回向着远方呜咽几声便作罢。
我不知道店主施了什么法度,让这一猫一狗分工负责,尽职尽责,又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是他手里执着的那一把拂尘吗?那拂尘肯定不是道士的法宝,而是驱蝇和瞌睡虫的神器。苍蝇是一种人见人恶的家伙,在动物世界中,它们真是臭名远扬。它们像一架架火力全开的战斗机,在货物堆里绿莹莹地嗡嗡嗡。拍又拍不得,拍死了它,弄脏了东西,得不偿失,所以只能驱赶。苍蝇粘问市并得到应用后,仍然无法帮助店主消灭苍蝇的嚣张。我们便经常看见店主手里挥着那把拂尘,在货物面上轻拂,洒脱飘逸,闪展跳跃下,苍蝇飞舞。在许多无人光临的午间,他是坐在一把竹靠椅上瞌睡的。他在半睡半醒中也不忘轻拂拂尘。此时看他,仙风道骨凸显,不是道长,胜似道长。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以为我是忘不了店儿里那么多令人向往的杂货,常常想起的却不是哪些具体的东西,而是那些东西的主人。
店主原先是货郎,挑着货郎担上山下乡,我们追着他的货郎担跑中长大。他在下社街上发现了商机,于是脚步被粘在这条街上。他的口头禅是:兴才。人们问他,青干多少钱一斤?他说:兴才;问他什么东西什么价,他第一句话的回答就是:兴才。“兴才”,本地话是“随便”的意思。于是人们就叫他“兴才”,全乡的人都叫他兴才,大名是啥,没人知道了。
兴才的“兴才”是“打嘴花”,也不是“打嘴花”。落实在具体表现上,有四个方面上的随便:一是价格“兴才”,会根据来客熟不熟悉、精不精明和所要买的货物多少主动降一点儿单价;二是量足,秤翘得半天高,眼看秤尾挂不住秤砣,他眼疾手快地按住秤尾,称好,让顾客瞄一眼秤花;三是都称好了,他会“青干再撮几尾”贴秤头,买水果的,再送一两个烂苹果烂梨;四是他笨拙地拨拉着算盘,算好总价的时候,减一点儿尾数算逢五逢十的整。
这漫不经心的四招,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实际上也没让顾客占去多少便宜,却拴住不少回头客。人们对兴才说:兴才啊,你可发财了。兴才说:哪发财呀,您不花钱,我发得了财吗?
大家都说,兴才一家人在这条街上扫走了不少钱。我却不懂:兴才一家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十年如一日,都在这一坎店儿里。他们家赚的钱去哪了?是回老家盖房子了吗?盖了房子也没回家住呢。是供孩子们上学吗?孩子长大后,女的出嫁,男的成家后成了店员,子承父业。兴才不是守着店,就是坐着班车到城里进货,早出晚归,有点空闲了还得打瞌睡扑苍蝇,他没时间花钱的呀。
街中部拐一个S 弯,有一坎店儿。赶街的年轻人并不在意,说笑着就过去。来往的车辆专注行车,不便巡视,加上店面低矮、昏暗,很难一目了然,也快快地过去。那店铺没有招牌,只在门口处吊着一圈毛巾。店主在忙着剃头,来了客,点点头,示意当问候。谁知简陋如此的剃头店,却养出兴旺。
店内墙壁上挂着两面大镜子,镜子下方是镜台,镜台上摆放着各种剃头工具,镜台前是两把椅子。一把是老板椅,能转动,这是后来才有的,才添置的。一把是自制的木工剃头专用椅,很有年头,污渍斑斑,能转动,后靠又能根据需要而上下移动,可以当躺椅。在老板椅上剃头,然后洗头,再躺在转椅上修面,剃头财把两把椅子综合使用。靠门处的墙上吊着一个塑料小水桶,水桶的底壁上凿了一个洞,装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上接一条黑棉布车成的“水管”。水龙头一拧,水顺着水管下流。一手洗头,一手把着水管,洗哪水管移到哪,很是灵活方便。水不是自来水,而是女店主从水缸里舀的,一勺一勺添加的。热水从里店煤炉上的水瓮中舀的,一勺一勺添加的。洗一个头有固定的水量。冷热的水在水桶掺参和后,女店主用手试一下冷热,然后放下一点水让顾客试一下冷热,说冷了加热水,说热了加冷水,夏天就不大讲究了,有点儿温就行。
卸下来的门板扎堆靠墙排放,一头在店里,一头压着门槛探出店外,成为简易的排椅。顾客在排椅上落下屁股,排队等候。不是一本正经的排队,而是进了店儿,先打量一下店内的人数,排在什么号心中便有数了,瞧着哪儿有个空当就坐。都不拘着,谈古论今,谈天说地,谈笑风生。新闻,八卦,也有各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个剃完,自然有一个上去接班。接班的人也有客气的,对其中的某一个人说:你先来?那人说:你先你先。没有人随便插队。偶尔有忘了序号的,剃头财也会提醒一下,现在应该是谁谁,叫号似的,或者客人会互相友情提示谁来得早。来这儿接龙剃头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和孩子。他们对发型不在意,好像是例行公事,剪短就是。
但是剃头财在意。他剃得认真,不管顾客有多多,总是剃得一丝不苟。剃发,洗发,剪发,修发,吹发,他的细致入微表现在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修面,剪鼻毛,刮胡子,采耳,丝毫不含糊。到最后,把沉重锋利的刮刀在后脖上放下,连续三下。这个颤刀法让人全身触电一般发颤,无比惊险又无比舒爽。最后,双手拿捏几下脖子,强按几下双肩,又是一阵舒畅通向全身。快意人生当如此!大概这也是吸引顾客的绝招吧。一个头,街上剪流行发型的小妹几分钟就搞定了,剃头财至少要细细折腾半个钟头才能完工。却有那么多的人愿意等。所谓专业状态和职业精神,大抵如剃头财此般。
剃头财主剃头、聊天。女店主主洗头、烧水、做饭、收钱、带孩子,偶尔也剃头,偶尔也聊天。女店主只在客人多的时候,帮着剃孩子的头和简单地剃一下大人的发,后面的细功夫再由剃头财完成。两个人从日光忙到日暝,都是站着,没见过坐着的。剃头财夫妻俩两个大的孩子,一女一男,已上学,每天早出晚归,一个小的孩子还小。三个孩子圆脸,眉清目秀,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漂亮。小的孩子刚会站,没时间抱。剃头财用木片做成一个四方形的围笼,除了睡觉、喂食、拉撒,整天就让孩子在围笼里站着。小孩子也乖,很少哭闹。日子久了,他竟然站成大罗圈腿,稍大一点后,在店儿里走动,整一个小武大郎。人们说,可惜了这孩子。剃头财说,没事,长大了腿脚会回形的。
每天劳碌。孩子又多,家务又多。每天都是腰酸腿麻。五口人挤在一张板床上。剃头财可能把很多体己话、体己事删繁就简了。再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剃头财赚的钱多,有时夜晚经常会被人“请”去打麻将等文娱活动。女店主难免会声讨几句,发泄怨气。剃头财由着老婆说道,从不还口,总是笑嘻嘻的一副二流子相,也没把她当泼妇看。他越不还口,老婆越骂得起劲。只要能让老婆“自娱自乐”放松一下,剃头财脸上的表情严肃得如同版画一般,仍一声不吭。老婆的谩骂就开始像小说创作,有时抽丝剥茧,直指要害,有时充分想象,拿男女之事发挥,跟某邻居媳妇有关等。
老婆口无遮拦带来的厄运,像乌鸦一样落在剃头财的头上。
这一骂,恰好被邻居婆婆听到。这还了得?直接和女店主接上火。四邻相劝,大都肯定是绝不可能的事。但是婆婆在这条街上是“地主”,平常就觉得自己家高人一等。她不依不饶,要当一回“讲话人”,非要剃头财他们给她儿媳妇洗名不可。
于是,剃头财夫妇跟在婆婆身后,抱着一箱香烟,挨店儿一坎一坎一包一包分下去。人们心知肚明,剃头财守着一个漂亮老婆,自己整天都在担心着红杏出墙,哪有那闲心闲力去“吃着碗里,看着人家锅里”的?剃头财笑嘻嘻地分烟,婆婆跟在后面一家一家地解释说明情况。人们对剃头财分的烟爱接不接,婆婆有一句没一句的话爱理不理。人们笑笑地接不接烟,笑笑地听没听着。
本想挑个软柿子捏,没想到破鞋扎了脚。婆婆这才觉得自己作妖了。这下好了,她终于知道大家在看谁的笑话。
打铁智邻村人,剃头财邻乡人,兴才平原区人,并非是他们要走到一起来,而都是为了到这小街上挣吃来的。店儿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一个月几十块钱租的。下社街对他们来说,不是小街,而是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心灵手巧得到施展的舞台。他们之间都互相认识,都各忙各的。剃头财、兴才不找打铁智打铁,也没空找他下棋。打铁智、兴才找剃头财剃头。打铁智、剃头财找兴才买东西。不称兄道弟,各自来清去明,最多的交情就到这儿了。剃头财分红七匹狼给打铁智、兴才的时候,他们一手接过,一手拆开,弹开烟就抽。很坦然,就像抽自己的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