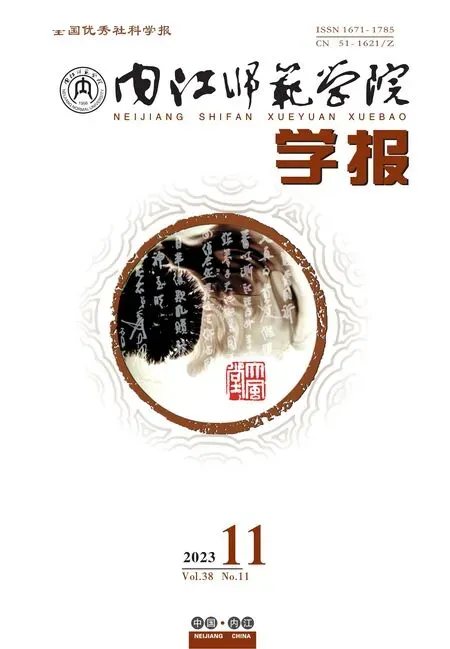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述与金毓黻学术交游及治史异同考论
杨 情, 刘开军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陈述(1911—1992),字玉书,河北乐亭人,与冯家昇、傅乐焕并称为“辽史三大家”,又被金启孮誉为“辽金史学之纛”[1]。金毓黻(1887—1962),原名玉甫,字静庵,辽宁辽阳人,于史学、文献学、历史地理、考古学等领域都有研究,尤精于东北史和史学史。吴廷燮评价金毓黻称:“今中夏言东北故实者莫之或先。”[2]1金毓黻虽年长陈述24岁,但二人志趣相投,从最初的信笺交流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同在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任教,朝夕论学,遂成忘年之交。目前学界尚未有专文梳理二人交谊,故本文尝试聚焦陈述与金毓黻的交游史实,进而考察他们的治史异同,敬请方家指正。
一、信笺上的共鸣与争鸣
1929年,陈述初中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史学系本科。在北师大求学期间,陈述得以受陈垣、朱希祖、钱玄同、陆懋德、张星烺等人的教诲。其中,又以陈垣对他的影响最大。至于陈述与金毓黻的学术因缘,则要从《金史氏族表初稿》说起。
1932年前,陈述已在史学上表现出不凡的才华。继《陈范异同》《蒋心余先生年谱》之后,陈述又撰成《金史氏族表初稿》八卷。此文受清儒顾炎武、钱大昕的启发,特仿“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之例,以《金史》为据,旁及《宋史》《辽史》《元史》与夫别史、杂记、文集、墓志、碑刻”[3],参考文献达180余种[4]368。1933年春,陈垣将此文推荐给陈寅恪。出人意料的是,陈寅恪竟因此文主动约陈述见面,二人相谈甚欢,陈寅恪还对陈述说:“平日我在清华园,周末进城,以后再来。”[5]180凭借此文,陈述还获得了傅斯年的认可,并于1935年4月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金史氏族表初稿》全文于1935年连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3、4分。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3分仅刊登了三篇文章,另外两篇作品的作者分别是胡适和郭宝钧。该刊第5本第4分上,与陈述同期发文的有赵元任、罗常培和岑仲勉等。也正是此文,引起了金毓黻对陈述的注意。金毓黻在1936年7月2日的日记中高度评价陈述的《金史氏族表初稿》,以为“其用力之勤可与钱氏《元史氏族表》相比,皆有裨研史之作也”[2]3873。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性人物,所著《元史氏族表》久为学林称赞。金毓黻却将年仅24岁的陈述与钱氏相提并论,足见金氏对陈述史学之赏识。两天后,陈述的名字再次出现在金毓黻的日记中。当天,金毓黻论及国内史学风气,写道:“近顷国人研史之风颇盛,盖倡于梁任公,王观堂。而继起者,以二陈为最,如陈垣之治元史,陈寅恪之治隋史、唐史是也。……冯家昇之研辽史,陈述之研金史,著作斐然,亦属后起之劲。”[2]3875金毓黻对素未谋面的陈述可谓青睐有加。
陈述与金毓黻初次见面,地点当是在南京。1931年东北沦陷后,金毓黻一度身陷囹圄。1936年3月,金毓黻以考察文物为名,经由日本东京到达上海。是年秋,金毓黻又转赴南京。金毓黻到南京后,常往史语所拜访傅斯年。陈述此时正在史语所工作。金、陈初晤当在此间。陈述写给金毓黻的信笺也证实了此点。1939年1月2日,金毓黻的日记中附录陈述来信,有“南京别来,未遑教益,二年内几曾大变,真想不到”之语[2]4267。陈述此信当作于1938年底。由此上溯两年,则二人在南京初识的时间约在1936年末或1937年初。
抗战的烽火很快将金毓黻和陈述分隔在两地。史语所几经迁徙,陈述也先至长沙,后携家眷到昆明,继续在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金毓黻则随内迁的浪潮,转赴重庆。但即使转徙于西南天地之际,陈述与金毓黻的学术联系也并未中断。1938年,陈述写成《曳落河考释及相关诸问题》后寄赠金毓黻。金氏“发缄快读,喜心翻倒”,但未及回信,“私心滋歉”[2]4263。不久,陈述再次由昆明致函金毓黻:
近试草《头下考》一文,解释头下为一契丹通制,不仅头下军州,他日录清再呈删正。曾在南京时,先生曾谓辽陵壁画有薙发一围,未审是男是女?抑男女皆开薙耶?又教关于舍利氏一点。二年来车船旅舍中,未能检比群册,谅先生近必有高见也。敝所书籍久装箱箧,大著《渤海长编》亦不得细细拜读为憾!述意舍利始初或是一种制度,后以名官,以为氏,不过为臆度之辞,还希赐教。[2]4267-4268
由此信可知,两年前金毓黻就曾与陈述讨论过辽陵壁画和舍利氏问题。陈述此番来信,发抒己见,意欲延续二人两年前的学术话题。此时,金毓黻正讲授“宋辽金史”课程,对辽金史用功甚勤,且陈述所提之问题亦正是金氏待考之题目。故此次金毓黻给陈述的回信极为认真,“作覆陈玉书笺,约二千字,时许乃毕,存稿”[2]4263。金毓黻高度评价陈述的《曳落河考释及相关诸问题》:“精当无伦,不能再赞一词,谨表钦佩。”[2]4267在回信中,金毓黻又对陈述提出的问题一一答复。金毓黻认为头下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所谓头者,其义或如首领,头下即在首领之下之义,所谓横帐诸王、国舅、公主、外戚、大臣皆即当时之所谓头也”。二是据清代建国之初,允许王公、勋戚圈地,“有带地投充之户,就所投充之户而加以编制,是为各王公之包衣、奴仆,亦犹辽代于所俘掠生口而部勒以团集之制也。清代之视投充户亦犹俘掠,或者辽、元之世亦视俘掠如投户、头下之意,即谓所投之下,以投、头音同,故亦谓之头下”[2]4264。至于辽陵壁画,金毓黻也详加描绘:“辽陵壁画之所绘者为男子像,将其顶发薙去,所余者仅其外围,其形略如《明太祖实录》所纪元代薙发之式,此正可证契丹与蒙古同俗。”[2]4267关于“舍利”之义,金毓黻举《新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国语解》等多条文献,基本赞同陈述之说,“舍利之为官名已无疑义”,并补充到“舍利之称,为契丹先世特定之官,又用契丹语为名者也”[2]4265。另外,金毓黻还对“横帐”一词作出辨析,认为“横帐之初称,盖专指太祖所居之帐,继则命其子孙之居帐亦曰横帐,再继则凡三父房所居之帐,俱得谓之横帐”[2]4266。金毓黻对自己的这一考释还是颇为满意的,尽管陈述来信中并未涉及“横帐”,仍忍不住与陈述分享这一心得。金毓黻还在信末鼓励陈述作文考释“舍利”,托陈述帮忙代求姚从吾的《辽金元史讲义》,希望能尽快读到陈述的《头下考》。“尊作《头下考》,必得有多证,且谓为契丹通制,颇欲以先观为快,不示能否择要钞示。”[2]4267这封信笺,生动地呈现出民国时期辽金史研究的两辈学人之间的深厚交谊。
继1939年1月2日的信函之后,陈述提出的“舍利”“头下”等,成为金毓黻日常阅读和研究中放不下的问题,双方也在信笺上往复商讨。如1939年2月8日,金毓黻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修正了他此前的看法,“愚以舍利为官名,本无可疑,惟宋人所释,一为舍利,一为舍利郎君,舍利为军校之称,舍利郎君则为皇族子弟无职事者之称,据其一称以定其舍利之通义,自属未当。愚于陈君所释,未能首肯,亦以此也”[2]4282-4283。1939年3月3日,金毓黻在日记中详载关于“头下”的考释。本月,金毓黻作长函给陈述,依次讨论“头下”“舍利”和“横帐”之意,但此信未及时寄出。至是年7月,金毓黻读到陈述寄来的《契丹舍利考释》《越里、野利、逸利、越利诸族考》二文,又于7月18日写信商讨,并将3月所写长函一并寄给陈述。在7月信函中,金毓黻将陈述的“舍利”之意概括为七点,而将自己的观点总结为四点。二人观点有同亦有异,金毓黻认为陈述以皇族之义释“舍利”,“未敢以为允当也”。“陈君又谓亲近者非皇族莫属,亦未敢谓然。……陈君又谓豪民纳财以得舍利之号,即捐为皇族之意。愚意谓舍利之内,含有皇族之大部则可,而不必迳谓为皇族之称;谓豪民纳财捐舍利之号则可,而不必谓捐为皇族。以此为释,界义乃清。”[2]4352
对于金毓黻的主张,陈述十分重视。如在“横帐”辨析上,陈述就认为金毓黻的解释胜过日本人稻叶君山:“日人稻叶君山撰《契丹横赐横宣释》谓横帐之义犹之黄帐,而黄色之来历,则以蒙古语西喇为黄,以世里与西喇对音,仍循白鸟之见。……金静庵先生曾论横为特设之义,较前说为胜。”[6]91但陈述在一些问题上仍坚持己见,比如在“头下”问题上,金毓黻认为:“太宗以后,头下之制,似止限于军州一种制度。”[2]4340而陈述在公开发表的《头下考(上)》一文中,仍称:“所谓头下,实是一种通制。头下军州,不过此制之一种。”[7]陈述将此文从昆明寄给金毓黻。对此,金毓黻在1940年10月1日的日记中写到,陈述“于此致力极深,其未能得确解者,史实缺乏,有以限之也”[2]4592。
综上,自初识至1940年底,陈述与金毓黻往复论学已四五载,在学问上相互问难,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作为后辈的陈述自然尊重金毓黻,金毓黻也将陈述视为学术知音,并因不能朝夕相见为憾,“友辈仅见陈玉书、傅乐焕二君喜研宋史,然皆不在此间”[2]4483。自古知音难觅,更何况山水阻隔,硝烟弥漫。这种情形直到金毓黻借调陈述到东北大学才有所改变。
二、三台时期的论学、雅集与别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大学校舍被日寇占领,金毓黻被迫流亡,先后辗转于北平、西安、开封等地,最终于1938年3月迁至四川省三台县。此前,金毓黻已于1938年2月重回重庆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①。是年8月,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邀请金毓黻到三台东北大学执教,金氏以“方草《史学史》未就,且拟续撰《东北史》,需参考书甚夥,一经移转,则旧业立废,未忍舍此就彼”,故“作书谢之”[2]4205。1939年9月,臧启芳再邀金毓黻,金氏便向中央大学请假半年,到东北大学讲授东北史。一个学期结束后,金毓黻又回到中央大学讲授宋辽金史,金毓黻就这样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两校交替授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秋。此后,金毓黻便专心在三台东北大学任教。
1940年8月,东北大学设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聘金毓黻为研究室主任,主持研究室工作。金毓黻遂借此机会向傅斯年请求借调陈述。据《静晤室日记》,金毓黻于11月5日分别致信傅斯年、陈述[2]4602,应是商量借调之事。六天后,金毓黻“晤傅孟真于聚兴村,商聘陈玉书事已谐”[2]4605。12月26日,陈述抵达三台[2]4621,受聘为研究室的研究员。就这样,金毓黻与陈述在三台再度重逢,二人从学术同道变成了东北大学的同事。金毓黻原拟借调陈述一年,但陈述在东北大学一待就是六年。如前所述,金毓黻春季学期任教于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秋季学期任教于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在金毓黻赴渝任教期间,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的工作主要由陈述负责。研究室创办的《东北集刊》第一、二期亦由陈述主持集稿付印,可见金毓黻非常器重陈述。这一时期也是两人交往最密切的阶段。
三台时期,陈述与金毓黻常在一起切磋学问。1942年8月13日,金毓黻举《宋史·忠义传》所载何充之语,认为“欲辫其发而髡其顶”[8]13239八字最应注意,并解释“余向见辽陵壁画,武臣顶发皆髡去,而留其四围,留发皆下垂,而在两鬓者犹长,正与女真人髡其四围,止留顶发者相反,由此可证契丹、蒙古二族同出一源,《何充传》所记之军帅大将,即蒙古军帅也。”陈述“检以相示,因亟录之,以证余说之有征”[2]5006。而陈述“谈《北盟会编》卷三所纪女真事,即《北风扬沙录》之详本”,金毓黻以为“此可谓一大收获。”②,[2]4623金毓黻为研究生讲宋代官制时,提到宋代有堂后官之称,后从陈述处受到启发,撰成《堂后官考》一文。金氏在文末特别感谢陈述:“余考证此事由陈玉书(述)教授之提示,不敢没其由来,附笔致谢。”[9]陈述初到史语所,便开始校辑《辽文汇》,至1940年春校讫,但因战乱未能付印。《辽文汇》是辽朝一代史料的总集,所收较完备。金毓黻曾向陈述借抄《辽文汇》,从中寻觅史料,以补所缺。1942年2月12日,金毓黻便将《辽文汇》中之贾师训墓志录出,“并撰考证一文”[2]4886。金毓黻曾到朝阳县考古,得见韩瑜、韩槆二人墓志铭,但未拓印。这两篇铭文恰收录于陈述的《辽文汇》。1945年12月,卢前向金毓黻借《辽文汇》时,金毓黻想到尚未将二文录入其日记中,遂取《辽文汇》,原文抄入,以备日后研究之需。③,[2]5982
金毓黻雅好游历,在治史经验上有“脚勤”之说。所谓“脚勤”,就是要勤于游历,一则广见闻,二则“太史公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故《史记》文有奇气;明人徐宏祖撰《霞客游记》,以写所见南北各地之山水,卓然为一名作,此游历有资于文章者也。……坐诵一室,冥与古会,难言治史”[2]4146。所以每至一地,金毓黻常外出踏查。他受聘于东北大学史地系主任后,便为自己定下四项计划,其中一项即为三台附近史迹之调查。这一时期,金氏常邀好友外出郊游、访友。在这些雅集中,陈述与金毓黻总是形影不离。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记载1941年2月23日“午前,同陈玉书入城,偕校中同人渡江至东山寺野餐。与会者二十七人,童子三人,午后尽兴而归。在潼游观之乐,此为第二次”[2]4657。1941年9月26日清晨,金毓黻同陈述一道“诣乐安铺访吴君希庸,距草堂十余里,行时许至焉”[2]4803。同年12月7日,金毓黻在日记中又载:“晨起,偕玉书入城,至校内,与同人作北郊之游。步出北便门,行三四里,过北塔下,又经一小塔下,折而西行,至观音渡,造涪江航务工程处憩焉。……午后乘舟,顺流至东郭登岸,遂穿城而返草堂。今日之游颇能竭尽欢悰,为数月来所仅觏。”[2]4855“偕玉书入城”表明陈述与金毓黻同进同出,交情甚笃。半个多月后,金毓黻在亚芳餐馆宴请徐子明,也邀请陈述和吴希庸等作陪。1942年1月25日,金毓黻又“邀本校诸公饮于草堂,食豆腐,颇能尽欢,谓之草堂雅集,与其事者十余人”,陈述亦在其列[2]4878。此类聚会有古代文人雅集之趣,在那段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日子里,给了金毓黻和陈述等人一份情感上的慰藉。
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之旨趣与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相似,以养成研究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为目标[10]649。第一届研究生5人,平均每周上课四至六小时[11]678。陈述十分勤勉,除了授课,大多数时间待在办公室读书、写文章。1941年3月,东北大学发生“暗杀聂有人”事件,由此牵扯出文学院长萧一山和校长臧启芳的矛盾[12]172,校内人心浮动。陈述只愿埋头做学问,不愿参与政治斗争,此种状况之下,自觉不胜其扰。金毓黻便开导、鼓励陈述:
方今之负责者,皆以敷衍门面为事。及其内部溃决,至于不可收拾,补救已晚,究其病源,乃由平日精神不能贯注所致,吾辈作事,自当以此为戒。……君研究学问之精神,锲而不舍,因小见大,弟极端钦佩。惟气象规模应再力求开展,方足以应付环境。弟愚不自揆,谓于此端,似胜左右一筹,以马齿加长之故也。大凡吾辈应以陶铸人才为己任,有为之青年在吾指导之下,应以诚恳之精神感召之,久久未有不为所动者。只要气象光昌,规模闳大,则无事不可举重若轻,是在吾辈之努力耳。[2]4675
金毓黻现身说法,向陈述谈治史经验及应付社会环境之方略,并以培养弟子、光大气象相砥砺,此番肺腑之言非知音不可道也。当然,金毓黻与陈述交流时偶尔也会言语直率。事后金氏亦自我检讨:“晚邀研究所同人及诸生聚餐,餐后对陈君玉书颇致诤言,措词太直,使陈君踧踖不安。此诚余之口过,非所以全交要好,不可不戒。”[2]5075从《静晤室日记》来看,这一小插曲并没有影响金、陈二人友谊,品茗叙谈依旧[2]5269。
1944年冬,东北大学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出现了反对校长臧启芳和“东北五老”(金毓黻等)的运动[13]211。金毓黻时任文学院院长,风波发生后,金氏遂辞去院长职务,“时至今日,万不可再延,故应有决心辞职之表示”[2]5730。 此后,金毓黻又决定辞去东北大学教授职务,并于1945年春离开了东北大学,重回中央大学。临别之际,陈述夫妇邀金毓黻夫妇晚餐,席间陈、金二人相谈甚欢,“不觉已二鼓”。金毓黻向陈述谈及朋友之于人生的可贵:
人罹重疾,展转呻吟于床褥,当此之时,至亲契友勤来慰问,则中心必为之一快,此盖人情之常也。至若遭逢非常,荆棘横生,正如人罹重病,友人于此时而来慰问,而中心之感慨正与呻吟病榻时相等,此古人所谓“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也。人生不可一日无友,而良朋互相慰解于寂寥之中,推而至于其极,又可与生死人、肉白骨相等。人必喻此理而交道乃可敦,否则以世俗浅薄之见处之,今日为朋友,明日则为仇讎,则朋友一伦,可以无有,而世运亦几乎息矣。”[2]5811
将金氏此番言论与其离开东北大学的另一原因联系起来,便可知其深意。金毓黻初到东北大学时,对校内人事关系融洽十分满意。但在日后的相处中,金毓黻逐渐与萧一山、高亨、丁山三人产生矛盾,日记中屡见其记载人事方面的不快。因组织结构与院系变化,加之派系斗争,东北大学人事更迭频繁。金毓黻常感苦恼,几欲离开。在金毓黻看来,萧、高、丁三人便是“以世俗浅薄之见处之”。而陈述则是“良朋”,上和下睦、相亲相近,能“互相慰解于寂寥之中”。在金毓黻处在低谷之时,他与陈述“交情乃见”。翌日,金毓黻“慨当以慷”,写出“快意之作”《古意》,赠给陈述:
君家在辽西,吾家在辽东;辽西与辽东,一水可遥通。夷齐吾所慕,田畴吾所崇。夷齐不仕周,田畴能固穷。生有高世节,殁为诸鬼雄。君既生其里,必能习其风。知君苦不早,邂逅在兵戎。我方淆群言,君为折其衷。得失等秋毫,毁誉比鸡虫。人心本如面,世论亦不公。时事一朝异,悠悠谁与同。君子不宿怨,所贵全始终。愿坚白首约,相慰寂寥中。[2]5812-5813
“知君苦不早,邂逅在兵戎”,实是真情实感,直抒胸臆。“愿坚白首约,相慰寂寥中”道出了一代学人在艰难岁月里的深厚友谊。从1936年至1945年,陈述与金毓黻相识近十年,他们的情谊,既是真挚的,也是深厚的。20世纪50年代,陈述与金毓黻同在北京履职,亦有往来。遗憾的是,留存的相关史料较少,暂时难以重建这段史事,唯有俟诸来日。
三、陈述、金毓黻治史异同
金毓黻、陈述为中国辽金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均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在金氏之前,罕有人对辽金史进行专门研究,所著《宋辽金史》是近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辽金史的早期代表性学术著作。而陈述也毕生致力于辽金史研究。张博泉说陈述是“当代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的前辈和盟主,我辈踵其后而治学。他在辽金史的研究、领导学会、团结国内外学者,以及推动辽金史研究的开阔过程中,功当居首,素为予所敬”[1]30。但是同为开风气,金毓黻与陈述对辽金史的研究,既有齐同,亦有殊异。
第一,金毓黻与陈述皆擅考证,都强调金石证史。
金毓黻在北大师从黄侃,同时受章太炎的影响,汲取了古文经派考证注释的治学方法。金毓黻阅《潜研堂集》后,对钱大昕推崇备至,称其“精研经史,言必衷于有物,学必期于致用,为乾、嘉间学者首屈一指”[2]686。又在日记中自陈:“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余用其法以治史,其途出于考证,一如清代之经生,所获虽鲜,究非甚误。”[2]5404金毓黻认为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精通音韵、训诂的经学大师,“虽以余力究心史籍,然所得不多,未为名家”。而钱大昕与全祖望“于史籍致力最深,旁及舆地、金石,至为精绝”,得出结论:“盖舆地金石有裨于史事者甚多,研讨史学者未有不究心于此者也。”[2]1324故金毓黻治史向来重视金石资料。《辽史》《金史》因错误、缺漏处甚多,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金毓黻对此也深有感触。例如,据辽道宗皇帝哀册拓片、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拓片,道宗年号有大康、寿昌。《辽史》则载道宗咸雍十年改元太康,太康十年改元大安,大安十年改元寿隆。而《契丹国志》谓道宗咸雍十年并未改元,三十年始改元寿昌。两书记载有异,金氏据《金石萃编》中北京行满寺经幢、慈悲庵经幢,又遍考辽碑,考证《辽史》将大康记作太康,寿昌记作寿隆之误[2]2335,2336,2761。又有一金代印信文曰“上京路军马提控木字号之印”,背镌“贞祐三年十二月”,而《金史·百官志》无军马提控之官,金毓黻根据《宣宗本纪》贞祐三年九月,设潼关提控总领军马等官,推测“上京路军马提控”一职亦设于彼时,为新设之官。至于《金史》未载的原因,金氏认为“至贞祐三年,金已南迁,新设之官不遵祖制,故志不能悉载,据此可补其缺也”[2]1871-1872。金毓黻将金石证史的方法充分运用到辽金史研究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陈述师从陈垣。而陈垣“服膺嘉定钱氏”[14]326,亦有“百年史学推瓯北”[15]570之语,曾谓“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16]85。陈述跟随陈垣学习,受到陈垣“史源学实习”的严密训练。众所周知,陈垣秉持对史料搜集“竭泽而渔”的原则。《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陈垣提出理证、书证、物证、实地考察四种考证方法,其中所谓“物证”即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16]101。在时代学风熏染和陈垣的谆谆教诲下,陈述亦重考据,践行金石证史的路数。陈述校辑《辽文汇》,便将新出土的碑文、契丹石刻等收录其中,认为“以此治契丹史,容可于汉文文书有所补苴也”[17]3。陈述所著《辽史补注》《契丹史论证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等采用的出土资料,亦多取自于此。至20世纪80年代,辽代碑文所出增多,陈述将所得新出者抄拓录存,重新核校、订补,成《辽文汇续编》,又将二者合刊为《全辽文》,足见陈述对金石资料的重视。在《契丹军制史稿》中,陈述对属珊军进行考释,认为属珊军属于留后支援部队,举《李内贞墓志》为证,据“大圣皇帝(阿保机)兵至,迎降。加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兼属珊提举使”之语,推测李内贞以降辽的汉官受命提举属珊,加官工部尚书,应是管理一些被俘掠的工役[18]3。陈述又据《贾师训墓志》,证明契丹国曾在宋辽边界地带设过类似特务机关的机构,负责军事情报的密侦调查[18]28。陈述晚年提出辽金史研究要朝着补阙拾遗的方向努力,第一项任务便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可以直接纠正、补充文献记载[19]。
第二,金毓黻崇尚“由专而通”,陈述则恪守专精之道。
关于“博通”与“专精”在治史中的关系,金毓黻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大致呈现由专而通的学术轨迹[20]。金毓黻以“求博”为戒,以为“凡人于学问,只宜求精,不可务博,博则力分,力分则业荒,业荒则永无求精之日”[2]157-158。1921年6月,金毓黻读吕思勉的《论整理旧籍之方法》一文后,写道:“专则易精,泛则难备,专门史之优于普通史以此也。”[2]362但至1938年,金毓黻的博约观已发生明显转向,“学贵综博,治史尤要,隘涂自限,决难有成”[2]4145,一改此前看法,屡屡强调先博后约,求通重于求专。之后,金毓黻对通史撰述极为关注,推崇钱穆的《国史大纲》,在与缪凤林的信中说:“治国史难,治通史尤难,倘今日多得几辈,如左右及宾四、荫麟者,萃其力以治国史,岂不足以通古今之故,成一家之言,发千载之幽光,建永世之伟业乎。”[2]5092金氏亦曾多次在日记中表达想要撰写一部通史的想法,虽未能遂愿,但他此后一直沿着博通的路数治史,不仅在东北史领域作贯通研究,于宋辽金史、明清史、近代史(太平天国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都取得了成就。反观陈述,他第一次拜访陈寅恪时,陈寅恪就对他说王国维“是中外闻名的大学者。他的兴趣经常转换。如果他不换,成就会更大”,陈述体会到陈寅恪教导他做学问要专一[21]。所以,陈述自青年时代起,即潜心矢志,博观而约取之,深耕于辽金史领域,虽困难重重,但一生不改志向。他在《辽史补注》自序中说:“所谓简要,须是由博返约,并非夺漏史实。”[22]自序8他一直恪守“返约”原则,心无旁骛,自成一家。
第三,在辽金历史地位的认识上,金毓黻以宋史为正史,以辽金二史为别史,陈述则将辽、金与宋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
1938年,金毓黻在中央大学讲授宋辽金史,撰《宋辽金史讲疏》,后多次修改,于1946年易名为《宋辽金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一章总论部分,论述宋与辽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实际上涉及到宋辽金正统之辩。金毓黻认为治这一时期的历史,应该“以宋为主,辽金为从,一言宋史,即含辽金在内,此基于汉族及中华民族之立场,以明宋与辽金在国史上之地位者也”[23]1。但他又认为“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存偏狭之见,斥辽金史为不足观,则精详之史实,既不能尽弃,亦大背史家宁繁勿略之旨”[23]2。金毓黻得出折中的结论:以宋史为正史,以辽金二史为别史。陈述则与金毓黻看法不同。1948年,陈述所撰《契丹史论证稿》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刊行,陈述在书中指出“契丹为中华民族之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广溢,亦吾中华民族之光荣”[24]13,这一论断已然跳出大汉族主义的窠臼,而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来看待历史问题。他又说:“方今全国一家,纵以地域、气候所限,容有生活方式之殊,而精神之凝聚无间,是又吾人所不可忽视者也。”[24]11陈述斟酌取舍,详细考证,目的在于用史实证明南北文化的结合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础,为加强中华民族整体团结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提供了支撑,其中寄托的爱国精神深切著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述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对此观点进一步补充。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陈述指出辽、金及五代与两宋的对立,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他认为契丹“建国二百余年,形成国史上又一次的南北朝,在此期间,他们加强了北边部落的联系,沟通了长城南北的某些隔阂、差别,为祖国统一准备了有利条件。对于当时和以后的各族人民,都有不少直接间接的影响”[25]2。到20世纪80年代,陈述对这一观点的论述更为全面。在《契丹政治史稿》中,陈述直接将 《契丹史论证稿》第一篇“亚洲之游牧民族” 改编为“契丹在祖国历史中的地位”,还撰写专文《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深入分析辽金政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阐明辽金两朝“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的交互影响和发展前进,起着极其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26]2。时至今日,宋辽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的观点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四、结语
通过比较金毓黻与陈述学术风格的同异,可以发现,他们各具风采,于学术理念、治史态度等方面均有殊异,但是他们彼此尊重,有着共同遵循的“道”,即史学家的使命感。正是由于这样的使命感,金毓黻不辞辛劳地奔波于三台与重庆,要将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组织和维系起来。陈述答应借调,离开当时顶尖的学术中心——史语所,转至东北大学,亦是希望为国家、为东北地区做贡献。他们充分认识到研究东北问题的学术意义,遵循着共同的“道”,力图通过历史研究,运用知识促进社会进步。金毓黻一直坚信:“夫人之所以为人,以其有修己安人之心,博施济众之念也。能时存此念,努力为之,而民族命运乃能延续不坠,继长增高。”[2]5473陈述亦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肩负起本学科的时代责任。”[27]正是由于他们都能坚守史家本心,在国家危难之际著书立说,展现爱国情怀,才奠定了二人深厚的学术交谊。陈述与金毓黻之间这段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交游,彰显出那一代学人的学问境界与爱国正气。
注释:
① 1936年金毓黻到达南京后,由傅斯年引见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后金氏受邀出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便向罗家伦请假离开了中央大学。此时中央大学已从南京迁至重庆,故文中有“重回”之说。
② 《北风扬沙录》系南宋陈淮撰,记录女真族由来及其分布,对其生活环境、习俗、衣食、组织形态等内容均有涉及,是了解女真族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③ 卢前(1905—1950),字冀野,江苏南京人,历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平生致力于古戏曲的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