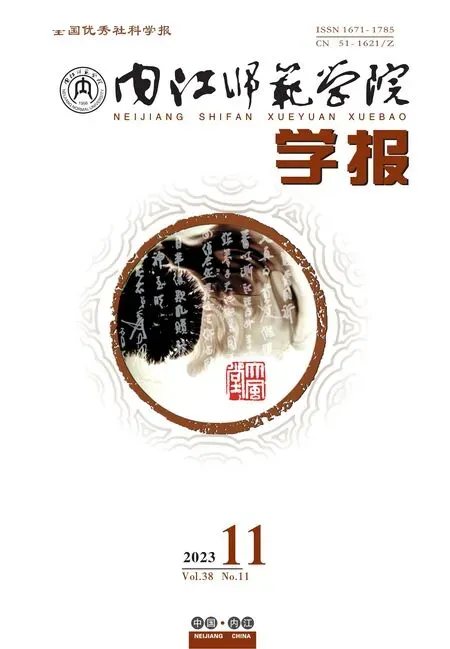阎真小说知识分子“失节”论
陈 如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知识分子的“失节”问题是阎真系列长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故事生长点,从《沧浪之水》到《曾在天涯》《活着之上》《因为女人》,再到最新出版的《如何是好》,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语境里,往往面临着在现实生存和人格理想间作何选择的自我悖反的两难选择困境,而“失节”则是历经一番挣扎后知识分子的最终宿命。所谓“失节”的论断,参照符合社会普遍想象的人格审判标准,取诸文本人物在理想屈位于现实后的心理表征,例如矛盾、忏悔、无奈等,也参考了隐藏在文本中的作者情感话语基调。在“失节”的判断中,“节”的内容不乏独立、道德、精神、志业、终极价值等与社会良知相关的概念。在来自传统演绎与世界、时代格局新变的现代性焦虑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形象由于符合社会的期待,因而被不断固化加深形成一种身份前见,文本内外审判知识分子的当代选择“失节”与否成为可能。“失节”事实使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批判的靶点,然而,重点并不在于知识分子“失节与否”,而是“何以失节”,知识的有限性以及知识分子对其的献祭姿态对此责无旁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处理男女知识主体的“失节”困境时,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对于男性知识主体,人生志业、人格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架构了失节的空间,而对于女性知识主体,人生志业退化为婚姻、爱情,人格理想浓缩成女性贞洁,这体现了一种男性的凝视。面对“失节”困境,作者也体现出探讨知识分子如何调整传统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与现代社会自适的意图,但是往往止于牢骚的喟叹。究其原因,作家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立场身份与为底层发声的意图逻辑无法自洽,其力图以极度写实暴露当代年轻人的现实困境,对知识分子话语身份的征用却只局限于讨论其朴素的庸俗道德,主体的选择问题被置换成宿命问题。作者预期将知识青年困境打造成社会现实镜像的“特异性典型”,以放大社会的矛盾,却因为庸俗化的处理,缩小了反思的范围、弱化了反思的力度。同时,其群像化的写作既造成了审美疲劳也见证了作家的自我重复困境。
一、知识的“原罪”属性与知识分子的“献祭者”姿态
纵观以阎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其中对知识分子的失节有“社会归因”和“自我归因”两种解释路径。从表面上来看,文本中知识分子的“失节”多出于事与愿违、被逼无奈的社会原因。例如,如果体认池大为具有知识分子的良心,他的失节便成为集体失节逼迫下的结果。但这种分析只是对现象的披露,将知识分子失节渲染为一种环境使然的后果,批判的重心陷入了虚空,毕竟,失节集体中的个体或许就是由一个个池大为“发展”而来的。而以一种内观的视角来看,大部分的论断则是否认池大为的知识分子身份,认为池大为是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典型。诸多评论直指池大为这一个体,认为池大为“以虚构的超越性的人格价值来伪饰自己作为堕落时代平庸个体的渺小与猥琐”[1]。其中一种公论指向池大为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超越性的缺乏。内在的超越性的缺乏有几种话语阐释模式,一是从传统语境切入,剖析其文化根性纠缠下的矛盾人格,即在儒家的“功名利禄”和道家的“韬光养晦”间徘徊不定;二是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剖析其现代性焦虑,即获得终极价值与对现代性既渴求又疑惑的矛盾。对池大为是否可以被指认为知识分子典型的判断,其实是决定相关批评立场分歧的关键所在,而对其所征用的“知识”及其对“知识”的态度决定了池大为“何以失节”这一问题的本质。
作为知识分子赖以自证身份的文化与精神资源的“知识”,具有相当程度的有限性。一方面,传统文化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知与行的分离、理论与实践的互不适用,好形而上的理念高蹈而轻具体的实践总结等等,导致传统文化在处理现代经验上十分有限。池大为以家承的历史人物画像高自标持,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心态,即实现从“凡”到“圣”的超越,其中隐约见到传统的写史模式对中国知识分子行为的塑造作用。那种“为尊者讳”的颂史话语在塑造了历史典型的同时,也造成了评价标准的单一化,进而导致认识评价路径多元化的封锁。这无疑会助推具有诸多弊端的传统的一元化思维方式的延续,诚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我文化根性的坚守本身就蕴藏着危险”[2]。此前的省身标准放置现代社会固然有其实践价值,但是却并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现代社会的无限可能性,要求现代人不能做削足适履、刻舟求剑这样的死板僵化之举,而要在“通”与“变”中找到传统标准与现世社会的自洽方式。另一方面,知识的符号化属性压抑了其理性实在的一面,无法实现回心践行的省身效用。知识分子以承载着各种内容的知识建构自己的身份,并期待获得社会的认同,然而这个社会只是一种理想的概型,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导致这种实践失败。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更大且直白露骨。
知识的有限性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将既有的精神资源转换为应对现实问题的方案。可见,“知识”本质上成了一种“原罪”式的存在,既作为知识分子自身行动的内驱力,又作为社会现实与历史审判的资源,禁锢着知识分子。然而,如果失节者不再是“知识分子”,那批判的指针又要落入何处?知识分子链接了“知识”和“品节”的相关性,他们不断继承、演示、创造这种相关性。可见,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一种“自我献祭”般的认同与继承,也使得他们陷入知识的围城里。
在现代文化语境里,知识分子对知识,有着一种“知识拜物教”的传统。正如孔乙己的那身“长衫”和对“回”字的几个写法的自吟所暴露出的知识分子的脆弱与精神的贫瘠,以及鲁迅笔下以自立为目标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孤立’与‘寂寞’”,“必须承认,现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寂寞’实际上也同孔乙己等人的‘寂寞’相关”[3]82。阎真的知识分子小说,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商品拜物教时代下,承袭了孔乙己式的知识的“自我献祭”的精神姿态。作为形而上层面的概念物存在的知识,具有的“宗教性”的神秘感在进化论的实践开展中不断祛魅。尤其在商品经济时代,知识逐渐落位于一种商品,知识分子以知识赖以自豪与自证,环顾四周无人响应,知识因而成了他们“寂寞”的源泉,这是知识拜物教的自我献祭。无论是池大为、高力伟,还是许晶晶,他们身上都隐约可见这种献祭的“鬼气”。用余英时的话来说,“‘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和‘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做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4]6。无论是丸尾常喜所指认的“鬼气”,或是余英时所谓的“幽灵”,对这种传统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依附效果的形象化指称,不可谓不警醒。
回顾人文知识分子惶惶自危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这一点会有更具体化的认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热潮下,知识贬值、话语媒介发展、教育普及等现象,使每一个人都有了阐释和对话的权利。人文知识分子引以为豪的话语权与阐释权不断被稀释,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前后落差无疑会让人文知识分子无法自适,向来以社会思潮先锋引以为豪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如韦伯所言的“诸神黄昏”困境。然而竟不止人文知识分子如此,市场运作下,知识经济快速发展,当知识的商品属性不断膨胀之时,知识的征用者也无法避免被异化而成为知识的奴隶,即便是专业知识分子也无法适从。
二、特异性典型与失贞的多重隐喻
阎真笔下“失节”的知识青年群像中,还存在一种特异性典型,即女性知识青年。相较于男性知识分子,女性知识分子的失节表征更为复杂。一方面,知识女性同样面临着知识失效的问题;另一方面,阎真采取了替换与遮蔽的话语策略,对女性知识群体的道德理想的“失节”审判背后,实际上隐喻了对女性伦理“失贞”的拷问。小说所构建的社会文化场域暴露了男性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征用上的失败,这一失败继而导致人生志业的理想失落困境。但作者对知识女性理想失落困境的架构始终没有溢出爱情、婚姻的理想与现实冲突这一框架,也就是说,对于“人生志业”这一理想失落困境,女性其实并未被纳入到讨论中,或者说,因为诸多问题的缠绕,例如围绕爱情、婚姻—物质困境所置入的一些观念(女性的外貌肉体与性欲观、情感前史与贞洁观等等),对女性在这一问题上的反思力度极其有限,也暴露了男权话语下对女性的物化凝视,从头到尾隐藏着不自知的性别偏见。从男性个体到女性群像,作者试图将女性的两性困境普遍化为当代青年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其现实视野虽然更加宏阔,但是对女性的自我成长与突破的探索依旧十分有限。
不管是作者还是批评者,他们的视野下,知识女性游离在知识分子的人生志业困境的讨论之外,这是作品的文本以及相关批评所体现的第一重偏见。以知识女性为主体群像的两部小说《因为女人》和《如何是好》里,阎真好以爱情作为主人公近乎唯一的内省驱动力,常常设置一个“现实诱惑”与“爱情理想”的两难选择困境,将女性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局限在“爱情”和“物质”的考量之间,悬置了女性主体发展的更多可能。五四文学中,爱情书写寄予了个人意识觉醒的期待,但在阎真的小说里,“爱情”却渐变成女性自我价值的唯一证明。同时,诸多批评聚焦女性在面临爱情和物质选择的两难困境中的犹疑,得出诸如“眼高手低”“爱慕虚荣”“理性不足感性多余”之类的评判,力证女性“自我主体性”的缺乏,但鲜有评论对作品中女性在“知识自救”上抱有期待。柳依依获得了硕士学位,却无法借助知识实现精神的超越,超越对女性身体的自我攻击。许晶晶的人生择业已经远远逸出知识带给她的专业价值。“知识”给她们带来社会场域的“入场劵”,而当她们真正陷身于现实的泥淖无法自拔时,知识并不能带来理想的效用,反而作为建构身份的符号给她们的行为戴上枷锁。可见,知识的符号化属性在女性群像作品中更为突出。
选择以“爱情”作为女性人生困境结构的支点,则构建了另一重偏见,隐藏了男权话语下对女性的“物化”倾向。“爱情作为五四新文化价值体系的标志之一,从感性方面启蒙、教化反封建的一代青年,被文学作品征用为一种反封建伦理秩序的文化手段”[5]49。而在阎真的文本中,爱情之于女性是围城,女性的爱情消解之路,也是女性主体不断被物化之路。柳依依的爱情观历经了下沉式的发展,她在夏伟凯身上,寄予一种“主体间性”爱情的理想期待,包括肉体欲望的宣泄、灵魂的共鸣、感情的纯粹忠诚等。但第三者篮球宝贝的入侵,消解了她和夏伟凯爱情的排他性。一番逡巡,她将目光锁定在秦一星身上。秦一星是一个有妇之夫,二人之间的爱情不具备世俗的合法性。同时,秦一星带给柳依依的爱情体验,基本可以用肉欲两个字来概括,二人无法实现精神上的平等对话:秦一星之于柳依依是精神教父般的存在,给她提供物质、学业、婚姻上的指导;而柳依依之于秦一星,无异于一个精致的玩偶,甘心被“囚”于他安排的住所里,寂寞等待他的“垂青”,甚至还要接受秦一星对她“忠诚的第三者”这一荒诞的要求。在宋旭升身上,柳依依的爱情体验完全消失了。她对于宋旭升,是男性话语权在婚姻这一“政治制度”中的实践,宋旭升对她的期待不外乎子宫的占有以及通过柳依依对他物质凭附所实现的男性尊严。
柳依依的爱情消解之路,即她被“物化”之路。然而,将爱情的消解与女性的物化统一起来论述,并不是要再次陷入“女主主体性缺乏”的自证逻辑,然后将矛头又重新对准女性自身。女性是被物化的,是爱情的蒙蔽者,她们在爱情的消解之路中,不曾放弃过对现有爱情的合理化行为。如柳依依,沉沦之际对既有的爱情依旧怀抱着专一、忠诚、精神共鸣的期待,各种期待的实现程度并不一样。与夏伟凯,二人的爱情真实却短暂;与秦一星,爱情是她以物质自证的自我建构;到宋旭升,爱情最终落位于一种凌空的想象。即便爱情一次次令其失望,但她却从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爱情的期待。而作品中的男性对女性的物质、肉体、生活、精神的关照,是由欲望驱使的,并以此暗合女性对爱情的期待。不平等的“互动”关系极具遮蔽性,放大了女性主体在这一过程里的能动性,从而将矛盾焦点置于女性自身,而本应处于批判视野中心的男性却游离出视线。女性对爱情的追寻于是成了男性话语权实现的工具,在他人的旁观下呈现出自我献祭式的本质,对理想、独立精神、肉体自由的献祭。在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里,这种偏见更成为一种陈规,对“爱情理想”的坚定选择被预设为作品中女性的不二立场。不管是《沧浪之水》中的董柳,还是《曾在天涯》中的林思文,一个因为爱情选择了人生前程并不明朗的池大为,一个为爱情跨国等待多年,最后因激情淡去又重新开始追逐新的爱情。她们至少在选择的那一刻是坚定的,而她们在坚定选择后面临婚姻中的现实物质困境时所表达出来的需求,被自然地征用成对男性主体的现实压迫话语,女性俨然成为问题的根源之一。
婚姻是另一种社会装置,将女性收归到“家庭”的政治制度里。在这一政治制度中,女性的社会职能得到明确,男性则获得某种秩序的安顿,“因为父子们借此把原本很难把握的政治的、文化乃至心理生理的异己固定在一个可把握的位置上,把本来也许是不可理喻的异性群体幻化成一种不必理喻的对象”[5]17。阎真在新作《如何是好》中,对女性的困境结构进行了调适,突出了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求学”“求职”等社会问题,呈现了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图像,自予一种普遍的社会意义。但女性在婚恋上的选择依旧成为贯穿文本始终的因素。许晶晶突破了柳依依的“依附”思想,在多重考量之下,她以一种理性的姿态选择了对她而言虽穷但却最“合适”的叶能。许晶晶对叶能的主动选择体现了她理性的一面,但是她选择叶能作为婚姻对象的底层逻辑,在于叶能可以带给她一种“穷且益坚”的安全感。许晶晶不因家境悬殊而自卑,叶能因为清贫也不会有过分的世俗欲望,这种安全感契合许晶晶对婚姻的想象。许晶晶这一近乎“妥协”的婚姻选择也是作者对许晶晶的那一句“将来我在世界上一个人怎么办”给予的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是婚姻真能带给女性可预见的稳定人生吗?许晶晶在进入婚姻后,又面临了一系列的人生问题,包括育儿、婆媳关系、安居等等。
虽然阎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婚恋中逐渐变得庸俗琐碎,但是《曾在天涯》中的林思文却可作为父系秩序下的社会性别的“差异性关系”的“冲破者”,“女性的真实价值必须在与父系秩序下的社会性别的差异性关系中才能得到确定”[5]27。作为一个主动“出走”的女性,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高力伟在她身上未能满足“征服欲”,无法消除对女性在家庭秩序中夺权的恐惧,无法适应这样一种对他而言“反传统”的两性关系,他对那些温柔的、顺从的女子念念不忘,最后他选择与林思文离婚。高力伟眼中的“强势”实际上是林思文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此看来,从林思文到柳依依,再到许晶晶,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在加码,但社会的婚姻制度、两性的不平等关系依旧压制着她们,女性未能实现有效的破局。
除此之外,在爱情和婚姻的理想结构中,隐藏着传统的世俗道德观对女性的审判,是影响女性婚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文本中也被予以结构化的强调。女性的“失贞”行为从而变成了一种“特异性典型”,知识女性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
三、当“失节”成为宿命
陷入现实泥淖的知识青年,无疑是被阎真作为“底层”来表达的,但作者为“底层”代言的意图与其“中产阶级”的身份立场,使得作品的写实品格与艺术价值存在着诸多缺憾。一方面,作者对非亲历的材料进行了一种极具戏剧化的处理,把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戏剧化成了宿命问题,虽然极度写实,但是许晶晶等人并不能作为一种全面的典型。另一方面,作者对作品中的困境主体的“知识”征用也存在着技巧上的不足,对其选择往往陷入二元对立式的庸俗道德讨论,作者对知识的个人趣味化的征用,对知识代表的话语权的漠视都在削减作品的现实向度。作者对知识青年困境的无意识“宿命化”处理与对其话语权的潜意识否定,无一不指向一个现代性的焦虑症:主体性的丧失。
作者的“底层”知识分子写作,有其突破性。作为接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写实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阎真的小说并不像刘震云、池莉、王朔等人那样,消解知识分子的崇高性,他对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寄予了人格上的审美期待:高力伟顺风而呼,似乎有些屈原沿江放歌的清高之姿,池大为坟前泣泪往昔,也有阮籍穷途恸哭之遗风,而许晶晶最后眺望漫天繁星觉察我之渺小,更是千古以来文人骚客在自然万物前“愁予”的镜像……但是阎真也不像贾平凹、李洱、阎连科等人,探讨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与身份认同困境。他所处理的材料,是赤裸裸的关乎物质的现实生存问题,用阎真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贴地而行”的写作。作者以知识分子视角切入底层写作,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往的底层书写中对底层作为无法发声的“惰性群体”的偏见预设。同时,将知识分子书写的空间从精神楼阁拉下,将知识分子的生存重新投入现实物质、性别、出身等生存视野之中,也拓宽了知识分子书写的路径。
但是其局限性更为张目。坚持“贴地而行”的写作姿态的阎真,在采访中如是说,“我个人现在没有艰难的问题,在生活中有着中产阶级的从容”,“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来自生活现实的”,“那些在竞争中被边缘化的年轻人,面对生活无奈地躺平的年轻人,他们的痛苦,需要被体验,他们的痛感,需要被表达”[6]。作者的自陈表达了其现实主义写作的自觉与人民本位的写作立场。但是,这种“代言”的完成度并不高。首先,作者自身的立场与姿态,无法以超拔的视野为知识分子困境提供一种超越性的解决方案,所以他文本中出现太多无谓的喟叹,哲思的高蹈和鲜血淋漓的现实之间有非常大的割裂感。前一秒作品中的知识分子还在为几毛钱的菜价斤斤计较,后一秒又对空发出一大串的神思感慨,作者似乎不断以此来强调知识分子的“感物”属性,这些感慨不外乎人之渺小,时间易逝等。然而,这些感慨对于现实问题的施救效用十分有限。这种独特的审美趣味造成了文本艺术统一性的折损。其次,作者对知识分子的选择进行了一种“宿命化”的处理。阎真在处理知识分子的困境时,采用了“突转”的呈现方式,在写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时,拥挤的材料在突转的处理中接踵而至,人物还来不及反思立马又被一个接一个的现实问题围住,人物的困境遭遇有如“宿命”一般,选择问题被置换成了宿命问题。宿命化的处理,意在呈现知识分子向下沉沦这一悲剧中社会面的无限逼迫,但我们还是能找到其他因素切入对知识分子生存问题的探讨。在许晶晶的升学、求职、成家立业的人生困局中,当事人奔走于一个又一个的“突发状况”,但是若以人之常理,作为知识分子,她缺乏一种基本的反思能力。这种处理体现了一种中产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此前的底层写作中,这种优越感有赖于作者的文化性身份,在和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结合后,又有赖于文化场域内部“表达者”的话语掌握程度。这暴露了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危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挤压收缩,甚至存在无法发声的知识分子。作者无疑体认了这一事实,将知识主体的困境进行宿命化的处理由此表露出一种“话语压制”的倾向。作者无法真切地体验年轻人的边缘化痛楚,这让作品为底层知识分子代言的意图蒙上了一层雾障。
当“失节”被表述成一种宿命而知识分子却又无法自我言说时,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正在不断被稀释。虽然“如何失节”有理路可循,但是,重点并不在于给知识分子的“失节”找一个可以批判终极的始作俑者,或将知识分子所失之“节”进行一番改造。而是要认识到,不论知识分子失节与否,其面临的都是“被驯化”的结局,否则,知识分子就要在“失节与否”的拷问中继续沉沦。“失节”的条件是对知识原教旨主义的背叛,而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不管是“失节”,还是“守节”,实际上都是一种“驯化”的结果,前者被现代化所驯化,后者则是对知识原教旨主义的自觉遵从。不管是在前现代还是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似乎永远是一种“被驯化”的角色,被驯化去认同并符合社会的“承认”标准。因为前现代视野下的身份认同机制如幽灵一般规约着知识分子自我的认知与行动,也让他们不断陷入认知与现实的矛盾与分裂处境。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所感受到的矛盾、纠结,都是在主动接受“失节”的审判:失节作为一种罪名,被自我指控,被社会指控,被读者指控……这种接受本质也是另一重自我的建构,然而,建构自我,并不是要做哪一个群体的“分子”,而是要建构自己的主体性,“问题不再是如何发现、发明、建构、拼凑一个认同,而是如何防止长期坚持一个认同——而且,要防止它紧紧地附着在身体之上…后现代生活策略的轴心不是使认同维持不变,而是避免固定的认同”[7]105。对于现代社会的专业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而言,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抵抗驯化,摆脱“承认的政治”这一身份认同陷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四、结语
阎真作品对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的关注,在写作策略上有其创新性,这类作品展现了一种极度写实的真实品格,无论是谁,都能在作品中窥见生活、人性的亲历面向。然而,结合人物所历经的处境并以全景视角观之时,似乎又会生发出“过犹不及”的非现实之感,作品中的人物及现实经历具有片面的典型性,不具备全面的典型性。同时,人物形象的下沉式发展以另辟蹊径的方式再现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形构了阎真笔下诸多经典的形象。然而,过度强调“现实”的下沉面向导致了主体性的疲软,这无疑是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