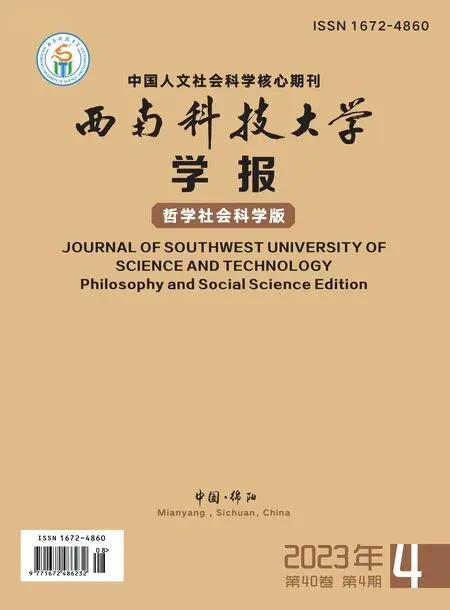蒂姆·英戈尔德的身本人类学路径与思想研究
赵 荣
(1.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2.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英国人类学同其催生者大不列颠帝国共同经历过辉煌,筑造起西方现代人类学理论范式和田野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大厦。然而,二战后,随着帝国的衰落和人类学阵营中心向美国转移,英国在西方人类学理论的主场地位被美国取代。由此,也造成了当代中国人类学在引介西方现代、后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学术思想、代表学者及其论著时,过度集中在美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从而遮蔽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人类学界的学术贡献。战后英国新一代人类学家既有古典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正统根基的出身,同时又深受德法国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对人类学理论的开拓更具有人文主义的浪漫关怀和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反思,经过几十年努力,逐渐形成了有别于美国人类学发展的特色路径:一方面对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新理论如何运用于实践,实现学科创新进行探索[1]65-69,并对社会结构与政治经济展开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承袭了英国人类学传统,继续巩固和扩大对全球范围内田野调查地区的占领[2]89-91。面对目前我国人类学理论视野狭窄,研究易陷入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窠臼,有必要将美国之外的欧洲人类学研究新趋势和新成果引介进来,而蒂姆·英戈尔德理应在其列。
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以下简称英戈尔德)是当代英国人类学学者代表之一①,他开拓了身本人类学的独特研究路径,打破了笛卡尔建构的身-心/人-物“二元论”,以“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将人类世界看作是有机体的人与非人互动同构的生态性居所,因此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应该转向探讨意识和行动在人与环境互动中的隐喻,关注实践中人的技能获得与行动者认知与能动性的具体化,从而打破“人类所为”与“物所是”以及艺术领域与技术领域之间的生硬划分——这些都对西方生态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在4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践行着推动英国人类学发展的目标,而且还剑走偏锋,脱离英国人类学传统主流之轨道,选择从生态到技术,再从技术到艺术的转换路径,怀揣着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内部界限的野心,力图整合科学、人类学、生态学、考古学、艺术、语言和考古,以重新看待人与世界、人与自然,进而思考自然、社会、文化、知识、经验与艺术之间关系。
一、蒂姆·英戈尔德的人类学研究路径演化
蒂姆·英戈尔德出生于1948 年,本科就读于剑桥大学生物学专业后转入社会人类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76 年),这样的学习经历为他以后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限,对人与自然、人性与动物性、生活世界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英戈尔德的学术生涯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次路径转换:
第一阶段(1975-1986 年),以“环境与技术”“环境与经济”作为研究主题,主要从事北方极地民族的生态人类学和新进化论研究,先后出版著作《今日之斯科特拉普人》(The Skolt Lapps Today)(1976)和《猎人,牧民和牧场主:驯鹿经济及其转型》(1980)。对极地驯鹿养殖和狩猎的研究使得英戈尔德的研究关注点逐渐扩大到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人性与动物性边界概念化,以及狩猎采集者与牧民社会的比较人类学等方面,其中以《进化与社会生活》(1986)为代表,采用了从十九世纪末期延续到现在的人类学,生物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进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
第二阶段(1990-1999 年),其研究重心转向“文化、感知与认知”。英戈尔德对工具制作和言说作为人类独特性标准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对人类进化过程中语言和技术之间的联系产生了浓厚兴趣②。同时,他也试图在人类学领域内寻找合适的方法将技术和艺术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了他以技术实践为核心的研究路径,并逐渐完成了由生态人类学向技术实践研究范式的转换。在这一阶段,由于受到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关于知觉系统的研究影响,英戈尔德也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将生态学方法融入到人类学和心理学之中,并可以如艺术般充满感知的魅惑与实验性的对话。
第三阶段(1990 年至今),以转战阿伯丁大学为分水岭,英戈尔德的研究路径最终从科学技术转向了艺术人类学。在涉足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过程中,他尝试将环境认知和技能实践的主题联系起来,并试图以新达尔文生物学和认知科学联盟取代遗传和文化传播的传统模式,以关系方法为重点,讨论在人类发展的社会和环境背景下的感知和行动,考察了文化中使用的“线条”,以及人类学,建筑学,艺术和设计之间的关系③。同时,受现象学哲学思想的浸润,他也有意识地采用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现象学理论对社会和环境发展背景下的具身性技能的感知、知觉和行动进行反笛卡尔二元论的反思性探讨。
二、蒂姆·英戈尔德的人类学研究关键词:身体化、制作、技能、栖居
英戈尔德怀抱整合人类学、考古、艺术和建筑四学科的雄心,将多年教学和研究积累的经验、知识与成果诉诸笔端,完成了《制作:人类学、考古学、艺术与建筑》(Making:Anthropology,Archaeology,ArtandArchitecture,2013)一书④。英戈尔德从史前石器制作到中世纪大教堂建造,从圆垛到纪念碑,从风筝到编织,从绘画到写作——对一系列人工制作、教学实验和生活范例进行跨“4A”学科的分析,“试图揭示围绕运动哲学对物体内在的物质性进行评价的潜在悖论”[3]。我们可以用身体化、制作、技能和栖居这四个关键词来总结在此书中形成的身本人类学研究思想。
首先,他以反思人类学研究范式作为全书的“立眼”,重新反思人类学、民族志与参与观察民族志三者关系,通过对“制作”的意义、材料、形式、景观感知、生命生活、个人知识以及手工等进行“身体化方法论”的阐释,提出了身体化范式,以反对将经验和意义的文本简化为民族志写作的传统。身体化研究路径强调关注田野中的切身体验,以实践(practice)和表现(performance)为基础,用“对参与的观察”方法取代传统的“参与观察”,进而扩展民族志境遇的经验性理解。
在身体化研究范式基础上,英戈尔德以“生活的材料”为对象,从图像到物体,再从物体到物体,研究视角进行不断转换,以探讨“制作”(Making)作为生长的动态过程。他认为,人并非由身、心、文化同构互补的复合实体,而是一个在持续展开的领域内不断与物产生链接、创造关系而生成的“此在”。因此,人作为有机体的感官意识所生成的图像是在人-物、身-心的流动中生成、变化、再生成的。例如,古代雕塑作为人造物,设计其稳定性不在于静置于展厅内,由人被动地观赏,而在于当人驻足在此,其大理石的固态质料被不同时间维度的制作者以“奔跑中的身体”的形式呈现给当下的观者,这种质料的流动又在观者的感官意识作用下与雕像制作者、雕像、大理石共同形成图像与生命的此在意义。同样,英戈尔德在分析手斧制作、房屋建造仍以时间和历史进程为维度,讨论了质料与形式之间的关系,物质的固体形态可以通过形式产生时间维度上的生命生长状态,质料的流动在观者感官意识作用下形成图像与物的共同生长、变化,这种关系会在不同的历史空间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现。由此可见,法国现象学的哲学思想之光对英戈尔德在探讨艺术本质和文化本质的思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受感知生态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关于“人类如何感知周遭环境”理论的影响,英戈尔德提出了“互补性观点”(Complementarity thesis)[4]2-3,将人类看作是一种进化有机体与依赖社会的文化意识能动性的综合体,人类既是生态系统中的有机体,同时也是社会关系中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以此来弥合人类学在生物物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巨大裂隙。作为有机体的人类,其生活、生产与再生产不仅依赖于其他有机体的联系和互动,也依赖环境中那些非生物存在以及与其产生的关系和互动——这是英戈尔德认知中的人类生活方式,这种生活被具象化为技能的获得与使用。这里的技能(skills)突破了身体技术(techniques)的身-心二元对立限制,英戈尔德将其定义为一种整个有机生物在环境中的系统化行动与感知能力,即技能既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因此,在生活实践过程中获得并使用的技能是人类有机体在特定环境中与各种存在要素互动并经过训练,累积经验而获得一种此在的有机体运作方式。也就是说,技能的获得是环境中的行动者感知、认知与反应能力的具身化过程。
在谈及技能的学习时,英戈尔德提出了“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概念⑤。很显然,这一概念采借自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诗意”被海德格尔表述为创造,人存在的首要条件是择世界一隅而栖居,当人敞开自身,与周围的事物因有用性而遭遇时,人与物共同营造出一种合适的状态,此时人的能量影响周围的事物从而使它们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这就是一种诗意化的创造。而梅洛-庞蒂将人作为在世之存(being-in-the-world)的感知能动者,身体是感知的工具,创造是人具身化存在的方式。在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影响下,英戈尔德“栖居视角”下的人类是环境中的能动者,有机体(人类或生物)作为一个整体在所处环境中与环境进行功能性的、持续的活动,有机体能动者在感知、制作的实践中与环境建立联系、调适身体相应部位与环境相适应并积累经验、掌握技术从而获得技能。就这样,有机体能动者与其所栖居的环境相互渗透、形塑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三、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突破——身本人类学
(二)英戈尔德眼中的人类学、民族志与参与观察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学科标志,与人类学理论和学术专业相依相伴。格尔茨提倡从民族志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做民族志[5]5-6。但是,英戈尔德却对民族志研究的传统范式和权威提出了质疑并指出,民族志实践所留下的无名、不被承认的东西已经贬低了应有的价值,所以说,民族志记录与转换之间的区别等同于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区别,不以周密、细致的观察为基础的感受和思考是无法完成真正转换的。英戈尔德反对这样一种自负,即事物可以与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世界隔离开来并理论化,并且这种理论化的结果提供了假说,而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假说去理解事物[6]4。为了抵制这种自负,英戈尔德提出民族志的参与观察应该成为一种“探究的艺术”(The art of inquiry),他认为,思想的行为伴随着我们工作材料的流动而流动,并持续地做出反应。当我们通过它们思考时,这些材料就在我们的思考中。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思考这种实践行为不是为了描述世界,也不是为了表达它,而是为了展现我们对此处/彼处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它做出回应。也就是说,民族志作为一种探究式艺术就是要建立起与世界的密切活动的关系[6]6-7。
英戈尔德对“探究的艺术”这一新的参与观察法做了进一步解释,在实践中理解和探索感知、创造力、技能相互间的关系。他在4A 课程的教学中将这种研究方法做了实践运用:根据他对课程设定的目标⑥,采用了讲座、实践、项目开发、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组合,在为期10 周的教学时间里,用实践活动取代课本学习,在每次会议上,学生要讨论本周讲座中产生的问题以及随后的阅读材料,同时进行具体的实践练习,以将这些问题置于体验环境中;除了参加讲座和实践活动外,还要求学生亲自开展一个项目,通常学生会被要求选择一个建筑物、桥梁、长凳、古代纪念碑、公共雕塑或地标等实体,每周花费大约一小时对项目对象进行细致观察并做详细记录,还必须画出所观察或发现的内容,并反思他们的绘图如何影响他们的观察结果,最后,他们必须从现成的原材料中制造出一个模型,而且模型要制作成可以被讲解的形式,同时还要考虑事物与模型之间在形式、规模和材料方面的差异。课程结束时,学生在这门课程中所形成的笔记、图纸、模型、辅助文件等被汇编成档案,以供评估。
(二)身本人类学范式
对人类学、民族志和参与观察反思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路径,然后在教学实践中加以运用——这是英戈尔德的人类学研究范式新突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身本人类学”范式。
自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欧美一些人类学者尝试将身体作为核心范式进行民族志研究。不过,首先要明确的是,身本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the body)不等同于身体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body)⑦,它不仅仅是对身体的社会文化做研究。事实上,身本人类学借鉴了后现代理论,试图要把身体从笛卡尔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恢复它的完整性,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象征性和政治性。因而,可以说身本人类学是对身体人类学理论的补充和整合。从英戈尔德对身本人类学范式的论述来看,实际上是将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吉布森的反认知主义和发展生物学对新达尔文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范式,正如马力罗对其评价:“他的身体理论努力将社会、文化人类学与体质、生物人类学结合,试图超越那些‘补充性理论’。这些理论声称要弥合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断裂,最终却还是将‘作为生物机体’的人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立起来,因此,它们实际上是在重造身、心和文化间的区别。”[7]136
在英戈尔德的眼中,人是身与心紧密结合的完整有机体,思维(mind)同样是有机体,“身体化过程与有机体在环境中的生长过程如出一辙”[4]168,它积极地参与到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并深嵌入周遭环境中。因此,他提出有机体式的理解方式是用“生命”代替“思维”,用“有机体”代替“身体”,用“有生命的有机体”代替“思维性身体”(mindful body),而这种替换不仅克服了笛卡尔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他把“人”放进了有机生命的序列中,“肉体性存在是建立在身体积极性基础上的意向性在场,身体的姿势和动作展示出理解和行为之间的相互联系:理解是个体行为的直接功能,它是先于一切‘象征——再现’中间机制的意义性行为”[7]137。因此,意义既不是阐释的产物,也不是思维赋于客体的事物,相反它内在于有机体的实际活动中,内在于由具体实践所生成的关系场景中,故身体不只是感觉之源,不只是社会和文化的被动载体,而是文化的“主体”,是文化存在的根基。因此,身本人类学强调的民族志方法是以身体为中心的身体学习法,而调查者的身体就是其使用的研究工具,它制造出通过技能学习而获得的身体性知识,训练形式包括感觉、理解、实践以及与他人的交际互动。
四、制作、感知与生长:英戈尔德理论的现象学基底
英戈尔德毫不掩饰地承认其借用胡塞尔、海德尔格和梅洛-庞蒂的理论来论证和阐述自己对于建筑、手工艺品、生活器具、环境的“现象论”观点。《能动性与生命力》(Ingold on Making-Agency and Animacy)一文就指出,英戈尔德《制作》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显著优势在于“现象论”与田野工作紧密结合,并用了一个形象生动“肖像描写”作说明:“即使他正在重建干石墙或弯腰考古挖掘,也总是揣有一卷海德格尔或德勒兹的书卷。”[3]无独有偶,努森(Knudsen)也同样明确地指出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对英戈尔德“栖居本体论”所产生的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8]181-201。国内研究者也提出类似观点,认为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对扭转笛卡尔传统下理性主义本体论的逻辑顺序的努力对于英戈尔德形成“栖居视角”奠定了哲学思想的基础[9]55-56。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拒绝传统知识的再现论,他们相信,有关外部世界存在的传统怀疑论的考虑中之真实哲学问题,并不需要去发现合理的基础以证明我们对此世界的信念,而是需要说明此种考虑是如何发生的。对胡塞尔来说,其中心观点是:“意识是一切经验的条件,它甚至以关键的方式构成着世界,而意识本身的作用是隐晦的,不容易被分离及描述。胡塞尔因此不断追求着如何克服阻碍认知纯粹意识领域的偏见,并对其说明,这导致了一个新哲学开端的出现。”[10]74海德格尔虽然师承胡塞尔,但他最终在现象学研究道路上与老师渐行渐远。在哲学研究进入第二阶段的过渡期间,他开始对艺术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其代表作《艺术作品的起源》探讨了“作为揭示真理的艺术”,海德格尔的研究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从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主体与偶性的关系研究方法论的分析,到对笛卡尔二元论的批判,再到借鉴康德美学对形式的评判,强调着艺术作品的本体论特性,然后发展到用新康德派的关于感性把握事物的概念,结合以主体性的先验客观化结构来对事物的性质进行彻底地反思。海德格尔认为,关于“以形式-质料关系来思考事物”的本体论产生于人对工具的熟悉性,但是工具本身的性质不是通过工具而是通过艺术品显示的,因而,真正的艺术为世界提供了根基[10]237。
笛卡尔关于心智和躯体相分离的主张妨碍了我们对认知过程的理解,因此一旦我们突破这种二元对立,就能实现从“常识”到“意识”的感知扩展过程。在《制作》一书中,英戈尔德在讨论自然物与人工建筑物,物性与艺术性的时候就引用了海德格尔关于物品的讨论。此外,英戈尔德在分析手工绘画与线条的形式、生存与流动时,还引用了梅洛-庞蒂的理论:绘制任何东西的秘密是发现特定方式——其中一个特定的折线,其生成的轴,以及通过它所形成的整个范围,这样的一条线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实际上,它总是在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之间或之后[6]135。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研究为身体性存在的原初体验进行了一种彻底性的描述,是继胡塞尔现象学之后做出的最具独创性和持久性的贡献。梅洛-庞蒂特别推崇胡塞尔在《危机》中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以及在《经验与判断》所形成的“前述谓的认知”概念。他反对作为自发的、首先是认知性行为的意向性概念,而强调将其看作世界和生命间自然的、前述谓的统一体。我们身体的意向已经在我们从概念上对其认知之前就引导我们进入一个为我们而构成的世界之中[10]456。这里要明确的是,梅洛-庞蒂提出的“现象学的根源”,其目的在于教导我们如何以新的方式观察自己的经验。对正常人来说,我们的感官经验和运动世界之关系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似乎具有一“潜在的身体”或现象的身体,而此“潜在的身体”关联着一个“潜在的空间”,身在其中,人可以于实际运动之前探索如何运动。举个例子,当我们看见一个苹果时,苹果已经在我们身体内动员了某种运动的潜能告知我们如何伸手去抓取、拿起。因此,当我们实际去拿这个苹果时,正是我们的“现象的身体”而不是“客观的身体”运动着。
五、蒂姆·英戈尔德学术思想的缺陷与不足
英戈尔德关于手工品、建筑、工具等如何制作的研究说明了人如何通过制作对艺术、文化、世界和意义进行思考并促使我们认真反思人类学家与世界相对应的需要。同时,他也试图通过对人类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为当下人类学面临的表述危机和民族志研究困境提供可探索的新路径。但是,我们仍需要辩证地来看待英戈尔德学术思想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首先,尽管英戈尔德希望通过弥合学科间的分裂以消除笛卡尔二元认识论所带来的自然与文化、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等的二元对立,但在学术思想继承上,他更倾向于借用梅洛-庞蒂对主/客二元对立的批判,却较少提及布迪厄在处理实践论时产生的“结构/实践”对立。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对身体实践进行分析时,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与场域理论是不可缺席的,但英戈尔德在分析中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对布迪厄理论的讨论。
其次,在对身本人类学范式的探索中,虽然身本人类学重新定义了民族志主体和调查实践,但是由于过度强调对民族志境遇的经验性理解从而淡化了对民族志学术话语权威建构的关注,而且对经验性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复杂的社会性。
另外,虽然英戈尔德的身本人类学范式强调参与观察的身体实践,但是他却轻视民族志写作。在谈及如何把田野实践撰写成文本这一问题时,英戈尔德似乎刻意回避,表示他不参与有关写作的讨论,因为这种讨论对学科的进步毫无意义。然而,无法否认的是,田野研究是人类学学科得以存在的基石,民族志是人类学田野实践的产物,同时也以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身份存在。所以民族志应被视作不同性质的主体在对话、合作中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实践[11]7。我们应当将民族志视作一种更高层次的对话体系,借助其所具有的理论和分析这一基础特性来理解人类如何生活。
注释
① 英戈尔德先后在赫尔辛基大学(1973-1974 年)、曼彻斯特大学(1975-1999 年)、阿伯丁大学(从1999 年至今)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他的研究理论成果获得了英国学术界的极高认同:1990 年英戈尔德被任命为曼彻斯特大学主席;并于1995 年成为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社会人类学教授;1990 年至1992 年期间担任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学术期刊《人类》(Man,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的编辑,还负责了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人类学百科全书》(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1994)的编辑工作;1997 年获得英国科学院学术奖金,并于1999年担任英国科学促进会人类学和考古部的主席。2000年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员。
② 1990 年,他与凯瑟琳.吉布森(Kathleen Gibson)共同组织了相关主题的国际会议并编辑了会议的论文集《人类进化中的工具、语言和认知》(Tools,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human evolution)(1993)。
③ 以这一研究路径为基础,在《环境的感知》(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2000)一书中,英戈尔德收录了此前近10 年的以生计、定居和技能为主题共计23篇论文,对这些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讨论。
④ 英戈尔德曾前面向高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命名为4A 的课程,即对人类学(Anthropology)、考古学(Archaeology)、艺术(Art)和建筑(Architecture)提出的思考,通过讲座、实践、项目工作、研讨会等多种形式进行,讲座主题包括“设计和制作、材料、物体和事物、姿态和表现、工艺和技巧、感知中的感官、线、画画、符号”。
⑤ 英戈尔德称,技能的学习要求一种称其为“栖居”的视角,即从一开始就将实践者置于和他/她的环境积极互动的情境中。
⑥ 该课程目标被设计为“是培养学生探究的艺术,增强观察力,并鼓励他们通过观察而不是后面的观察。像猎人一样,他们必须学会学习,跟随生物和事物的运动,并且反过来以判断和精确的方式回应他们”(参见Ingold,T.2013.Making: Anthropology,Archaeology,Artandarchitecture.Routledge,pp.12-13)。
⑦ 身体人类学有其深刻的人类学传统,它把身体从自然和生物领域解放出来,让身体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得到关注。但身体人类学只是把身体当成社会文化的被动接收器,仍用客观主义态度对待身体,它不过是人的物质基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