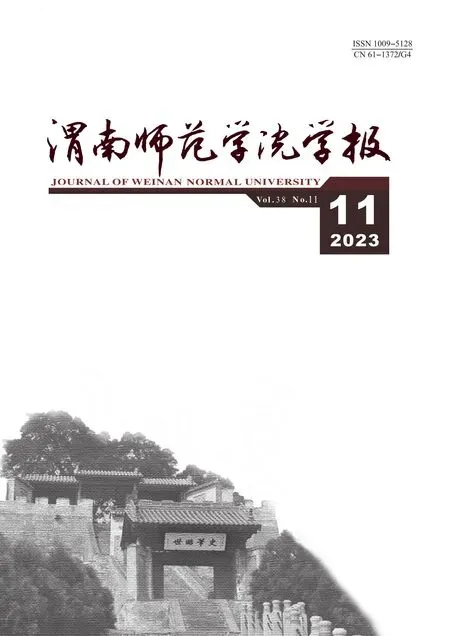论文词派与明传奇的文人化
艾 钊
(山东大学文学院,济南 250100)
文词派是明嘉靖朝及万历前期盛极一时的传奇流派,不过到了万历后期,受到了各方面的尖锐批评,最终走向了衰落。从戏剧史的角度看,文词派的出现、兴盛与衰亡,是明代剧坛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关于文词派的发展历程、特征和影响,郭英德先生《明清传奇史》一书论曰:
文词派(也称骈绮派),是传奇生长期的主要流派。它滥觞于邵灿(成化、弘治间人),开派于郑若庸,李开先、梁辰鱼等推波助澜,至梅鼎祚、屠隆而登峰造极。文词派以涂金缋碧为能事,以词藻堆垛为嗜好,将文人才情外化为斑斓文采,这固然加强了传奇剧本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但却违背了戏曲艺术“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的文学特性,削弱了传奇剧本的可演性和戏剧性,使传奇沦为案头珍玩。从此以后,传奇的艺术风格一直受文词派的影响而不可自拔,典雅绮丽成为传奇作品的主导风格。[1]18
郭英德先生将从明成化初年(1465)至万历十四年(1586)这122 年称为“传奇生长期”。把文词派视为该时期的主要流派,指出此后传奇艺术风格深受文词派的影响,都足以表明文词派在传奇发展史中的重要程度,而对文词派的批评,显然受明后期曲论家观点的影响颇深。目前对文词派的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厘清,有些甚至与历史真相南辕北辙。如王世贞在文词派发展壮大中所起的作用被夸大,而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吴中文学传统却被忽视了;后起曲论家对文词派的批评意见遮天蔽日,而文词派自身的理论主张却湮没无闻;文词派的主要受众是文人士大夫,然而却以市民本位的戏曲观来非议文词派传奇。本文的重点即是探讨文词派出现、兴盛的原因,并还原文词派在明传奇文人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文词派产生及兴盛的原因
文词派主要作家包括郑若庸、梁辰鱼、张凤翼、屠隆、梅鼎祚等人,吕天成、汤显祖、沈璟等人早期的传奇创作也有浓厚的文词派色彩。文词派的产生和盛行,自有其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概括言之,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与社会风尚的变化
明代政局自正统朝以后日趋腐朽,深刻的社会危机促成了思想文化的变革。成化以后,程朱理学的桎梏开始松动,学者们逐渐摆脱理学的束缚,自抒胸臆成为新的潮流。正德年间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和传播,更是动摇了理学的根基,思想学术的多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之洪流。思想解放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人们更重视个人的适意,这无疑为文人投入戏曲的创作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
另外,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明代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商业呈现繁荣的景象。成化以后,社会上开始出现追求享受、奢靡之风。明前期的“民俗勤俭,不竞浮华”一去不返,“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风尚日趋流行。世风的变化波及士林,士大夫也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娱乐。他们蓄养家乐声伎,以此为乐,更有甚者亲自登场,串演戏剧。
在思想解放和浮华世风的双重作用下,风流自赏成为当时文人的一大共同心理。纵观文词派主要作家的生平与阅历,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有过一段风流经历。如《玉玦记》的创作与作者出入妓院的经历有关。《浣纱记》的作者梁辰鱼少时不屑就诸生试,任侠豪纵,好冶游,常与诸名士出入青楼酒肆。屠隆更是浪荡不羁,放纵情欲。可以说,没有风流文人,也就没有典雅工丽的文词派传奇。
(二)吴中崇尚靡丽的文学传统
文词派有时又被称为“吴音派”,如凌蒙初《谭曲杂札》云:
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然。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崇尚华靡。弇州公以维桑之谊,盛为吹嘘,且其实于此道不深,以为词如是观止矣,而不知其非当行也。以故吴音一派,竞为剿袭。靡词如绣阁罗帷、铜壶银箭、黄莺紫燕、浪蝶狂蜂之类,启口即是,千篇一律。甚者使僻事,绘隐语,词须累诠,意如商谜,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余,即人间一种真情话,埋没不露已。[2]第3 集188
凌氏将步武梁辰鱼工丽曲风的文词派作家称为“吴音派”,概括了他们用靡词、使僻事、绘隐语的创作手法,并指出了其抹尽本色语、埋没真情话的弊端。这表明凌蒙初已经意识到,文词派与吴中特殊的地域文化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比凌蒙初更早的王世贞在列举“吴中以南曲名者”时,共提及祝枝山、唐寅、郑若庸、陆氏兄弟(陆粲、陆采)、张凤翼、梁辰鱼、陆之裘等八人,其中祝枝山以“大套”、唐寅以“小词”、陆之裘以“散词”出名,剩下五人均以传奇出名,而这五人又恰好都是文词派作家。文词派作家以吴人为主,这不是偶然的。在明代戏曲批评史上,李贽首先引入“关目”的概念,对戏曲结构和情节给予了关注。又经过王骥德等曲家的努力,戏曲的结构才受到应有的重视,戏曲的中心才开始由“曲”向“戏”转移。而在这之前,传奇作者和评论者都倾向于以诗文的思维方式来创作和评鉴戏曲。因此,同时代、同地域的诗文风尚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传奇的创作。文词派传奇的典雅工丽,实际上正是受到吴中诗文传统的影响。
以吴中为中心的苏杭地区,向来有重文的传统。差不多与前七子复古思潮同时,一股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潮在吴中出现。王世贞提到的南曲名家中,唐寅、祝枝山、陆粲都是这一股思潮的提倡者。由于商业的繁荣,士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趣味也随之受到影响,对政治的热情降温,转而更注重追求高雅、闲适,融入市民生活。这一思潮从成化后期一直延续到了嘉靖中期,前后约70 年。[3]346而文词派产生、发展的时间,也与此大致相当。
吴中的诗文传统,在主流文学史中常常是被批判的。如王世贞在给王文禄的书信中,就对吴中的文风加以指摘:
国初诸公承元习,一变也,其才雄,其学博,其失冗而易。东里再变之,稍有则矣,旨则浅,质则薄。献吉三变之,复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厌。勉之诸公四变而六朝,其情辞丽矣,其失靡而浮。晋江诸公又变之,为欧曾,近实矣,其失衍而卑。……六朝之华,昌谷示委,勉之泛澜,如是而已。[4]卷一百二十七在这封书信里,王世贞指出江南的靡丽文风由徐祯卿开启,黄省曾扬其波澜,而徐祯卿和黄省曾又都是吴县(今苏州)人。
王世贞对吴中崇尚六朝的诗风也极为不满。他认为吴中诸能诗者,“雅好靡丽,争傅色”,其高者“剽齐、梁”,而下者“不免长庆以后”。[4]卷六十六在《李氏山藏集序》中,王世贞又说道:
某吴人也,少尝从吴中人论诗,既而厌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闾而望欢者,自视宁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奈乎客之浣其质而睨之也。[4]卷六十四
南威是楚国人,夷光指西施,二人均是古代美人。“巧倩妖睇,倚闾而望欢者”不知其丑态,自视甚高,欲与南威、西施比美。如此辛辣的嘲讽,足见王世贞对江南靡丽诗风的反感。
王世贞是吴中人,他对吴中诗文风气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深刻的。从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的诗风、文风以靡丽为尚,其长处在于“情辞丽”,其弊端在于“靡而浮”。这不也正是文词派的特点之一吗?因此,吴中重视独抒情怀的文学传统和雅好靡丽的文学风尚,对文词派产生和走向兴盛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既然王世贞领导的诗文复古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江南的靡丽文风与诗风,那么王世贞“盛为吹嘘”风格绮丽的文词派传奇,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呢?事实上,长期以来,王世贞以及复古运动对文词派兴盛所起的作用都被夸大了。
王世贞论曲,主才情。才情不是简单地堆砌学问,而是要在曲中表达作者的才华和情趣。王世贞认为,《琵琶记》所以“冠绝诸剧”,不仅仅是因为“琢句之工,使事之美”,更在于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2]第1 集518恐怕后者才是王世贞心中的“词家大学问”。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恰恰是文词派堆砌学问的反面。
文词派雄踞嘉靖剧坛,王世贞在谈曲时提及文词派作品是很正常的事,不能因此就给他扣上“盛为吹嘘”的帽子。相反,王世贞对文词派作品颇多微词。如批评文词派滥觞之作《香囊记》“近雅而不动人”[2]第1 集519。再来看王世贞对文词派作品的评论:
吾吴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郑山人若庸。……郑所作《玉玦记》最佳,他未称是。《明珠记》即《无双传》,陆天池采所成者,乃兄浚明给事助之,亦未尽善。张伯起《红拂记》洁而俊,失在轻弱。梁伯龙《吴越春秋》满而妥,间流冗长。[2]第1 集523
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说“《玉玦记》最佳”,只是说在郑若庸的数种传奇中,《玉玦记》最好,而其他作品并不好。退一步讲,王世贞比较的范围仅限于吴中,《玉玦记》也确实能当得起这个“最佳”之称。同时,王世贞也指出了文词派其他作品的缺陷,远远谈不上“盛为吹嘘”。
文词派绮丽的审美倾向直接受到吴中靡丽文风和诗风的影响,而对骈四俪六、体用排偶的形式追求则是受到八股文的影响。这一点其他学者已有考察,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八股文对文词派传奇的影响,除了体用排偶之外,还在于程朱理学对文词派的思想旨趣的规定,甚至认为文词派传奇就是八股文在戏曲领域的变奏。诚然,八股文对《香囊记》的影响巨大,文词派传奇也有浓厚的时文气。然而,从滥觞之作《香囊记》到立派之作《玉玦记》,理学的桎梏是在日渐松动的。并且文词派传奇的内涵,也远非理学所能够概括,因此,八股文对文词派的影响,恐怕主要还是形式方面的骈四俪六。
(三)文人士大夫的观剧需求
传奇的受众问题,也一直是明清传奇史上的一个论争点。受众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往往反作用于剧作者,从而间接影响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传奇由民间南戏演变而来,民间南戏的受众是社会底层的“畸农”“市女”,文人染指南戏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明代批判文词派传奇者,一般都认为传奇的受众应该是底层民众。如徐复祚《曲论》云:
传奇之体,要在使田畯红女闻之趯然喜,悚然惧;若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何异对驴而弹琴乎?[2]第2 集259
这一问题到了清代的李渔才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其《闲情偶寄》云:“戏文作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女及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5]第3 册20
文词派作家虽然没有明确地论述传奇的受众问题,但从其受到的批判和创作实践来看,他们在作传奇时预设的受众应该就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文词派盛行时期,文人传奇的主要服务对象正是士大夫阶层。
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文词派受到后起曲家的批判是因为案头化倾向严重,不适宜舞台上出演。实际情况是,文词派的许多作品演出效果很好。如《红拂记》出,“演习之者遍国中”[2]第3 集65,“梨园子弟皆歌之”[6]丁集卷八;《浣纱记》成,长期盛演;吕天成也说《玉玦记》“可咏可歌”[2]第3 集125。那么观赏这些演出的人是谁呢?正是文人士大夫。
成化之后,士林风气发生了变化,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娱乐成为时尚。杨慎《词品》云:“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2]第1 集254正是对这一风尚的反映。士大夫豢养家乐声伎,平时自娱,宴时娱客,如李开先家中就有“戏子几二三十人”[2]第1 集461。
文人士大夫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对于各种典故了如指掌,曲词中的典故并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加上他们本身也对雕琢词句有浓厚兴趣,整齐对称的形式也是自身所熟悉的,因而文人士大夫成为文词派传奇的忠实拥趸,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除了观赏演出,士大夫阶层还将传奇作品当作案头之书来阅读。因此,他们更容易跳过演员的动作和语言,直接欣赏传奇的文本。这也是文词派传奇容易在士林获取成功的一大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阅读式观剧贯穿整个明清传奇。晚明戏曲家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自序》称,其选剧标准就是“可演之台上,亦可置之案头,赏观者以其作《文选》诸书读可矣”[2]第3 集467。
嘉靖后期,市民阶层日益壮大,文化需求随之日益增长。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平和品位基本上介于白丁和文人之间,他们既不满足于民间南戏的鄙俚浅俗,也不习惯于文人传奇的典雅工丽,因此雅俗共赏的戏曲语言成为时代的新宠。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也造成士大夫审美趣味的世俗化,文词派传奇存在的根基被彻底动摇。文词派成为众矢之的,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衰落。
综上所述,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和社会风尚的趋向奢华是文词派传奇出现与盛行的重要原因,吴中崇尚靡丽的文学传统直接催生了文词派传奇的绮丽风格,而文人士大夫是文词派传奇的主要受众,他们的观剧需求推动着文词派的盛行。
二、文词派与明代戏曲的文人化
那么,文词派在明代传奇的整体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基于对文词派的以上认识,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察。
(一)南戏的文人化过程
明清传奇由南戏演化而来,以南戏为参照点,传奇的形成过程就是南戏不断文人化的过程。
南戏文人化的第一步,是高明完成了《琵琶记》。徐渭《南词叙录》云:
(南戏)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顺帝朝忽又亲南而疏北,作者猬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2]第1 集482
《琵琶记》的完成标志着文人开始与南戏这一民间戏曲建立了血缘关系。然而,从明朝开国至成化年间,剧坛相对沉寂。不过在改编旧戏文的过程中,文人们确立了明确的戏文体制规范,为下一阶段的戏曲创作提供了条件。
南戏文人化的第二步是由“伍伦派”(或称“教化派”)完成的。“伍伦派”以《伍伦全备忠孝记》《香囊记》为代表,其创作目的就是宣扬程朱理学。这种功利性在剧本中就有明显体现。如《香囊记》第一出《家门》宣称“为臣死忠,为臣死孝,死又何妨”[7]香囊记。《伍伦全备忠孝记》之《副末开场》云:
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作《伍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为弟的看了敬其兄,为兄的看了友其弟,为夫妇的看了相和顺,为朋友的看了相敬信,为继母的看了不虐前子,为徒弟的看了必念其师,妻妾看了不相嫉妒,奴婢看了不相忌害。[8]
“伍伦派”的作品在构思方式上都是对理学观念的图解,谈不上有多少艺术价值。其贡献在于,将正统文化与民间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并且在士大夫以留心词曲为耻的高压环境下,创作戏曲,对文人投入戏曲创作有着带动作用。
南戏文人化的第三步,就是文词派的形成。“伍伦派”的作家多是板正的学究,而文词派的作家多是富有才情的风流文士。因此不同于“伍伦派”的宣扬教化,文词派的创作更多地渗透进了作者的个人精神与情感。举例来说,郑若庸的《玉玦记》旨在批评妓女负心,警戒浮浪子弟,表彰贞节,而该剧创作的动机与作者出入妓院的亲身经历有关。张凤翼的《红拂记》作于新婚之时,暗寓了新婚的欢乐,剧中李靖的英雄豪迈,也是作者豪情壮志的寄托。梁辰鱼的《浣纱记》既有功名失意的愤懑,又有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和思考,思想意蕴十分丰富。通过这些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文词派作家们已经开始将戏曲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在戏曲作品中寄托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如此一来,戏曲语言向抒情言志的诗文借径也就顺理成章了。
文词派对南戏文人化的另一个贡献则在于曲律。传奇作为一种戏曲艺术,“曲”是其灵魂所系。高明的《琵琶记》“也不寻宫数调”,《伍伦全备忠孝记》“白多唱少”,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对曲律的不甚在行。文词派肇兴,在规范剧本体制、雅化语言风格之外,还致力于钻研曲律,以显才情。郑若庸与梁辰鱼在文词派的中坚地位,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在曲律方面的成就相关。
郑若庸的《玉玦记》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词派传奇作品,也是确立文词派剧坛地位之作。《玉玦记》受到了学士的激赏,后起文人争相效仿,蔚然成风。《玉玦记》的成功,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严守曲律。王骥德《曲律》卷二《论韵》云:“南曲自《玉块记》出,而宫调之饬,与押韵之严,始为反正之祖。迩词隐大扬其澜,世之赴的以趋者比比矣。”[2]第2 集69“词隐”指的是沈璟,王骥德这番评论,就等于将“吴江派”对音律声腔的重视溯源至郑若庸的《玉玦记》,更能反观文词派在曲律方面的努力。
梁辰鱼在曲律方面的成就更为明显,其《浣纱记》将舒缓绵邈、格律严整的昆曲新腔,配以典雅工丽的曲词,风行海内,梁辰鱼也因此蜚声曲坛,为一时词家所宗。《浣纱记》的成功带动了昆腔新声的风行,使传奇创作出现了竞奏雅音的局面,对文词派的壮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词派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奠定了传奇戏曲语言的审美格调,标志着传奇与戏文的最后分界”[1]75,至此,南戏的文人化基本宣告完成,文人传奇成为剧坛的主角。
(二)光辉的文人形象
文词派以前的戏曲作品,也有以文人为主要角色的。但是那些作品中的文人都不是“文人眼中的文人”,而更多的是民间视角下的文人或者是理学家眼中的文人。而传奇作品以文人为主要角色,并浓墨重彩地渲染文人才士的学问与才情,实则始于文词派作家。因此,从文人形象的变迁管窥戏曲的文人化,可以说是一条捷径。
民间南戏中,文人多以反面形象出现。如《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蔡伯喈背亲弃妇,为暴雷震死;《王魁负桂英》中的王魁负心,被鬼魂索命。在这方面,张协可以说是反面中的典型:他在进京赶考途中遭逢强盗,钱财被抢,身受重伤,幸得贫女收留,悉心照顾,才捡回一条命。可是他非但不知恩图报,反倒对贫女动辄打骂。考中之后,贫女上门,被他棍棒赶出。更为丧尽天良的是,在赴任途中,他还亲手杀害救护过自己的贫女。如此禽兽行径,真是令人发指。
即使不是大奸大恶,民间南戏中的文人也沾染着市侩之气,毫无儒雅可言。《幽闺记》里的蒋世隆,在逃难途中遇到了王瑞兰,居然乘人之危,强迫瑞兰与其结为夫妇。如此行径,怎么能谈得上是君子所为呢?
再来看标志着文人与民间南戏建立血缘关系的《琵琶记》。虽然作者有意将蔡伯喈塑造为一个全忠全孝的完美文人形象,但剧中的蔡伯喈实质上是一个性格软弱、对自己命运不能做主的人。
“伍伦派”作品中的文人,虽然已经以正面形象出现,但是流于理念化,缺乏生气。《伍伦全备忠孝记》中的伍伦全、伍伦备毫无个性可言;《香囊记》中的张九成虽然也有在策论中慷慨陈词和身陷敌营不辱气节的不俗表现,然而也远远谈不上有血有肉。
到了文词派传奇,文人的形象才真正地高大和丰满起来。前文已经提到,文词派作家将戏曲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在戏曲作品中寄托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顺理成章的,他们将诸多美好的品质赋予剧中的文人角色,剧中的文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作家主体精神和情感的外化,因而大放异彩。
文词派传奇作品中的文人,大多是文才出众、相貌不凡的儒雅君子,懂得怜香惜玉,并且对待感情忠贞不贰。 除此之外,他们还胸怀天下,忧国忧民,入则为相,匡扶朝纲;出则为将,戡乱安民。比如《玉玦记》中的王商,才情出众,跻身翰林。过江慰劳三军,为敌所虏,他不畏威逼,忍辱偷生,后来手刃敌将,趁夜渡江回朝复命。虽然有误中烟花之计的瑕疵,然而能知己改过,两次升官之时,心里惦记的都是不能共享富贵的妻子。如此富文才、有胆识、重情义的饱学君子,与民间南戏中薄情寡义、阴险狠毒的斯文败类,人物形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正显示了戏曲的文人化。
应该说,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人形象,不仅是明代戏曲文人化的一个标志,也是文词派对明代戏曲史的一大贡献。在此之后,传奇中的文人形象逐渐失去了光辉,变得孱弱起来。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举止轻佻,热衷功名,胸中已无安邦济世之志。又如《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差点一时糊涂为阮大铖说好话,与李香君的深明大义比起来,显得多么黯然失色呀!
(三)文词派作家的理论自觉
在明代戏曲文人化的过程中,文词派作家无疑起到了主要的作用。那么,文词派作家对此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呢?这就要从他们的创作心态入手分析。
有别于教化派和职业剧作家,文词派创作传奇,不是单纯地为了宣扬教化或者牟利,而是有着抒发个人襟怀、展示个人才华的目的。如郑若庸在“英雄袖手,阻风云,困圭窦”的情形下,“闲将五色胸中线,杂组悬河辩口”[7]玉玦记。文词派的这种创作心态,在梁辰鱼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浣纱记》第一出《家门》云:
〔红林檎近〕佳客难重遇,胜游不再逢。夜月映台馆,春风叩帘栊。何暇谈名说利,漫自倚翠偎红。请看换羽移宫,兴废酒杯中。 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问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7]浣纱记
佳客如云,胜游堪夸,转眼已成往事,而自己仍然伏于枥下、困于樊笼,壮志难酬。梁氏创作《浣纱记》,正是为了寄托其人生的失意,不言自明。
与抒发个人襟怀、展示个人才华的创作心态相一致,文词派论曲尤重曲词之意趣。梁辰鱼批评李日华的《南西厢记》“蹈袭句字,割裂词理”,“毁西子之妆,令习倚门;碎荆山之玉,饰成花胜”[2]第1 集475,就是着眼于李日华在改编《西厢记》时增损字句来迁就南曲腔调,导致曲意的破碎支离。这一曲学主张在屠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总结。在《章台柳玉合记叙》中,屠隆批评了明代前期戏曲的两种不良倾向:
椎鄙小人,好作里音秽语,止以通俗取妍,闾巷悦之,雅士闻而欲呕。而后海内学士大夫则又剔取周秦、汉魏文赋中庄语,悉韵而为词,谱而为曲,谓之雅音。雅则雅矣,顾其语多痴笨,调非婉扬,靡中管弦,不谐宫羽,当筵发响,使人闷然索然,则安取雅?令丰硕颀长之媪施粉黛,被裲裆,而扬蛾转喉,勉为妖丽;夷光在侧,能无咍乎?故曰:非妙非宜,工无当也。[2]第1 集589-590
屠隆在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文词派作家所反对的,一是鄙俗的“里音秽语”,一是学士大夫“痴笨”而不谐曲律的“雅音”。才士之曲与民间戏曲,其区别在于雅俗,这一点很明白。而才士之曲与学究之曲相比,不仅工雅,更要“妙”,使人不索然闷然。而何谓“妙”?屠隆接着解释道:
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斯其至乎![2]第1 集590
在屠隆的时代,雅俗共赏的戏曲语言已成为主流追求,因此他论曲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雅俗的通融。但是在实际创作中,要做到“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是很不容易的,文词派优秀作家也只能做到“极才致则赏激名流”而已。因此,文词派作家事实上自觉追求的是文辞之美,以文辞呈现声、色、情、态,达到“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的妙境。
可以看出,文词派作家并非一味地卖弄学问,他们也是非常重视才情意趣的,只不过在实际创作中,没把握好分寸,以至于才情意趣常常被学问所掩盖。然而文词派重意趣、尚才情的追求影响深远,泽被后世曲家良多。比如汤显祖“意趣神色”之论,不正是文词派重意趣、尚才情的发扬光大吗?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文词派作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自觉,他们有意识地在传奇创作中渗入文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从而在根本上提高了传奇的文化品位。
三、结语
文词派在明传奇文人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文词派作家重意趣、尚才情的理论主张和重视曲律的创作倾向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汤显祖和沈璟早期的传奇作品都深受文词派影响,晚明剧坛的“汤沈之争”,既是明代戏曲文人化的继续深入,也是以不同方式扬弃文词派传统的结果。
文词派是明代文人传奇发展的重要一步。卖弄学问、争奇炫博的背后,是对才情和文采的追求,是文人阶层主体精神的日渐高扬。文词派作家客观上提高了明传奇的文化品位,自文词派开始,文人阶层的精英文化成为传奇的内在思想意蕴,文人阶层的文雅蕴藉成为传奇的主导审美趣味。正是在文词派传奇的基础上,文人传奇实现了新的飞跃,形成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足堪媲美元杂剧的第二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