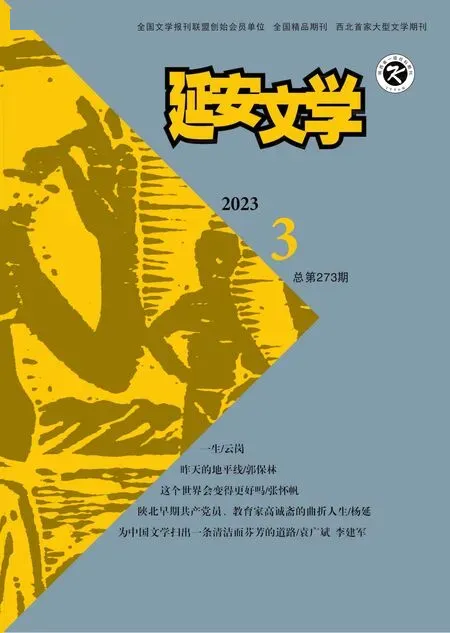中年期综合症
叶 灵
一次莫名眩晕的追根究底
许多人用尽全力,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我也不例外。
浓郁的艾灸气息,混杂着呼吸之间淡淡的草药味,久久弥漫在我的周围,以及屋子的每个角落。而我,不知从何时起,早已习惯了这被草木气息笼罩的空间。
走着走着,时光就成了加速度。大把大把的日子身不由己,在没有腰颈的沙漏中一泻而下。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内服中药,外用艾灸,看似双管齐下、内外兼治,实际上却如一支浩浩荡荡却目标不明的军队,在此虚张声势一番。于我,不过是安慰心头日益严重的疑虑而已。
这段日子,突如其来的眩晕总是不时惊扰着我。短短的十几秒,身体就失重般恍惚起来,意识暂游离于身体之外,眼前的世界奇幻般开始缓缓旋转——脚下的水泥地仿佛成了虚空的棉花垛,路边的梧桐树一股脑儿地朝西倾斜,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倏地一下子散开,飞向四面八方;一辆辆疾驰而过的电车,瞬间被拉扯成虚幻的五彩斑斓的条影……一切让人始料未及。然而,就在我强作镇定的瞬间,那莫名的眩晕又随即逃离得无影无踪,再也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以至于在医院我向医生一遍遍陈述症状时,总怀疑自己是否在心安理得地撒谎——不知是眼前的世界摇摇晃晃向我而来,还是我摇摇晃晃地向这个世界奔去。
就这样,每天如此反复。如迷一般。是身体发出执着而隐晦的预警?还是在伺机寻找喷涌的借口?逃避最终不是办法。
耳朵成了最大的嫌疑。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十几年前,两个耳膜因为疏忽都已穿孔,当时,只是手术了左耳,会不会是右耳因常年耽搁而成了美尔尼斯症?这个洋味十足的名字,是我从百度上得知的。为彻底查清真相,我自作主张地一夜又一夜地在网上乱查,越查心里愈是慌乱,赶紧连看了两家医院。
第一个耳科医生,是个年轻女孩。我详细描述了症状后,她只是例行公事般拿起耳窥镜看几秒后,用一种不太确定却又很肯定的语气说,眩晕不一定是耳朵的缘故,可能是颈椎的原因吧。太多的不确定与确定都让我惊悸不安。还是决定去另一家医院看看吧。
这是市里最大的医院。耳科医生是位中年妇女。谁知,还未等我把症状说完,她就很利落地拿起耳窥镜,然后,又果断地下了“权威”结论——说这不可能是耳朵的原因。
到此为止。不能再纠缠耳朵了。去看看颈椎吧。在原因没弄清楚之前,只有先一个个排除了,我想。
于是,挂号,排队,就诊。疼痛科。我不厌其烦地复述了一遍症状。颈椎医生双手提托着我的脑袋,前后左右地转来提去,“蹦蹦”的声响清晰地从喉腔传出。“是强直性颈椎。但头晕却与此无关,看会不会是脑血管的问题?”“脑血管”这三个字,瞬间又好像一只无形的魔爪紧紧攫住了我。
又于是,再挂号,排队,就诊。眩晕科。第一次知道医院还有这么一个科室。一个胖医生这次问得详细,还让我像模特一样走了几个来回,又反复做下蹲的动作。不知怎么,有点拘谨的我,总感觉动作没有平时那样灵活自如。
胖医生略一思忖,随手开了张检查单子,磁共振脑血管成像。我没有任何纠结,不然一会下班就得到明天了。我又摇摇晃晃地赶紧排队,缴费,检查。
磁共振检查室里,一台巨型“航天仓”式的白色机器,丝丝冷意隐隐扑来。躺在上面,头被紧紧箍在了一个圆形的容器里。“千万不要乱动!”医生这句交代让我更为紧张。绷直略显僵硬的身体缓缓被送进仓内,逼仄的空间让人压抑,我紧闭双眼,瞬息,“咔嚓咔嚓”的火车声与“突突——”的拖拉机声不时交替,如此反复。头部纵横交错的无数血管,甚至于毛细血管,都被放射磁线一遍遍仔细勘探。
短短不到半小时,紧张而漫长。在高科技仪器前,我无疑是被“赤裸裸”了一回。这仪器能不能读懂脑袋里那数以万亿的细胞?否则,人们太多不愿为人所知也不能为人所知的隐秘,都将无处遁逃。
身体零件的日益磨损,生活琐碎的时时纠缠,中年的我犹如困兽,不知所措却竭尽全力,卑微弱小却又负重前行。生活在底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检查结果并无大碍。可随之而来的是我愈加的困惑——科学仪器的精密检查,当然不容置疑。那么,之前我向医生所有的陈述,岂不成了自己一次次臆想的虚构?也许,从一开始,我就处在了一种神经质的猜想?
不知是我摇摇晃晃向世界奔去,还是世界向我摇摇晃晃而来?
当医生的弟弟面对我多次的陈述询问,劝我说,你那毛病都不是事,没事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整天别乱猜想。可即使这样,我依然消除不了心头的疑虑。这具我使用了四十多年的身体,成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最终,我还是把自己交付给了中药。中医于人体和宇宙自然之间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精妙的理论体系,这点我深信不疑。草木一秋,春夏轮回;人生一世,生老病死。酱黑色的草木汤汁应该更懂——或苦或涩或辣或麻的汁液,顺着喉咙,一点点渗入五脏六腑。那隐约的草木气息,穿过肝肠,抚慰着脾胃……满满的一碗汤汁,不过是草木把从天地自然吸收的精华,按照一套神秘的密码,慢煎细熬而成。
寻常的草芥,于苍茫宇宙之间沉浮,生于自然,又将归于自然。有时,药汤就像天地间一把能打开所有玄虚的钥匙,不仅仅救赎着人的身体。草木本心,就如此刻之与我。
才发现,自己竭尽全力苦苦索求的,不过是这一团人间烟火。
一场与白发的纠缠较量
四五年前,无意间,当我偶然发现头上竟然冒出几根白发时,针刺般的隐痛从头皮一闪而过。手里捏着几根刚拔下来的白发,在空中几乎完全可以忽略,可在额前却是那么刺眼。我有点惊慌不安——仿若多年建造的坚固城堡,就这样被不速之客轻而易举地攻破。
我一次次以“勇士”的姿态企图阻挡时光——对着镜子,先用发卡夹住刘海,然后手指撩开额前的绺绺头发,仔细挑出藏匿其中的白发,最后一根一根猛然拔去。有时,不免会误伤旁边无辜的黑发。单调的动作,不厌其烦的重复,直至胳膊酸痛、手指发麻,我也要彻底扫荡干净,才肯罢休。常常,为了一根躲藏隐蔽的白发,我竟耐心满头一绺绺地搜寻,一块块排查,常常不觉间会荒废半日时光。面对几根白发,连我都惊讶自己竟然有如此大的耐心。
我倔强得如一个幼稚的孩子。
是时光的温馨提示?还是岁月的提前警告?也许就如田垄边角被遗忘的庄稼,因营养不良便以自尽来抗议罢了。我安慰着自己——夸张矫情也罢,自我炫耀也行。这恼人的白发,无疑是时光庄严宣判的“无期徒刑”,或身体衰老主动妥协的“降书”。
刚开始只有几根,没过多久,那额前白发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相继从头皮钻出,不是这里冒出几根,就是那里窜出一撮,在我惊慌失措间,肆意蔓延。即便是小小一簇,数也数不过来。终于,我决定快刀斩乱麻,索性用剪刀来了结,就算它们再疯长,怎么也不及剪刀利索,每一根白发都注定“在劫难逃”——明晃晃的刀刃贴着发根,轻轻一剪,仿佛便了却了积蓄在心头的牵绊。
我暗自窃喜。
但随之,每当我不经意间掠起额前头发时,那短短发茬微微的扎感总是从指腹一闪而过。我在头皮上狠狠摁几下,仿佛只有这样,白发就会老实一点。镜子里,明晃晃很是刺眼的白发短茬,才几天功夫,又冒出半公分,而我,只能望镜兴叹,任由其肆意攫取。
最终,我还是忍不住,每隔几天,就拿起剪刀“扫荡”一番。单调的动作,渐渐也重复成了一种习惯。每每此时,家人见怪不怪笑笑说,再剪得勤也没头发长得快。
确实,倔强的白发,一如倔强的我。
如此,让我常常心怀恐惧——甚至在梦里梦到自己满头白发,孤独地站在高速运转的巨型齿轮,它们相互咬合、相互搓磨,一秒又一秒,瞬息将自己碾压,黏合。循环反复。
前几日,见到一个省城的朋友,聊天间,她用羡慕的眼神说,你的头发还这么黑,有光泽多自然。我默然,顺手撩起刘海,那匿藏其中的发茬明晃晃地完全暴露无遗。哈哈,我以前也经常这样剪,后来白头发长得太快了,剪不及了,干脆就罢手了。
剪掉了白发,却逃不掉时光的追赶,孩童般的赌气也不过是杞人忧天的自我安慰。不剪也罢,不剪也罢,该疯长就疯长吧。毕竟,曾经拥有过的一袭秀美黑发,已然穿过漫长岁月。
或许,女人对于年龄的恐惧,比男人更为敏感而脆弱——她并不在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容颜,而是担心自己随着岁月的增长,会大梦一场,仍然一无所有。
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太太。她眉慈目善,一身得体的休闲布衫,满头微烫的银发细卷,梳得很是妥帖,没有一丝杂乱。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一定很漂亮有气质吧。老太太穿越世俗烟火,历经熏烤沾染,却依然保持着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优雅——她已把自己活成了一幅美丽的作品。
看着镜子里额前的白发隐隐约约多了起来,我不再去理会——
纵然满头银发,染遍风霜,那也一定是时光和荣耀的冠冕。
一些被遗忘的烟火诗意
当夕阳从天际收走最后一丝余晖的时候,除过有一对白色的鸭子正在悠闲地畅游,河面上的一切都渐归于平静。这时,在河滨西路的公园里,我已来来回回地不知折了几个来回。
习惯每天傍晚来这里散步。待了一天的办公室,喜欢这样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行走。或置身于丛林花园之中,或穿行于熙攘人流之间,而周围的喧嚣热闹,我却能完全置之身外,独享着闹市中的片刻宁静。我常常边走边胡乱想一些事,大多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比如在路边看到母亲最喜欢吃的香脆梨上市了,便想着周末时记得给她带一些;天凉了,远在南方城市的儿子还好吗?差点忘了,花圃老板刚电话告知,说昨天刚进了一批花木,让得空去看看;还有,与闺蜜好久没见了,有点想念了,找机会聚聚……就这样,生活被我凭空胡乱涂画,却也充实快乐。
就这样,一个人来来回回不停地走,漫无目的的,散步成了条件反射,行人,湖水,树木,道路,从眼前渐渐消逝,时间也仿佛停在某个节点……完全放空,好像什么都不属于自己,又好像自己只属于自己。
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没了往常那样洒脱,内心的纠结如河底蔓草缠绕般翻腾——一件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小事,怎么莫名其妙就成了压倒自己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告诫过自己多少次,遇事好好商量慢慢说,可我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瞬间就爆发了呢……我双脚机械地挪动着,从南折到北,又从北折到南。
秋后的傍晚很宜人。河滨殷红色的跑道上,人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几个孩子骑着车子在人群中穿来逐去,甚是热闹。广场上几个大妈正围着音响调试准备开始跳广场舞,叽叽喳喳地,这是她们一天中雷打不动的幸福时刻。还有一家三口推着轮椅上的老人,说说笑笑。靠近架桥下的地方,有几个垂钓的已架好了钓具,渐入状态……
这一刻,他们是幸福的——在寻常的日子中,静享着小城所赐予的美好。我庆幸自己能在这个小城生活。
我常辗转行走于那些寻常巷陌中,或城郊河坝的柳堤上,感受着小城的一切所呈现的自然状态——喜欢在城郊村头,看几个顽童在草地上正肆无忌惮地打滚;看南河边大片的芦花荡,郁郁苍苍,随风摇曳;看河岸顺势堆砌的石头,蜿蜒曲行,随性舒展;看河面上的横斜疏影,影影绰绰,瞬间被水流冲散……
雨后,我都要出去走走。尤其是在初春时节。往往是这样,昨日还光秃秃的草坪,今天就会不经意突然冒出片片新绿——那根根细蒙蒙的草尖,丝丝可辨,嫩蓬蓬的芽儿,在乍暖还寒的春光中,颤巍巍地顶着一小抹儿绿意,似隐似现,又咄咄逼人。连墙角的那几株狗尾草,也高调地随风招摇,没了平时的含蓄;石缝间久经踩踏的不知名枯草,也翠生生得可爱,挺直了腰板。大地上的生命力,隐隐如潮,蓬勃而汹涌。
我沉浸于此,也欣喜于此。
小小的梦想更易让人感到知足和快乐。我清楚,太远太高的梦想,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即使踮起脚尖也永远无法抵达。我也曾如一个偏执迷茫的孩子信誓旦旦地要苦寻人生所谓的意义,只是到后来,忙忙碌碌奋斗了几十年,如今依然平凡普通,没有让世人羡慕的所谓显赫地位与财富,每天为生活打拼,依然过着清贫的日子。化繁就简,或许会让人更易感知幸福。生活本身不过就是场无师自通的修行。也许,寻常日子就是把平凡的生活嚼得吱吱作响,如此这般——每天萦绕在身边的那团烟火诗意,只是我把它忽略太久了。
每晚在广场北边唱歌的那位老人,总是那么准时。他穿着件大红软麻布衫,拉着音箱盒子,拿着麦克风,自顾自地放声歌唱——好端端的歌,经过他的改编,高音成了低音,低音成了哑音。刚开始,还有稀拉拉几个听众围观,后来,就没人了。可这位老人依然兴致勃勃地唱着,一唱便是几个钟头。有次,还见他虚心请教一个男孩如何下载K歌软件。
看到此,我常心怀惭愧——大多数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大多时候,是否也有如此的热情拥抱着眼前的每一天?
夜色渐浓,身边路过的人愈来愈少。那几个垂钓的人,也已收拾好东西回家了。空荡荡的河面沉入了梦乡。远处闪烁的霓虹灯倒映在河面,像是把一大堆红的绿的蓝的颜料随手洒在河里,洇成一团,恍恍惚惚。
路灯渐次熄灭。孤零零的我,依旧伫立于河边,一阵风吹过,身旁簇簇树木在夜色中静默着,似一尊尊禅修的佛——我独钓于这偌大的夜色与静谧之中,未敢有一丝的企图。
忽然,扑面迎来一阵水气,濡濡的,凉凉的。不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上次第燃起了淡黄的明亮。
转过身,我准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