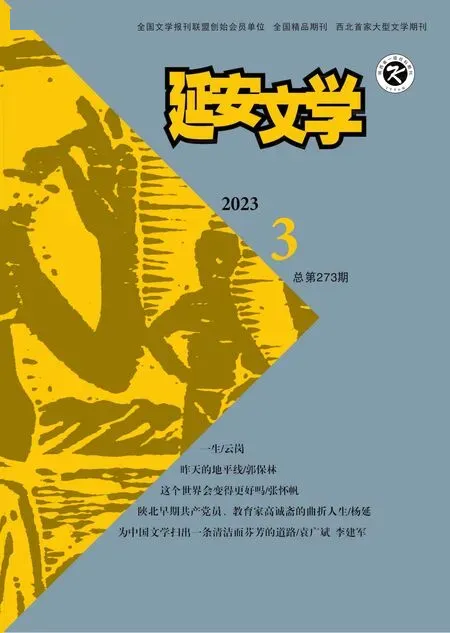绿色火焰
李 敏
细米跑回学校,学校还笼罩在灰蒙蒙的晨雾之中。空气又冷又潮,细米打着颤,倒在空荡荡的宿舍床上,捂上被子,呆呆地看着窗户上层的三块玻璃。江康屋里火红的铜炉子,或许能驱走这彻骨寒意。但她不知道该怎样向江康陈述昨晚的事。
书摊后面的江康看见细米,除了多看了一眼她的额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他把她让进屋,用跛脚勾了炉边小木凳让她坐,晃了晃炉底灰,提起铁壶,添了些炭块进去。拿棉棒蘸了碘伏水,给她涂擦额头上鸡蛋大的伤痕。擦完,江康把热水杯塞到她手里,又从旁边木箱里,拿出软装版《梵高画册》递给她。这是细米最喜欢翻看的一本书。江康一句话没说,一句话没问,出去继续守他的书摊了,这令细米很感激。这个男人不爱说话,扑克一样的脸,总是不愿意流露出任何情绪,别人喊他僵尸康。
随着炉火跳跃,炉上的铁壶嗤嗤冒着水汽。梵高层层叠叠的色彩在画面堆积着绚烂,书上说,那是画家嗤嗤燃烧的热情,细米却从他明亮的黄色后面看见了黑夜,扭曲的笔触中感到了疼痛,她知道,梵高在用艺术家的狡猾掩藏悲伤,如果梵高还在,她真想和他聊聊那些缠缠绕绕枝花疯癫的舞蹈。细米冻僵的身体暖和过来,心情逐渐平静。门外风越刮越紧,街上空荡荡的,那些皮绳压着,一排排卷角泛白的书,被风翻得哗啦哗啦响。看书的孩子真是越来越少了,手机和作业让他们无法安心好好读一本书。角上那本高尔基的《童年》,江康说过要送给第一个拿起它的孩子,可一直没有送出。
江康在寒风里端坐在书摊前,像个忠诚的卫士,盯着风中乱飞的树叶,不停搓着残了的半截小拇指。
周五,整整一个下午,细米一直没有听进去课,她的耳畔老是回响起妈妈堵满了沙子一样的声音。妈妈让丁来捎话,说放学时来接她回家。
课间时,几名男同学煞有介事地讲流血、步枪和战士,仿佛他们经历过战争似的,那种狂热和冲动带着一股生不逢时的遗憾。好像他们生长在那年代,就会成为大英雄似的。细米觉得十分可笑,她努力去设想战争的场景,可她眼前总是晃动着妈妈粗壮的腰身和大强的黄头发。
最后一节课。风呜呜吹得紧,窗外什么东西被风吹得吧嗒吧嗒响,数学老师正因为同学们心神不宁,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老师,找俺家丫头哇。”突然,一妇女趴在门口朝教室喊,嗓子像塞满了沙子。
“干吗呢?讲课呢!门卫呢?随便进教室,这课没法讲了!”数学老师把书狠狠拍在讲桌上,半截粉笔摔在墙角。
细米一激灵,伸长了脖子一看,把头低了下去。
妈妈趴在门口,探进半个身子,好奇地往教室里张望。她很胖,穿一件黑色化纤毛衣,看不见脖子,像只黑熊,毛衣很紧地勒着她,腹部随着呼吸颤颤起伏着。
教室里哄堂大笑。同学们本来不想听课,所有同学眼睛像被线牵着看这位不速之客。随后转向细米。细米脸腾地红了。同桌丁来说:“快出去呀。”细米在注视中机械地走了出去。数学老师冲细米点点头,似乎叹了口气,再没说别的,细米瞬间有想抱住她的冲动。
“死丫头,一个多月不回家了,不想娘哇?”细米身后传来排山倒海的爆笑。
细米坐上妈妈电动车后座,回了桃花坪的家。桃花坪房子大都屋檐不高,矮趴趴的,细米的家处在村东的小溪边,小溪再往后就是栽满桃花的鲁山了。到家时,正是晚饭时间,村里炊烟四起,一派平和之气。
细米上初中后,选择寄宿。寄宿的同学周末都回家,细米不想回家,不是因为妈妈的暴躁,也不是因为桃花坪路远,是因为害怕大强。
拐进家门,大强倚在门框上,扬了一下蒜黄一样的头发,露出土霉素牙冲细米笑,他一手夹着烟,一手插在破洞牛仔裤裤袋里。他脸上青春痘越来越厚了,被他挤成紫红色。细米咬了嘴唇,侧身挤进门。妈妈停下电动车,抓起一把羊角葱进了厨房,她在吃上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细米低着头,默默地走到餐桌旁,把文具盒和书本一一掏出来摆在桌子上,静静地写作业。大强在一边看电视。细米已经想好了,如果大强这样说:“玩玩再写吧?”她就说:“不行,作业太多了。”如果大强再拽她的头发,她就大声喊妈妈。大强却没过来,只是不时转过头,盯着细米笑。
妈妈饭菜做好了,一股葱香味也被她带进屋来,细米麻利收拾好书本。三人围桌坐下吃饭,气氛很微妙,妈妈喜欢一边嚼饭一边不停说话:谁家的夫妻不和谐了,谁家的孩子偷东西了,谁家杀猪了,谁家的女人添了件时兴衣服等等这样小事,这次啥也不说了,只是呼噜呼噜吃,吧唧吧唧嚼。大强也不抖腿也不吧唧嘴巴,只是默默往嘴里扒饭,眼放在碗沿上看细米。饭吃完,细米习惯性收拾桌子,妈妈突然一把夺过细米手中筷子,冲大强喊:“大强,收拾桌子,怎么让细米收拾?”大强咧着嘴,把遥控器扔到沙发上,眼睛不断地往细米身上瞟。
细米拿了扫帚扫地面的瓜子壳。她走到哪里,妈妈的目光追到哪里,她确定妈妈有事情要讲。
细米扫了地面,搓洗了脸盆架上黑乎乎的毛巾,擦了手,躲进自己小屋。果然,长长一口气还没叹完,妈妈推门侧身挤了进来。
妈妈在细米床上坐下,和颜悦色说:“米啊,看你瘦的,都是念书累的,念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我喜欢念书。”细米绞着手指。
“大强崴过年就三十岁了,不让人省心。”
“我刚刚考了一个满分,老师表扬我了。”
“我要被气死了。”
“又惹事儿了?”
“偷看刘寡妇上厕所,让人捉住了。”
“是很丢脸,我们有啥办法呢?”
“结婚就好了。”
“再给苏四娘送点礼。”
“送得还少?白搭,愁煞人。”
“大强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不干正事。”细米说。
妈妈是个没耐心的人,很容易发火。被点到痛处,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干巴栗子,啃去皮,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嚼,腮帮咬得鼓鼓的,胸部起伏剧烈起来:“操他妈的,没一个省心的。老东西常年躲在外面吃喝嫖赌,等于没这个人。大强,还真是老死鬼的种,天天作死,天天惹事,不让人省心。小东西,不是自己身上的肉,根本不替你着想。没一个省心的,操他娘的……”妈妈口水就像夏天知了尿,噗噗溅到细米脸上。
妈妈开口骂人,怎么也要骂烧开一壶水的时间才解气,细米只能任她骂。小屋很久没有打扫,窗台布满灰尘,角落蛛网沾满白色碎屑,有股难闻的腐烂味道,估计是堆在墙角的南瓜坏掉了。
“越上学越野心,家都不愿意回了,白白养了不成……”妈妈摔门而去。
大强在看电视,不知看到什么好玩的,嘎嘎地笑。细米眼泪热热地顺着鼻翼流下来。她把门插上,把一件半新白毛衣叠成一小团,塞进书包。再次检查了门闩,和衣躺下,伸手灭了灯,一切淹没在黑暗之中。
睡梦中,细米猛然惊醒,窸窸窣窣的细碎声音传到耳膜。细米支起耳朵,屏住呼吸。有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很轻,很慢,一点点试探,喳,喳,咝。一阵细细碎碎。抽出锁孔。咝咝,再插进一把,吧嗒一声,锁打开了。门被推开一条缝。细米听见粗重的呼吸。
细米伸手去抓他的脸,他却有着惊人力气,抡圆了拳头。
细米尖叫划破黑夜,丁来家黑狗汪汪叫起来,黑影拔脚而逃。
妈妈屋里的灯亮了一下,立即又灭掉,一切归于平静。细米坐在床头,不停颤抖,茫然瞪着窗外,窗外黑蓝色天空挤满了星星,毛刺刺地如一个个战士,张牙舞爪挥着手中武器,跳跃着,咒骂着,旋转着,挤成漩涡,汇成流水,倾泻而下,一如梵高画册里的星月夜。细米额头上有血水不断地流出来,浑身火辣辣地疼,没有一处妥帖,院子里死寂一片。细米抱着书包,拉开大门,一路狂奔。
妈妈再次来到学校找细米,门卫没让她进门,而是打发别人去找细米。细米很害怕,跑去找班主任王老师,说妈妈来学校找她,要带她回家,不让她继续读书了。王老师一听很着急,细米是学习很好的学生。王老师说:“这怎么行呢,九年义务教育法不懂么,我去找她理论。”她领着细米去学校大门口见了妈妈。王老师从远到近给妈妈讲道理。妈妈懒得听,没听完,气鼓鼓地骑上车走了。
周末,同学都回家了,教室里只剩下刻满划痕的桌椅,操场也只有落光叶子的梧桐树,学校大门洞开着也没有同学进出,校园到处空荡荡的。细米便发慌,她怕妈妈再来学校找她,她不敢待在宿舍,只好整天在江康那里看书。学校门口不让摆摊后,卖水果的,卖粽子的,卖冰糖葫芦的,卖玩具的,统统搬走了,江康的书摊安在了街头的苦楝树下,这地方正好是他租住的地方,卖的书少了些,但收摊摆摊方便了很多,他腿脚这两年跛得更厉害了。
小镇不大,卫生所、派出所、学校、商店都在这一条街上,所以这条街还称得上繁华。书摊东邻是炸油条的老孙头,似乎油把他整个人熏透了,身上油腻腻的。他喜欢喝酒,喝醉了大声骂人,都是对着他的老婆骂,矮小的老婆脸上不带表情,只管把老干烘泡上,端到他面前,随他去骂。西邻是卖塑料盆和拖把等杂货的花姑,她看上去很干瘦,却有很大力气,进货出货都是她一个人搬来搬去,他的矮老公和胖儿子也不知道忙啥,总是不见人影。她声音很尖,人精明得很,谁也甭想赚她一分钱便宜,街上的人喊她“辣子鸡”。
周末,看到细米带了菜篮子帮江康买菜回来,又拿了水杯,泡了茶端给他,花姑嘴角撇了又撇说:“僵尸康,从来不见你笑,最近怎么喜滋滋的,找了小媳妇啊?”
老孙头也附和:“我早就看出来了,老牛想吃嫩草哩。”
江康说:“这条街最俊的女孩子哪,你俩眼馋了?快去整上十个大碗,十个凉盘,我商量商量细米,让她去你们那里坐坐。”
“呸,金枝玉叶了还。”
细米捏着江康给她的一截茴香味儿香肠,头很低地看膝盖上的书。她的布鞋子,脚底磨薄了,鞋脸被大脚趾拱出一个小洞,凉凉地透风。
寒冬来了。早操时同学们嘴里呼出来的气体清晰可见。没有足够棉衣,细米只能穿件毛衣硬撑着,手上结满冻疮。裤子短了,露出干瘦脚踝,脚脖子皴裂得像操场边老柳树皮,风一吹,破碎般疼痛。更让细米难堪的是同学们指指点点。
丁来又塞给细米三十元钱说:“不多,先用着,记好哈,有了加倍还我,高利贷我最行,嘻嘻。”
细米眼圈一红,接过来,说:“不说谢了,有了还你。”
真不忍心再从丁来手中接过,这都是丁来从自己生活费里省下的。作为一起长大的玩伴,妈妈怎样与好吃懒做的父亲吵得鸡飞狗跳,大强怎么用打火机烧她的辫子,怎么把毛毛虫放进她口袋,丁来都知道。当然,十几年前,爸爸带女婴回家,脸被挠得稀巴烂,因为他说是路上捡的。妈妈不信,妈妈怀疑他是与别人生的。以后的日子里妈妈怎样讨厌这个女孩,丁来也知道。这些,树底下那些老婆婆老在说,细米一家总是桃花坪人谈论的话题。
若不是他和江康不断接济,她早已无法在学校继续生活。妈妈一分钱也不给细米了,决心把她熬回家。
终于期末考试结束,同学们纷纷回家等成绩,又要放寒假了。
外面下着小雪,细米独自躺在冰冷的宿舍,连续几天的咳嗽让她嗓子嘶哑。昏睡到中午,似乎有火烧着她,细米爬起身,摸摸自己脸,摸到焦干的嘴唇,她挣扎着站起来下床找水,宿舍的热水瓶没有,水杯里也没有,学校停课的时候,水房是没有热水的。
肉香把细米唤醒,她慢慢睁开眼睛。被子很干净,有一股陌生的、微微放久了的肥皂味道。床头小桌上放着玻璃杯,旁边有药片。离床不远的炭炉上,正烧着一口双耳铁锅,炖着排骨和莲藕,嘟嘟冒着热气,整个小屋氤氲着一层香暖气息。外面很亮,透过窗户,对面房顶上积了厚厚一层雪。天已经放晴了,明亮的阳光照在雪上,莹白透亮,苦楝树的树枝伸在空中,落着几个麻雀,尖尖的小嘴巴,眼睛乌亮,灰褐色的羽毛带着点点花纹,偶尔忽地飞起,落向屋顶,扬起点点雪花,从屋檐上纷纷飘落。
透过蓝布帘一角,能看见排在墙角一箱箱熟悉的书,这是躺在江康家里。似乎昏沉记得,昨天下午是奔这里来的。细米看见自己单薄的衣服,挂在火炉后面的椅子上,又脏又旧,像蛇蜕下的皮,她用手捂了脸。
门“吱呀”一声,江康侧身挤了进来,裹着一身寒气,怀里抱着一个大塑料袋,嘘嘘地吸着气,跺着脚上的雪。看到细米睁着眼睛,冲她笑了笑。说:“终于醒了,好些了吗?昏睡了好久哦,急死人呀,瞧瞧给细米买什么啦。”
他把怀里鼓鼓的包裹在床上打开,东西一下子呈现了出来:一件绿绒袄,一双黑靴子,白毛袜,红色毛衣,毛裤。
“发烧近四十度呢,盗汗哪,衣服都湿透了,像水里捞出的一样,只好给你脱下来了,这么瘦,体质太差了,要好好吃饭。小脚都冻烂了呢,唉,还发烧么?”
他边说边把手搓了搓,放在细米额头上,努着嘴,很认真的样子。
断指从眼前划过。细米的眼泪顺着耳根流,“吧唧吧唧”滴落在枕头上。
在江康的坚持下,细米在床上喝了一点点米粥汤。吃完药片,又躺了下去。
江康坐在床沿上,拉着细米的手,紧紧地攥着,看着细米,没说话,喉结一动一动地,眼泪流了一脸。
江康把窄小的折叠竹床打开,铺上些被褥,和衣躺下,过不久就要起来,给细米换一下额上的毛巾,或端些水给她喝。
一筹莫展的寒假和新年,在江康家度过了。细米几乎不出门,若有人来,她会快速藏在蓝色大布帘后面。幸好江康朋友不多,没有多少人到他屋子里去,省去了很多尴尬。也幸好有很多书作伴,天天藏在屋子里看书,日子也不多么寂寞。细米常常怀念桃花坪家中的院落、火炉、水缸、大鹅和丁来家的小黑狗,又怕又盼望家里人找她,可假期快过完了,也没有见到谁来找过细米。
江康做饭非常有耐心,配菜、调火、入味,一点也不含糊,变着花样给细米做好吃的。细米蜡黄的小脸眼看红润起来,江康话多了,脸上也喜滋滋的。他说,来北方这么多年,今年终于有人陪他过大年了。他把浇了汤汁的松鼠鱼端到细米面前,花儿一样漂亮,简直把细米惊呆了,一尝,酸酸的,甜甜的,香酥爽脆。
“真好吃啊,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
“我妈妈做得才好吃呢,我家厨子刘叔都竖拇指呢,但她不常做。她爱吃清蒸鱼丸,最爱喝银耳莲子粥,她熬粥,喜欢放些柴鱼干,小火慢慢煲,喝一口,那叫一个润滑香甜呢。”
“想妈妈了吧?”
“想也没用,家被我毁了,我妈被我气死了。”
“唔,你来这儿多久了?”
“十二年了。”
“多久没回家了?”
“一次也没回。”
“哦,是够久的了,你腿怎么伤的?”细米太想知道了。
“五楼跳下摔的。”他说。
细米还想问,他的半截小指头怎么回事,为啥跳楼,有没有娶媳妇,但江康脸色很难看,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反复擦,她便不敢再问了。
“找机会,我得和你家里人谈谈。”江康端起剩鱼,“拖嗒——拖嗒——”拖着跛脚出门,他总是惦记着那个流浪猫。
江康还是每天忙碌他的书摊,放假了,孩子们稍稍多了起来。江康脸上笑容多了。别人常常逗他说说像外语一样的南方话,惹得一阵大笑。有时,隔着窗户,听见隔壁的花姑说:“没想到,僵尸康笑起来很好看呢,哎,那女孩怎么老在你家,她可才上初一,你可不能欺负人家。”
江康说:“说啥呢辣子鸡,听不懂哩。”
“僵尸康别装呆,我可什么都知道。”
“收个闺女养老,有什么不对么,你想照顾我啊?”
“呸,死僵尸康,看我不撕你的嘴!”
“想亲嘴就亲嘴,说什么撕嘴,来啊来啊。”江康跛脚扑向花姑,夸张地做侵犯状。花姑尖叫着躲闪,黄脸出现了红晕,平日里尽量掩藏的两颗龅牙,也无所顾忌地暴露出来。
大年气息还未尽,风里有了暖意,新学期开始了。同学们白胖了不少,都穿上了新衣裳。女同学看谁新衣服漂亮。男生却在谈论着压岁钱和鞭炮,一派新气象。
来学校前,江康看出细米的不安,教细米说:“记劳我的话啊,别人问起,说我是你干爸。”他越是这样嘱咐,细米越是不安。
丁来和细米说:“你没回家过年,你爸也没回家过年,去你家要欠账的倒好几个,听奶奶说,你妈对着电话骂了足有两个时辰,把你爸骂关机了。媒人给大强说了个媳妇,黑,矬,还有狐臭,大强睡了人家,却嫌人家丑,不想结婚,姑娘要你家出八万块钱才算完,你妈气得要上吊……”
细米说:“怪不得没来找我,原来没顾得上。”
丁来又说:“村里说,你找了个新爹,也有说你准备给那个老头做那个啥的,你那家,出来找个爹也对,那个嘛,我不信。”丁来吐吐舌头。
“信不信由你。”细米说。
丁来撇撇嘴。他年后白胖了些,又长高了,理了一个新兴发型,穿着红色羽绒服,看上去帅帅的。女生下课的时候,都喜欢找他说话,他却愿意跟细米说话。
学校到江康住的地方不远,过一个丁字口就到了,细米怕别人说闲话,开学后三个周末没去了。
周六一早,淅淅沥沥下起了雨,雨很大,十点多光景,雨还没有停的迹象。细米在空荡荡的宿舍门口,独自望着雨出神。
看雨小了些,顶上一把破伞,去找江康。
门落着锁,窗台下面放着的几盆鸢尾花,陶泥花盆碎了,散乱一地。细米趴在门上,就门缝往里瞧,屋里黑乎乎的,没瞧见什么。细米脸在黑伞下更显苍白。她撩开花姑家红色塑料珠帘:“姨,我找江叔,你看见他了没?”
花姑坐在板凳上,拿把红塑料梳子梳头,一下一下,一下一下,她抿着嘴,斜着眼瞅着她,也不让细米进屋。
外面下着雨,细米就站在门框下,一手撩着珠帘,一手撑着破伞,屋檐上落下水滴噗噗打在伞上,落到地面,溅到细米裤脚和早已湿透的鞋子上。细米揪着裤子,手在颤抖。
“你真不知道?走了……黄毛,满脸青春痘的那个,下手那么狠,吼声又那么响,谁敢帮他呢?估计手臂被打坏了,真是可怜人啊,年轻时因为赌,妻离子散,躲到咱这里过些安稳日子,又这样……”
细米脑袋里嗡嗡作响,就像上课时敲打柳树下挂的生铁钟。她拖着破伞,在雨里机械地走,不停地走。
雨停了,西边天空布满血色云霞,水库里一片红光跳跃。细米把湿透的鞋子脱下来,厚胶底白帆布鞋子,高帮外侧有颗红心,是江康买给她的。她倒掉里面的泥水,把粘的枯草烂叶捏干净,轻轻摆放在水库岸边湿漉漉的青石板上。
傍晚时分,青山有了深色轮廓,不远处几个矮趴趴的旧坟茔,再过两年或许就不见了踪影。一棵孤零零的柏树,天空下如燃烧的绿火焰,向天空升腾喷吐,一如梵高拿着巨大的画笔,舞动他痛苦的灵魂,在大地和天空之间呐喊。
田野里一片寂静,恍惚中,她似乎听到了江康“拖嗒——拖嗒——”的脚步声向她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