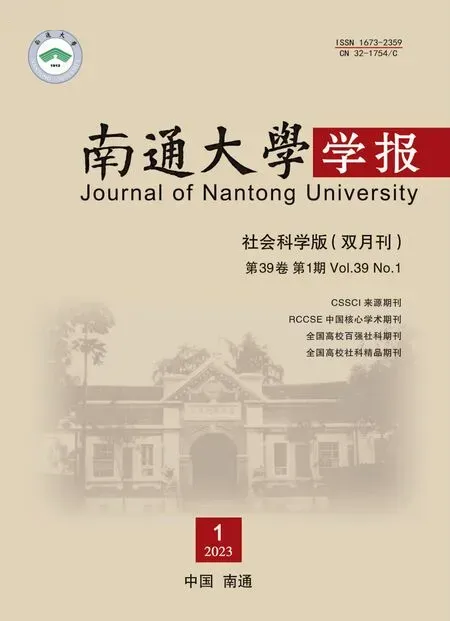家庭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具体效应及其影响路径
高功敬
(济南大学 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一、问题的提出
由迈克尔·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所创立的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理论(Social Welfare Theory Based on Assets)自20 世纪90 年代韧始以来,因其突出的整合性、包容性、发展性特征,被学界普遍视为社会福利政策领域中的一场范式革命[1]viii[2]28-30[3]1488-1496。该理论对基于收入和消费为本的传统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强调其由于忽视了贫困内涵的复杂性以及贫困家庭的资产建设,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没有实质性减少贫困或缩小贫富分化。[4]199-200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理念与实践把贫困狭隘地理解为消费与收入的匮乏,不鼓励甚至抑制贫困家庭进行资产积累。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与消费匮乏,更是资产或财富匮乏[5]1-11、可行能力匮乏[6]23-25、权利匮乏或社会排斥导致的脆弱性[7]108-110以及稀缺性思维模式的表征[8]1-8,132。基于对贫困现象复杂性理解的多维整合视野成为有效反贫困的内在要求。[9]132以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不仅能直接促进穷人进行资产积累,更重要的是,将会产生显著的“资产效应”:促进家庭的稳定;改变稀缺性思维模式;促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发展;增强专门化和专业化;提供承担风险的基础;增加个人效能、社会影响与政治参与等[5]180。显然,资产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建立在资产效应理论基础之上的,然而,资产效应理论所提出的九大效应命题还普遍缺乏相应系统的经验验证[5]1-11[10]1-9。更重要的是,作为静态结果的资产本身与作为活动、行为、过程的资产建设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尽管二者也存在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因此,资产效应并不等于资产建设效应,二者在理论逻辑与经验现实中都应有所区分。然而,谢若登所提出的资产效应理论倾向于模糊二者的区别,而不是清晰区分二者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其把资产建设效应包括在资产效应之内,但这样做实际上严重忽略了资产建设行为与过程相对于拥有资产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效应。本文拟正式提出资产效应与资产建设效应是虽有关联但本质不同的两种效应,把资产建设效应理论从资产效应理论中区分出来,以期为资产建设福利政策提供更为坚实与直接的理论基础。
儿童发展关乎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儿童发展尤其是贫困家庭儿童全面发展是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内在要求,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国内学界对儿童发展的相关探讨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焦点[11-16]。关于资产以及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假说层面,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十分匮乏,个别相关研究依然停留在相关关系的探讨上[17]。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基于资产效应理论对儿童发展的相关经验研究日趋增多,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家庭资产对儿童学业成绩、儿童行为表现、儿童心理等方面的效应[18-22]。这些基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所做的相关实证研究从不同的时空情境中验证了资产对儿童发展相应维度所具有的各种效应。然而,国外相关研究依然没有对资产与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具体效应进行明确区分,相关资产效应是否对中国情境同样适用也有待基于中国经验数据基础上的检验。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拟在区分资产效应理论与资产建设效应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运用CFPS2018 数据实证研究家庭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主要维度的具体效应及其影响路径,进而检验资产效应理论与资产建设效应理论在解释儿童发展主要维度变异上的各自效应和能力。
二、文献述评:资产效应、资产建设效应与儿童发展
(一)资产效应与资产建设效应
1991 年,谢若登在《资产与穷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资产效应理论”,认为“资产具有各种重要的社会、心理和经济效应。人们在积累资产时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行为,社会也会对人们产生不同的回应。具体而言,资产改善经济稳定性;将人们与可行有望的未来相联系;刺激人力或其他资本的发展;促使人们专门化和专业化;提供承担风险的基础;产生个人、社会和政治奖赏;增强后代的福利”[5]180。简言之,资产效应蕴含九个基本命题:“资产促进家庭稳定、创造未来取向、刺激其他资产的发展、促使专门化和专业化、提供承担风险的基础、增强个人效能、提高社会影响、增强政治参与以及增进后代福利。”[5]180-181“资产效应理论”是谢若登在社会政策界备受赞誉的“以资产为基础的福利理论”的前提,“作为具有包容性的以资产为基础的政策的主要原理,资产效应至关重要”[10]7。
然而,关于“资产效应理论”一直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基础问题:其一,“资产效应理论”蕴含的9个因果性命题还缺乏相应的经验验证,现有经验研究仅停留在关联性(相关性)探讨上。谢若登指出“资产效应理论”的九个命题中,“每一个命题都是基于业已建立的理论和证据,然而,现在还没有专门确认每一个命题的真实程度、前提条件以及相互之间的可能联系……今后应当提出专门的经验性问题,并设计有针对性的研究来解答这些问题”[23]148。“多项研究均发现,拥有资产与大量各种不同的积极结果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是缺乏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如果这些效应(资产的九大效应)存在,并且假设其收益大于政策成本的话,那么这将是针对所有人的资产建设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案例。遗憾的是,本研究没有直接解决这些关键问题。”[10]7其二,“资产效应理论”强调了拥有“静态的”资产本身的重要性,客观上忽视了“能动的”资产建设及其过程的重要性,并没有严肃区分强调拥有资产本身的“资产效应理论”和注重活动与过程的“资产建设效应理论”。事实上,尽管谢若登注意到了“资产效应”概念与“资产积累(资产建设)”概念之间的区别,但并没有明确区分“资产效应理论”与“资产建设效应理论”之间的实质性差别,而是倾向于在修辞时把二者混同在一起,或者认为后者并不重要。然而,二者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资产效应”概念及其理论强调的是拥有资产的静态结果,而“资产建设”强调的是资产积累的活动与过程。为突出作为活动与过程的资产建设本身和作为静态的资产拥有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本文认为有必要明确提出“资产建设效应”概念以及“资产建设效应理论”,以区别于“资产效应”概念及其“资产效应理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一穷二白,但并不妨碍其开展资产建设或资产积累,而在这个行动或过程中所产生的资产建设效应并不比拥有资产本身所产生的各种效应弱。实际上,本文假设资产建设效应比资产效应更重要,而谢若登所提出的资产效应九大命题,资产建设效应不仅基本都具备,而且其本身更多地体现在资产建设或资产积累的行动与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资产效应与资产建设效应既有本质区别但也存在内在的密切联系,除了个人或家庭继承或接受赠与的资产外,家庭资产基本上都属于家庭资产建设的结果,家庭资产建设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资产效应。为此,可把资产建设效应作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资产建设效应既包含资产建设过程与行为本身的效应,也包括了资产效应——作为资产建设行为的结果;狭义的资产建设效应仅指资产建设行为与过程所产生的各种效应。
(二)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效应研究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持有资产会以积极的方式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21]35-49。其中资产对儿童发展的效应研究逐渐成为相关实证研究的焦点之一。这不难理解,儿童作为家庭、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也作为斩断代际贫困传递的关键,一直是资产建设效应关注的重点,同时,也因其可塑性强更易被用来验证资产建设效用命题。学界关于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资产建设对儿童教育程度、学业成绩、心理健康、行为表现等方面。
梅叶尔发现,家庭投资额比家庭收入可以更好地解释儿童考试成绩差异[24]1-15;奥尔利用国家青年纵向调查数据发现,即使控制了父母教育、职业和家庭收入,资产对儿童考试成绩也有积极的影响[25]281-304。更多的研究表明,金融资产、住房所有权与孩子的教育程度、情绪和行为健康正相关,可能至少部分是因为资产改变了对未来的预期[20-21][26-29]。家庭开展教育储蓄对儿童教育通常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艾利奥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儿童教育储蓄对儿童的数学成绩、大学升学率、大学毕业率等方面具有显著积极效用[30-32]。一项来自乌干达的2000 名初中生参与的教育储蓄实验结果表明,参与教育储蓄对于青年学生的入学率、学业成绩具有积极的结果[33-34]。尽管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家庭资产(财富)对儿童教育具有积极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资产对儿童教育的效应也不同。有学者通过对坦桑尼亚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虽然非生产性资产(如家庭耐用品和住房质量)与儿童教育成果呈正相关,但农业资产对儿童的学业成绩具有负面影响[22]14-28。
除了资产建设对儿童学业成绩的相关实证研究,学界也日益重视资产建设对儿童心理行为方面的效应探讨。凯尔尼运用加拿大统计局开展的全国人口健康调查数据(NPHS,1994—1995),研究发现住房形式的资产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生活在租赁房屋的儿童心理困扰水平显著高于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儿童,儿童抑郁症患病率也高出三倍[18]。资产也被证明可以增强儿童的心理健康,埃辛和邓肯运用底特律大都市地区867 个家庭的纵向研究数据发现,父母在子女一年级时为其大学预留金钱,子女23 岁时的自尊指数会显著提高,这意味着资产可以增强儿童心理健康[19]。目前有两种关于资产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解释:一是家长存在经济压力,反过来向家人施压,破坏了家庭关系,导致幸福感降低,影响孩子心理健康;二是因为经济资源影响后代社会经济地位,反过来又影响子女心理健康[35]。也有学者注意到资产对儿童行为表现也具有影响。波义耳综合考察了儿童在社会参与过程中出现的反社会、注意力不集中、过度活跃、焦虑等反应,发现拥有房产的家庭儿童问题评分明显低于租房家庭的孩子,且无论收入是否高于收入贫困线,这样的效应依然存在[36]。
关于资产建设对儿童教育、心理健康、行为表现等方面影响机制探讨,目前学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认为资产建设对儿童教育、心理健康、行为表现等产生直接影响[5]1-11[37]1829-1878[29]3-16;二是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方面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家长的教育期望、教育参与、教育机会以及家庭环境(包括家庭关系)等中介因素间接产生影响[21][26][38-40]。然而,关于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主要局限在理论探讨层面,相关的实证研究或经验验证依然付诸阙如。
三、因果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目的是实证研究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具体效应及其影响机制,检验资产效应理论以及资产建设效应理论在儿童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及其差异。基于上述文献探讨和研究便捷考量,本文把资产建设效应作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资产建设效应不仅包括了作为活动与行为的资产建设效应,也包括了作为资产建设结果以及家庭先赋资产积累结果的资产效应;狭义的资产建设效应仅指资产建设行为与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不包括资产本身的效应。儿童发展是一个多维概念,主要包括儿童身体维度、心理维度、行为维度、教育(学业)维度、信心维度等。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考察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健康、儿童行为表现、儿童学业表现以及儿童自我期望的各自影响,这四个维度基本上涵盖了儿童发展中的核心内容。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不仅是直接的,更多的是通过一系列中介机制完成的。谢若登的资产效应理论以及学界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中介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教育机会、学校质量等方面实现的。同时,相关研究与经验证据表明,家庭关系会对家长参与和家长期望产生影响,而家长参与也会对家长期望、教育机会以及学校质量选择产生影响。基于上述文献探讨与理论假设,本文提出如下因果模型(见图1)。

图1 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因果模型图
图1 表明,本文关于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包括如下两点假设:
第一,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各个维度)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学校质量、家长期望以及教育机会分别对儿童发展产生间接影响。
第二,尽管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各个维度(身心发展、行为表现、学业表现、未来期望)的影响可能存在具体差异,但本文在模型建构上假设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各个维度的影响路径基本是同构的。这样做一方面主要基于资产建设理论以及相关经验研究中针对不同的儿童发展维度的总体框架是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比较和简化模型的考量,在检验时方便比较广义与狭义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不同维度的效应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广义的资产建设(包括资产与资产建设行为)还是狭义的资产建设(仅指资产建设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各个维度的因果机制基本是一致的,但具体效应可能会存在显著性差异,尤其是狭义的资产建设与资产本身对儿童发展的各个维度的效应可能会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因果模型图以及上述因果模型图所蕴含的两个基本理论假设,本文提出如下系列待检验的具体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资产建设(广义与狭义)对儿童发展的各个维度(身心健康、行为表现、学业表现、自我期望)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研究假设2:资产建设(广义与狭义)对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学校质量与教育机会都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且分别通过这些中介变量进而对儿童发展的各个维度(身心健康、行为表现、学业表现、自我期望)产生重要的正面效应。
研究假设3:家庭关系对家长期望、家长参与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家长期望对家长参与、学校质量选择以及教育机会产生显著正面效应,进而资产建设通过这些中介通道对儿童发展各个维度产生积极的效应。
四、数据、测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2018 年追踪调查数据(以下简称CFPS2018),个别匹配变量使用了包括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以来的历次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2201420162018)。CFPS2018 在中国25 个省、市、自治区成功调查了约15000 户家庭,并对每个样本家庭户进行了五份问卷调查:家庭经济问卷、家庭成员问卷、个人代答问卷、个人自答问卷(针对10 岁及以上个人)和少儿家长代答问卷(针对0—15 岁个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且完成了自填问卷的小学与初中阶段的儿童(主要为10—15 岁儿童,其中包括30 个16 岁处在初中阶段的儿童)。为了实现本文上述研究目标,本文把所需要的可观测变量在不同数据库中进行了匹配处理,具体为把少儿家长代答问卷、家庭经济问卷、家庭成员问卷、个人代答问卷、个人自答问卷进行了配对,成功匹配2860 个样本。由于后期数据标准化处理中个别省份样本过少导致关键变量的大量缺失,为此,经过逐一核查剔除了北京(5 个)、天津(15 个)、新疆(4 个)、宁夏(2 个)4 个省份共计26 个样本,其他样本中变量存在的部分缺失值经过插补处理,最终得到了2834 个有效样本。
(二)测量
1.核心解释变量:广义资产建设与狭义资产建设
家庭资产建设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上文探讨,本文把家庭资产建设分为广义的家庭资产建设与狭义的家庭资产建设,前者不仅包括资产建设行为与活动,而且包括了家庭拥有的资产——资产建设的结果,后者仅仅包括资产建设行为与活动本身。作为狭义的资产建设主要用如下三个变量进行测量:(1)是否为孩子教育存钱;(2)是否有住房出租;(3)是否进行金融投资;除此之外,作为广义的资产建设还包括家庭已拥有的各种资产本身;(4)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对这一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5)耐用消费品总值,家庭耐用消费品不仅是消费品,而且具有直接提高家务劳动效率的功能,具有长期的生产性效应,属于家庭重要的资产[41];(6)家庭净资产,这一变量来自家庭经济数据库,将家庭净资产这一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
2.主要被解释变量:身心健康、行为表现、学业表现、自我期望
儿童发展的主要维度包括儿童身心健康、行为表现、学业表现、自我期望等。(1)儿童身心健康,主要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两部分。身体健康在CFPS 2018 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健康状况”,心理状况主要问题为抑郁程度量表(CESD)得分。健康状况为连续型变量。CESD 得分在CFPS2018 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N4A(抑郁程度量表),CFPS 将选项依次赋值为1-4,数值越大表示该感受或行为的发生频率越高。其分为CESD 构建分数,连续型变量。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八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得到CESD20sc 变量。CESD 构建分数的取值范围为22~72,数值越大表示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越差。(2)儿童行为表现,主要包括生活行为表现与学习行为表现两部分。生活行为指标包含“孩子做事时注意力集中”“孩子遵规守纪”“一旦开始就必须完成”“孩子喜欢把物品摆放整齐”四个变量。学习行为指标包含“孩子学习很努力”“孩子完成作业后会检查”“孩子完成作业后才玩”三个变量。(3)学业表现,主要用主观学业评价和客观测试表现两个方面测量儿童的学业表现。主观学业评价指标包含“语文成绩评价”和“数学成绩评价”两个变量。客观测试表现指标包含“词组测试得分”“数学测试得分”和“班级排名”三个变量。(4)自我期望,儿童自我期望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内容,具体包括自我职业期望、自我教育期望以及优秀程度自我评价三个变量,均为连续性变量。
3.主要中介变量:家长期望、家长参与、家庭关系、学校质量、教育机会
(1)家长期望,具体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和孩子的成绩分数期望两个方面。(2)家长参与,具体包括为孩子学习放弃看电视、常与孩子谈学校里的事、要求孩子完成作业、检查孩子作业四个变量。(3)家庭关系,具体包括“婚姻/同居”生活满意度、与配偶关系亲密度、家庭美满和睦程度三个变量。(4)学校质量,本部分主要参照了李忠路教授[11]的相关研究设计,依据CFPS 数据库,采用四个观测变量对学校质量这一潜变量进行测量:对学校的满意程度、对班主任的满意程度、对语文老师的满意程度以及对数学老师的满意程度。(5)教育机会,本文主要采用两个指标对教育机会进行测量:孩子是否参加辅导班、过去12 个月教育总支出的对数。
4.主要控制变量
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为省份、年级、就读阶段、性别、民族、城乡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由父母最高教育程度、父母最高职业威望以及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三个指标所构建的,并据此进一步划分了高社会经济地位与低社会经济地位两类。。对于儿童学业表现而言,省份与年级之间的差异是实质性的,学生学业成绩的比较在中国只有在同一省份、年级内进行才有实际意义。为了使学业成绩具有可比性,并基于对省份、年级控制的简洁性考量,本文通过对儿童学业成绩表现在内的主要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等进行省份与年级的分组标准化操作,以实现统计控制省份与年级的目的[11]。
本文研究的样本分布中,男生样本为54.0%,女生样本为46.0%;城市样本占42.0%,农村样本占58.0%;就读于小学阶段的儿童占60.0%,就读于初中阶段的儿童占40.0%;汉族的比例为87%,少数民族的比例为13.0%。表1 报告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2834
(三)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估计可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需要采取结构方程模型(SEM)来估计变量间的关系,所运用的分析软件为Amos26.0 与Stata17.0。基于上述理论模型与变量测量描述,本文对结构方程模型(包含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分别进行了具体设定,参见图2 至图5。潜变量和测量指标的对应关系请参照表1。

图2 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健康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M1)

图3 资产建设对儿童行为表现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M2)

图4 资产建设对儿童学业表现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M3)

图5 资产建设对儿童自我期望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M4)
上述模型中,除了依照上文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设定外,还假定了测量指标的误差项之间暂不存在相关性,个别测量指标的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届时同时根据具体模型修正指标与理论解释的合理性进行调整。当然,在模型的设定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均假设为线性关系,这也是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要求。另外,行为表现与学业表现所在的模型中,运用了高阶潜变量模型设定,分别用生活行为与学习行为两个潜变量估计行为表现,分别用客观测试表现与主观学业评价两个潜变量估计学业表现。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针对外生潜变量资产建设,本文还分别用广义的资产建设(标识为“资产建设”)、狭义的资产建设(标识为“资产建设1”)以及资产本身(标识为“资产建设2”)进行依次替换,进而在同一模型结构假定下比较资产效应理论与资产建设效应理论在儿童发展各个维度上的差异。
五、数据分析
(一)模型拟合度评价
模型的拟合度评价是解释测量模型和潜变量之间关系的前提,通常把绝对拟合度指标和相对拟合度指标看作模型拟合好坏的标准。绝对拟合优度指标包括规范性卡方值(CMIN/DF)、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拟合优度指标(GFI)和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标(AGFI)。其中,CMIN/DF 的值在1 至5 之间表示模型配适度很好,但在大样本研究中,参考意义不大;RMSEA 和SRMR 的值均要小于0.05;GFI 和AGFI 的值要大于0.9。规范化拟合优度指标(NFI)、非规范化拟合优度指标(NNFI/TLI)、增量适合度指标(IFI)和比较适合度指标(CFI)等相对拟合优度指标也可以用来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相对拟合度指标通常要求大于0.9,并且越接近1 代表模型的拟合度越好。
本文模型评价结果显示,在绝对拟合度指标中,12 个模型的CMIN/DF 的值均在1 至5 之间;RMSEA 和SRMR 的值均小于0.05;GFI 和AGFI的值均大于0.95;在相对拟合度指标中,12 个模型的各相对拟合度指标基本都大于0.9,仅模型M2、模型M2.1、模型M2.2 的NFI 和TLI 指标小于0.9,模型M3 和模型M3.1 的TLI 指标小于0.9,但这些模型的指标也均接近0.9。因此,综合各项模型拟合指标的结果来看,可以认为最终模型拟合效果很好。模型最终输出的拟合优度情况如表2 所示。

表2 结构模型适配度指标一览表 n=2834
(二)测量变量拟合情况
在资产建设—身心健康模型、资产建设—行为表现模型、资产建设—学业表现模型以及资产建设—自我期望模型的测量模型中,大多数因子载荷系数大于0.5,这说明可测变量具有较高效度,较好地测量了潜变量①“测量模型情况一览表(资产建设—儿童发展)”因表格较大,受篇幅所限没有列出,具体请向作者索要(sl_gaogj@ujn.edu.cn)。。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测量模型中,个别因子负载小于0.5,表明相应的指标测量存在着一定的瑕疵。比如“2010—2018 年是否为孩子教育存钱”“是否持有金融产品”“是否有住房出租”测量指标的因子负载均小于0.5,但是作为外生观测变量,因子载荷系数并不是反映该指标在多大程度上测量了家庭资产建设潜变量,而是表明2010—2018 年是否为孩子教育存钱、是否持有金融产品、是否有住房出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家庭资产建设潜变量,并且这三个测量指标也是本文理论解释所需要的,因此不是本研究聚焦的测量问题。
(三)资产建设影响儿童发展的路径分析
关于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发展、行为表现、学业表现和自我期望的影响各涉及三个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是广义资产建设(记为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发展、行为表现、学业表现和自我期望的影响模型(分别记为M1、M2、M3、M4),狭义资产建设(记为资产建设1)对儿童身心发展、行为表现、学业表现和自我期望的影响模型(分别记为M1.1、M2.1、M3.1、M4.1),以及家庭所有的资产财富本身(记为资产建设2)对儿童身心发展、行为表现、学业表现和自我期望的影响模型(分别记为M1.2、M2.2、M3.2、M4.2)。图6 至图17①图6 至图17 中路径系数标注*、**、***分别表明对应系数在0.05、0.01、0.001 水平上显著。和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影响的路径系数表②“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影响的路径系数”因表格较大,受篇幅所限没有列出,具体请向作者索要(sl_gaogj@ujn.edu.cn)。报告了结构模型M1、M1.1、M1.2、M2、M2.1、M2.2、M3、M3.1、M3.2、M4、M4.1、M4.2 潜变量之间关系的结构路径图、路径系数的检验结果及解释力。

图6 广义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发展影响的路径(M1)

图7 资产建设1 对儿童身心发展影响的路径(M1.1)

图8 资产建设2 对儿童身心发展影响的路径(M1.2)

图9 广义资产建设对儿童行为表现影响的路径(M2)

图10 资产建设1 对儿童行为表现影响的路径(M2.1)

图11 资产建设2 对儿童行为表现影响的路径(M2.2)

图12 广义资产建设对儿童学业表现影响的路径(M3)

图13 资产建设1 对儿童学业表现影响的路径(M3.1)

图14 资产建设2 对儿童学业表现影响的路径(M3.2)

图15 广义资产建设对儿童自我期望影响的路径(M4)

图16 资产建设1 对自我期望影响的路径(M4.1)

图17 资产建设2 对自我期望影响的路径(M4.2)
首先,从模型的解释力来看,(1)结构模型M1、M1.1、M1.2 分别解释了儿童身心健康差异的88.1%、90.1%、87.0%,均具有极高的解释力,其中核心解释变量广义资产建设、狭义资产建设以及家庭资产对儿童身心发展变异的解释力分别为57.3%、37.3%、51.9%,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2)结构模型M2、M2.1、M2.2 分别解释了儿童行为表现差异的29.7%、34.1%、29.0%,解释力均一般,其中核心解释变量广义资产建设、狭义资产建设以及家庭资产对儿童行为表现变异的解释力分别为0.23%、3.5%、0.006%,除了狭义资产建设外,广义资产建设与家庭资产本身对儿童行为表现差异的解释力可忽略不计。(3)结构模型M3、M3.1、M3.2 分别解释了儿童学业表现变异的96.4%、96.3%、97.0%,均具有极高的解释力,其中核心解释变量广义资产建设、狭义资产建设以及家庭资产对儿童身心发展变异的解释力分别为:4.9%、4.24%、7.8%。(4)结构模型M4、M4.1、M4.2分别解释了儿童自我期望变异的64.8%、65.0%、64.6%,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其中核心解释变量广义资产建设、狭义资产建设以及家庭资产对儿童自我期望变异的解释力分别为9.5%、8.9%、1.6%。
其次,从路径系数及其检验来看,(1)广义资产建设(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健康既具有直接的显著正效应,也通过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产生间接的显著正效应。狭义资产建设(资产建设1)对儿童身心健康不仅具有直接的显著正效应,而且通过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产生间接的显著正效应。(2)广义资产建设(资产建设)以及家庭资产本身(资产建设2)均对儿童行为表现不存在直接的显著性影响,而狭义的资产建设(资产建设1)则对儿童行为表现具有直接的显著负效应。这一方面可能主要反映了家庭的资产建设行为本身挤压了对儿童生活行为与学习行为培养所需要投入的大量时间与精力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反映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行为表现的负面影响。无独有偶,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习行为具有显著负效应(路径系数为-0.15)[11],尽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家庭资产建设变量有明显差异,但二者无疑具有较强的相关性。(3)广义资产建设(资产建设)、狭义资产建设(资产建设1)、家庭资产本身(资产建设2)均对儿童学业表现不存在直接的显著性影响,各自对儿童学业表现的显著性效应都是通过中介渠道实现的。(4)广义资产建设(资产建设)、狭义资产建设(资产建设1)、家庭资产本身(资产建设2)均对儿童自我期望既存在直接的显著性影响,也存在显著的间接影响。
再次,从具体影响路径来看,(1)值得强调的是,家庭资产本身(资产建设2)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不仅如此,在中介效应通道中,通过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是显著负效应。(2)虽然狭义资产建设(资产建设1)对儿童行为表现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广义资产建设(资产建设)、家庭资产本身(资产建设2)对儿童行为表现的直接效应不存在,但三个模型对行为表现的间接效应是存在的,均通过家庭关系、家长期望对儿童行为表现产生积极的正效应。(3)家庭资产建设对儿童学业表现的显著效应均是通过家庭关系、家长期望、教育机会、家长参与来实现的。需要注意的是,其中通过家庭关系、家长期望与教育机会中介渠道实现的是显著性正效应,而通过家长参与中介渠道实现的是显著负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家庭资产建设实质性影响到家长参与的方式与内容所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家长参与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模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不当的或过度的家长参与方式会对儿童尤其是对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儿童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进而影响学业表现。无独有偶,另一项利用学生调查数据所作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家长参与对儿童学业成绩表现具有显著负效应[42]。(4)就中介机制而言,资产建设主要通过家长期望对儿童自我期望产生显著正效应,家长参与、教育机会、教育质量中介通道均对儿童自我期望不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家庭关系对儿童自我期望具有显著负效应。
六、主要发现与相关讨论
本文试图在资产效应理论与资产建设效应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运用2018CFPS数据实证研究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主要维度的具体效应及其影响路径,进而检验资产效应理论与资产建设效应理论在解释儿童发展主要维度变异上的各自能力。本文主要研究发现概述如下:
第一,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健康、行为表现、学业成绩以及自我期望等儿童发展的关键维度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不仅如此,广义资产建设、狭义资产建设以及家庭资产本身对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也都具有显著正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资产效用理论与资产建设效应理论中“促进家庭稳定”“创造未来取向”“增进后代福利”等关键命题。
第二,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主要维度效应的具体路径存在显著的不同。具体而言,(1)广义资产建设与狭义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健康存在着直接的正效应,也通过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产生间接的正效应;(2)广义资产建设与资产建设本身对儿童行为表现不存在直接效应,主要是通过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对儿童行为表现产生间接的正效应,而狭义资产建设则不仅对儿童行为表现具有直接的正效应,而且也通过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对儿童行为表现产生间接的正效应;(3)无论是广义资产建设,还是狭义资产建设,抑或是家庭资产本身对儿童学业都不存在直接效应,而均是通过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对儿童学业表现产生影响;(4)广义资产建设、狭义资产建设以及家庭资产本身对儿童自我期望的影响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正效应,而且也通过家长期望对儿童自我期望产生正效应,但通过家长参与则对儿童自我期望产生显著负效应。
第三,就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健康、行为表现的效应而言,资产建设效应与资产效应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区分资产建设效应与资产效应是有效的。值得注意的是,广义资产建设与狭义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健康、行为表现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也通过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家长期望中介机制发挥积极效应;而家庭资产本身对儿童身心健康具有显著的直接负效应,不仅如此,在中介效应通道中,家庭关系、家长参与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是显著负效应。这说明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健康的积极效应主要是由狭义的资产建设行为所贡献的,所拥有的家庭资产本身并没有对儿童身心健康产生预期的积极效应,相反,还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另外,狭义资产建设尽管对儿童行为表现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在直接效应通道中具有显著负效应,而家庭资产本身对儿童行为表现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资产建设行为与资产本身对儿童身心健康、行为表现的效应差异(尤其是直接效应差异)验证了资产建设效应与资产效应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表明资产建设效应理论与资产效应理论在解释儿童行为表现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在解释儿童身心健康、行为表现方面具有显著不同的解释路径。就资产建设对儿童身心健康、行为表现的效应而言,有充分的理由区分资产建设效应与资产效应概念,进一步区分资产建设效应理论与资产效应理论。
最后,有如下几点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结构方程模型预设了各变量间的关系为线性,从实证结果来看,家长参与对儿童学业成绩的显著负效应很可能表明家长参与对儿童学业成绩的因果效应是非线性的。第二,通过截面数据探讨因果效应有自身的局限性。如何从截面观测数据中进行更精确的因果效应分析,接下来可进一步采取“Do演算”(Do-Caculus)、“反事实算法”(Counterfacual Agorithm)等“因果革命”(Causal Revolution)新思维、新思路、新方法进行相应演算与验证[43],继续深入探讨资产建设对儿童发展的具体效应。第三,对资产效应理论与资产建设效应理论的验证及其对儿童发展效应的探讨,应拓展到其他相应经验数据中展开,以求多方对比交叉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