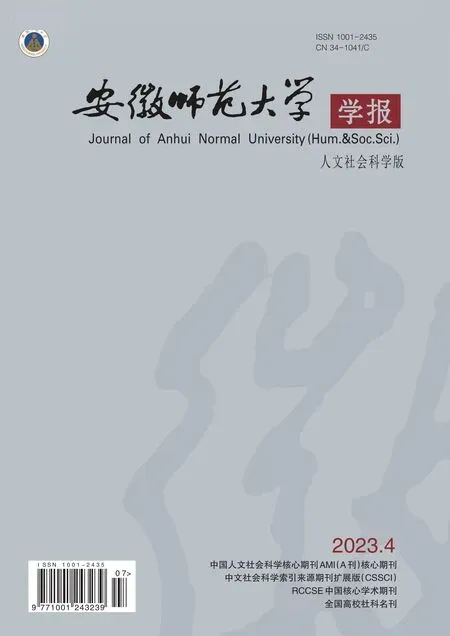方回诗学的“出位之思”新论*
郭庆财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太原030031)
方回是公认的江西诗派的护法和殿军,又对理学奉守始终,常以朱子后学自任。愈到晚年,方回对朱子的仰慕愈甚,认为即以诗论,朱子亦不逊于黄庭坚、陈师道等名家。他七十四岁所作的《夜读朱文公年谱》十二绝之一云:“澹庵老荐此诗人,屈道何妨可致身。负鼎干汤公岂肯,本来馀事压黄陈。”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71页。最后一句说,作诗对于朱子而言虽只是馀事,但仍较胜于黄、陈等辈。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朱子书与诗》条中引用了这首诗,对之批评甚厉:
虚谷(按:方回号)晚年俨以理学家自居,推江西诗学而排江西道学。洛闽真传,言之勿怍,集中又屡推朱子为乡前辈,故遂并涪翁、后山而不之屑矣。《律髓》屡言朱子诗学后山,得其三昧,而此处忽又将朱子压倒后山,真是兴到乱道。……文人而有出位之思,依傍门户,不敢从心所欲,势必至于进退失据。②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7-88页。
钱先生对方回的理学甚为不屑,在同一条中甚至认为方回“秽德彰闻,依托道学,其去《金莲记》中贾儒者几希”;而作为诗人又依傍朱学则是“出位之思”,这也造成了其诗论中的门户之见和前后抵牾,比如认为朱子的诗胜过黄、陈就有些“言不由衷”。总之,对渗入方回诗学的朱子之学,钱先生的评价是负面的、否定的。对钱先生的批评,我们需要略作辨析。
首先是方回的理学。方回故家在歙州紫阳山下,是朱子的旧籍,基于同乡关系他对朱子或有推尊过当处,但绝非钱先生所讽的“依托道学”的“贾儒者”。他十八岁时阅读真德秀的《读书甲记》等著作,系统学习性理,二十六岁时又师从徽州知州魏克愚(魏了翁之子),对朱学的造诣更深。③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91页。其晚年系统探讨朱子思想的篇章有《晦庵集钞序》《徽州路修学记》《润学重修大成殿记》《有有堂记》等,于朱子读书法、中和说、仁说等皆颇有心得,并非陈词滥调。此其一。其次是“本来馀事压黄陈”这句诗,是方回晚年的说法,笔者认为“黄、陈”二字不可死看,宜视为包括黄、陈在内的江西诗派。我们这里不对朱子诗与江西诗派分出轩轾,而是想考察方回由早年的推尊黄陈到这里的推尊朱子,是否体现了诗学观念的逻辑演进,而不是像钱先生那样仅斥之为“进退失据”。此其二。钱先生又指出,朱子学对于诗人方回而言属于“出位之思”,似乎是方回误入歧途而败坏了诗学,对此更须认真辨析。这涉及方回思想体系中朱子学与黄陈诗学能否相容相贯的问题,这也是方回诗学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此其三。
为此,本文将从“斯文”(方回的文化理想)、“格高”(方回的诗学理想)、“活法”(方回的学诗思想)三个角度,考察方回思想体系中的朱子学与黄陈诗学的动态关系,对钱先生的说法亦有所反思。
一、“斯文”理想中的朱子与黄、陈
钱先生一向秉持文学本位的立场,即注重辨析文学和道学的边界④参见钱钟书《说复古》一文(《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06页);以及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2页)。,对道学(亦即理学)向无好感,因而对方回的诗学相对缺乏同情之理解。方回并非一位纯粹的诗人,他身为江西诗派护法又自居为朱子后学,与其说是“出位之思”,不如说是基于一种弘大的文化意识,即对宋代文化的坚守和继承,尤其是宋亡元兴、宋文化中衰背景下对“斯文”的继承意识。
“天丧斯文”是宋末士人的常见论调,如深受理学和家学影响的刘将孙,以及深受方回影响的陈栎、张之翰、袁桷均好称“斯文”,表达了“斯文”不与政权俱亡的心愿。⑤如刘将孙:“斯文之得丧,天也。”(《瞿梧集序》,《养吾斋集》卷十)张之翰:“斯文仅如线,愈久则愈衰。”(《鄙诗奉饯墅斋学士移疾归东平》,《西岩集》卷一)袁桷:“斯文剥丧余数十年。”(《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方回更把宋文化的衰落追溯至庆元党禁以来,其表现有二:一是朱学失传以及理学的衰落和俗化,理学失去了批判色彩而沦为抽象的教条和高调的真理,方回指出,“晦庵老寿,不究其用,乃有伪党之祸。及三大儒(按:指朱子、吕祖谦、张栻)皆沦谢,……假道于是者,以剽窃哗世取宠而行不至,微言绝大义乖,孰有能振斯文而起之者乎?”①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74页。对理学的世俗化和教条化感慨系之。二是江湖诗派的大盛。诗派中人多为江湖游士,经常伏谒于权门,以诗为荣身之具,甚至以诗为商品去讨生活,难免受到正统士人的非议。从诗风而言,他们作诗大多效法晚唐的许浑、姚合,诗风琐细、柔靡、熟套,一言以蔽之即“格卑”。诗格的卑下说到底乃源于人格的卑琐,其“工”“丽”诗风则是媚俗型人格的外在反映。方回对此指斥颇多,比如:
炎祚将讫,天丧斯文,嘉定中忽有祖许浑、姚合为派者,五七言古体并不能为,不读书亦作诗,曰学四灵,江湖晚生皆是也。呜呼痛哉!②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136页。
值得注意的是,方回论及道学的俗化和江湖诗派的盛行时均用了“斯文”一词,隐含了“斯文不传”的忧虑,将文人才士的心术蛊坏归为宋代儒学文化的沦落。相反,程朱理学和黄、陈诗学皆是“斯文”的重要内容,是宋代文化中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如果说江湖诗学和理学末流的弊病在“俗”,而朱子学和黄陈诗学的共同品质即在“不俗”,是对当下庸俗世态、诗风的对治;进而言之,两者不仅最重统绪和“学法”,而且大体同源、同步、同道,因此成为最重要的“斯文”载体。
首先,就统绪来说,不论朱子学还是黄、陈诗学,皆流脉绵远,均可溯源至上古三代。方回不但把朱子视为周敦颐以来的道统“七君子”之一③方回《览古五首》之五:“弥缝救破断,谁实心斯传。始以营道翁,终之紫阳仙。堂堂七君子,如日常在天。”(《全元诗》第6册,第157页),且认为朱子学是通向尧舜、孔子之道的不二之途:“学尧舜者必自孔子,学孔子者必自朱子。”④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322页。论及江西诗派,方回也有一个类似的“诗统”谱系:“雅衰风息离骚降,迩来此道尤荆榛。少陵一老擅古今,学所从入须黄陈。”⑤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第264页。“上饶自南渡以来,寓公曾茶山得吕紫微诗法,传至嘉定中赵章泉、韩涧泉,正脉不绝。”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第272页。综合方回的诗统说,江西诗派的传续脉络为:杜甫→黄庭坚→陈师道→吕本中→曾几→赵章泉、韩涧泉,而其远源则是《诗经》的风雅正音。他将此诗统称为“正脉”。三代的风雅传统和周孔传统是“斯文”之源,而江西诗学和程朱理学均为“斯文”正统。
其次,就时势来说,程、朱理学与黄、陈诗学的兴衰是基本同步的,两者的兴盛在北宋元祐至南宋乾、淳之间,衰落则在南宋嘉定、绍定之后,且与国运密切相关。元祐是北宋文治昌明的时代,乾、淳则是宋文化的中兴时期。而延至南宋嘉、绍时期,一方面是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等奸臣柄命,浊乱天下,一方面是江湖诗风盛行,文丐奔竞,共同造成了“斯文”的中断衰落,方回诗云:“乾淳以后学无师,嘉绍厌厌士气衰。何等淫辞《南岳稿》,不祥妖谶晚唐诗。三风盍遣郑声放,一日忽惊周鼎移。”⑦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第325页。甚至将刘克庄的“晚唐”诗风视为郑卫之音,是亡国的先兆;宋元鼎革更将国运与“斯文”一起斩断,故方回对“斯文”的思考尤为沉痛。他以一种综合融贯的文化视角,寄望于朱子学与江西诗学的融会共生,是对“斯文”的接续和弥缝。
就程、朱义理之学和黄、陈诗学而言,方回又是有所偏重的,“义理之学”才是“斯文”的根基。他说,汉唐以来的传注、古文、词赋、制度考究等学问,“虽各自名家,而求其言之合于义理,号为知道君子,则鲜其人”。“今之为士者一切不讲,惟诗辞之学仅存。予朱子之乡晩出者也,仕而归老,去朱子之没未百年,求所谓义理之学者不一见焉”。⑧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124页。这里所说的衰敝的“诗辞之学”所指有二:首先当然包括江湖诗学;此外,宋末的江西诗学末流,也与义理之学愈发疏离和隔膜。如江西诗派的后期代表赵蕃本为刘清之门人,并从朱子问学,但朱子“与语道理,如水投石”⑨[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3页。;与赵蕃齐名的韩淲也已浸染了晚唐格调①参见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1页。。再如方回所推崇的江西诗派后学张良臣,反倒成为晚唐诗风的代表②参见祝尚书:《张良臣及其“晚唐”律绝》,《文学遗产》2021年第1期。。相反,程朱理学一系的义理之学,以“学为人而求见道”为最终诉求,乃是复兴宋文化的基础。它虽然排斥单纯的诗艺追求,但在人格修养方面的探索和对庸俗士风的鄙弃,成为滋养诗人心灵的重要源泉,也会增加诗歌的深度和厚度。此前,叶适、刘克庄等人对理学末流颇有非议,斥之为“洛学兴而文字坏”③[宋]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49页。,将文学的衰落归咎于理学,但方回恰恰相反,他认为“文字坏”的原因恰在于诗人们割弃了义理之学,而专骛于“诗词之学”。鉴于江湖诗派“组丽浮华”、溺华忘实,“义理之学”对江湖诗派乃至没落的江西诗派均有针砭意义。
总之,“斯文”观是一种宽广的文化视阈,既有现实批判色彩,也表现出文化传承和整合的意识,肯定了江西诗学与朱子理学在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朱子学所承的周孔之道,还是江西诗学延续的风雅传统,共同的精神简言之即是“不俗”,且与卑俗的士风相对,尤其是程朱所代表的义理之学,在宋元之际士风不竞的时势下更是改造人心、复兴“斯文”的基础。
二、“格高”说中的朱子与黄、陈
一般讲方回诗学思想,绕不开的是其“格高”思想,方回认为“夫诗莫贵于格高”④[元]方回撰,李庆甲汇评:《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50页。,又说:“诗以格高为第一。”⑤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134页。对于方回“格高”说的内涵和渊源,学者已有较多讨论,查洪德先生更由唐宋人“以格论诗”的先例探究其渊源⑥参见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附录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7-490页。。笔者则认为,虽然唐宋人的“以格论诗”可能是方回“格高”说的源头,但格高作为诗品、人品所共具的“不俗”品格,乃是方回“斯文”理想的题中之义,其直接渊源则是黄陈江西诗学和朱子理学。我们先从方回论“格高”的文字看起:
予乃创为格高、格卑之论何也?曰:此为近世之诗人言之也。予于晋独推陶彭泽一人格高,足方嵇、阮;唐惟陈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刘禹锡、韦应物;宋惟欧、梅、黄、陈、苏长公、张文潜,而又于其中以四人为格之尤高者:鲁直、无己,上配渊明、子美为四也。⑦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134页。陶渊明、杜甫、黄庭坚、陈师道四者诗风各自不同,或“自然质朴”“诗体浑大”,或“瘦硬枯劲”“恢张悲壮”,均被方回视为“格之尤高”者,说明“格”并不限于某一种风格,但均有端正、不俗的品性。
首先,“格”应是基于用字、句法、意象等形式因素,又超越了具体形式的美学品格,“格高”实以“不丽”“不工”为特点,或说是对“工”“丽”等世俗审美趣味的超越。如从句法方面而言,方回反对刻意对偶;若从用字来说,方回主张于助词或虚词多加考究;从情景关系而言,方回反对刻意摹画景物,而主张以情意为主;就风格而言,“格高”之诗又以瘦硬枯劲和自然平淡两种风格为主,而这正是江西诗派的主导诗风。对此学者多所论列,无须详述。
其次,“诗格”是由作者的“人格”之所显发和决定的。人之“格”主要包括创作者的品格、识见和胸襟,尤以儒学之“道”为根基且修养深醇所致。方回论陶诗:“不纯乎天理,公论不尽;不拔乎流俗,人品不高。……必知此者,始可与语渊明之诗也欤!”⑧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76页。又评价江淹、韦应物,认为他们学陶仅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关键在“人格”之不同:“江淹为人,又岂可望陶之万一哉!”韦应物“本富贵宦达之人,燕寝兵卫,岂真陶乎?”①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260-261页。“天理”“人品”云云,蕴含了儒学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它超越了形式乃至风格层面,而关乎儒者的出处进退大节,成为宋元士人精神风貌的表征和价值论的内涵。
就以上两个层面而言,江西诗派和朱子学为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两者在儒者之“道”的层面上大体一致:人格、人品、襟怀,说到底都源自对“道”的学习和体悟,学者学为人、学作诗,都是“学以明道”的行为。理学固然是“道学”,江西诗学则“诗”与“道”兼修,如黄庭坚就并不以单纯的文人自居,终其一生都对道德涵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曾对理学宗师周敦颐“光风霁月”般的人格推重备极,且有着匡正世道人心的强烈使命感。陈师道对俗学、俗文的厌恶和至死不渝的凛然之操均有似于黄庭坚。此外,曾几、吕本中、赵蕃皆为道学弟子,又卓然于诗。②比如吕本中之学“本之家庭,而遍叩游、杨、尹诸老之门,亦尝见元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宋元学案·紫微学案》,第1241页)曾几为胡安国门人,其著名的《答胡文定书》于天理人欲之说颇有心得。赵蕃为刘清之门人,且从朱子请益。《宋元学案》称:“乾、淳间……学道而工诗者惟先生(赵蕃)。”(《宋元学案·清江学案》卷五十九,第1945页)从理论表述来看,江西诗人和朱子都多以根本和枝叶为喻来论文道关系,强调诗人胸襟、人格、操行对写作诗文具有根本意义。黄庭坚说:“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闳深矣。”③[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第702页。“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飘摇。”④[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第704页。这种修养主要指养治心性的功夫,以读书为重要法门:“岷山之水滥觞,及其成江,横绝吴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源本故也。学而知本者,盖可以求师友于书册矣。”⑤[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第717页。黄庭坚所说的读书包括经史著作和先贤诗作,长期阅读对自我性情和文学才华自会有所启沃,人和诗文的品格也都会有所提高。朱子亦然,而且他的根本枝叶论更为明确:“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⑥[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319页。这里的“文”当然也包括了诗在内。落实到作家本人,诗文应该是从作者的性情中流出:“有那情性,方有那词气声音。”⑦[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626页。他又说:
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⑧[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319页。这段话的基本理路和黄庭坚一样,都是“读书→心灵→诗文”学诗进路,读书以滋养此心,涵育自我的性情和品格,此为“诗格”的基础,因此也可简化为“为人→为诗”两重。方回“格高”说的两个层面与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不过,黄庭坚作为著名诗人,其修养论与其说以“道”为最终目的,毋宁说是以“诗”为目的。上引黄庭坚的根本、枝叶论,意谓修养心性以深其根本,其最终目的在诗文之高明。这种逻辑和朱熹“诗文道流”的说法是相反的。在黄庭坚等江西前辈那里,用力于诗歌的句法、意脉、字眼,与儒学品格修养之间是并行的,两者虽统一于“不俗”,但道德追求和艺术追求毕竟是二元关系。相比之下,朱子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一元论”由早期儒学的“伦理”“义理”而上达于精微的“性理”,并提供了“学以致道”的具体方法,仅读书法即可归结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条⑨[明]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14页。,都远较黄庭坚细密。在此基础上,朱子以本末、体用、内外论道与文的关系,可谓极深研几;由心性存养外发为诗文,自然格调高远,显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高度圆融。这不但为方回诗学提供了本体论的视野,进而影响到方回对诗学主体品格的强调。
综上,朱子诗学与江西诗学均以“道”为根源,诗人的品格、节操、胸襟也是“诗格”的根本,这是方回“格高”理想的渊源和思想内核。不过,“学道”与“学诗”两者是并行关系还是体用关系,何者才是诗人努力的重心,乃是朱子学和江西诗学的分歧所在。比较而言,方回自青少年时即受朱子学的影响,其影响远大于黄、陈;随着他对朱子读书法、中和说、太极说等思想愈有心得,其诗学重心也逐渐下移至“道理”和人格心性层面,其论诗有云:“反求乎根柢之所在,而无徒掇拾菁英以事其外焉。”①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78页。他又认为相较于诗歌的音韵、典故、语料等内容,“心之所主有高于此者,贵乎见之一,守之一”。②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150页。这些言论均有重内轻外、重道轻法之意。他论江西诗学,也更突出其“道理”和“心灵”层面,而淡化其“技”“法”的色彩,意在将诗派拉回到人格本位上来,从而营造一种健康而深刻的诗歌路径。
三、“活法”说中的朱子与黄、陈
明确了方回“格高”说的思想渊源后,须进一步探究的是如何达致“格高”,即如何“学诗”的问题。既然“格高”包括了“诗格”与“人格”,相应地,学诗亦应内外并进:一是诗歌句法、字眼、意脉方面的学习锻炼以致不俗,二是学诗者心性修养和胸襟识见的不俗。两者均可归结为一个“活”字。前者指句法方面的突破常规,不主故常,此为诗歌的形式之“活”,后者指向作者心灵之“活”;前者与江西诗派的“不俗”追求具有一致性,后者则体现了方回对江西诗法的超越,乃深受朱子理学思想的影响。
首先是江西诗法之“活”,即一种变化不常、圆活流转的诗学追求,主要体现在方回作于中年的《瀛奎律髓》中,其中所设的“变体”一类尤为典型。“变体”与精巧匀称的“常体”相对,包含了情景、物我、轻重、虚实的错综互换,也突破了江湖诗人周弼宣称的“四实四虚”的格套。江西派诗人是“变体”的楷模,他评黄山谷:“变之又变,在律诗中神动鬼飞,不可测也。”③[元]方回撰,李庆甲汇评:《瀛奎律髓汇评》,第1144页。评曾几:“盖斡旋变化之妙。”④[元]方回撰,李庆甲汇评:《瀛奎律髓汇评》,第1169页。评赵蕃:“江西苦于丽而冗,章泉得其法能瘦,能淡,能不拘对,又能变化而活动,此诗是也。”⑤[元]方回撰,李庆甲汇评:《瀛奎律髓汇评》,第386页。拘于格套则难免卑俗;以意为主而变化不常则通于格高。这种“变体”即是一种“活法”,尤其是黄、陈等人的造句谋篇本无一定之规,活化流转,乃是源于诗人的“心胸气力”:
此等诗不丽不工,瘦硬枯劲,一斡万钧,惟山谷、后山、简斋得此活法,又各以其数万卷之心胸气力鼓舞跳荡。初学晚生不深于诗而骤读之,则不见奥妙,不知隽永。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第125页。“心胸气力”,也即胸襟、学养、识见等心理内容。但问题是如何涵养得此“心胸气力”?黄庭坚等江西前辈虽有论述,但并不详明,他们的一些说法如“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⑦[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8页。“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⑧[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第56页。“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⑨[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第592页。等等,均容易让人忽略“读书→心灵→诗文”中的“心灵”一环。其实,句法的“工”或“不工”均属纸上工夫,算不得真正的“活法”;作者的心灵才是最大的变量。每论诗到此,方回必祈灵于儒学的心性论,因为这才是其诗学的生命和源泉。他晚年曾说:“吾儒之学上穷性理,下缀诗文,必得活法。”⑩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305页。
把儒者的性理和诗文联系起来讲“活法”,乃得力于朱子学的沾溉。作为格物之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朱子读书法的目的在发现天赋的性理,以德盛仁熟为旨归,“活”则是将道理体验纯熟后的心灵状态:
凡人看文字,初看时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见得未定,犹没奈他何。到看得定时,方入规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说相似,都不活,不活则受用不得。须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后,方始会活,方始会动,方有得有受用处。①[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78页。 [宋]吕本中撰,韩酉山辑校:《吕本中全集》,第1360页。读书若不能浃洽自得,则所得知识、道理只是死板的教条;而熟读浸渍,终至心与理一,理成为活的理,此心亦臻于活泼泼之境。因此读书不仅仅是求知,也是治心养性之法。朱子诗文中所谓的“水到船浮”②[宋]朱熹撰,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4页。“此日中流自在行”③[宋]朱熹撰,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第90页。云云,就是对此“活泼泼”心灵的隐喻。而且,朱子晚年好以“言志”论诗,“志”以正大的圣贤人格和道理为目标,“志”发为诗,是从心中自然流出,这个过程亦是“活泼泼地”。朱子《答杨宋卿》云:“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④[宋]朱熹撰,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第1757页。意思是说“志”有高下,学者应志于光明正大的道理;诗以言志为本,是心灵内容的自然外发,朱子称为“真味发溢”⑤[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333页。,工拙并非关键,反倒是专意于诗、计较工拙往往妨碍了为学工夫,才是理学家的大忌。方回晚年论诗亦好称“言志”,所秉持的亦是由格物积学而自然外发的路径:“古圣人作,民有康衢之谣,君有歌,臣有赓,皆所以言其志,而天机之不能自已者也。”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81页。
以“活法”说诗并不新鲜,出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赵蕃乃至杨万里等人对此均津津乐道,其中尤以吕本中的“活法”说影响最大。针对江西后学斤斤于规矩而不知变化创新的弊病,吕本中亦曾有过批评:“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⑦[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第333页。他用“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来讲“活法”,主要是指“有意于文者之法”⑧[宋]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第4030-4031页。,重点是关于用字造句方面的问题⑨参见顾易生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南宋诗文批评”部分第二节《吕本中》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其所谓“胸中尘埃去,渐喜诗语活”⑩[宋]吕本中撰,韩酉山辑校:《吕本中全集》,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304页。“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⑪[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78页。 [宋]吕本中撰,韩酉山辑校:《吕本中全集》,第1360页。的说法,也只是指此心的神明变化,属于心灵的作用而非心性本体,并无关乎道德属性。另外,如何掌握“活法”,他和韩驹、曾几、杨万里等人均好言“悟”,周必大也说“诚斋万事悟活法”⑫[宋]周必大撰,王瑞来校正:《周必大集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614页。,实则掺入了禅学而太过玄虚。但方回的“活法”则明确以性理之学为根基,显得端正而稳实,且体用圆融:一者朱子学提供了由格物积学而“活”的为学路径,故有径可循;二者“理”作为心之主宰,乃是心灵活动的道德依据,故“活”而无偏;三者此心体认到天理流行,亦洒落活泼,故有鸢飞鱼跃之高致,对诗人的构思和抒情均是一种解放。所以方回关于“学诗”之“活法”,仍是对江西诗学与朱子学的融会。他那里既有浅层次的句法之“活”,又有更深层面的心灵之“活法”,其诗学思路是由“用”而探“本”,由“纸上之活法”透至“胸中之活法”。⑬参见[宋]俞成《萤雪丛说》(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上“文章活法”条,有“纸上之活法”与“胸中之活法”的分别。故其着力点不在诗法技巧,而是转向了创作主体的心性。作诗求变只是表象,根本在于心灵的真正启悟,后者乃有赖于格物积学的长期工夫。这些都是方回吸纳了朱子学而对江西诗学品格的提升。
以上方回的“斯文”说、“格高”说、“活法”说,均体现了其对朱子理学与江西诗学的融合,也是我们深入理解方回诗学精神的三条入路。首先,方回持守的“斯文”理想,包括了江西诗学和义理之学,而以后者为根本;其次,方回诗学的“格高”理想,包含了“诗格”与“人格”,而以人格为根本;其三,方回学诗的“活法”路径,包括句法之变和心灵之活,乃以“心活”为根本。以上三对关系中,义理之学、人格之高、心灵之活均以朱子学为最终根源。这使方回于江西诸子与朱子之间不能不有所偏倚,就其整个体用兼备的思想体系而言,朱子的地位当然根深蒂固。
四、朱子学与方回晚年诗作风貌的变化
我们再从方回的诗作考察一下:在江西诗风与朱子诗学之间,其诗风有无畸轻畸重的变化。大致而言,江西诗派和朱子在为诗方面有艰苦和自然之别。江西诗派往往将创作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推敲锻炼、尚奇尚难的阶段,二是技法纯熟乃至豁然贯通后的自然平淡阶段,这是一条由艰难而至于平易之途。不过黄庭坚多留意于前者,诗作至晚年亦未真正达到自然平淡之境。①参见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陈师道的苦吟则更为人熟知。率意为诗容易流于“俗”,而苦思锻炼则是“免俗”的重要保证。朱子则不然,他一向认为高明的诗歌应从胸中自然流出:“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②[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328页。因此对黄庭坚的诗多有訾议,“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谓巧好无余,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诗较自在,山谷则刻意为之”。③[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329页。为诗乃是“学道”之馀事,或者说“学道”之法就是学诗之法,不必分出精力专门学诗,他还说过“作文何必苦留意”④[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3321页。的话,这里的“文”当然也包括了诗。用力于诗是舍本逐末,反倒会分了为学工夫。
受到朱子“活法”的影响,方回晚年的诗学观念、诗风均有过重要调整,其六十二岁时曾反省此前“所作诗滞碍排比,有模临法帖之病”,于是“翻然弃旧从新,信笔肆口,得则书之,不得亦不苦思而力索也”。而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读书致知,他将读书的路径总结为“五经一圣之言以为律令,九贤之言以为格式”⑤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120页。。“九贤”,即周代的颜、曾、思、孟,宋代的周、张、二程、朱子,朱子更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同篇文章中他又指出:“既而亦于子朱子有得,追谢尾陶,拟康乐,和渊明,亦颇近矣。”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7册,第122页。
与朱子理学趣味最近的乃是陶诗,朱子既推崇陶渊明的人品,亦崇尚其诗作⑦参见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四编第三节《理学家与陶渊明典范地位的确立》,齐鲁书社2002年版。,而崇陶也是方回晚年的重要诗学取向。其晚年有诗云:“崛强轮囷谓绝奇,刮摩剔抉更多疑。彭门峻步勤除道,栗里高风晚得师。乃后容赊十年死,定应全废一生诗。”⑧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第141页。“栗里”是陶渊明的故乡,方回说自己晚年方悟到陶诗的高明,颇有悔其少作之意。“崛强轮囷”“刮摩剔抉”即太过于刻意,隐然指向自己早年所归依的江西诗学,而后期心态变得从容和平,诗风趋于平易淡然,暗合了陶诗的风味。如《七十翁吟五言古体十首(其一)》寄寓了深沉的人生感喟,既哀叹治生乏术又有君子固穷的坚守,诗风浅易,颇有陶诗格调:
无妻牧犊子,带索荣启期。予亦年七十,幸犹未至兹。颇亦似陶翁,粗有五男儿。乃父休官早,致汝恒苦饥。挂冠六七闰,方当挂冠时。治生了无策,惟耽酒与诗。室人愧交讁,虽寿夫奚为。后死信无益,固穷谅何悲。⑨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第403页。
当然,对朱子本人的诗风亦应饱参熟味。方回晚年的《诗思十首》之九专拈朱子诗:“生年同孔氏,传道仰文公。烂却沙头月,谁参到此中。”①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第541页。“烂却沙头月一船”本是朱子的诗句,诗思深远,颇有大道不行、闭门待尽的无奈,后世诗人却鲜能体会其道理和深致,方回不禁感慨系之。但以上仅止于朱子诗思和诗风的影响,其实朱子学包含的“活”的精神对方回诗学的影响更大,主要指心灵的活泼而满蕴生机,以及诗歌的意味舒徐。方回现存诗作均为五十七岁解职以后所作,从体裁来看,古体诗较之律诗更多,且大多写放荡湖山之间的生活情态,多以“偶书”“杂兴”“即事”“排闷”为题,此外写雨、春景、午睡的诗均明白如话,很难见到方回自谓“虚翁亦嗜诗,瘦骨枯崚嶒”②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第154页。的风貌,和江西诗派瘦硬枯劲的典型诗风亦不相似。相较来说,学江西则难免摹其形迹,诗风略似;由朱子所获致的是心灵的透脱,发于诗作,则未必专似朱子。比如方回的“直到全无马粪处,山僮竹箒扫松钗”(《三竺道中》之二)“不如斟月入杯中,诗酒肠吸杯月空”“山头拏月月愈远,尘里抉诗诗不出”(《俞鉴山月歌》)等诗句中也显然能看到苏轼、杨万里等人的影子。可见他晚年并不拘于江西门户,涵纳众家,但更崇尚自然平易的诗风。
综上,方回的“格高”“活法”说均是整合了江西诗学和朱子诗学的思想资源,而由于强调“人格”“心性”对诗歌的始基作用,以及儒学的浸渍和读书自得,朱子学成为方回诗学中越发浓重的底色,也影响到方回学诗的“内转”趋向:从苦思锻炼达到“不俗”,不如修养心性以达致“不俗”——前者是黄陈诗法,后者乃是朱子诗法。明乎此,再来看方回晚年评朱子时所说的“本来馀事压黄陈”亦并非奇怪,无论从诗风的自然高明而言,还是格高不俗而言,认为朱子较胜于黄、陈,乃是方回诗学发展的自然逻辑,并不像钱先生所说的,是方回的“言不由衷”。
五、结 语
钱钟书先生一向坚持文学本位和艺术审美的标准,对方回的诗学背后的文化融合视野、体用思想较缺乏同情之理解,故指方回诗学为“出位之思”“倚傍门户”,这都是欠公允的。我们认为方回晚年确实对朱子学的体悟更深,且以朱子学为思想坐标,充实和改造了没落的江西诗学。从风格而言,方回本来和黄庭坚一样,强调“平易中寓艰苦”,晚年则从原来讲求“艰苦”“推敲”转向了平易自然,而“自然”“平淡”恰是江西诗派的最终诗学旨归,只不过黄、陈是由琢磨锻炼而臻于自然,朱子则由心性的涵养中和而臻于自然,两者在“格高”“不俗”方面可谓殊途同归。方回晚年受朱子影响更大,他凭借朱子学的助力,在把江西诗派更加理学化的同时,也将没落的江西诗学激活了。
钱先生一向反感宋代理学家和他们的诗,甚至认为“有时简直不是诗”③钱钟书选注:《宋诗选注》,第152页。。其《宋诗选注》中理学家的诗只选了刘子翚一人,连朱子之诗都没有选入;对深受朱子影响的方回晚年诗作则评价更低:“其六十前诗不可得见,然六十后遽败坏至此,则早年拟议临摹之未有真得,可知而已。卷二十七《赠叶宗贵一山》自负近诗‘颇通大道合自然,拙朴有馀巧不足’,吾睹其拙而滑矣,未睹其朴也。”④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2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4-195页。不可否认方回后期确有少数枯燥的诗作⑤如《送家自昭慈湖山长》《哭鲍景翔鲁斋》《题祝公辅静得斋》等诗,多为理学思想的阐发,诗风较枯燥。,但“拙”或有之,朴率自然之作更多,“滑”则绝少,浮滑率易之风与方回标榜的“格高”截然相反,方回是始终持以为戒的。其晚年诗“退为平易”,但并没有流于率易,琢磨推敲的功夫当然是不可少的,他曾说自己晚年诗作“中有阆仙之敲而人不识也”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7册,第514页。。钱先生对方回后期诗风的评价难免包含了一定的偏见。如上所述,方回所盛推的江西诗学和朱子诗学均含有程度不同的性理思想,方回对此的深刻体认非但没有造成诗学的偏狭,反倒启发自己摆脱了门户之见,在诗思和诗风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对此我们应作出公允的评价。
——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