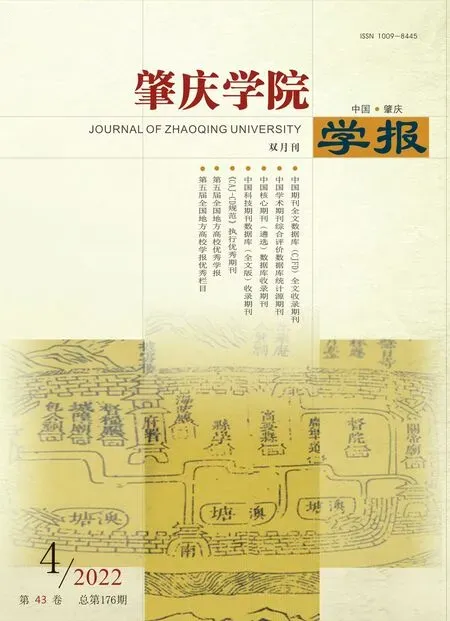关于刑法中盗窃行为的概念分析
李居全
(肇庆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肇庆526061)
近几年来,在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盗窃行为方式的秘密性与公开性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争论的焦点也很多。本文鉴于篇幅有限,不全面讨论各个焦点问题,仅从盗窃行为概念这一个角度进行分析,以与学界同仁商榷。
一、概念的意义
(一)概念的统一性对于人类交流的意义
人是社会动物,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人与人之间必须展开协作。而协作只能建立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之上。交流的本质是信息的传递。信息是人的大脑对于客观对象的描述,是由各种相关概念所构成的。
概念是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反映,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先形成对该客观事物的概念,然后再通过对概念的运用来进行判断和推理。“概念是思维机体的细胞,是思维最基本的形式,因此,思维对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就只能在形成概念的基础上来进行。”[1]概念之所以是思维机体的细胞,是因为概念具有分类的功能,它是人脑将复杂而又笼统的客观世界,划分成若干类的客观存在物。一个概念的外延所囊括的客观事物,就是这个概念从完整的客观世界中切割出来的一个类,即概念的对象物。概念的这一分类功能,正是信息传递的基础。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不可能是整体进行的,只能是从局部开始逐渐进行,因而交流的内容也不是以整个客观世界为对象,而只是以经过概念分类后的某个局部的、具体的事物为对象,也就是某个具体的概念所反映的对象。人类就某个客观对象所进行的交流,只有通过相互传递与该对象相关的概念信息才得以实现。然而有效的概念信息交流的前提,必须是主体之间各概念的同一性,即各概念必须具有相同的外延——各参与交流的主体大脑中的同一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必须相同。
法律是社会主体即公民的行为规范,其调整对象是普通公民的行为,而不只是法学专家的行为。法律的制定与颁布,其实也是一种交流,是立法者与公民之间的交流[2],尤其是在法治社会里,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立法者必须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告诉公民什么事能为,什么事不能为。法律既然是立法者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交流,那么立法者在法律中所使用的概念与社会普通公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概念,必须是相统一的,否则立法者就不能将其意志传递给公民,法律也就会失去法律的意义。
(二)不同语系人群之间的概念差异
在不同的人类群体中,因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的经历不同,其概念对于客观对象的划分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长度”这个概念,在社会历史实践中英语人群将长度划分为英尺、英寸等概念,而汉语人群则将其划分为市尺、市寸等概念。一个英国人与一个中国人就长度问题进行交流,要么都使用英制单位,要么都使用市制单位,否则双方无法进行交流。
概念,作为大脑对客观对象的反映,自身是不具备传递能力的,一个人大脑的想法是不可能自己跑到另一人的大脑里去的,它必须借助一种形式或者媒介才能传递,而这种形式或者媒介就是语词。语词是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3],也是人类交流过程中概念信息的载体。大脑对客观对象的反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概念的差异通常也表现为语词意思上的差别。从一门语言中的外来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语言人群中的概念发展是不平衡的。之所以使用外来语,是因为本语言中本身没有该词汇,因而也没有该词汇所表达的概念。例如,英文中的“romantic”(浪漫,罗曼蒂克)[4]779,860,汉语中本来是没有的,而之所以没有,是因为我们不曾有“浪漫”这个概念。再比如说“功夫”这个概念及其语词,在英语人群中原本也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在做比较研究的时候,不能忽略不同语言中的语词差异。
“盗窃”,在我国普通公民的意识中,就是“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4]268,不管我们对于“秘密”做何解释,“自己认为秘密”也好,“他人认为秘密”也好,但绝不可能将其解释为“以公开方式”,因为“秘密”与“公开”作为概念它们是矛盾关系,作为语词它们互为反义词。然而,汉语中的这种“盗窃”概念,在其他语系中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本文将在第二部分详细论述。
二、“盗窃”概念比较研究
夏勇教授说:“没有一部刑法不规定盗窃(窃盗、偷窃、偷盗)罪”[5]。这话未免说得太绝对了,至少不够严谨。严格地说,英美法系刑法中基本没有规定“盗窃(窃盗、偷窃、偷盗)罪”,德国刑法中也没有规定。
英美法系刑法中没有规定“盗窃罪”,主要是因为在英语中几乎就没有“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这一“盗窃”概念①在英语口语中,人们有时会用sneak或nick来表达“盗窃”的意思,但他们都不是正式用语。。如前所述,语词是概念的载体,首先,我们来看看与汉语中“盗窃”概念最接近的几个英文单词。第一个,Larceny,准确意思是“以据为己用为目的将他人的财物取走且情节严重”的行为②“The felonious taking and carrying away of the personal goods of another with intent to convert them to the taker's use.”参见语言学会编辑的《牛津英语词典》第6卷L-M(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VI L-M),牛津大学出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年版,第71页。,完全不涉及“秘密”方式问题;第二个,Theft,意义是“将他人的财物拿走且情节严重”的行为③“The felonious taking away of the personal goods of another.”参见语言学会编辑的《牛津英语词典》第11卷T-U(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VI L-M),牛津大学出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年版,第265页。,与Larceny一样不涉及“秘密”方式问题;第三个,Steal,意义是“不诚实地或者秘密地拿”④“To take dishonestly or secretly.”参见语言学会编辑的《牛津英语词典》第10 卷Sole-Sz(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ume V Sole-Sz),牛津大学出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3年版,第884页。,“或者”是选择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是“不诚实”即使是非秘密地拿也属于Steal,因此,它与汉语中纯“秘密地取得”这一“盗窃”概念的外延是不同的。然而在英汉词典中,无论是Steal还是Larceny抑或Theft,都被译成为“盗窃”。正是我国翻译家们的这个不严谨的翻译,导致了我国刑法学者们的误解,误以为英美法系中也有盗窃罪;误以为在英美法系中“‘秘密性’并不成其为盗窃罪的一个问题”[5]。
基于以上英语语境,英美法系的刑法中不可能有“盗窃罪”。英国刑法中通常被我们翻译成“盗窃罪”的犯罪实际上是Theft(侵占罪)。英国1968 年《侵占犯罪法》第1条第(1)款明确规定:以永久剥夺他人财物为目的,不诚实地侵占他人财物的,构成侵占罪(theft)⑤“A person is guilty of theft if he dishonestly appropriates property belonging to another with the intention of permanently depriving the other of it;and‘thief’and‘steal’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其中“appropriate”是指未经他人同意将他人之物据为己用,因而翻译为“侵占”比较贴切,但应区别于我国刑法典中侵占罪中的侵占。。由此可见,英国法律对于Theft 罪的定义与该词的普通含义基本一致,这说明其立法者与社会普通民众所使用的概念是一致的。
德语中的盗窃概念是用“stehlen”⑥悄悄拿走别人的东西并据为己有(unbemerkt etw.nehmen,das einem anderen gehören,u.es behalten)(叶本度主编译:《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8页。)一词表达的。然而在德国刑法中却没有“盗窃(stehlen)”这个概念,《德国刑法典》中文版中的所谓“盗窃”,在德国刑法典原文中并非stehlen⑦如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将德国刑法第242条中的“Diebstahl”翻译为“盗窃”。,而是Diebstahl。Dieb-stahl 是指“非法拿取(盗窃)别人的东西”①das verbotene Nehmen(Stehlen)von Dingen,die anderen gehören(叶本度主编译:《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1页。),而“非法拿取”包括盗窃但不限于盗窃,也就是说“非法拿取”既包括秘密非法拿取,也包括公开非法拿取。“非法拿取”的外延大于盗窃,属于盗窃的上位概念。因此德国刑法典中的Diebstahl 严格地说不是“盗窃罪”,而是“非法拿取罪”。由此,德国刑法对于Diebstahl罪的定义与该词的普通含义也是基本一致的,说明德国的立法者与社会普通民众所使用的概念事实上也是一致的。然而在日本和中国,刑法学者们都将Diebstahl 理解为“盗窃罪”,其原因仍在于翻译家们的误导,如日本人编写的Grosses Deutsch-Japanisches Wörterbuch(《德日大辞典》)就是将Diebstahl翻译为“盜み,竊盜,盜難,竊盜罪”[6],我国国内编写的《德汉词典》也是将Diebstahl翻译为“偷窃,偷窃行为”[7]。这就造成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德国刑法中也规定了盗窃罪的误解。
我们知道,日本现行刑法典是于1907 年按照1871 年德意志刑法典制定的。日本现行刑法典第235 条规定:“窃取他人财物的,构成窃盗罪……”②日本刑法典第235条原文:“他人の財物を窃取した者は、窃盗の罪とし……”,其中行为方式为“窃取”。在日语中,“窃取”是指“以秘密的方法盗取”[8]。因此日本刑法中的“窃盗罪”实质上不同于德国刑法中的Diebstahl(非法拿取罪),日本刑法中的“窃盗罪”应该具备秘密性要素。然而日本刑法学界则普遍认为公然的行为也能构成盗窃罪,如西田典之认为:“窃取,本来是秘密取得的意思,但公然实行也可以成立本罪。”[9]日本刑法学之所以普遍认可“公然盗窃”,原因有二:一是翻译家的误导。如前所述,日本翻译家将Diebstahl 翻译成了“竊盜罪”,然而刑法学家在学习外国刑法之前都必须先学习外语,学习外语的工具书则都是翻译家们所编写的。众所周知,在外语学习中越是简单对应的词汇越容易掌握,而翻译家们又并非法学家,他们对概念的要求没有那么严谨,因此,为了达到词汇的简单对应目的,通常会找一个最为接近的词来翻译,于是Diebstahl 理所当然地被翻译成了“竊盜”。二是日本刑法乃至刑法学受德国刑法及刑法学影响太大。正如西原春夫所言,“本来日语中就没有明确的有关法律关系的词汇,而这些法律词汇主要是从外语翻译过来的。事实上,不仅‘法律用语’是如此,而且甚至日语不适宜于‘法的思考’。……如果极端地说,我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不符合法的思考的语言是日语, 而最符合法的思考的是德语。”[10]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刑法学者按照德国刑法对Diebstahl 的定义来理解“窃盗罪”则是情有可原的。
三、盗窃行为的主观要素与盗窃罪的主观要件的区别
(一)行为构造中主观要素的意义
虽然犯罪即行为③也有少数学者提出告别“犯罪即行为”这个命题,告别的理由主要是因为行为的有意性在理论上不能解释“过失行为”,在实践中不能解决“汽车司机疲劳驾驶案”及“瓷器店晕倒”案。(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著,徐凌波、蔡桂生译:“论犯罪构造的逻辑”,《中外法学》2014 年第1期)。事实上,“过失行为”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过失行为”,实际上是从行为的外部所作的一种评价,其所谓的“过失”并非行为的构成要素。很明显“过失行为”一说是受过失犯罪的影响,认为犯罪是行为,既然有过失犯罪就应该有过失行为。这种说法混淆了犯罪与行为之间的差异。关于汽车司机疲劳驾驶案,汽车司机K为了能行驶更多的路程而在夜间疲劳驾驶。一段时间后他睡着了,车撞上了迎面开来的货车,并导致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金德霍伊泽尔将有意识的疲劳驾驶与无意识的梦中驾驶绝对分开,认为事故是梦中驾驶所致,与疲劳驾驶无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梦中驾驶只是因果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它不是原因,相对于疲劳驾驶而言它属于结果,相当于枪击事件中“子弹飞行”环节。如果我们不能说被害人不是被开枪的人打死的,而是被子弹打死的,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说事故不是疲劳驾驶引起的,而是由梦中驾驶引起的。即使按照金德霍伊泽尔的避免义务违反说,也需要成立汽车司机的驾驶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否则不能归责于汽车司机。汽车司机明知疲劳仍然继续驾驶这一有意识的疲劳驾驶行为,正是导致梦中驾驶的原因。因此,应该非难的是汽车司机的有意识的疲劳驾驶行为,而不是无意识的梦中驾驶状态。汽车司机在实施疲劳驾驶行为时对于事故的过失心理态度,并非包含在疲劳驾驶行为的意识之中,而是从行为外部对于行为所作的评价,属于犯罪的主观要件,而不是行为的主观要素。同理,一个人在一家瓷器铺突然晕倒并因此打碎了一只贵重的花瓶,由于不存在有意识的原因行为,因而在刑法上只能评价为意外事件。,但犯罪与行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事物。无论是根据哪一种犯罪构成模式,行为都是犯罪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不是犯罪的全部构成要素,仅此就可以说明犯罪与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因为犯罪与行为属于不同的概念,因而它们各自的构造也不相同。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划分上,行为属于客观要件要素这是无争议的。然而无论在哪个犯罪论体系中,目前处在通说地位的行为理论都认为行为的构造包含主、客观两个方面的要素,如大陆法系的有体性和有意性,英美法系的身体状态和自觉性(Voluntariness)①英美刑法学中,无论何种行为理论,包括“行为自觉性的消极理论”,都不否定行为的自觉性要素的存在。(参见拙文“论英美刑法学中行为的构造”,《岳麓法学评论》2000年第1卷,第185-196页。)。也就是说,犯罪客观要件(行为)中也包含有主观要素,这种主观要素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而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
行为的主观要素,无论是大陆法系的所谓有意性②有学者提出行为有意性不要说,认为“将有意性作为行为的特征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从而主张将无意识的举止也纳入行为范畴之内(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五版,第143页)。首先,在理论上,犯罪是行为这个命题所建立的理论基础是:1、行为具有原因力,能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从而具有侵害的可能性;2、行为受意志支配,而意志则是可以通过对刑罚的权衡作出自由选择的,权衡刑罚之苦大于犯罪之乐,那么行为人就会选择放弃犯罪行为的意志。由此,行为又具有被威慑的可能性。而无意识的身体状态因不具有被威慑的可能性,因而对于刑法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其次,即使是使用三阶层犯罪构成模式,无论何种情况下,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不满12岁的人杀人,至少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必须的,而因果关系的内容则属于构成要件的内容,我们不可能绕过构成要件符合性而直接作责任判断。最后,认为“知道自己患有癫痫病驾车肇事”与“不知道自己患有癫痫病驾车肇事”是“完全相同”的情形的观点,与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所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参见上页注释③),忽略了因果过程中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刑法非难的不是癫痫病发作时的所谓“驾驶”,而是明知自己患有癫痫病仍然驾车的行为,癫痫病发作只是这个有意识行为所引起的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如果不对明知自己患有癫痫病仍然驾车的行为作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何以对行为人对待结果的心理态度做责任判断?,还是英美法系中的自觉性,都绝不是空洞无物的,而是应该有其实质内容的。在一定程度上行为的主观要素决定了行为的性质。首先,根据目前通说的行为理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目的支配下的身体状态。也就是说,人的身体无时无刻不是处在一种客观状态中的,但我们不能说人时时刻刻都在实施行为。那么,什么身体状态(有体性)可以被界定为行为呢?这就只能看其身体状态是否是由特定目的所支配的。从这个角度看,行为的主观要素决定行为的存在。其次,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人的行为种类繁多,为了交流上的方便,人类使用概念将人的行为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可以这么说,一门语言中有多少个非同义的动词,那么这个语言族群就将行为划分为多少个行为概念,因为概念毕竟是用语词来表达的,如杀人、伤害、强奸、诈骗、盗窃,等等。这么多的行为概念相互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行为的主观要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行为实质上是人类基于对因果规律的认识,为达到特定目的而展开的一个因果过程。而这个过程不仅要以主观认识为基础,而且还需要先形成特定的主观目的,更需要这种特定的主观目的去支配身体的状态。不同的主观目的决定了行为的不同性质,如杀人行为与伤害行为,尽管身体状态相似,也不管是否发生死亡结果,关键的区别在于支配身体状态的主观目的是希望行为对象死亡还是受到伤害。因此,行为的主观要素不仅决定了行为本身的存在,而且还决定此行为与彼行为之间的区别。
(二)正确区分犯罪的主客观要件
行为的主观要素与犯罪的主观要件都属于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内容,但除了它们在犯罪构成中地位不同以外,他们的概念本身也各不相同。犯罪的主观要件,实质上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对于犯罪结果的一种心理态度,这种态度除了追求该犯罪结果发生以外,还包括对犯罪结果的放任,漠不关心,不重视等态度,而这种放任,漠不关心或不重视等态度却并不是行为的主观心理要素。如在过失犯罪的情况下,行为的主观要素必定是行为人追求各该过失犯罪的犯罪结果以外的其他结果,否则行为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身体状态就不能被评价为“行为”,因为无目的的身体状态不是行为,因而也不能成为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行为的目的有时候比较简单,但有时候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行为目的本身也体现了行为人对结果的一种态度,即行为人对于犯罪结果的追求态度,而这种态度与犯罪构成主观要件是竞合关系,如杀人行为希望死亡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既是行为的目的,也是犯罪的直接故意。这种竞合关系使得这种心理态度既是行为的构成要素即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也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不只是犯罪故意如此,就连部分犯罪目的也是如此。众所周知,犯罪目的分为法定犯罪目的和非法定犯罪目的。所谓非法定犯罪目的,顾名思义,就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犯罪目的。那么,这种非法定的犯罪目的从何而来?不能由学者或者法官主观臆断。事实上,非法定的犯罪目的就是从行为的主观要素中提取的。尽管行为可能由各种动机所引起,但就单个行为概念而言,行为可分为单目的行为和复合目的行为,如杀人行为就是单目的行为,尽管杀人的动机可能各种各样,但希望他人死亡这个目的足以满足杀人行为的主观要素。而盗窃行为则属于复合目的行为,直接支配盗窃行为的意志是希望在不被他人察觉的情况下转移他人的财产,然而仅希望在不被他人察觉的情况下转移他人的财产尚不足以成其为盗窃行为,因为那也有可能是愚人节开玩笑的玩笑行为,因为以开玩笑为目的在不被他人察觉的情况下转移他人财产的行为明显是不具有盗窃性质的。因此,在不被他人察觉的情况下转移他人财产的行为若要具备盗窃性质,其行为还必须受非法占有目的所支配。也正因为盗窃行为性质本身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刑法无需再为盗窃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这是非法定目的犯的犯罪目的存在的理论基础①据此来看,我国刑法学中争论的关于伪造货币罪是否目的犯问题不难解决。“伪造”并非复合目的行为,就伪造行为的性质而言,主观要素除了意志以外并无其他目的,而我国刑法也并没有为其犯罪构成规定一个目的。因此在我国,伪造货币罪不是目的犯。。
综上,盗窃行为中行为人“自认为秘密”是行为的主观要素,因而属于犯罪构成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简单地说,属于客观要件中的主观要素。不仅如此,连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也属于犯罪构成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因此,“自认为秘密”的说法,并没有混淆犯罪构成中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区别,而恰好是该要素在犯罪构成中的正确定位。
四、刑法中行为概念的意义
(一)简单罪状中的概念必须是众所周知的概念
我们知道,刑事立法中对于部分犯罪构成要件的描述使用的是简单罪状。应该说,法律条文涉及到是非曲直,同时涉及到责任追究,因而在用语的使用上都是最为严谨的,对于罪状的描述也应该是最为准确的,尽可能避免产生歧义。然而立法者之所以会使用简单罪状,是因为立法者确信简单罪状中所使用的语词,既能够精确地表达立法者所要表达的概念,也能够精确地把立法者所要传递的法律信息传递给它的调整对象,不至于影响法律的实施。而能担此重任的语词及其概念,必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清晰的,不易产生歧义的语词和概念,“只有在某一罪行是众所周知而不需要在刑法分则条文中专门叙述其特征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简单罪状。”[11]54而盗窃则正是这种概念,所以刑事立法上对于盗窃罪使用了简单罪状[11]54②我国《刑法》第264条所规定的盗窃罪的罪状虽然使用了较多的字数,即:“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但这只是为了符合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量的规定性而增加的情节要素而已,而在质的规定性上盗窃罪状仍然是简明的。。社会大众对于生活中各种常见概念的认知,来源于他们所受的语文教育,而语文教育中各个概念的语词含义则来源于各该国的通用词典,如汉语教学中所通用的《现代汉语词典》,因而我国一般社会民众对于“盗窃”的理解应该是与《现代汉语词典》一致的。
(二)公开盗窃论不利于刑法机能的实现
刑法具有行为规制机能(或称规范[12]或规律[13]机能)。尽管学界对于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在刑法中的地位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刑法具有这一机能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所谓行为规制机能,就是指刑法通过对犯罪的否定评价(评价机能),来影响公民的自由意志选择,使之作出“不选择犯罪”的意思决定(意思决定机能),其中评价机能是手段,决定机能是目的。然而,手段要能服务于目的,就必须保持刑法评价中的犯罪行为的概念与普通公民所认知的概念是一致的。如果刑法与公民的认知之间没有共同的概念信息,就不能形成有效的交流。没有有效的交流,公民就得不到正确的信息。没有正确的信息,公民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意思决定,从而刑法的意思决定机能就不能实现。“公开盗窃”超出了公民的认识范围,不利于刑法的意思决定机能的实现。
(三)公开盗窃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为了保障人民自由,刑法必须事先明确告诉人民什么是犯罪及犯罪后应该受到什么样刑罚处罚。“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行为,即便其法益侵害再严重,也不可能科处刑罚。”[14]56“国民通过刑法用语了解刑法禁止什么行为。在了解的过程中,国民当然会想到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14]51从而预测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对于“盗窃”,国民所能想到的当然是他们在语文学习中所学到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所解释的含义,即“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尽管语言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会不断发展,但“盗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该词条被修订之前,只能是“秘密地取得”,而不只是“其原本含义也是秘密窃取”[15]949。如果将国民根据刑法用语所预想不到的“公开盗窃”[15]949解释为刑法用语“盗窃”所包含的内容,就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从而就会妨害国民的自由。
纵然刑法的适用是离不开解释的,罪刑法定原则也不会完全排斥刑法的解释,但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绝对不允许类推解释,因为“类推解释的结论,必然导致国民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后果,”[14]51国民面对刑法的类推解释是没有自由可言的①“法官一旦形成了她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其结果就会有人失去了自由、财产、孩子,甚至生命。”(Robert M.Cover:Violence and the Word,The Yale Law Journal,1986,Vol.95:1601)。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的解释不能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判断依据,则是“一般语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标准的语言用法。”[14]58如对于“盗窃”来说,若依一般语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标准的语言用法,则不能超过《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这一含义。将所要解释的概念提升到更上位的概念作出的解释,则是类推解释,比如将“窃取”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窃取”是偷窃的意思,而“偷窃”则是盗窃的意思。解释为“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人(包括单位)占有”[15]949,因为“违反他人意志将他人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的不只是窃取,几乎所有财产犯罪行为都具有这一特征,尤其是抢夺行为。事实上“违反他人意志将他人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的行为就是各财产犯罪行为的上位概念,刑法正是根据财产转移的方式不同才将财产犯罪行为区分为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等下位概念。同时,将“公开盗窃”解释为盗窃,不只是让一般国民感到特别意外,就连大多数中国刑法学者都感到意外,这也充分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由此也可以说这种解释属于类推解释[14]59。中国已逐渐进入法治时代,即便不能将所谓“公开盗窃”的情形解释为抢夺,那也不能用类推解释的方法来填补“处罚上的空隙”[15]949,因为通过类推方法来填补的漏洞,属于真正的刑法漏洞,而这种真正的刑法漏洞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来填补[13]56。因为,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行为,即便其法益侵害再严重,也不可能科处刑罚。”[14]56如果仅仅为了弥补刑法处罚上的空隙而适用类推解释,那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是对国民自由的侵害。将国民根据刑法用语所预想不到的事项解释为刑法用语所包含的事项,会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从而导致国民实施原本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却受到了刑罚处罚[14]51,这样才会真正造成不公正现象。
五、结论
概念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整个客观世界进行切割、分类所形成的最基本的思维形式,是思维机体的细胞,是相互交流的基础。概念的统一是有效交流的前提。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是立法者与调整对象之间的交流,因此,法律中所使用的概念必须与它所调整的对象之间保持统一,否则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地实施。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因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经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有所不同,所使用的概念也一定会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在借鉴他国经验时,必须要考虑这些差异,不能盲目吸收。中华文明中的“盗窃”概念,在有些国家是没有的,翻译家们的牵强附会,在法学研究中不能当然地接受。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没有日本当时的时代背景,日本刑法学可以将错就错,而我们则不能盲从。
尽管行为是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要素,但行为与犯罪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它们的构造也各不相同,不仅犯罪有其主观构成要件,行为也有其主观构成要素。行为在犯罪构成中属于客观要件,那么行为的主观要素当然也随之归属于客观要件,不能因为行为的主观要素与犯罪的主观要件发生竞合而否定行为的主观要素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区分行为的主观要素与犯罪的主观要件,不等于混淆犯罪构成中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区别。
立法者为了与调整对象之间保持概念的统一,在语词的选用上有较高的要求,确保能够精确地把立法者所要传递的法律信息传递给它的调整对象。然而刑法中之所以使用简单罪状,是因为立法者确信简单罪状中所使用的语词,既能够精确地表达立法者所要表达的概念,也不至于影响法律的实施。能够被用于简单罪状的行为概念,必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清晰的,不易产生歧义的概念,而“盗窃”则正是这种概念。由此,刑法学家对于盗窃行为的解释,不能超越人们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内容,否则不仅会阻碍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的发挥,而且也违反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
(本文是许富仁博士生前与本人合作的一篇文章,由许博士提议,本人执笔完成的。许富仁博士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学者,退休后仍继续从事刑法学研究,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躺在病床上也不时通过微信与我讨论学术问题,其治学精神令我十分感动。今将本文献给许富仁博士,以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