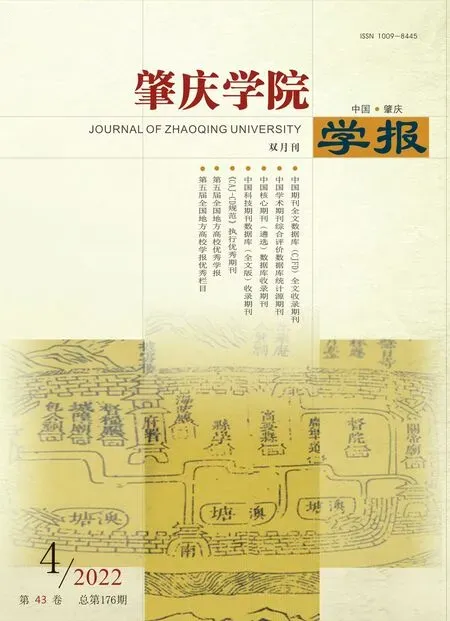论《四世同堂》中小文夫妇的艺术形象
马凯凤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基础部,广东 广州 510000)
一、引言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市民文学作家,老舍塑造了许多小人物形象,如人力车夫祥子、鼓书艺人方宝庆、妓女月牙儿和“臭脚巡”福海等,这些小人物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职业,也承受着人间不同的痛苦和折磨。老舍的下层生活经历和底层关怀意识,决定了他对历经苦难的小人物抱有深深的同情,并促使他把这些了然于胸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对于老舍作品中的小人物,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是老舍笔下的人力车夫、妓女等市民形象,很少有人关注其作品中的“戏子”形象。笔者认为,老舍塑造的“戏子”形象虽然极少,却代表了某类颇具刚硬风骨的艺人群体,是对传统“戏子”形象的颠覆性书写,他们不仅承载着小说人物本身的艺术功能,还凸显了作者信奉的道德信条和某种抗日理念。所以这类人物形象之于老舍小说的意义并非无关紧要,而是一种隐喻着其价值观和文化选择的重要存在。就此而言,这类“戏子”形象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下面,我们就以《四世同堂》中的小文夫妇为例,来谈谈老舍对“戏子”形象的正面塑造及其承载的多重意蕴。
二、老舍与小文夫妇形象的生成
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老舍其实最了解北平文化的底细,即使这座城已然亡于敌手,作家也照旧摸得准北平人的脉象会是什么样”[1]55。老舍在下笔写作《四世同堂》之前曾经构思过很长一段时间,内心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出身北平的他对故土无疑是热爱的,可值得深思的是,如此热爱北平的老舍居然描绘了一个又一个冷冰冰的事实,进而展现了抗战背景下深受封建家庭观念束缚的北平人的敷衍、苟且、寡廉鲜耻、不作为等国民劣根性。老舍的长篇巨制《四世同堂》以沦陷了的北平为背景,描写了日伪统治下北平尤其是“小羊圈”胡同里的百态人生。“它涉及十七八个家庭和一百三十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他们中有中学教员、老诗人、拉车的、棚匠兼耍狮子的、教授、戏唱的、开布店的、‘打鼓儿’的、‘摆台’的、‘窝脖儿’的、巡警、税局长、剃头的、流氓、妓女、汉奸、老寡妇、英国外交官员、看坟的、特务,等等。”[2]虽然小文夫妇在《四世同堂》中是作为配角形象出现的,但作者用了约一章的篇幅来专门交代小文夫妇的身份背景和生活方式,并偶尔在文中穿插能够凸显他们人生态度的文字片段。可见,作者对这对夫妇倾注了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同时,老舍作品里的每个人物都具有很强的典型化和类型化特点,小文夫妇也不例外。
客观地说,老舍的创作风格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存有一定的差异,其建国前的创作流露出悲苦乃至绝望的情绪,这与其满族身份和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老舍出生、成长于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父亲为保卫北平而牺牲,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成人,这让他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的艰辛。清王朝覆灭后满人的地位一落千丈,老舍接触到了形形色色因生活困顿而挣扎的满族底层民众,他把这些沦落于社会底层的满人作为自己笔下的主要人物,书写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和困苦遭际。在民国时期,北平的满人犹如“过街老鼠”,不敢光明正大地表明自己的族籍和身份,生怕说出后会失去最后一片故土,老舍亦如此。每当遇到满族同胞被批判时,老舍总是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一面附和批判一面又暗自心痛。老舍希望消除世人对满人的偏见,他想为善良的满族同胞正名,只是在当时“排满”风潮极为浓厚的社会环境下,他只能用隐晦的方式去表达这种愿望,而小文夫妇作为“戏子”形象的建构就是伴随着他为满族同胞正名的愿望完成的。
《四世同堂》始作于1944年1月,其中《惶惑》《偷生》在1945 年底完成,《饥荒》则在1949 年于美国完成。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老舍把自己对满族族群与文化的认同感潜隐在小文夫妇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在小说中,老舍告诉读者:“小文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降生在一座有花园亭榭的大宅子中的”“假若他早生三二十年,他一定会承袭上一等侯爵,而坐着八人大轿去见皇帝的。”[3]243“文侯爷不是旗人。但是,因为爵位的关系,他差不多自然而然的便承袭了旗人的那一部文化。假若他不生在民国元年,说不定他会成为穿宫过府的最漂亮的人物,而且因能拉会唱和斗鸡走狗得到最有油水的差事。”[3]244在这里,老舍表面上并未明言小文夫妇的民族身份,但内里已经暗示得非常清楚,并点出了他们身为满人的某些特质。小文生于民国时期,也立足于民国的土地上,可他的思想、趣味、生活习惯与本领完全属于清朝,从清朝的贵族跌落至民国的平民,小文成了非贵族非平民的“怪物”,他在北平被日寇侵略、霸占时以一个淡漠的旁观者生活着,直到最后拿起椅子砸死那个杀妻日寇并壮烈死去,他才与历史、国家、民族发生了密切关系。通过小文夫妇形象的塑造,老舍告诉读者:并非所有的满人都是“卖国者”,在社会底层有一群爱国的满人在民族国家危难来临之际是可以直面敌人、无惧生死的。“《四世同堂》里面凛然目敌慨然赴死的小文夫妇,是他首次确切地知告世人,即便是那些最不愿过问时事政治的满人,也会是这等样子!”[4]43不管小文“以椅杀敌”的行动是出于什么原由,但正是因为有了众多像小文夫妇那样为守护心中珍爱物事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才使得中国不至于完全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以是观之,老舍笔下的“戏子”形象与大众心目中的“戏子”印象完全不同,他所建构的“戏子”——小文夫妇形象承袭了他的“精气神”。也就是说,读者可以在小文夫妇身上看到老舍式的尊严和气节,尤其是小文,他与老舍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北平人,都是满人的后裔,都保有满人爱唱戏的特点。老舍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十分喜爱看戏,由于生活拮据,所以经常和好友罗常培跑到茶馆里去听免费评书,工作后有了余钱就开始“泡戏园子”,久而久之还可以喊上两嗓子,甚至还能将曲艺嗜好化作个性化文学创作活动当中的“一项‘绝活儿’般地专长”[4]167。老舍的尊严和气节来自他的母亲,“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5]292,这是母亲给予他的“生命的教育”,而尊严和气节是他心中不可逾越的原则界限。可惜的是,老舍自杀身亡。“老舍的自杀,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既是形势使然,也是性情使然”,更兑现了那无比宝贵的“生命的教育”[4]27。返观小文夫妇,读者虽然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那种老舍母亲式的“生命的教育”,却可以看到他们如老舍一样践行了这种“生命的教育”。
如是说并非随意揣测。1944 年,日寇逼近重庆,时人纷纷准备逃难,但老舍从未想过逃离重庆,他对朋友说:“我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我决不落在日寇手里,宁死不屈!”[6]一句“宁死不屈”明示了老舍的铮铮傲骨,而小文无疑承袭了老舍这种直面日寇、宁死不屈的气节,这才有了后来那无所畏惧的“一砸”。小文的这“一砸”,不但砸死了枪杀他妻子若霞的日寇,也“砸出”了满族艺人的气节和傲骨。小文夫妇刚强不屈,并不是时人刻板印象中的“软媚之主”。与此同时,老舍还直面小文夫妇的缺点,把他们塑造成了对周围的人事物淡漠却又讲义气的矛盾形象。一方面,太阳旗高高挂起时,小文夫妇可以装作没看见,继续沉醉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曲艺追求;另一方面,当别人来寻求帮助时,他们又会毫不吝啬和全力以赴地去帮忙。可以说,小文夫妇形象的塑造,既承载了老舍对北平文化、满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也暗含着他对以小文夫妇为代表的不问国事的同胞们的批判意识。正因为老舍出身于底层平民,所以他深知自己的同胞兼具人性美与丑的特性,因此在塑造小文夫妇形象时,并没有把身为艺人的他们写得那么完美,也没有把他们写得那么不堪,而是让读者在反思他们不足之处的同时,也能看到他们优异的道德品质、刚硬人格和人性光辉。
三、小文夫妇与“戏子”形象的颠覆性书写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戏子”一词充满了贬义,但在老舍的笔下并非如此。“早在晋代时,便有了‘戏子’之说,也叫优伶,是个贬义的名词,因为在当时,戏子的身份很低贱,宴饮不能与官员同桌,子女不得参加科举,死后不得进祖坟。”[7]“在封建社会里,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有所谓‘一妓二丐三戏子’之说。把戏曲艺人与妓女、乞丐并论,甚至戏曲艺人还要名列于妓女、乞丐之后,足见其被社会所歧视之严重程度。”[8]再者,古时人被分为三六九等(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一流帝王相、二流官军将、三流绅贾商、四流派教帮、五流工塾匠、六流医地农、七流巫乞奴、八流盗骗抢、九流耍艺娼”[9],其中“艺”指的就是戏子,由于以前的戏子总是以声色侍人,还有的以出卖肉体过活,因而他们和娼妓一同被归为下九流行列。由此可见,古人对“戏子”是十分不待见的,甚至极为厌恶和歧视,所以才有了“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种不成文的说法。不过,老舍通过小文夫妇形象的塑造消解了读者对于“戏子”负面形象的认知和偏见。这对于抗战力量的扩展和挖掘是有启示性的,对于提高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和丰富抗战人物形象画廊也是具有突出贡献的。
《四世同堂》是老舍“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5]405,描述了抗战期间“小羊圈”胡同周围发生的一系列悲剧故事,以及大杂院里的人们面对日寇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态和行为方式。《四世同堂》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作者把这些人物主要置于“小羊圈”胡同里,让人与人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譬如:面对日寇侵略时积极参与反抗斗争的祁瑞全、钱默吟和钱仲石;惶惶不安地苟活于乱世的祁老太爷和陈野求;沦为日本人走狗的大赤包、冠晓荷、祁瑞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塑造了尤桐芳、冠高第这类抗日女性形象,她们也曾在“惶惑中偷生”,可当身边人一个个死去时,她们终于走向了觉醒与反抗,尤桐芳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小文夫妇以隐性的“末世旗人”身份出现在《四世同堂》中,并作为满族艺人的代表被放置到“八年抗战”生活中。透过小文夫妇的身份、行为、性情,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专属于满人的“勤恳、善良、纯正、耿直、自尊以及侠肝义胆、凛然无惧等精神特质”[4]39。不过,老舍对于小文夫妇并不是一味的偏爱,他还把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满人身上的弊病透过小文夫妇的表现折射出来,以此批判其满族同胞的“国民劣根性”。
小文在没有住进“小羊圈”胡同之前是满清末代侯爷,出生、成长在金子堆里,得了一种“贵人病”,他像所有旗人贵族子弟一样没有办法拒绝“玩”的生活艺术对他的吸引力,所以他会斗蟋蟀、蝈蝈和养金鱼、白鸽,并凭着聪明劲八岁学会唱整本的老生戏,十岁学会弹琵琶拉胡琴。小文的一切几乎都属于清王朝。可是,辛亥革命来了,清王朝变成了民国,他的亭台阁榭和金鱼白鸽跟着王公府邸一道变成了换米面的东西,他也由贵族子弟沦落为北平的底层平民。他的太太若霞是受父母之命定下的,她与小文有着一样的身世遭遇和共同爱好——唱戏,他们夫妻俩简直就是一对天造地设、“像花一样的美”的艺人。六号杂院的东屋是小文夫妇的家,在这里他们靠唱戏养活自己,由于与生俱来的自尊意识,他们并没有“下海”搭班儿唱戏,而只是作着“拿黑杵的票友”[3]246。
对于大杂院里的居民来说,小文夫妇就像迷一样的人物,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知道他们总是不卑不亢、从容不迫,每天沉迷于唱戏。小文夫妇的住所内除了一两样家具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能引人注意的只有客厅墙角上的藤子棍,让人感觉到他们就是为了唱戏而活的,除了唱戏其它事情都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当日寇的轰炸机横行于北平上空时,当大家忙着拆天棚以防患于未然时,小文夫妇反倒光明正大的在院中排练,好像天塌下来也不能阻止他们唱戏一般,甚至在大伙儿因为日寇侵略不知何去何从而惶惑沉寂时,小文夫妇依旧拉胡琴、调嗓子。“在他们心中,他们都不晓得什么叫国事,与世界上一共有几大洲。他们没有留恋过去的伤感,也没有顾虑明天的忧惧”“他们经历了历史的极大的变动,而像婴儿那么无知无识的活着;他们的天真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3]245所以当丁约翰和刘师傅因为“上海战事”而担忧、吵嘴时,小文依旧可以超然世外般为太太设计“新腔”。当日寇要求北平每家每户都必须安装广播以便对中国人“洗脑”时,他们索性利用广播来听戏曲,仍然像“乐天派”那样只专注于唱戏。对于小文夫妇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态度,老舍是怒其不争的,在日寇全面侵华的时代背景下,每个中国人都与民族国家命运有着必然联系,超然物外者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动荡年代活下来的,因而小文夫妇的性格特征为他们的死埋下了伏笔。
老舍除了揭出小文夫妇身上的弊病外,还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善良、讲义气的品性。见惯了大宅门的人生百态,小文为人处事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方式,哪怕面对觊觎自己太太美貌的大汉奸冠晓荷,他就算打心底里看不起对方也没有表露出来。每当邻里真正需要帮忙时,小文都毫不吝啬地给予他们帮助,他会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作为小崔的安葬费,也会在祁天佑死后主动上门帮助祁家处理事情,这些都证明小文在淡漠超然的态度之下藏着一颗炽热、善良的心。而作者灌注于小文夫妇身上的独异品格和艺人气质,使得他们不因身为“戏子”就自降身份去讨好任何人,无论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走狗都不能让他们低头迎合。
瑞宣被捕入狱后,小文说:“改朝换代都得死人,有钱的,没钱的,有地位的,没地位的,作主人的,作奴隶的,都得死!”[3]585此外,长顺替小崔领安葬费时,他又说:“人都得死!谁准知道自己的脑袋什么时候掉下去呢!”[3]615这两句话暗示了小文夫妇必死的命运,可他们何时何地死去,以及如何死去,这有很大的讲究。小文夫妇的死跟唱戏有着必然和直接的关系,他们是在唱演《奇双会》这部戏时正面接触到日寇的,那时的他们正沉浸在自己的曲艺世界里,如此若霞才会因无视日寇的调戏而被枪杀,小文也才会与杀害若霞的日寇同归于尽。唱戏就是小文夫妇的命,只是他们的生命和戏曲已经在这一刻同时终结。小文夫妇的死既成全了他们对于唱戏的热爱,也成全了他们的生命尊严、艺人气节和英雄壮举。
淡漠而又讲义气的小文夫妇就像一对“矛盾结合体”,老舍把自己对满族同胞的怜悯和“恨铁不成钢”的复杂心理都加诸在小文夫妇身上。小文夫妇可以不分种族、不分敌我地给任何爱看戏的人唱戏表演,就连对方是侵略自己国家的日寇也不在乎;他们可以为了身边的朋友“两肋插刀”,哪怕明天就要饿死也无所谓。老舍对小文夫妇的怜惜态度是通过瑞宣的心理活动表达出来的。“从一种意义来说,他以为小文夫妇都可以算作艺术家,都死得可惜。但是,假若艺术家只是听天由命的苟安于乱世,不会反抗,不会自卫,那么惨死便是他们必然的归宿。”[3]817是的,小文夫妇的死是那么惨烈,让人既意外又震惊,谁都没有想到“超然世外”的小文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且无所畏惧地直面日寇和汉奸的手枪。他在砸死仇人后仿佛释然了,他回头看了看若霞:“霞!死吧,没关系!”[3]808对于他们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深爱的物事与亲人,当人格尊严与曲艺追求双双幻灭时,死亡就是他们最好的生命归宿。
随后,作者借日本人控制下的北平报纸高扬了小文夫妇“勾通奸党,暗藏武器,于义赈游艺会中,拟行刺皇军武官”[3]809的烈士形象,给小文夫妇设定了一个极好的名声。不管小文夫妇因何而死,又如何死去,总归他们是被日寇害死的,但最震撼人心的是,柔弱的小文居然在剧场观众面前直接砸死了一个日本鬼子。在这样复杂污浊的社会大环境中,小文夫妇就像一股清流,他们的死让处于日寇蹂躏下的北平市民意识到一味的惶惑与偷生并不能解决任何事情,这正如作者借钱默吟之口所说的那样:“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3]225
四、小文夫妇形象的多重意蕴
20世纪30年代后期,老舍的创作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此之前,老舍由于受朝代更替和现代化思潮的影响,作品反映的多是封建社会的遗留问题、新老市民的可笑行径以及新旧时代碰撞下涌现出来的社会弊病。“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老舍毅然投身抗战洪流并积极主持“文协”活动,这一时期其作品中的政治意识和抗战立场越来越明显。这一点在《四世同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关键的是,《四世同堂》凝聚了老舍太多的痛苦和挣扎,它们来自他的肉体、心灵和生活本身。比如,老舍在抱病创作《四世同堂》的过程中曾发表三篇《多鼠斋杂谈》,讲述他为了养好身体完成这部巨作主动戒烟、戒酒和戒茶的艰难过程,可见他对这部作品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是故,对于小说中精心着墨的配角——小文夫妇,老舍还是赋予了他们多重意蕴。
首先,老舍借小文夫妇之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杀戮罪行。“丧尽人道的日军显示了像‘吃茶与插花那么讲究’的杀人艺术,生存在丧失主权的故都里,市民与死亡成了‘近邻’。”[1]52纵观老舍的所有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写小人物的悲剧是沿着个人命运——社会命运——民族命运这样一条创作思维线索向前发展的”[10],而《四世同堂》就是老舍对于民族命运的思考成果。老舍的创作语言具有极其深厚的“幽默味”,但读者往往能在他笔下充满趣味性的言语和啼笑皆非的事件中感受到悲愤、感伤乃至绝望的情绪。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依旧用幽默笔调去描写“小羊圈”胡同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他讽刺冠晓荷、大赤包之流沦为日本走狗后显露出来的令人作呕的丑态;他赞扬祁瑞全、钱仲石这些走向抗日前线的志士;他也对偷生于日伪统治下的国人感到羞愧和愤懑。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死”了很多人,如因日寇侵略而被劣等食物害死的小妞子,跟一车日寇同归于尽的钱仲石,不堪日寇侮辱跳水自杀的祁天佑等,这些好人的死使得整部作品从头至尾弥漫着悲伤的气息,其中最让人意外和震惊的莫过于小文夫妇的死。小文夫妇淡泊的性格特质与悲壮的死亡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人既同情他们的命运遭际又痛恨日本鬼子的无差别杀人。老舍认为这样的悲剧事件具有“很大的教育力量”[11],能够增强作品的说服效果,能够促使读者积极反思“八年抗战”这段“痛史”背后的诸多教训。
其次,小文夫妇形象的塑造既包含了老舍的批判意识,也折射了动荡社会中北平市民不同生存方式背后的生命抉择。《四世同堂》是老舍根据真实的社会现实写就的,“小羊圈”胡同就是日寇侵略下的北平乃至整个中国的缩影。以是观之,老舍笔下的小文夫妇形象具有独特的意指。清王朝覆灭后,大多数满人沦为整日为生计奔忙的底层平民,有着相同身份、类似经历的老舍与其中的很多满人成了朋友,他熟知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抗战全面爆发后,老舍深知自己身为作家虽不能奔赴前线杀敌,却可以“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战行列中,于是他“以笔代枪”创作了诸多反映时事政治的话剧,甚至“亲装上阵”表演抗战话剧,以此增强话剧的抗战宣传功能。在老舍的心目中,艺人就应该像梅兰芳那样为国事为抗战而努力,“蓄须明志”不与日寇同流合污。北平沦陷后,老舍痛心于故土沦丧以及同胞们的茫然无措与抗战不作为,于是借小文夫妇形象的塑造批判了国人遭逢日寇侵略却依然想着世界大同的愚昧心理,也批判了在抗战年代无视人间地狱惨景只求一隅苟安的自私做法,更批判了残害同胞、助纣为虐、卖国求荣的汉奸行径。如果小文夫妇能够投身抗战行列,把戏曲当作宣传鼓动广大民众抗战的工具,那么他们的命运就会变得不同,他们的曲艺追求也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可他们是那么天真淡然,即便知道是为日寇表演也欣然前往,最终落得双双惨死的悲剧结局。这就等于在告诫世人,任何人在抗战年代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像小文夫妇这样超然世外的好人都会惨死,更遑论他人。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小文夫妇的情状折射了抗战时期多数安于现状、苟且偷生的市民心理,他们在是非善恶面前没有真正的主见,不会直面反抗斗争,所以才会以充满悲剧色彩的方式丧命于日寇和汉奸之手。换言之,老舍给乱世中苟活的底层民众指出了一条出路和活路,那就是像小文一样拼死反抗日寇的侵略和压迫,哪怕反抗过程中充溢着流血和牺牲,也远比苟活、附逆要有价值得多。
再次,老舍希望通过小文夫妇形象的塑造来为其满族同胞“正名”。对于小文夫妇这样的戏子形象,作者除了批判之外,更多的是在展示满人的淳朴、善良、讲义气等特性,希望以此让读者知悉,在抗战中有很多满族同胞同样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其时,满族旗人被打上了“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标签,身份地位一落千丈。作为满族旗人后代的老舍,不能接受自己的族群同胞们被诬为“封建余孽”“亡国奴”而处处遭到排斥和讥嘲,也不能接受满人为保家卫国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全部被粗暴抹杀的情状。所以,在不宜光明正大地描写满人抗日斗争的情形下,他透过小文夫妇形象的建构隐性地传递了他对满族同胞爱国情怀的认可与高扬。老舍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敢于正视满族同胞身上的缺点,他遵照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原则把小文夫妇塑造成了专注唱戏、不问政治的人物形象。可就是这样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觉醒了,小文成了“小羊圈”胡同里第一个敢于当众击杀日寇、无畏敌人刀枪的艺人。为此,连钱默吟都钦佩他的杀敌壮举,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人。老舍还把满族同胞淳朴、善良、讲义气等特性加诸在小文夫妇身上,这就进一步彰显了他为满族同胞“正名”的强烈诉求。
最后,小文夫妇形象的塑造不仅体现了老舍的批判立场和启蒙意识,还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和抗战理念。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国土大量沦陷后,沦陷区里的同胞们几乎全部丧失了自主生存权利,国破意味着个体家庭也将不复安宁和完整。老舍借小文夫妇的事例告诉读者,每个人都与民族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敌人的残暴“统治”下,只有奋起反抗才能拯救国家、拯救民族、拯救家园,进而拯救自己。所以老舍在小说中意味深长地暗示读者,小文夫妇的壮举就像一阵微风,一旦吹拂和传播开来,就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随着无数小文夫妇的群起反抗,中国的抗日浪潮就会如同秋风扫落叶般摧垮貌似坚不可摧的日本侵略者。这种充满正能量的隐喻,无疑映射了老舍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当然,老舍是反对战争的,因为战争是对人类的最大戕害。老舍的抗战理念、和平思想和反战诉求并不矛盾,反而体现了他的人道情怀、人类视野及其辩证思维。
五、结语
老舍作为一个“勤奋而又多才多艺的作家”[12],在《四世同堂》中刻画了诸多寓意丰盈的小人物形象。小文夫妇作为老舍作品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戏子”形象,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意义。小文夫妇与中国历史上的“优伶”形象完全不同,他们以死亡作为觉醒的代价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使命”。小文夫妇作为老舍精心塑造的“戏子”形象,不仅在其作品的人物谱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还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画廊,更隐喻着他独异的艺人观。老舍认为,现代艺人并非富人的优伶或玩物,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还可以具有高贵的独立人格,更可以拥有勇于抗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在某种层面上,他们不但是挺直中华民族脊梁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抗日英雄人物形象系列中独特的一对夫妻形象,这同样体现了老舍与《四世同堂》独特的艺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