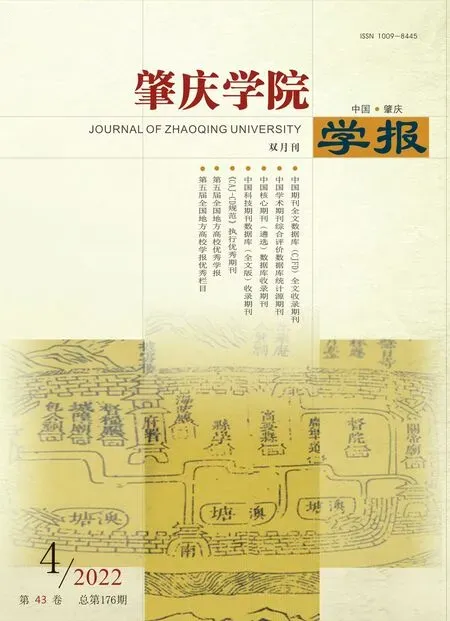宋初小说视域下的僧传系统:《太平广记》“异僧”类研究
盛 莉
(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在倡导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研究回归本位化、民族化的今日学界,很多从文学现象到理论构建的重大问题都需要从古代政治、学术、宗教等多重历史场域下综合审视。而古代文学中一些重要的文体、作品也亟待在回归历史的语境中发掘出其文化内涵和思想背景,小说即是其中的研究热点之一。中国古代小说在理论建构、文体形态和文本指向上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发展态势,小说在文人生活中既具有娱乐谈谑的功能,亦可广资博闻,补充文人的知识结构。从《汉书·艺文志》始列“小说家”类起,后世官方书目中大多设置了“小说”类,小说的观念内涵固然在各历史时期有所变化,但其所包含的知识要素、文本作品已成为古代文人知识体系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其中,李昉、徐铉等人编纂的《太平广记》尤为值得注意。作为北宋四大类书之一,《太平广记》显然蕴藏了宋初官方的小说意识、文化诉求,代表了宋初官方的小说观念[1]。所收篇目基本可视为宋初官方指称的小说。
小说在宋初除了娱乐谈谑外,还具有广见闻的知识功用,关于这点详见下文。《太平广记》的编纂并不完全是今天文学观念意义上奇闻趣事的收录,还承担了搜集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各种庞杂文类的任务,反映了非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其类目设置是对当时人文世界秩序的认识与分类,一些类目如“异僧”类揭示了类目编纂与当时宋初文化构建、三教合流思想背景相关联的内容。本文即以《太平广记》“异僧”类为中心,探讨《太平广记》僧传系统所传达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整合的知识内涵。
一、小说:宋初文人知识结构的补充
唐代官修类书皆没有专门的“僧”类或“异僧”类,至宋初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时,却都设置了“异僧”类,要探讨“异僧”类的僧传系统,首先要明了小说与宋初文人知识结构之间的关联。
小说与文人知识结构的关联可溯源至汉代。《汉书·艺文志》始列“小说家”,并收录《百家》一书。刘向《说苑叙录》称“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2],故学界一般以为刘向是《百家》的编者。刘向言《百家》“浅薄不中义理”,这是对《百家》知识属性的论断,但《百家》作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小说家”书目,则亦为“小说家”中学术思想之一说。有学者认为,小说在汉代进入官方目录,与汉代新文人群体的出现有关。这个新文人群体的知识结构包括经艺传书、百家之言、古今之事等,刘向、刘歆父子及班固皆是这个新知识结构的重要起点[3]。
六朝以后,小说的内涵愈趋庞杂丰富。小说在唐代的发展更为蓬勃显著,刘知几的《史通》在理论上将小说引入史部,抬高了小说的地位,并根据知识内容将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而于小说创作上,唐代笔记的编纂固然同文人助谈资、喜嘲谑的文化诉求有关,也缘于文人对儒家正统学术之外知识的探求。以高彦休《唐阙史》为例,序云是书乃为“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葅醢也”。文人以小说作为知识补充的学习方式甚而影响至宫廷。元和中,谏议大夫韦绶充皇子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太子因侍,或以绶所谭言之。他日,帝谓宰臣曰:‘侍读者当以经术辅导太子,使深知其君臣父子之教,今或闻绶之谈论有异于是,岂导太子者?’因命罢其职,寻又出之。”[4]这则材料中提到韦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谐戏当指有趣的典故异闻,内容多同唐五代笔记所记载的小说[5-6]。韦绶因侍讲太子时谈论小说遭到罢职,这固然表现了帝王对小说的拒斥,却反映了小说在当时文人知识体系中的风行。其后的南唐后主李煜亦表达了对小说浸染文人学风的担忧,曾批评身边的文学侍臣“今之为学,所宗者小说,所尚者刀笔,故发言奋藻,则在古人之下”[7]。
宋初,小说依然是文人六经之外不可忽视的内容。一些在文坛卓有影响的文人如孙光宪、徐铉、张洎入宋前都著录过笔记,其中绝大部分为小说,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徐铉的《稽神录》均是《太平广记》的重要引书。与徐铉同由南唐入宋的文人乐史著《广卓异记》,是书序云集汉魏以降并唐之人异事,以求文人能从“其累代簪缨,盖世功业,三复省之,不无所益”“虽不补三馆之新书,亦拟为一家之小说”[8],代表了宋初官方文人对小说知识功能的认识。其序“今臣寮若见《卓异记》,必如曹景宗之读列传也”是将小说的功能等同史传,内容指向正史史事之余。由此来看,宋初延续唐五代小说观念,小说在称谓上指向传统史志书目里子部下设的二级类目“小说”类,但在文本上已包含史部的一些杂史杂传类作品。
北宋中期,宋人笔记的数量突增,随之而来的是文人小说创作的趋盛,这其中包括一些政坛领袖对小说知识功能的肯定。如欧阳修为已故好友余靖撰写碑铭时赞其博学强记,“至于历代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外,暨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通”[9],他自己撰写的《归田录》被时人吴处厚《青箱杂记序》论为小说:“近代复有《闲花》、《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欧阳修编撰《新唐书》虽将小说归入子部,但对小说仍抱以史家的标准衡量,提出小说出于史官之流[10],遂采五代小说所载王凝妻李氏事入《新五代史》。此外,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也记载了一些在当时属于小说的见闻。
小说内容的庞杂和日常化则能从传统经典之外反映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咸平四年四月,宋真宗在崇政殿试贤良方正秘书丞查道、著作佐朗李邈、前定国军节度推官王曙、前奉国军节度推官鲁骧、进士陈越五人,制策曰:
朕奉祖宗,不敢失坠。思得天下方闻之士,习先王之法、明当世之务者,以辅朕之不逮。……十代之兴亡足数,九州之风俗宜陈,辨六相之后先,论三杰之优劣。渊、骞事业,何以首于四科?卫、霍功名,何以显于诸将?究元凯之本系,叙周召之世家,述九流之指归,议五礼之沿革。六经为教,何者急于时?百氏为书,何者合于道?汉朝丞相,孰为社稷之臣?晋室公卿,孰是廊庙之器?天策府之学士,升辅弼者谓谁?凌云阁之功臣,保富贵者有几?须自李唐既往,朱梁已还,经五代之乱离,见历朝之陵替,岂以时运之所系、教化之未孚耶?或者为皇家之驱除,开我朝之基祚耶?是宜考载籍之旧说,稽前史之遗文,务释群疑,咸以书对[11]137-138。
上述真宗的策问包含了对秦汉以来王朝史事、九州风俗的重视,及九流、五礼、六经、百氏等学说的思考,并就诸朝历史上人物将相的事迹设问,以冀求得教化治国之道。这些治国之道的答案在真宗看来,是要博览群书才能做到,朝廷求贤的重要标准是“方闻之士”,不仅要“习先王之法”,还要“明当世之务”。但是,追求广博之学又易造成科场士子所习泛滥无著。咸平五年十一月,河阳节度判官清池张知白上疏真宗详陈弊端:
进士之学者,经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诗赋策论也。故就试者惧其题之不晓,词之不明,惟恐其学之不博,记之不广。是故五常、六艺之意,不遑探讨。其所习泛滥而无著,非徒不得专一,又使害生其中,何为其然!且群书之中,真伪相半,乱圣人之微言者既多,背大道之宗旨者非一。……若使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题考试,不必使出于典籍之外,参以正史。至于诸子之书,必须辅于经、合于道者取之,过此并斥而不用[11]151。
张知白谈到科场士子为了解题,无暇深研儒家的五常、六艺之意,而广阅经史子集中各类典籍,以致泛滥无著,所习不专。他建议以后科举考试的命题仍要从儒家经典中命题,诸子之书中的言论必须辅于经、合于道取之。
张知白痛斥的科场士子所习泛滥之弊当包括以小说增广见闻的现象在内。虽然现存文献里关于小说与科举之间关联的材料不多,但仍能从中略窥一二。如太平兴国八年,文人李巽以《六合为家赋》登第,而他平日以《蜃楼》《士鼓》《周处斩蛟》三赋驰名[11]61。“周处斩蛟”典出《世说新语》。又雍熙二年,太宗于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颖川贡白雉赋》《烹小鲜诗》《玄女授兵符论》题[11]66。“玄女授兵符”见汉代纬书《龙鱼河图》,《太平广记》“女仙”类《西王母》引《墉城集仙录》在前人传说上予以敷演,详述九天玄女授符黄帝的故事。此二例均说明宋初一些士子应举往往熟习小说异闻。
随着北宋中期儒学的复兴,国家希望通过科举来规范整饬文人们的治学习尚。天圣七年,仁宗诏曰:
国家稽古御图,设科取士,务求时俊,以助化源。而褒博之流,习尚为弊,观其著撰,多涉浮华。或磔裂陈言,或会粹小说,好奇者遂成于谲怪,矜巧者专事于雕琢。流宕若兹,雅正何在?属方开于贡部,宜申儆于词场:当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探典经之旨趣,究作者之楷模[11]289。
文人竞尚博学,著撰多涉浮华,标志之一是会粹小说,“好奇者遂成于谲怪”。但是,唐宋社会文化的转型使士大夫们更重视现实世界里日常生活的思考,源于街谈巷议和文人宴坐侍谈的小说异闻在此时恰恰以其日常化、小道之言成为辅助文人重构儒家学说的支流之一,如欧阳修采五代小说入《新五代史》即是例证。即便之后举子就科场考试题目竞务新奥而广阅群书[11]357,出于文人自身的文化诉求和日常生活需要,小说在当时也有一定的文人阅读群体和影响力,至少有部分文人将之作为补充自身才学的来源。
二、《高僧传》:《太平广记》对僧传“异”文化的知识选择与建构
当小说或多或少承担起知识功能的时候,编者的文本编排便反映出对知识的选择与建构。《太平广记》“异僧”类反映了宋初官方文人对佛教人物的选择喜好与知识倾向,在引用文献方面,表现为对佛教僧传经典《高僧传》的知识选择与建构。
《太平广记》“异僧”类71人,收《高僧传》人物依次为释摩腾、竺法兰、康僧会、支遁、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杯渡、释宝志9人,占《太平广记》“异僧”类人物的八分之一。“异僧”类隋唐以前的僧人17人,引《高僧传》中的僧人比例近53%。虽然《高僧传》是《太平广记》异僧类中引用篇目最多的引书,《太平广记》“异僧”类却未如《太平御览》“僧”类和“异僧”类那样,将《高僧传》人物作为僧史系统的核心。
《高僧传》的内容性质介于小说和百氏之间。全书的文本形态近于史部杂传类,思想内容涉及各种典故异闻和内学[12]。因此,《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异僧”类都将其作为引书。那么,是什么造成《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所引《高僧传》的差异呢?显然,还是与两书的内容性质不同有关。《太平广记》所收篇目基本为小说,《太平御览》所收篇目属于百氏。
小说和百氏在文人知识结构中不同,生活中的功用也不同。两者都是六经以外的非主流知识,自汉代以来一直在官方图书目录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唐以后,不仅小说成为文人知识见闻中的部分,一些倡导儒学的文人在其学术思想中更表现出对百氏的吸纳。如韩愈自称“仆少好学问,自六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也”[13]。百氏与小说入宋后亦都是文人知识结构中的内容。前述真宗咸平四年殿试贤良方正时“百氏为书,何者合于道”的疑问即表达了对传统学术思想中百氏一系的关注。宋人多有将百氏、小说并称[14]。就学术价值而言,来自诸子百家的百氏比内容庞杂的小说更重要。《太平御览》引书以正史和诸子之书为主,表现出较规范的学术严肃性。了解《太平御览》“异僧”类人物的收录,有助于我们从小说视域探讨《太平广记》“异僧”类僧史系统的思想史因素。
《太平御览》“异僧”类前设“僧”类,大略相当于佛教高僧思想言行经典的总叙。这些高僧的生活年代除玄奘一人为唐代外,其余均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可见这一时期高僧的思想言行是李昉、扈蒙、李穆等编纂官较为关注的。这种关注既有对早期佛教高僧为代表的教义教派的推崇,也隐含对佛教自身发展中与儒道文化相融合过程的肯定。如“僧”类的前三位高僧是引自《宋书》的竺道生、释休善和慧琳。竺道生为东晋高僧,提出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倡导顿悟成佛。释休其人事迹不见僧传,但他善属文,后奉孝武帝命还俗,位至扬州从事,其个人经历颇有半文人半僧人的色彩。慧琳有才章,兼内外之学,其事迹在《高僧传》中事附《道渊传》,但却名列“僧”类第三。主要原因或与其所著《均善论》有关。《太平御览》“僧”类引用了《均善论》中的一段文字:
有白学先生以为中国圣人经纶百世,其德弘矣,智周万变,天人之理尽矣。道无隐旨,教罔遗荃,聪睿迪哲,何负于殊论哉?有黑学道士陋之,谓不照幽冥之途,弗及来生之化,虽尚虚心,未能虚事,不逮西域之深也。为主客酬答。其归以为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伍[15]。
身为佛门中人,慧琳认为中国圣人经纶百世,其德弘矣,智周万变,已将天人之理尽矣,“黑学道士陋之”的评语俨然暗含对佛教徒固守教义的批评。因《均善论》倍受佛门争议的慧琳之所以受到《太平御览》的重视,缘于他以儒家道论为宗。
不离儒家道论是《太平御览》释部的重要编纂思想。编纂《太平御览》的文臣是宋初文坛的精英,他们的佛学观点在各自的文集中难以梳寻。但王禹偁提到参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两书编纂的李穆与高僧赞宁交好,李穆“儒学之外,善谈名理,事大师尤为恭谨”[16],由“善谈名理”一语来看,李穆应该熟悉六朝僧人与文士的清谈逸事。
此外,佛教徒撰写的僧传一方面语言较文人传记失之杂乱粗浅,另一方面内容上表现出因宗派繁复而互相攻讦。北宋中期,有僧人进言惠洪重修僧史,批评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和赞宁《宋高僧传》在内容撰写上难与儒家正史相比。这种批评的声音与当时部分文人相合,黄庭坚曾欲重新整理出符合文人学术标准的僧史,惜未遑暇,竟以谪死。
以上种种或许能补充说明:《太平御览》“僧”类和“异僧”类不以弘扬佛教义理和宗派为主①《太平御览》“异僧”类节录《高僧传》传主事迹时,有时删去其师承门户文字。如“异僧”类录释法安事,删去《高僧传》载其为慧远弟子的文字;“异僧”类录释昙邕事,删去《高僧传》载其从道安出家又南投慧远为师的文字。,重在收录早期玄学思潮影响下的佛教高僧,引录唐代《高僧传》仅两篇,对隋唐佛教众多宗派代表人物简单略过。
《太平御览》“异僧”类为异僧单设一类,引《高僧传》中人物大多节选本传所载神异事迹。如“异僧”类录竺法崇事仅35 字,叙山精化为夫人诣崇请戒;有些僧人是《高僧传》传主事迹所涉人物,如群鸟衔果飞来授僧伽达事节自《高僧传》中《畺良耶舍传》,宝意念神咒事节自《高僧传》中《求那跋陀罗传》。“异僧”类的知识视角建立在百氏的基础上,但重在记叙《高僧传》人物的神异事迹,与六朝至宋初僧传越来越重视僧人神异事迹的倾向一致[17]。
明了《太平御览》“僧”类和“异僧”类的人物收录,再深入比较《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便会发现同样是奉《高僧传》为僧史经典,庐山教团的僧人领袖慧远、《肇论》作者僧肇等俱没有被收入《太平广记》“异僧”类。《太平广记》虽在尊崇早期佛教流传史这点上弱于《太平御览》,所录《高僧传》人物还是具有一定的佛学识见,引《高僧传》人物依次为:释摩腾、竺法兰、康僧会、支遁、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杯渡、释宝志。除释摩腾、竺法兰是《四十二章经》的译者外,康僧会是三国时期江南佛教的初创者,所译佛经“具有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印度经典予以改编的强烈色彩,就中国佛教思想史而言,其意义十分深远”[18]51。支遁是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道安是本无宗的代表人物。佛图澄为道安之师,北方佛教的传教代表。鸠摩罗什是著名佛教翻译家,所译佛经对中国佛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杯渡和释宝志则是南朝佛教史上以神异著称的高僧。
较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更注重高僧事迹的详细神异,二书所录引《高僧传》人物有重合。《太平广记》“异僧”类释摩腾、竺法兰、康僧会、支遁、道安5 人见录于《太平御览》“僧”类,鸠摩罗什、佛图澄、杯渡、释宝志4人见录于《太平御览》“异僧”类。
据《高僧传》记载,释摩腾是早期来中国传法的第一位高僧,他和竺法兰均翻译了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太平御览》“僧”类依引书正史在前、僧传次之的顺序将释摩腾、竺法兰列于竺道生、释休、慧琳、支遁、竺法仰、惠岩、惠议诸人之后。《太平广记》则依时间顺序列释摩腾、竺法兰于“异僧”类前两位,所引《高僧传》文字详于《太平御览》,释摩腾讲经和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文字保留甚多。
又汉明帝梦金人事初载《后汉纪》,《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三“叙佛”类引《后汉纪》记录了这段材料,但在“僧”类叙释摩腾事迹时予以略过。《太平广记》引《高僧传》叙明帝梦金人后,遣蔡愔、秦景往天竺寻佛法,后遇释摩腾,邀还汉地。这样的记载无疑增加了释摩腾其人的神异色彩。
《太平广记》“异僧”类其他《高僧传》人物也凸显出强烈的神异色彩,其中支遁和佛图澄二人的选录鲜明地体现了《太平广记》的小说视角。支遁与当时名士谢安、王羲之、郗超等人交往密切,所注的《庄子·逍遥游》被时人称为“支理”,他是东晋佛玄交流会通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贡献最突出的人物[18]150,其佛学思想具有玄学色彩。《太平御览》“僧”类著录支遁事迹时引《建康实录》《支遁传》二书,所引文字简略,近于介绍名士典故逸事,描述的支遁带有隐士形象,与历史上结交知识人士、不以神异眩人的支遁基本相符[18]166。
而《太平广记》“异僧”类引录了《高僧传》中支遁事迹的主要内容,保留了支遁幼时受其师神异之术感悟蔬食的文字,既详细介绍了支遁的生平,又凸显了支遁的神异色彩。
《太平御览》“异僧”类引《晋书·佛图澄传》,主要介绍佛图澄善诵神咒、听佛铃辨吉凶、洗肠等民间流传的神迹。《太平广记》则将佛图澄单列一卷,表现出对佛图澄的钦赏,这当同佛图澄以神异传教有关。《高僧传》述佛图澄以异术慑服石勒,使之慎于杀戮,时中州之胡,皆愿奉佛。后又凭咒术、听铃音辨吉凶在后赵预测军国大事,救度大臣,倡导仁政。颇具意味的是,《太平广记》“异僧”类保留了大量《高僧传》中北方后赵暴君石虎敬奉佛图澄的事迹。这其中包括中书著作郎王度维护传统儒家典制,提出佛是出西域,外国之神,华戎异制,国人不应诣寺烧香礼拜。石虎则回以只要于事无害,不必拘守前代定制。夷夏之争一直是儒、释两家辩论的话题,《太平广记》“异僧”类记录王度、石虎二人的言论隐含对宋初奉佛思潮中异声的审慎回应。
佛图澄是《高僧传》“神异”类的代表人物,《高僧传》“神异”类“论”强调了神异对于维护佛教神圣性的重要:
神道之为化也,盖以抑夸强,催侮慢,挫凶锐,解尘纷。至若飞轮御宝,则善信归降;竦石参烟,则力士潜伏。当知至治无心,刚柔在化,……渊、曜篡虐于前,勒、虎僭凶于后。郡国分崩,民遭屠炭。澄公悯锋镝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骋悬记于襄、邺。籍秘咒而济将尽,拟香气而拔临危。瞻铃映掌,坐定吉凶,终令二石稽首。……但典章不同,祛取亦异。至如刘安、李脱,书史则以为谋僭妖荡,仙录则以为羽化云翔。夫理之所贵者,合道也;事之所贵者,济物也。故权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务[19]。
上文中述及神异的力量是为了抑夸强、催侮慢、挫凶锐、解尘纷。佛图澄通过神异之力使石勒、石虎这类暴君礼敬佛法,少行杀戮,德行功业无可比拟。对神异之事的祛取随典章而论,刘安、李脱在正史中被视为谋逆妖荡,在道书仙录中被视为羽化仙人。通权达变者虽反常而合道,合理利用就能成就事功。
以之来解释《太平广记》“异僧”类对佛图澄的钦赏亦无不可。与同时期高僧相比,佛图澄没有在佛教思想上有所建树,他主要通过神咒、幻术、预言等方法在北方传教,传教方式更贴近知识素养不高的群体,亦更能让人从世俗信仰的实践层面理解佛教。
三、道宣:“异僧”类融汇感通与述异思想的律宗祖师
《太平广记》“异僧”类在尊奉《高僧传》为僧传经典的前提下,强化了《高僧传》人物的神异事迹,“异僧”类所录人物均是具有神迹的僧人,构建了一部小说视域下的佛教神通人物传。这种构建思想是基于《太平广记》之前的各种感应、神通小说而形成的佛教史观。关于佛教史籍中的大量感异事迹,“宋道发先生提出了以感应史观与神通史观去理解佛教史籍中的相关内容,这样才能使有关感通的事迹有了佛教语境下的合理性,能够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此类记载所具有的历史与宗教意义。”[20]
以感通宣扬佛教的神圣性究其源流当追溯至六朝时期的各类宣验小说和异僧传记。《高僧传》“神异”类代表了当时以神异弘法的观点,将佛图澄作为以神异传教的高僧代表。《太平广记》“异僧”类在《高僧传》“神异”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改造,使佛教的神异观与儒道文化相融合,具有践行现实人生各层面的特点。这一思想在《宣律师》篇的引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异僧”类《宣律师》引自《法苑珠林》“敬佛篇”“感应缘”之《唐故净业寺天人感应缘》,文体异于“异僧”类其它篇目,近于佛经中的佛答弟子问形式。《法苑珠林》辑录了大量异僧事迹,《太平广记》独引《唐故净业寺天人感应缘》,改名为《宣律师》,并单列一卷,可见是有意彰显道宣。
那么,该如何看待《宣律师》在《太平广记》“异僧”类中的意义呢?这要从道宣在唐代佛教史上的影响谈起。道宣开创律宗,佛教史学成就斐然,著《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等。但他也有大量佛教感应、神通类的著述,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遗法住持感应》《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等,“道宣对这类感通事迹的喜爱,正是他追求‘神圣’的体现,……以道宣的学识,他自然知道经典中对相关历史的记载是如何,但他宁可选择更神秘的感通故事,来树立佛教的历史,这正是他刻意宣扬佛教神圣性的用心。”[21]
《法苑珠林》中《唐故净业寺天人感应缘》的内容来自道宣本人所作《道宣律师感通录》,《宣律师》为道宣从世俗层面对佛、经、寺在民间一些传说的解释。该篇以道宣与天人的对话为主,借天人之口回答了佛祖遗骨舍利入东吴,佛教四方天下的划分,《感通记》中的种种感应,目连与舍利佛显迹人间等佛教传说中的问题。在对话中,天人的很多回答将佛教与中国古代传说联系在一起。如提到夏桀时已有佛之垂化,周穆王游大夏曾遇佛,并为文殊造寺供养。又引《玉篇序》提出隶书之兴,兴于古佛之世。苍颉其人,罕知其源。这些说法里,佛入汉地同中国古代帝王传说人物周穆王交糅在一起,苍颉造字的传说被淡化,隶书的兴起可追溯古佛之世。儒家文化的传统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与佛教有了共同的时空联系。
道宣的另一部著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也收录了一些感应缘故事,这些故事里,不仅有象道安、安世高这样的佛教著名高僧以及释遗俗、史呵誓这类民间异僧,也有严恭、陈公太夫人这类信佛俗众。道宣的感通思想广泛指向僧俗两类,并同中国本土祥瑞、志怪的述异传统融合在一起。《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瑞经录序》云:“然寻阅前事,多出传纪。《志怪》之与《冥祥》,《旌异》之与《徵应》,此等众矣,备可揽之。”《瑞经录序》中明确提到《志怪》《冥祥记》《旌异记》《徵应记》这类书籍是佛教感通故事的来源。《法苑珠林》也载录了大量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未予收录的感通之事,“传记篇”“感应缘”之《叙三宝感通灵应嘉祥意》引用了《瑞经录序》,赞同道宣引中国本土述异传记入佛教感通故事的观点。各篇“感应缘”里大量引用中国本土典籍中的奇人异事,“神异篇”“感应缘”里引用13部,分别是《述征记》《神异经》《临海经》《地镜图》《晏子春秋》《述异记》《吴录》《晋阳秋》《搜神记》《博物志》《抱朴子》《孙绰子》《玄中记》,占“神异篇”“感应缘”17部引书的76%,可见《法苑珠林》广泛吸纳中国本土的述异材料来阐发佛教神异观念。
道宣和道世为同学,在调和儒、释、道三教的感通、述异思想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法苑珠林》“千佛篇”“灌带部”引《道宣律师感通录》称道宣所撰佛教各类结集仪式、偈颂、灵验等为天人嘱说,则道世的佛教感通思想亦受道宣影响较深。
正因为道宣在所作感通著述中多以与天人对答的面貌阐说佛教感通事迹,所以道宣本人在佛教传播中被渲染成具有灵验色彩的高僧。道宣曾随玄奘在西明寺译场译经,《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道宣被描绘成“有感神之德”,所译律钞得天神指正。这一传说为宋初赞宁编撰《宋高僧传·道宣传》沿用。《宋高僧传·道宣传》载录各种道宣相关的神异之事,其中包括毗沙门天王之子那吒送道宣佛牙的感通故事。道宣与佛牙的传说曾引起宋初官方的争议,其事见王珪《左街大相国寺释迦佛灵牙序》:
道宣律师居长安西明寺,忽一夕足跌庭下,有异人者捧而登,曰:“吾五方天使也,以师有妙行,与北方毘沙门多闻长子那吒偕来卫师。”道宣因问佛所宣言教。那吒自言:“我尝见佛,当佛灭时,帝释下取佛牙有二。捷疾蔽身于茶毘处,亦得佛二牙。今以一奉师。况师持静密戒,即心为境,乃是亲见如来。”那吒去,道宣宝之,众莫得闻。后授其徒文纲,葬长安崇圣寺塔下。至代宗出之,会昌中复还西明。宣宗时,有檀越张义均者,別建塔于崇圣寺以安之。凡都人有祈,嘉应屢见。昭宗幸洛阳,奉牙置天宮寺。涉五代之乱,亦晦其缘。艺祖受命,以道宣所传得之天神,且疑非真佛牙,遣使取自洛,以烈火鍛之,定果之色,了然不动,因而制愿文。太宗又验以火,为制伽陁文。于是更大相国寺灌顶院为法华院,建重阁院中,以奉佛牙[22]。
《左街大相国寺释迦佛灵牙序》记载了那咤授道宣佛牙的传说,并述宋初太祖因佛牙为道宣得之天神,疑其真假,以烈火锻之。太宗亦验佛牙以火,锻试后更大相国寺灌顶院为法华院尊奉佛牙。太祖、太宗二帝重视佛牙之验说明宋初官方对佛教的推行持审慎态度,以天神授道宣佛牙为代表的感通故事因过于神妙而难辨真假。这在《太平御览》中也有所反映,《太平御览》“叙佛”一方面引《异国记》述佛牙灵验,另一方面却收录韩愈的《论佛骨疏》,保留疏中“乞以此骨付有司投水火”的文字。不过,太宗供奉佛牙最终推动了宋初官方崇佛政策的实施,道宣及其本人相关的感通事迹在宋初的影响由此提升,这是《太平广记》“异僧”类单列《宣律师》为一卷的重要原因。
《太平广记》“异僧”类推崇道宣及其融入中国本土述异观念的感通思想,为了进一步强化“神异”之中国本土色彩,“异僧”类收录的隋唐人物除道宣外均来自文人笔记,这其中不乏如玄奘、万回、一行、无畏、华严和尚这类唐代名僧,但更多的是民间僧人,此外还引录了徐敬业、骆宾王出家为僧的传说。较之佛教徒撰写的僧传,文人笔下的异僧事迹淡化了佛教感应灵验色彩,一些僧人的异事近于方士、异人。如《一行》中一行以瓮封藏化为猪的北斗七星。类似北斗七星化降人间的情节见“方士”类《李淳风》,该篇写李淳风奏请太宗候取化为僧人的北斗七星。再如“异僧”类《明达师》,僧人明达能预知吉凶,往来过客皆谒明达以问休咎。“异人”类亦多预知吉凶者,不逊僧人,《宋师儒》述异人宋师儒在预知吉凶的能力上胜过僧人常监。
显然,《太平广记》“异僧”类在讲述佛教史上著名高僧神异事迹的同时,将目光更广泛的投射到民间僧俗群体,民间僧人的神异面貌间有与异人、方士相同者。而除“异僧”类外,《太平广记》其它类目亦收录有异僧传记,“异人”类有《王梵志》《苏州义师》《建州狂僧》,“方士”类有《泓师》《慈恩僧》《岳麓僧》。《太平广记》“异僧”类的神异观念在承接《高僧传》“神异”类和道宣感通思想的基础上引入更多中国本土述异传统。其后,赞宁《宋高僧传》取材文人笔记中的高僧人物事同《太平广记》“异僧”类者计19 人[20],占《太平广记》“异僧”类隋唐僧人总数的35%,足见《太平广记》“异僧”类构建的僧传系统在融合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余论
就学术价值和严肃性而言,《太平广记》显然弱于纂集百氏的《太平御览》,《太平御览》不便收录的许多篇目进入了《太平广记》。两书选录的高僧有重合,《太平广记》基于小说的娱乐性、文学性和庞杂性,所录人物事迹或更丰富详细,或更奇异有趣。“然末俗多敝,护其法者,有非其人。或以往时丛林,私于院之子弟,闭门治产,诵经求利,堂虚不登,食以自饱,则一方之民失所信向矣。通人高士,疾之茲久,而未克以澄清。”[23]五代末期,流民涌入禅林,丛林禅文化加速了对传统佛教的瓦解。《太平广记》“异僧”类反映了这种佛教知识信仰下倾民间的趋向。宋初官方在尊奉《高僧传》为僧传经典的同时,重点关注其人物的神异事迹。隋唐以后的众多佛教宗派高僧只有道宣、玄奘、一行等少数人见录于《太平广记》“异僧”类。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忽视《太平广记》“异僧”类所传达的其他佛教知识信息。
道宣开创的律宗在宋初佛教仪式的践行中具有典范意义,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云:“今右街副僧录广化大师真绍先募邑社,于东京大平兴国寺,造石戒坛,一遵南山戒坛经。宏壮严丽,冠绝于天下也。”赞宁专习南山律,入宋后得太宗赐号通惠大师,咸平元年,充右街僧录,以道宣的佛学成就和宋初僧官尊奉南山律来看,四分律的流传本应在《太平御览》有所记载,然而不仅道宣事迹未被《太平御览》“僧”类和“异僧”收录,道宣律学基础中的四分律也不载《太平御览》“戒律”类。“戒律”类首引《梁书》叙江革、陶弘景等人受戒事,后引《高僧传》叙弗若多罗、鸠摩罗什诵十诵律。李昉、扈蒙等人对道宣的认识似乎主要缘于其佛教感通事迹而不是律学成就。
道宣撰《续高僧传》为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立传,却对禅宗一系隐有不满[24],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亦提出“夫释迦之经本也,达磨之言末也。背本逐末,良可悲哉”。《太平御览》“释部六”列“禅”于“戒律”之后,“禅”类引《宝林传》述禅宗南宗祖统。然《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未录达摩、慧可等人事迹。这些或许说明,宋初官方对佛教的弘扬偏重于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世俗信仰层面,禅宗一系在宋初尚未得到官方的特别重视。关于此一论题,笔者将在今后撰文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