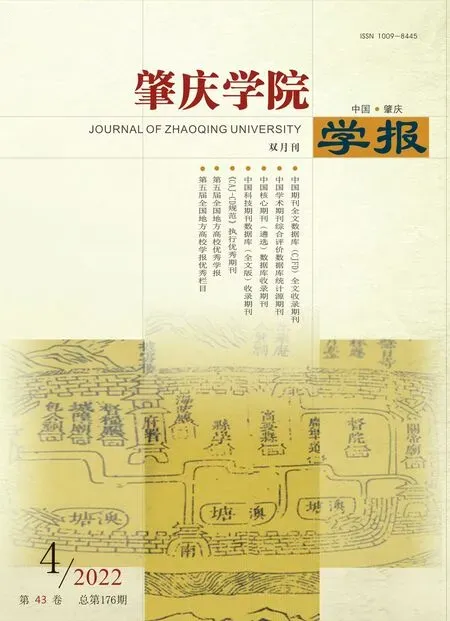肇庆七星岩与德庆三洲岩“东坡题刻”考略
温爱民
(广东省德庆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广东 德庆 526600)
一、引言
北宋权相蔡京与苏轼不和,除政治上的打压外,还极力贬低苏轼在文学、书法上的成就,以“元祐党人”罪名,“诏毁”苏氏文集、碑刻等,致使苏轼虽在岭南多年,但留存在岭南的题刻真迹并不多见。以金石学著称的翁方纲著《粤东金石略》一书,曾遍搜苏轼在岭南的题刻真迹,未得片言只字,留下“(韶州)苏文忠九成台铭,以元祐党事碑毁台废”的慨叹。苏轼留在岭南的题刻真迹,唯德庆三洲岩“北归题刻”完好,尤显珍贵,诚为研究苏轼晚年行迹和书法艺术的重要史料。历史上,三洲岩苏轼“北归题刻”曾一度消失,在粤东金石界引得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一说此刻在德庆三洲岩,因“党禁”已遭磨灭;一说此刻在肇庆七星岩黑岩中;亦有说三洲岩、七星岩均有苏刻。本文根据历史文献梳理分析,揭示、重构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二、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辑录“苏刻”所据存疑
肇庆七星岩因有唐代李邕《石室记》摩崖石刻而名闻岭南,但因“沥湖”水浸、交通不便等原因,直至明代尚未广为人知。
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肇参将钟坤秀邀广东参政吴桂芳游七星岩,众人“因念此岩僻在岭海,轩盖罕临,声称未著……缔观岩下苔藓满目,荒秽成丘,共为兹岩大惜”[1]356,于是,吴桂芳提议修葺开发七星岩,遂带头捐俸,“伐石于山,鸠工于肆,引石为梯,直抵岩所……凡旧所未备者益之,污漫不饰者除之”,谓七星岩之辟建“自余今日始”[1]357。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桂芳任两广提督,同年将提督府由梧州迁至肇庆,肇庆成为两广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吴到任后整饬军务、发展农桑,大规模辟建七星岩景区。自此大批深藏岩洞中的珍贵石刻,如李邕、李绅、周敦颐、包拯等名人题刻得以为世人所知。
苏轼在肇庆七星岩留有题刻的记载,始见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郑一麟修纂的《肇庆府志》。其在“古今题名”条下,辑录“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一条[2]134,在粤东金石界曾引起关注。一般情况下,著录金石是要据“原刻”或据“石本”,其次是据“版本”,那么郑《志》辑录该条所据何本?不得而知。
自嘉靖末吴桂芳辟建七星岩景区至万历间郑一麟修纂《肇庆府志》,民间搜碑拓印盛行,一些民间拓碑高手将石室岩洞中诸多珍贵石刻拓出,流传于市,这也为郑《志》著录金石、补阙郡志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推测郑《志》辑录该条或有可能录自“原刻”。但翁方纲著《粤东金石略》时,曾往返七星岩寻找该刻,以翁氏团队之搜拓能力竟“遍搜不获”。由于找不到“原刻”,似也未获“石本”,故翁氏并未正式著录此条,只是根据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版本”所记,将其放在“七星岩诸刻”中作“附录”存留[3]275。据此,郑《志》辑录“苏刻”条录自“原刻”存疑。
就“版本”而言,在郑《志》之前,尚有两部著名的地理类书可供分析参考。一部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刊行的何镗著《古今游名山记》。何镗(1507—1585),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广东潮阳知县,擢广东按察使,任职期间曾多次到端州,对七星岩摩崖石刻有较深的研究。据明陆鏊《肇庆府志》记载,何氏有《游七星岩记》存世[4]888,但均未提及七星岩有“苏刻”的任何信息。
另一部是万历四年(1576)慎蒙撰《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此书是在何镗《古今游名山记》基础上“删繁削冗,复纂诸通志所未及者”①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自序,第2页。本文所引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来自个人收藏旧书电子版,出版信息不详。下同。,如其在自序中述及:“近得同年友何宾岩(何镗号宾岩)所辑名山一书,则自胜纪、名言以至先贤题名刻石巨细毕举”②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自序,第2页。;并谓此书“本何宾岩名山记者十之六,而增通志及别集所得记文者十之四”③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凡例,第1页。。由此可知,“慎本”是在“何本”基础上增补而成,期间正是七星岩辟建之初,碑拓大量流出之时,内容增加近半。值得注意的是,慎蒙在“名山记”中辑录了“(德庆)三洲岩宋周敦颐尝游,苏轼有题识及李纲书玉乳岩三字,俱存”④慎蒙《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卷11,第9页。等信息,说明慎蒙对苏轼的题刻比较关注,但并未提及七星岩有“苏刻”的片言只字。
综上所述,郑一麟《肇庆府志》辑录“苏刻”条录自“版本”所据存疑。
崇祯三年(1630),明代史学家曹学佺编撰《大明一统名胜志》,采录了郑《志》辑录的“苏刻”条目。曹氏所辑“苏刻”有两处:一处是该书“古今题名”条下辑录七星岩“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一条⑤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广东名胜志》四册卷6,第6页。本文所引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来自个人收藏旧书电子版,出版信息不详。下同。;另一处是辑录德庆三洲岩“东坡居士自海南还来游,武陵弓允明夫、东坡幼子过叔党同至,元符三年九月廿四日”一条⑥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广东名胜志》四册卷6,第25页。。审其文句,曹氏版本明显受郑《志》的影响,抄录痕迹明显。曹学佺在《名胜志·序》中述及:其收集资料为“沆观四库诸书,凡可为各省山川名胜资者悉标识其端”⑦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北直隶名胜志》首册自序,第2页。。也就是说,他将各省《通志》《府郡志》、文人《笔记》等文献定为收集资料的重要来源,但又未必“每景必到”,这就为误录留下了空间。因此郑《志》将王化清《游石室新记》误为李邕《石室记》[2]134,曹学佺《名胜志》也照抄不误⑧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广东名胜志》四册卷6,第5页。。众所周知,李邕《石室记》在石室岩洞口外,而王化清《游石室新记》则在洞内。这说明曹氏确未到过七星岩,以致以讹传讹,为人诟病。这也说明郑《志》“金石门”辑录石刻比较粗糙,条目未经详考。
方志之讹误,影响甚远。崇祯六年(1633),肇庆知府陆鏊修纂《肇庆府志》,辑录“苏刻”条目时,既未订正郑《志》的讹误,反而将德庆三洲岩苏轼“北归题刻”条合并于七星岩“苏刻”条,凡增十五字,中段改为“东坡还自海南重游”,全句衍为:“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东坡居士还自海南重游,武陵弓允明夫子过叔党同至,元符三年九月念四日也”[4]910,值得注意的是,同书又将苏氏“北归题刻”记在德庆三洲岩条下[4]914。至此,苏轼“北归题刻”出处出现了重复。
很明显,“东坡还自海南重游”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陆《志》署“重游”时间为“元符三年九月念四日”,与苏轼游德庆三洲岩为同一天。德庆三洲岩至肇庆七星岩相距百余里,以当时的交通水平,并不具备一天游两地的条件。因此,一直有人质疑郑《志》所辑“苏刻”条的真实性。
崇祯五年(1632),南海人陈子壮游七星岩,所撰《游端州石室记》就明确指出“眉山挈家已疑傅会……”[4]894,也就是说陈子壮否定七星岩有“苏刻”的存在。陈子壮(1596—1674),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历官编修,累迁礼部右侍郎。而陆《志》既收录了陈氏《游端州石室记》一文,就应该知道七星岩并无“苏刻”或存疑,然陆《志》不仅未作订正,反而使之复杂化(衍文)。
三、肇庆七星岩专著梳理分析
为进一步说明七星岩有无“苏刻”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梳理历史上曾流传的几种七星岩专著,看有无“苏刻”的记载。
(一)王泮《石室志》。万历八年(1580),肇庆知府王泮组织撰写星岩《石室志》,并亲为作序。王泮在《序》中述及:“而岩故无志,仅得学博梁君手录草本……于是以嘱别驾陈君,陈君乃参稽互考、删繁补略各得其宜”[5]。据此,王泮《石室志》应该是最早一部关于七星岩的专著,可惜该书未能传世,所载内容不得而知。
(二)李开芳《星岩志》。万历二十七年(1599),岭西分巡道李开芳在星岩四周树界碑,以杜民之伐石。以刘克平、朱完、苏景熙、区怀瑞四人重辑王泮《石室志》,改名为《星岩志》。修志之事,见于李氏《重修七星岩记》[4]893。此为七星岩第二部专著,可惜该书亦未能流传至今。
(三)吴绮、韩作栋《七星岩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岭南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齐聚星岩,商讨修订《石室志》之事,有题记刻于星岩石壁,如录:
康熙癸亥仲冬十有九日,江都吴绮园次、秀水吴源起准庵、海盐曹燕怀石阊、顺德陈恭尹元孝、嘉善蔡鸿达去闻、嘉兴缪其器受兹、嘉善柯崇朴寓匏,凡七人,分韵赋诗于星岩之上……。晋庵主僧寂隆真际,出《石室志》请共商订。观察鄜州韩公作栋公吉,因受诸梓。嘉会难常,盛事不朽,题名石壁,与此山并存云尔。[6]
韩作栋时任分巡肇高廉罗道按察司佥事,因重修《石室志》,改名为《七星岩志》,共十六卷。这次修志,虽群贤毕至,但实以岭南大家齐聚唱和、分韵赋诗为主,仅吴绮为之润色,并未重新补阙考核,盖沿曹学佺《名胜志》所载增益,讹误较多。如道光《肇庆府志》引《四库全书提要》所论:
……志本明王泮所撰,作栋因而重修,吴绮又为之润色。然有关考核者寥寥无多,如石刻门于唐李邕石室记后乾道己丑秋一条,以后人题名之年月误为摹石之年月。又载元符元年苏轼正在儋州,安得有挈家至七星岩之事?盖据曹学佺名胜志所载,而不知为傅讹之文也。[7]778
《七星岩志》乾隆间仍传于世,该书《四库全书》未录,今亦不存。
此《四库提要》即翁方纲所撰,翁氏对苏轼题刻尤为关注,为获得一手资料曾往返七星岩寻找苏氏真迹,冥搜不可得,始疑之为傅讹之文。因此著《粤东金石略》时并未正式采录“元符改元……挈家来游”条,只以曹氏“版本”作“附录”存留。翁方纲对曹学佺《名胜志》和韩作栋《七星岩志》有关收录“苏刻”条目分别作过考证:
附录《名胜志》一条: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按:元符元年戊寅,苏公在儋州,安得有端午日挈家游端州之事?且是时,公在儋州并无家室,亦不得云挈家矣。志书记载之讹,类如此,特辩正之。[3]275
然此志亦载元符改元苏刻云云,则亦未尽足据也。《七星岩志》十六卷,国朝康熙癸亥关中韩作栋辑,附记于此。[3]271
(四)黎汉杰《星岩今志》。1936 年高要黎汉杰撰。该志体例详略得当,考核精详,石刻、诗文、营建、方物尽括其中,而将七星岩有关“苏刻”讹误条目删去不录。
(五)刘明安主编《七星岩志》。1989年,星湖管理委员会刘明安主持编撰星岩专著,由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是志共辑地理、风景、营建、文物、历史沿革等共十六篇,尤对摩崖石刻的搜集整理着力较深。该书“旧有可考,新有可观”,但并无辑录有“苏刻”条目。
(六)刘伟铿等编辑《肇庆星湖石刻全录》。该书1986 年铅印出版,共收录唐宋至清星湖石刻500 则,并无著录“苏刻”的任何信息。1994 年,刘伟铿校注《肇庆星湖石刻全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附录”将上述七星岩“苏刻”条列为“今寻未见石刻”,并指出“该(条)日期与仪克中在德庆三洲岩掘得的苏轼石刻日期相同,尤不可解。”[8]
综上著述,均不认为七星岩有“苏轼挈家来游……重游”题刻存在。
四、德庆三洲岩“东坡北归题刻”概述
元符三年(1100),苏轼于海南儋州获赦,“以徽宗登极恩移廉州(今合浦)安置”[9]1323,又“诏苏轼等徙内郡居住”[9]1326。苏轼旋取道廉州、容县、藤县至梧州与长子苏迈汇合,沿西江而下,经三水折入北江度岭北归。途经康州(今德庆)时,在三洲岩登岸游憩,留下“东坡居士自海南还来游,武陵弓允明夫、东坡幼子过叔党同至,元符三年九月廿四日”题刻,记录了东坡遇赦北归时留在岭南的最后行迹。
明崇祯间,苏轼“北归题刻”仍存三洲岩。据清康熙《德庆州志·艺文》,明人李逢升有《三洲岩记》云:“洞之北,峻壁词章,苔封剥落则苏文忠、祖无择之诗记也……”[10]320。显然此时苏轼题刻依然完好,只是年代久远“苔封”而已。
但乾隆间翁方纲据此到三洲岩搜剔苏刻,竟又寻之不获,也不知“此段石崖何年劈去,其旁犹有东坡遗迹四字可辨”[3]306。由于三洲岩苏刻神秘消失,翁方纲只能据《德庆州志》(版本)著录“苏刻”,注明此段文字非录自“原刻”,将其排在《粤东金石略》“三洲岩诸石刻”之末,以示区别。
明清时期,三洲岩屡遭地震、雷击的破坏,刻有苏东坡、周敦颐、祖无择、李纲等题刻的北岩口发生大面积坍塌,岩体连同石刻悉数坠落北洞口而湮没,此后仍不断受到人为或自然的破坏,原有二百余则诗词、题名石刻,现仅存九十余刻。康熙《德庆州志·山川》记载了三洲岩北岩口崩坠后的情况:“三洲岩,昔门在北,为石所压……,康人李逢升另劈一门,从西入洞”[10]161。清举人梁修在《三洲岩记》中也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三洲岩两口可入,南口绝狭而险,北口洞若巨门,容旋马……或云康熙间雷起此岩,震石落,巨若屋,字当在石下”①梁修《三洲岩记》辑自民国《德庆县事半月刊》残页,现存广东省德庆县档案局。。据此可推定,北岩口坍塌当在明末清初。此时北门(北岩口)堵塞,三洲岩大部分石刻、尤其北宋石刻,多集中在北岩口,因此,几乎所有北宋时期的石刻均因岩体崩坠而湮没。虽然李逢升另辟一门入洞,但北岩口诸石刻压于巨石下已无迹可寻。这与翁方纲当年看到的情况一致,北岩口被坠石所压,西江潦水淹至岩腹,题刻半湮沙土,翁氏因与“苏刻”真迹失之交臂,仅看到后人所刻“东坡遗迹”四字。
值得庆幸的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洲岩《东坡北归题刻》被民间拓碑高手仪克中发现。仪克中(1793—1834),先世山西太原人,寄籍广东番禺,曾到德庆三洲岩采访古刻。嘉庆二十五年,仪克中受两广总督阮元破格提拔,以布衣身份参修《广东通志》,任职采访[11]。仪克中奉阮元之命,遍历岭南各府、州、县,缒幽跻险,剔苔扪碑。三洲岩今存“嘉庆庚辰五月既望平阳仪克中访搨古刻来此六日”石刻②该刻现存三洲岩,拓本存广东省德庆县博物馆。,其中记载仪克中于嘉庆末在德庆三洲岩掘土数尺,将湮没于乱石中的苏轼题刻真迹拓出,苏氏“北归题刻”得以重见天日。阮元《广东通志》著录如下:
苏东坡题名,存。东坡居士自海南还来游,武陵弓允明夫、东坡幼子过叔党同至,元符三年九月廿四日。吴用之至此,此在题名之左。王元勋来观、黄期遇来观,此在题名之右。东坡遗迹,此在题名石旁。
阮元谨按云:
题名在德庆三洲北岩,石崩坠覆压岩口,外视石旁仅见东坡遗迹四字耳。俯身而入,此刻仰刊石底,因掘土三尺拓得之。东坡遗刻经党禁后辄遭磨灭,此刻独完或以崩坠故耳。[12]
道光十三年(1833),知府屠英修纂《肇庆府志》,其“金石”卷重新著录了仪克中三洲岩挖掘出土成果,并在“苏东坡题名”条下加注,指出“苏刻”未出土前众皆疑在七星岩石室,盖因吴绮、韩作栋《七星岩志》沿曹学佺《名胜志》之误。如录:
右刻(东坡题名)在德庆三洲北岩,此亦仪克中掘土所获者。未出土之前,人皆疑在高要石室黑岩,冥搜不可得,盖由吴绮收入七星岩志,沿曹学佺名胜志之误也。[7]806
五、结语
历经245 年后,道光《肇庆府志》终于订正了郑一麟万历《肇庆府志》、陆鏊崇祯《肇庆府志》有关“苏刻”条目之讹误,确认七星岩并无“苏刻”。
光绪《德庆州志》引苏东坡年谱:“留此(儋州)过中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筏下水,历容、藤至梧与迈约,搬家至梧相会,则东坡至藤后或即至梧,由梧至康当在其时”[13]541。据此分析,苏轼遇赦后于八月底渡琼州海峡先至合浦,后经容县、藤县到梧州与长子苏迈汇合,沿西江顺流而下,经三洲岩时作短暂停留,挥笔写下“北归题刻”,记录了苏东坡在岭南的最后行迹。而后三洲岩因岩石崩坠,且所处偏辟,最终使苏东坡真迹得以保存。
可能有人要问:苏轼当年为什么不在端州停留?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笔者并不认为苏轼遇赦北归时曾在端州停留,原因是多方面的,苏东坡当年北归度梅岭时曾有《赠岭上老人》诗: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14]
可以说,这首诗是其北归时真实心境写照,也在某种意义上透露了他途经端州而未作停留的端倪。加之其他史料的分析,笔者认为苏轼未停留端州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多次的流放不断给苏轼以沉重的打击,使之早已厌倦了官场奉迎,对朝廷也已心灰意冷;二是长期的颠沛流离、艰难的旅途跋涉,其不独生计困窘,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这时的苏东坡已筋疲力尽、百病缠身,归心似箭……;更重要的是,苏轼获赦只是宋徽宗赵佶登基大赦天下循例之举,其封邑端州于元符三年置“兴庆军”,成为军事重镇,戒备森严,且其时朝廷还掌握在蔡京等官僚集团手上,使得他途经端州,不想也不敢登岸,免得招惹是非。因此,苏轼在三洲岩作短暂停留后,便沿西江水路直至三水,转溯北江度岭北归,“十月十四日已复在清远矣”[13]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