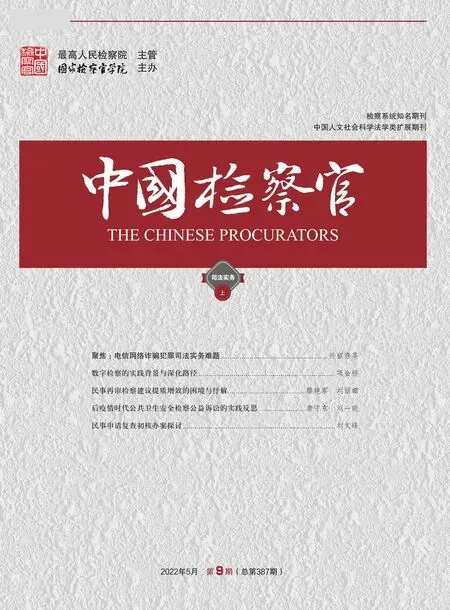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的司法认定
● 陈 玲/文
电信网络诈骗的产业化发展和技术分工降低了其犯罪门槛,也增加了打击和惩治的难度。早在2011年,“两高”就出台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诈骗案件解释》),对诈骗犯罪的网络技术支持行为的罪名适用做出了规定。为进一步应对网路犯罪上下游分工协作的全链条犯罪形态,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外,“两高一部” 先后于2016年和2021年专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适用颁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二)》,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关联犯罪惩处作出了细化规定。这些立法和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为有效惩治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及其技术帮助行为提供了规范指引,但司法实践仍然存在诈骗罪与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罪的适用难题和争议。
一、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罪名适用的实践争议
司法实践中,同样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罪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存在不同的罪名认定。在李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中,被告人在知晓其提供维护服务的彩铃软件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后,仍然继续提供维护服务予以技术帮助,法院认定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1]参见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赣1127刑初284号。在王某某诈骗罪一案中,被告人在知晓承租人利用其出租的彩铃业务语音平台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后,仍然提供租赁服务,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共同犯罪)。[2]参见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赣1127刑初271号。而在柯某某诈骗罪一案中,被告人组织制作诈骗网站并出售给他人用于诈骗。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构成诈骗罪(共同犯罪)。被告人提出上诉,认为罪名适用错误,应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二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同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诈骗罪(共同犯罪),应择一重罪,以诈骗罪定罪处罚。[3]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新刑终103号。
类似行为的不同司法认定反映了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的规范适用偏差,以及背后理论逻辑的不统一和认识分歧,值得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因此,有必要对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罪名适用的规范进行整理和分析,探寻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罪名适用的理论分歧,为其罪名适用找到正确可行的司法进路,从而消除认识分歧和法律适用争议,实现“类案类判”,提升司法公信力,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二、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罪名适用的规范分析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了“共同犯罪”,要求帮助犯和正犯之间具有共同故意。2011年,“两高”发布的《诈骗案件解释》第7条规定,主观明知状态下实施的诈骗犯罪网络技术支持行为,以共同犯罪论处。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主观明知状态下实施的信息网络犯罪技术支持行为独立入刑,创设新的罪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并特别强调该技术帮助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处。2016年,“两高一部”《意见》第4条第3款则为主观明知状态下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技术帮助行为以共同犯罪论处新设了限制条件,即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其他定罪量刑的特别规定。2019年,“两高”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列举了推定行为人“明知”的若干情形,细化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及例外,明确了被帮助对象只要具备实施犯罪行为的客观违法性即可,无需到案、定罪或有责。2021年6月,“两高一部”出台的《意见(二)》则主要是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涉及“支付结算”的部分进行细化规定,没有增加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技术帮助行为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诈骗罪的共同犯罪的进一步规定。
从以上立法和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条文规定来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技术帮助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主观上并不局限于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之间的共谋,还包括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虽无共谋但明知被帮助者实施电信诈骗犯罪的情形,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换而言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增设是否是此处的“法律另有规定”,即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犯罪构成是否排除了诈骗罪(共同犯罪)的成立?而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角度而言,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为“明知”,其是否仅包含技术帮助行为人与电信网络诈骗人不存在共谋的“片面共犯”的情形,还是也包含技术帮助行为人与电信网络诈骗人存在共谋的“双向意思联络”情形?“明知”的程度是否仅要求技术帮助行为人知道被帮助者实施的是信息网络犯罪而无需知晓犯罪的具体内容,还是需要确切知道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的具体内容?上述立法和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限定,从而使得在该罪的理解上产生了理论分歧,导致了实务中的同案不同判。
三、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罪名适用的理论分歧
目前,理论上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认识主要存在“帮助犯的量刑规则说”和“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说”两种对立的观点。前者认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增设只是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帮助行为规定了特定的刑罚裁量规则,而非将其提升为独立的正犯行为,行为人要构成该罪仍然要满足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帮助犯的条件,但此时刑法总则的帮助犯的量刑规定不再适用,而直接适用刑法分则条文(第287条之二)所规定的独立的法定刑。[4]参见张明楷:《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说”则认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帮助行为被立法机关提升为了实行行为,具有了独立的刑法评价意义。其内部又细分为不同的观点,其中“共犯独立性说”主张,应超越被帮助行为来思考帮助行为本身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无论下游被帮助者是否着手实施了信息网络犯罪,不妨碍帮助行为本身被视为独立的正犯行为予以定罪处罚。[5]参见皮勇:《论新型网络犯罪立法及其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共犯从属性说”则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入刑并没有改变其帮助犯的性质,其成立仍然要求被帮助者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6]参见刘宪权:《论信息网络技术滥用行为的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政法论坛》2015年第6期。“共犯限制从属性说”则认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虽然来自于被帮助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但这种从属性具有一定的限制,只要求被帮助者的行为符合“犯罪行为类型意义上的要素”即可,即被帮助者的行为包括达到罪量要求的犯罪行为,也包括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但尚未达到罪量要求的严重违法行为。[7]参见陈洪兵:《“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限缩解释适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的理论分歧影响了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的司法认定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诈骗罪(共同犯罪)的罪名适用。应在综合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基础上,厘清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认识,从而合理把握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罪名适用的司法进路。
四、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罪名适用的司法进路
(一)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罪名适用中的客观认定
其一,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条文上看,其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都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新罪,前者的刑法法条中明确使用了“犯罪”一词,而后者的刑法法条中则明确使用“违法犯罪”一词。从这一文本区别可以得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需要满足的条件之一是被帮助者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不能是一般的违法行为。此外,2019年“两高”《解释》将“违法犯罪”解释为“犯罪行为和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可见此处的“犯罪行为”是指符合犯罪定性和定量要求的行为,而“违法行为”是指符合犯罪定性要求但尚不符合犯罪定量要求的行为。从这一点上看,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认定上,司法解释排除了“共犯独立性说”和“共犯限制从属性说”的观点。[8]虽然《解释》也规定了例外情形下对犯罪定量要求的直接证明的放弃,即在确因客观条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程度时,当帮助行为自身的法益侵害危害性为普通情形下的五倍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时,亦可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这并非是对犯罪定量要求本身的放弃。
其二,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逻辑上看,其要求被帮助者实施了犯罪行为,且原则上须达到定性和定量的双重要求,此外法条还要求“情节严重的”才构成本罪,而增设该罪的目的又在于扩大对相关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以及解决司法实践中因难以查获正犯而导致的难以追究帮助犯责任的证明难题[9]参见臧铁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208页。,那么被帮助者的犯罪行为在犯罪形态上以及技术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之间的主观犯意联络上的要求应低于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10]但不以“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来衡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并不排斥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同时成立被帮助犯罪的共同犯罪。某一技术帮助行为可以同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被帮助犯罪的共同犯罪,择一重罪处。,否则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增设将不具有实践价值。因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不要求被帮助者已经着手实施了被帮助的信息网络犯罪,还包括被帮助者尚未着手实施而尚在被帮助的信息网络犯罪的预备阶段。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被帮助者尚未着手实施而尚在预备阶段也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前提是,该预备行为符合犯罪的定量要求,成立犯罪。在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案件中,因为处于预备阶段的诈骗行为不具备犯罪的定量要求,通常情形下尚不成立犯罪,因此从客观方面来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技术帮助行为是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诈骗罪(共同犯罪)的余地相对较小。
(二)电信网络诈骗技术帮助行为罪名适用中的主观认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被帮助者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行为,其包括片面共犯情形下技术帮助行为人的“单向明知”和共同犯罪情形下技术帮助行为人和被帮助者的“双向意思联络”这两种形态。当技术帮助行为人知道被帮助者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没有与被帮助者形成犯罪的共同故意时,仅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时技术帮助行为人主观上无需知道被帮助者在利用信息网络具体实施何种犯罪,只要知道时信息网络犯罪即可。司法解释列举了推定“明知”的数种客观情形,但也允许在有相反证据时予以推翻。如果技术帮助行为人与电信网络诈骗人形成了犯罪的共同故意,则其在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同时,还成立诈骗罪(共同犯罪),应当择一重罪处,此时技术帮助行为人需要确切地知道被帮助者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对于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而言,行为人和被帮助者应具有共同故意,即“双向的犯罪意思联络”,但在实务中,司法解释通常会将“共同犯罪”的情形扩展至“明知”,并列举或规定如何分析认定“明知”,从而使其主观上不仅包括“共谋”,还包括虽无共谋但明知被帮助者实施诈骗犯罪而提供帮助,此时行为人需要认识到被帮助者在实施诈骗犯罪,虽然不要求其知晓具体的犯罪细节。此处需要注意的是,2011年《诈骗案件解释》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而2016年“两高一部”《意见》则在“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共同犯罪论处”的条文之后额外补充“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知,2015年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以(诈骗罪)共同犯罪论处”的除外规定。因此,当技术帮助行为人“单向明知”被帮助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属于“以(诈骗罪)共同犯罪论处”的除外规定,不再成立诈骗罪。当行为人和被帮助人之间存在双向的电信诈骗犯罪意思联络时,行为人和被帮助人之间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此时不是“以共同犯罪论处”,而是构成“共同犯罪”),同时行为人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择一重罪处。
回到前述第一部分的三个案例,在前两个案例中,行为人都是中途知晓被帮助者利用其技术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行为人和被帮助者之间没有形成双向的犯意联络,行为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排除诈骗罪(共同犯罪)的成立。在第三个案例中,行为人制作和出售诈骗网站,帮助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人和被帮助者之间具有双向的电信网络诈骗意思联络,此时行为人既构成诈骗罪(共同犯罪),又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由法院择一重罪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