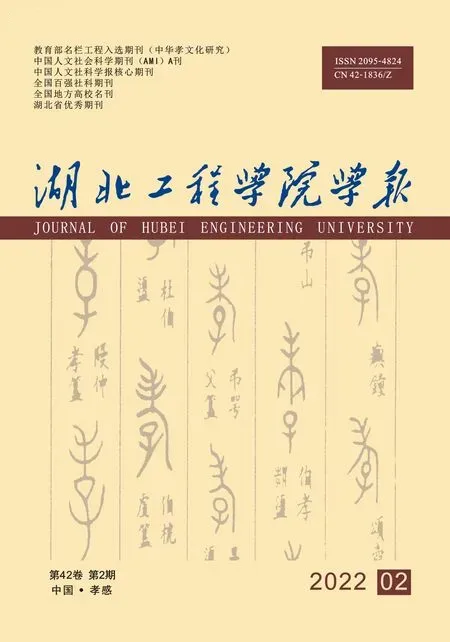论“孝”与“法”
——以“秦鸾犯盗”案例为研究重点
李宗敏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
《文明判集残卷》是《敦煌文书》中的一部分,现存十九道判例,它是唐代法制成果的重要体现,这些案件虽不是真实发生的案件,而是虚拟判例,是唐代选官时的考试内容之一,但从这些判词中也能体现出当时执法者的司法判决中司法判决原则。这些案例目前被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刘俊文先生将其收录于《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一书中,“秦鸾犯盗”一案也被收录其中。
该案例内容:“奉判:秦鸾母患在床,家贫无以追福。人子情种,为计无从,遂乃行盗取资,以为斋像。实为孝子,准盗法合推绳。取舍二途,若为科结?
判词:秦鸾母患,久缠床枕,至诚惶灼,惧舍慈颜,遂乃托志二乘,希销八难;驰心四部,庶免三灾。但家道先贫,素无资产,有心不遂,追恨曾深。乃舍彼固穷,行斯烂窃,辄亏公宪,苟顺私心,取梁上之资,为膝下之福。今若偷财造佛,盗物设斋,即得着彼孝名,成斯果业,此即斋为盗本,佛是罪根,假贼成功,因赃致福,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深乖至理。据礼全非孝道,准法自有刑名。行盗理合计赃,定罪须知多少,既无匹数,不可悬科。更问盗赃,待至量断。”[1]437-438
该案例中对“孝”的认识已经与先秦时期儒家所倡导的“孝”不同,其中所体现出的“引律决狱”也与汉时的“春秋决狱”原则不一致。
一、动机与结果的考量:何为孝
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自汉以后,“忠”“孝”始终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汉朝皇帝驾崩后都以“孝”作为谥号,如孝文帝、孝景帝等。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征召李密,李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2]2274为由而不仕,晋武帝对其称赞“士之有名,不虚然哉”[2]2275。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孝”在君主治国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古代治国方式中的重要内容。自汉武帝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后,执法者在司法判决上便延续着“春秋决狱”的司法判决原则。而在唐朝“秦鸾犯盗”一案的司法判决中,却体现出另一种司法判决原则。
“孝”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何为“孝”的问题上,先秦时期儒家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只是孔子在与学生的谈话中因每个学生性格的不同而对“孝”进行了“无违”(《论语·为政》[3]104),“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3]108),“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3]110),“色难”(《论语·为政》[3]113)不同的阐释。
其中“无违”、“色难”体现出孝顺父母首先要顺从父母,而“父母唯其疾之忧”便是要求人们不要使父母担心自己。孔子讲“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3]54),这里孔子实际上强调的还是为人子对父母的顺从。应该说明的是,这种顺从并非是盲目顺从,当父母有过错时,也要对父母进行规劝,孔子讲“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3]349)这里对父母的规劝是基于对父母的尊敬、敬重上,是委婉的规劝,而非强制的要求。
从孔子“不敬,何以别乎?”之问中,可以看出在孝顺父母的问题上,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够从心里真正地尊敬父母、孝顺父母从而去赡养父母。所谓的“无违”,“父母唯其疾之忧”,“色难”等等的背后都是要求人们对父母应存孝心。《礼记·大学》中讲“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4]2237,也可以看出“诚”对于一个人修身、齐家的重要性。因而,在儒家看来,孝顺父母也需要“诚”,诚心诚意地孝顺父母。《论语·八佾》篇云:“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3]184-186这就是说,孔子所提倡的礼,归根到底是要人们从心底去认同它,而非只关注于礼的形式本身。
从孔子对“孝”的阐释可以看出,儒家关于孝道有两个原则,一、行为上顺从父母,二、内心动机的正当性。儒家不仅要求人们行为上对父母遵从,更要求人们在心底树立起孝顺父母的观念,从而做到内外统一。
这一时期由于儒家思想还未上升为国家统治思想,因而在“孝”与“法”关系问题上,并没有过多探讨,叶公告诉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论语·子路》[3]1189),而孔子提出“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3]1192),到战国时孟子以“窃负而逃”回应桃应的诘难,更多地是理论上的争论,还并未上升到国家的司法判决中,还并未关注到犯罪动机的问题。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的司法判决原则,可以说是儒家对于“孝”与“法”问题的初步实践。当伦理道德开始被纳入到法律之中,在司法判决中是否应考量犯罪者的道德动机便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不断争论的主要问题。
董仲舒将儒家思想政治化,提出春秋决狱,即除了以现有法律作为依据之外,还需以“春秋大义”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董仲舒讲:“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5]92。也就是说,以“春秋大义“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在依据事实的基础上探究当事人的动机好坏,动机邪恶者,判决加重,而动机正义者,罪行减轻。这也就是说,道德动机不应作为免去犯罪者罪刑的标准,而是将其作为减刑的标准。这里董仲舒强调道德动机的正当,而正当与否的标准便是儒家所倡导的忠孝仁义,这是道德动机与司法实践的初步结合,这也使得在汉朝时期有的人虽然违反了法律,却由于其行为符合儒家倡导的道德,从而获得减刑。但是自伦理道德被纳入法律,汉武帝实行“察举制”以后,“孝”就已不再仅仅是子对父天然情感的萌发,其中夹杂着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6]76-78,这种情况下在汉朝末年便出现了一些人为了获得名利而假意孝顺父母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依旧延续这一司法判决原则,据《晋书·桓温传》记载,江播杀死桓温之父桓彝,等桓温长大后,杀掉江播全家,而官府并未追究其罪行,“时人称焉”[2]2568。
到唐朝,《唐律疏议·名例律》中讲:“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7]61,《唐律疏议》对“孝”的定义虽然延续了孔子关于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却忽略了孔子对道德动机的关注。秦鸾因母亲生病盗财为母祈福,从道德动机来看,秦鸾行为符合孔子“诚”的要求,符合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但却违背了法律。《唐律疏议·窃盗》中规定:“诸窃盗不得而笞五十;一尺杖六十”[7]1382,并未在盗窃者因动机不同而进行不同处罚方面具体规定。因而《文明判集残卷》中,官吏对秦鸾的惩罚是基于盗窃律法进行判决。《唐律疏议》中虽也有过失犯罪(“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其误杀伤者不坐,但偿其减价。”[7]1107-1108)等方面的规定,但是都并未涉及违法者的道德动机亦正当与否(1)要明确《唐律疏议》中规定的过失犯罪是否具有对动机考察的因素,就要明确何为“过失犯罪”。我国刑法根据人们是否预见危害的结果,将过失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两个方面。根据这一内容,《唐律疏议》中对过失犯罪的规定很明显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薛瑞麟指出“动机是意志的必要组成部分。过失犯罪是一种有意识、有意志的行为,而有意识、有意志的危害行为则离不开动机。应当指出,作为违反义务的过失行为在造成法定的危害结果之前还不是犯罪行为,其动机也不具有犯罪性。如果过失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它就变成犯罪行为,其动机也就随之转化”(薛瑞麟:《关于犯罪动机的几个问题》,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2-117页)[8]。这里薛瑞麟所讲的动机并不是犯罪性动机,他是基于犯罪事实结果回答行为人基于何种原因实施犯罪行为,由于任何行为一旦发生都存在行为动机,这一行为所造成的犯罪事实与行为动机并没有事实上的因果关联。这里所讲的主要是犯罪动机,依据犯罪性动机(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只有直接故意犯罪才存在犯罪动机(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77页)[9]。应该说由于对动机理解的不同,对“过失犯罪”行为是否具有动机存在争议,但过失犯罪与犯罪动机并不是一回事,因而,《唐律疏议》中对过失犯罪之人进行减刑,并不涉及犯罪动机的考量。。要说明的是,虽然唐朝法律中没有规定道德动机正当与减刑的问题,但在司法判决中,执法者基于不同的学说立场对于同样的案件有着不同的司法判决。这里不做具体论述,待见下文。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司法判决开始突破过去以“春秋决狱”作为司法判决原则的判决方式。在司法判决中,执法者逐渐倾向于认同法家思想的现实性,更多地关注于民众的行为本身,而非对违法者道德动机正当与否的探查。案件中官吏对秦鸾的处罚,就说明这一时期,在“孝”与“不孝”的问题上,执法者认为“孝行”以不能违背法律为前提(今若偷财造佛,盗物设斋,即得着彼孝名,成斯果业,此即斋为盗本,佛是罪根,假贼成功,因赃致福,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深乖至理。据礼全非孝道,准法自有刑名[1]438),也就是说孝顺父母的基本原则即不能违法,违法行为不能被视为孝行(2)这里并非否认本案中秦鸾“为母盗财祈福”行为中的道德动机,只是否认将其视为“孝行”。,这是执法者基于维护社会稳定作出的决定。
虽然秦鸾是为了母亲的病去盗取财物,应该说其道德动机是好的,从春秋决狱的原则来看,也应该从轻处罚,但是官吏依旧根据事实结果去进行处罚(行盗理合计赃,定罪须知多少,既无匹数,不可悬科。更问盗赃,待至量断[1]438。),并没有提出考虑秦鸾的道德动机。《唐律疏议》中将盗窃罪定义为“诸盗,公取、窃取皆为盗”[7]1453,这里并未关注盗窃的道德动机,只关注事实结果是否符合盗的罪名。刘俊文也讲:“《唐律》盗罪之基本概念,乃建立于目的实害一致的基础上,即必须以非法取得并占据公私财物为目的,且已经在事实上取得并占据公私财物者,始为盗罪”[7]1455。在判词中可以看出,执法者认为,秦鸾不能因父母生病而去盗财,将为母盗财的行为认为是个人私情,盗取财物的行为认为是亏公,不能以私废公。这种认识与法家的思想主张具有一致性,韩非认为公、私是对立的,他所认为的“公”即国家制度,而私则是每一个个体、团体组织等。他所讲的“公”更多指维护国家(君主)利益,相对而言“私”则是维护个人、家庭利益(3)对于韩非的公利、私利问题,学术界对于公利是谁的公利?私利是谁的私利?的问题。一种是张岱年、朱伯崑认为韩非的公利指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君主、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种是宋洪兵认为韩非最终的公最终是人民整体利益的体现。(参见王威威:《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韩非列举了八种以私害公的行为,讲“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韩非子·八说》)。这里韩非提出“人主之公利”,这就说明,韩非的“公利”是为人主所有,对于臣民而言,人主的利益便是公的体现。但是虽然在家天下的时代中,君主之家与国是高度契合于一起的,对于臣民而言,二者区别不大,但是对于君主而言,家与国的矛盾实际也是公、私矛盾的体现。在韩非看来,当君主为了自己的私人情感或者自己的“家”去损坏国家利益时,君主便是自掘坟墓,也是在“以私废公”。因而,韩非维护公利的体现便是维护君主利益,君主不以自己的私人情感损坏公法,也是君主维护自身的利益的体现。因此,可以说韩非的公利包含社稷利益、君主利益两部分。在家天下的时代背景下,土地私有制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最终公利的体现一定不是人民整体利益的体现而是统治阶级利益(地主、奴隶主利益)的体现,最明显的便是,韩非主张封建土地私有制,但是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土地,当有土地的人与没有土地的人并存,韩非提出维护私有财产,便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看问题。因而这里的私利,也指的是君主的“家利“、个人之私利以及臣子之私利。。一般认为,韩非认为,无论君臣还是民众都不能以私废公(4)王威威讲“‘虚静’排斥人的情感和欲望”(王威威:《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徐克谦讲:“韩非子所谓”去私“也不是叫人完全没有为己的私心,而在于划清私与公的界线不能利用公权力来谋私”(徐克谦:《私德、公德与官德——道德在韩非子法家学说中的地位》,《国学学刊》,2013年第4期)。。在这一案例中,很明显可以看出该案例中的执法者具有明显的法家倾向。另一方面,虽然在判词中“舍彼固穷,行斯烂窃”一句引用了孔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3]1353),但这并不能视为执法者司法判决具有儒家倾向,在《礼记·檀弓上》篇中孔子承认“为父杀人”[4]287的合理性以及在以春秋决狱原则为指导的司法判决中都体现出,儒家承认为亲人违法的合理性这一立场,儒家既然承认为父杀人在道德上的合理性,基于杀人是比偷窃更恶劣的行为,也就必须承认为母盗窃在道德上的合理性,并将其纳入司法判决中进行考量,但是在这一判词中明显可以看出,执法者并未将秦鸾盗窃在道德上的合理性纳入到司法判决中进行考量。
孝与法(伦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也是儒、法两家在进行理论构建时必须回答的问题。自汉以后,在“外儒内法”的治国模式下,作为国家的执法者甚至皇帝往往在实践二者理论主张时,往往带有明显的个人选择倾向。
二、孝与法之伦理困境与政治解决
孝与法之间的冲突对立实质上是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对立,这也是先秦时期儒、法对立的重要体现。这里孝与法的伦理困境的直接体现便是当亲人生病,身为人子是否应该偷窃?这其中涉及人与人之间血缘伦理道德与国家制度之间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儒法两家有着不同回答。
当有人问孟子瞽瞍违法,舜应如何处理时,孟子讲:“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10]1103)。舜不阻止官吏对瞽瞍的惩罚,是对法律的维护,而放弃天下与瞽瞍逃亡是舜对瞽瞍的孝。孟子试图将孝与法的冲突消弭(5)对于孟子的回答,熊逸指出“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对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的答案的……按照儒家的原则,解决方案应该是这样的:受害者家属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天涯海角追捕杀人凶手,甚至不妨手刃仇人;皋陶,那位公正的法官,应该做的则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不懈地追捕逃犯,直到将逃犯(瞽瞍和舜两个人)缉捕到案为止,瞽瞍应该做的是投案自首,主动认罪伏法(虽然他这个至奸至恶的角色绝不肯这么做,但也不排除他有朝一日终于被大舜成功感化的可能,而这显然是儒者最乐于看到的结局);舜应该做的是继续协助父亲潜逃,处心积虑以求永远都不要被法官和仇家找到”(熊逸:《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8页。)这种将追捕犯人的成功与否寄希望于犯罪者的良知,显然不符合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但是这对于国家政治而言却难以实践。从孟子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孟子认为,即使是身为天子之父,一旦犯法也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与韩非所倡导的“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相一致,但是当孟子认为舜应主动放弃天子之位与瞽瞍逃到政府找不到的地方,舜应为了父子之间伦理道德放弃天子所应承担的责任之时,就可以说“在孟子的理想规范里,血缘伦理优先于政治伦理,家庭亲情优先于社会责任”[11]5。孟子这一思想主张,在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君主那里都不会被接受,任何一个统治者其所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巩固自身政治权力,因而也绝不会为了“孝”而放弃君位。
对于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儒家往往主张支持人们“为父报仇”行为,《礼记·檀弓上》中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4]287,这里孔子认为对于父母之仇,身为人子是可以去复仇的,这里孔子对于“为父报仇”的行为进行了肯定,但这里并未提到法理上如何判决的问题。《春秋公羊传》中讲“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旬,古之道也”[12]562,这里可以看出,《春秋公羊传》中承认“为父报仇”的合理性,但有一根本前提便是其父为非正常死亡,若为有罪被判刑,且罪当致死,那便没有“复仇”的合理性。综上,可以说儒家是主张“为父报仇”的行为,因而在汉朝时董仲舒基于“春秋大义”提出“春秋决狱”,主张符合道德动机的犯罪行为应获得减刑。
与儒家恰好相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主张政治伦理先于伦理道德,社会责任先于家庭亲情,他更强调政治中个体的责任,忽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韩非讲“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韩非子·用人》[13]219),主张君主用人,臣子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心尽力履行自身的职责,如韩非认为臣子有“必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韩非子·南面》[13]127),臣子“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韩非子·初见秦》[13]1-2),规定臣子应尽的职责。韩非又在《外储说左下》中以“解狐荐其仇于简主以为相”之事为例提出“私怨不入公门”[13]331,公、私有着明确的界限,不以私怨废公事。这就是说,在韩非看来,个人的社会职责重于私情,任何人都要守法,主张“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13]41)“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韩非子·主道》[13]32),也就是说法不避亲疏,不避贵贱。执法权属于国家,民众不能够代行执法。
儒、法对于伦理道德与国家法制之间的冲突的不同主张,体现出中国古代两种不同司法判决原则。正如上文所言,秦鸾为母盗财的道德动机是正当的,是符合“孝”道的,因家贫无以治病,盗取财物,这虽违背法律,但也符合伦理常情。汉朝时也有类似案例,据《汉书·薛瑄传》记载,薛瑄因未能为其母守孝而被申咸指责,其子薛况唆使刺客毁申咸容貌,刺客毁其容。案发,有司判决薛况死刑,但廷尉认为,薛况犯案的道德动机是为父报仇,是出于孝心,最终改判为徒刑。[14]2525-2526薛况为父打人在汉朝被认为属于孝行,可以被减免罪行,而秦鸾为母治病而盗财则不属于孝行。要说明的是,薛况行为实际上并不符合“春秋决狱”原则,正如上文所指出合理“复仇”的前提是自己的父母获得的惩罚与其罪刑不一致,但是薛瑄未能为其母守孝是客观存在的行为,在以孝治国的汉朝这很明显的是一种错误,申咸指责薛瑄的行为是合理的,并不存在冤枉,因而薛况以此为由“复仇”是不合理的,也不能以“春秋决狱”的司法原则为依据作为减刑标准。
从性质来讲,薛况指使人打人,属于打击报复,是故意伤害罪,相较而言,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比秦鸾偷窃更为恶劣。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秦鸾被执法者依据偷窃罪金额的多少进行量刑,而薛况获得减刑。从犯罪动机来讲,以现代刑法学的视野来看,秦鸾的犯罪动机是非法获得财物,道德动机则是为母祈福,薛况的犯罪动机则是私仇报复,道德动机为父报仇,但是汉朝执法者承认了薛况指使人打人的道德动机,基于其道德动机为其减刑,但是在唐朝秦鸾的道德动机则不被承认,执法者以其犯罪动机进行惩罚。这就说明,从汉到唐,执法者在司法判决中逐渐以犯罪者的犯罪事实取代道德动机,将道德动机在司法判决中剥离,逐渐以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作为考察伦理道德依据。
将道德动机剥离于司法判决之外,不作为量刑的标准,是司法判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进步。但要说明的是,在司法判决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以及执法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依旧延续着“春秋决狱”的判决方式。这也就是说,虽然“秦鸾犯盗”一案,执法者依据秦鸾的犯罪事实进行判决,突破传统以“春秋决狱”为司法原则的判决方式,但是应运用“春秋决狱”判决原则还是“秦鸾犯盗”一案的判决原则进行司法判决依旧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争论(实质上是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争论)的主要焦点。
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执法者由于不同的立场在判决中往往有不同的选择倾向。据《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武则天时期,徐元庆为父报仇杀死仇人后自首,武则天欲赦免其死刑(这也就是说在最早的司法判决中是将其处死的),但陈子昂却提出反对,他指出徐元庆杀人悖法,为父报仇又符合儒家礼义,在法律与礼义之间,陈子昂试图对二者冲突进行兼顾,既主张将其处死,又主张对其孝行进行宣扬[15]5585-5586。与秦鸾一案不同,陈子昂作为执法者承认了徐元庆的行为符合“孝”,但最终选择将其处死,对其行为进行宣扬。这就说明陈子昂虽然延续着儒家的“孝”观念,但是他也承认着法律在统治者治国中的至上性。无论陈子昂是否具有这个意思,实际上,当陈子昂选择了依据法律处死徐元庆时,便是与秦鸾犯盗案件中的执法者一样,将道德动机的考量置于司法判决过程之外,对徐元庆行为中所体现的“孝”的宣扬已经不是呼吁人们向徐元庆学习,而是具有警戒的意味,具有明显的法家倾向,也就是说若是真的要宣扬徐元庆的孝行,鼓励大家向徐元庆学习,便不能处死徐元庆。柳宗元对这一案件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的行为符合“孝”,法律不能作为维护恶人的武器,因而,不能判处徐元庆死刑(“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15]5587),也就是说柳宗元承认徐元庆行为的合理性,他的这一主张,与汉“春秋决狱”的司法原则相一致,具有明显的儒家倾向。但是二人都并未关注徐元庆自首的这一客观事实,就说明了这一时期不同思想家、政治家争论的主要问题还是犯罪者的道德动机是否应作为犯罪者量刑的标准。不同的司法判决原则体现着执法者不同的思想倾向,无论是儒家倾向还是法家倾向,从历史的结果来看,两者都各有利弊。
三、评“春秋决狱”与“秦鸾犯盗”所体现出的“引律决狱”
“春秋决狱”司法原则与“秦鸾犯盗”一案中所体现的司法原则,最直观的不同便是在司法判决中执法者是否应考量违法者的道德动机作为犯罪者的量刑标准?
“春秋决狱”的司法原则是在依据事实的基础上探究当事人的动机好坏,动机邪恶者,判决加重,而动机正义者,罪刑减轻。这种判决方式并非要求司法判决中“唯动机论”,它的基本要求是查清事情原委,了解事件真相,在这一基础上,考察犯罪者道德动机,这种方式满足了人们的道德需求,是基于对人情的维护。当法律允许人们为父报仇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便是鼓励人们用行为孝顺自己的父母。虽然这种“为父报仇”属于一种极端表达方式,但这里它所要彰显的不仅是法律的惩罚作用,还有教育引导作用。正如黄源盛所讲:“纯粹从刑法学的观点言,的确颇能救济行为人因过误等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以舒缓刑律某些严酷僵硬的条文。”[16]169法律对无意过失者进行挽救,也对道德动机正义且违法之人具有教育意义。
但是这种判决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危害。即当执法者将“孝”与子为父报仇相挂钩或者将道德动机作为违法者的量刑标准,那么对于社会稳定而言,便是一种隐患。汉朝末年,复仇之风盛行,正如上文所讲的汉朝薛况为父报仇,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正如上文所言,薛况之行为并不符合“春秋决狱”的司法原则,最后却被依据“春秋决狱”司法原则获得减刑。实际上,承认为父报仇行为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将执法权交由到平民身上,虽然这里的“父”必然且只能是非正常死亡或受到伤害,“子”才有“为父报仇”的依据,但是当“子”能够以孝名来合理地报仇之时,便会造成“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尽心下》[10]1043)的局面,虽然依据《春秋公羊传》中的解释,对“为父报仇”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除了其父罪与刑不一致的标准以外,还指出复仇时不能牵连仇人之家人只可针对仇人本人,但是对于仇人之子而言,他的父亲也并非是正常死亡,况且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执法者无法判断仇人与复仇者之间的仇恨,那么最后仇人之子进行复仇之时,极大可能会被认定为合理,并被冠以“孝名”。从薛况为父并不符合“春秋决狱”司法原则,却获得减刑,就说明执法者并未探查到申咸与薛瑄之间的矛盾,并未探究申咸为何会指责薛瑄。执法者由于对道德动机探查的困难性,“复仇之风”现象的盛行,也就无法避免。这种现象,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治理以及司法判决的公平与公正。
而唐朝对“复仇”这一类型案件的处置中所对道德动机的考量,也并非完全依据“春秋决狱”的司法判决原则,据《旧唐书·孝友传》记载:“王君操,莱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业中与乡人李君则斗竞,因被殴杀。君操时年六岁,其母刘氏告县收捕,君则弃家亡命,追访数年弗获。贞观初,君则自以世代迁革,不虑国刑,又见君操孤微,谓其无复仇之志,遂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杀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诣刺史具自陈告。州司以其擅杀戮,问曰:‘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对曰:‘亡父被杀,二十余载。闻诸典礼,父仇不可同天。早愿图之,久而未遂,常惧亡灭,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据法处死,列上其状,太宗特诏原免。”[17]4920,从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王君操为父报仇,执法者将其判为死刑,执法者在对这一案例的判决中与秦鸾犯盗一案一样,没有将违法者的道德动机纳入量刑的标准之内,但与上文徐元庆一案中的武则天一样,唐太宗也要赦免王君操之死刑。从这两个案件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司法判决中所体现出的“春秋决狱”原则与皇帝对司法的干涉有着密切联系。而从柳宗元对徐元庆一案的不同看法来看,皇帝对司法判决的干预也是“外儒内法”治国模式在司法领域的缩影。即无论统治者如何认同法家主张,也需要披着儒家的外衣,借着圣王之道的外衣进行治国(6)以唐太宗为例,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李建成、其弟李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页)。李世民为达其政治目的完全不顾血缘亲情,杀害兄弟,谋取皇位,完全可以说他不忠不孝,但是他的谥号却是“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页),突出一个“孝”。由是观之,先秦儒家所提倡的“孝”逐渐成为统治者美化自身形象的工具,统治者是否符合“孝”并不重要,“孝”只是该政权治国的口号,是该统治者能够合理执政的工具。。正如瞿同祖所言:“中国的学者,除法家外,都偏向于礼经,不肯否认复仇的道义……从复仇罪和私和罪的关系中,法律对复仇罪的基本态度是要求子孙依据法律程序告官请求深雪,私和不究或私行擅杀都是法律所不容许的”[18]98-99。
在“秦鸾犯盗”一案中可以看出,执法者并不承认秦鸾的道德动机。这种判决方式更多地侧重于发挥法律的惩罚作用,统治者将“礼”“道德”纳入法律内容的同时,也延续了法家“法不诛心”的思想主张,即在司法判决中以事实结果为依据,而不关注违法者的道德动机甚至不承认违法者的道德动机。从效果来看,这种判决方式相较“春秋决狱”更为有效,更有利于统治者治理国家。黄源盛讲:“《唐律》的礼教法律观所给予刑法者,可以说,不是道德理由,而是实效的考量……礼本刑用观乃是由他律的权威机构而强迫施行的社会伦理机制”[16]241-242。从徐元庆、王君操的案件中可以看到,对于二人的自首行为执法者并无考量,他们关注的还是道德动机是否应作为量刑标准,唐太宗、武则天要赦免二人死刑也是基于二人的道德动机,也就是说当执法者在司法判决中将道德动机剥离,执法者的判案已经丧失了对道德动机的探查,仅仅就事实结果依据法律进行判决。
这种司法判决原则,虽然强化了社会治理,使人们不敢以任何理由从而轻易违法,更有利于社会的管理以及国家政策的推行,但这种判决方式也有着一定的缺陷。假设甲乙两人都去偷窃财物,二人虽然都是偷窃财物,不同的是甲偷窃是由于家中父母或者妻子生病,不得不去偷药或者偷盗财物买药,而乙并无任何的道德动机,仅仅是偷窃财物。按照“秦鸾犯盗”一案的判决原则,执法者在量刑中将道德原则剥离,与乙定同样的罪即同罪同刑。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便产生出这么一个疑问,甲为了其父母或妻子是否应当偷窃或者说他应该坐看其父母亲人病逝而无动于衷还是去偷窃药品财物从而使亲人得到救治?
若因其道德动机而对甲减刑损害的是法治公平,若惩治甲从另一方面来看,是对甲之亲人生命的忽视。对这一问题延伸便是法律的权威重要还是生命的价值重要。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法律的公正,在司法判决中需要尽可能去除影响司法判决的道德性,在个人私德与国家公法之间,应尽可能去除犯罪者违法行为之中蕴含的个人私德。从集体与个人的角度出发应该是这样,在现代司法判决过程中也往往对于违法者的道德动机在量刑中不做考量,往往将违法者的自首、立功表现、行为危害性等作为量刑标准。
但是当违法者的行为动机中关系自己亲人的生命,这便不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之争,而是个人生命与法律公正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法律是由人所创立,它首先维护的便是人们自身的基本权利——生命权,血缘亲情对于人们而言又是先天所固有。另一方面,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回护,韩非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因情》[13]470),《礼记》《春秋公羊传》中承认“为父报仇”合理性,汉朝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决狱”司法判决原则能被实行并被后世所延续,都是因为看到了人的道德情感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应该说人的基本情感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国家政策、法律能够贯彻实施的前提。在中国古代法律以维护人情为己任[19]244,人们往往对严格执法者心怀不满,甚至招致非议,如商鞅、汉朝酷吏等比比皆是。法律的判决不在于惩罚,更重要的是惩罚后使违法者心服,仅仅做到公正是实现不了这一目的的,韩非就曾讲了孔子相卫一事(7)《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门。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曰:‘尼欲作乱。’卫君欲执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从出门,跀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问跀者曰:‘吾不能亏主之法令而亲跀者之足,是子报仇之时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跀危曰:‘吾断足也,固吾罪当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倾侧法令,先后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乃狱决罪定,公憱然不悦,形于颜色,臣见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公也。”,违法者最终能被子皋判罚却不埋怨子皋,就是看到了子皋司法判决中所体现的仁爱之心,而依据子皋的主张,在判决中必定将违法者的道德动机作为了量刑的标准之一。
从孔子相卫这一案例所达到的最终的结果来看,在量刑中将违法者的道德动机纳入到量刑标准之内,有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有助于达到违法者“以罪受诛,人不怨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13]312)的法治目的。而在秦鸾一案的司法判决中,执法者忽略了法律中道德的教化作用,仅仅追求形式上的稳定与和谐。道德的教化是使人向善,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但是这种司法判决方式,执法者更多地关注于人们的行为是否违背法律,便使得法律的教育引导作用降低,使得伦理道德与司法判决相脱离。
马克思认为“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20]349这里马克思将法律与人民的意志相结合,对法律自身的要求则是既要科学又要符合社会已形成的观点。这就为当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将道德动机与法治建设的统一提供理论依据。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下,大多数的司法判决结果,人们都能从网络上得到了解,因而,对于当前的法官而言,所要做的不仅是维护法律的公正依法判决,还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满意。在这一条件下,违法者的道德动机成为法官量刑的标准之一,便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秦鸾盗窃之后不去买药为其母治病而是去寺庙祈福,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荒诞的行为,但也反映出唐时佛教对人的影响,以此为视角对“秦鸾犯盗”案例的司法判决中的宗教因素进行分析。
四、佛教对唐司法判决的影响
随着西汉末年佛教的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发展,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政治不断交融。一方面,在司法判决中,官员在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在不少官员的司法意识中,佛教起着比儒家更大的作用”[21]145。另一方面,佛教思想也成为统治者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唐朝时期,武则天借佛教为其称帝寻找“天命”依据(《旧唐书·武后纪》记载“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17]121),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佛教与政治联系密切。
秦鸾盗取财物供奉寺庙为母祈福,但官吏认为:“今若偷财造佛,盗物设斋,即得着彼孝名,成斯果业,此即斋为盗本,佛是罪根,假贼成功,因赃致福,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深乖至理。”[1]438
若秦鸾以盗窃所得财物造佛设斋为母祈福的行为符合孝道,实现其目的,那么“佛”“斋”便不是至善之物,其他人为求“至孝之名”便会效仿秦鸾以违法之资“造佛设斋”。这种现象并不利于国家管理,官吏不将秦鸾之为母盗财判定为孝行,也是基于秦鸾的行为是对国家法制的破坏。官吏若承认秦鸾的行为符合“孝”,那便是将“孝”与“法”对立,不符合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国家政策,因而便不能承认秦鸾行为符合孝道。这一判决与汉朝时董仲舒“春秋决狱”的理念大相径庭。而执法者能够否定秦鸾行为的正当性,也是基于其对佛教主张的基本认识。
通过判词可以看出,佛教对执法者司法判决、民众都有重要影响。案件中,秦母病,秦鸾盗财并非为母买药治病,而是为母造佛设斋祈福,除了显示出人们思想中“迷信”之外,还体现出佛教在这一时期已经深入人心,影响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执法者认为秦鸾之行为并不符合孝道,也是“恐人人规未来之果”,说明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虽受到统治者的支持,但是佛教思想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也较为突出。执法者对“斋为盗本,佛是罪根”的否定,也就是肯定了佛是善的体现,而这里所谓的“善”便是不能够违反法律。从中也体现出政治上,官吏对佛教的认同,这就说明佛教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冲突的同时,相互吸收、共同发展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
从判词中看出,秦鸾的行为涉及的不仅仅是违法问题,也涉及到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从秦鸾在其母生病后,所盗之财不去买药治病,反而设斋造佛为母祈福,就说明以秦鸾为代表的社会民众对佛教的认可,他们从心底是真的相信“佛祖显灵”。因而,对秦鸾孝行的否定,便是对世俗法律的维护,它不仅是“孝”“法”的关系问题,也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从佛教的思想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了官方统治思想,因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其必然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方立天讲“佛教中国化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便是伦理道德的儒学化”[22]203。佛教最终能够在中国发展也必然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其与中国古代政治也密切相关,可以说,佛教“能扎下根并不断发展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得到统治阶级的培植与支持”[23]176。
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佛教将儒家“孝”与佛教“戒律”相结合。东晋士族孙绰讲:“唯得其欢心,孝之尽也”,唐代时,神清大师讲:“盖孝者以敬慈为本,敬则严亲,慈则爱人;严亲则不侮于万物,爱人则不伤于生类”。(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这都可以看出,佛教与儒家都主张子对父母的尊敬与顺从。同样,佛教也反对盗窃,《梵网经》中讲“若佛子!自盗、教人盗、方便盗,盗因、盗缘、盗法、盗业,咒盗乃至鬼神有主、劫贼物,一切财物,一针一草不得故盗。而菩萨应生佛性孝顺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乐,而反更盗人财物者,是菩萨波罗夷罪”[24]。从这里可以看出,佛教将孝与盗完全对立起来,孝行作为善行是能够得到善报,而盗窃则会有恶报。
到了宋代,契嵩将“孝”与“不盗”结合在一起。他讲:“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妄言信也。不饮酒智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共亲。不亦孝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佛教将“盗”纳入“不孝”的范围之中。
从佛教对“孝”“盗”认识的发展来看,佛教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将世俗法律所禁止的部分上升到“不忠”“不孝”等伦理道德的层面。虽然佛教在与唐代政治交织的过程中,在对“孝”的认识上,依旧强调动机的重要性(“孝自内心”),但是对世俗法律的认同,主张维护法律,遵守法律,则是佛教世俗化的主要发展方向,佛教戒律与世俗法律有许多矛盾之处,但是“中国僧众采取了有利于实际的选择”[25]114。
因而,从佛教视野来看,秦鸾的行为也不能算作“孝行”。佛教主张“因果”论,也就是说,以佛教思想来看,秦鸾的行为也终将不会得到善报,反而会得到惩罚。可以说,当佛教世俗化之后,在佛教文献中固有之教义在传播过程中,佛教不仅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吸收改造还对佛教戒律进行一定幅度的抉择和修订[26]1178。可以看到,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互吸取,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部分,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的各个方面,对司法判决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