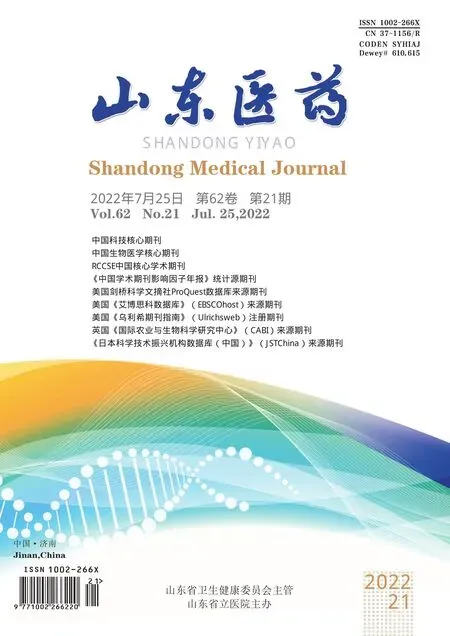脓毒症的免疫病理机制及诊断和预后预测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翟昭,王楠,张宇晨,钟佳宁,刘先发,易会兴
1 赣南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2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3 保定市人民医院
脓毒症被定义为由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引起的潜在致命有机功能障碍,机体感染后可表现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并迅速发展到多器官功能障碍和脓毒症性休克,危及生命,是重症监护病房常见死因,也是世界范围内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重大卫生保健问题。脓毒症是严重创伤、感染、烧伤或大型手术后的常见并发症,病情进展迅速,病死率高,据国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每年约有超1 900万人患脓毒症,而只有1 400 万人可存活出院,存活的脓毒症患者中仅半数能康复,六分之一的人伴有持续性机体损伤,三分之一的人在出院后第二年死亡[1]。脓毒症发病涉及组织损伤、全身炎症网络、免疫功能障碍、凝血功能异常、基因多态性等多方面,最初作为机体对内毒素的免疫反应而被发现。当病原体侵入机体时,宿主先天免疫系统发现并清除病原体,而当病原体作用强于免疫反应时,机体内炎症反应与免疫反应发生失衡,表现为细胞因子风暴和免疫抑制。目前,判断病情进展并给予相应治疗是临床脓毒症诊疗面临的一大困难,而生物标志物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脓毒症的诊断及预测准确性,为脓毒症研究提供了新方向。现在将脓毒症的免疫病理机制及其诊断和预后预测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脓毒症的免疫病理机制
脓毒症发病机制与免疫反应关系密切。脓毒症会导致先天性免疫及获得性免疫反应的改变,前者表现为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1β(IL-1β)、IL-6、IL-8 和干扰素-γ(IFN-γ)等参与的细胞因子反应,后者表现为免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中性粒细胞以及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等的凋亡。细胞因子风暴和免疫抑制是脓毒症中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两者虽为不同阶段,但在发展上并无严格转变,机体内促炎与抗炎的平衡关系决定两阶段的发展。
1.1 细胞因子风暴 疾病早期,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识别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或损伤相关分子 模 式(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激活细胞内信号传导和基因表达程序,导致一系列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等介质产生,引发机体炎症反应[2]。细胞因子激活免疫细胞,被激活的免疫细胞进一步产生细胞因子,形成一个正反馈调节,即细胞因子风暴[3]。脓毒症高炎反应还可导致补体系统及凝血系统激活,前者促进补体C3a、C5a等小激活片段释放而发挥强大的促炎作用和促血栓活性[4],后者加重脓毒症患者微血栓形成概率[5]。同时,高炎反应刺激抗炎因子IL-4、IL-10 等大量分泌,但其急剧分泌增加会使机体抗炎功能因反应过度而代偿性下调,以致出现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CARS)[6],内源性抗炎介质失控性释放是机体免疫功能抑制的主要原因。
1.2 免疫抑制 免疫抑制被认为在脓毒症后期占主导地位。免疫细胞凋亡是脓毒症免疫抑制的主要发展因素,可发生于多种病原体感染、多个年龄段患者及多部位免疫组织中,主要特征在于淋巴细胞耗竭及APC 的重新编程。淋巴细胞耗竭主要与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及程序性死亡配体(Programmed Death Ligand,PDL)的相互作用有关。T 细胞表面PD1 表达增加,巨噬细胞上PDL 表达增加,导致耗竭的T 细胞失去其效应功能,而干扰PD1/PDL 通路后T 细胞活性可恢复[7],研究也证实抑制PD1/PDL 相互作用后脓毒症诱导的小鼠存活率有所提高[8]。淋巴细胞耗竭的另一原因与调节性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比例增加有关,效应T 细胞丧失致Tregs 百分比增加,Tregs 抑制效应T 细胞功能、延长T 细胞恢复时间并促进其凋亡以维持自身耐受性,诱导DCs 表面共刺激分子表达下调,加剧了脓毒症免疫抑制,所以降低Tregs 表达对脓毒症具有保护作用[9]。
APC的重新编程表现为单核细胞表面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类分子(Human Leukocyte Antigen DR,HLA-DR)表达减少,引起抗原提呈能力下降,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减少,IL-10 等免疫抑制因子增加,加重机体免疫抑制[10]。这与基因的表观遗传调控有关,我们已经了解基因启动子和增强子的高甲基化通常与基因抑制有关,低甲基化与基因激活有关,目前临床研究[11]表明,脓毒症患者IL-10 表达与启动子中甲基化水平呈负相关,这与免疫抑制病理生理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观遗传修饰可在脓毒症消退后持续存在,其可能与脓毒症后持续免疫抑制导致多器官衰竭有关[12],且这种修饰可编写入正常细胞内并遗传,对机体免疫应答产生长久的不利影响[13],感染性疾病发生的遗传关联的存在表明脓毒症患者存在基因组异质性,这也提示我们表观遗传在脓毒症机制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大量免疫细胞凋亡也会导致尚存活的免疫细胞功能紊乱。吞噬细胞吞噬清除凋亡的免疫细胞而减少了对病原体的吞噬,表现为机体免疫系统被抑制,导致脓毒症耐受。中性粒细胞数量增加但功能受损,脓毒症期间可分化出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亚群,该亚群可分泌大量IL-10 从而干扰机体正常免疫功能。脓毒症患者即使度过严重期存活下来,也会表现为长期慢性免疫抑制,称为持续性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Persistent Inflammation- Immunosuppression Catabolism Syndrome,PICS)[14]。
2 脓毒症诊断和预后预测的生物标志物
临床中对于脓毒症进程的判断会依靠不同生物标志物的短期或长期监控来实现,如何准确把控各种生物标志物对脓毒症诊断或预后的预判作用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2.1 促炎细胞因子 促炎细胞因子是目前脓毒症中研究的较为透彻的一类生物标志物,即便如此,能运用到临床中的少之又少。IL-6、IL-8、IL-18 和TNF-α 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预测脓毒症严重程度及死亡率,但同时,促炎细胞因子的初始量产是导致脓毒症高炎症的原因之一,所以其变化程度在临床中不易掌控。研究[15]表明,脓毒症组患者IL-6水平显著高于非脓毒症和正常组,且在病后28 d左右明显升高,这表明IL-6 高敏感性的特点可以有效预测脓毒症患者预后情况,有可能确定脓毒症患者发展为重症脓毒症的风险大小,因此可作为理想标志物之一,其他促炎因子效果则不甚理想。
2.2 抗炎细胞因子 IL-10是脓毒症中具有高特异性的初始标志物,其可增加T 细胞IFN-γ 产生,减少TNF-α和HLA-DR表达,其中对适应性IFN-γ的产生增加仅见于脓毒症患者,对先天性及获得性免疫发挥负性作用。研究[16]表明,抑制小鼠IL-10水平可改善脓毒症免疫反应及预后。临床数据[17]显示,与存活的脓毒症患者相比,IL-10水平在脓毒症危重病死者中更高,表明IL-10 升高与疾病进展存在相关性。也有与之相反的结果,早期动物实验中,使用IL-10治疗的小鼠存活率更高,阻断IL-10 则会增加脓毒症模型小鼠的死亡,提示高水平IL-10 与脓毒症危重患者的预后和死亡相关[18]。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或许可以解释为IL-10 变体对不同免疫细胞进行作用而导致的不同免疫效应,不同动物的耐受力及脓毒症模型使用的病原体不同,从而表现出抗炎和促炎效果[19]。
2.3 HLA-DR 正常生理情况下,HLA-DR 被T 细胞表面受体(T Cell Receptor,TCR)识别提供第一信号,表达于T 细胞表面的CD28 与表达于APC 表面的CD80、CD86 相互作用提供共刺激信号,T 细胞被激活,参与免疫应答。而在脓毒症病理生理中,代偿性抗炎反应致使机体免疫反应减弱,表现为巨噬细胞、单核细胞等表面HLA-DR 表达减少,T 细胞激活必需的第一信号无法提供。另外,T 细胞调节阴 性 共 刺 激 分 子CD152 表 达 增 加[20],CD28 与CD152 的作用并非提供T 细胞激活所需的共同刺激,而是导致T 细胞无反应,免疫应答无法完成。研究[21]证实,脓毒症患者体内淋巴细胞衰竭,HLADR 被显著抑制,而存活患者体内10 d 左右会恢复,我们可以认为淋巴细胞绝对计数和单核细胞HLADR 表达减少是脓毒症免疫抑制的生物标志物,住院一周的恢复水平可对脓毒症预后进行一定程度的判断。
2.4 血乳酸 目前临床上最广泛使用的器官功能障碍生物标志物是血乳酸浓度。脓毒症期机体代谢功能障碍,乳酸水平变化缓慢,不能用于急性期的指导治疗,但连续测定可明确患者变化,评估整体病情。临床研究表明,应每隔1~2 h 测量血乳酸水平以进行病情评估,若在脓毒症性休克复苏的前6~8 h降低乳酸水平,可能改善患者预后[22]。临床中主要偏向认为血乳酸水平升高是氧输送不足,脓毒症期间缺氧器官进行无氧糖酵解,丙酮酸生成乳酸[23]。但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即使组织灌注没有受到影响,其他因素也会导致乳酸堆积,高乳酸血症除组织缺氧型外还有无组织缺氧型,后者与先天性代谢障碍、基础疾病、药物或毒素等相关,另外乳酸清除率降低也是原因之一,多出现在脓毒症致肝功能损伤患者体内,回归分析结果表明24 h 内血乳酸清除率延迟与脓毒症肝功能障碍患者的医院死亡率有独立关系[24],因此血乳酸清除率可作为脓毒症伴肝功能障碍或脓毒症性休克初始复苏期间患者死亡率的潜在预后标志。
2.5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和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PCT 和CRP 都是机体应对感染和损伤时产生的蛋白质。PCT正常生理情况下由甲状腺C 细胞合成,而在脓毒症中由甲状腺外组织负责合成,机体内轻微或局部感染、慢性脓毒症等不会引起PCT 水平的升高,急重症脓毒症导致PCT水平大幅升高,可反映炎症的严重及缓急程度。另外,细菌感染引起PCT 水平升高,病毒感染、过敏则不会。有研究[25]表明,PCT 可准确区分脓毒症和非感染性SIRS,所以其又可作为鉴别细菌性与非细菌性感染的有效标志,但对脓毒症患者28 d 死亡率没有明显指导作用[26]。
炎症期间CRP 在机体内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目前已知其在肝脏中受IL-6 刺激而合成上调,可以与微生物的磷脂成分或损伤细胞结合,利于巨噬细胞清除,是公认的感染与炎症期生物标志物。CRP 具有高敏感性,对感染及炎症刺激快速反应,通常用于脓毒症早发检查,也可预测脓毒症患者28 d 死亡率[27],但具有低特异性。急性炎症、严重感染性疾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中CRP水平均可升高,所以近年来其他高特异性标志物的发现降低了CRP 单独作为脓毒症生物标志物的重要性。
CRP与PCT单独应用对诊断脓毒症是否更具优势仍存在争议。早期UZZAN 等[28]发表了一项比较CRP 和PCT 诊断脓毒症的Meta 分析,OR 值与集成ROC(SROC)曲线结果表明,在危重脓毒症患者中,PCT 变化程度始终高于CRP,这表明PCT 比CRP 有更优的准确性,可以作为一种成人脓毒症的早期快速诊断或筛查实验;此外,研究还认为,PCT 水平升高不能确诊机体感染,但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效果,因此可以在诊断危重脓毒症患者时发挥一定作用。
2.6 表观遗传修饰相关生物标志物 表观遗传修饰是指控制基因表达但与DNA 序列变化无关的调控机制,其建立在内毒素耐受上,主要包括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s,ncRNAs)作用,在脓毒症代谢相关病理生理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DNA 甲基化是表观遗传修饰中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类,属于胞嘧啶残基的修饰,主要在胞嘧啶-鸟嘌呤(CpG)基序的背景下进行[29]。DNA 上甲基的添加或去除可改变局部染色质结构,导致蛋白质结合改变,基因表达随之改变。功能研究[30]表明,DNA 甲基化相关位点在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炎症之间存在可测量的表观遗传学差异,对诊断及预后有所助益。差异甲基化区域(Differentially Methylated Region,DMR)指同一基因位点不同程度的甲基化区域,可控制基因表达。脓毒症与非脓毒症危重患者体内均存在DMR,脓毒症中发挥作用的DMR 相关基因,如C3、MPO、ANGPT2 等,与涉及抗原提呈和组蛋白甲基转移酶基因重叠[31],说明脓毒症与非脓毒症患者先天免疫反应和获得性免疫系统的表观遗传调节存在根本差异。但目前DNA 甲基化作为临床生物标志物仍不现实,相对于临床中疾病的快速变化而言,基因位点检测不够简单快速,不能够作为首选。
组蛋白修饰可以直接参与基因转录和染色质调节,在机体正常生理和疾病病理生理中均能发挥作用。组蛋白由H2A、H2B、H3、H4 构成核小体,再由DNA 双螺旋缠绕在周围组成。由于受共价修饰的影响,核小体内彼此间的作用及与DNA 的关系发生改变,进而与DNA 甲基化发生互补,共同决定局部基因的表达模式。脓毒症涉及的组蛋白修饰主要表现为H2A、H2B、H4 的高度乙酰化及H3 中的特定甲基化,在多种免疫细胞中均起作用。研究发现,机体遭受内毒素攻击后,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的促炎细胞因子启动子区域H3赖氨酸9二甲基化(H3K9me2)和DNA 甲基化水平增加,释放炎性因子能力降低而产生抗炎因子能力增加,导致免疫耐受发生[32]。淋巴细胞的发育与调节过程中,组蛋白修饰通过使B细胞基因组发生低甲基化和高乙酰化,T 细胞中H3K27me3 水平升高等变化,淋巴细胞表现为不活跃,甚至基因沉默的表观遗传状态[33]。目前关于脓毒症中组蛋白修饰的研究已经非常广泛,但其在患者体内的作用仍未清晰,距离应用于临床还有很长的距离。
ncRNAs 中研究最广泛的是microRNAs(miRNAs),这是一类内生的、长度约20~24个核苷酸的小RNA,在重症脓毒症患者血浆、尿液中均可检测到,虽然这类小分子的来源尚不清楚,但在脓毒症病理生理过程中,其作用网络的动态变化可参与促炎或抗炎过程,控制机体免疫系统表达,调控内毒素耐受转入免疫抑制。目前miRNAs 已被认为是脓毒症的生物标志物,如miR-150与miR-155表达与脓毒症病理程度呈负相关,miR-146a、miR-223 联合使用的诊断效果优于PCT、CRP 等常规标志物,miR-13a 水平可反应疾病严重程度及患者长期死亡率,miR-15a、miR143 可以较好的区分脓毒症和SIRS[34]。虽然这些研究已经得出针对脓毒症的有效结果,但在临床操作中如何应用尚存在争议,尽管如此,该领域仍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综上,脓毒症病理生理过程主要反应为免疫机制的变化,细胞因子风暴和免疫抑制的强弱关系影响脓毒症疾病进程及严重程度,控制促炎反应与抗炎反应平衡是维持内环境稳定的关键。脓毒症是一种高异质性疾病,不同的病原体、感染方式、个体差异等因素导致疾病效应千差万别,以至脓毒症治疗一直不甚理想。近年来,关于脓毒症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数量稳步增加,除了对脓毒症整体诊断及预后进行预测外,各系统损伤预测的标志物也有所发现,如Syndecan-1、血小板预测脓毒症患者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及死亡率[35]。目前脓毒症的诊断主要依据器官功能衰竭评分,但反应脓毒症患者状态变化的生化指标仍存在不及时的问题。多标志物联合的预测手段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最终治疗效果仍取决于患者的个体化状态。这里所讨论的是目前研究较广泛,能够在病床前获得的标志物,关于其他方面如肠道微生物、补体系统等领域以及针对各器官系统的标志物仍有较大研究空间。对于脓毒症这种进展迅速、致命性强的特点,或许高灵敏性标志物比高特异性标志物来的更实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