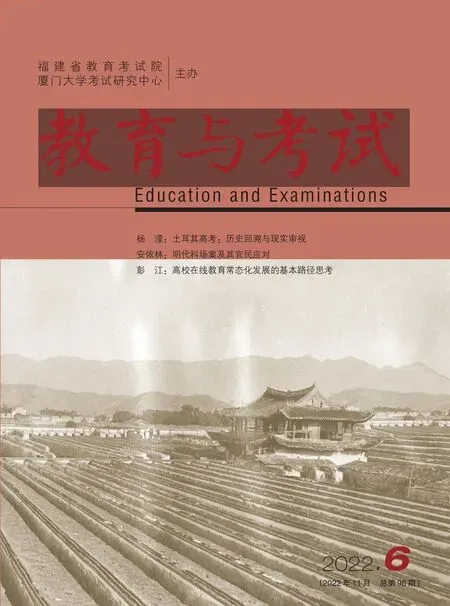明代科场案及其官民应对
安依林
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以其公正和开放的特性受到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它肇始于隋,终结于清,前后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从科举制度产生之日起,科场案就与科举制度相伴相随。“明代处于我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时期”[1],也是科场大案、要案频发的时期。明代的科场案对整个科举制度的发展以及明代的政治、社会乃至国运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但直至目前,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很薄弱,相关研究如张德信的《明代科场案》和白金杰的《明代科场案与明代政治——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主要是对明代科场案进行分类,对明代科场案的发生始末进行梳理;牛明铎的《明代乡试冒籍问题探析》等文章则主要是对科场案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个例作具体的剖析。鉴于此,本文拟从明代科场案的特点、官方应对和民间反应三个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一、明代科场案的历时性特征
(一)太祖至宣宗(1368~1435):科场“大抵服帖”期
从太祖到宣宗时期为明代科场案发展的第一阶段,此时期是明代科举制度的初创及初步发展期,其各种制度很不完善,故而该时期的科场案多由制度不完善引起,呈现出数量少、客观原因导致的科场案件多等特点。
明初,取士之法为科举、荐举、学校三途并用,进士出身还不像后世那般显赫,相反,学校和荐举在明初选拔人才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史载“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2]此外,再加上明初对科举舞弊处罚极重,故弊窦较少,“自太祖重罪刘三吾等,永、宣间大抵服帖。”[3]1703
明代科场的第一大案为洪武三十年(1397)的“南北榜”案。“南北榜”案的发生始末及其深层次原因可谓广为人知,它与明初科举制度的不完善有着莫大的关系。明初,会试取士是以成绩为准择优录取,南方士子中第人数远高于北方士子。如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会试中,共录31 人,其中南方22 人,北方9 人;[4]190洪武二十七年(1394)会试中,共录100 人,其中南方78人,北方22 人[4]191。南北方士子文学素养之间的差距据此可见一斑。由此推之,洪武三十年会试中试举人皆为北方人亦很有可能。由此可见,此时的科举制度无法平衡南北方势力,北方中试者寥寥对于加强北方人对明王朝的向心力和维护明帝国统一是极其不利的。
“南北榜”案发生后,明朝统治者有意从制度上完善科举取士之法。对于一直存在的南北取士不均问题,洪熙元年(1425),杨士奇建议实行“南北卷”制,但未及实行即驾崩。宣宗即位后,立即实行南北分卷取士之法。不久,再立中卷,“后复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名为中卷”。[5]至此,会试南北中分卷制度大体完备。
(二)英宗至穆宗(1435~1527):科场“弊窦丛生”期
从英宗到穆宗时期为第二阶段,此时明朝的政治已步入正轨,科举制度也不断发展完善并臻于成熟,这一时期的科场案与明初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其规模大,数量多,贪墨舞弊案以及上层官僚干预科场等主观类科场案急剧增多。
自仁宣以来,明朝各项制度趋于完善,统治者统治策略也由猛苛治国转为宽济治国,以内阁为主要代表的官僚集团地位上升,权力也进一步扩大。英宗初期,已是“太皇太后张氏同听政,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居辅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杨处分。”[6]因此,士人也由明初的惧仕转为此时的乐仕。与此同时,荐举与学校在取士中的地位大为下降,科举成为士人进入官僚集团的最重要途径。英宗时期,已经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3]1702的局面。
在此情形下,一些位于权力中枢的辅臣开始以权谋私,干预科场。景泰七年(1457),阁臣陈循、王文的儿子陈瑛、王伦乡试落第,二人大肆攻讦主考刘俨取士不公。复核证明,考官刘俨等并无违规舞弊行为。为照顾二人颜面,景泰帝非但没有对其进行严惩,反而以“陈循、王文,辅导有年,国之元老,岂可以一事之失,而遂加之罪”为由宽宥二人,并特准“王伦、瑛明年俱准会试。”[7]1558自成化以后,诸帝多不视朝而权柄下移,一些辅臣或联合权阉,或径直干预科场。正德三年(1508)廷试,焦芳因其子居二甲,竟然降调考官以泄愤;嘉靖二十三年(1544),翟銮干预廷试,被世宗发现,翟銮及其二子皆被贬为民。
士子为求科举中第,以跻身于上层官僚集团,也多违规舞弊。他们“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而关节为甚。”[4]1705而一些相关官员也大开方便之门,或受贿“代为答策”,或受贿“易卷”,或对舞弊行为视而不见。明朝中期,朝纲渐坏,这些弊病史不绝书。以冒籍为例,仅嘉靖一朝就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冒籍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冒籍两起大案,其他案件更是不可胜数,以至于《万历野获编》辟出专目《京闱冒籍》与《乙酉京试冒籍》载之。
(三)神宗至思宗(1527~1644):科场“积重难返”期
神宗至思宗时期为最后一个阶段,其间皇帝多委顿于上,朝臣党争于下,科举制度也日益僵化,弊端百出,已成积重难返之势。此时期的科场案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达到顶峰,各种违规舞弊行为空前增多,具有普遍性、公开性、复杂性,并多与明末党争相始终。
神宗初期,张居正当国,内阁权力达到顶峰。与此同时,辅臣干预科场案亦达于顶峰。这不仅表现在此类案件的增多,还在于辅臣的干预不仅没有得到皇帝的制止,反而得到皇帝的默许。自张居正以后,内阁势衰,阁臣再不敢公开干预科场。而此时皇帝不理朝政,党争又起,继而宦官专权,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会试,因状元归属引发了宣党和东林党之间的互斗。这场党争始于“辛亥京察”,余续延至清初,对明朝的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案中,韩敬为汤宾尹的受业弟子,而汤宾尹在当时属于宣党。本科廷试的主考官多为东林党人,他们本欲让钱谦益为状元,结果却因汤宾尹作弊而让韩敬夺得头筹,汤宾尹此举引起了东林党人的反击。在第二年的京察中,“尚书孙丕阳因置宾尹、敬于察典”。[4]1704叶向高、孙丕阳等东林党人以科场舞弊案大肆攻击汤宾尹。由于当时东林党权势正盛,结果“宾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称病去。”[4]6153而东林党的攻击又引起了宣党的回应,宣党联合齐、楚、浙三党共同反对东林党,从此,明末党争达到一个新高度。
明朝后期,科场不仅被肆意干预,还成了结党营私的重要场所,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场已成了进行党争的重要阵地。其时,无论韩敬还是钱谦益皆有大才,且二人关系甚好,二人无论谁中状元都不出乎意料。然而由于明末科场之弊、政局之乱,二人还未入仕途即已陷入党争。此时的科场已成积重难返之势。
二、科场案之官方应对
明代的科场案可分为客观因素造成的科场案以及人为因素造成的科场案。其中,客观因素造成的科场案主要发生于明朝前中期;人为因素造成的科场案则贯穿于整个明朝,到明中后期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是明代科场案最主要的内容。
(一)客观因素科场案的应对
1.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科场遭遇水火灾害等自然因素造成的科场案后,明朝官方一般都会妥善处理善后事宜,一方面维持科场秩序,保障科场公平;另一方面,积极抚慰遭灾考生。正统三年(1438)顺天乡试发生火灾。主考官曾鹤龄提出“必更试,然后百弊涤至公著,不然,虽无所私,亦招外谤……命下,悉如鹤龄所言。”[8]这既考虑了科场的公正性,也有效地杜绝“外谤”,使考生心服。天顺七年会试大火,“时举人死者九十余人”[9],此次会试考场火灾的伤亡之惨前所未有。面对严重灾情,政府一边安排重考,以保证科场的公正,“改试期以八月,命太常少卿彭时、侍读学士钱溥,取中吴鈛等”[7]1559—1560;一边抚慰遇难考生,“上怜之,赠死者俱进士出身。”[7]1559
2.着眼长远,加强制度建设并完善科场硬件设施
英宗时期科场的两场火灾使明政府意识到科场防火防灾的重要性。成化二年(1466),礼部在奏准改革会试条例中,就提出对科场的“给烛”制度加以改革。对于改革的原因,礼部在奏疏中写道:“今士子比昔倍蓰,中间多有故意延至暮夜,请烛之时,抄写换易;或有弃烛于席舍中而他出,因而误事者,最为可虑。”[10]因“弃烛于席舍而误事”已成为此次“给烛”制度改革的最主要原因。由此可见,“给烛”制度改革显然与天顺七年(1463)会试火灾案有着直接联系。
此外,政府还加强考场中的硬件建设。顺天贡院于天顺七年毁于火灾,之后重修时充分考虑了风火的预防问题,“累经建议盖造板舍,以防风火之虞,实为永便……于中止盖楼房一间,四角望楼俱不必用,临时止用军士二三十人四面观看,最为省便。”[11]这已经提出要彻底地以楼房取代临时搭盖的席蓬,以期消除风火隐患。随后,在万历二年(1574),再次对顺天贡院进行改建扩建,这也是明朝政府对顺天贡院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扩建,而防风火也是此次贡院改建扩建的一个重要考量。
正因科场硬件设施的日益完善,水火灾害等自然因素造成的科场案在明朝中后期大为减少。
(二)人为因素科场案的应对
1.惩治涉案人员,以儆效尤
在我国古代,科举取士被称为国家的“抡才大典”,受到历朝历代的高度重视。明代,最重科举,相应的,明朝政府也极为注重科场秩序,对于科场违规作弊者,多予以惩治。
明初,政治清明,百官肃然,科场中违规舞弊者寥寥,而敢于作奸犯科者皆受严惩。
明朝中后期,朝政渐坏,纲纪渐弛,科场案骤多,但各朝仍极为注重科场秩序。对于违规舞弊的士子绝不姑息。如景泰四年(1453)顺天乡试冒籍案,“乡试取中举人尹诚、汪谐、陈益、龚汇、王显、李随、李森、钱轮俱系冒籍人数,……乞明正其罪,以警将来。命锦衣卫俱执送刑部问。”[12]不仅如此,还终身不予录用。对于不按规定答题的士子,亦严惩不贷。万历三十八年(1610)顺天乡试,“第一名赵维寰,浙江平湖人,以文体被参,礼部复试,罚科。”[13]以文体被参而不顾其真才实学,虽有因噎废食之憾,但亦可看出明廷对于科场违规行为的态度。
此外,违规舞弊的官员,亦是科场案发生后的主要处治对象。正统元年(1436)四月,山东乡试发生了冒籍大案。“训导江振为帘外官,受士子赂,代为答策,考官朱经亦受赂托弥封官易卷”。[14]事情暴露之后,所有涉事人员皆受严惩,监临官也以“防范不严”论罪。对于因考官失误而造成的科场案,政府亦不姑息。弘治三年(1490)正月,“巡按江西监察御史赵炯以监临江西会试,进《小录》装轶失次,下刑部逮问,赎杖还职。”[15]嘉靖年间,世宗严控科场。因此,辅臣如张孚敬、夏言、严嵩等俱不敢干预科场,而干预科场之阁臣瞿銮,与其子俱贬为民。
明朝对科场案中违规舞弊之士子、官员的惩治,极大地震慑了意欲舞弊的士子与官员。
2.姑息养奸,刻意纵容
有明一代,政府对科场案的处治以严惩为主。但在明朝中后期,或出于对高级官僚的尊敬,或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政府有时也会对参与科场舞弊人员采取姑息态度,甚至于默许纵容。
此类事件最为典型、最为频发的是神宗一朝。
神宗以冲龄践祚,大政悉委之于张居正,故当张居正干预科场后,神宗不仅不加以干预,反而刻意纵容,此事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多赘言。张居正去世后,神宗独揽权柄,但对于阁臣干预科场,亦多有纵容。万历十六年(1588)顺天会试,以王锡爵之子王衡为解元,这遭到了一些朝中大臣的不满。次年(1589),内阁首辅申时行之婿李鸿再次高中,朝臣更为不满,要求复试以保证科场公正“礼部郎中高桂论劾举人李鸿等,并及衡:‘……宜一体复试,以明大臣之心迹。’”对于高桂的复试请求,神宗非但不允,还“谪桂于外,下伸狱,削其官。复试所劾举人,仍以衡第一,且无一人黜者。”[3]1703
张居正之后,神宗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纠正科场弊病,对申时行、王锡爵之亲属中第也未采取妥当的办法使朝野内外为之信服,科场更为大坏。
此外,由于明朝中后期皇帝对某些科场舞弊者采取纵容态度,使得一些正直的大臣开始不断弹劾或攻击干预科场者。万历后期,皇帝怠政,奏疏留中,科场弊端丛生,科场大案发生后,各党派之间互相攻讦,党争不断,此事如前文之万历庚戌科场案。
3.实行复试,求取公道
顾名思义,复试即对正常考试有所怀疑,为求公平公正,政府对全部或某些士子另行考试,若复试卷与原卷笔迹文理相符,则可证明被疑士子的清白,反之,则说明有舞弊行为。明代复试特别频繁。尤其是疑似违规舞弊案发生之后,政府一般都会进行复试,以确认是否确有舞弊之实。
复试制度在明朝前期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一些并无舞弊行为的被疑士子通过复试获得了清白;一些靠舞弊中第的士子则被绳之以法,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应天会试通过舞弊中第的沈同和。虽然明朝中后期科场复试亦有种种弊病,但总的来说,其在保证科场公正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舞弊士子亦起着一定的震慑作用。
4.严控关防,加强制度建设
明代科场案发生后,政府也从长远入手,吸收借鉴前朝科举防弊措施与制度,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朝的一系列防弊制度。
首先,加强考前防范,拒科举舞弊于考场之外。一方面,政府加强身份检查,以防止冒籍。冒籍案主要是在“南北中”分卷制度实行后产生的。英宗之时,冒籍已十分严重,对此,政府下令严禁。“科举本古者乡举里选之法,近年奔竞之徒利他处学者寡少,往往赴彼投充增广生员,诈冒乡贯应试,今后不许”。[16]明朝中后期,科场窦弊繁多,冒籍现象更是有增无减。科场冒籍一方面带来了科场不公,一方面又加剧了官员的贪腐,因此明代历朝都申明冒籍之禁。
另一方面,严格考前搜检,以防夹带。明初,科场多守法,诸帝也多尊重士子,搜检时“止就身搜检,举巾看视,不必屏脱衣服,剥露体肤,致损士气。”[4]166仁宣以后,科场弊窦丛生,夹带者甚多,于是明廷对夹带的搜检也愈益严格。“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17],若搜检发现士子敢有夹带行为的,处罚甚重。此外,明廷对怀挟考官等为考试服务人员的搜检与处罚也更加严格,对其处罚不仅有捉拿、问罪、罚俸还有充吏、充军等。
其次,加强对考官的管理,完善锁院制度与考官回避制度。明代考官有内帘官和外帘官之分。为了防止考官泄露考题,与外部暗通关节,串通作弊,自宋代以来科举考试皆对内帘官实行锁院制度。锁院制度的实行,很大程度上截断了科场舞弊案的发生途径。明廷实行考官回避制度,是为了防止任人唯亲。有明各朝,都对这一制度加以补充和完善。景泰二年正月,礼科都给事中金达上奏言科举事,其中就提到“监察、巡绰等项官军,前科曾入场及有弟男子侄亲戚见在应试,俱令回避。庶几较文无偏执之失,取士无侥幸之弊。……事下礼部议:会试考官宜遵旧制,进士临期取中式名数奏请定夺,监试。巡绰等官军前科入场及有亲属应试者俱合回避。……从之。”[18]考官回避制度愈益完善。
最后,加强试卷管理。在试卷管理上,沿用唐宋以来的糊名、誊录制度。明代关节舞弊等案频发,明廷一面颁布诏令,严守糊名誊录之制;一面探索完善此制,至嘉靖年间,糊名、誊录之制已十分完备。
三、科场案之民间反应
科举取士是明朝各类人群跻身于官僚阶层的最重要途径,“夫科目者,国家所以鼓舞天下之大权大柄也。”[19]1610科场的公正与否与明朝普通人尤其是士子们息息相关。因此,一方面,政府为笼络士子,巩固皇权的统治基础,大力加强科场建设,积极应对各种科场案件,以维护科场公正;另一方面,各类人群为通过科举跻身官僚阶层,也极力反对科场不公现象。相对于政府而言,民间人士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科场案的处置措施不具有强制性。但是,随着各类科场案层出不穷,民间人士亦多有行动。
(一)上奏揭发,施压政府
在明朝,当科场案发生之时,一些士子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出于士人自身的责任感,时常会上奏各级政府,要求政府维护科场公平,严惩舞弊违规之人。士子为官僚阶层的后备军,是皇权的重要依靠力量。对于士人的这种要求,政府一般都会做出相应的回复。
明朝中后期,由于政治生态的不断好转,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士人阶层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对于各种频发的科场案,也敢于更多地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隆庆四年(1570)顺天乡试,提学副使陈万言在科举取士时遗失甚多,引起了考生的不满,他们强烈要求进行复试。由于要求进行复试的人数太多,政府表示同意,“巡按御史刘思问于八月初一日在省考选遗才,众至者三万八千余人。”[20]虽然此次复试现场失控,导致了严重的踩踏事故。但士人们的行动对于科场的监督有利于科场的公正运行。
万历十三年(1585)顺天乡试,冒籍者甚多,此科选中的外地举人达八人。对此,顺天士子愤愤不平,以为不公,“投匿名文书,诉中试者不应皆外郡,及各州县进学之弊。”[19]1593给事中钟羽正随即将此事上奏,要求清查并处治冒籍生儒。与此同时,顺天的一些权势之家也利用手中权势大举造势,诡言考官与提学有私。很快,“飞言乃闻上,上愈疑,法司勘上。”[19]1593最终将冒籍者发还原籍为民并严厉的处罚了相关考官。此次,民间力量对科场不公现象的揭露,以及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获得了一些朝中正义大臣的支持并最终使政府解决了此事。
(二)制造舆论,发泄不满
有明一代,当科场案发生之时,虽也有民间力量直接上奏以向政府施压,但大多时候民间人士还是以制造舆论的方式来发泄不满。
在这些舆论中,有的因影响过大而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相应的回复。万历四十四年(1616)会试,发生了明代科场中最大的一起作弊案件。白丁沈同和靠抄录怀挟及同乡赵鸣阳之文高中会元。此案影响很大,榜发之后士论哗然,都城竞相传言“白丁会元”。政府很快闻听此事并对沈同和、赵鸣阳等人进行了严肃处理。此外,隆庆四年(1570)乡试中,有两个平时被弥封官刘绍恤看中的士子中第,引起了其他士子的怀疑,“士论大哗,谓绍恤私二人,从落卷搜出改洗冒中”,政府很快对此事做了调查并公布结果,“……行抚臣逮问,二人中式,绍恤实不私,然不应招致门下以起事端,其以不及调用。”[21]从最后政府的调查结果可推知:士子们所传布的实非亲眼所见,应为子虚乌有。但政府仍给予刘绍恤以处罚,应该是受到了民间的舆论影响。
也有一些舆论并没有被政府采纳,而仅仅流传于民间,其涉案人员也只受到民间的评判。如天顺元年(1457)会试,群众对于考题以及石亨干预科场十分不满,民间多有俚语传唱,“薛瑄《性理》难包括,钱溥《春秋》没主张。问仁既已无颜子,告祭如何有太王。……总兵令侄独轩昂。”[7]1559由于当时石亨权势正炽,政府并没有对此俚语作任何回应,但群众却用俚语的形式对此科场案进行审判,将石亨等人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此后万历初期,张居正干预科场,使其三子俱登第。慑于张居正之权势,民间亦是以俚语的形式表达不满,“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22]
虽然有的民间舆论政府并未给予回应,但却基本都能对政府产生特定的影响。如天顺四年(1460)石亨被治罪,有人便以俚语加其罪,“后坐亨败除名,及以怨谤剐于市”。[7]1559此后张居正败没亦然。
(三)乘机攻讦,肆意诽谤
民间对科场案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民意色彩,但不可否认,明代科场中也始终充满着民间人士尤其是士子们诽谤的声音。他们或公报私仇,恶意中伤;或道听途说,肆意诬陷;或科场落第,泄己私愤。
天顺四年(1460)既有下第举人诽谤考官之案例,“会试举子不中者俱怒考官……上意方回,乃命礼部翰林院考此举子,验其学,多不能答题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众,众议方息。”[23]在经过严格的复试之后,诽谤的士子被严惩。明代中后期,随着士人群体的不断壮大,士子恶意诽谤、恶意攻击的事件屡见不鲜。正如郭培贵所言“特别是弘、正以后,士人思想日趋开放;而与此同时,其出路甚至生存竞争日趋激烈。所有这些,都使举人成为当时最不安分的群体之一。”[24]隆庆元年(1567)九月,“(南监)监生下第者数百人喧噪于门外……诏南京法司逮治其为首沈应元等数人,如法发遣”。[25]
士子们的恶意诽谤喧噪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因此,明代历朝都严禁士子造谣诽谤。早在洪武三年(1370)颁布的《科举诏》中,即明确规定:“应试下第之人不许喧闹、摭拾考官及擅击登闻鼓;违者究治。”[26]此后,对于士子喧闹诽谤的处罚愈益严厉和具体。嘉靖十二年(1533)、万历三十年(1602)、四十三年(1615)、四十四年(1616)、天启七年(1627)都颁布了众多条例,提出要亟除谤贴,严惩不法士子。
士子们造谣诽谤之风在明后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当时的考官常为众矢之的。万历十六年(1588)顺天乡试,主考黄洪宪向皇帝所上的奏疏,深刻而全面地表达了作为考官的处境和难处。[19]1601此外,再加上明中后期的士风日坏。正因如此,政府对民间士子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对其处治也日益增多。
四、结语
明代科场案的发展始终与明代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明初,政治清明,科场肃然;明朝中后期,政治逐渐败坏,科场亦窦弊丛生。
面对愈演愈烈的科场大案,官方和民间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其中,民间对科场案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民意的色彩,是维护科场公正,督促政府秉公科场的重要力量,对科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民间人士尤其是士子们的恶意诽谤造谣使政府对民间力量越来越不信任。由是,官民否隔,科场益坏。明朝中后期,政府在科场案的处理中则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有明一代,政府积极预防并打击各类科场舞弊现象,而民间士子则利用各种方式舞弊以求高中,舞弊与反舞弊使二者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双方的矛盾斗争也使科举制度在明朝中后期日益僵化。为保证科场的公正,防弊成了科场的最主要目标,而选拔的人才则趋于平庸。
清承明制,明朝灭亡后,清朝继续沿用明朝的科举制度并加以发展,明朝科场的弊端在清代亦暴露无遗。清代的科举较之明代更趋僵化,已逐渐失去选拔人才的作用。作为封建社会附属品的科举制度因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必将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