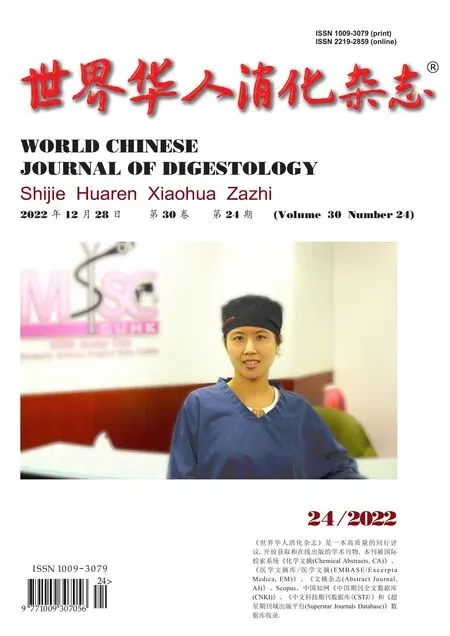肠易激综合征低度炎症研究进展
池肇春
池肇春,青岛市市立医院消化内科 山东省青岛市 266011
0 引言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种常见的肠道疾病,其特征是慢性腹痛或不适以及排便习惯改变.病因可能是多因素的,包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us pituitary adrenal gland,HPA)轴失调、神经内分泌改变和内脏超敏反应,导致腹痛和肠道运动紊乱的标志性症状.慢性、低度、亚临床炎症与疾病过程有关,并被认为是IBS症状的永久性表现[1].研究表明IBS是一种多因素疾病.IBS既涉及遗传因素,也涉及环境因素,尤其是似乎易患IBS的心理困扰[2].全身或黏膜细胞因子的改变过程以及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似乎在IBS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可归因于多种情况,如肠道炎症、内脏敏感性改变、食物敏感性、基因易感性、肠道-宿主微生物群改变,以及大脑-肠道信号传导改变相关[3].以前,在大多数IBS患者中,常规组织学检查未发现明显的肠道黏膜异常;然而,通过现代测序技术、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和超微结构分析,已经报道了细微的微观和分子改变[4],这对IBS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
据新近的研究,炎症可能在IBS发病机制和一组个体IBS症状的发展中起作用.有大量研究证据表明IBS持续发炎,这些研究在IBS患者中检测到低水平的抗炎细胞因子[5],或其他研究发现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或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比例失衡[6].
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之间的失衡在IBS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已被世界各地的几项研究证实.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是免疫反应的重要调节剂,它们也在肠道炎症中发挥作用.细胞因子的产生受遗传控制,由于细胞因子分泌水平的不平衡可能导致疾病的易感性以及临床症状[7,8].
1 肠黏膜与肠道免疫系统
肠黏膜是复杂的肠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具有多种免疫细胞.暴露于食物、细菌、寄生虫和病毒等可能有助于肠道免疫系统的致敏和炎症级联反应的激活.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具有典型IBS症状的患者结肠黏膜固有层免疫细胞增加,油酰乙醇酰胺[一种内源性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α,PPAR-α)激动剂]和具有抗炎特性的脂肪酸酰胺水平显著降低[9].这些在显微镜水平上提示慢性低度炎症.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黏膜肥大细胞浸润增加.由于肥大细胞通过激活和脱颗粒介导人体内的多种炎症反应,因此认为观察到的肥大细胞体积密度增加可能是IBS患者持续炎症反应的结果[10].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肥大细胞稳定剂酮替芬具有良好的有益效果,为肥大细胞和免疫激活在IBS中的作用提供了进一步证据.黏膜T型和B型淋巴细胞也构成胃肠道适应性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来自IBS患者的结肠活检发现T细胞密度和激活增加[11],再次符合IBS疾病过程中潜在低级别免疫激活的假设.十二指肠活检也证明了免疫激活增强.来自IBS患者的血样也显示出活化表型[12],表达肠道归巢整合素β7的CD4+和CD8+T细胞频率增加.这些发现提示IBS患者肠道免疫活化增加,是导致 IBS低度炎症的重要一步.
细胞因子是在信号传导中起重要作用的免疫成分,由免疫细胞分泌,当它们连接辅助T细胞1(T helper cell 1,TH1)、TH2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s,Tc)时,它们会影响其他细胞[13].细胞因子在肠道炎症中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些细胞因子中的一些降低了IBS的风险,如抗炎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s,IL)-10,而其中另一些细胞因子发现与IBS的发生与发展相关,如促炎细胞因子,其总是促进炎症反应,见于IL-1、IL-6、IL-8、IL-12、IL-1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等[14,15].研究证实与IBS相关的主要促炎细胞因子是IL-6、IL-8和TNF-α.在一些研究中,发现IBS患者的IL-6、IL-8、IL-12和TNF-α水平升高和IL-10(一种抗炎细胞因子)水平降低而导致IBS发生[3,14].
IBS时肠黏膜中活化的免疫活性细胞数量增加,包括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提示黏膜免疫系统在发病机制中起作用.随后的调查发现IBS患者的胃肠道肥大细胞数量增加[15,17].肥大细胞与创伤愈合、病原体防御和胃肠黏膜过敏有关.它们脱颗粒产生炎性和免疫介质,将额外的炎性细胞吸引到胃肠黏膜.根据许多研究,IBS患者肥大细胞的增加与IBS的特定症状有关,如腹胀和胃不适.IBS患者黏膜活检标本中存在活化T淋巴细胞是另一个发现[17].几项研究发现,患者肌间神经丛中的淋巴细胞浸润率高于健康对照[16,17].此外,IBS患者的结肠活检和血液样本中含有更多活化的T细胞.T淋巴细胞在适应性免疫中发挥作用,并执行多种任务,包括激活B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以及破坏受污染的宿主细胞[18].此外,外周血单核细胞和血清中促炎细胞因子表达的增加可能表明IBS患者的免疫激活倾向.支持炎症和促炎细胞因子在IBS中的功能的研究结果[3].
2 感染后IBS和改变的微生物群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感染性胃肠炎后,超过10%的受感染者会发展为感染后IBS[1].与病毒性胃肠炎相比,细菌性胃肠炎感染后IBS的风险更大.在感染后IBS患者感染后3个月的直肠活检中报告了IL-1βmRNA表达上调[19].研究显示IL-1β是一种促炎细胞因子,可导致细胞炎症.
感染后IBS患者的系列直肠活检也显示,与症状最终减轻的患者相比,T细胞和其他肠内分泌细胞持续增加.感染后IBS患者的胃肠黏膜中的CD3+、CD4+和CD8+T细胞计数也显著升高[20].这些细胞参与肠道的适应性免疫反应.综上所述,这些发现均支持IBS的炎症-免疫病因导致IBS的发生.
感染性胃肠炎的另一个后果是正常肠道菌群的破坏,通过使用16S rRNA测序,研究发现感染后IBS患者的微生物多样性减少[21].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类杆菌和普氏杆菌的相对增加已被频繁报道.研究证明微生物组可调节炎症,并通过微生物代谢产物直接或间接发挥作用.因此,微生物失调已被证明会促进炎症并损害正常淋巴细胞功能,最终导致慢性低度炎症的持续(参见本文4)[22].临床上也看到补充益生菌可以缓解IBS症状,并对肠道微生物群产生持续的影响[23].
3 神经炎症、脑-肠轴与IBS
心理社会因素与IBS的病因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儿童期虐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成年期IBS的发展有关.压力(应激)被认为会增强免疫激活,因为它刺激促炎细胞因子和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焦虑和情绪障碍也是感染后IBS的公认风险因素,其风险与严重感染性胃肠炎发作相似.现代心境障碍病因学研究常常暗示IBS时有系统性和神经性炎症的持续存在[24].
由于大脑可以干扰肠道功能,IBS症状被认为是一种心理表现.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IBS的发病机制中,脑-肠轴(brain gut axis,GBA)的失调微生物群起着关键作用.GBA的概念是大脑和肠道之间存在串扰,因此暗示串扰具有影响其个体功能的能力[25].GBA是一个双向网络,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肠神经系统和HPA轴.它主要参与胃肠运动的调节、消化酶的分泌以及使用各种神经递质(如乙酰胆碱、多巴胺和血清素)与其他器官的沟通.在涉及的各种系统中,肠神经系统是主要的网络,不仅调节肠道运动和分泌,还参与免疫系统和维持肠道内环境平衡[26].通过与肠道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GBA失调被认为是IBS的病因之一.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可以通过影响涉及肠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或肠肌巨噬细胞的途径以影响胃肠运动,其改变是IBS的一个标志,这可能是IBS导致胃肠运动改变的潜在机制[27].
色氨酸途径已被强调为微生物群相关GBA的代谢途径.在这些代谢途径中,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尿氨酸和吲哚衍生物等分子可能通过GBA影响肠道微生物群[28-30].色氨酸是从饮食中获得的一种必需氨基酸,是5-HT的重要前体.据报道[31],IBS患者的5-HT稳态发生改变,并可能与运动障碍有关.吲哚胺-2,3-双加氧酶激活或饮食限制导致宿主色氨酸耗竭,减少了乳酸杆菌的增殖,色氨酸水平的恢复选择性地诱导了乳酸杆菌的扩展.因此认为色氨酸代谢受损(可调节GBA)可能参与IBS症状的表现,且与局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相关.
早期生活虐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已被证明会导致致敏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系统和HPA轴失调[32],从而促进促炎表型.业已证明,炎症前血浆细胞因子IL-6和IL-8水平升高与IBS患者有关.由于促炎细胞因子增加,吲哚胺-2,3-双加氧酶(色氨酸降解途径中的限速酶)的活性将上调,最终影响色氨酸代谢并导致5-HT功能异常,与肠道运动改变和伤害性疼痛敏感性增强相关[33],而这两个症状都是IBS的特征.
4 肠道微生物与IBS
目前认为肠道微生物失调是IBS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肠道微生物群在食物色氨酸(tryptophan,Trp)分解代谢为多种代谢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代谢物调节黏膜免疫和稳态、肠道运动和神经生物学功能[34,35].色氨酸代谢遵循三条途径: 肠嗜铬细胞中的5-HT途径、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中的尿氨酸途径以及肠道微生物群中的吲哚途径[34].多种细菌能够产生吲哚,包括乳酸杆菌、梭状芽孢杆菌和类杆菌属.吲哚衍生物能够结合并激活芳基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通过先天性淋巴细胞3(group 3 innate lymphoid cell,ILC3)诱导下游细胞因子如IL-22的表达,从而调节上皮完整性和免疫力[36].值得注意的是,无AhR配体饮食或IL-22基因敲除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可发生改变[37].最近,微生物群诱导的结肠神经元AhR表达已被证明在微生物群的神经元编程中很重要,以维持肠道运动,从而调节肠道生理[38].最后,多种Trp代谢途径的失调可能与IBS有关[39].
在临床前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post-infectiousirritab Iebowelsyndrome,PI-IBS)模型中,AhR/IL-22信号通路发生了改变.IL-22通过作用于肠黏膜完整性,减轻PI-IBS症状,如结肠超敏反应、认知障碍和焦虑样行为.因此,可以开发针对该途径的治疗策略来治疗患有慢性腹痛和相关障碍的IBS患者[40].
在无菌小鼠和胃肠道感染模型的几项临床前研究中观察到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可以影响认知功能[41].最近,色氨酸代谢,特别是犬尿氨酸途径代谢产物对大脑功能和行为损伤的影响,包括焦虑、抑郁以及认知表现和内脏疼痛感知,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的焦点[42,43].对相关黏膜微生物群的分析表明,如PI-IBS患者所观察到的,啮齿类梭状芽胞杆菌感染可导致结肠功能失调.虽然肠道感染恢复后可能会出现生态系统恢复力,但PI-IBS患者可能由于宿主因素而无法恢复微生物生态系统[44].因此在清除病原体后,在受感染小鼠中观察到细菌丰度下降,且其微生物群与未受感染小鼠微生物群不同.在IBS患者中观察到类杆菌相对丰度降低,这一点得到了厚壁菌/类杆菌比率显著增加的支持,该比率是IBS患者细菌种群变化的粗略指标.厚壁菌门的丰度,更准确地说,拉奇诺菌科的丰度在患者中增加[43-45].在感染后的小鼠中,瘤胃球科家族的丰度也增加.此外,根据对IBS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几项分析报告,受感染动物的乳酸杆菌科减少[45].
结果表明[46],感染改变了肠道的完整性、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尤其是色氨酸向AhR配体的微生物分解代谢,即使在病原体清除后,也可以减少结肠IL-22的数量.在PI-IBS患者中,描述了肠通透性增加和低度炎症,并在病原体清除后持续存在.
肠道微生物群被认为是肠易激综合征生理病理学中的关键角色,通常与焦虑样行为的发展相关[44].Trp衍生的代谢物是微生物群肠脑轴功能成分的一部分.在感染后小鼠的粪便和血清中,尿氨酸/色氨酸的比率显著增加.同样,临床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IBS患者的尿氨酸浓度增加.此外,发现IBS严重程度(包括结肠超敏反应和焦虑)与犬尿氨酸/Trp比率呈正相关.该比率反映了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2.3-dioxygenase,IDO)的活性,该酶催化Trp分解为犬尿氨酸,并在炎症过程中诱导其表达.比较Trp代谢物,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观察到患有IBS的妇女血清中吲哚代谢物水平(吲哚-3-乳酸)降低[45].
色氨酸激活芳基烃受体,这表明这种吲哚代谢物在啮齿类梭菌感染模型和PI -IBS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关键作用.研究发现,感染后的生态失调与乳酸杆菌科家族的减少有关.在感染后的小鼠中,类焦虑行为与乳酸杆菌科家族的减少呈显著的负相关.这个乳酸菌家族使用色氨酸作为能量来源,并产生AhR配体,激活ILC3和IL-22的释放,从而刺激抗菌肽的产生[46].病原体清除后,观察到AhR配体和IL-22表达减少.AhR信号被认为是肠道屏障免疫反应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通过作用于上皮更新、屏障完整性和许多免疫细胞类型,如上皮内淋巴细胞、Th17细胞和先天性淋巴细胞,它们对肠道内稳态至关重要.肠腔微生物群产生的AhR配体可以激活肠壁中的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47],但它们也可以到达肠神经元及其投射附近,以调节肠神经回路的运动输出[36].研究认为AhR/IL-22途径应该具有关键作用,针对IL-22产生可以恢复肠内稳态,最终恢复脑-肠轴通信.因此认为AhR/IL-22信号通路是逆转PI-IBS相关症状的重要药理学靶点[40].
大量证据表明[47],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有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在IBS病理生理学中起着关键作用.内脏过敏的IBS模型,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组成.此外,这种微生物失衡,即生物失调,是通过增加循环脂多糖和促炎细胞因子水平介导的,系通过破坏肠道屏障,并增加促肾上腺皮质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CRF)触发的HPA轴的活性所致.这些证据表明,通过激活促肾上腺皮质释放因子Toll样受体4(CRF toll like receptor 4,CRF-TLR4)-促炎细胞因子系统受损的肠道屏障可能改变微生物群,从而导致内脏过敏[48,49].
另一方面,微生物群及其代谢物是肠上皮屏障完整性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生物失调可破坏上皮屏障以增加肠道通透性[50].丁酸是一种来源于肠道细菌的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可增加紧密连接蛋白(tight junction protein,TJP)的表达,并有助于维持肠道屏障功能.此外,丁酸盐还可阻断CRF或脂多糖诱导的胃肠道改变[51].与此同时,Vicario等人[52]报道,重复的使用白色脂肪(white fat,WAS)降低了产生丁酸的微生物群的紧密连接蛋白表达,补充产生丁酸的细菌可逆转TJP的这种变化.此外,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微生物群会诱导无菌大鼠的内脏过敏,而健康个体的微生物群则不会.
因此,微生物群可以通过其代谢产物改变肠道屏障,这似乎是生物失调损害肠道屏障的机制之一.也就是说,微生物群的改变和肠道屏障的受损被认为是一个原因和结果,这是通过CRF-TLR4-促炎细胞因子信号介导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肠道完整性异常,表现为肠道通透性增加[43].肠道高渗性诱导细菌移位,随后激活免疫系统,导致炎症.在这个过程中,LPS通过TLR4释放并触发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在IBS中观察到血浆促炎细胞素和血清LPS水平升高[44,45].此外,在IBS中,LPS诱导的外周血单核细胞促炎细胞因子释放的刺激作用增强,可发生如急迫、腹泻等更严重的症状[46].
5 肠易激综合征中的免疫反应与炎症相关的证据
如前所述肠易激综合征被认为是一种脑-肠相互作用疾病(disorders of gut-brain interaction,DGBI),表现为慢性腹痛和排便改变.症状通常与食物有关.该领域的许多工作集中于确定患者结肠中的生理、免疫和微生物异常;然而,小肠免疫激活和微生物失衡的证据在小型研究中已有报道.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小肠内环境平衡失衡与DGBIs的发病机制有关.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和小肠肥大细胞数量增加经常与IBS相关,在IBS的发病机制中涉及微生物失衡和低度炎症.目前的文献表明IBS的发病机制不限于结肠,而是可能涉及整个肠道的功能障碍[47].
5.1 结肠适应性免疫系统在IBS中的作用 IBS患者的细胞因子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促炎性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与IL-10的比例失衡[48].IL-10被认为具有抗炎作用,因为它能够限制T细胞分化,防止辅助T细胞极化,突出了作为IBS特征的体内平衡失调.一项用脂多糖刺激外周血单核细胞的小型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IBS患者的单核细胞更成熟[49],IBS患者表达活化标志物的T细胞水平更高[50].结肠中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表达改变和粪便中抗菌β-防御素2水平升高的发现表明,微生物成分激活先天免疫系统也可能有助于疾病的发病机制,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患者受TLR激动剂刺激的全血样本中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6、IL-8和TNF)的过度释放支持了这一点.重要的是,结肠免疫细胞的荟萃分析突出了免疫细胞数量的区域和亚型特异性差异[51],支持IBS是一种不局限于结肠某一区域的疾病的概念.
IBS最一致的报道特征是小肠和结肠中肥大细胞数量增加[52,53].结肠类胰蛋白酶和组胺分泌的增加支持肥大细胞在IBS中的作用[54].此外,肥大细胞接近肠神经与IBS患者腹痛、内脏过敏、疲劳和共病抑郁的严重程度相关,表明这些细胞在IBS的病理生理学和心理负担中起着重要作用.
鉴于在IBS中发现肥大细胞增多,免疫激活的一个突出假设是抗原的概念,可能来自食物和/或微生物,刺激Th2型反应的诱导.在这种情况下,抗原通过抗原呈递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呈递给幼稚的T细胞,这些细胞驱动分化为活化的Th2细胞,以刺激B细胞产生免疫球蛋白E(IgE).随后IgE与肥大细胞结合并再次暴露于抗原,导致神经细胞附近的炎症介质脱颗粒和释放,从而导致炎症症状的出现[55].
基于患者外周TNF和IL-6增加的间接证据[56],也提出了IBS微炎症特征中Th17反应的可能性.Th17细胞与Treg保持平衡,以维持肠道免疫稳态[57];然而,Th17反应也可诱导炎症和自身免疫反应.一项研究表明,IBS-D患者的血清IL-17a和TNF水平显著升高,同时IL-10水平降低[58],这意味着该亚型的Th17/Treg轴发生改变.虽然对IBS中结肠免疫细胞的荟萃分析发现患者的总淋巴细胞群(CD3+)增加,可能是由于CD4+细胞增加所致[51],鉴于Th2和Th17免疫反应可能与肠腔抗原相关,IBS可能代表了对管腔抗原的适应性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在小肠和结肠上表现为异质性.
5.2 肠易激综合征与小肠免疫有关的证据 肠易激综合征中黏膜屏障完整性的降低可能促进管腔抗原的易位,以直接接触免疫系统,从而周期性地促进屏障的持续通透性.小肠和结肠屏障通透性的增加与内脏超敏相关[59],独立于疾病亚型,表明屏障完整性的丧失可能是IBS免疫系统启动的第一步.然而,一项研究确定了小肠通透性仅归因于IBS-D亚型,发现与对照组相比,IBS-C中小肠通透率的改变受混杂的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并且结肠通透性在使用多糖测试测量时没有变化[60].考虑到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与空肠肥大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之间的关联,失调的应激反应可能介导小肠IBS的免疫激活[61,62].
研究表明,IBS患者十二指肠和空肠的淋巴细胞负荷更大,而回肠的总淋巴细胞密度没有变化[63].与门诊对照组相比,确定了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上皮内淋巴(intraepithelial lymphocyte,IEL)亚临床增加和淋巴细胞浸润空肠肌间神经丛.鉴于肌间神经丛在收缩和运动协调中的作用,该部位的淋巴细胞浸润表明肠道系统特有的亚临床炎症,提出可能与患者的运动功能障碍有关[64].研究确定了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回肠肥大细胞增加,但未发现十二指肠或空肠肥大细胞增加.研究小肠IBS病理学的唯一人群研究之一确定了腹泻和便秘亚型十二指肠中的IEL(仅针对IBS-C)和肥大细胞增加.似乎免疫细胞群的改变是一部分患者的小肠特征.
6 IBS的抗炎治疗
近几年来对IBS病理生理机制的理解,如IBS低度炎症、胆汁酸代谢改变的作用、神经激素调节、免疫功能障碍、肠上皮屏障和分泌特性等,使IBS的治疗有一些新的进展.临床研究证据表明,低度肠道炎症在IBS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关键作用,IBS患者结肠黏膜固有层中的免疫细胞、巨噬细胞和肠内分泌细胞显著增加.这增加了肠道抗炎药可能有效治疗IBS的可能性[65].尽管如此,鉴于对发病机制的复杂,且尚不能完全了解,因此疗效仍不理想.下面就IBS的抗炎治疗的进展与现状进行探讨.
6.1 益生菌治疗 益生菌的抗炎治疗是当前共识的IBS有效治疗策略.婴儿胃肠道的早期定殖可能是后期肠道微生物群形成的关键决定因素[66].在健康成人中,益生菌可增加SCFA的产生、粪便水分、排便频率和粪便量.肠道内益生菌的酶活性可在这些益生菌生物效应中发挥作用.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表现出超过20种不同的酶活性,其中β-半乳糖苷酶活性是最典型的.肠道细菌β-葡萄糖醛酸酶将葡萄糖醛酸代谢物水解为肠道中的有毒形式,导致肠道损伤.此外,粪便中β-葡萄糖醛酸酶活性低与结肠腔中致癌物等物质的数量增加有关.
益生菌与肠腔中的胆汁酸相互作用,改变胆汁酸代谢,进而影响胆固醇吸收.胆汁盐水解酶(bile salt hydrolase,BSH)是一种酶,由与胃肠道相关的多属细菌和大多数已知益生菌产生;BSH从益生菌中酶解胆汁酸被认为是益生菌引起的低胆固醇效应的主要机制之一[67].
益生菌引起短链脂肪酸增加,结果使胰岛素敏感性增加导致脂质积蓄减少,脂肪分解降低,游离脂肪酸摄取增加,由于大脑饱胀感增加,改变了神经元兴奋性.此外一益生菌还可增加细胞粘附和产生粘蛋白的能力[65].
肠道微生物群通过产生具有免疫调节和抗炎功能的分子来调节免疫系统,这些分子能够刺激免疫细胞.这些免疫调节作用是由于益生菌与上皮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以及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相互作用所致[68].
益生菌的主要作用机制之一是调节宿主免疫反应.益生菌调节分泌型免疫球蛋白(secretory immunoglobulin A,sIgA)和细胞因子的产生.sIgA由肠B细胞分泌,并在肠上皮的基底外侧表面作为抗体转运体表达.sIgA促进IgA二聚体向上皮细胞腔表面的移位.几项研究报告表明[69],益生菌能有效刺激sIgA的产生,从而增强屏障功能.无论如何,益生菌与肠道和特异性免疫细胞相互作用,从而产生选定的细胞因子.因此,食用唾液酸杆菌CECT5713可增加健康成年志愿者中NK细胞和单核细胞的百分比以及免疫球蛋白M、A、G和IL-10的血浆浓度.此外,干酪乳杆菌增加了循环T细胞和NK细胞上CD69(一种Ⅱ型跨膜糖蛋白,属于C-型凝集素受体家族,也是NK细胞信号传导基因复合体家族的一员)活化标记物的表达,并在健康成人中诱导黏膜唾液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IgA1和IgA2浓度的增加[70].此外,施用短芽孢杆菌CNCM I-4035导致粪便sIgA含量显著增加;在用该菌株治疗的志愿者血清中,IL-4和IL-10的血浆浓度也升高,而IL-12的浓度降低.
益生菌混合物De Simone制剂诱导上皮细胞NF-κB.最近有研究表明,TNF-α可以刺激上皮细胞增殖,因此,益生菌可能通过上调TNF-α参与上皮屏障再生.许多选定种类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已被证明是具有抗炎特性的显著益生菌,通过增加IL-10和Th1型细胞因子的浓度来抑制促炎反应[71].益生菌能够通过下调TLR表达、分泌可能抑制TNF-α进入血单个核细胞的代谢物以及抑制肠细胞中NF-κB信号传导来抑制肠道炎症.不同的菌株,如短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和干酪乳杆菌在人和小鼠原代免疫细胞中诱导不同数量的细胞因子产生.因此,短双歧杆菌以TLR9依赖的方式诱导细胞因子的产生,而较低的炎症水平是由于TLR2的抑制作用所致[72].
已如前述益生菌与脑-肠轴的相互作用.肠道微生物群、脑-肠信号系统以及微生物群与遗传受体的相互作用已被证明与儿童的健康以及短期和长期行为的发展有关.肠道微生物群在生命最初几年的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有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可以影响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由生理或心理因素引起的压力可能与微生物群脑肠轴的失衡直接相关.最近,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分类器定量评估微生物群-大脑区域关联的强度,发现大脑结构的变化与肠道微生物群的饮食依赖性变化相关[73].
关于益生菌在减少过敏反应中的作用,潜在机制可能包括将淋巴细胞Th1/Th2平衡向Th1反应转移,从而减少Th2细胞因子(如IL-4、IL-5和IL-13)的分泌,以及降低IgE浓度和增加C反应蛋白和IgA的产生[74].
一般来说,肠道微生物群对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的机制是多因素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学),但这些影响被认为主要通过细菌代谢物的产生而发生[73].SCFA改变神经元的兴奋性,肠道细菌产生多种神经活性化合物,包括多巴胺、γ-氨基丁酸、组胺、乙酰胆碱和色氨酸,色氨酸是5-HT生物合成的前体.
总之,益生菌在IBS治疗中的应用仍需要调查和标准化.并非每种益生菌、益生菌及其组合都是每种IBS亚型的合适治疗模式,这也需要更详细的研究.尽管如此,在基于微生物操纵的治疗领域中,益生菌是缓解IBS患者症状的一个有希望的方向.
目前益生菌的种类繁多,世界各国应用的制剂也不尽相同,可根据当地资源合理选择使用.
6.2 抗生素 利福昔明是一种利福霉素衍生物,通过抑制细菌核糖核酸(RNA)的合成发挥作用.口服后几乎不被吸收,因此主要用于治疗胃肠道内的局部功能障碍.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最初批准利福昔明用于治疗由大肠杆菌引起的旅行者腹泻,并防止肝性脑病的复发.
随后,FDA批准利福昔明治疗IBS-D患者,剂量为550 mg,3/d,持续14天,以及症状复发的患者.利福昔明通过针对胃肠道的多种机制改善IBS症状.事实上,动物实验的大量证据表明,利福昔明改善或维持IBS中的微生物群多样性和细菌组成,减少肠道细胞因子炎症,提供肠道屏障保护,防止大肠菌群和病原体的附着和内化,减少上皮细胞炎症和病原体诱导的炎症反应,减少内脏痛觉过敏[75].
在对两个独立的3期试验的联合分析中,IBS-D患者每天三次服用550 mg利福昔明14天疗程,与安慰剂相比,治疗后10周内,IBS-D患者的整体症状缓解率显著提高,IBS相关的腹胀、腹痛、不适、稀便或水样便得到改善[76].
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包括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SIBO),可能在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机制中发挥作用.利福昔明能有效、安全地改善IBS症状.利福昔明治疗后,所有参与者的胃肠道症状亚区均有显著改善.此外,随着临床症状的改善,生活质量分数增加[77].
最近,Ghoshal等人[78]评估了有无SIBO的IBS患者接受诺氟沙星治疗后的症状缓解情况,以及与安慰剂相比,其在获得阴性SIBO试验结果方面的疗效.与安慰剂相比,服用诺氟沙星的SIBO患者在1个月时,症状更容易转为罗马Ⅲ阴性.没有SIBO且菌落计数为10 CFU/mL的患者比菌落计数小于10 CFU/mL的患者反应更好.
6.3 美沙拉秦 目前美沙拉嗪(Mesalazine)治疗IBS的疗效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美沙拉嗪是5-氨基水杨酸(5-Aminosalicylic acid,5-ASA)最常用的制剂,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已被证明影响白细胞趋化性、功能和上皮防御相关的多种介质和信号通路[79].先前的研究表明[80],IBS患者的肠黏膜含有更多的免疫细胞、细胞因子、免疫介质,它们代表免疫激活和黏膜损伤.因此,有人认为美沙拉秦可能通过发挥抗炎作用而对IBS有效.几项研究表明[81],美沙拉秦是减少肥大细胞浸润的有效且安全的方法,可以改善IBS患者的腹痛、腹泻、排便习惯和总体健康状况.但也有研究表明[82,83],美沙拉秦在减少肥大细胞数量和改善IBS患者症状方面没有明显作用.
临床研究证据表明[84,85],低度肠道炎症在IBS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关键作用,IBS患者结肠黏膜固有层中的免疫细胞、巨噬细胞和肠内分泌细胞显著增加.这增加了肠道抗炎药可能有效治疗IBS的可能性.美沙拉秦治疗降低了粪便细菌的丰度,并重新平衡了菌群的主要成分[86].一些研究显示[87],IBS时免疫细胞(尤其是肥大细胞和T淋巴细胞)数量增加,胃肠道不同部位释放组胺、细胞因子和蛋白酶等炎症介质.研究表明[88],美沙拉秦可以激活核受体,从而下调炎症过程并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此外,美沙拉秦可显著减少IBS患者肠黏膜中免疫细胞的数量,尤其是肥大细胞的数量.还有一些初步研究表明[89],美沙拉秦可以改变IBS患者的肠道菌群,并改善肠上皮的屏障功能.
新近Zhang等[90]病例荟萃分析,结果显示美沙拉秦在缓解腹痛、腹胀和肠易激综合征的临床症状方面并不优于安慰剂,与安慰剂相比,美沙拉秦没有减少每日排便次数和免疫细胞浸润以及改善粪便稠度的优势.由此可见今后需要大数据的临床研究,以便进一步评估其治疗价值.
6.4 皮质类固醇 在Dunlop等[91]进行的研究中,29名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接受了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口服泼尼松龙3周,30 mg/d.治疗前后直肠活检中评估了黏膜肠嗜铬细胞、T淋巴细胞和肥大细胞,并在每日日记中报告了肠道症状.在这项研究中,强的松或安慰剂治疗后,肠嗜铬细胞计数没有显著变化.虽然泼尼松龙治疗后固有层T淋巴细胞计数显著下降,而安慰剂治疗后无明显下降,但这与治疗相关的腹痛、腹泻、频率或紧急程度的显著改善无关.硫酸脱氢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 sulfate,DHEA-S)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而具有抗炎特性.DHEA-S可以改善应激诱导的内脏变化,DHEA-S通过γ-氨基丁酸A型(γ-Aminobutyric acid type A,GABAA)、NO、阿片类、中枢多巴胺D2和外周CRF2信号传导阻断应激诱导的内脏变化.认为DHEA-S可用于IBS的治疗[92,93].
此外,强的松、甲基强的松龙、氢化可的松、丙酸倍氯米松和布地奈德还可改善肠屏障功能.IBS时肠道微生物群耐受性受损,在这一过程中,肠屏障功能(intestinal barrier function,IBF)不足可能是关键因素[94].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在IBD中的应用不仅受到长期治疗中众所周知的副作用的限制,而且还受到25%-30%的患者对GCs无反应以及无法延长复发期的限制[95].
在基础条件下,GC似乎会降低渗透性并收紧细胞连接.因此,在肠上皮6(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6,IEC6)和IEC细胞中,氢化可的松(500 nM)增加了小带闭塞蛋白(zonula occludens-1,ZO-1)表达,相关的跨上皮电阻(transepithelial resistance,TEER)升高,这与细胞间结合更紧密、微绒毛形成、内质网重组、反高尔基复合体和细胞骨架网络一致[96].在Caco 2细胞中,另一种肠细胞模型,地塞米松(0.1 μM-10 μM)能够增加紧密连接蛋白-4(tight junctional protein claudin-4,CLDN4)的表达及其在细胞接触中的存在,同时,在基础条件下,它降低形成孔的紧密连接蛋白2(claudin-2)的表达和连接位置[97],从而促进屏障功能恢复.
由于皮质类固醇治疗的众多副作用,用药时应小心选择和观察,一般不作为首选药.
6.5 肥大细胞稳定剂治疗 近年的研究显示IBS日益被视为一种低度炎症性疾病,肥大细胞参与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机制.一方面,肠道内的局部微环境,包括共生细菌和产物、食物抗原、过敏原和毒素,在调节肥大细胞的活化和分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中枢应激,如心理痛苦和负性生活事件,也可能通过直接途径(外周神经支配)和间接途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肾上腺髓质轴)促进肥大细胞的激活和脱颗粒.另一方面,肥大细胞的激活参与IBS肠道的多种病理生理过程: (1)通过作用于紧密连接调节上皮通透性;(2)调节上皮水和离子转运;(3)调节血流和内皮功能,以及免疫调节、炎症和抵御微生物;(4)调节肠蠕动;和(5)通过神经免疫机制调节内脏传入和感觉功能[98,99].肥大细胞(mast cells,MCs)增生被认为是IBS患者的共同特征.许多研究集中于MCs浸润与IBS临床方面的关系.IBS的严重程度与结肠MCs计数和类胰蛋白酶的自发释放显著相关.靠近神经的MCs与腹痛/不适的严重程度和频率显著相关[100,101].
MCs被认为是肠道炎症回路启动和维持的关键角色.作为一种低度炎症状态,IBS患者的结肠黏膜免疫细胞计数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包括MCs、上皮内淋巴细胞和固有层淋巴细胞.MCs释放炎症介质导致肠道MC脱颗粒诱导小鼠肠道炎症浸润增加[102].
鉴于上述情况,IBS时采用MCs稳定剂治疗,主要通过稳定MCs的质膜来发挥治疗作用,用药后可显著改善D-IBS患者的腹痛和大便稠度.同样,酮替芬提高了IBS患者的直肠不适阈值,显著降低了腹痛的严重程度,并改善了生活质量[101].
靶向MC成熟、发育和归巢到肠道以及MC激活和主要介质的候选药物正在开发中,色甘酸二钠(disodium cromoglycate,DSCG)和酮替芬是两种经典的MC稳定剂,可用于IBS治疗,有利于改善IBS症状.初步临床数据表明,6个月的DSCG治疗显著减少了空肠活检中类胰蛋白酶的释放,并增加了D-IBS患者肠功能的临床改善[103].一项针对60名IBS患者的安慰剂对照试验表明,酮替芬治疗8周后,IBS患者内脏超敏反应的不适阈值明显增加,IBS症状减轻,并改善了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104].此外,包括黄酮类化合物在内的天然药物,如槲皮素和非西汀,已被证明对MC稳定有效,这可能是IBS的潜在选择[105].
人源化单克隆抗IgE抗体是一类新型MC稳定剂,可中和可溶性IgE,下调MC和嗜碱性粒细胞的高亲和力IgE受体(FcεRI)密度,使其对过敏原不敏感[105].其他靶向MC激活的药物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受体(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 receptor,CRF-R)和神经激肽受体拮抗剂,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IBS的创新治疗方法.α螺旋CRH9-41是一种非选择性CRF-R拮抗剂,可改善IBS患者的运动和知觉改变.多项研究还表明[106],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和蛋白酶激活受体2(protease activated receptor 2,PAR2)拮抗剂可以控制小鼠结肠的黏膜炎症并阻断亲伤害作用.因此,拮抗PAR2可能是IBS治疗的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手段.
肠易激综合征黏膜5-HT再摄取转运体的表达受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肥大细胞前列腺素E2调节.IBS-D患者粪便脂多糖与胰蛋白酶协同作用,刺激黏膜肥大细胞释放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从而下调黏膜5羟色胺转运体(serotonin transporter,SERT),导致黏膜5-HT增加.这可能导致IBS常见的腹泻和腹痛.给小鼠结肠内输注IBS患者粪便上清(fecal supernatant of IBS patients,IBS-D FS)可上调小鼠结肠5-HT水平,下调血清素再摄取转运蛋白(SERT)的表达,从而减少结肠转运,增加粪便含水量,并增加对结肠扩张的内脏运动反应.昂丹司琼阻止了这些变化[107].
6.6 多酚在IBS抗炎治疗中的应用 多酚被归类为一种有机化学物质,其酚类单元显示出一系列生物功能.人类体内的多酚可以通过上调各种内源性抗氧化剂来激活抗氧化系统,从而有效清除过量的自由基.此外,多酚可以作为一种天然金属螯合剂,抑制人体自由基的生成和脂质过氧化[108].此外,据报道,多酚除了具有抗氧化活性外,还具有一系列生物功能,包括抗炎、免疫调节、抗癌、抗糖尿病以及心脏保护、肾保护、神经保护和胃肠保护功能[109,110].然而,每种多酚的生物功能与它们的代谢(生物转化)、吸收(肠屏障)和生物利用率有关.
6.6.1 芦荟: 芦荟(芦荟科)是一种在传统医学中用于多种诊断的草药[111].胶乳和凝胶是从芦荟叶中提取的,富含多酚化合物,凝胶主要用于治疗IBS[112].芦荟的抗炎作用可通过降低肠道过敏性而对IBS症状有利.维拉通常被用作强泻药,改善胃肠动力[113].
临床试验的数据突出表明[111],在使用芦荟多酚提取物治疗前后,IBS症状评分有显著变化.随机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与安慰剂组相比,芦荟治疗组在改善IBS症状和生活质量得分方面有显著差异,但没有观察到异质性的迹象.结果表明,在1个月的短期治疗中,芦荟可显著改善IBS症状和生活质量评分.另一项荟萃分析报告[111,114],与安慰剂组相比,维拉芦荟组的有效率较高,研究之间没有异质性和不良事件.治疗1个月后,治疗组的生活质量IBS评分有所改善.
芦荟多酚还通过清除自由基和超氧化物自由基,以及通过抑制PGE2的产生、下调各种转录因子、抑制脂氧合酶和环氧化酶的活性,发挥抗氧化剂的作用,从而导致IBS症状的控制.此外,藜芦已显示出积极的抗菌活性,主要是通过破坏细菌细胞壁.芦荟对革兰氏阳性和阴性细菌都有活性.相反,据报道[115],芦荟汁的抗菌活性仅限于革兰氏阴性细菌.
芦荟的治疗作用主要是通过其清除自由基.植物化学研究表明,大部分芦荟多酚化合物属于非类黄酮多酚.叶凝胶提取物由酚酸/多酚、吲哚和生物碱组成;具有氧自由基吸收能力(oxygen radical absorbance capacity,ORAC)和铁还原抗氧化能力(ferric ion reducing antioxidant power,FRAP)分析证实的抗氧化性能,有助于改善IBS[116].
6.6.2 胡椒薄荷: 从薄荷(薄荷科)中分离出的薄荷油含有萜烯混合物,已被证明具有多种治疗作用.薄荷油和L-薄荷醇被认为是5HT3拮抗剂、平滑肌钙通道拮抗剂,可以减少钙的流入,也被认为是卡帕阿片类激动剂、抗感染剂和抗炎剂[117].临床研究将该油作为IBS的一种有吸引力的药物治疗候选,甚至优于抗痉挛药物三环抗抑郁剂.
口服187 mg(每日3至4粒)后,薄荷油对78%的患者的腹痛、腹胀、大便次数和稠度、腹痛和肠胃胀气有积极影响,明显优于安慰剂.在24小时时,薄荷油导致IBS症状总评分下降,显著高于安慰剂组[118].
薄荷油可逆转乙酰胆碱诱导的收缩,并通过钙通道阻滞拮抗5-HT诱导的收缩.据观察,薄荷醇通过阻断肌膜L型Ca2+通道的Ca2+内流,直接抑制收缩力,从而诱导人结肠平滑肌松弛[119].薄荷油也可能直接影响肠道神经系统.薄荷油(通过薄荷醇)可通过减少位于肠道中的瞬时受体电位阳离子通道(TRP通道)超家族的瞬时受体电位M型8(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M8,TRPM8)和/或瞬时受体电位阳离子通道A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A1,TRPA1)受体,减少IBS患者口服或腹腔内给药时的内脏疼痛.薄荷油的抗炎活性可预防二甲苯诱发的小鼠肠道炎症和醋酸诱发的大鼠结肠炎.薄荷油的抗炎作用可能至少部分通过TRPM8介导[120,121].
6.6.3 紫苏: 紫苏是一种富含多酚的植物.该植物含有多种酚类化合物,如酚酸、肉桂酸衍生物、类黄酮和木脂素.百里香草本提取物(Serpylli herba extract,SHE)由野生百里香(百里香属百里香科)上部分组成,最近,SHE引起了人们对IBS管理的极大兴趣,这可能是因为其在实验性结肠炎中表现出的肠道抗炎特性,以及其活性成分可以保护肠屏障完整性.
紫苏在IBS上的治疗作用,鼠的试验证明,SHE改善了疼痛和内脏过敏反应.此外,SHE通过下调促炎介质IL-1β、IL-6、IFN-γ、Tlr-4和诱导酶Cox-2的表达来增强免疫状态,从而诱导内脏镇痛,并通过上调粘蛋白Muc-2和Muc-3,SHE能够使两种粘蛋白的表达正常化,从而促进肠屏障功能的恢复.这些抗炎作用可能与它对肥大细胞的作用有关,因为它显著抑制大鼠嗜碱性细胞白血病细胞(RBL-2H3)细胞中β-己糖胺酶的产生[122].
紫苏提取物改善大鼠内脏高敏感性.SHE能够改善大脱氧胆酸引起的机械性躯体痛觉过敏和痛觉异常,其程度与加巴喷丁相同.紫苏减少IBS相关肠道炎症过程,与IBS对照大鼠相比,SHE给药后,IL-1β和Cox-2的表达显著降低,这可能会下调前列腺素的产生和分泌,可以改善痛觉过敏[123,124].
SHE削弱肥大细胞脱颗粒.SHE补充(25 μg/mL、50 μg/mL和100 μg/mL)显著抑制了C48/80诱导的肥大细胞β-己糖胺酶的产生和表达.这些结果揭示了SHE给药的高度相关和新颖的作用机制;其有益效果可归因于其抑制β-己糖胺酶释放并因此调节肥大细胞脱颗粒的能力[125].
总之,SHE改善了大鼠的免疫状态,降低了在内脏镇痛中起作用的促炎介质的表达,并修复了肠上皮屏障的完整性.SHE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IBS新治疗方法,因为它可以改善过敏反应、内脏痛觉过敏和炎症.这些有益的作用可能是由于肥大细胞脱颗粒和5-HT途径的抑制所致[122].
6.6.4 没食子酸: 没食子酸降低大鼠海马、脊髓和脊髓背根神经节(dorsal root ganglion of spinal cord,DRG)中嘌呤能离子通道型受体7和磷酸化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2的表达.此外,没食子酸治疗降低大鼠的血清IL-1β和TNF-α浓度,同时提高了IL-10水平.因此,没食子酸可能通过抑制海马、脊髓和DRG中嘌呤能离子通道型受体7(purinergic ligandgated ion channel 7 receptor,P2X7受体)的表达,成为治疗并发内脏疼痛和抑郁症的有效新候选药物[126].具有抗炎、抗氧化、抗抑郁和抗凋亡作用[127,128].然而,没食子酸是单独作用于P2X7受体还是作用于其他途径仍有待研究确定.此外,确切的分子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总之,研究表明P2X7受体可能是内脏疼痛和抑郁的有效靶点,没食子酸可以通过抑制海马、脊髓和DRG中P2X7的表达来减轻大鼠的内脏疼痛及抑郁行为.没食子酸的可能机制可能与抑制ERK1/2磷酸化和炎性细胞因子密切相关,值得进一步临床研究与应用[123].
6.6.5 反式白藜芦醇: 白藜芦醇具有抗氧化、抗炎和心脏保护特性.该化合物还通过靶向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和磷酸二酯酶(phosphodiesterase,PDEs)等多种分子显示出神经保护活性.有人认为,这种化合物可以通过增加海马中的BDNF蛋白水平,在各种动物模型中具有抗抑郁和抗焦虑作用[129].有证据表明[130],白藜芦醇通过对中枢神经和外周疾病的双重作用,保护肠屏障功能免受氧化应激.例如,白藜芦醇通过抑制负责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调节的cAMP降解磷酸二酯酶来改善精神和肠道功能障碍,因而具有抗抑郁和抗焦虑作用.
抗氧化和抗炎特性白藜芦醇还显示出抑制脂质过氧化物的生成,并可调节脂蛋白代谢.白藜芦醇参与增加抗炎免疫调节细胞因子IL-10.在另一项研究中,白藜芦醇改善了T细胞和B细胞的活性,导致PGE2和各种细胞因子如TNF-α、IL-1β、IL-6、IFN-γ和IL-12分泌减少[131].
白藜芦醇的抗炎活性主要归因于COX活性的抑制.白藜芦醇通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c-Jun(大鼠V-Jun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和JNK(大鼠C-Jun氨基末端激酶)途径抑制过氧化物酶抗过氧化物酶(peroxidase anti-peroxidase,PAP)和嘌呤能2受体(purinergic 2 receptor,P2受体)信号传导,从而干扰凝血酶的促炎信号传导,进而减少活化血小板腺苷核苷酸的分泌,降低中性粒细胞功能[132].
6.6.6 姜黄素: 姜黄素是姜黄的主要成分,从姜黄根茎中提取,传统上用作草药,具有抗炎、利胆、抗菌、抗癌和保肝等功效.姜黄素通过抑制COX-2和iNOS的表达而发挥抗氧化、神经保护和驱散作用,这对IBS等胃肠道功能紊乱有益.姜黄素促进了症状改善(即大便增多,排便次数减少,腹部疼痛和痉挛减少),并降低了IBS的患病率和评分,同时改善了IBS症状和生活质量评分[133].姜黄素显著上调IBS患者5-HT 1A的释放和再摄取,也增加了海马中BDNF蛋白的水平[134].与非应激载体组相比,姜黄素(20 mg/kg和40 mg/kg)的施用增加了粪便排出量.姜黄素(40 mg/kg)可抑制大鼠粪便排出量中的慢性-急性复合应激.
核因子-红细胞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Erythrocyte 2 related factor 2,Nrf2)-抗氧化介质反应通路的激活是细胞内防御氧化应激的重要机制.Nrf2参与控制与系统中活性氧化自由基的解毒和消除相关的蛋白质的基因表达.姜黄素显著抑制了氧化应激和ROS,部分原因是Nrf2诱导内源性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的表达.Nrf2参与控制与系统中活性氧化自由基的解毒和消除相关的蛋白质的基因表达[135].
7 结语
直至今日IBS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了,提出IBS是低度炎症疾病,拓宽了人们对IBS本质的认识.本文系统复习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和现状,列出了证据,总结了相应的治疗.今后应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有望在防治上有新的突破,为广大患者带来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