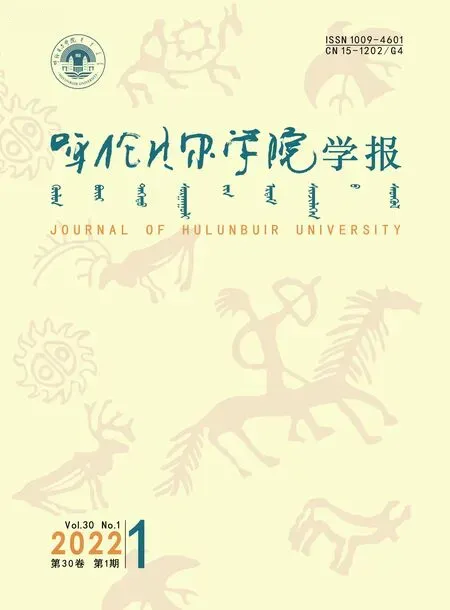《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文化的叙事与再现
余吉玲
(兰州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简称《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是中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关于鄂温克族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全书。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位90岁高龄的鄂温克妇女,也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抛开加注在她身上标签,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鄂温克女人,在追忆自己的一生,也在追忆鄂温克百年历史。故事以她的回忆为视角,以她讲故事的口吻展现鄂温克族近百年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婚姻家庭和社会文化变迁图景。从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鄂温克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更能直观地感受到发生在鄂温克族身上的变迁,以及鄂温克族从相对封闭的环境融进现当代文明旋涡中的那段历史。岁月流转、传统消逝,伤痛的不只是历经历史的老人,还有那些故事之外的人。对于无文字的鄂温克族来说,这部小说是文化遗产,是历史珍品,是了解自己祖先生活的一把钥匙,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记忆,而它开启的不只是尘封已久的过往,更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读者,我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都市文明的席卷下,人口较少民族生存发展的现实语境如何?他们有没有举族经历过社会转型、文化传统流失的阵痛?若是,他们又是如何调适与重构以保住民族发展的根基?读《右岸》之所以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与震撼,除了作者讲述的故事优美、语言充满诗性和文笔细腻之外,更重要的是激发我们以鄂温克民族为镜像反观自身文化的何去何从。
《右岸》通过对区域文化的历史性叙事,再现了使鹿部鄂温克族百年时空镜像下文化事项、生活场域、精神信仰以及民族心理一脉传承与顺从适应的变化,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鄂温克族的窗户,通过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的世界,透过温热的文字我们接触到了独特的文化。故事寄托着作者深深地故乡之情,故事中绚丽多彩的文化符号吸引我们走进鄂温克族。自《右岸》出版以来,对其文学价值的讨论持续不断。陈晓明认为,《右岸》“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消失的主题,倒是呼应了国际上由后殖民理论带来的文化反思,也表达了作者批判强势文明的后现代态度”[1]。刘中顼则认为,《右岸》是“以语言文字的建筑材料,为鄂温克原始狩猎文化树起了一座历史的纪念碑”[2]。鄂温克族作为一个跨国又地处边界的人口较少民族,其生产生活方式、历史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神话传说、文化传承、婚姻习惯法、生态旅游、生态移民以及教育发展改革等主题引起了学界的持续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右岸》中涉及到的文化事项,从人类学的角度做进一步的讨论。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根河市、阿荣旗、扎兰屯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省呼玛、逊克、黑河、嘉荫等县市。历史上鄂温克族有“通古斯”“索伦”“雅库特”三个族支。狩猎鄂温克人是我国鄂温克族中独具特色的一支,由于他们以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历史上被称为“使鹿部”。1957年,在征得本族人民同意的基础上,正式将族称统一为“鄂温克”。《右岸》讲述的就是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过着独具特色的放牧驯鹿和狩猎生活的鄂温克“使鹿部”。
一、《右岸》中鄂温克人的居住场域与文化
布厄迪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由无数个体所构成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在布厄迪看来,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场域是指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的环境。[3]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分布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鄂温克族,比较典型地保留了原始公社制。其居住是简陋的易于拆建的圆锥形帐篷——仙人柱,又称“撮罗子”。“仙人柱”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柱”的木架子,叫“仙人”;另一部分是木架上的遮盖物。
定居前,我国北方广袤的大兴安岭是鄂温克族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和进行文化创造的空间场域。以狩猎为生游牧在森林中的鄂温克族,其生活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森林、河流、白雪、驯鹿构成鄂温克族生活的图景。在特定的生存空间他们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符号,如“乌力楞”“撮罗子”“萨满”“风葬”“熊图腾”等,这些显性的文化符号同样是鄂温克传统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因子,承载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右岸》中,每一个鄂温克部落构成一个特定的场域,生活的场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形成独特的亲缘组织、部落社会形态和信仰精神。场域不是一个无限扩大的空间,它是以“关系”存在为前提的,这种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4]任何人的生产和生活空间都是以一定长度为半径划定的圆圈,即在一定的圆圈之内。在《右岸》中,鄂温克人世代过着采集狩猎与驯鹿饲养业的流动生活,所获的猎物平均分配。家庭、父系家族公社、部落迁徙的路线是他们生活的圆圈。鄂温克族后来从游猎到定居,再到后来的“生态移民”工程,生产生活场域的变化带了文化变迁。
鄂温克族是在俄罗斯境内曾被称为通古斯人,现定名为埃文克族、埃文人。作为一个跨国民族,鄂温克族的文化场域延伸至国与国之间的跨境交流互动。地域空间上的相连为鄂温克人在中俄两国间进行跨国贸易、跨国婚姻及文化传播等创造了条件。《右岸》中,中俄民间的交往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发生巨大的裂痕。俄国安达从俄国带来了很多文明的产物,用以交换鄂温克的兽皮、鹿茸;俄国安达罗林斯基对于鄂温克女孩列娜的爱纯洁美好;俄国姑娘被贩卖到中国为妓,鄂温克小伙伊万买下娜杰什卡娶为妻子,解救了一个将面临厄运的异国姑娘。
二、《右岸》中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关系
鄂温克猎民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他们长期以驯鹿为伴,居无定处、迁徙不断,游猎于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其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为“乌力楞”,是鄂温克族一种具有家族公社性质的生产集团,一般由五六个或十余个“柱”(即家或户)组成,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父系家族公社,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族长和公社的会议,人们通常会选举一个男子为族长,也就是酋长,称为“新玛玛楞”,族长管理公社的生产和生活,带领大家迁徙,分配狩猎任务,主持分配猎物,调节纠纷等,酋长参与劳动,无特权。社内遇有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重大问题,要通过由老年人组成的“乌力楞”会议来决定。
驯鹿俗称“四不像”,头似马而非马,角似鹿而非鹿,身似驴而非驴,蹄似牛而非牛,在鄂温克游猎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鄂温克族将其视为幸福、吉祥的象征。性情温顺的驯鹿在林海中可代替马匹的作用,帮主人搬家、驮运猎获物。在鄂温克人眼中驯鹿浑身是宝,皮毛可御寒,茸角、鹿筋、鹿心血是名贵的药材,香甜的鹿奶是鄂温克人主要的食物之一。严寒以及随时出没的野兽是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鄂温克族选择集体生活的客观原因。虽然如此,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生命是那样脆弱,死亡是那样的常见。主人公的父亲在经过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时被雷电击中身亡。她的丈夫拉吉达死于一场雪灾,尼浩(主人公的弟媳妇,女萨满)的女儿被大马蜂蜇死,儿子被洪水卷走……鄂温克人面对死亡时少有哭天抢地、声嘶力竭,仿佛悲伤在眼泪中转化为坦然或者是一种无可奈何。人死后,由萨满跳神舞祷告灵魂升天,其他族人饮酒食肉参与仪式,后将遗体悬挂于树枝上风化。这一风俗映射出鄂温克人的生命观,即从自然中获取衣食维持生命,死后将躯体奉献给自然。
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鄂温克族过着集体生活,实行平均分配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体融洽和谐,但是生活中的矛盾和小摩擦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避免。在鄂温克族的集体生活中,即使个别人之间出现矛盾,或者有那么一两个很不合群的人处处与大家作对,集体也不会抛弃、孤立或打击他。个体之间的嫉妒、仇恨和冲突不会摧毁和瓦解集体生活。小说中,伊芙琳就像是一个恶魔,对其他人的悲惨遭遇幸灾乐祸。马粪包酗酒,侮辱他人,故意破坏吃熊肉时的禁忌,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但当他被熊骨卡住喉咙时,大家齐心协力救活他,他才悔悟于先前的行为。这是集体的包容,是集体调解的功能,更是鄂温克人带给我们的温情与感动。
三、鄂温克族的宗教信仰
鄂温克族敬畏自然,相信自然界的万物中存在神灵,人的行为会引起神灵的喜怒,所以人要遵循种种禁忌,以防止神灵发怒给人类带来灾难。如鄂温克族崇敬火神,认为火中有神,不能往火里吐痰、洒水,不能朝火里扔不干净的东西。如《右岸》中写到,“矮个儿(汉人)……对着一棵大树滋了泡尿。他怎么能往大树身上撒尿呢!瓦加罗说,他一定是触犯了山神!坤德说,山神怪罪下来了,我看他肯定保不住命了!”
鄂温克族将熊作为图腾。“图腾”一词源于分布在北美的奥杰布韦(Ojibways)人,其大意为——“他是我的第一个亲戚”[5];“那是我一族之物”[6];彼之血族、种族或家庭[7]。由此可见,“图腾”通常被看作与氏族成员有着亲属(血缘)关系的象征物,它表征着氏族的血亲属性。[8]学者们对图腾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表达了各种观点。约翰·麦克伦南指出图腾崇拜具有原始宗教的性质。[9]涂尔干认为,“图腾就是相关民族中社会宗教的明显代表,它是共同体的体现,而共同体才是人们崇拜的真正对象”。[10]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图腾关系意味着物种的每个成员与图腾群体的每个成员之间都有图腾意义上的关系。一般而言,图腾群体的成员不能相互通婚”。[11]总体而言,上述观点是从宗教信仰、思维形式以及社会制度三个方面论述图腾。[12]汪立珍认为,狩猎生产与熊的生理特征是熊图腾神话产生的重要条件。鄂温克族对于庞大、凶猛又长着与人相似形体的熊,不得不产生一种惊奇、敬畏和崇拜的心理,从而产生与这种心理结构和特定社会条件相适应的神话世界观。[13]一方面崇拜熊如祖先,(鄂温克族称公熊为“合克”,是对曾祖父、外曾祖父的尊称;称母熊为“鄂我”,是对曾祖母,外曾祖母的称呼。)一方面猎熊杀熊。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人们用许多人为的萨满禁忌和祭祀仪式为猎熊开脱罪责[14]。如《右岸》提到的,猎人把猎熊,说成“我们去做客”,熊被打死了,说成“睡了”,猎熊的枪说成“吹火筒”,并要反复说是外氏族的人打死了熊。在吃熊肉时,吃肉的人都要先学乌鸦“嘎—嘎—”叫,表示乌鸦在吃熊肉。他们认为熊的灵魂在熊的大脑、心肝、食道、眼睛、肺等处,所以任何人不许吃。吃完肉后要把熊头和熊骨用桦树皮包好举行风葬仪式。鄂温克族为熊送葬时,边走边唱诵:“把您打死的不是我们,是俄罗斯人!把您吃尽的不是我们,是乌鸦群!发现您的尸骨并把它埋葬的那才是我们!”
鄂温克族信仰萨满教,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萨满。萨满主持结婚、丧葬仪式为本氏族消灾弭祸,祈求风调雨顺,牲畜兴旺。猎到黑熊或堪达罕时,萨满都会跳舞祭神祷告一番。萨满还肩负着以跳神的形式为人治病的重任。萨满教相信宇宙有三界说,认为人类生活在中层空间,上层有许多善神居住,下层是恶神和魔鬼的世界。许多人生病常常是因为病人的灵魂被带到了下层,萨满若是到下层将病人灵魂取回来,病人就会痊愈。萨满是人神魔沟通的媒介,他通过跳神舞、唱神歌、击神鼓,甚至服用致幻药物诱发自己进入到一种“迷魂”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的灵魂进入到神或魔鬼的空间,经过与神魔沟通互动,达到为本部落人治病、祈福及消除祸患的目的。《右岸》中的泥浩萨满每次跳神舞救活一个人,就要以牺牲自己的孩子为代价。即便是面临着巨大的丧子悲痛,她仍然会选择拯救他人的灵魂,在她心中这是一项神灵的职业,超越着世俗的悲痛与牵绊。
四、《右岸》中鄂温克族的婚恋观
婚姻家庭、亲属称谓制度向来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在没有接触小说和鄂温克族文化之前,普通人一般会想象鄂温克族婚姻的缔结,恋爱性爱会相对自由、松散。人们想象在一个流动性的氏族社会中,男女有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婚姻家庭建立在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少了来自父母、世俗礼教的束缚。《右岸》中,鄂温克族的婚姻大体上建立在男女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婚姻牢固不会轻易破裂,即使在夫妻双方关系不和睦、矛盾冲突不断的家庭中,都不会出现离婚、抛弃的现象。婚姻仿佛是一种终身的责任,忠贞是一种广泛认可的美德。相爱是建立家庭和夫妻关系和睦的前提。故事中主人公对丈夫的爱,依万对娜杰什卡的爱,哈谢对玛利亚的爱,达西对杰芙林娜的爱等等,都缠绵悱恻、刻骨铭心、忠贞不渝。依芙琳对丈夫坤德一生冷漠,只因她婚后才知道坤德曾经爱慕于一个蒙古族姑娘,后因坤德父亲不同意,坤德被迫与伊芙琳成婚。伊芙琳认为与不爱自己的男人同居是件极其恶心的事,而且处处挖苦、讽刺、打击坤德。即便如此,他们的婚姻延续到彼此终老都没散开。婚姻的不幸是造成伊芙琳变得偏执、古怪与不合群的主要原因。后来她执意要为自己的儿子订下一门她儿子不愿意的婚姻,将自己的儿子逼向了死亡。从坤德父亲对坤德婚姻的干涉、伊芙琳在自己儿子婚姻中的强势表现,以及玛利亚对儿媳杰芙林娜的百般刁难,丧偶一方要守孝三年才能再组建家庭等。可知,鄂温克族的婚姻并不完全是男女双方的事情。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作为新的成员进入另一个氏族,要得到其他氏族成员的接受与认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鄂温克族的婚姻会受到来自父母的影响与制约。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故事人物可以虚构,但是文化背景、民俗风情、民族心理不能虚构,艺术来源于现实的沃土。通过文学作品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鄂温克人的婚恋观、家庭组织、亲属称谓、社会伦理观和价值观等。
五、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
小说分为清晨、正午、黄昏和半个月亮四个部分,象征着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前两个部分的年代,正是祖国处于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在那个变革和动荡的年代,祖国领地不断沦陷,人民生命朝不保夕。
抗战时期、饥荒时期以及“文革”时期的大动荡都没有打破鄂温克族的与世隔绝。然而,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摆脱国家的统一领导而孤立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鄂温克族也不可避免的卷入了现代化的潮流中;另一方面,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开发开始后,林场、伐木工段越来越多,山中的动物越来越少,驯鹿所食的苔藓逐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使鄂温克人无法在林中生存。社会生活从流动实现定居,政府在定居点建立新的乡政府,选任乡长,代替过去的酋长。政府在定居点不仅为鄂温克族建造了房子,还建了学校、卫生院、粮店、商店和猎品收购站。人们走出深山老林,剪掉了长头发,从“山民”变成了村民,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份子。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碰撞、冲突、阵痛不可避免。在《右岸》中,鄂温克人面对生活方式的变迁很不适应,部分人因为不适应定居生活又进入林中。如小说所反映的“很多人因为驯鹿,对定居是有顾虑的。那个挂着听诊器的男医生在给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遇见了麻烦。他让男人解开胸口还比较顺利,让女人这样做,除了伊芙琳外,遭到了大家的抵制。两年以后,那些定居在激流乡的各个部落的人,果然因为驯鹿的原因,又像回归的候鸟一样,一批接着一批地回到山上......”还有鄂温克部落的第一个大学生,她在城市的时候觉得城市里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实在无聊。在城市不多久,她就会想念山里安静的生活。然而回到山中不多久,她又觉得山里太寂寞,嫌弃山里没有酒馆,没有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书店。她回不去传统又融不进现代,内心始终处于矛盾、孤独与彷徨的境地。这大概代表着处于转型时期大部分鄂温克年轻人的心理。传统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族为适应自然环境在内部发生的变迁是缓慢且容易被群体所接受的,外部文化嵌入一个民族,引起民族文化的变迁,难免会伴随冲突、矛盾,经过不断地调适才能被民族成员最终所接受。从林海中刚走出的山民,会遭遇文化的偏见,外界的有些人将生活在莽莽林海中的鄂温克人视为“吃生肉、穿兽皮”的“野人”。只有经过多方的努力,消除文化冲突、偏见和歧视,才会最终实现和谐共生。
费孝通先生认为,以文化界定的自觉指生活在某一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产生的“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方向,由此而加强自身在新时代、新环境下进行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费先生同时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与其他文化有所交流,取长补短,建立一个各抒所长,保持各自文化差异,但又可以和谐共处的原则。[15]传统与现代不是完全对立与相互博弈的关系,在二者交融互动的过程中,文化会由自觉走向自信。
结语
论文从鄂温克民族生存的场域、社会形态与社会关系、宗教信仰、婚恋观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碰撞交融五个方面论述《右岸》对鄂温克文化的叙事与再现。《右岸》叙事了鄂温克族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发展演变。“森林”“冰雪”“驯鹿”“仙人柱”“乌力楞”“熊图腾”构成鄂温克族最显性的文化符号。《右岸》对鄂温克文化符号的历史性叙事,向世人再现了无文字民族在百年时空镜像下其文化的传承与演变。民族文化符号承载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凝聚族群认同,彰显民族文化自信,它们是再现鄂温克族历史与文化的线索。正因为对自己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与坚守,即便是在现代都市文明的强有力冲击下,鄂温克族在调适与重构中保持了自身文化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