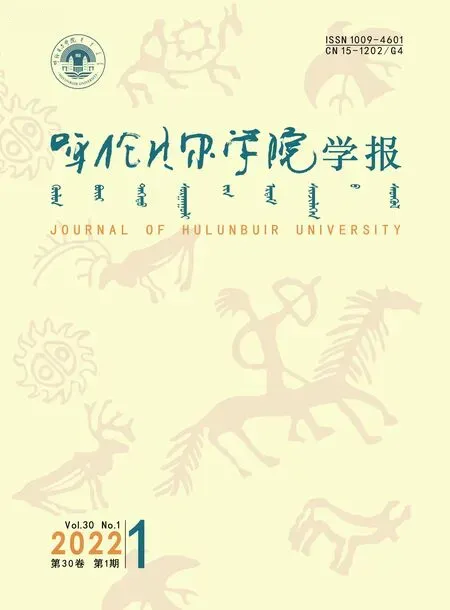宋辽金元狩猎赋用典研究
杨晶瑜
(呼伦贝尔学院 内蒙古 海拉尔 021008)
狩猎,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开始使用的向大自然索取动物类生活资料的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历代统治者往往通过大规模狩猎来检验军队的战斗力。赋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文学体裁,而狩猎则是赋体文学的重要题材,历代狩猎赋都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历史上兴起于内蒙古地区的辽、金、元这三大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阶级本就是以游牧与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他们在与两宋王朝对峙、交流的过程中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往往也在狩猎活动之中吟诗作赋。这些赋作中流传到现在的完整篇章多数符合赋体文学的整体特征,包括骈散兼行、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大量用典等。也有很多狩猎赋已经残缺甚至亡佚,我们只能通过仅存的只言片语甚至一个题目来管窥其文。
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这种修辞手法就是用典。[1]用典的形式可分为用事典和用语典,典故来源主要是儒家经典、神话传说,前人诗文作品等,用典方法包括明用、暗用、正用、反用等等。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给历朝历代文人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典故素材。本文对宋辽金元狩猎赋的用典情况进行研究,力图得知这个时期不同作者的艺术风格、思想倾向以及时政对作者创作的客观影响等等。宋辽金元时期的狩猎赋创作活动跟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密切,对此进行用典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认清历史,了解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社会和谐。
一、宋代狩猎赋用典情况
宋代文学兴盛,散文大家往往也是辞赋大家,多有赋作传世。田锡存赋24篇,王禹偁存赋27篇,宋祁存赋45篇,范仲淹存赋38篇,文彦博存赋20篇,[2]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赤壁赋》更是天下闻名。马积高先生主编之《历代辞赋总汇》收录宋代辞赋作家347人,辞赋作品计1445篇。宋代的文学赋以颂德、咏物、说理、抒情为主,惟狩猎题材的赋作只有丁谓《大蒐赋》一篇流传下来。此篇延续了汉赋之传统题材,沿袭古赋的形式,内容上则与宋代文赋一样更加注重议论,其用典情况当可做宋代狩猎赋之代表。
《大蒐赋》正文第一句“仲冬,天子严祀事,答神佑,伫农隙,谨蒐狩”一句典出《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3]开篇即指出天子举行大规模狩猎的时间,是在冬季农闲之时,用典故来说明这是古已有之的礼法制度,而非放纵扰民之举。
后文中“麋鹿狼狈以投林”看似简单的情景描写,其实也是用典。典故出自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4]丁谓在这里化用原文语义,既描写了麋鹿在猎人的追捕下狼狈逃窜的情景,又暗示了猎手的技艺高超,麋鹿终究逃脱不了被捉住送进厨房的命运。
“始建旗以誓众,亦斩牲而戒失。”出自《周礼·夏官司马》“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5]原文中“陈”通“阵”,各位官吏在军阵之前听大司马的训诫,杀牲示众,以免军吏不听命令而有所失。作者在叙述天子大蒐前的程序时用这个典故来进一步证明天子的狩猎活动合乎礼制。
“外事尚刚,戊日惟吉”典出《诗经·小雅·吉日》“吉日维戊,既伯既祷。”《吉日》是典型的狩猎诗,主要内容是对周王的狩猎活动加以歌颂。丁谓写作此赋时皇帝未必真就是选择在戊日出猎,这里用典主要是为了暗示当朝天子像周朝的先贤一样圣明,这种用类比来对天子进行阿谀奉承的手段在历代文学作品中都屡见不鲜。例如唐代李程应试时所作的《日五色赋》结尾句“故曰惟天为大,吾君是则”,就是化用《论语》中孔子推崇尧帝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原文意思是只有上天是最伟大的,只有尧帝能效法上天。李程用此典暗示当朝皇帝的圣德可与尧帝比肩,无怪乎主考官大为赏识,擢为状元。
“弓斯张而矢斯挟”依然是化用了《诗经·小雅·吉日》中的句子,原文为“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再后面的“射必三兽,发则五豝”则是出自《诗经·召南·驺虞》中的“彼茁者葭,壹发五豝”,意思是射出一支箭就射中了五头野猪,用这种夸张的说法来渲染猎手的高超射艺。
“鼓以三阕,围不四合”和“罗氏设商汤之网拥群”则是运用了商汤“开三面网”的典故。典出《史记·殷本纪》:“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6]作者用此典故来歌颂天子不滥开杀戒的仁德之心。
“肉堕庖丁之刀,血溅鲁阳之戈。”此句分别用了“庖丁解牛”和“鲁阳挥戈”的典故,表现出厨师的技巧和战士的勇武,当然能够驱使如此能人勇士为之服务的天子自然更是雄才大略。
“庙献禽而神其享哉!”反用《左传》中宫之奇向虞公进谏时所说的“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原文意思是如果国君没有德行,百姓就不和睦,神灵就不会保佑这个国君。这里反其意而用之,当朝天子在宗庙里进献祭品,神灵会来享用,侧面说明天子是明德之君。
“如是则不曰暴天物,不曰教民战。”也是分用两个典故。前半句典出《礼记·王制》:“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原文意思是如果不按礼制进行狩猎,即为暴殄天物。后半句典出《论语·子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学者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分歧颇多,基本可以解释为用没有教化的百姓作战,这叫做放弃他们。孔子一向讲究礼,从本赋对天子狩猎过程的描述来看,显然是合乎礼制的。
“借如汉武……以至欺猛狂而手格,喜暴恶以力争。”用了汉武帝徒手格杀猛兽的典故,抑古以扬今。出自《汉书·东方朔传》:“(汉武帝)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秔之地。民皆号呼骂詈”。汉武帝自恃勇武,行为狂悖,驰猎扰民,天下愁苦,不合于礼,以致晚年颁下《罪己诏》,这对当朝天子也有一定的讽谏警示作用。
“是以发狂之心,无自入焉”所用典故出自老子《道德经》:“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和《礼记·玉藻》:“非辟之心,无自入也。”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反对大肆张扬的驰骋田猎活动,认为那会使人心里发狂。而当朝天子则“措虑寂尔,存神泊然”,自然不会产生邪恶的非辟之心。
二、辽金两代狩猎赋用典情况
辽代疆域一直局限于塞北,未能真正的入主中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极少,赋体文学的创作相对也少得多。《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之后即为金元卷,辽代辞赋仅列于金代辞赋之前而未体现在卷名中。所收篇目也只有辽道宗萧后的《绝命词》和辽天祚帝文妃的《讽谏歌》,并无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赋。但这并不意味着辽无赋。据《辽史》记载,“九月癸巳,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7]这样我们起码知道辽代冯立和赵徽都作有狩猎赋。还有“(刘)三嘏献圣宗《一矢毙双鹿赋》,上嘉其赡丽。”[8]这几篇狩猎赋今均不存,无从得知其内容的用典情况。单从题目来看,为什么辽兴宗猎获三十六头熊要特意命人作赋以颂之呢?恐怕不只是宣扬武力,更可能的是暗用周文王出猎时在渭水之滨遇到姜尚的典故,认为这是将得贤臣的预兆。这个典故在历代狩猎赋中曾多次出现,唐代可频瑜《畋获非熊赋》题目即用此典。另有李白《大猎赋》:“获天宝于陈仓,载非熊于渭滨。”元代朱德润《雪猎赋》:“盖将息牧野之如虎如貔,获渭滨之非罴非熊。”清代陈沆《南苑春蒐赋》:“观置兔而喜得闳夭,卜非熊而思迎渭叟。”都是此意。
金代统治者积极支持和提倡学习中原文化,反映了他们对中原先进文化的仰慕和认同中原文化的价值取向,他们重视宗室子弟汉文化的教育。这种价值取向和种种教育举措最终使得整个金代宗室群体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涌现出了一大批在文学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文学家、史学家。[9]赵秉文和元好问为其中翘楚,均有赋作传世。在《金史》中有两则提及狩猎赋的记载:“熈宗猎于海岛,三日之间,亲射五虎获之。(完颜)勖献《东狩射虎赋》,上悦,赐以佩刀、玉带、良马。”[10]“施宜生……试《一日获熊三十六赋》擢第一,其后竟如僧言。”[11]然未收录赋中文句。查南宋岳珂所作《桯史》,则记录了其中一句。“逆亮时有意南牧,校猎国中,一日而获熊三十六,廷试多士,遂以命题,盖用唐体。宜生奏赋曰:‘圣天子,讲武功,云屯八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亮览而喜,擢为第一。”[12]但此句是否为施赋原文并不确切,在南宋陈鹄《耆旧续闻》中记载“(施宜生)举进士,廷试《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赋》,云:‘圣天子内敷文德,外扬武功,云屯一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13]《耆旧续闻》所记文句更符合赋体文学中语句格式的“四六”倾向,且《金史·完颜亮传》中提到了十三次狩猎活动,却并无获三十六熊的记载,则《桯史》所述未必为真。此次廷试的赋题很可能取材于辽兴宗在黄花山猎获三十六头熊的故事,亦为暗用非熊之典。
三、元代狩猎赋用典情况
元代与辽金两代虽然同样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其真正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元代政府科举取士依旧试赋,使得天下知识分子将大量精力投入在作赋之中。元仁宗制定科举考试的政策时,明确反对传统大赋所擅长的铺采摛文的表现手法。“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14]故此以铺排夸张为特色的狩猎题材并未出现在已知的元代科举试题中,便得不到文人的重视。流传至今的元代狩猎赋仅有朱德润《雪猎赋》一篇而已。
元代赋家多以“祖骚宗汉”为宗旨,朱德润也不例外。《雪猎赋》就模仿了汉大赋的结构和修辞手法,甚至好多典故都是前人赋作中反复出现过的,下文着重分析《雪猎赋》中这些模仿前人的用典情况。
本赋的序言中“干豆、宾客、充庖,三田之义”之句已经用典,此属正用语典,出自《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郑玄有注:“干豆,谓腊之以为祭祀豆实也。”[15]指出天子每年三次狩猎并非为了个人享乐,而是要将所得猎物分成三部分,分别用于祭祀、宴请宾客和充君之庖厨。历代狩猎赋中最早使用此典故的当为汉代扬雄的《羽猎赋》:“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长杨赋》:“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干豆之事,岂为民乎哉!”晋代成公绥《射兔赋》:“盈得获于后乘,充庖厨之所贡。”唐代常衮《春蒐赋》:“六军之节制可观,三畋之礼文斯得。”路季登《皇帝东狩一箭射双兔赋》:“或备鲜于干豆,或荐芬于祖宗。”可频瑜的《畋获非熊赋》中提到“十旬失位,悲夫洛汭之歌;三品充庖,讵比渭滨之叟。”均为此例。
在列举将士们所用兵器时,有这样的神兵利器“乌号繁弱,莫邪干将”。干将、莫邪作为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名剑,为读者所熟知,而乌号和繁弱则都是古代的良弓。在西汉枚乘的《七发》里关于狩猎活动情景的描述就有此典:“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雕弓。”司马相如《子虚赋》:“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完全沿用《七发》里的句子,只是换了顺序而已。《上林赋》“弯蕃弱,满白羽”一句中的蕃弱即繁弱。北朝庾信的《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有:“繁弱振地,铁骊蹋空。”初唐王粲《羽猎赋》仅剩残篇,保留下来的部分正好也有此典故:“相公乃乘轻轩,驾四骆,驸流星,属繁弱。”李白《大猎赋》:“集赤羽兮照日,张乌号兮满月。”这些都成为了朱德润写作时的参照对象。
朱氏在描写狩猎场面时大量用典,其中“纵离朱之明睫,步章亥之宏跧。”用了三个人的两个典故。离朱是传说中视力极好的人,也称离娄,能察针末于百步之外,曾帮助黄帝寻找玄珠。章亥则为大章和竖亥这两个善走之人的合称,曾受大禹之命步行丈量大地东西南北的距离。作者选用这两个典故是为了吹捧当朝天子,暗指其就像能驱使这些能人异士的黄帝和大禹一样伟大。扬雄《长杨赋》:“且盲者不见咫尺,而离娄烛千里之隅。”唐代陆贽《圣人苑中射落飞雁赋》:“固离娄之明眸,其才能觌。”李白《大猎赋》:“大章按步以来往,夸父振策而奔走。”都是同样的用法,显然也为朱氏所借鉴。
还有明用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的语典“讲春蒐秋狝之举,临夏苗冬狩之期”、出自《史记》的事典“效成汤祝网之三面,思文王蒐田之以时”、反用《诗经》语典的“士弓矢胡未张”等等。由于篇幅限制,笔者在这里不一一列举,读者自可细读原文,自行判断分析,也是一大乐趣。
综上所述,宋代狩猎赋用语典和用事典的频次几乎相当,典故来源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用典方法不一。辽金两代狩猎赋存世太少,题目即用典。元代狩猎赋中的典故前人惯用者极多,赋体文学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后继乏力,可见一斑。而利用各种典故来为天子歌功颂德的主旨则为历代狩猎赋所共有,这在治世可以成为加官进爵的青云之梯,于乱世则可粉饰太平,都体现了作者的学识及其政治倾向。